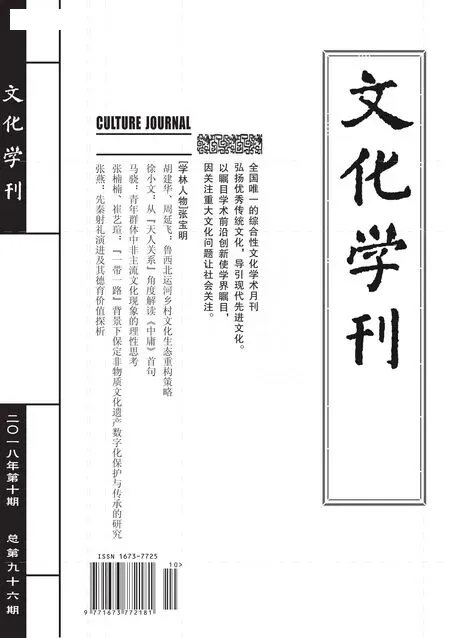陶成章的新史学思想
王莉楠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陶堰西上塘村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家。目前,学界关于陶成章的研究都是与革命相关的,几乎没有对其史学的研究,殊不知他在革命时期以史学为革命武器,客观上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陶成章家境贫寒,六岁入义学,十五岁担任塾师。十八岁时,甲午战争爆发,清军的惨败使他有了从军之心。1895年,陶成章在维新思潮下开始接触新学,虽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但新学对其触动很大。不幸的是,不到三年时间,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运动宣告结束,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接着,义和团运动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强,陶成章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1902年,陶成章赴日学习,对西学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改变,再加上“新史学”[注]1901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2年继而发表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由此爆发。“新史学”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西方史学,经日本传入中国。“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主张以民统代君统、为生人不为死人,强调历史的公理公例、因果关系,力求史籍整全、史料完备,并提倡利用其他学科做研究和将比较法、统计法应用于史学等。的影响,他决定以史学为革命武器,并于1904年写成《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目的在于唤醒沉睡的国人来参加战斗。根据《总目》,此书应有卷之上三章,卷之中一章,卷之下三章,以及卷下续一章,共八章,但原书只有卷上,即“邃古时代”和“太古时代”两章,写到夏朝以前。即便如此,亦可从书中发掘出作者的新史学思想。
一、史家叙事应专叙民族盛衰之原因
1902年,梁启超于《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直指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传统史家作史把君主作为绝对的叙事主体,传统史学叙事主要以王朝治乱兴衰为主,所以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传统史书多见于列传、本纪,多叙王侯将相等“人格者”的历史事迹,而对于群体的论述寥寥无几。以上两点皆批评传统史学在叙述对象上的弊病,认为叙述对象过于狭窄。
对此,陶成章指出:“我国无历史焉,并无所谓记述耳,并无所谓记述焉,仅有一家一姓之谱谍帐簿耳。洪水泛滥,祸烈猛兽,探抉所弊,有二大因也,一则视祖国为一家之私物,于是革一朝,则盛述本朝之谱谍,散理前朝之账目,著成一史,再革一朝,则又盛述本朝之谱谍,散理前朝之账目,又著成一史。陈陈相因,而统族祖先之发迹,反不得而详。”[1]进而指出:“中国历史者,汉族统治之历史,而非一人之家谱。故叙事专叙民族盛衰之原因,而于一人之事,多从略焉。”[2]“叙事专叙民族盛衰之原因”的目的在于使国人了解民族的发展状况,从而激发其民族爱国主义,来挽救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中国权力消长史》从民族角度出发叙述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因时势之变更为时代,以各个时期中国民族及相关民族的盛衰状况和中国民族与相关民族的关系为线索,厘定为三大部:葱隆之部、开展之部、衰落之部。三大部中别为六时代:邃古时代、太古时代、中古时代、近古时代、近世时代、近今时代,每时代中就形势之稍有变易者,小别之为期,如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等,全书统计凡分五十四小期。
二、重视因果关系的探讨
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的第四大弊端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理想”即史之精神,“史之精神”谓何?即因果关系。“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3]简言之,传统史学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景象。为革除这种弊端,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后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公理公例”改为“因果关系”。
陶成章同样重视因果关系,“天下无无因之果,亦断无无果之因,人类之创建邦国,人类进化成立之大果也。”[4]“夫有其果,必有造其因者夷。”[5]洪水泛滥,祸烈猛兽,探抉所弊的另一原因即“不悟原人进化之公理”,故其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旨在通过叙述中国民族盛衰史探析中国民族盛衰的原因,以供现代国人资鉴。
三、强调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
“读中国史,不可不知中国之地理。”[6]陶成章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之一大要素,古今地理沿革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他指出地理环境对历史有极大的作用。“原人立国,非借天然之地理,不足以启发文化,故世界文明最初之发生多在温暖炎热地区,如印度、埃及之事可证。盖文明麹蘖,不依暖热之空气,则到底不能发酵者。夷考吾族太古时期,文明发生,滥觞自黄河。夫黄河南北,沃野千里,便于农业,固易为文明发易之区。然试以黄河与长江比例之,则二者又熟适培养文明者乎?彼黄河之水,常泥浊而不清,且有溃决之虑,若江水则反是,除上流有峻端之区,其余大致千里一碧,无泛滥之忧,由地理以推人类进化,则苗族开花之早于吾族也,又从可知。”[7]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皆仰赖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如温暖的气候、充足的水源、肥沃的土壤等。再者,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文明,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发达程度亦取决于地理环境的优劣。这也正是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第四节“地势”中提到的地理与历史的关系:“高原适于牧业,平原适于农业,海滨、河渠适于商业。寒带之民擅长战争,温带之民,能生文明。凡此皆地理历史之公例也。”[8]虽表述不同,但所表达之精神相同。
四、主张利用其他学科进行研究
梁启超“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9],他批评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10]要知地理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及经济学都与史学有直接的关系,其他的诸如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文学、物质学、化学及生理学,也都和史学有间接的关系。梁启超主张利用各种学科的学理解析历史,尤其是“群学公例”、地缘学说、经济学原理及社会学者眼光。
陶成章也深刻地领会到了新史学的这层含义,他尤其注重借用社会学、考古学进行历史研究。在说明原人文明程度由渐而进时,他利用社会学、人类学中原人进化所经历的各时代以资考证:原人进化,由居住者可分为五代,即穴居时代、巢居时代、宫室时代、城郭时代、铁道时代;原人进化,由器用者可分三代,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原人进化,由生存要素者可分六代,即渔猎时代、游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商务时代、工艺时代;原人进化由文化者可分四代,即结绳时代、绘画时代、书契时代、历史时代。在考证中国民族迁徙时,他利用古籍,如《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等书中的相关表述来证明中国民族由西亚迁入,但最后他指出“此不过臆断之词耳”,即要想确其无误,还需要靠地质学的发明即地层中之遗物发现来保证,这也正是考证学派王国维主张的“二重证据法”的精神所在。
五、重视神话的史料价值
以往的史学家认为神话是非理性的象征,是不可信的,所以在史学编撰过程中不把神话纳入史料范围。而陶成章认为:“神话者,原始人类进化之一大阶级,而历史学家之阶梯也。是故欲明历史不可不先明神话,欲明上古时代之历史,尤不可不先就神话中之所有而推阐之。”[11]他强调神话的重要性,认为通过神话故事可以推演历史,因为“夫神话者,代表一国民之思想者也,其一国民对于古代,有如何之思想,即知其有如何之智识,于后代文化即有如何之进步。”[12]神话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心理和思想的反应,通过神话可推测当时的国民素质,从而推测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这有益于历史研究。
新史学“尚全”之要义,一是力求史籍整全,二便是要求史料完备。梁启超认为除史部文献以外,诗词歌赋、小说、“寻常百姓家故纸堆”皆有史料价值。此外,“文字记录以外”的实迹也在他关注的范围,且对于采访所得的资料更是相当重视。如此说来,神话更应纳入史料研究范围。
六、世界史观
《中国历史研究法》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13]换句话说,历史应当记述全人类的事业。而传统史学:“高自位置,不悟原人进化之公理,不识寰宇之广大,逞一孔之见,而因以为天下惟有地,地之上惟有中国,中国之外无人类也。”[14]陶成章批评传统史学只叙国事,而于国外史事一概不予说明,其倡导世界史观,于《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可见一斑。
附《太古西亚人种盛衰记略》中,陶成章介绍了太古时期西亚哈米人、塞米人、思米尔人、阿加逖人、亚述人、非尼基人及希伯来人等盛衰的历史及迁徙的路径。书中对于日耳曼民族、英吉利民族、美利坚民族、拉丁系派、法兰西族及意大利族也有一定篇幅的介绍。更值得注意的是,陶成章运用与中国文化比较的方法,将太古时期西亚的文化呈现出来,包括西亚太古时期的学术与技术、制度及信仰、文字及文学。还有通过与东洋文明做比较来介绍西洋文明,通过与中国神话做比较来介绍希腊、埃及、印度之神话等,此类事例不在少数。由此亦可见,陶成章还特别重视文化,他说:“读中国史,当知中国之人文。”[15]他认为中国文化发达,且影响深远,如中国的文字、佛教、医学、历学、数学、音乐及四大发明等诸多文化特质。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并沉淀下来的重要遗产,对民族和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史家著史应当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作为陶成章革命的思想武器,不是一本纯粹的史学著作,所以书中有不少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同时,受“中国文化外来说”的影响,陶成章认为中国民族是由西亚迁入的,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更应该看到作者在此书中表现出来的先进的、科学的一面,尤其是作者在史学上的认识,客观上推动了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