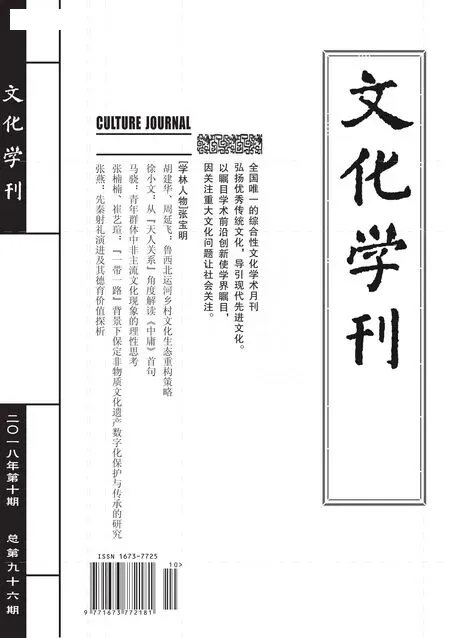东晋南朝血亲复仇案件中孝与法的冲突及解决方式
——以南齐朱谦之案为例
阚可心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 洛杉矶 90024)
血亲复仇现象由来已久。吕思勉先生说:“血亲复仇,初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1]先秦时期复仇盛行,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严禁私斗,然而秦末农民战争被认为是“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2],可见社会上复仇思想依旧根深蒂固。汉代血亲复仇虽应受到法律制裁,但在事实上蔚然成风。黄初四年(223),魏文帝下诏“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3],然而民间复仇风气依然盛行。后《魏律》又将禁令放松为“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4]。
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血亲复仇案件是儒家孝治和国法冲突最为显著的表现。东晋南朝虽偏安江左,但法律制度在西晋《泰始律》基础上删定改易得到了发展,同时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原政权的礼乐制度,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复仇案件已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控制,同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朱谦之案是其中一起典型的亲属间连环复仇案件,史载较为完整,案情较为复杂,讨论意见与处理结果也较具代表性。本文以此案为例,兼及东晋南朝其他复仇类案件,探究这一时期对待孝与法冲突的态度及解决方式,并就其体现出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局限进行初步讨论。
一、朱谦之案的复仇特征
朱谦之案发生于南齐永明年间。朱谦之幼时生母去世,其父临时将其生母遗体安葬在田边,被族人朱幼方放火烧毁。朱谦之虽小而“哀戚如持丧”,长大后杀朱幼方复仇并自首。此案上报到朝廷并引发了一场讨论,最终齐武帝免其死罪,并遣朱谦之移乡避仇以终止相互报复。但在朱谦之临行前,朱幼方之子朱恽伺机刺杀朱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杀朱恽,齐武帝认为“此皆是义事,不可问”,将其一概赦免。[5]
朱谦之案反映出东晋南朝血亲复仇案件的若干典型特征。第一,这一时期人们对孝道的伸张依然极端重视,复仇手段往往过当,但依然被看作义举。在本案中,朱谦之之所以与朱幼方结仇,并非因为其有所杀伤,而是因为其放火烧毁了朱谦之之母的遗体。朱谦之之母“假葬”田边,朱幼方“燎火”焚毁,即很可能因放火烧田而无意间延烧至葬地,因此,非出故意,但朱谦之依旧将其等同于杀母仇人并手刃朱幼方。在南朝宋时,垣阆之母墓被僧人昙落等盗发,垣阆与其弟杀昙落等五人[6],也是将冒犯先人庐墓者等同于杀伤其先人。东晋南朝时期,复仇手段过当的情形亦屡见不鲜。东晋沈充被故将吴儒诱杀,沈充之子沈劲后灭吴氏满门[7];沈林子之父沈穆夫参与孙恩之难,被族人沈预告发,沈林子与兄沈田子杀沈预,男女无长幼悉屠之[8];南朝梁成景隽之父为常邕和所杀,成景隽购人刺杀常邕和,后又购人杀其子弟[9]。
第二,父债子偿、冤冤相报情形依然普遍。本案中,朱谦之杀朱幼方,幼方子恽又杀朱谦之,谦之兄选之又杀恽,造成同族相残的悲剧。东晋谯王司马承为荆州刺史王暠所杀,其子司马无忌欲杀王暠之子王耆之复仇[10];桓温父桓彝为韩晃、江播等所害,桓温杀江播之子江彪等三人[11]。从上述复仇手段和复仇持续世代的角度看,东晋南朝时期的复仇特征仍与前代有较强的承继性。
第三,这一时期复仇者自首意识比前代更强烈,法律对复仇案件的介入更为频繁。本案中,朱谦之复仇后即“诣狱自系”,国法此时即介入本案的处理,尽管处理结果仍以宽宥告终,但从县令报告上级、州郡官员讨论,到皇帝做出最终决定,复仇者自始至终都未逃出法律控制范畴。东晋以来,复仇者自首的情形屡见史载,刁彝之父刁协在王敦之乱中为人所杀,后刁彝斩仇人党,以首祭父墓,诣廷尉请罪[12];王谈父为窦度所杀,王谈杀窦度,归罪有司[13];宋钱延庆之父为奚庆思所害,钱延庆杀奚庆思,自系县狱[14];齐李庆绪父为人所害,李庆绪于部伍手刃仇人,自缚归罪[15];梁张景仁父为韦法所杀,张景仁杀韦法,以首祭其父墓,诣郡自缚,乞依刑法[16]。相比于汉代复仇泛滥、法不能制的状况,这一时期法律对复仇的约束力有所加强。
第四,东晋南朝时期的复仇案件皆以宽宥告终,法律服务于儒家孝治并居于次要地位。在朱谦之案中,不论是州郡官员意见,还是齐武帝的最终决定,都反映出在复仇者投案自首、法律权威得到肯定与尊重的前提下,法律的执行服务于孝道的弘扬这一基本取向。在前述自首案件中,所有自首者均得到赦免,乃至获得嘉奖。复仇者甚至会因此获得任用,宋宗越父为蛮人所杀,宗越于市中刺杀之,太守嘉其义,擢为队主[17];齐闻人敻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位至长水校尉[18];淳于诞之父于为群盗所害,淳于诞结客以报父仇,益州刺史召为主簿[19]。
朱谦之案亦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法律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调与尊重,但依然时常被凌驾与无视。在法律已经介入,皇帝处理决定已经下达的情况下,连环复仇发生在移乡避仇的执行中,已是完全置国法于不顾。这与对朱谦之本人的处理存在不同之处,朱谦之有自首情形,因此,经过孔稚珪等人的论证,认为赦免朱谦之既符合孝道,也不算屈法。而对于朱恽、朱选之的相互报复,齐武帝不问国法是否得到尊重而一概加以赦免,体现出这一时期法律时常出现缺位的局限性。
二、复仇案件中孝与法的冲突
(一)血亲复仇为弘孝思想所提倡
血亲复仇案件集中体现了儒家孝治和国家法度的冲突。儒家弘扬孝道,复仇思想自先秦以降,即为儒家经典所接纳乃至提倡。《春秋公羊传》云“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为父复仇与为君复仇为儒家家国同构思想的一体两面。东晋南朝尽管玄风炽盛,佛教长兴,而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统治思想的主流。这一时期统治者尤重《孝经》,西晋泰始七年(271)皇太子讲《孝经》,东晋永和十二年(356)晋穆帝亦讲《孝经》,此后东晋南朝历代皇帝、皇太子皆有亲讲《孝经》之例。齐高帝登基伊始召经学家刘瓛问以政事,刘瓛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20]永明年间文惠太子临国学,临川王映就“孝为德本”话题提出谘问,此时孝道已被统治核心阶层视作统治思想架构的基础与核心。统治者有借复仇孝子的典型以弘扬孝治的需求,这就为朱谦之等案中的复仇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二)血亲复仇为国家法度所约束
血亲复仇在被孝道提倡的同时也受到法律的约束。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法律在对待血亲复仇问题的态度上,较之前代更为严格。东晋世家大族与皇权共治,阀阅间兴衰代际,利益与矛盾错综,冲突与平衡交替,禁止冤冤相报的血亲复仇有利于维护士族间利益平衡与统治秩序。以司马无忌复仇案为例,晋成帝虽然肯定了复仇行为的情有可原,但并未因其合乎孝道而加以提倡,而是强调“自今已往,有犯必诛”。其原因在于司马承之死出于王敦授意,司马无忌之仇并非仅针对王暠而实际在于王敦,王敦之乱虽平而琅琊王氏依旧贵显,在皇权须依赖士族门阀力量进行统治的背景下,必须对传统的私相报复行为加以制止。
南朝处在士族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时期,对皇权的强调使得此时更加重视法律的权威。在齐永明律的创制过程中,孔稚珪提出“律文虽定,必须用之;用失其平,不异无律”[21]。血亲复仇一旦逃脱法律约束,必然陵犯法律的公平统一,从而使法律权威荡然无存。萧子良也认为“狱讼惟平,画一在制”,张融之父曾为张欣时之父所救,张欣时犯死罪,张融请求代死,萧子良对此虽在道德上进行了肯定,却因“朝有常典”而拒绝了法外代死请求[22],其中反映出的法律与道德相区分的思想,使得该时期对血亲复仇案件的处理较前代更为严格。
另外,长年战乱导致人口减少,一旦统治相对稳定,统治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促使人口恢复。血亲复仇作为鲍宣所谓“七死”之一,往往造成“灭户殄业”的后果,显然与恢复人口的统治方针相悖。对血亲复仇加以法律上的约束,体现了巩固统治基础的要求。
综上,东晋南朝时期儒家思想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孝道又被包括南齐在内的历代统治者作为统治思想的核心。不论是出于维护士族政治抑或皇族政治秩序的要求,还是动乱后休养生息的考量,法律对血亲复仇较之前代有了更多的约束。在朱谦之案中,孔稚珪、刘琎、张融等人提出“礼开报仇之典,以申孝义之情;法断相杀之条,以表权时之制”,即是对复仇类案件中孝与法冲突的精要总结。
三、复仇案件中孝与法冲突的解决
法律是推行儒家教化的工具。在孝与法产生冲突时,统治者一方面要弘扬孝治,一方面又要维护法律威严以巩固统治权威。不同于前代强调孝治而忽视国法、纵容复仇,也不同于后世唐代礼律结合达到完备状态而出现了第一例复仇死刑案件,东晋南朝对血亲复仇案件的处理,大多遵循以孝治的实现为价值导向,以法的设置服务于弘孝、宽宥复仇者的思路,来解决血亲复仇案件中孝与法的冲突。在朱谦之案中,移乡避仇执行之前的处理方式是上述思路较为典型的体现。
(一)弘孝原则优先适用
朱谦之案中,孔稚珪等人认为孝治是最终目的,法律只是“权时之制”,因此,“杀一罪人,未足弘宪;活一孝子,实广风德”,将复仇者绳之以法,并不能达到法律服务于孝治的最终目的。“广风德”的价值取向应优先于“断相杀”而适用,这是本案的基本前提。
孔稚珪等人的思想是弘孝原则优先于具体法律适用的典型体现。国法服务于孝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定的遵循,以南朝宋为例,宋初侍中蔡廓建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朝议从之[23];宋武帝时规定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郑鲜之认为“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义疾理,莫此为大”,后允许二品以上官遇父母及祖父母坟墓崩毁及疾病可去官而不受禁锢[24]。在非血亲复仇的案件中,统治者也时常因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孝友价值观而屈法开恩。孙萨坐充兵役违期不至论死,其兄孙棘诣郡求以身代,后二人俱免。[25]此时期,尽管复仇案件越来越多地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但统治者认为弘孝原则优先于法律适用,与后来唐玄宗时期处理张瑝、张琇复仇案时,认为“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具体情节论心定罪
这一时期在处理血亲复仇案件时,力图将孝治的弘扬纳入法律的框架。朱谦之案中,孔稚珪等人认为,“谦之挥刃酬冤,既申私礼;系颈就死,又明公法”,其动机合乎礼义,又存在自首情节,因此,不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客观行为上,都具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具备从轻处理的合理性。
孔稚珪等人的意见只针对此案提出,并未引申推广至其他同类案件。而对于个案而言,针对具体情节而推究其主观心理状态,又符合古代“论心定罪”的惯常做法。这就不但在理论上尽可能少地陵犯国法的公平统一,在个案上也符合正常的刑狱推问程序,使得对复仇者的宽恕不仅合乎孝道,也被纳入了法律框架内。
(三)层报上级最终决定
朱谦之案较为明晰地体现出处理复仇案件的层报程序。本案案发后,县令先上报州郡,再由州郡官员上报皇帝,在地方乃至中央官员提出讨论意见后,由皇帝最终下达赦免和避仇迁徙决定。东晋南朝时期死刑复核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地方官员根据授权等级不同在不同范围内拥有生杀之权,但对于纳入法律规制下的血亲复仇案件而言,尽管都以赦免告终,可最终决定权仍由皇帝掌握。东晋王谈复父仇后“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勇,列上宥之”,宋钱延庆复仇后自首,亦由太守上表请求不加罪。
这一程序亦存在例外情形。南齐李庆绪、淳于庆两例案件发生于益州,彼时“蜀中多夷暴”,常以将领为刺史,多作军备,二人由刺史赦免。梁代张景仁由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决定赦免。梁代崇孝风气较之前代愈盛,此案发生于普通七年(526),此年对北魏战争刚刚结束,萧纲又被委以镇边重任,或可作为出现此例外的背景。在战争频发时期,法律效力几乎不存在,因此,这类案件不在讨论之列。血亲复仇类案件的决定权不论是由皇帝掌握,还是在常修战备情况下由刺史掌握,都体现出孝与法冲突的解决以维护统治者权威为最终指向。
(四)移乡避仇以防后效
朱谦之案中,齐武帝“虑相复报,乃遣谦之随曹虎西行”。至此,以孝治为指导、在法律框架下由皇帝决定宽恕孝子、移乡避仇以避免后续仇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处理思路。移乡避仇制度正式入律当在晋《泰始律》中,《宋书》载“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26],“旧令”即指《泰始律》。但移乡避仇的实际运用具有局限性。刘宋时黄初之妻赵氏杀儿媳,遇赦,应徙二千里外以避其孙寻仇,刘义庆认为“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27],傅隆认为“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28],赵氏远徙,其子孙较大可能跟从,移乡避仇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故而家族内部直系亲属之间的杀伤不适用移乡避仇。这再次反映了国家法度让位于亲族内部秩序的时代特征。
朱谦之案中,避仇迁徙未及实施,即发生了两次乃至三次报复,移乡避仇的止杀作用化作泡影,对于这种显著置国法于不顾的行为,齐武帝依然“悉赦之”。因此,本案中的避仇迁徙,既构成了这一时期法律框架下处理血亲复仇案件的完整程序,也成为了实际执行中亲族秩序时常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典型反映。
四、处理复仇案件的时代局限与发展趋势
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对血亲复仇类案件孝与法冲突问题的解决,总体上体现出强调国法权威,将复仇案件纳入法律规制的趋势,唐代即出现了多例复仇者论死或流徙的案例。而在东晋南朝时期,法律的约束力虽然较前代得到提升,但依然并未达到可以与道德上的孝治取向相抗衡的地步。复仇类案件虽然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调整,但复仇者均免于承担责任。这一时期,亲族内部秩序往往得到统治者肯定,因而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脱罪的保护伞。南朝宋时,尹嘉母熊氏以身贴钱为其偿债,尹嘉坐不孝当死。何承天认为尹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后遇赦俱免[29];向劭侄向亮因私愤杀其伯母施氏,向劭杀向亮,匿不闻官,为有司所奏,免罪[30];当行为违背法律但符合亲族内部秩序时,法律往往让位于后者,统治者也对这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宽忍甚至鼓励的态度。
东晋南朝时期社会动荡,法律效力的强弱取决于皇权控制力的强弱。在战争时期,复仇往往被认为“义”与“勇”的体现而得到嘉奖,这种态度已超出法律调整范围。即便在统治者留心法制的短暂稳定时期,法律效力亦存在局限,例如梁武帝虽明确禁止复仇,但适用范围也仅限于战后的“缘边初附诸州部内百姓”[31],并非普及全国。同时,即便在相对稳定时期,也尚有地区并未完全开发,部分地区亦有零星战争,国家对国土的控制力较弱,例如南齐时越州地区“刺史常事戎马,唯以战伐为务”,无推行法令的空间可言,法外复仇行为依然有相当大的发生空间。
在中国封建时代,血亲复仇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即便在唐代,将复仇者绳之以法后,舆论依然鼎沸,具体司法实践也时常出现反复。但随着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民间刑事案件越来越多地不需要借助私力救济,对孝道的伸张也逐渐被纳入法律体系。从法律缺位、复仇现象泛滥,到法妥协于孝以解决二者冲突,再到“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的观念,法律对血亲复仇案件的约束力,呈现出了日益增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