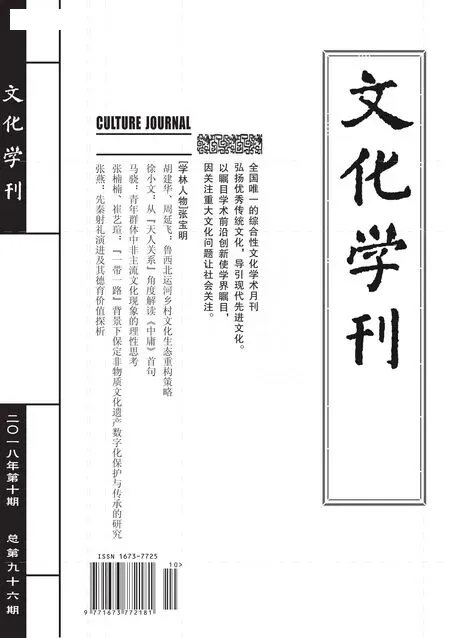梁启超思想的渊源及主要内容
赵文敏
(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梁启超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了解清末思想史的任何尝试都不可能回避他。
一、时代背景及思想渊源
改良思想的发轫,主要源于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嘉、道时期,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许多在其位或不在其位的士大夫,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状况的恶化,并提出种种应对措施,以求改良政治,应付时艰。早期的今文经学主要关注行政和制度的改革,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对外来器物有一定认识的先进中国人逐渐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绝不改变政治体制到接受“求富”,再到对中国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进行变革,改制成为了儒学的核心内容。
康有为在19世纪末的中国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自小接受新儒家思想的道德教育,师从朱次琦,受到了汉学的影响,后由于反对传统的考证方法又转向了陆、王学派,并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对佛学的研究,康有为加深了其拯救时势的决心,这与儒家的圣人思想相融合。但仅仅有菩萨或圣人的救世之心不可能扭转局势,远大的抱负必须辅之以可行的实施手段和改造理论。康有为这方面的理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的知识,二是对今文经学的解读。前者为改良指出了方向,主要体现在废科举、设国会、发展工商业等具体改良措施;后者则为改良的实行创造了舆论和理论根据,主要通过《新学伪经考》、将孔子看成是一位热衷于改革的“圣王”及公羊学说的“三世”理论来达成。[1]综上所述,汉学、宋学、今文经学、经世学派、佛学和西学都不同程度地对康有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最终成为梁启超思想的来源。
二、个人经历及思想发展
梁启超自幼聪颖,十二岁时参加童子试,中秀才。次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在这里学习汉学,从而对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接触了宋学,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接受杂糅了汉学与宋学的知识。在十六岁考中了举人后,梁启超于1890年参加会试,但科举落榜,经同学陈通甫的介绍,认识了康有为,并成为康的学生,从此开始服膺其学说,从而接受了康有为关于改良的思想,同时也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生涯。“公车上书”、成立强学会、从事出版宣传工作,以及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使梁启超崭露头角,并很快成为改良派的重要领袖。在进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梁启超接触了众多知识人物,并或多或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如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其印象深刻,谭嗣同激进的思想也对梁产生着重要影响,和李提摩太的接触使他对基督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则丰富了梁启超的西方知识。[2]但客观来看,在公车上书到戊戌维新期间,尽管梁启超接触了新的思想和知识,但没有摆脱康有为的影响,强调经世的重要意义。
在强调经世时,梁启超注重养性,强调学习实用知识,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梁启超排斥儒家的“三纲”,肯定男女基本平等,肯定实利主义和利欲心;为了经世以改变现实,梁启超强调动力论和“群”。受谭嗣同的影响,梁启超从中国传统中找寻力本论的思想,力陈中国大众应积极进取、勇于挑战,学习西方和日本敢于冒险的品质,推动国家的发展。对于“群”的理解,他强调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必须要将不“合群”的国人整合起来,以集合群体的力量来维持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在对“群”进行解读时,梁启超将其与民主、法、国家相结合,并与西方进行对比,力求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存亡问题,梁启超还倡导“保教”,企图从文化上保存中国,树立广大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信心。至此,梁启超糅合中外思想与学说,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全身心投入到变革运动中,但维新运动的失败迫使他和康有为流亡日本。随后,康有为离开了日本,梁启超成为了留日人士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梁启超一面创办报纸,抨击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一面与会党联系,企图营救光绪皇帝,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在留日人士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与其主张分歧较大的孙中山也希望与梁合作,共同推翻清政府。最终,梁启超由于个人政治观中固有的矛盾和易变的思想,加上老师康有为的激烈反对,梁启超未与孙中山走到一起。从思想变化方面来看,梁启超在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极大地扩展了他在西学上的见识,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升,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有了进一步思考,但并不能由此武断地得出这是促成他向保皇转变的主要因素,梁启超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可能仍然是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产物。
三、梁启超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第一,“新民”。在谈这一问题时,梁启超从公德和私德、竞争和国民理想、进步精神和冒险精神、权利和自由、社会功利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大量引用西方思想和理论,力求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研制出一整套治疗方法。在理解“新民”时,梁启超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否定,但由于理解的偏差,导致其对西方的某些思想认识出现了误差,其从西方借来的知识只不过是“为我所用”,并未深究其认识是否准确。而纵观梁启超接受西学的过程,其思想同样是易于变化的。
第二,“改良”还是“革命”。两者的取舍对梁启超来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梁对现存秩序的看法;二是对于文化传统的态度。在对现存秩序的认识上,限于思想多变可能导致的不确定性,梁启超不能在“改良”和“革命”这两个问题上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最终还是倒向了“改良”。而在文化态度上,梁启超反对传统文化,歌颂西方先进知识,但并不彻底,在宣传西方知识、放弃保教态度时,同时又赞同儒家思想中诸如“孝”之类的论述,同时认为宗教对个人“修心”、培养优秀的品性具有巨大意义。由此可见,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革命者。
第三,“新民与国家主义”。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源于梁启超1903年3月开始的美国之行,对西方美好事物的憧憬与所见现实的差距,使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西方民主政治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使梁启超开始服膺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即倡导开明专制。但梁启超接受开明专制的态度是审慎的,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经济的大发展可能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另一方面开明专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才智。[3]因此,在赞成开明专制时,梁启超显得十分审慎,且没有底气。在关于个人自由的认识上,梁启超表现得更为保守,认为人的自由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利益,甚至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无可指责的。由于国家主义的观点,梁启超反对社会主义,倡导通过对外竞争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哪怕暂时牺牲工人的利益。另外,梁启超还要求建立财政预算制度,政府应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
第四,新民与私德。在对公德和实现国家富强进行系统地思考后,梁启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私德。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论证的材料,尤其是“陆王心学”中对于个人内心的关注。尽管梁启超因拥有了开阔的西学知识而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进行了否定,但“陆王心学”中求诸“内”的价值取向被他所接纳,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应付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而是他发自心底对传统文化在培养“私德”中重要作用的认同。
四、结语
在《新民丛报》停刊以后,梁启超的思想已经过了影响的高峰期,不再是中国思想界的最强音。从1890年到1907年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经世思想在拯救现实和接受西方思想挑战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一时期对于西方思想的认识,梁启超和革命派似乎存在着巨大的沟壑,但在构建民族国家、培养公民私德方面并无分别,两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是对于具体政治制度、组织原则的选择以及民族主义的重点到底是反帝还是排满。[4]与“五四”一代人相比,梁启超更注重传统文化的道德意义,因而不可能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进行否定。但在建构现代国民意识上,梁启超更强调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这与后来的知识分子具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五四”一代人更反对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思想与后继者是一脉相承的,其关注点大都着重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文化中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这使得梁启超的思想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