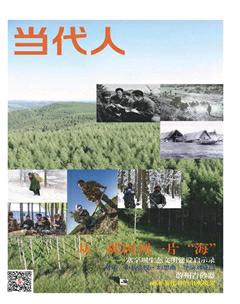寂静深处
1
寂静的深是那种不见底的深,无法触摸不可琢磨的深,像一个人躺在棺材里,寂静围绕着他,只是他再也感觉不到了,其实没必要再苛求他感觉到,寂静现在就埋在他身体中,和他一生的时光一样深。
这浩大得如死亡般的寂静很多事物都感觉到了,比如那头牛,一到这个时辰它就放慢了反刍的速度,它慢条斯理地嚼,仿佛嚼的不再是草末,而是这广阔的寂静。它领会了寂静的深度和广度,它知道只有慢慢嚼,才能嚼出它想要的滋味;它知道只有慢慢嚼,那些平素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图景才能画轴般慢慢展开,才能把原野、四季、犁耙、农人、节气、季风、庄稼、收成这些单个的关键词一个个串起来。农人扛着犁耙在前面走,牛跟在后面,细雨飘洒,农人没有穿雨衣,他觉得牛也淋着呢,自己穿上了对牛不公平。牛拉犁耙的时候很卖力,牛看到农人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牛想犁完了地快点儿回家。牛身上也湿透了,说不清是雨水多一点儿还是汗水多一点儿,农人故意放慢脚步,牛知道农人对它的好,把头埋得更低了,身上的绳索绷得更直……
牛拉着粮车走在回村的路上,它走得稳稳当当的,不急也不燥,几只麻雀在后面追赶,大胆落在车上叼几粒粮食。农人也不催促牛,农人自己走得也很慢。牛看到农人脸上堆着笑,一向严肃的农人笑起来有些生硬呆板,像张家的鸡跑到李家的鸡窝里下了个蛋,却弄得李家人很不好意思。牛知道农人在故意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收成,其实牛也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收成。牛拉着满满一车的粮就像拉着满满一车的汗水,它的喜悦和自豪不知道怎样表达,就把头高高地昂起来,这是它第一次把头昂得那么高。
想到这些的时候,牛心里美滋滋的,牛不怕累,一踏进田地,它就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只是现在牛闲了下来,闲下来的牛感觉身体懒懒散散的,骨头好像生锈了一般,浑身不自在。牛很少到田地里去,就在村子里逛逛,但走不了半个村子牛就觉得倦了,就不想逛了,它有时候觉得自己突然间老了,对什么都缺乏热情。即使阳光很好,暖暖地照着村庄,照着村庄里的柴垛,牛靠着柴垛站着,一站就是一晌午,什么也不想,就这样任阳光在身上晃来晃去,一晃就晃走了大半天的时光。
夜晚是最难熬的,就像现在,风停止了奔跑,墙角的一把陶壶停止了啸叫,鸡们上树了,月亮也上树了,农人给牛添上最后一筐草料就吱嘎把门关上,熄灯睡下了,世界一下子掉进了寂静的陷阱里。牛咀嚼着草料,感觉是在咀嚼黑暗、寂静和孤独,牛觉得无味,长长地哞了一声,牛在反抗,在用它独特的方式对抗孤独。这一声哞叫传得很远,树上的鸡听到了,咯咯——咯咯——回应着;农人听到了,跟着咳嗽了两声;风也听到了,伸手摇了一下老柿树,啪——一枚千柿子砸下来,重重地打了夜晚一巴掌……
其实农人在这漫长的冬夜也感到不自在,像牛一样劳动惯了的,一旦离开了原野就像失去了远方。他们沉浸在寂静深处,身体像被钉进了棺材,但他们还活着,他们的心还在向着庄稼的方向,怦怦怦把身体里私藏的一条田间小道敲响。
2
这样的寂静狗也感觉到了,只是狗不怕寂静,汪汪——呜呜,看,狗多么轻易就打破了这种寂静。只是狗轻易不叫,狗已经习惯了这种寂静,狗寂寞得很,寂寞久了性格就慢慢孤僻了,反而不喜欢嘈杂,反而很向往这种寂静。
狗听到牛还在反刍,还在摆动尾巴把墙角的一垛玉米秸碰响,狗理解牛的寂寞,因为狗看到牛总是闷闷不乐的,其实牛也理解狗的寂寞,牛早就发现狗不那么活泼健谈了,不那么乐观了。狗看到几只老鼠从墙洞里哧溜钻出来,在院子里晃了晃又钻回去,狗没叫,狗觉得那是猫应该管的事情。狗看到风还在使劲儿摇着柿树,就剩最后一颗老柿子了,风显然毫不留情,狗似乎听到了老柿子的嚎叫,它却异常平静,以往它会打抱不平的,现在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狗怎么了呢?
狗现在其实挺消极的,狗常常在村庄里游荡,走进这家,空了,走到那家,空了。狗看到草攻陷了大半個村子,到处是残砖断瓦、破损的房屋、冰冷的灶台、废弃的农具,一把锁牢牢锁住破碎的春光,一张蛛网打捞着时光的落寞……狗看到这些就心痛不已,就很想流泪。狗盯着墙上几把生锈的镰刀看了很久,它想镰刀此时会多痛苦啊,它们曾经那么幸福地拥吻麦子,在五月的大地演绎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现在锈迹爬满了它们的身体,像一个人的眼角长满了鱼尾纹,它们再也没有机会爱了,而它们的情人还在不远的田野里,一年又一年孤独地青了黄,黄了又青。
狗不忍再到空空的宅院里晃悠,索性走到大街上,大街上也空旷了很多,它想遇到另一条狗,想和它说说内心的压抑和苦闷,但它失望了,村庄的狗很少了,这烟火寥落的村庄竟凋敝到连几条狗都养不住的程度。
和牛不一样,狗不喜欢回忆过去,它觉得回忆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沉浸在回忆里只能加深它内心的不满和痛苦。狗喜欢畅想未来,就像现在,深更半夜的,寂静像个木桶把村庄罩住,狗趴在一个月亮照不到的角落,而它的思绪却爬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村口的大槐树底下。
狗看到两个衣着光鲜的人正向村庄的方向走来,越走越近了,狗还是没能认出是谁,或许它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但狗听到了他们的交谈。他们说村庄是他们的根,拔也拔不走,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都是别人的,他们还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就守着村庄过踏实的农家日子。狗听到这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背弃村庄的人又回来了吗?
狗看到两个人叫来了一帮人,开始动手在废弃的老宅院里砌墙造屋,拉起院墙,垒起灶台,竖起烟囱,牛棚、羊圈、鸡窝、狗舍,一个都不少,陶缸里荡漾起日子的水纹,粮囤里回响起粮食的呓语……当炊烟被一股风放飞起来的时候,厨房里就飘散出饭菜的香气,他们的孩子也回来了,新房子刹那间被欢声笑语填满……一家,两家,三家,狗看到那些外出的农人都从城市的霓虹中抽身回来了,他们擦拭农具,修缮房屋,饲养家禽和牲口,又重新过起了久违的农耕生活……
狗想着想着竟然含泪睡着了,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不知一声响动把狗惊醒的时候,是否也能把它从幻觉中拉回来?endprint
3
这样的夜里乌鸦通常也睡不着,乌鸦很喜欢这浩大的寂静,它卧在巢里听风一趟趟搬运云朵,搬来一块压在老树上,再搬来一块压在屋顶上,月光渐渐黯淡下来,乌鸦听到村庄被越堆越厚的云朵压得喘不过气来,听到睡梦中的村庄长长地吸气呼气。乌鸦也感到胸腔里被一团棉花样的东西填满,嘎——它憋不住叫了一声,它感到像从喉咙里抽出一把利剑,直刺向头顶的云朵。雪片开始往下落,一片,两片,三片……它把云层捅了个大窟窿,这是它没想到的。一片雪砸下来,砸中了狗,狗呜呜了两声;一片雪砸下来,砸中了树上的鸡,鸡咯咯了两声。寂静刹那间被打破,鸡狗的叫声、风的喘息声、雪花的奔跑声、骡马的响鼻声、农人的咳嗽声、灯花的爆裂声、老鼠的惊慌声、村庄的长吁声……这一夜风雪无眠,乌鸦无眠,村庄也被搅扰得无眠。
如果说牛需要沉浸在寂静中回忆,狗需要沉浸在寂静中放飞憧憬,而乌鸦却需要这种大寂静来反思,乌鸦是个修行的隐者,不食人间烟火,或者说它是个大彻大悟的哲人,读透了大地上最朴素的哲学,它在辩证的法则中醍醐灌顶,从容淡泊,不悲亦不喜。
种子萌发,苗出得很齐,农人脸上露出了欣喜;禾苗拔节、开花、结实,丰收在望,农人脸上又露出了欣喜。但在乌鸦看来农人没必要欣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了汗水收获果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农人离开了,村庄茂盛的人间烟火渐渐稀落,农耕文明代代相传的火种明明灭灭,乌鸦没有失落,没有悲伤,乌鸦觉得该来的总会来,它能做什么呢?它能给农人想要的富裕生活吗?它能掐灭农人疯长的欲望吗?
一个农人死了,儿女们哭天喊地,好像一家人的天都塌下来了,好像失去了他,家人什么都没有了。唢呐锣鼓吹吹打打,哀乐声铺天盖地,乌鸦蹲在枝头听得也很伤心,也很想哭。一个活生生的农人就这样倒下了,他昨天还牵着牛到井边饮水,还摆弄擦拭他的农具,还把粮食整齐地码在屋角,但从今天起,家里就再也没有了他的影子,田地里也再看不到他的影子,他的家人,他的牛和农具,他的烟锅和蓑衣,只能在回忆里搜寻他的喜怒哀乐了。乌鸦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可能是累了,乌鸦转念一想,累了就倒下来睡长长的一觉,不用操心农事,不用挥洒汗水,不用费尽心血在大地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农人此时多幸福啊。乌鸦这样想着时,被感染的悲傷情绪竟消失了。
农人其实还活着,乌鸦脑海里突然蹦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在村庄的人都是一棵庄稼,一棵麦子也罢,一棵玉米高粱也罢,一棵地瓜一簇花生也罢,他们土里生土里长,天下不下雨都能活命,天早就长成歪瓜裂枣,雨水充足就长得体格健壮,不论高的矮的,弱的壮的,最后都能结籽,都能捧出多寡不等的收成。农人死后埋进土里,他们的身体化为肥料滋养庄稼,农人就融入庄稼中,以庄稼的形式生活在大地上,一年又一年守望着村庄。
乌鸦的头脑里已没有了生死,乌鸦的观念里人和庄稼一样一茬一茬被时光的镰刀收割,乌鸦觉得即使自己是一只鸟,也是大地和村庄的一部分,它最终也会成为庄稼的一部分,乌鸦觉得那是它亲近大地的最完美的方式。
村庄空无,浩大的寂静里,牛在反刍,把回忆一遍遍咀嚼到无味;狗进入了梦乡,乌鸦嘎——从枝头丢下一声鸣叫——
那些被击中的事物都抬了抬头,没有任何的反抗,它们安于命运,安于时光布置的一切……
(张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星星》《诗选刊》《散文百家》《福建文学》《江河文学》《北京文学》《芒种》等刊。著有诗集《季节的容颜》《六瓣雪》。)
编辑:刘亚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