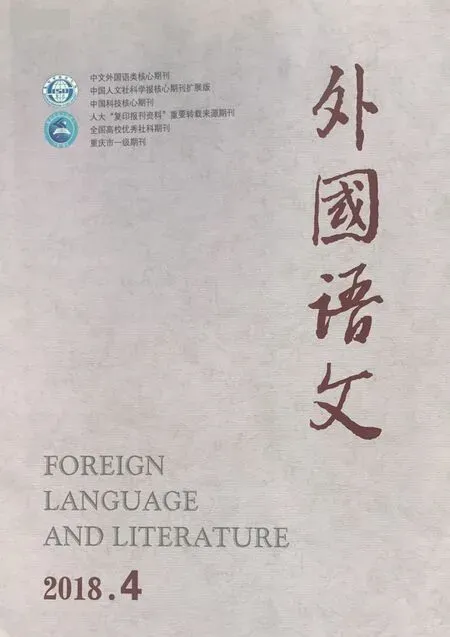莎士比亚的印刷术与怀疑主义
胡 鹏
(四川外国语大学 莎士比亚研究所, 重庆 400031)
0 引言
文艺复兴时期诸如印刷术、航海术、火药等科学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与自身、他者乃至世界的关系,而其中最具影响力、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无疑是15世纪50年代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及其促成的印刷革命(Cohen et al., 2012:249)。①批评界对莎士比亚与印刷革命关系的讨论通常有两种方式:渊源学研究与目录学研究。前者挖掘莎士比亚所阅读过的书籍,后者则探讨莎士比亚的多种版本问题(Marcus, 2000:18-28)。莎士比亚经常在其作品中提及同时代重要的信息技术,几乎每一部作品或诗歌都提到了书籍,而且很多戏剧对白中都暗示了某些印刷的诗歌或民谣,而且莎士比亚作品中对读书人大部分持积极态度,有时也幽默地嘲讽书籍、诗歌、民谣甚至戏剧都是荒谬的、无聊的、肤浅的、误导的,但《亨利六世》中凯德在起义时对法律、知识、书籍文化、甚至提供印刷的造纸业的抨击显然是愚蠢而无理的。印刷史学家艾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注意到早期现代读者对印刷文本普遍保留着适度的怀疑态度:“当读者阅读一本书时,心里必定有着对印刷制品的用途、状态和可靠性方面进行判断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正决定了他们对不熟悉对象(指新得到的书)的接受程度。” 同时约翰斯也讨论了某些特殊文本与怀疑主义的关系(Johns, 1998: 31)。本文将梳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六世》《暴风雨》三部作品中关于印刷术和印刷书籍的表述,通过角色本身对印刷术及印刷革命的态度和认知进行分析,指出莎士比亚戏剧角色对印刷革命所表现出的适度的怀疑主义②。
1福斯塔夫的情书
对印刷术持怀疑态度最幽默的例子当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的情书事件。他愚蠢地将完全相同的情书分别给了裴琪大娘(有趣的是,剧中火枪Pistol和裴琪大娘Page的名字分别意为手枪和页码,实际上都指向了新的科学技术,与火药、印刷术有关)和傅德大娘。裴琪大娘读到傅德大娘相同的信件后既震惊又愤怒:“你有一封信,我这里也有一封信,就只差‘裴琪’换了‘傅德’,两个名字不同罢了!……这儿是你那封信的孪生兄弟……我敢担保,他有一千封这样的信写好着,只是在信的上面流出一块空白,好填上不同的姓名——没准儿还不止一千封呢!——你我这两封信已经是翻版了(second edition)。不用问,他一定会把信一封封的印出来;他才不管把什么人的姓名拖进了他的印刷机——(He will print them…put into the press)你看,连你我都没有放过。叫我睡到他的床上去,我宁可像神话里的巨人那样,让一座培利恩大山压在我身上。嘿,你要我找二十头贪淫的鹁鸪还容易,找一个规规矩矩的男人可是难哪。”傅德大娘立即回应道:“嗳,这两封完全一模一样!一样的笔迹,一样的字句!”(350-351)随后火枪向傅德大娘解释福斯塔夫的生活哲学:“他玩起女人来,管你高管你低,管你富的穷的,年轻年老,傅德,他玩了这个玩那个。他爱吃大锅汤,是女人都配他胃口。你留神吧。”(352)在裴琪大娘看来,复制的信件让人联想到印刷出版工厂,在哪里可以无限制地复制任何作品。而且这段话里的“版本(edition)”“印刷(print)”“出版(press)”等词汇与“上千”封信件一起都指向了使用活字印刷机器生产的产品。显然,众人对福斯塔夫复制信件的反应为我们提供了早期现代英国大众对待印刷术的某些消极态度和观点。
首先,戏剧流露了人们对印刷术泛滥的忧虑。在裴琪大娘看来,福斯塔夫已经写好了上千封留有空白可填上不同姓名的情书,她暗示着由于印刷术的滥用而欺骗他人的焦虑。据传当时著名的人文学家伊拉斯谟就采用了福斯塔夫式的策略从不同的赞助人手中获得钱财,他在新书封皮后插入不同的题献页后寄给不同的赞助人。倘若赞助人中有两人对比得到的书时也会像裴琪大娘和傅德大娘发现福斯塔夫骗局的反应一样,但是伊拉斯谟似乎比福斯塔夫更精明,显然他已经成功使用这一策略从不同赞助人处获得了资金(Eisenstein, 1979: 401)。同时代剧作家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在《灯笼和烛光》(LanthornandCandlelight, 1608)一书中就描述了类似的骗局:某个流浪者误导一位绅士,让他相信一本印刷的书籍是题献给他的。显然莎士比亚知道这一异闻,从而在戏剧中表现出矛盾的态度(Cohen et al., 2012: 250)。
其次,作品还暗含着性与印刷的类比。两种身体活动之间联系的中心就是“press”一词,在罗思德(J. F. Rossd)看来,“press”将两种语境区别开来,一种是印刷时的感觉,一种是身体活动的感觉,或者其他感觉中的一种(Ross,1981: 133)。更明确地说,这个图书出版词汇的比喻具有双关含义:一是印刷,二是性生活(Melchiori, 2000:168)。印刷和性活动的比喻性联系明显是低俗的玩笑,因为两种活动都意味着复制/生殖、释放(enfranchisement),纯洁的事物变成商品并进入公共流通(Saenger, 2006:111)。进一步而言,裴琪大娘还将印刷与性背叛(sexual infidelity)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其中press一词的双重含义,既指向福斯塔夫的信件因为同一内容能够无限复制,同时又讽刺了其不检点的私生活。伊丽莎白·皮腾格(Elizabeth Pittenger)就强调她们 “对机械复制信件的蔑视态度,好像表达出她们会选择真诚、稀有的手写情书……印刷和复制代表着福斯塔夫的口是心非和永无止境的欲望”(Pittenger, 1991:394)。温蒂·沃尔(Wendy Wall)也注意到了这一时期印刷产品的粗制滥造和性背叛盛行的类似之处:“印刷的多样性……与表里不一相似及对没有经过鉴定的写作的放任相联系,制造出一种非法的独特的混合因素。”(Wall, 1993:347)莎士比亚在pressing上的双关既指印刷,也指对裴琪大娘的性欲望,因此沃尔称这是一种“文本的自涉(self-reflexive)” (Wall, 1993:346)。
实际上印刷和性之间混合的比喻是正常的,因为印刷与生育都是通过复制/繁殖得以保留和延续。大卫·斯科特·卡斯坦(David Scott Kastan)在比较印刷制品与舞台表演时就指出印刷是“更保守的媒介”,因为“它为文本提供了持久的想象,避免了表演的短暂性”(Kastan,2001: 7)。正如繁衍后代是保留了个体的物质和精神实质一样,印刷品的传播也能够宣扬保存作者的思想和精神。裴琪大娘对信件充满智慧的描述指出了关于书写信件的某些关键文化的假定条件:手写的文本是唯一的、私人的、真诚的;而印刷文本则是批量的、公共的、潜在虚伪的。尽管福斯塔夫的情书是手写的,但由于多个相同版本就像印刷的一样。因为真爱都是唯一对象,而情书的价值就在于唯一性,印刷的情书就是欺骗,复制即破坏了原本的真实和可靠。然而,印刷的情书在早期现代是非常普遍的——在16世纪成为标准书信书籍的一大标准特色。在早期现代,所有的书信写作已变得高度程式化。现代的观点应用于16世纪会误导我们认为信件并没有确切反映个体的真实想法,但其实书信和其他写作一样,更多的是有着正式的规定和传统(Moulton, 2014:107)。“Press”在这里首先和“Print”相关,福斯塔夫将手写和印刷混为一谈,因为他的情书是固定格式的套用信函。“He will”则通过未来时态表达一种夸张,这种语法修辞的逻辑展开即是暗示着他下一步同样的愚蠢行为。但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无序文本状态,使得人们对于确认这是莎士比亚独立创作的观念产生了怀疑。正如伊丽莎白·皮滕杰(Elizabeth Pittenger)指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故事的传播和接受从某种程度而言是通过戏剧照本宣科的。”(Pittenger, 1991:393)戏剧中言语的控制不当、错误翻译的文本以及复制的信件正是恰当的例子。莎士比亚将印刷术性别化为男人对待女人的行为,而裴琪大娘把出版物看作是混乱的,换句话说,复制的信件表现出作者及其文本可以虚构和伪造。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原本才能让她相信福斯塔夫的爱(Wall, 2003:388)。
再次,裴琪大娘虽不是贵族阶层,但其对印刷文本生产的随意性这一本质的强调,是符合桑德斯(J. W. Saunders)所提出的“印刷的污名(stigma of print)”这一概念的,桑德斯注意到一些贵族反对印刷自己的诗歌作品,因为印刷生产一方面将诗歌变成商品沾上铜臭味,另一方面则能让任何人购买阅读变得大众化 (Sauders, 1951:139-164; 1970:237-259) 。福斯塔夫类似于爱情诗的情书,实际上是他套取女人钱财的商品和策略:“我要去接收这两个娘儿的家产;他们俩就好比我的国。这两个娘儿,一个是我的东印度,一个是我的西印度,这两笔生意买卖,我一笔也不放过。”(334) 亚瑟·马洛提(Arthur Marotti)就指出印刷的污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本土文学传统中缺乏的某种类型抒情诗,认为爱情诗是粗糙而存在道德疑虑的,以及爱情抒情诗的私密性属性,还有抒情诗是特定的社会语境相连的等等(Marotti,1995:210)。实际上印刷术开始应用时,行业中存在某些固定的规则,即对原本的尊重和模仿。虽然我们现在通常会区别对待手写和印刷,但文艺复兴时期这两者的界限并不明显,特别是印刷术的发明相对还是新技术,印刷与手写产品的联系依然紧密,此时的印刷依然保留了很多手写稿的特点。正如柯特·布勒(Curt F. Bühler)指出:“15世纪的手写和印刷书本的差异很细微。”(Bühler, 1960:40)而产品的原材料也可能是一样的:“很多手稿写于纸张之上,很多印刷的书籍也印在羊皮纸上。”(Farquhar, 1977:12) 而版式和格式也是类似的,早期的印刷书籍和大多数手稿一样缺少封面和页码;还缺少记录一些重要信息的封底,如出版地、出版人、作者等。哈罗德·洛夫(Harold Love)从印刷排版着手分析早期现代印刷技术的规范,他指出早期的印刷者会为了模仿作家的手写而修饰打印稿并选择相应字体。而16世纪中期的印刷者则“开始重视有利于印刷的事物而非原稿本身”,包括了“更加规范的信件形式”。到16世纪90年代,印刷者开始摒弃单纯的黑体字,多采用像罗马体和斜体这类更易辨识的字体。这种转变“意味着印刷行业出现的一种新的自信,即不再需要伪装成原稿或为了原本的声誉而做出妥协”(Love, 1985: 96)。
此外裴琪大娘对福斯塔夫情书的谴责也呼应了同时代伦敦市民对印刷商店的不满,他们认为印刷商店是垃圾制造者。早期现代英国的印刷者会印刷任何可以用的手稿,班尼特(H.S.Bennett)就指出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印刷者渴望“印刷任何东西,不管是为自己或他人,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收支平衡获得利润”。很多印刷者采用的方法是批发给书商或承担古怪的自由职业作家的印刷项目,诸如“多种公告……多种事件的项目,描述庆典进程,葬礼……彩票公告、奖券、价格清单等”(Bennett, 1965:274) 。众多作家都表达出对这一过度拥挤的书籍市场竞争的焦虑及对书籍声誉的损害,显然莎士比亚借裴琪大娘之口抨击了书籍印刷市场的乱象,因为莎士比亚在世时除长诗外从未出版过剧本,市面上流传的都是瑕疵颇多的所谓“坏开本”。
2凯德的起义
倘若说“印刷的污名”属于贵族和上层阶级的话,那么《亨利六世(中篇)》中成衣匠杰克·凯德的起义则说明了劳动阶层对印刷革命的反抗。剧中凯德抓住赛伊勋爵对其进行审判,但他的罪行很快就从政治和经济转向了对印刷术的使用上。赛伊勋爵辩解说:“对于饱学之士我总是慷慨地大量馈赠,我蒙王上知遇之恩靠的就是我的学位;我看出了愚昧无知是上帝诅咒的东西,知识乃是助我青云直上飞上天堂的羽翼,除非你们是恶魔附体,你们绝对会克制自己,而断乎不忍下手置我于死地的。”(280)在赛伊勋爵这样的贵族看来,知识正是人们获得救赎的途径。但凯德则视之为欺骗,因为他曾经因此吃过亏,于是谴责对手:“你居心叵测地设立了一所文法学校,毒害腐蚀了咱们国家的一代青少年;从前,咱们的祖先除了记账用的刻痕标签,别无其他书籍;偏是你却使印刷术大行其道,还违背王上的王位和尊严,建立了一座造纸坊(paper mill)。我可以当面向你证实,你身边的那些人张口就是什么名词动词,以及诸如此类叫基督徒的耳朵不能容忍的可恶的词汇。”(278)凯德指出印刷的滥用和弊端并没有错,因为这正是我们所追寻的线索和原因,比如印刷的书籍成为法律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凯德下令派人去“把律师学会夷为平地”(277)。对不识字的民众而言,所有书写和印刷制品都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凯德直接说“把国家的文件档案统统一把火都烧了”(277)。他坚持认为正是印刷和读写能力造成了阶级的划分,因为文盲总是不能完全了解宫廷法律中不利于自己的部分,他们也不能祈求神职人员宽恕其粗鄙的语言。虽然当局将印刷的公告广泛派发,但对未受教育的人来说依然是晦涩而难懂的,因此凯德提出重返口头表达时代的主张:“我的这张嘴将来就是英格兰的议会。” (277) 虽然他在听过赛伊辩护的理由后有一丝懊悔和同情,但依然将其处死,象征着对英国印刷术的摧毁和消灭。
苏萨(Geraldo U.De Sousa)指出莎士比亚在农民起义的故事中发现了对书写权力的质疑,因此合并了1450年杰克·凯德起义和1381年的农民起义,并解读出了凯德起义中农民的愿望(Sousa,1996:185)。在凯德看来,写作、教育、印刷是文艺复兴的国家用以保护富人和权势者特权的排他性工具,从而表达出他对读写和权力的质疑。实际上英国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允许知识分子可免除刑讯的法律正说明了读写能力造成的更不公平的社会功能,由于被告可以仅简单通过读写能力请求牧师帮助,由此强调了阶级特权对法律责任的逃避。文艺复兴作家骄傲地宣称印刷术促进了英国国族性构建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印刷技术成为政府进行更加有效宣传和控制的媒介,同时也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离。因此莎士比亚通过将1381年农民起义和1450年凯德起义的史实编入《亨利六世(中篇)》中凯德的故事,进而提出了权力的滥用。在第四幕中,凯德及其追随者颠倒社会形式,其中之一就是重估写作和读写的价值。凯德:“无辜的羊羔之皮,被他们弄成羊皮纸,羊皮纸上涂上些密密麻麻的字把好端端的人整死,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岂不可恨可气。”(266)凯德感觉到印刷是与社会暴政紧密相连的,其政治表述出现在将出版与维护阶级社会秩序的镇压措施结合起来。沃尔就注意到凯德对赛伊勋爵的起义理由中包含印刷术,这在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中并不是个例:“凯德的话中认为印刷与社会暴政和政治镇压有密切关系,而刑罚的公布出版往往用以保证阶级社会秩序。”(Wall, 1993:342)菲利斯·拉金(Phyllis Rackin)也指出莎士比亚对起义描述最终通过凯德对写作/历史/印刷这些意识形态力量的恐惧得以表达。因此凯德成了印刷用以服务独裁主义的符码,他成为莎士比亚表现此种功能最具说服力的批评家(Rackin, 1990:203-17)。
实际上在这部戏剧中所体现的印刷术指涉相当奇怪,有着明显的时代谬误,因为1476年以前印刷术都还未传入英国。戏剧中凯德起义的实际时间则是1450年,而在27年之后才有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英格兰建立的第一家印刷厂(Evans et al., 1997: 696)。或许凯德提到的造纸厂是1588年设立的一家重要的新造纸厂,正是莎士比亚创作剧本三年之前。伊丽莎白一世的珠宝供应商约翰·斯皮尔曼(John Spilman)在肯特郡的达特傅德建立了英国首家造纸厂,之后一个世纪都在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纸张(Timperly, 1997:201)。而且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英国的纸张主要来自于法国,17世纪前半段英国印刷者所采用的纸张有95%来自海外。阿尔弗雷德·肖特(Alfred Shorter)分析了英国依赖进口纸张的四大原因:一是进口纸张(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产的)价格相对便宜;二是制造纸张原料的匮乏;三是养羊的巨大规模导致羊皮纸盛行;四是英国缺乏足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Shorter, 1957:3)。由于国家依赖纸张进口给英国人造成心理上的不适,从而也导致对印刷产品的怀疑。
3普洛士帕罗的魔法书
近年来《暴风雨》引起了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学派的持续关注,甚至大有变为研究该剧的唯一思路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暴风雨》批评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从将殖民主义视为根本不值得研究的议题到将其称作唯一值得研究的议题(Willis, 1989:277-289)。但我们发现《暴风雨》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本——魔法书,这是讨论莎士比亚与印刷术所必须面对的对象,因为它本身具备的固有权力与危险因素具有典型意义。
当普洛士帕罗让蜜兰达“穿过倒退的时间,那黑沉沉的深渊”(511)时,他把自己描述为沉溺于神秘的书本知识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他在学问艺术上一时无双,于是“专心致志研究学问,对朝政便越来越荒疏,把邦国大事都交给兄弟,自己却废寝忘食沉溺在玄秘的魔法中——”(512-513)普洛士帕罗的行为折射出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典型知识分子的行为,如某些印刷史学家就注意到印刷革命鼓励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在阅读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而罔顾其他 (Eisenstein, 1979:131)。正如普洛士帕罗说道:“我这样摆脱了俗务,抛却了杂念,过着修身养性的隐士生活——要不是得与世隔绝,我这门学问胜过众生的一切。”(513)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出印刷革命使阅读大众分裂,进一步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在他看来早期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新教强调独立阅读和个体阐释的直接后果(McLuhan, 2011:176-180)。而批评家芭芭拉·莫厄特(Barbara Mowat)试图将《暴风雨》批评绕开印刷文化的争论,指出普洛士帕罗的魔术书最像一种被称为“魔法书(grimoire)”的纯手写书稿(Mowat,2001:4-5)。不管普洛士帕罗是否阅读手稿或印刷本,他在米兰的作为似乎告诉了我们他所谓的“亲密(closeness)”的警告寓言,即沉迷于学文的危险和自我毁灭(Cohen, 2002:86)。我们能够想象普洛士帕罗在米兰坐在书轮(bookwheel)*书轮(bookwheel) 是1531意大利工程师阿戈斯蒂诺·拉梅利(Agostino Ramelli)设想的一个复杂奇妙的装置,它就像一个水车轮一样满载各种图书,而且以同一种角度展开,通过手或者脚来控制轮子转动,阅读者就能轻松地在不同的书之间穿梭浏览。批评家推断类似普洛斯彼罗的人或许从未使用过书轮,他们认为书轮是那些被贵族雇佣专门从事朗读和摘录古典作品的清贫学者或秘书的理想工具(Jardine et al.,1990:30-78)。面前感受到对书本的控制感和权威感,甚至有某种全知全能的感觉(Jardine et al., 1990:30-78)。有趣的是,虽然之后普洛士帕罗失去权力被逐出米兰,但其爱书之心未减。他告诉蜜兰达:“(贡札罗)知道我爱书本儿,让我从我的书房把心爱的书带走——这些书对于我比一个公国还宝贵。”(517)由此可见普洛士帕罗对书本的重视程度。卡力班没有知识,正如普洛士帕罗骂道:“可恶可恨的奴才,你心里‘善良’留不下半点痕迹(any print of goodness wilt not take);坏事儿样样会!”(529),但是他明确了解普洛士帕罗正是凭借书本的力量控制着小岛。他告诉斯蒂番可以在普洛士帕罗午睡时“先把他的书偷过来”,强调“记住,先要把他的书拿到手;没了书,他成了个傻瓜,跟我一样;就连个精灵也使唤不动了——各个精灵都恨他,跟我一样地恨如切骨。只消把他那些书烧了”(580)。而普洛士帕罗也承认对书籍的依赖:“我要去读我的书了,赶在晚饭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办呢。”(576)
虽然莫厄特后来又指出“普洛士帕罗的书不是一本魔法书”,或“同时是一本魔法书和舞台道具魔法书”,并最终得出就是“书本身”(bookperse)的说法,认为它“让普洛士帕罗的小岛统治成为可能”,即意味殖民者的科技知识(Mowat, 2001:27,29,32)。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普洛士帕罗的魔法书是否有用,但他无疑是帝国主义者。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在其实验性电影《魔法师的宝典》(Prospero’sBooks)中注意到“普洛士帕罗的力量源自他的书”,因此决定设置其图书馆有“二十四卷书”,其中包含“动物志、草本志、宇宙志、地图集、天文集、语言书、理想国、游记、游戏集……色情书、运动书、爱情书、色彩书及建筑音乐书”。对格林纳威而言,之所以设置这些书籍“不单因为它们能让普洛士帕罗和蜜兰达在岛上身心健康地生存,同样也让普洛士帕罗获得可以拥有驱使死者、令海神俯首的强大力量”(Greenaway, 1991:9,12)。因此书本不仅仅是普洛士帕罗力量的象征,同样也是其力量的源泉。《暴风雨》结尾时作家并未交代书的最终命运,正如普洛士帕罗考虑离开小岛时,他承诺:“那我就此折断我的魔杖,埋进地底的深处,我那魔法书,抛进海心,由着它沉到不可测量的海底。”(611)但不能否定的是普洛士帕罗就像浮士德一样,试图利用对神秘书本的研究获得某种权力。虽然普洛士帕罗最终夺回了他的领国,浮士德的灵魂也最终进入了天堂,但其过程都说明了书本能够引诱有野心的学者走向堕落和毁灭(Cohen,2006:86-7)。
亚当·马克思·科恩(Adam Max Cohen)指出在印刷革命开始的一个世纪内多种文本和个体文本的多重版本让欧洲人生活在“透视法的轻松(perspectival lightness)”氛围之中(Cohen,2006:87)。而艾森斯坦认为在欧洲人印刷术的世纪能够“与存在的矛盾观点共相妥协,对相反的运动不做任何偏袒也不会置放于过于简单的宏伟计划之中”(Eisenstein, 1979:440)。而这似乎是莎士比亚创作天赋的最好注解。莎士比亚以独特而有依据的视角排列角色,但他并没有给我们勾勒出一套系统的伦理和道德思想体系,而是真实再现问题的本身。蜜兰达在结尾时惊叹:“这个新世界多棒啊(a brave new world),有这么好的人们!”,其父普洛士帕罗则回应:“对你是个新世界。”(620)在科恩看来,对同一现实的不同视角并不是由于英国和欧陆印刷工厂所发行的文本造成的,而是折射出印刷品的流通扩散与技术发展巧妙地平衡(Cohen,2006:88)。蜜兰达所提到的 “新世界”常被置于后殖民话语中进行理解,但其同样也与早期现代印刷文化产生共鸣。有学者指出,16世纪印刷品暴增的状态其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全新世界的文本诞生,这对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而言比起之前跨越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更加重要。尼尔·罗兹(Neil Rhodes)和乔纳森·索戴伊 (Jonathan Sawday)认为“新奇的世界——纸媒的世界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新世界约5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而纸媒世界的诞生是“欧洲文艺复兴关键性的运动” (Rohodes, 2000:1)。不论《暴风雨》中普洛士帕罗的书是不是魔法书,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众多不同类型的印刷出版物对剧作家莎士比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笔下的大部分角色都是源于其他的剧本和故事,倘若没有大量阅读书籍的话,莎士比亚显然无法顺利发展其剧作家的职业生涯并取得空前成功。同样由印刷术发展带来的出版作品的涌现也为整个早期现代带来了知识的普及。
4 结语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在诸如制图、玻璃制造、透镜磨光、锻造、造船、机械仪器制造、航海等领域的实践性(通常有着经济因素的促进)技术发展,人们了解到更多的知识,也更易获得知识(Shirley, 1985:74-93)。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和数学仪器制造不但直接扩展丰富了知识,更是开拓了知识的维度。但印刷术的发展却是这一时期欧洲在知识生产创造、传播和储备的最有力武器。为了传播文艺复兴知识而进行的书籍印刷制造,其巨大的重要性在那时就常被提及(Grafton, 1991: 37-8)。印刷术与造纸、铸字、雕版、专业作家、出版等新兴行业相互促进发展。大量相关的教育、文化产业从标准化的低价印刷书籍中获益。例如,印刷术鼓励对已知或新发现古籍的学习、编辑、整理和翻译,而这则进一步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而印刷书籍的实用性也促使专业和私人图书馆的建立,大大拓展了大众文化和博物学文化(Sokol,2003:98)。众所周知,作为戏剧家的莎士比亚在生前对印刷出版剧本并没有多大兴趣,剧场演出才是其剧本出版的唯一形式。他对出版漠不关心,甚至也不在乎那些市面上众多的盗版“坏开本”。他唯一关心的是叙事长诗的印刷出版(Kastan,2002:23)。*很多学者都对莎士比亚与印刷出版的关系进行过讨论,推测其生涯中的“消失的那些年”(lost years)在从事印刷出版业(Murphy, 2003:16)。
通过分析莎士比亚戏剧角色对待印刷术的态度,我们一方面能看到印刷术在早期现代英国的接受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掺杂着复杂的政治、宗教、经济、爱国主义、婚恋关系等内容,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印刷广泛传播所扩大的书籍和书写的巨大力量*宗教观念也影响了对待印刷技术的态度。因为新教徒高度提倡对圣经的个体阅读和阐释,于是印刷术与宗教改革紧密相关。本文限于篇幅省略了这一部分的讨论。。我们也看到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甚至同一阶层中不同人群对待印刷术的态度都是不同的,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早期现代英国人的怀疑主义。莎士比亚对印刷术泛滥的担忧正体现出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的大量复制所带来的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和原真性的丧失,但他并未因噎废食,而是同时肯定了印刷术所带来的正面积极作用,因为实际上他也是印刷革命的受益者之一(本雅明, 200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