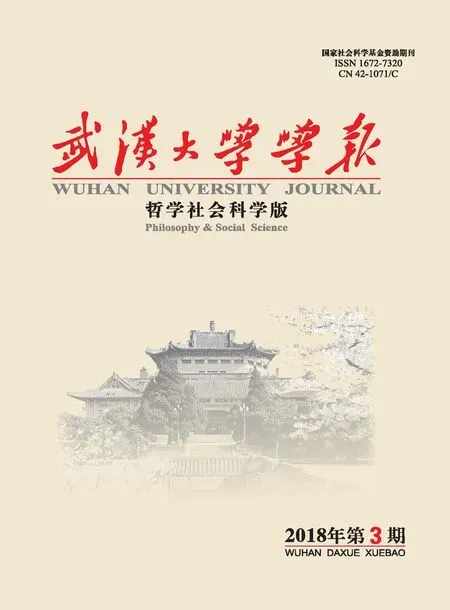论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
乔洪武 邓 钺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再次重申,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由此可以预见,我们党在近几年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的基础上,必将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的成就。既然是全面从严治党,其治理的维度显然是多维的,包含政治、思想、组织和道德文化等维度。习近平多次强调,从1949年至今,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四大危险[1]。“四大考验”中最核心的考验就是市场经济的考验,因为它会带来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利益分配方式和机制,由此更有可能诱发党员领导干部经济伦理观念的蜕变,滋生消极腐败现象,从而危及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也应包含经济伦理维度。
一、经济伦理与政体正义的关联
所谓经济伦理,按照最早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马克斯·韦伯的界定,是指“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的与历史的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2](P4)。其次,“‘伦理的’尺度就是这样一种尺子,用它来衡量人的价值合乎理性的信仰的特殊方式,作为衡量‘好习俗’这个评价所要求的人的行为的准则……这个意义上的伦理的准则观念可能对行为具有很深刻的影响”[3](P143)。也就是说,经济伦理是由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人们在经济利益取舍和经济行为评判中应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准则。那么,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呢?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求其成员在市场经济下,利益取舍和行为评判中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准则。为何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经济伦理维度的治理?这是因为执政党成员经济伦理的腐败蜕变不仅是其个人道德全面退化的诱因,而且会因其执掌政体的领导权而使整个政体从正义向非正义转化。作为古希腊三贤之一的伟大思想家柏拉图,最早就揭示出经济伦理的蜕变必然导致社会整体道德退化和正义的政体向非正义的政体变异的规律。
柏拉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过五种政治体制,除了他阐述过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之外,其余所谓四种政治体制的正义性是逐步递减的,而其非正义性却是逐步递增的。从理想国一步一步蜕化堕落到越来越非正义的政体,正是统治者和卫士——这种精英阶级的经济伦理观念被腐蚀所致。在理想国中,对于统治者和卫士而言,他们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更不能保有金银钱财。精英阶级产生道德蜕变过程大多是:一位年轻人有一位担任统治者的好父亲,这位父亲不要荣誉和权力,他宁愿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那么他的儿子怎么会变成爱好虚荣和金钱的人呢?起初,他老是听到他的母亲在抱怨他的父亲不会当统治者,不太关心挣钱,而是把这些事情都看得很轻。此外还有其他人也在这种场合惯常唠叨的其他怨言。于是两种力量就像拔河一样对他展开争夺。他的父亲向他的心灵灌输和培养理性的原则,其他人向他灌输和培养欲望和激情的原则。尽管他的天性并不坏,但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使他发生了变化,他灵魂的自律转变成野心和激情的中间状态,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4](P552-553)。一旦人的经济伦理道德由于诱惑和腐蚀被打开一个缺口,整个的道德防线立刻就会崩溃——“这些人像寡头制的统治者一样贪图财富,热衷于搜括金银,收藏于密室,他们的住处筑有围墙,建有爱巢,他们在里面供养女人以及其他宠幸者,尽情享乐。他们热爱金钱,但由于不能公开捞钱,因此只能偷偷地寻欢作乐,逃避法律的监督,就像孩子逃避父亲的监督一样。他们也很吝啬,乐意花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4](P551)这时的政制已经是一种善恶混杂的政制。
柏拉图不仅在个人微观层面上揭示出个人经济伦理蜕化变质的过程,而且在致变原因上总结了人的经济伦理是如何发生蜕化变质的。概括起来,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发生:第一是个人自身的原因。他指出,人身上存在着必要的欲望和不必要的欲望,假如个人不好的欲望得不到法律与理性结盟的较好的控制,一旦受到外界的不良诱惑,那些从前只在睡梦中才会出现的兽性的、野蛮的欲望就会驱使他弃善从恶,“没有任何极端愚昧和无耻的事情”[4](P581)是他不敢做出来的。第二是家庭和朋友的影响。最初的影响是来自他的母亲,当孩子的母亲从孩子童年时代就开始报怨担任城邦统领的父亲不会以权谋私、捞取金钱时,实际上就开始引导孩子的价值观向非正义的方向变化。当家中长辈和朋友反复向他灌输这种思想时,就会逐步把这位年轻人灵魂中的美德全部摧毁,尽管这个年轻人“他天性并不坏,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受了影响而坠入邪恶的泥坑”[4](P553)。第三是制度环境的影响。柏拉图分别研究了四种非正义政制对人的正义、善和道德观念和行为的作用机理。在刚从理想政制向寡头政制转化时,由于社会道德氛围的抑制,贪婪的当权者尽管热爱金钱,但由于不能公开捞钱,所以只能偷偷寻欢作乐。当寡头制度稳固之后,财富便成为衡量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一种用财产来确定资格的制度,富人掌权,穷人被排除在外。私人拥有大量的金钱会摧毁荣誉政制……财富和美德就好像被置于天平两端,一头往下沉,另一头就往上翘。”[4](P554)而在民主政制下,“当一位年轻人在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不自由的和吝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尝到了当雄蜂的甜头,和那些只知千方百计地寻欢作乐的粗暴狡猾之徒为伍的时候,你必须毫不动摇地相信,这就是他的灵魂从寡头型转变为民主型的开始”[4](P566)。年轻人同那些贪图安逸的人公开生活在一起,当外界的诱惑最终攻克他心灵的城堡时,如果他的亲友要来支持这位年轻人心中的节俭成分,入侵者便会立刻关闭他心灵堡垒的大门,不让他接受良师益友的忠告。等这位年轻人灵魂中的美德全部被摧毁,他们灵魂中那些有害的欲望都会被释放出来[4](P567-568)。不仅如此,民主政制恰恰是最不正义的僭主政制产生的温床。这是因为,正是“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这种体制,为专制的必要性开辟了道路。”[4](P570)这些当上领导的坏人就是民主社会中那群又懒惰又奢侈的人,尤如有刺的雄蜂,而社会上最富有的阶级会“向雄蜂提供丰富的蜜汁”。所以,“这个富有的阶级实际上可以称之为雄蜂的花园。”[4](P574)这些“有刺的雄蜂”先是以人民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赢得民心,而这正是僭主产生的根源。柏拉图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揭示出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恰恰是导致个体经济伦理腐败退化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尽管柏拉图所认可的正义并不是现代语境下的正义[5](P193-195),正如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柏拉图当然没有认识到,“正义的形式原则作为人格的抽象的共性,而以个人的权利作为现存的内容,亦必须浸透全体。”所谓浸透全体,就是指“这原则必须获得它完全充分的现实性,且必须表现为财产。这才是真的现实精神,这个现实精神的每一环节都有其充分的独立性”[6](P265)。他对正义政体之所以退化为非正义政体的分析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试图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正是由于经济伦理的蜕化变质,才导致一种较为正义的政体向越来越背离正义的政体转变;而生活于不同政体中的个人,也会因其经济伦理观念的蜕化,导致其整个向善能力的退化和作恶能力的增加。这一规律,在柏拉图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已经被无数次地反复证实。
二、防止经济伦理蜕变的经验和教训
正是由于柏拉图揭示的上述规律为后人所认识,执政者或执政党期望长期执政都必然要防止自身经济伦理的蜕化变质,以避免其因背离正义、丧失民心而丢掉政权。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就指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有人认为,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与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7](P1)。由于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具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诸如此类的感觉,而且人“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所以,治理一个国家“公正是为政的准绳……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7](P6-7)“正确的政体必然是,这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然而倘若以私人的利益为目的,无论执政的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人,都是正确政体的蜕变。”[7](P86)中国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强调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P179)“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P12)在现代人民共和制的国家中,因其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更有权要求执政者掌权廉洁和公正,要求他们在经济伦理及道德方面没有瑕疵。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政治问题的根本是找到一个最有德、最开明、最睿智并且从而是最美好的民族的那种政府,在他看来,尽管执政掌权者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强力,但“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9](P13-14)。社会上的每个人因社会公约而将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整个集体,“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一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即:它就是人们所称之为主权者的、由社会公约赋之以生命而其全部的意志就叫做法律的那个道德人格——卢梭注),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9](P25-26)。在民主的共和国和政治体中,执政掌权者作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其利益追求与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治理社会就应该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9](P35)。卢梭还明确指出,在民主制的国家,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腐化是对共和国最大的危害,“没有德行,(国家)就都无法维持”[9](P89)。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廉洁和为公被公认为执政正义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人民之所以授予执政者代表人民主持正义权利的原因。如果当权者由于自身经济伦理的变质,导致其整个向善能力的退化和作恶能力的增加,那么势必背叛代表人民主持正义的神圣职责,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被人民赶下台。
现代政党最初诞生于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第一次给政党下了明确的定义: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也是实际上的领袖。共产党属于刚性政党,它不仅有严格的党章和政纲,而且依靠民主集中制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团结人民群众,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和党的既定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执政掌权更应该遵守执政伦理的最基本正义原则——廉洁和为公。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以严格的政治和组织纪律,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道德形象赢得人民拥护和爱戴。若不遵循廉洁和为公这一执政伦理的最基本正义原则和道德底线,它也无法忠实履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神圣职责,难免会走向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境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直在努力预防和纠正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党员出现的腐败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中央一直强调从严治党。从1951年底开始,毛泽东发动并亲自督办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变质、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1963年,毛泽东又亲自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这个运动的重点就是教育党的干部,“使我们的干部……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0](P1321)。在1976年3月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10](P1770)尽管毛泽东的出发点是为了预防党员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变质,但他的方式不是凭借完善法治和党章党规,而是依靠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方式是不正确的。他将遏制党员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变质与铲除滋生这种腐败的经济私有制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并将此上升到走何种社会道路的层面,不利于人民在经济道路选择上的自由和非公经济的发展。
柏拉图曾为遏制社会经济伦理的堕落开出过他自认为有效的药方。柏拉图指出:“我们必须把实施正义与摆脱贪婪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寻找我们避免这种危险的方法。”[11](P495)为避免引起贪婪的危险,“第一个治疗方法是,从事商业的人要尽可能少;第二,让那些即使腐败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大害的人去从事这些工作;第三,必须制定某些具体措施来防止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把邪恶传给别人。”[11](P686)就第一个治疗方法而言,处于城邦的管理者和护卫者的精英阶级“家庭的家长都不得从事商业,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甚至不能与商业活动有关联……如果有公民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卑贱的商业,那么他要为玷污高贵的血统而受到审判,任何人发现了都可以去法官那里告发”[11](P686)。就第二个方法来说,为防止从事商业把邪恶传染给别人,应当“让外国侨民或外国人经商。”[11](P686)。第三个办法就是利用严格的法律限制来“保证商业道德,尽可能减少商业中的恶行。”[11](P686)
而在柏拉图看来,更为根本的医治对策,还是建立他所谓的理想国。因为只有在那个国家中,才会有如下道德准则:“我们的社会一定不要金银,也不要用手工技艺谋利……而只允许有限度的农耕,人们不能用它来谋利,以至于忘了拥有财产的目的……在我们所推崇的事物序列中,财产所据的地位应当最低,因为人的普遍利益以三样东西为目标:正当地追求和获得财产是第三位的,最低的;身体的利益居第二位;灵魂的利益居第一位。对我们现在考虑的体制来说也一样,如果按照上述原则来规定荣誉,那么就可以正确制定国家的法律,但若有任何法律使公众对健康的推崇高于明智,或者对财富的推崇高于健康和明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法律的制定是错误的。”[11](P502)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要确保理想国及其道德理想不发生变质,根本策略在于确保理想国的公有经济制度永恒不变。反过来,要确保这种制度不变,有赖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和道德对其不断巩固。唯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维系和巩固理想国上形成合力,再辅之以个人的道德修炼,才能有效防止个人和社会政体的伦理道德蜕变。
柏拉图的上述主张存在着重大缺陷,这诚如他最赏识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质疑的,一个秩序井然的城邦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呢,还是像在柏拉图的《国家篇》中所倡议的那样好呢?[7](P31-32)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此做了彻底否定的回答。亚里士多德在全面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后得出的结论是:按照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那样去做,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7](P32)。黑格尔也指出,柏拉图认为“正义国家”不仅必须关闭一切通向发财欲望的大门,也必须关闭每个人有权利自由选择和自由发展的大门。产生这种谬误的原因在于他否定了主观自由原则。“由于废除了财产和家庭生活,由于取消了对于职业的任意选择,简言之,由于排斥了一切与主观自由这一原则相关联的这些规定,柏拉图相信他可以关闭一切通向情欲、仇恨、争执等等的大门了。”[6](P266)正是这些缺陷和谬误,使得柏拉图要确保理想国及其道德理想不发生蜕变的设想只能是一种空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则进一步证明,用柏拉图式的治理方式来防止党员的经济伦理蜕变非但达不到从严治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还让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得我国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国民经济也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
三、市场经济下从严治党经济伦理之维的切入点
如前所述,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之维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求其成员在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在利益取舍和行为评判中必须遵循的价值观念标准和道德准则。那么我们首先应当弄清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什么样的经济伦理特质。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2](P99)对于人们从市场经济中会获得什么样的经济伦理观念,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市场经济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个人为了其理想的或物质的利益而进行并完成的。”“即使一个经济制度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当然确实存在只建筑在单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但更为肯定的是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在市场经济中使收入最大化无疑是所有经济行为的动力。”[13](P233-234)汉斯·里切尔也曾说,在诸如社团、合作社或慈善组织等小的集体中,“从内部来说,爱或牺牲,团结或慷慨可能是决定性的;但不管内部结构或动机如何,经济单位在市场中彼此的关系总是受个人自我利益的控制。”[14](P123)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确带有肯定和鼓励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伦理导向作用,而这正是市场经济能比其他任何经济形态能够更有力地解放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大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经济伦理之维的切入点应该是:
首先,面对市场经济的长期考验,我们党“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15]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道德教育中,最关键的维度是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这不仅是因为,柏拉图早就告诫我们,造成个人道德沦丧甚至正义政制溃败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诱因,就是经济伦理观念上的蜕变。一旦外界的诱惑击溃了领导干部的心灵城堡,经济伦理中拒腐的防线被突破,所有坚持政治忠诚、为民造福的理想信念都会被抛弃,所有的道德底线也会被逾越。这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执政党成员和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种种诱惑就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更在于,市场经济伦理的诱惑并非是不可抗拒的,连最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奠基人米塞斯也承认:在市场经济下,“当然,有些男女是以利他主义和彻底献身的精神提供服务。没有一部分精英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人类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文明状态。在改善道德状况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那些打算为自己认为正义和公益的事业而牺牲个人幸福、健康和生命的人取得的成就。他们从事着他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事情,不在乎自己是否为此而牺牲。这些人不是为了奖赏而工作,他们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虽死而无憾。”[16](P70)奥尔森也指出:“要想改变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伦理观念,依靠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的效果并不大,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14](P71)但是,他也承认这种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14](P70-71)这种激励就是道德力量。作为中国执政党的成员,党员在入党之初就应懂得,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因此,让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廉洁和为公的最基本道德底线,也是守护我们党执政伦理的必然义务。这种经济伦理观的教育,对于激励党员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自身经济伦理观念的侵蚀和诱变,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可能要求全体党员都达到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侵袭的道德境界,但在党的核心干部身上是应该而且可以具有这种道德境界的,这一核心干部集体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也是“打算为自己认为正义和公益的事业而牺牲个人幸福、健康和生命的道德精英”。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想要担任政体中最重要的官职,就必须具备三项条件。”首先,必须忠于现存政体;其次,必须具有为政方面的最高才能;第三,必须具备为每一政体特有的、与之相符的德性[7](P187)。正如现代科学那样,新的观点和新的科学必然总是从一个或少数人身上发源,然后向更大的核心归依者和追随者公开传播,进而逐步发展成某个自然或社会的公理或共识。共产党的宗旨的实现也必须要有一个由献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所组成的团体,他们愿意践行共产主义道德并自觉地把这种理想信念传播给他人。而共产党的核心干部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的政治担当,自觉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引导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如此才能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各种诱惑可能导致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强调:新形势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自觉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坚持不忘初心,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所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济伦理治理关键在于确保党员领导干部牢固确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党的核心干部自身也应自觉地提升道德修养水平。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遏制党员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还要以限制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为重要路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经济利益更是人们的经济伦理道德的基础。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自由裁量权越大,以权谋私的机会就越多,他们所受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多,经济伦理观念腐化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正如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说的那句名言,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针对这一问题,除了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经济伦理观的教育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外,另一个釜底抽薪的治理对策就是从根本上限制各级领导干部的自由裁量权。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这条规律”[17]。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必须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法治化,使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18]这两个决定的出台,正是我们从根本上限制和减少各级领导干部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依据和强大后盾。因此,根据这两个决定,我们必须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纠正过去那种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让企业当好“运动员”,法院当好维护规则和秩序的“裁判员”,政府只扮演好社会服务的角色,从而形成“小政府,大市场”,促进政府率先守法、依法行政目标的早日实现,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规则和惯例尽快接轨。显然,这对于我国防治领导干部经济伦理的蜕变和遏制贪污腐败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党员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必须以加强法治和党内规章制度建设为手段,决不能以排斥和否认市场经济为手段、以重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为目的。如前所述,50年代后期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教训之一就是:为遏制党员的经济伦理蜕变而将滋生诱发经济伦理蜕变的私有制经济也一并废除,排斥和否定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不正确。1981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己有定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摒弃了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的传统极“左”观念,强调改革就是为了建设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这种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既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形态,也重申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更加完备的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决心。
市场经济有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优势,但它也确实带有某些天然缺陷。作为最早为现代市场经济进行经济伦理辩护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明确地指出,“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19](P76)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依靠经济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动力具有二重性,它既可以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也可以成为“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成为“一切骚乱、忙乱、劫掠和不义的根源,它给世界带来了贪婪和野心”[19](P69-76)。所以,斯密特别强调:“自私的激情在其它方面介于社会性的和非社会性的感情之间”,“当它除了使个人关心自己的幸福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后果时,它只是一种无害的品质”,而当“它一妨害众人的利益,就成为一种罪恶。”[19](P399)但是,斯密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可能成为我们道德败坏的诱因而否定它,而是强调法治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道德败坏、构建良好的社会道德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对那些厚颜无耻、不讲道义的人,“法律通常必然能吓住他们,使他们至少对更为重要的公正法则表示某种尊重。”[19](P74)事实上,现代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也正是依靠严格的法治来制约政府公权力,规范市场行为,防止执政党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而依法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越是严厉和完备,该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的运转也愈高效,它所带来的经济伦理负面影响也愈轻微。
所以,遏制执政党成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经济伦理观念蜕变,不是要摒弃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而是要靠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诚如习近平在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所强调的,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既让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深入解决,又有效预防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防范已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复发。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建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充分释放监督的制度优势[1]。党的十九大还特别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组建各级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要我们党有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扎紧制度笼子的有力手段,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在反腐上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那么,市场经济对经济伦理的诱变企图永不会得逞。
[1]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人民日报,2016-11-02.
[2]韦伯文集:下卷.韩水法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3]韦伯文集:上卷.韩水法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4]柏拉图全集:第2卷·国家篇.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乔洪武.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7]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8]论语.张燕婴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1]柏拉图全集:第3卷·法篇.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4]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10-28.
[16]米塞斯.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冯克利,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11-16.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10-29.
[19]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