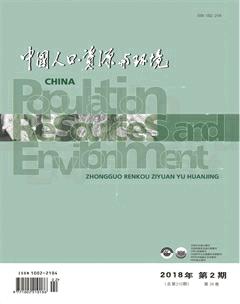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董梅+徐璋勇+李存芳
摘要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基于碳强度约束的行政型减排措施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分析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碳减排机制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文构建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模拟2012—2030年在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的情景下,城乡居民福利水平、消费结构以及CO2排放等指标相比基准情景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①城乡居民收入无显著变化,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②居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大幅下降,农村居民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③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大幅降低,电力消费显著上升,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城乡居民的煤炭消费降幅最大,农村居民对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降幅远超城镇居民,对电力、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④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的福利等价变化降幅超过城镇居民。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生活减排起到积极作用;二是这一政策使城乡居民福利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三是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负向影响超过城镇居民。总体而言,政府在碳强度约束政策的基础上,首先,应增加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增加农村清洁能源的供给;再次,提高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能源的补贴力度,从而降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碳强度约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居民福利;动态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2-0094-12DOI:10.12062/cpre.20171017
气候变化是当今各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起,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以下简称碳强度)约束的减排目标。在国际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以下简称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0%左右。在国内,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左右。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是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碳强度约束是否会对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抑制?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城镇和农村哪个居民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通过明确这些问题,有利于中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缓解碳减排措施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不利影响。
1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碳减排约束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依据不同研究角度,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碳减排目标和政策措施的种类。在污染治理中,碳减排目标分为总量减排目标和强度减排目标。其中总量减排目标是指在政策期内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约束,有效实施该目标可以促使实际碳排放下降。
强度减排目标是在政策期内对单位经济总量的碳排放进行约束,在为经济增长留有余地的同时灵活调整碳排放量,当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时,实际碳排放总量会减少。张友国[1]认为这两种减排目标的差异体现在成本有效性、环境效益和政策可接受性三个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度目标更稳定和公平,无论出现始料不及的经济繁荣或萧条都不会改变目标实现的难度;若采用总量减排目标,则经济增长超过预期的国家需要付出额外的减排成本,相当于对这些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实施惩罚或征税。因此,发达国家主要承诺总量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承诺强度减排目标。基于以上两种碳减排目标,Fischer[2]等人认为有两类政策措施分别与之对应:第一类是市场型措施,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政策,发达国家通常采取该类措施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第二类是行政型措施,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现阶段主要采用该类措施控制碳强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碳减排政策正在积极的由行政型向市场型轉变,以期未来在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等多种措施下,形成更长效的减排机制。然而,市场型措施的建立和有效运行需要经历和调整很长一段时期。目前,中国尚未实施碳税政策,全国性碳交易体系已启动,但仍处于体系建设阶段,“十三五”时期的碳强度目标仍通过行政措施分解到各省和各行业来实现。
第二层,模拟碳减排目标约束的政策影响。碳减排约束会传导为对能源供给和消费的约束,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系统,众多学者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模拟碳减排政策的影响。张友国[3]、周县华[4]等人对碳强度约束和总量约束进行比较,认为碳强度约束更适合中国的碳排放控制。林伯强[5-7]、张友国[8]等人认为碳强度目标约束对煤炭消费和碳排放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但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碳密集部门所受到的冲击较大。Dai[9]、Yuan[10]、刘小敏[11]等人模拟得出2020年中国的碳强度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张晓娣[12]、范庆泉[13]等人更多关注社会福利的变化,认为碳强度约束使社会福利的损失较小。
另外,由于中国各省碳强度目标约束不同,Zhang[14]认为各省受到的经济影响差异很大,Springmann[15]认为碳排放有从中国东部省份向西部省份转移的现象。
第三层,影响碳减排效果的因素探讨。在以上碳减排目标约束的模拟中,有三类因素显著影响碳减排效果:第一类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Dai[9]、何建坤[16]等人认为碳强度的下降速度取决于能源强度下降速度和能源排放因子下降速度的叠加,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可以有效降低电力对应的排放因子,使碳排放的降幅超过能源消费的降幅。第二类是技术进步。Wang[17]、Li[18]等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强度,这是实现碳强度目标的重要保证。第三类是碳税政策的合理设置。张晓娣[12]、娄峰[19]等人认为在碳税政策制定中,若政府保持税收中性,将所得碳税收入返还给企业和居民,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双重红利”。endprint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发现碳强度约束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存在两个特点;①研究重点关注碳税和碳交易情景下是否能够实现中国碳强度目标,并不关注行政型减排措施的影响。②研究重点关注碳减排政策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而对居民福利层面关注很少,且与居民相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模拟碳税政策下“双重红利”是否實现,不探讨行政型减排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冲击,也不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差异。中国通过行政型措施约束碳强度,会对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消费结构产生何种影响?以上文献并未给出答案。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将研究聚焦于行政型碳强度目标约束,即假设2012—2030年,中国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通过行政型措施实施碳强度目标约束,并实现非化石能源比重的增长目标,利用动态CGE模型,评估城乡居民的福利变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消费、碳排放等变化情况。
2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机理
碳强度目标约束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进而使居民福利发生变化,该过程可以从供给和消费需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碳强度约束和碳排放总量约束是不同的,碳强度约束允许碳排放随着经济总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就经济增长而言,众多学者和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10—20年将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在预测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可将碳强度约束转化为碳排放总量约束(见图1)。
从供给角度来看,碳强度目标对生产者的生产决策产生约束,调整能源供给,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束,居民福利受到影响。其影响过程为:①行政型碳减排,是将碳强度目标分解到各省和各行业,使生产者进行生产决策时,将其作为生产约束,在成本最小化条件下制定生产方案;其中,能源生产者在碳强度约束下,预测未来市场的能源需求量,选择成本最小的供应方式,使部分能源供给减少。②由于各能源的排放因子不同,碳强度约束对排放因子较大的能源(如煤炭)产生的约束也较强;而随着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清洁电力供应不断增加。③在中国工业化阶段,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价格对能源需求的影响不大,因此能源供给的变化会助推部分能源价格上涨(主要是碳排放因子较大的化石能源),使能源投入较多的生产部门增加生产成本,影响这类部门的生产决策;因此,碳强度约束会对应理论上的最优能源结构,该能源结构下,生产部门对化石能源的消费减少,特别是对煤炭的依赖度下降,使碳排放得到有效控制。④由于包括能源商品在内的各种商品价格和供给量都会发生变化,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束,使居民福利受到影响。
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碳强度约束会从消费成本和消费习惯这两个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①就消费成本而言,一方面,由于碳强度约束使部分能源价格上升,增加了居民能源消费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能源投入较多的生产部门所提供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居民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调整能源商品和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形成最优的商品消费结构。②就消费习惯而言,为配合碳强度约束,政府会不断推广和普及低碳消费观念,使居民的低碳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在生活中节约能源和更多选择清洁能源。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的模型构建中,暂未加入居民主动改变消费习惯的因素。
3模型构建与情景设计
3.1SAM表的编制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42部门基本流量表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对部门适当合并,最终编制出2012年中国宏观SAM表,以及细分31个部门的微观SAM表。由于数据来源不一,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使SAM表行列加总不相等,因此本文采取交叉熵法(CE法),借助GAMS软件对SAM表做平衡处理,以平衡后的SAM表作为CGE模型建立的基础。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不涉及中国港澳台地区。
3.2动态CGE模型设计
本文以张欣[20]的CGE经济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生产模块、贸易模块、国内经济主体模块、能源-碳排放模块、动态机制模块和宏观闭合模块在内的六大模块。模型中的各种替代弹性系数在参考国内外同类文献后做适当调整。因篇幅所限,以下给出居民主体模块、能源-碳排放模块、动态机制模块的方程形式,其他模块的方程均在张欣的模型基础上做小幅改动,未详细列出。
3.2.1生产模块的设计
为了体现各能源之间的可替代性,生产模块采用六层嵌套的结构(见图1)。其中,中间投入部分仅包含26个非能源部门,采用列昂剔夫函数形成中间投入。形成国内总产出的其他各层嵌套均采用不变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
3.2.2贸易模块的设计
贸易模块体现了国内总产出与国外部门在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替代关系。其中,国内总产出以CET(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转换函数形式分配为内产内销商品和出口商品,而内产内销商品和进口商品在阿明顿(Armington)假设基础上形成了国内销售商品。
3.2.3国内经济主体模块的设计
国内经济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该模块包含三
个假定:①居民的效用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②政府收入由非税收入、税收和国外对政府的转移支付共同构成。③投资总额和政府支出由外生给定。其中,居
民的收入和消费方程分别为:
YHh=WL·shifh-l·QLStot+WK·shifh-k·QKStot+transfh-ent+transfh-gov+transfh-row(1)
PQc·QHch=shrhch·mpch·(1-tih)·YHh(2)
式(1)中,h取HR和HU,分别对应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YHh是居民h的收入,WL和WK分别为劳动力价格和资本价格,shifh-l和shifh-k分别为居民h所占的劳动力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QLStot和QKStot分别是劳动力和资本的总供给,transfh-ent、transfh-gov和transfh-row分别为企业、政府和国外部门对居民h的转移支付。式(2)中,c=1,2,…31表示商品集的31种商品,与生产部门一一对应,但居民仅对包括能源商品在内的24种商品产生消费(见图2)。PQc为商品价格,QHch和shrhch分别是居民h对商品c的消费量和消费份额,mpch和tih分别为居民h的边际消费倾向和个人所得税税率。endprint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可采用希克斯等价性变化(Hichs equivalent variation,EV)进行测算,公式如下:
UHbh=∏c(QHbch)shrhch(3)
UHsh=∏c(QHsch)shrhch(4)
∑cshrhch=1(5)
EV=e(PQbc,UHsh)-e(PQbc,UHbh)
=(UHsh-UHbh)·∏cPQbcshchchshchch(6)
式(3)~(6)中,UHbh和UHsh分别为政策实施前后居民h的效用,QHbch和QHsch分别为政策实施前后居民h对商品c的消费量,PQbc是政策实施前商品c的价格,EV是福利变动的等价性变化量。
3.2.4能源与碳排放模块的设计
在以上CGE模型的构建基础上,需要将能源、碳排放与经济系统关联起来。其中,碳排放的方程如下:
TGHGCO2=∑ce[λce·(∑aQINTce.a+∑hQHce.h)·PQce](7)
式(7)中,TGHCCO2为碳排放总量,ce=coal,crude,prod,gas,ele,分别表示煤炭、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a=1,2,…31表示生产集的31个部门,由于2012年SAM表没有政府能源消费的数据,因此能源消费环节的碳排放仅对应居民主体。QINTce.a和QHce.h分別是a部门生产过程中能源ce的投入量和居民h对能源ce的消费量,PQce是能源ce的销售价格,λce为能源ce的CO2排放系数(以下简称碳排放系数),由于SAM表内的数据是价值量(亿元),因此碳排放系数也需转换为价值型。本文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方法1”,估算出2012年各能源及总的碳排放量,再与SAM表中各能源最终需求总量相除,从而获得价值型碳排放系数(见表1)。
3.2.5动态机制模块和宏观闭合模块的设计
模型的动态机制主要考虑资本要素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并采用递归形式实现动态化。受此影响,CGE模型中所有的内生变量全都增加了时间维度。其中,资本要素积累的递归公式如下:
QKDta=QKDt-1a·(1-ηa)+It-1a(8)
Ita=It-1a·(1+gIa)(9)
QKSttot=∑aQKDta(10)公式(8)~(10)中,QKDta和QKDt-1a分别表示a部门t期和t-1期的资本需求量,t=2012,2013…2030,ηa是各部门资本折旧率,由于各部门生产特点不同,本文采用的各部门折旧率在3%~5%之间。Ita和It-1a分别是各部门t期和t-1期的新增投资,gIa为各部门新增投资增长率,结合产业发展政策,本文采用的各部门新增投资增长率在2%~23%之间。QKSttot是t期的资本总供给,在动态机制中将该指标设置为外生参数。
QLDta=QLDt-1a·(1+gLa)(11)
QLSttot=∑aQLDta(12)
公式(11)~(12)中,QLDta和QLDt-1a分别表示各部门t期和t-1期的劳动力需求量,gLa表示a部门的劳动力增长率,依据中国人口增速和产业发展预期,本文设煤炭和原油部门为0.1%,农业部门为0.25%,其他行业为0.33%,其余部门均为0.3%。QLSttot是t期的劳动力总供给,将该指标在动态机制中设置为外生参数。
αq.ta=αq.t-1a(1+gna)(13)
式(13)表示技术进步逐年增加,其中,αq.ta和αq.t-1a分别为t期和t-1期总产出的技术进步参数,gna为各部门技术进步的增长率,由于中国原油的可采储量相对较低,本文设原油gna的为1%,其他行业设为2.5%,其余部门均设为2%。
在模型的宏观闭合模块设计中,首先,考虑各市场均衡,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衡、商品市场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储蓄与投资平衡;其次,采用新古典主义宏观闭合形式,即资本、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内生决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外生给定,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最后,假设汇率固定。
将以上动态CGE模型作为基准情景,可衡量在没有碳强度目标约束情景下,居民福利等相关指标的发展趋势。
3.3碳强度目标约束的情景设计
为了模拟2012—2030年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的影响,本文将碳强度目标约束转换为各年碳排放约束,并考虑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下电力碳排放系数的变化。相关目标约束推导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各年实际GDP。将2005—2015年作为历史期,2016—2030年作为预测期。首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历史期的GDP,并换算为2005年价格的实际GDP。其次,计算预测期的实际GDP。由于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逐渐转为中高速,在此背景下,以林伯强[6]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以及张友国[8]对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设定为参考,本文设2016—2020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为6%,2021—2030年实际GDP年均增速为5%,以此可确定预测期的实际GDP(见表2)。
第二步,估算历史期碳排放,确定2005年碳强度。首先,估算历史期碳排放数值,即2005年的碳排放为57.456亿t,2015年碳排放为94.839亿t。其次,计算历史期的碳强度。2005年的碳强度为3.067 t/104元,这一数值是中长期碳减排目标约束的参照基础。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公布碳排放数据,但本文估算的历史期各年碳强度下降幅度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历年报告中的相关指标基本一致,因此估算结果是可信的。再次,计算历史期碳强度的累计增长率,得到2015年的碳强度比2005年累计下降33.863%。endprint
第三步,计算预测期2005年价格的碳强度。首先,确定预测期各年碳强度的累计增长率,设碳强度匀速下降,即碳强度累计增长率由2016年的-33.863%匀速下降至2020年的-40.001%,再匀速下降至2030年的-60.002%。其次,依据碳强度下降率,推算预测期碳强度数值,可得2030年的碳强度为1.227 t/104元。
第四步,推算预测期碳排放的约束值。依据预测期2005年价格碳强度和实际GDP,推算2016—2030年碳排放的约束值,可得碳排放由2016年的98.785亿t逐渐上升至2030年的123.846亿t。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当各年碳排放不超过该约束值,则碳强度的降幅符合目标约束。本文将碳排放约束值作为目标情景的外生变量。
第五步,计算预测期电力的价值型碳排放系数。非化石能源主要用于电力生产(例如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随着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提高,电力的碳排放系数逐渐下降,即生产等量电力而产生的碳排放逐渐减少。依据电力消费预测和碳排放约束,可得出电力的碳排放系数由2012年的8.631 t/104元,逐渐下降到2030年的4.151 t/104元,并将该系列数值作为参数加入动态CGE模型。
在基准情景的模型构建上,对公式(3)进行改动,并添加时间维度,形成目标情景公式:
aim_TGHGtCO2=∑ce[λtce′·(∑aQINTtce.a+∑hQHtce.h)·PQtce](14)
式(14)中,aim_TGHGtCO2是t期碳排放的约束值,即取表2中碳排放列2012—2030年的数值。λtce′是能源ce在t
期的碳排放系数,其中,煤炭、原煤、成品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不随时间变化,而电力t期的碳排放系数取表2中的动态值。QINTtce.a、QHtce.h和PQtce分别是t期ce能源的生产投入数量、居民h的消费数量和销售价格。将模型调整为目标约束情景,可分析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福利等相关指标变动情况。
4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动态CGE模型设置以居民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通过GAMS23.8.2软件的PATHNLP求解器对模型系统进行计算,分别模拟2012—2030年基准情景和目标约束情景,可获得居民福利等相关指标变动情况。
4.1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4.1.1基准情景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相关指标的预测
在基准情景下,2012—2030年居民的收入、生活总消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稳步增长(见表3)。居民收入增长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前提,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几乎同步增长,年均增速分别为5.002%和5.006%,到2030年两个居民群体的收入分别达到66.749和17.28×1012元,在预测期内,城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之比稳定在3.86,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不变。就居民生活总消费而言,城乡居民的消费都稳定增长,且消费增速略高于收入的增速。其中,农村居民的年均增速比城镇居民高0.187%,这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有关。王晓华[21]等人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农村居民仍以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为主,即食品、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消费比重较高,而城镇居民已具有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特点,即家庭电器设备、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消费比重较高,但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消费升级(即由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过渡到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空间很大,因此基准情景预测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速略高于城镇居民。
依据李艳梅[22]对居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划分,本文仅研究直接能源消费和由其产生的碳排放,即居民用于炊事、取暖、电器及私家车等活动而直接消费能源商品并产生的碳排放。表3顯示居民的能源消费持续增加,且增速略高于生活总消费的增速,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年均分别上涨5.276%和5.916%,到2030年,两个居民群体的能源消费价值量将分别达到1.448和0.288×1012元。由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带来的碳排放年均增速分别为5.286%和5.883%,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碳排放将分别达到10.247和2.295亿t,可以看出,若没有碳强度约束,居民生活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会快速增长,且农村居民的碳排放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居民生活消费引起的气候变化压力不容忽视。
4.1.2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相关指标的变动
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下,居民的收入、消费及碳排放等指标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动如表4所示。就居民收入而言,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动很小,就生活总消费而言,居民消费在2021年前小幅下降,2022年后略有上升,这是由于生产部门,将碳强度目标作为生产约束,使部分能源(主要指化石能源)供给减少而推动价格上升,能源投入密集的其他生产部门也增加生产成本。因此,能源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供给和价格都发生变化,影响到居民消费束,导致居民生活总消费略有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逐渐调整消费结构,在预测期后半段,居民消费小幅回升。但农村居民消费降幅略高于城镇居民,这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有关,城镇居民对商品的选择更多元,且对服务类商品的消费比重更高,因此所受影响略小一些。
碳强度约束对居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较强,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下降幅度超过城镇居民。其中,到2030年,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比基准情景下降了12.026%,碳排放也下降36.433%。与之相比,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下降幅度更大,多数年份的能源消费降幅都超过10%,到2030年,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下降了16.613%,碳排放下降了56.173%。以上特征的原因有:①碳排放的降幅超过能源消费的降幅,是由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带来的叠加效应。②城乡之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变动的差异,与城乡能源供给、消费模式和城乡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城镇的能源供给和消费模式相对集中、多元和先进,由此产生了规模效益和集约效益,能源成本相对较低,另外,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能源价格上升对其能源消费的影响并不大。而对农村居民来说,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户使用电力的比重不断增加,且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持续下降,因此农村居民碳排放endprint
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这符合Hosier[23]的“能源阶梯”(Energy Ladder)理论,即农村能源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户主要依赖生物质能源;第二阶段,随着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农户转向使用煤和木炭等过度型能源;第三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户更多的使用电力。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已处于“能源阶梯”的第三阶段,电力消费增加对降低农村碳排放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的能源供给比较单一和分散,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的能源效率提高空间很大,这使得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下降的空间也更大。
4.2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在基准情景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有显著差异(见图2)。在基本生活需求消费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显著高于城镇居民;在发展与享受的消费方面,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以上差异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密切相关。其中,城乡居民消费比重最高的商品是其他行业(包括金融、房地产、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公共管理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子部门),城镇和农村居民对该商品的消费比重分别占总消费的34.5%和28.7%。农村居民消费比重排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食品和烟草(22.2%)、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业(17.2%),其消费比重均显著高于城镇居民。与食品相关的这两类商品的消费比重之和,相当于依据SAM表计算的恩格尔系数,即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其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高于城镇居民。除以上三类商品外,城乡居民对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的消费比重都超过5%。就能源消费而言,居民消费比重最高的是电力,均占城乡居民消费的1.4%;其次,城镇和农村居民对成品油的消费比重分别为1.3%和0.4%,对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分别为0.8%和0.2%;再次,城镇和农村居民对煤炭消费的比重分别仅为0.04%和0.02%,可见居民生活消费中对煤炭的需求极少。
在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都发生变化,其变化如图3所示。
就各商品消费的总体变动而言:①消费比重变化较大
的商品恰好对应基准情景下消费比重较低的商品,这是由于基准情景下消费比重较高的商品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其效用的权重较大,即使这类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其消费比重也保持稳定。与之相反,基准情景下消费比重较低的部门,其效用的权重较小,居民可以充分调整对这类商品的消费结构,以满足效用最大化。②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消费大幅下降,而电力消费显著上升。由供给角度分析可知,碳强度约束使部分能源价格上升,提高了居民获得该类能源的消费成本,致使需求量大幅降低;而电力所受的影响较小,且对其他能源的替代性较强,因此居民增加对电力的消费以满足能源需求。③资本密集型商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和仪器仪表等)在生产中的能源投入较小,所受碳强度约束的影响也较小,因此居民增加了对该类商品的需求。
就城乡居民消费变动的差异而言:①城镇与农村居民对煤炭、成品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变动差异较大。首先,碳强度约束对煤炭消费的抑制作用最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煤炭消费分别下降了81.85%和79.53%,这是由于居民对煤炭的需求极少,且煤炭在生活中的炊事和取暖功能容易被其他能源替代,因此煤炭的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高,其价格上涨会显著抑制居民对煤炭的消费。其次,农村居民对成品油的消费降幅(71.01%)远超城镇居民(19.17%),这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有关。《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2万元和1.14万元,在动态CGE模型的预测期,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不变,因此,成品油的互补品——私家车对农村居民而言更接近奢侈品,该能源对农村居民的需求价格弹性远高于城镇居民,碳强度约束使农
村居民的成品油消费大幅下降。再次,农村居民对天然气的消费降幅(39.9%)也远高于城镇居民(4.57%),这与农村的天然气普及率过低有关。2015年城镇居民天然气消费达到358.38亿m3,而农村均仅为1.43亿m3,由于普及率很低,
使农村居民对天然气的消费习惯还不稳定,天然气价格上涨会使这些农村居民转而使用电力或生物质能源,因此农村居民天然气消费降幅超过城镇居民。②农村居民电力消费涨幅(24.87%)高于城镇居民(10.91%)。由于非化石能源比重增加,电力的碳排放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可增加电力消费来满足能源需求;基于“能源阶梯”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也使其电力消费大幅上升。③农村居民对部分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消费增幅高于城镇居民,这一差距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比重较高有关。2015年的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分别占各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43%和11.14%,在消费中,农村居民也更倾向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消费支出,以期待增加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对专用设备(包括食品和饲料专用设备、农林牧渔专用设备等)的消费上涨了28.28%,而城镇居民对该部门的消费仅上涨了5.52%。此外,农村居民对通用設备、金属制品(包括搪瓷制品、金属制日用品等)、仪表仪器(包括钟表与计时仪器、眼镜等)和非金属矿物制品(包括砖瓦、石材、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等)的消费增幅也略高于城镇居民。
4.3碳强度约束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受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居民福利水平也发生变化。根据式(6)得到的各年城乡居民福利等价性变化EV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在碳强度约束下,城乡民福利均有小幅下降。由于动态CGE模型的拟合结果在居
不同年份产生振荡,城镇和农村EV的波动较大。为了厘清城乡居民福利变动的规律,消除模拟数据震荡的影响,分别对城镇和农村EV进行线性拟合,可看出农村居民EV趋势线的下降幅度超过城镇居民,2012—2030年间,农村居民EV每年下降139.57个效用单位,对应效用水平每年下降0.121%,而城镇居民EV每年下降87.343个效用单位,对应效用水平每年下降0.023%。可见碳强度约束对农村居民福利的负效应超过城镇居民。虽然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不断提升,其消费结构也发生变化,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升级相对迟缓,碳强度约束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较大。endprint
5结论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包含31个部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动态CGE模型,并将碳强度约束和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作为目标政策,模拟中国在2012—2030年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福利及相关指标受到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碳强度约束对居民收入无显著影响,居民生活总消费小幅下降,但不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冲击。其中,农村居民生活总消费的降幅略高于城镇居民。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特征下,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特别是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增加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和精准扶贫等措施,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努力降低碳强度约束对农村居民的负向影响。
(2)碳强度约束使居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大幅下降,到2030年,城乡居民的能源消费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了12.026%和16.613%,城乡居民的碳排放分别下降了36.433%和56.173%。从供给角度而言,碳强度约束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使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从消费需求而言,化石能源的价格上升抑制居民能源消费,促使电力消费增加。为保障居民能源需求,首先,政府应增加清洁能源供给,特别是继续扩大农村地区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推广普及;其次,应该积极引导居民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重点引导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的消费,增加对农村居民户用沼气建设、太阳能设备购置、节能家电产品购置的补贴,减少碳减排政策对农村居民的约束。
(3)碳强度约束使居民对部分资本密集商品的消费小幅增加。其中,农村居民对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等商品的消费涨幅超过城镇居民,这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居民对生产经营性消费的投入较多。从长远来看,要不断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民收入增幅不断上升的前提下,引导其消费升级,降低基本生活消费和生产经营消费的比重。
(4)碳强度约束使城乡居民福利水平略有下降。其中,农村居民福利的降幅超过城镇居民。2012—2030年间,农村居民EV每年下降139.57个效用单位,对应的效用水平年均下降0.121%,而城镇居民EV每年下降87.343个效用单位,对应的效用水平年均下降0.023%。但总体而言,碳强度约束下,城乡居民的福利降幅较小,不
会对居民生活产生强烈的负向冲击,但政府仍需完善农村集约和多元的能源供给,降低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农村居民福利的负向影响。
(编辑:于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张友国.总量还是强度:碳减排目标之争[J].学术研究,2015(9):76-80,122.[ZHANG Youguo. Total carbon emission or carbon intensity: the controversy about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J]. Academic research, 2015(9): 76-80,122.]
[2]FISCHER C, SPRINGBORN M. Emissions targets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intensity targets versus caps or tax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1, 62(3): 352-366.
[3]張友国.碳强度与总量约束的绩效比较: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3(7):138-160.[ZHANG Youguo. Comparison of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and total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 a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3(7): 138-160.]
[4]周县华,范庆泉.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与行业减排路径的优化设计[J].世界经济,2016(7):168-192.[ZHOU Xianhua, FAN Qingquan. Mechanism of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industrie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6(7): 168-192.]
[5]林伯强,姚昕,刘希颖.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战略调整[J].中国社会科学,2010(1):58-71,222.[LIN Boqiang, YAO Xin, LIU Xiying.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Chinas energy use structure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saving and carbon emissionreducing initiatives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1): 58-71,222.]
[6]林伯强,孙传旺.如何在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前提下完成碳减排目标[J].中国社会科学,2011(1):64-76,221.[LIN Boqiang, SUN Chuanwang. How can China achieve it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while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1): 64-76,221.]endprint
[7]林伯强,李江龙.环境治理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转变——基于煤炭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9):84-107,205.[LIN Boqiang, LI Jiangl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nergy structure und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straints: a peak value analysis of coal and carbon dioxid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9): 84-107,205.]
[8]张友国,郑玉歆.碳强度约束的宏观效应和结构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4(6):57-69.[ZHANG Youguo, ZHENG Yuxin. Macro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of 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6): 57-69.]
[9]DAI H, MASUI T, MATSUOKA Y, et al. Assessment of Chinas climate commitment and nonfossil energy plan towards 2020 using hybrid AIM/CGE model[J]. Energy policy, 2011, 39(5): 2875-2887.
[10]YUAN J, HOU Y, XU M. Chinas 2020 carbon intensity target: consistency, implement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2, 16 (7):4970-4981.
[11]刘小敏,付加锋.基于CGE模型的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目标分析[J].资源科学,2011, 33(4):634-639.[LIU Xiaomin, FU Jiafeng. Analysis of the scenarios of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in 2020 based on the CGE model[J]. Resources science, 2011, 33(4): 634-639.]
[12]张晓娣,刘学悦.征收碳税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研究——基与OLGCGE模型的增长及福利效应分析[J].中國工业经济,2015(3):18-30.[ZHANG Xiaodi, LIU Xueyue. Study on carbon taxation and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analyses base on OLGCGE model[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3): 18-30.]
[13]范庆泉,周县华,刘净然.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 25(6):62-71.[FAN Qingquan, ZHOU Xianhua, LIU Jingran. Double dividend of carbon intensity: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6): 62-71.]
[14]ZHANG D, RAUSCH S, KARPLUS V J, et al. Quantifying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CO2 intensity targets in China[J]. Energy economics, 2013, 40(2): 687-701.
[15]SPRINGMANN M, ZHANG D, KARPLUS V J. Consumptionbased adjustment of emissionsintensity targets: an economic analysis for Chinas provinces [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economics, 2015, 61(4): 615-640.
[16]何建坤.我国自主减排目标与低碳发展之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25(6):122-129,157.[HE Jiankun. Chinas voluntary mitigation target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pathway [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 25(6): 122-129, 157.]
[17]WANG K, WANG C, CHEN J.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different Chinese climate policy options based on a CGE model incorporating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Energy policy, 2009, 37(8): 2930-2940.endprint
[18]LI A J,LI Z.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or energy intensity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C]//Proceedings of the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ergy,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lausthalZellerfeld:Trans Tech Publications,2012:347-353,1093-1097.
[19]婁峰.碳税征收对我国宏观经济及碳减排影响的模拟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10):84-96,109.[LOU Feng.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carbon tax impact on Chinas macro economy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4(10): 84-96,109.]
[20]张欣.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原理与编程[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04-216.[ZHANG Xi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programming of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M]. Shanghai: Gezhi Press, 2010: 204-216.]
[21]王小华,温涛.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及结构演化的差异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10):90-107.[WANG Xiaohua, WEN Tao.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ces about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5(10): 90-107.]
[22]李艳梅,杨涛.城乡家庭直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变化的分析与比较[J].资源科学,2013, 35(1):115-124.[LI Yanmei, YANG Tao.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direc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J].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1): 115-124.]
[23]HOSIER R H. Energy ladder in developing nations [J]. Encyclopedia of energy, 2004(2): 423-435.
AbstractChinese government pledged to cut its CO2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by 60% to 65% from 2005 levels by 2030. Administrativ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based on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re one of Chinas major means of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o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is a significant content of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 design. This paper builds a dynamic CGE model of economyenergy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31 sectors to simulate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as well as CO2 emiss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nd increased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y from 2012 to 2030. R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① Theres no obvious chang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the general living consumption slightly drops. The decrease of rural residents living consump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② Resident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 experience a dramatic fall with greater decrease on the part of rural residents. ③ A sharp decline is shown in the consumption of coal, refined oil and natural gas; an obvious increase can be witnessed in 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ome capitalintensive sectors goes through a minor increase. The coal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ecline in consumption of refined oil and natural gas of rural residents far exceeds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Besides, their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of electric power, special purpose machinery, general purpose machinery and metal products surpasses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④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brings about a slight drop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but its a small range. The fall in the Hicks equivalent vari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rst,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econd, the policy make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lfare decline but it wont have strong impact on residents life; third, rural residents receive greater adverse influences on energy consumption than urban residents do.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erly increase the transfer payment for rural residents on the basis of carbon intensity restriction,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esid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clean energy for the rural area, and increase subsidies for rural residents using clean energy, thus reducing negative influences of the climate change policy over rural residents.
Key wordscarbon intensity constraint;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structure; welfare of residents; dynamic CGE model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