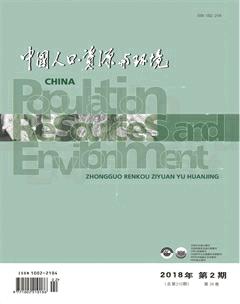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马丽梅+史丹+裴庆冰
摘要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关键词能源转型;产业革命;可再生能源;中等收入陷阱;低碳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2-0008-11DOI:10.12062/cpre.20170916
当前,中国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而与此同时,未来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十年,是实现工业化以及“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期,也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阶段。作为能源大国,中国的能源转型备受世界关注,国内外学者以及能源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归纳总结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方案,该方案的核心思路是从即刻起不断实现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约达到20%,直至2050年这一比重会达到60%以上,而2050年电力供应的80%也将来自可再生能源[1-2]。二是以煤为主的能源发展方案,到2050年煤炭仍然是中国的主导能源,化石能源比重约占60%,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如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CCUS等)应成为中国重点关注的技术领域[3]。历史经验表明,工业革命与能源革命几乎同时发生,能源革命能够推进工业革命以及生产力的极大提高[4],而现有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方案大多是基于气候变化的视角,往往忽视了中国的能源禀赋特征,特别是近10年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对经济的负向影响进行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另一方面,以煤为主的能源转型方案相对过于保守,忽视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对未来经济可能的“引擎”作用。中国的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基于KAYA指数分解,通过国际经验对比以及CGE实证模拟,提出中国能源转型可行的目标方案,并特别针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进行探讨。
1文献综述
回顾世界能源转型历史,至今人类已经历了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发生时间为19世纪初,是由生物质能(如秸秆、木柴等)向煤炭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发生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表现为石油对煤炭的替代,后半段发生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表现为天然气以及核电的应用增加。当前,第三次能源转型已经开始发生,可再生能源成为重要的目标能源,不仅影响着能源体系的发展,同样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结能源转型的特征,有学者形象地形容,人类的能源转型经历了由“固体”到“液体”,再由“液体”向“气体”的转型,而每一次能源转型均表现出“降碳化”特征,即替代能源中碳元素的减少,氢元素的增加,更确切的形容能源转型,可以称之为能源的低碳转型。
关于能源转型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分析与讨论。在量化研究上,现有研究将侧重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能源转型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能源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体兰等[5]研究了中国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影响因素,他们认为,GDP和电价对于可再生能源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电价补贴却作用甚微。邵庆龙和饶蕾[6]基于OECD国家的样本数据探讨可再生能源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原油价格、研发投入以及积极的政策是影响可再生能源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装机容量影响并不大。Duro和Padilla[7]依据KAYA等式对四个不同年份的人均碳排放Theil指数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国家能源转型进度及碳排放的差异性主要由人均收入差异造成。冯相昭和邹骥[8]利用修改后的Kaya恒等式对1971—2005年中国的CO2排放进行无残差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CO2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的低碳转型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有一部分研究,将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長相结合,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大多数学者提出的观点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而Ocal和Aslan[9]指出,可再生能源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Apergis和Salim[10]则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影响要区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研究讨论。齐绍洲和李杨[11]基于欧盟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均GDP较高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人均GDP较低成员国呈现出负向冲击。这些文献主要运用计量模型或指数分解来探讨能源转型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主要运用大样本的跨国面板数据,大多针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的能源转型路径进行分析,且对能源转型的具体路径并未呈现明确的表述。endprint
而对于中国国家转型路径的研究以及如何转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能源经济研究学者及部分国外研究机构。NBR(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4年12月的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煤炭消费很可能达到峰值,碳税的实施将面临较大阻碍而被搁浅。林伯强和李江龙[12]从环境治理约束视角提出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最优方案,他们提出在严格的环境治理下,到2020年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比重约为57.7%、18%、9.0%、15.3%,煤炭与石油的比重相比于在一般环境治理情况下低5.9%,天然气、非化石能源分别高出0.7%、0.3%。杜祥琬等[13-14]根据国际经验,从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耦合关系视角进行分析,得到2030年将成为煤炭、石油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转折点,2020年以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将呈现“解耦”趋势,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人均能源消费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张晓娣和刘学悦[15]基于OLG-CGE模型得到,如中国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35%(2050年),短期内将抑制消费、投资及产出的增长,这种抑制作用直到2035年才会出现转折。纵观以上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及能源转型带来的影响,忽视了能源转型路径研究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本文尝试从该视角入手,首先研究能源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总结能源转型的国际经验与规律,在此基礎上,探讨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即实现转型方案在短期内所带来的成本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包容,在长期又能够推进生产力提升,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能源低碳转型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现状
2.1国际能源低碳转型特征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不断提高,年均增长率约为2%~3%,至2013年,美国人均GDP接近46 000美元、法国约为34 000美元、其他三国处于37 000~38 000美元之间[14]。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均能源消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例,如图1所示,变化特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升期(1960—198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均GDP呈现同向变化,均呈上升态势;第二阶段为稳定期(1980—2005年),虽然人均GDP持续增长,但人均二氧化碳却维持在稳定水平,并未呈现大幅上升态势;第三阶段为下降期(2005年至今),尽管人均GDP不断上升,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呈现下降趋势。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呈现同样的变动趋势。
根据人均能源消费量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将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变动模式总结为三种类型:“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日本模式”。其中,“美国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加拿大等国家也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其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耗以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均处于较高水平;“欧洲模式”以德国、英国以及法国为代表,虽与“美国模式”的变动趋势一致,但各阶段的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费量以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均低于美国;“日本模式”以日本为代表,它与欧洲模式较为接近,各人均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其变动趋势与以上两种模式存在区别,实际上在本文界定的“稳定期”,日本仍然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增长趋势。各模式的具体特征可通过KAYA指数进行详细解析。
2.2基于KAYA指数的特征解析
KAYA指数是目前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的重要方法,它将二氧化碳排放(或能源消费)与人口、经济发展以及能源技术水平建立联系,用以辨别碳排放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CyCx=PyPx·[(G/P)y/(G/P)x]·
[(C/G)y/(C/G)x]
(1)
其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P表示人口,G代表GDP,x、y代表不同的年份,二氧化碳在某一时间点的相对变化可以分解人口、人均GDP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相对变化,由于各驱动因素间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关系,驱动因素的变化量,如
ΔPyPx
不能用以解释二氧化碳的变化量ΔCyCx。根据(1)式,某一年份i的碳排放量驱动因素即可分解为:
Ci=Pi·(Gi/Pi)·(Ci/Gi)
(2)
(2)式可进一步扩展为:
Ci=Pi·(Gi/Pi)·(ECi/Gi)·(Ci/ECi)
(3)
其中,ECi表示第i年的能源消费总量,Gi/Pi为人均GDP,代表一国的经济水平,ECi/Gi为能源强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及其技术水平,Ci/ECi代表能源消耗的强度。为研究人均二氧化碳的驱动因素,(3)式可转换为:
Ci/Pi=(Gi/Pi)·(ECi/Gi)·(Ci/ECi)(4)
可以看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可分解为人均GDP、GDP的能源强度以及能源消费的碳强度。Yamaji 等[16]指出,KAYA指数所分解的驱动因素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但它可用于辨别分析四个驱动因素之间哪一种占主导地位,例如,当前,从全球看,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以及人均GDP的增长,而相对来说,能源强度及碳强度的改进相对缓慢,其中,能源强度更多地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动,而碳强度则更多地反映了能源结构的变动特征。图2给出了按(3)式计算的主要国家碳排放的KAYA分解。图2中令1971年为1,以实现对各国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观察[17]。由图2可以看到,中国的KAYA分解与各国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根据KAYA指数反映的经济技术特性,本文从人均GDP、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碳强度(能源结构)三个视角进行跨国比较,以总结各国能源转型模式的特征。
2.2.1基于人均GDP的跨国比较endprint
图2显示,人均GDP仍然是驱动各国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通过真实值的横向对比发现,美国的人均GDP在各时期处于较高水平,日本、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人均GDP水平较为接近,整体上低于美国。从变动趋势上看,各国对碳排放的驱动相对平缓,但日本在人均二氧化碳进入“稳定期”(1985—1995年)时,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平均增速约为10%,1995年之后,人均GDP增速明显放缓,呈波动增长态势。而中国当前与这一时期较为相似,人均GDP从2005年开始呈现出较高速的增长态势,2005—2011年平均增速约为15.6%,2011年以后呈现放缓趋势。
2.2.2基于能源强度的跨国比较
本文所划分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由以上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经济发展初期,人均GDP的持续增长超出了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改进幅度,因此,人均二氧化碳呈现“上升期”,随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缓慢调整,以及技术水平的进步,能源强度、碳强度的改进幅度逐渐与人均GDP达到平衡,故人均二氧化碳进入“稳定期”,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能源结构的低碳调整,人均二氧化碳逐渐进入“下降期”。产业结构的变动虽然较为缓慢,但它是决定能源强度的重要因素,
故此成为驱动碳排放的关键因素。这里按照“上升期”、
“稳定期”和“下降期”对产业结构进行跨国比较分析。
美国在进入“稳定期”的1980年,其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65%,远超过第二产业,即便是在1950年,美国的第三产业比重也已达到了54.5%,约超出第二产业17个百分点。而中国2013年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0%、43.9%、46.1%,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德国在进入“稳定期”的1980年,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处在相当水平,1970—1990年,德国的产业结构进入迅速调整期,三大产业结构从1970年的3.9%、57.6%、38.7%变动到1993年的1.1%、36.4%、62.5%[18],就产业结构而论,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水平相当于德国1975年左右的水平,但从调整趋势上看,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远低于德国,中国第二产业比重近30年来一直维持在45%左右,第三产业结构变动虽然较第二产业快,但其增长速度仍低于德国;日本在进入“稳定期”的1980年,其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2%、36%、52%,1980—1985年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期,虽然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变化不大,但制造业内部正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化工制品、钢铁金属制品产业占比有所下降,机械机器制造占比不断提高。这一时期,信息产业化引导日本其他产业向高技术化发展,使得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并且成为之后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1986—1990年,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制造业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主要为第一产业占比的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到1990年,
同时计算了能源消费的KAYA分解,其变动趋势与碳排放基本相同。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计算整理。中国的能源数据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等省区数据。
三次产业结构约为6%、40%、54%。
总结以上三种模式产业结构变化特点,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在进入平台期之前就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德国模式虽然在平台期起点(1980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及美国,但在接下来的10年却发生了较大的发展,日本模式在1980年正经历产业结构的调整期。相较而言,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像德国在1970—1990年那样经历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也不具备美国的“高起点”产业结构,当前的产业结构变动与日本1986年后所经历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动较为接近。
从表1中可以看到,1973—1985年是日本制造业结构调整时期,表现为制造业产业比重基本维持不变,内部结构逐步向知识密集产业转变,维持在40%左右[19],中国的
1993—2005年基本与日本的这一时期接近,第二产业维持在47%左右;1986—2000年,日本产业结构表现为结构转换期,农业缓慢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这一时期;2001年至今,日本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农业基本不变,第二产业缓慢下降,第三产业缓慢上升的趋势,与上一时期比较,各产业比重的变化速度相对较慢。显然,中国尚未进入或刚刚进入这一时期,第一、二产业比重仍存在下降空间。
2.2.3基于碳强度的跨国比较
从数值上看,“美国模式”处于较高水平。在1970—1985年,三种模式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出快速下降态势,1990年以后下降幅度处于较为平缓状态。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方面與国家技术水平相关,
另一方面间接地反映了一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的比重。1980年以前,主要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呈
现下降趋势主要取决于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比由1970年代的25%提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40%。而进入“稳定期”,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的能源结构变动特征。
由表2可以看到,天然气和核能是发达国家实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进入稳定期的关键能源。“稳定期”期间,“美国模式”下各种清洁能源的比重未发生明显变化,能效的不断提高是其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欧洲模式”下,各清洁能源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变化,英国天然气、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均有上升,分别由20%、5%、0.4%提升至37%、8%、2%,德国主要依靠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分别提升了6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其核能比重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法国却主要依靠核能实现了低碳化,使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以上5国的最低水平;“日本模式”主要依靠核能,其次是天然气,比重分别提升了10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
进入“下降期”,“美国模式”中天然气仍发挥着重要endprint
作用,比重提升至30%,而核能及可再生能源虽有增长,
但其占比仍未得到显著提高;“欧洲模式”则呈现了“去核化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趋势,天然气占比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日本模式”虽然在2010年福岛核事故之后转向可再生能源发展,但在2013年,日本重新启动了核电站建设计划,预计未来日本的核电比重或将大幅度提升。
2.3国际经验与中国问题
表3总结了以上三种模式的要素特征。综合比较各国发展模式,其中,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是决定人均碳排放的两个重要变量。从产业结构看,各国在进入稳定期的前10年(稳定期以1980年为节点),第三产业占比均达到了50%以上,美国、法国均达到了60%,日本约为55%,虽然德国此时未达到50%,正如上文所述,其以较快的速度迅速实现了调整,到1975年,其第三产业结构已经接近50%。可以说,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必备条件,在产业结构相对优化的背景下,各国得以成功的完成了第二次能源转型,即天然气和核能对煤炭、石油的替代。在经历约25年的稳定阶段后,各国通过不同的能源转型方式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呈现下降趋势。“美国模式”注重于增加天然气的比重,从2005年的22%逐步增至2013年的接近30%,而“欧洲模式”则倾向于可再生能源,“日本模式”主要借力于核能的发展,在2010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前,其核能比重正呈持续增长态势,并在近年重新启动了发展核能的计划。
根据国际经验,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接近50%,具备了能源转型的经济结构基础,是中国能源转型的有利时机。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当前的人均GDP相当于各国1975—1980年的水平,具备了能源转型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经济技术水平看,中国当前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却与各国存在较大差距,相当于1980年,美国的2倍,日本的4倍,德国的2.5倍,除能源结构外,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还相对落后,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由以上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很可能由“上升期”进入“稳定期”阶段,按照国际经验约经历25年左右,进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期”,但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第三次能源转型的到来,这一时间段可能大大缩短,中国很可能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期”。此外,从上文分析看到,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变动及人均GDP增长与日本在“稳定期”(1985—1995年)的变动趋势较为接近,而当前的能源结构与日本1980年也较为接近(化石能源占比为90%,天然气为6%),这也又一次印证了中国目前已具备能源转型的基础,可以说,不仅仅是环境压力倒逼了中国的能源转型,实际上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决定了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而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下文将参考各国能源低碳转型模式进行模拟,探讨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最优路径。
3中国能源转型路径模拟——基于CGE的分析
3.1情景设计
中国工程院课题组提出了未来能源转型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石油,到2050年仍将在中国能源消费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指导思想是依据科学产能和用能对能源消费总量进行控制,鼓励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如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CCUS
等),注重节能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本文将该情景设定为情景1,该方案与“美国模式”较为接近,但与之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特性以及能源安全的考虑,中国
不可能大幅提高天然气的比重,该方案选择依靠化石能源的发展路径必须依靠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以及能效的提升。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提出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路线图,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取代化石能源成为支撑能源系统的主要能源,并将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本文将其设定为情景2,实际上该方案是借鉴了“欧洲模式”,走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借鉴“日本模式”,本文设定情景 3,发展核能的能源转型路径,根据以上三种情形的设定研究其对碳减排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情景1(S1):化石能源自身优化路径。到2025年,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占比为10%,化石能源达到75%,到2050年,实现天然气占15%,化石能源达到48%。
情景2(S2):可再生能源路径。到2025年,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为20%,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
情景3(S3):核能路径。到2025年,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核能占比为15%,2050年,达到40%。
3.2模型设定与数据基础
(1)模型设定。本文采用CGE模型来模拟以上情景对CO2排放量以及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整个CGE模型包含5个基本模块:生产模块、收支模块、贸易模块、均衡闭合模块以及动态模块。生产模块中,模型运用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其中,将能源要素细分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火电、核电与可再生能源电力。模型运用嵌套式的常替代弹性来描述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函数[20]。电力能源要素合成的CES生产函数为:
Yi,t=(αc,i,tCXρE,ii,t+αn,i,tNXρE,ii,t+
αr,i,tRXρE,ii,t)1/ρE,i
(5)
其中,Yi,t,CXi,t,NXi,t,RXi,t分别表示i部门t年的总电力投入,火电投入,核电投入以及可再生能源投入,对应的α系数分别表示第t年部门i的火电、核电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投入份额,且满足αc,i,t+αn,i,t+αr,i,t=1,此外,ρE,i=(ρE,i-1)/σE,i,其中σE,i表示部门i中3种不同电力能源間的替代弹性。部门i在生产中CO2排放量为:endprint
CO2i,t=∑5f=1CfEnergyf,i,t
(6)
其中,CO2i,t为第i部门t年产生的CO2排放量,cf分
别表示一次能源消费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CO2排放因子,具体参照IPCC(2006)。其他参数设定参考Bao 等[21]。
收入支出模块描述了国内生产总值,包括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收入,以及企业、政府、居民和国外部门等经济主体的收入支出。贸易模块采用常弹性转换(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 CET)函数与CES函数描述中国经济活动与国外的关联。
动态模块主要参数设定是动态CGE模型的关键,参考张友国[22]、张晓娣和刘学悦[1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研究报告[23]、李善同[24] 、Bao 等[21]设定主要参数,世界化石能源价格年均增长速率为2.0%(根据Hotelling法则),可再生能源技术每年改善率1.5%,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率为0.1%,劳动增进型技术进步率为2.5%,资本-能源合成投入的技术进步率为0.5%,劳动总供給增长率为3.76%,总资本供给增长率为9%,人口增长率为0.3%。为了求得量化能源结构目标下其他时间节点的能源结构,参考王锋[25]、林伯强和李江龙[12],运用马尔科夫链的转移概率矩阵得到量化目标情景下其他年份的能源结构,其具体形式为:
P=
pc→c(t)pc→o(t)pc→g(t)pc→n(t)pc→r(t)
po→c(t)po→o(t)po→g(t)po→n(t)po→r(t)
pg→c(t)pg→o(t)pg→g(t)pg→n(t)pg→r(t)
pn→c(t)pn→o(t)pn→g(t)pn→n(t)pn→r(t)
pr→c(t)pr→o(t)pr→g(t)pr→n(t)pr→r(t)
其中,c、o、g、n、r分别表示煤炭、石油、天然气、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以煤炭为例,pc→c(t)表示煤炭在一次能源结构中保持原有份额的概率,称为保留概率,pc→o(t)则表示煤炭向石油转化的概率。矩阵P的计算方法从保留概率开始,如果一次能源结构中从t时刻转移到t+T时刻,煤炭的消费比重增加则其保留概率为1,矩阵P第一行的其余元素值为0;如果煤炭的比重减少则其保留概率将小于1,矩阵P第一列的其余元素则为0,第一行上的其余元素由其份额决定。根据以上原则有:
① pc→c(t)=1{pc→o(t)=0;
pc→g(t)=0;pc→n(t)=0;pc→r(t)=0}
② pc→c(t)<1{po→c(t)=0;
pg→c(t)=0;pn→c(t)=0;pr→c(t)=0}
③
pc→c(t)<1
pc→g(t)≠0
pc→n(t)≠0
pc→r(t)≠0
pc→o(t)=
[1-pc→c(t)]×[s0(t+T)-s0(t)]
[s0(t+T)-s0(t)]+[sg(t+T)-sg(t)]+
[sn(t+T)-sn(t)]+[sr(t+T)-sr(t)]
pc→g(t)=
[1-pc→c(t)]×[sg(t+T)-sg(t)]
[s0(t+T)-s0(t)]+[sg(t+T)-sg(t)]+
[sn(t+T)-sn(t)]+[sr(t+T)-sr(t)]
pc→n(t)=
[1-pc→c(t)]×[sn(t+T)-sn(t)]
[s0(t+T)-s0(t)]+[sg(t+T)-sg(t)]+
[sn(t+T)-sn(t)]+[sr(t+T)-sr(t)]
pc→r(t)=
[1-pc→c(t)]×[sr(t+T)-sr(t)]
[s0(t+T)-s0(t)]+[sg(t+T)-sg(t)]+
[sn(t+T)-sn(t)]+[sr(t+T)-sr(t)]
根据各情景中设定的能源结构可适当调整矩阵的阶数,由于给定了2025年的能源结构,利用2014年能源结构的真实值,即可得到P,S*(2025)=S(2014)×P。再设Φ=(p)1/11,得到
S*(t+1)=S(t)×Φ
,运用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刻画能源结构的演变减少了设定的主观性,运用公式可求得2020年的能源结构,再运用S*(2050)即可求得2030年、2035年的能源结构演化结果。
(2)CGE模型的数据基础。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数据为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国财政统计年鉴》、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能源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3中国能源低碳转型路径探讨
3.3.1低碳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碳减排看,三种路径均在2025—2030年实现峰值,其中,S2、S3情景峰值期早于S1,三种情景均实现了中美联合声明中2030年之前实现CO2排放量达峰的承诺。然而,从对经济的影响看,S2情景将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2020—2025年被视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而按照S2情景路径,参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人均GDP超越12 275美元才被视为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至2035年,中国仍未“跨越”这一陷阱。 Felipe等[26]的研究认为,一国在“上中等收入”停留超过14年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按照S2情景,中国很有可能走入这一陷阱,将经过漫长的时间,经济才能够得以“修复回升”。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法国的跨越陷阱时间均发生在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前半段第二次能源转型包括两个阶段,前半段表现为石油替代煤炭,发生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段主要是核能、天然气替代石油,发生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时间段在1964—1974年,德国为1955—1971年,法国为1951—1969年[27],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具备了一定基础,这些国家才开始向核能、天然气转型。endprint
3.3.2能源转型方向与化石能源面临的挑战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能源转型已成必然,关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目前有两个代表性的版本[28],一是“可再生能源版本”,其核心思想是实现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可再生能源将作为基础推动全球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29]。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石油驱动内燃机车)将在科技革命的变更中被电驱动或燃料电池驱动所取代,信息技术的革命很可能使分布集中的传统化石燃料以及铀能源向分散式的新型可再生能源转移,当前互联性正在为跨行业关系创造新的机遇,从历史经验看,能源革命必将伴随产业革命,产生新型的经济范式。二是“制造业版本”,其核心思想是以制造业“数字化”为基础的“大规模定制”或将成为未来制造业的主流趋势[30]。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走向靠近第一个版本,其已将能源转型方向既定为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将逐渐被可再生能源所替代。如果向第二个版本靠近,化石能源实质上也需要面临两大关键挑战,一是必须逐步实现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清洁化利用,进而推进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二是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当前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不断下降。如同计算机行业,可再生能源行业虽然面临当前极高的投入成本,然而,诸多研究支持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正在经历“指数增长”。行业分析预计,未来10年内,太阳能和小型风力发电的采集设备将像手机与笔记本电脑一样便宜[29],对传统能源行业构成较为致命的威胁。
3.3.3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由表4可以看到,2015—2025年,过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将给经济系统带来高昂的转型成本,事实上,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未取得较大突破的情况下,即使按照现有的最大可开发量各非化石能源上限为:核电5 800万kW,水电3.8亿kW,风电2亿kW,太阳能1亿kW,生物能3 000万kW。进行计算,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耗比重也仅占到15.3%[12]。因此,在2015—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应遵循科学发展观,盲目的效仿欧洲是不可取的,正如表3所示,德国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以较高的人均GDP和优化的产业结构为基础的。
虽然就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现状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实现较为困难,但是,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地优化升级,人均GDP正不断提升,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二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环保,它或许在未来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新引擎,能源行业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过程中所减少的就业,会被要素深化以及经济变革带来的乘数效应不断消纳,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或正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步伐。
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便是在这一领域处于较领先地位的欧洲,也仅仅是部分国家实现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如丹麦、西班牙),而即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德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也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并引发了系列的政治问题,德国政府不得不放缓其发展脚步。借鉴“欧洲模式”,2015—2025年,中国应加快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而不是整个国家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尽早制定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中长期规划对当前来说至关重要。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中国低碳能源轉型的路径选择
本文针对各研究机构提出的中国能源转型方案进行CGE模拟发现:2015—2025年,是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期,这一阶段采取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是不可取的,也是违背能源发展规律的,很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警惕每一种能源或者说任何一种事物均有其自身的限制,能源转型需要科学的发展观。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能源转型的阶段式发展路径:
(1)2015—2025年,化石能源仍应发挥主导作用,并适当的提高天然气、核能的比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重点应放在示范区建设上。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兼顾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考虑到人口以及资源禀赋特征,需要实现能源的多元化发展。
(2)2025—2035年,此时中国的产业结构以及人均GDP已达到相当水平,并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能源转型的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甚至由其决定。
(3)2035—2050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中国或将呈现两种局面:一是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即到2050年整个能源系统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供应,局部地区可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核能也将占据一定的比重,而其充当主导能源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4.2政策建议
(1)中国的能源转型基础仍相对薄弱,可再生能源发展应注重科学发展观。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但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主导结构转变效应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制造业内部正逐渐实现质的变化,这为能源低碳转型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但从人均GDP上看,中国与已进入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期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积极推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将为能源转型奠定重要基础。当前,全球掀起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热潮,特别在中国以及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十分迅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应注重科学发展,必须警惕其所带来的高昂经济成本。
(2)以能源转型推进中国低碳工业化发展。就工业化而言,按照能源种类进行划分,可分为传统工业化和低碳工业化。传统工业化以利用化石能源为主,低碳工业化是将经济发展的基础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引领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工业化一般采用产业结构和人均GDP来衡量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低碳工业化则要采用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及单位GDP碳排放进行测度[31]。按低碳工业化衡量指标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远远小于传统工业化水平的差距。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也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endprint
(编辑:于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World Wildlife Fund. Chinas future generation 2.0[R]. Beijing:WWF, 2015.
[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中国2050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情景暨路径研究[R]. 2015.[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China 2050 high renewable energy penetration scenario and roadmap study[R]. 2015.]
[3]中国工程院项目组. 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综合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50-62.[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ject Team. China energy medium and long term (2030,2050)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omprehensive volum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50-62.]
[4]史丹,王蕾.能源革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J]. 产业经济研究,2015,74(1):1-8. [SHI Dan, WANG Lei. Energy revolution and its effe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J]. Industrial economy research, 2015, 74(1):1-8.]
[5]王兰体,蔡国田,赵黛青. 基于专利视角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15(20):161-165. [WANG Lanti, CAI Guotian, ZHAO Daiqing. An analysis of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patent perspective[J].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5(20):161-165.]
[6]邵庆龙,饶蕾. 可再生能源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ECD 国家的实证检验[J]. 软科学,2016(1):71-75. [SHAO Qinglong, RAO Lei.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newable energy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OECD countries[J]. Soft science, 2016(1):71-75.]
[7]DURO J A, PADILLA E. International inequalities in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a decomposition methodology by Kaya factors[J]. Energy economics, 2006, 28(2): 170-187.
[8]冯相昭,邹骥.中国CO2排放趋势的经济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5):43-47. [FENG Xiangzhao, ZOU Ji. Economic analysis of CO2 emission trend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8(5):43-47.]
[9]OCAL O, ASLAN A.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economic growth nexus in Turkey[J].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reviews, 2013, 28(8): 494-499.
[10]APERGIS N, SALIM R.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a sample of 80 countries and nonlinear estimates[J]. Applied economics, 2015, 47(52): 1-20.
[11]齊绍洲,李杨. 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吗?——基于欧盟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17(4):106-119. [QI Shaozhou, LI Yang. Does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drive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EU[J]. World economic studies, 2017(4):106-119.]
[12]林伯强,李江龙. 环境治理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转变——基于煤炭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9):84-107.[LIN Boqiang, LI Jianglong. Chinas energy structure transition und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straints:based on coal and carbon dioxide peak analysi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5(9):84-107.]endprint
[13]杜祥琬,刘晓龙,杨波,等.中国能源发展空间的国际比较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2013,15(6):4-10.[ DU Xiangwan, LIU Xiaolong, YANG Bo, et al.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energy development space[J]. Chinese engineering science,2013,15(6):4-10.]
[14]杜祥琬,杨波,刘晓龙,等.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解耦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12):1-7. [DU Xiangwan, YANG Bo, LIU Xiaolong, et al. Decoupling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5(12):1-7.]
[15]张晓娣,刘学悦. 征收碳税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研究——基于OLGCGE模型的增长及福利效应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5(3):18-30. [ZHANG Xiaodi, LIU Xueyue. Carbon tax and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research: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 analysis based on OLGCGE model[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3):18-30.]
[16]YAMAJI K, MATSUHASHI R, NAGATA Y, et al. A study on economic measures for CO2 reduction in Japan [J]. Energy policy, 1993, 21 (2):123-132.
[17]史丹,馬翠萍. 我国能源需求的驱动因素与节能减排政策效果分析[J]. 当代财经,2014(10):17-24.[SHI Dan, MA Cuiping. Analysis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energy demand and the effect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J]. Contemporary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4(10):17-24.]
[18]KUCERA D, MILBERG W.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manufacturing trade: factor content calculations for 1978-1995[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2003,139(4):601-624.
[19]高柏.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M]. 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0-122. [GAO Bo.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M]. Translated by AN Ji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00-122.]
[20]汤铃,鮑勤,王明喜. 核电项目暂停审批与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基于CGE模型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34(2):349-355. [TANG Ling, BAO Qin, WANG Mingxi. Suspension of nuclear power project approval and achievement of Chinas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based on CGE model analysis[J]. System engineering-theory and practice,2014,34(2):349-355.]
[21]BAO Q, TANG L, ZHANG Z X. Impacts of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 on Chinas sectoral emission: simulations with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3, 24 (1): 77-94.
[22]张友国.碳强度与总量约束的绩效比较:基于CGE模型的分析[J]. 世界经济,2013(7):138-160. [ZHANG Youguo.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carbon strength and total constraint: an analysis based on CGE model[J]. World economy,2013(7):138-160.]
[23]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1-8.[Research Group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 blue book: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15[M]. Beijing: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5:1-8.]endprint
[24]李善同. “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J].经济研究参考,2010(43):2-27. [LI Shantong. Prospec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2030[J]. Economic research reference,2010(43):2-27.]
[25]王锋.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减排政策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50-72. [WANG Feng.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growth and evaluati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M]. Beijing:Economic Science Press,2011: 50-72.]
[26]FELIPE J, ABDON A, KUMAR U. 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2, 48(3): 23-34.
[27]秦佳.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与中国发展道路[D].天津: 南开大学,2014:34-55. [QIN Jia. Medium income trap: theory, experience and Chinas development[D].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2014:34-55.]
[28]黄群慧,贺俊,等.真实的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促进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最新实践[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191-206. [HUANG Qunhui, HE Jun, et al. Real industrial policy: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atest practi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2015: 191-206.]
[29]杰里米·李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张体伟,孙豫宁,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 80-92. [RIFKIN J.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the new economic model changed the world[M]. Translated by ZHANG Tiwei, SUN Yuning.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3: 80-92.]
[30]MARKILLIE P.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N]. The economist, 2012-04-21.
[31]史丹. 以能源轉型促进低碳工业化发展[J]. 中国国情国力,2016(10):6-8. [SHI Da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industrialization with energy transformation[J]. China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2016(10):6-8.]
[32]SU Q H,WANG Q X,WANG D J,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energy
carbon emissions in Yantai from 2001 to 2011[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6,14(3):182-188.
[33]LIU Y,ZHOU M F,FENG S H,et al.Rebound effect and its decomposi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energy types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6,14(4):245-252.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hird round energy revolution is quietly occurring and China is now on the ‘crossroads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Most of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path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focus on energy transformation itself, ignoring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 linking energy transition to th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is, what kind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program will have the costs in the near future can be absorbed by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in the long term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uses CGE model and transnational comparisons to study Chinas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feasible path of Chinas energy trans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During 2015-2025, Chinas economy enters the ‘new normal, is experiencing economic growth shift period, structural adjustment pain period and early stimulating policy digestion period, which is called ‘threesuperimposed sta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period acros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In this period,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oderate means on energy transformation because high propor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will have a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which is not feasible. During 2025-2035, it is the period which will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We can either set up a higher proportion targets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or the fossil energy may still dominant the energy system due to its ‘clean itself potential. The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During 2035-2050, it is the mature period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will enter a new stage. Chinas energy system may have two possibilities. One is that by 2050, renewable energy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60% in the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The other is that in some areas renewable energy can provide 100%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in the entire energy supply system, fossil energy and nonfossil energy will equally share the market.
Key wordsenergy transformation; industry revolution; renewable energy; middle income trap; lowcarbon development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