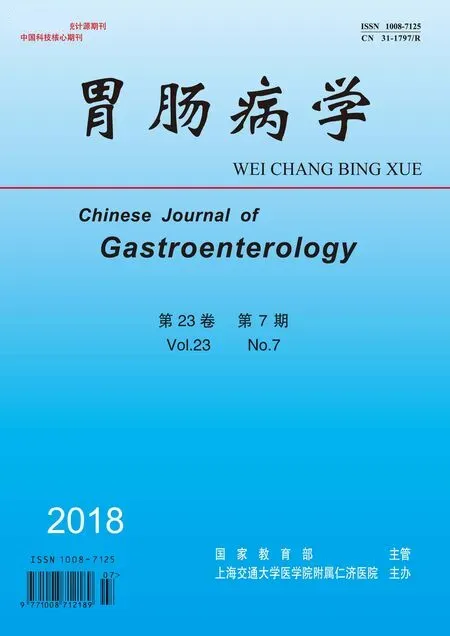肠-肝轴在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施莹莹 陈颖伟,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1(200092) 上海市小儿消化与营养重点实验室2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是一种病因和发病机制未明的慢性复发性肠道炎性疾病,肝胆系统症状是其最常见的肠外表现。近期报告指出,1.4%~7.5%的IBD患者伴发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SC),而70%~80%的PSC患者在病程中出现IBD,提示IBD与肝肠病变可能存在相互关联的发病机制[1]。肠道与肝脏在结构和功能上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称之为“肠-肝轴”。近年研究发现,胆汁酸肠肝循环异常、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移位以及淋巴细胞归巢紊乱可能通过肠-肝轴参与IBD的发病。本文就肠-肝轴在IB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一、肠-肝轴概述
肠道和肝脏具有相同的胚胎学起源,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肝脏分别通过门静脉系统和胆管系统与肠道维持着直接的输入和输出关系[2]。而肠道淋巴细胞起源于发育中的肝脏,这为肠肝间淋巴细胞归巢和再循环提供了解剖学的理论基础。75%~80%的肝脏血供来源于肠道,正常情况下,细菌及其产物和各类抗原等肠源性物质仅少量穿过肠黏膜屏障经门静脉进入肝脏,激活肝脏的固有免疫系统和少量适应性免疫细胞,维持免疫耐受并抵抗感染。此外,肝脏通过胆管分泌胆汁至肠道,调节物质代谢和肠道微生物组成。
1998年,Marshall[3]正式提出了“肠-肝轴”的概念,认为机体在受到强烈打击后,正常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并伴随肠道免疫系统的主要抗炎作用缺失,导致肠道细菌移位和大量内毒素吸收进入门静脉血流和体循环,激活Kupffer细胞,促进促炎细胞因子释放,从而引发不可控的系统性炎症反应,正反馈加重肠黏膜损伤甚至影响远隔器官。随着“肠-肝轴”学说逐渐被广泛认可,肠肝相互作用已成为消化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和治疗应用中的研究热点。
二、胆汁酸与IBD
1. 胆汁酸的肠肝循环:胆汁酸是胆固醇代谢的终产物,是机体肠-肝轴的重要成分。机体的胆汁酸库共约3~5 g,远远无法满足机体的需求,故借助有效的肠肝循环机制使有限的胆汁酸能反复利用。约95%排入肠道的胆汁酸可在肠道被重吸收,其余5%则是每天随粪便排出的最少损失量。结合型胆汁酸在回肠末端通过主动转运被有效地重吸收,少量未结合型胆汁酸在小肠和结直肠中通过被动扩散被重吸收。肝细胞则通过与门静脉血流直接接触的基底侧膜摄取循环胆汁酸。大部分循环胆汁酸通过环氧化物酶介导的Na+依赖性主动转运被肝细胞重吸收,仅约25%通过Na+非依赖性机制被重吸收。在肝脏内,未结合型胆汁酸与甘氨酸或牛磺酸结合成为结合型胆汁酸,并与重吸收、新合成的结合型胆汁酸再次随胆汁进入肠道。上述胆汁酸在肠道和肝脏之间循环流动的过程即为胆汁酸的肠肝循环[4]。
2. 胆汁酸受体介导的肝肠免疫失调:除促进脂肪乳化、肠道吸收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功能外,胆汁酸还能作为一种信号分子,通过与特殊的细胞受体结合,调节肝肠免疫应答[4]。G蛋白偶联胆汁酸受体5(G protein-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 5, TGR5)和法尼酯衍生物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 FXR)是多种胆汁酸受体中尤为重要的两种受体。TGR5在整个肠道中的表达水平较高,尤以回结肠为甚;而在肝脏中的表达水平较低,主要集中表达于肝窦内皮细胞、胆囊上皮细胞和Kupffer细胞[5-6]。激活TGR5能通过抑制核因子(NF)-κB,减少Kupffer细胞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1α、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6]。Ichikawa等[7]的研究显示,胆汁酸通过激活TGR5-cAMP通路,诱导巨噬细胞向分泌低水平IL-12的树突细胞分化,提示TGR5可能在CD中发挥保护作用。Cipriani等[8]的研究发现,TGR5选择性激动剂能维持肠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减轻肠道异常免疫反应。与TGR5不同,FXR在肠道和肝脏中的表达水平均较高。Gadaleta等[9]的研究表明,激活FXR对实验动物的肠道炎症具有保护作用,并可改善结肠炎症状,抑制肠道通透性增高,减少杯状细胞消亡;此外,激活FXR可抑制IBD患者黏膜固有层细胞分泌干扰素(IFN)-γ、IL-17、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Zhou等[10]在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fate sodium, 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发现,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α, PPARα)-UDP-葡糖醛酸转移酶(UDP-glucuronosyltransferase, UTG)轴发生活化,可抑制下游FXR及其相关反馈通路,上调胆固醇7α-羟化酶(CYP7A1),改变胆汁酸稳态,最终加剧结肠炎的发展。Nijmeijer等[11]对缓解期IBD患者肠黏膜标本进行检测发现,与UC组和健康组相比,CD患者回肠FXR激活减少,此变化继发于胆汁酸的肠肝循环改变和炎症信号的转录抑制。由此可见,胆汁酸的肠肝循环异常可导致FXR和TGR5受抑或过度活化,从而影响IBD中肠肝病变进程,但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肠道细菌、内毒素与IBD
1. 肠道细菌移位与内毒素信号转导:肠上皮细胞是机体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能阻止包括细菌和内毒素在内的多种有害物质穿过肠黏膜进入血液[12]。当肠黏膜屏障受损时,肠道上皮的通透性增加,为肠道菌群及其产物移位进入肝脏提供了合适的门户。内毒素是位于革兰阴性细菌细胞壁上的一种复杂成分,也称为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LPS的独特分子结构组成脂质A、核心寡糖和O-特异性多糖易被宿主的防御系统所识别,如被LPS结合蛋白(LBP)、CD14、Toll样受体4(TLR4)和髓样分化蛋白MD2组成的核心受体复合物所识别,触发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TLR4属于TLR家族,被外源性配体LPS激活后,可通过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MyD88)依赖型或非依赖型方式启动下游信号通路[13]。MyD88依赖型信号通路主要以IκB激酶途径激活NF-κB和以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途径激活激活蛋白1(activator protein-1, AP-1),进而调节促炎细胞因子和免疫功能相关基因的表达。MyD88非依赖型信号通路由Toll/白细胞介素1受体结构域所介导,后者可活化干扰素调节因子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3, IRF-3),诱导IFN-β表达。
2. 内毒素通过肠-肝轴引发肝肠病变:在肝脏,肝细胞和多种非实质细胞均表达TLR4,包括Kupffer细胞、肝星状细胞、胆管上皮细胞和肝血窦内皮细胞[13]。正常情况下,Kupffer细胞和肝细胞负责清除不断通过门静脉进入肝内的肠源性LPS,导致肝脏对LPS高度耐受,因此健康肝组织内TLR4的表达水平极低[14]。一旦超过正常的免疫耐受阈值,肝内TLR4表达上调,LPS立即激活多种细胞内的TLR4信号通路,释放一系列促炎细胞因子,引发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早在1977年的个案报道发现,在UC患者门静脉和体循环中,经LAL法检测显示内毒素水平升高[15]。Gäbele等[16]的研究在实验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小鼠中发现,以DSS诱发肠道炎症会促进LPS移位、抑制肠道抗菌肽,导致肝脏炎症增强、肝纤维化进程加快以及促纤维化基因表达上调。Trivedi等[17]在实验性结肠炎小鼠中发现,闭合蛋白表达减少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引起多种结肠细菌和相关LPS移位至肝脏;肝内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增强,导致DNA损伤、脂肪肝、肝纤维化形成和肝功能异常,且肝脏损伤与结肠炎严重程度相关。肝内出现的LPS一方面可增加肝脏和肠道中微血管的通透性,另一方面可反过来促进肠道细菌移位,形成恶性循环[18]。由LPS诱导产生的肝源性炎性细胞因子,不但能使肠道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中断,提高肠道渗透性;而且能下调肝细胞内胆汁的生成,使胆汁酸分泌减少,加重肠道内微生态紊乱[19]。胆汁酸具有抑菌的功能,可损伤细菌细胞膜或DNA、造成蛋白质错误折叠或变性、引起氧化应激等,影响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结构[20]。Devkota等[21]的研究表明,以富含饱和脂肪的饮食或添加了牛磺酸的低脂肪饮食饲养敲除IL-10基因的小鼠,均能引起牛磺酸结合型胆汁酸合成加强,促进致病菌B.wadsworthia生长;而B.wadsworthia能有效利用有机硫,与肠道免疫反应密切相关,促进小鼠结肠炎的发生。Duboc等[22]的研究发现,IBD患者中由肠道菌群失调引发的肠腔内次级胆汁酸减少,会减弱后者对肠道上皮细胞的保护作用,增强肠道上皮细胞炎性反应,可能使IBD恶化。上述研究提示,肠道细菌和内毒素移位不但能引起肝脏损伤,而且能进一步加重肠道病变,可能是IBD发病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四、淋巴细胞归巢与IBD
1. 淋巴细胞归巢的机制:肝肠免疫以肠肝间淋巴细胞归巢/再循环为基础,近年已成为肠-肝轴研究的热点。淋巴细胞归巢指血液中淋巴细胞选择性穿过高内皮微静脉(high endothelial venules, HEV),趋向迁移并定居于外周免疫器官的特定区域或组织的过程。淋巴细胞表面不同的黏附分子(又称归巢受体)与特定组织表面的黏附分子(又称地址素)相互作用,决定该细胞的去向。淋巴细胞接受抗原刺激后活化,分泌一系列炎性介质,启动炎症反应并募集更多效应细胞,从而增强免疫应答[23]。正常情况下,CC趋化因子配体25(CCL25)和黏膜地址素细胞黏附分子1(mucosal addressin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MAdCAM-1)限制性表达于肠道,各自识别淋巴细胞表面的CC趋化因子受体9(CCR9)和整合素α4β7,募集CCR9+α4β7+T细胞至肠道黏膜;而血管黏附蛋白1(vascular adhesion protein-1, VAP-1)结构性表达于肝脏血管和血窦内皮细胞,招募表达相应归巢受体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肝脏[23]。
2. 黏附分子表达异常导致肠肝间淋巴细胞归巢紊乱:近年研究发现,肠肝间淋巴细胞归巢紊乱可能参与IBD肠道炎症和肝胆病变的发生。一方面,在IBD患者中原本特异性表达于肠道和肝脏的地址素出现交叉表达。有研究发现,IBD患者的肝脏内皮细胞表面CCL25和MAdCAM-1表达上调,募集存活期长的记忆T细胞至肝脏,进而引起肝脏并发症[24]。Salmi等[25]的研究发现,虽然VAP-1在正常肠道中度表达,但在IBD患者中的表达明显上调,表明淋巴细胞不仅能利用VAP-1进入肝脏,也能利用VAP-1进入炎性肠系膜血管。Trivedi等[26]的最新研究发现,VAP-1表达水平在IBD相关PSC患者肝组织中显著上调,并进一步指出,结肠上皮细胞和肠道菌群可产生半胱胺等物质,激活VAP-1的潜在胺氧化酶活性,调节肝脏内皮细胞表面MAdCAM-1的表达,促进肠道趋向性α4β7+T细胞迁移至肝脏。另一方面,淋巴细胞表面归巢受体的表达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研究[27]指出,CD8+T细胞并不稳定,当其在不同的组织区域被再激活时,可重新编码归巢受体,从而改变效应细胞的迁移途径。T细胞表面归巢受体的表达具有可塑性是由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 ATRA)调控所致,ATRA能提高T细胞表面CCR9和α4β7的表达[28]。以往认为仅肠相关淋巴组织(GALT)中表达视黄醛脱氢酶基因的树突细胞才能产生ATRA。然而近年研究发现,肝脏也具有产生ATRA并诱导循环淋巴细胞向肠道迁移的能力。Eksteen等[29]的研究指出,肝内树突细胞和星形细胞能生成少量ATRA,但无法维持淋巴细胞表面CCR9和α4β7的高表达状态。Neumann等[30]的研究显示,肝窦内皮细胞高表达视黄醛脱氢酶基因,能激活CD4+T细胞并使之获得稳定的肠道趋向性。反之,肠道能否诱导循环淋巴细胞表达特殊的归巢受体并获得肝脏趋向性,尚待更多的研究探索。
五、结语与展望
IBD是一种多病因引起的异常免疫介导性疾病,可伴发肝胆系统病变。目前研究表明,胆汁酸减少、肠道细菌和内毒素大量移位进入肝脏以及淋巴细胞归巢紊乱可通过肠-肝轴影响肝肠免疫,破坏两者正常的免疫防御功能,诱发和加重炎症反应。这有助于为临床诊断和治疗IBD提供新方向,如胆汁酸减少能否作为IBD新的预测因子,针对归巢受体和地址素的新型抗体和拮抗剂是否对IBD具治疗价值等。此外,胆汁酸稳态改变是IBD的直接病因还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继发性改变?肝源性致炎因子通过何种具体途径加重肠黏膜屏障损伤?哪些信号分子介导肠肝表面黏附分子异常表达?改善肝脏功能是否对治疗肠道病变有益等?这些问题尚需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