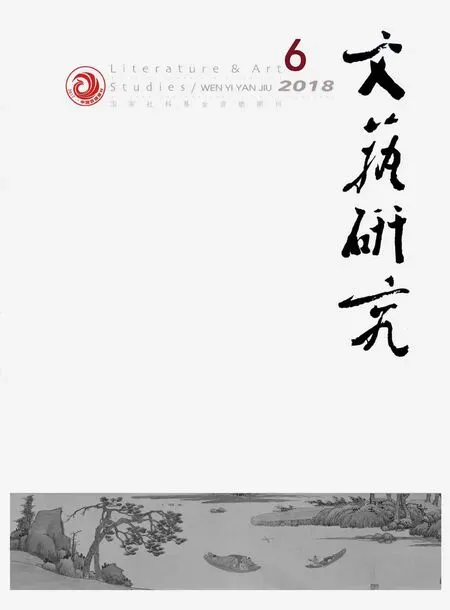不尊古法、不囿常法、不拘笔法:宋代禅门水墨画的重要转变
张令伟 戴莹莹
两宋之时,中国传统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在这个辉煌灿烂的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思想,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萌芽、发展、传播、融合的历史过程,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宋禅宗兴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以至于“人人谈之,弥漫滔天”①。此时,禅林和士林交游密切,诗文、绘画成为参禅悟道的重要方便法门。一方面,传统绘画的内容与形式得以进入寺院,受到禅门义理、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另一方面,禅门“以笔墨作佛事”②、“游戏翰墨”③、注重“妙观逸想”④的绘画理念,直接推动了传统水墨画的变革和发展。近年来,关于中国禅宗对绘画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学者提出了“禅画”“禅僧画”“道释画”“禅宗绘画”等概念,试图从内容、形式、风格、意趣等方面研究其内在和外在规律以及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本文拟以宋代禅门水墨画(即宋代禅门僧人创作的水墨画)为切入点,结合历代画论、僧人画作等,探讨宋代禅门水墨画的绘画理念、品评方式、创作题材、技法工具的转变,禅门水墨画派的形成,及其对宋元明时期文人画的影响。
一、重笔至重墨:宋代禅门水墨画气韵的整体转变
两宋时期,禅宗兴盛。高僧大德在“以心传心”“自悟自解”⑤的过程中,感受到佛法弘扬方式的某些弊端。有的禅林高僧认为,了悟佛法是最重要的,不应在语言文字及书法绘画上过于执著,但也不应直接抛弃这种形式。修行之人应当借助语言文字、书法绘画等艺术手段,明心见性。以文字参禅,“文字禅”盛行;以绘画参禅,则“禅画”兴盛。同“文字禅”一样,水墨画成为宋代禅宗思想的另一种审美表达。僧人不仅通佛典,还擅儒、释二教,文采、绘画素养甚高。在各种绘画类型中,水墨画基本只有黑白二色,含蓄蕴藉,意境深远,更能体现禅味、禅趣和禅悦。因此,宋代禅门僧人引禅味入画境,引禅趣入水墨。
水墨画起于唐代,盛行于宋元,一直延续至今。在其发展过程中,宋代禅门水墨画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值得引起重视。北宋初年,水墨画整体延续着唐末五代的风格。画家强调画有所宗,注重应物象形、骨法用笔和绘画构图,提倡气韵生动。据《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等记载,名重一时的画僧巨然善画山水,深得佳趣。“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⑥他师法北宋初年三大家之一的董源,工画江南风景与高山大川,以水墨山水见长,后与董源并称“董巨”,是江南水墨山水的代表,对元明清以后的水墨山水画有重要的影响。巨然的画,宏观上“古峰峭拔,宛立风骨”⑦;微观上“下至林麓之间,犹作卵石,松柏疏筠蔓草之类相与映发,而幽溪细路,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真若山间景趣也”⑧;技法上善用长披麻皴,鲜明疏朗,破笔焦墨;意境上幽溪细路,竹篱茅舍,重野逸清静之趣,淡墨轻岚深受文人士大夫喜爱。巨然的水墨山水,直接影响了元明时期的倪瓒、黄公望、文徵明等书画家。宋太祖年间,四明僧人传古尤善画龙,“独进乎妙”,“建隆间名重一时,垂老笔力益壮,简易高古,非世俗之画所能到也”;“皇建院有所画屏风,当时号为‘绝笔’”⑨。他的法嗣德饶、无染、岳阇黎等皆善画龙,在当时俨然形成了一个画派。
与此同时,在禅门中还流行着另外一种水墨画。相较骨法用笔、应物象形而言,画家更重视水墨蕴藉,强调触景生情、意兴所致。永嘉僧人择仁,采诸家所长,善画松,“每醉,挥墨于绡纨粉堵之上,醒乃添补,千形万状,极于奇怪。曾饮酒永嘉市,醉甚,顾新泥壁,取拭盘巾濡墨洒其上。明日少增修,为狂枝枯枿,画者皆伏其神笔”⑩。择仁先用水墨挥洒,再随其形绘画,实为泼墨之法。用墨微妙,不见笔迹,却能发画中气韵。北宋初年僧人居宁,擅长水墨草虫,其名藉甚。“尝见水墨草虫有长四五寸者,题云‘居宁醉笔’。虽伤大雅而失真,然则笔力劲俊,可谓稀奇。”⑪《宣和画谱》称其“喜饮酒,酒酣则好为戏墨,作草虫,笔力劲峻,不专于形似”⑫。从“不专于形似”来看,他的画作并不注重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而是“酒酣”“戏墨”“笔力劲峻”,更重意象生动。
北宋中后期,禅门山水画更加注重水墨神韵。元祐年间,华光寺僧人仲仁喜淡墨,善画梅。居衡州华光山,擅用水墨晕写梅疏影斜,能得梅之神韵,“所谓写意者也”⑬。他匠心独具,自成一家,开创了“墨梅”画派,对中国水墨画题材与技法的创新影响深远。仲仁的好友惠洪亦工画梅竹,代表作品有《墨梅图》。邓椿《画继》卷五“道人衲子”和夏文彦《图绘宝鉴》皆有记载,称其“能画梅、竹,用皂子胶画梅于生绢扇上,灯月下宛然影也。笔力于枝梗极遒健”⑭。惠洪绘画,更重视“戏趣”、墨法与气韵生动,对形似、笔法、绘画工具等皆不甚重视。
南宋初年,禅门水墨画由重笔至重墨的转变更加明显。高宗朝僧人梵隆,字茂宗,号无住,“善白描人物山水,师李伯时。高宗极喜其画,每见辄品题之”⑮。他师法李公麟,擅长佛像、人物和山水。杭州灵隐寺画僧智融,善画龙、牛,喜用淡墨,自号老牛,南渡后居临安万公岭。其今存《牧牛图》,不拘笔法,重视墨趣,寥寥数笔,形神俱见⑯。
南宋中后期,禅门水墨画不拘笔法、墨趣横生的创作风格已经基本形成。杭州上竺寺僧人若芬,自号玉涧与芙蓉峰主,长于诗画,善于泼墨山水与画竹,“模写云山以写意”,“因谓世间宜假不宜真”⑰。他的画作之中,西湘、潇湘、北山最为有名,作“钱塘八月潮”“西湖雪后诸峰”“极天下伟观”⑱。值得一提的是,其对日本绘画影响深远,日本仍存有他的《庐山图》《远浦归帆图》⑲。南宋后期蜀人法常,无准师范法嗣,杭州长庆寺僧人,号牧溪,喜好水墨,善作龙虎、人物、山水、花鸟、树石等,作画时信手拈来,随意点笔,不假修饰,意味深长。他在宋代禅门水墨画中承上启下:上承梁楷的简笔水墨,下启沈周、徐渭、扬州八怪等画家。然而,元代画家对其评价不高。元代庄肃《画继补遗》和夏文彦《图绘宝鉴》皆认为其画作是山野之画,只适合禅门修行,“意思简当,不费妆饰。但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⑳。但其作品在流传东瀛后,却对日本禅林和画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与“牧溪画意相侔”㉑的是钱塘西湖六通寺僧人萝窗,擅水墨山水、竹石、人物等,随笔点墨㉒。
南宋时期,禅门水墨画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有的画僧以一技闻名,比如仲仁、僧定、莹上人等擅墨梅,太虚、枯崖等擅墨竹,因师、子温等擅墨葡萄,智融等擅走兽,法常、梵隆、萝窗等兼擅山水、人物、走兽等,名重一时。不仅如此,南宋佛教界泰斗、蜀僧无准师范一门皆重禅画,在当时形成了重要的禅画派别。如果说北宋初年的禅僧更为偏重笔法,那么南宋的禅僧更为重视墨趣。他们不尊古法、不囿常法、不拘笔法,惯用粗笔淡墨,创作出禅意浓厚的作品。虽为元人诟病,却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形式与创作方法上做出了创新与贡献。
二、“笔墨佛事”与“游戏翰墨”:宋代禅门水墨画理念与品评方式的转变
作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和品评的标准,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之“六法”成为衡量绘画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北宋初年,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曾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㉓然而,宋代禅门义理给水墨画的绘画理念与品评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北宋著名的诗僧、画僧惠洪,将禅宗思想运用到文艺创作与品评之中,提出新的绘画理念与鉴赏标准。惠洪,禅林大德真净克文法嗣,精通佛学,出入禅门、士林、文坛、画苑,擅长以诗画入禅,他与“墨梅画”的始祖仲仁禅师、以诗画闻名的“苏黄”等士大夫交游甚密。惠洪主张“在欲行禅”与“游戏三昧”㉔,提倡对诗、画这种外在的弘法方式不离与不执,以诗、画说禅,以诗、画弘法。他与“苏黄”等当时的禅林泰斗、文坛领袖共同推进了“文字禅”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以笔墨做佛事”“游戏翰墨”的书画理念的传播与盛行。其《石门文字禅》一书,保存了大量的诗画理念。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代表了当时部分禅门与士大夫的绘画创作与品评理念。
禅宗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㉕。因此修行的人必须明心见性,方有所成。“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㉖因此,自心即佛,文字、绘画、音乐等都是阻碍修行的方式。然而,“以心传心”存在明显的传授困难。“心非言传,则无方便。以言传之,又成瑕玷。”(《堕庵铭》)㉗因此,合理地利用文字、绘画等手段传法,成为禅门僧侣思考的问题。“是知俾明悟者知大法,非拘于语言,而借言以显发者也。”(《题云居弘觉禅师语录》)㉘然而,文字、绘画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天全之妙,非粗不传。如春在花,如意在弦。”(《郴州乾明进和尚舍利赞》)㉙在惠洪看来,佛性是内在,是春和意,诗、画是外在,是花与弦。二者本为一体,但又不执不离。文字、绘画皆是修禅的方便法门。因此,他在为法友华光仲仁的墨梅题跋时说:“华光道价重丛林,而以笔墨作佛事。”(《跋行草墨梅》)㉚仲仁的墨梅,不以形似为重,而以神似为胜;不以笔法为重,而以墨趣为胜。仲仁的画,疏影横斜、平沙远水,虽与佛事没有直接关联,但却间接体现了禅机。他在《绣释迦像并十八罗汉赞序》中说:“余自顾贫,无以为世尊诸大士供,乃以笔语为之供,名曰‘笔供养’云。”㉛“以笔语为之供”,即“以笔墨作佛事”。好友苏轼画应身弥勒像,惠洪赞叹说:“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像。又为无声之语,致此大士于幅纸之间。笔法奇古,遂妙天下。”(《东坡画应身弥勒赞序》)㉜他认为,苏轼的诗文是“游戏翰墨”,是“大佛事”;绘画作品是“无声之语”,亦是佛事。在惠洪的《石门文字禅》中,多次出现“游戏笔砚”“翰墨为游戏”“游戏翰墨”等提法,“游戏翰墨”的思想,不仅存在于绘画领域,还广泛存在于诗文创作领域,得到了禅林和文坛的双重认可。同时,《石门文字禅》中保存了大量的诗文、赞偈颂、题跋等,内容涉及梅花、山水、佛像、花鸟、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等,并有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书画作品。由于受到禅门淡泊宁静的创作风格和“游戏翰墨”的创作理念的影响,这些作品主要呈现出宗教性和随意性两个特征。
禅、诗、画本为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诗、画是禅的外在表现,禅是诗、画的内在生命力。惠洪提出的绘画理念与鉴赏标准,对当时的禅门绘画、文艺创作影响极深。两宋禅门仲仁、惠洪、智融、法常、无准等大德高僧以参禅悟道为出发点,向内发明本心,向外体察万物,以诗、书、画为弘法供养的方便法门、遣兴抒怀的工具、交游唱和的媒介。他们践行“笔墨佛事”“游戏翰墨”的宗旨,认为诗画创作以适然随意、圆融自在为主,促进了传统水墨画创作理念、题材、风格、技法、工具等的转变。
三、宗教性与随意性:宋代禅门水墨画题材、技法、工具与风格的转变
谢赫《古画品录》开篇指出了绘画的功利意义:“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㉝因此,绘画必须以“六法”为尊,方能千载之后“披图可鉴”。而宋代禅门画僧进行绘画创作,并非为了“明劝戒,著升沉”,而是要再现一种修行悟道的体验与状态。这种再现,有的甚至是即兴的。他们从自然万物中吸收绘画题材与创作灵感,不拘泥于艺术创作旧有的法度与规则,追求圆融无碍、游戏翰墨的自由境界,借助疏淡简笔、水蕴墨章来表现禅意和禅悦。因此,宗教性与随意性是宋代禅门水墨画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无论是表现禅宗思想的绘画作品,还是受到禅宗思想启发创作的书画作品,还是相关赞颂、题跋,都体现出了浓厚的禅意。
从绘画题材来说,宋代禅门水墨画主要为佛教人物、墨梅墨竹、山水树石、花鸟虫鱼、龙虎猿鹤等。禅宗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可拿来证悟,无论什么题材的创作都能体现“直指本心、见性成佛”㉞的思想。惠洪自谓:“盖湘西皆吾画笥”(《题橘洲图》)㉟,“凡四海九州,山川烟云,皆吾画笥也?”(《又惠子所蓄》)㊱佛教人物一直是宋前禅门绘画的重要内容,直接体现了“以笔墨做佛事”和“以笔供养”的思想。两宋之时,禅门书画作品中,佛教人物画比重下降,山水花鸟、墨梅墨竹的比重上升。山水一般是水墨山水,以全景山水为多,小景山水为次。前者代表僧人有楚安、巨然、真慧、道宏、梵隆、若芬、法常、萝窗等,画面多呈现出笔墨闲远、气韵悠长的禅意;后者代表僧人有惠崇、仲仁等,画面多呈现出宁静雅致、自在明净的禅悦。花鸟题材的创作中,禅僧们往往以形写神,凸显花鸟背后的象征意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禅门水墨画开创了很多全新的题材,赋予世俗题材以全新的意义,比如影子与“悦影”说的形成。北宋时期,元蔼以墨画竹,推动了宋代墨竹题材的创作;择仁以墨画松,常有创新之处;仲仁以墨晕作梅,开创了墨梅的题材。南宋时期,因师以墨作葡萄,开创了墨葡萄题材;若芬擅墨梅、墨竹和水墨山水,尝试将人物和山水题材相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法常的蔬果题材的状物写生,常为惊叹。即便是日本画僧皆效仿法常,以法常之水墨画为宗。
从绘画技法来说,谢赫《古画品录》的“六法”曾明确提出一个系统的绘画创作体系㊲。从笔法、构图、赋彩、气韵、临摹等方面,具体而微地提出了创作的标准和原则。然而,宋代禅门水墨画家作画时却并没有过多地受这些法则的影响。他们在笔墨技法、构图着色等方面信手拈来,并无常法;品评绘画的重点则侧重于意境,即是否包蕴了禅意、体现了禅悦、发明了本心、证悟了佛性。举例来说,智融的《牧牛图》和廓庵的《十牛图》,源自《六祖坛经》的见性法门,在宋元以后的中国乃至日本禅门流传甚广。因禅修而证悟,因自性般若而作此图。智融、廓庵取《法华经》里三车之喻,将牛比作一切众生真常清净的佛性,认为修行者不能迷失本性,而应该寻觅本性,“见性成佛”。因此,画面构图随心所欲,随意点笔、意兴飞动。子温作水墨葡萄,自成一家,人莫能测㊳,《书史会要》称:“人但知其画葡萄,而不知其善草书也。其所画葡萄枝叶,皆草书法也。”㊴墨梅、墨竹、墨松的创作中,择仁、仲仁、惠洪、若芬、静宝、慧丹等人采诸家所长,笔随意兴,寥寥数笔,形神毕现。宏观来看,从笔法而言,白描减少,减笔、泼墨为多;从色彩而言,五彩减少,水墨为主;从构图而言,画面疏淡含蓄,留白较多。墨色之外,便是留白。在画面的结构布局中,留白体现着空灵、虚空的美感。虚实相生、浓淡相济,是另一种呈现禅意与禅趣、修道与悟道的方式。正因如此,禅门水墨还喜枯简淡墨,追求一种“逸”的脱俗之境,在澄净简当之中深藏禅机。具体来说,巨然长于长披麻皴和破笔焦墨,梵隆善用白描,若芬喜用泼墨,法常、萝窗、静宝等擅长随墨点染。其中,法常的状物写生,喜用简当的笔墨勾勒,再用浓淡深浅相间的墨色区别明暗,笔法与墨法微妙结合,让黑白二色在点缀勾勒与渲染烘托中爆发出色彩的张力,具有开创性意义。绘制山水树石时,法常几乎不用勾勒轮廓;若芬的山水树石,不仅没有轮廓线,还有大量留白。
从绘画工具来说,僧人作画,不专使用传统的纸笔,还常常信手拈来,使用蔗渣、草汁等工具。智融作画,“遇其适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岩石,尤为古劲”㊵。惠洪作画,“每用皂子胶画梅于生绢扇上,灯月下映之,宛然影也”㊶。法常作画,“不曾设色,多用蔗渣、草汁,又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不费妆缀”㊷。归根结底,工具的选择也是随意性的一个方面。智融作画,当在“适意”之时。所谓“适意”,即艺兴正酣、游戏三昧之时,也可以理解为定心、禅悦之时。反过来说,绘画技法、工具的改变,也促进了绘画风格、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
总之,宋代禅宗对水墨画的影响体现在绘画理念、创作题材、技法、工具等方面,以随心所欲的构图、清简的浅色水墨,甚至浓淡墨块的擦染混融,将禅意彻底融入书画作品中。宋代禅僧一方面以笔墨做佛事,通过书画来弘扬禅法,另一方面引禅意入画境,以超逸脱俗的禅境禅意彰显书画作品的气韵生动,推动禅门水墨画乃至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事实上,随着禅僧和文人士大夫两个群体的交流日深、逐渐融合,这种随心所欲、意到笔随的创作习惯,不遵循古法、不拘泥于常法的创作理念,对后来文人画的发展、定型影响深远。明代中后期,禅学与心学兴盛。在苏轼“士人画”理论和宋代禅门、元四家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董其昌以禅入书画,以皴法为主要依据,将唐宋以来的画家分为南北两派,并提出了“临济宗论”㊸和“文人之画”㊹的概念。董其昌上承两宋禅门、士林,推崇南宗顿悟之说,擅泼墨、披麻皴,喜用淡墨、留白,追求“意兴所至,辄尔泼墨”㊺的艺术效果。他将王维、董源、巨然、元四家等画家归类、定义为“文人画”,并提炼了“文人画”的创作技法与理论特征。
结 语
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发展史上,宋代禅门画僧一直是重要的力量。南宋邓椿《画继》卷五“道人衲子”、明莲儒《画禅》皆收录了大量的禅门画家。南宋中期以后,宋代禅门水墨画获得了新的发展。受“五山十刹”制度的影响,南宋中晚期大量的禅僧画家入浙求法,向浙江集结。这种集结,既有利于禅门水墨画的发展、变革与定型,也有利于禅门水墨画派的形成。禅宗内部涌现了大量的禅僧画家。其后,五山之首径山的无准师范禅师一门皆善诗文书画,形成了名重一时的禅画流派,并与日本禅林关系尤为密切。南宋中晚期,朝廷对五山之首径山的知名禅师十分推重,石桥可宣、无准师范、虚堂智慧等皆被赐予封号。他们皆善诗画,又德高望重,享誉禅林士林,推动了禅宗水墨画的发展。他们借助深厚的宗教和文学、艺术修养,将参禅悟道与诗文、绘画创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通相契,相证相悟。他们注重用含蓄蕴藉、浑然天成的水墨画来发明本心,弘扬佛法,禅与诗文、书画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创新了绘画理念、品评方式、创作题材、技法工具,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风格。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创作理念、品评角度都深深地影响了宋元以后的文学艺术创作,对文人画乃至日本“汉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②③④㉔㉗㉘㉙㉚㉛㉜㉟㊱ 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张伯伟等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52页,第1187页,第1188页,第1685页,第1243页,第1473页,第1198页,第1552页,第1141页,第1187—1188页,第1525页,第1527页。
⑤㉖㉞ 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49页,第350页,第348—349页。
⑥⑩⑪㉓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黄苗子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页,第91页,第102页,第14页。
⑦ 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⑧⑨⑫ 《宣和画谱》,俞剑华标点,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第157页,第319页。
⑬⑭⑮⑳㉑㉒ 夏文彦:《图绘宝鉴》,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3页,第58页,第74页,第74—75页,第75页,第75页。
⑯㊵ 楼钥:《攻媿集》卷七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5页,第265页。
⑰⑱⑲ 朱谋垔:《画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546页,第546页,第546页。
㉕ 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第235页。
㉝㊲ 谢赫:《古画品录》,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第355页。
㊳ 莲儒:《画禅》,《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827页。
㊴ 陶宗仪:《书史会要》,《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第59页。
㊶ 邓椿:《画继》,黄苗子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㊷ 吴大素编《松斋梅谱》,《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第702页。
㊸㊹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印晓峰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第76页。
㊺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8册,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