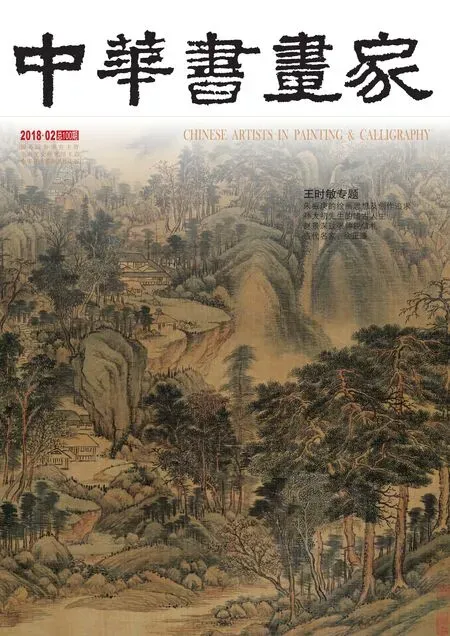猛兽形象在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异变
□ 倪纯如 李英武
在没有照相机、摄像机以及现代科学研究支撑下开放的动物园等辅助手段之前,猛兽的自然属性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对它的观察。正是这种限制,使猛兽形象在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中发生了循序渐进的异变现象,成为一个美术本体受外部因素直接影响的典型。猛兽题材与特定内涵相融形成图式的过程,呈现出相当的特殊性,猛兽的客观形象在唐、宋时期画家的笔下一度生动而写实,却在宋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一
唐、宋时期,随着花鸟画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猛兽题材绘画出现兴盛的势头。集中出现的擅画畜兽的画家有唐代阎立本、韦无忝、李元嘉、李渐,五代时期厉归真、王道求、蒲延昌,宋代包贵、包鼎、赵邈龊、辛成、龙章等。猛兽题材自魏晋南北朝形成的记录功能、宗教叙事、历史与文学典故及民俗祥瑞文化等几种主题,在他们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注重猛兽的真实形象与习性特征的表现,围绕笔墨变化特性与对象特质相结合表现的画面整体意境,展开了诸多探索。同一时期讨论猛兽题材绘画创作的画学理论也逐渐成熟,尤其围绕唐代李渐,宋代包鼎、赵邈龊等几位画虎名家的高下评断,对后世品评这一题材的绘画标准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在绘画中逐渐显现出对虎的表现远多于狮子且造型较为准确的现象。狮子受到画家的“冷落”,朝中任职的士大夫画家记录罕见异兽的形象尚且缺乏图式与理论的总结,宗教与民俗信仰图像中狮子的形象也由于缺乏现实的参照而神化夸张。魏晋南北朝文献记录中与虎同为被绘画表现最多的猛兽类中的狮子,在唐时尚有阎立本、韦无忝为皇帝记录贡狮而绘图的详细记载,元以后却几近消失。在清朝成书的《画史会要》中,阎立本、韦无忝两人记录中没有了画狮一项,唐以后至20世纪前再没有出现以画狮子而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的大画家。狮子的真实样貌渐少有人了解,甚至有误认前代绘画中狮子为獒犬者。
这一现象首先是由现实中人们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认识造成的。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分布有老虎且种类不同,如西伯利亚虎、华南虎、印支虎和孟加拉虎等,人们对虎的描绘和讨论更具普遍性。另一方面,凸显人与虎矛盾关系的典故在历史、文学、民间传说中流传相当丰富,遇虎脱险、虎食人、人猎虎事件,甚至人虎互化的故事,虚实皆有。狮子却大不相同,作为异域进贡的珍稀动物饲养于宫苑内,数量有限且古时没有人工繁育、饲养的知识和技术,观察其生存状态以描绘记录其形态是皇室专职画家或有绘画才能的大臣的专门任务,亲眼得见狮子真容对当时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而对描绘它的作品的高下优劣的评判讨论少有人参与,只能依据传说或前人作品,对狮子的样貌做带有想象夸张性的描述和总结。

图1 [元]佚名 仙女图 123.1×86.2cm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元]佚名 虎(局部) 205×122cm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虎的描绘从技术到理论的不断深化,与狮子在绘画中日益罕见的状态形成反差。陈怀宇在《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一书中指出:早期佛教文献中的十二生肖中的狮子在中国被替换为虎,以“驯虎”叙事塑造高僧形象与身份认同是中国佛教的发明,佛教僧人的名号中常出现的狮字亦逐渐被虎字替代,这三种现象都是由人所处的现实地域环境引发的①。虽然书中并未讨论佛教图像中的狮与虎形象,但为一般民众所熟知的“伏虎罗汉”是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
源自早期佛教的罗汉信仰在中国发展出了独有的形式,“降龙”与“伏虎”二罗汉形象出现,宋以后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几种组合形式,而在元以后出现的“降龙”“伏虎”二罗汉形象完全是中国佛教的创造。这之中既包含佛教传播需要对现实地域环境条件加以利用,也包含中国本土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中的诸多相关因素。而我们在宋以后见到的表现“伏虎罗汉”的图像中,画家将虎作为罗汉法力的参照物,通常画在罗汉座下方,以俯首或回望罗汉的姿态表现其已被佛法驯服。除“伏虎罗汉”外,法力高强的僧人、仙人将狮、虎作为坐骑或驯服的伙伴也开始成为一种固定的组合。元人画《仙女图》(图1)中对两只猛兽的描绘具有代表性,画面中心一白衣仙女坐在席上,身后竹篮中放着灵芝仙草,仙女左右一白虎、一青狮作伴。左手边白虎的描绘除颜色罕见外与真实的老虎形象特征基本吻合,精致的条纹排列组合与细笔勾画的毛发使虎的形象质感格外细腻丰富;仙女右手边俯卧的青狮则与狮子实际形象相差太大,虽然画家仍以细致的线条尽力描绘,但所画之物显然超出了画家能够观察的范围,画中的青狮成了一只“怪兽”。而不论白虎还是“怪兽”,它们在画面中心人物——法力高强的仙女身边,一则面带笑意紧盯仙女手中毛笔,一则懒洋洋地俯卧在侧,全无狮、虎的凶猛,只显得驯顺可爱,更似一猫一狗。
《仙女图》中的组合形式与表现,在之后呈现出程式化,这类作品中的猛兽形象也越来越趋于简化,不管是与行脚僧相伴而行的老虎还是被高僧法力驯服的狮子,在图像中几乎只需要传达出两个关键信息即可:一是辨识度——需要人们辨认出它们,这一点以老虎的皮毛条纹、狮子头部的鬃毛与球状的尾部毛发以及它们的身体尺寸等几个简要的特征为保证;另一点则是它们的顺从。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类图像中对猛兽形象的表现是次要的,让人们看到一只原本凶悍无比的“老虎”表现出完全的顺从,创作者显然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这也是我们无法从宋、元、明、清几代罗汉图像中,发现猛兽题材在绘画中更明显的技法、风格或审美标准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3 [元]归真(款) 虎 25.6×26.6cm 绢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 [清]余省、张为邦 清宫兽谱·狻猊 40.2×42.6cm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二
宋以后,猛兽题材的绘画创作渐衰,专擅画猛兽的画家寥寥,作品数量较少,相关的理论讨论多数只是重复前代画论的内容。除了猛兽动物特性造成绘画者难有机会细致观察、特定主题的表现不需要依赖写实的猛兽形象等因素外,元以后文人画成为画坛主流是造成猛兽题材创作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录元代画家擅画猛兽者仅杨月涧一人②,书中无作品著录。《石渠宝笈》中收录有元人画虎仅四件,包括素绢本著色元人画《虎》两件、元盛懋画《烈妇刺虎图》一卷及元归真画《虎》一件。元佚名画《虎》两件中一为全墨色的作品,画一只身躯较瘦的黑虎蹲踞在山崖下,虎头比例较小,四肢细长,虎面画双眼睁圆用白粉点染过,仿佛发出了亮光,再加上虎口稍向上弯曲的形状,这只黑虎的面部表情显得狡黠而神秘。另一件元人画《虎》(图2),绢本设色,画幅中部画一只身形巨大黄皮黑纹的老虎,虎躯干和四肢都很粗壮,虎面宽但虎头比例并不大,虎眼以金粉涂饰,面颊、上眼睑与额头的花纹被组合成较有规律的图案,这只老虎尾高首低立于青色山坡上,背部隆起、双眼直视,显得威风凛凛,画面有些许紧张的气氛。画无名款,《石渠宝笈》录为元人作,但其中较粗硬的线条与较鲜亮的设色更似明代宫廷画风,且虎额头向中心聚拢且对称的图案化的花纹,也与明人画法更相近。
另据《石渠宝笈》记有元盛懋画绢本《烈妇刺虎图》一卷,钱鼒题写于画卷拖尾的《烈妇行》是赵孟頫听闻妇女胡氏杀虎事迹而作,画中题写诗文缺尾句“呜呼猛虎逢尚可,宁成宁成奈何汝”!
元归真款《虎》(图3)画幅较小,本为团扇,但画家在较小的尺幅中却塑造了一个层次饱满、细节丰富的场景,画面主体分左右两部分,左侧画一只老虎伏在溪边喝水,右侧松树枝干上落着一只老鹰正低头看着老虎。这件作品右侧有经过涂改痕迹的“归真”二字,左侧亦有三字名款,邱世华认为是“李煜画”三字,并认为这两个名款均不可信③,但从技法风格来看应属元人画。
从以上几件作品的记载与实物来看,有明确作者署名者即盛懋画《烈妇刺虎图》,其他皆无署名或署名不实。盛懋身份虽为民间画家,但画风与题材受文人画影响较明显,《烈妇刺虎图》即是源于文学典故的主题创作。其他几件无署名或署名不实者,更无可能出自元时名气较大的文人画家之手。文人画自宋兴起后,以文人士大夫为创作主体,借山水、花鸟抒兴遣怀,深山隐者、江上渔父、“岁寒三友”等意象清静、文雅,形象特征较易掌握且更利于发挥笔墨特点的题材,成为他们绘画创作的首选。米芾《画史》中论绘画题材的选择时已说道:“鉴阅佛像、故事图,以劝诫为上;其次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景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仕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大抵牛马人物,一摹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处高也。”④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论画》一篇论绘画题材时说:“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⑤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总跋》中更是直接指出:“画家应以山水为主也,画山水必须将天地浑然涵胸中,直是化工在其掌握,而天地间飞潜动植,莫不兼绘,即人物、花鸟、畜兽,尽在图中,以为点景,必如是方可谓之有成。……禽兽虫鱼,更属小物。其间复有蝇萤蚊蚁,小之又小者,不堪入画。”⑥这些论述中以山水、人物为上,花鸟、禽兽为下的说法,可代表宋元文人画兴起之后人们对绘画题材选择的普遍认识。一则猛兽题材因本身特性包含更多与暴力相关联的内涵,且在宋元时狮、虎形象都已经是宗教与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具有世俗的祈福功能,这些都使他们的形象远离文人绘画创作“发表个性与其感想”的初衷;二则猛兽形象的描绘塑造需要画家投入更多精力、具备更加专业的造型能力,这与文人画家多强调自身“业余”身份来说也是背道而驰。
因此,作为宋以后画坛主流形态,我们在文人画作品中几乎见不到猛兽题材的踪迹,也更少有专门以画狮、虎闻名的画家,这一变化使得猛兽题材的创作数量与质量在宋元后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现象,直到明清两代书画市场的发展对具有祥瑞祝福内涵作品的需要才稍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宋元时期造成的猛兽题材图式传承的断层,明清时的猛兽题材作品创作水平也再难回到我们在少量作品和丰富的画论中可以看到的唐宋时猛兽题材创作尚真、生动与多样的状态。

图5 [明]戴进 罗汉图 91×29cm 纸本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
猛兽题材经过文人画兴起所造成的备受冷落阶段,到明清时宫廷画师与民间保有文人画意追求但不得不参与书画市场交易的具有多重性身份的画家们,在应对不同需求的情况下继续描绘猛兽,猛兽形象也朝着不同的方向持续发生变异。
身处皇家宫廷中为皇室作画的画师们,具有一般画家没有的条件,他们有的有机会亲眼见到那些只在宫廷中饲养的珍禽异兽,有的能够见到更多内府收藏的前代名家甚至西方画家较高水平的作品,因此在他们笔下,对猛兽形象的描绘还能够基本达到较客观的记录功能。明宣宗《狮子图》在《石渠宝笈》“乾清宫列朝人书画”部中录为“次等”,记“中素绢本著色,画款识云宣德丙午制”;明人画《狻猊图》,画一金黄色狮子趴伏在水流湍急的河边,狮子以工笔丝毛法绘成,头部鬃毛的描绘特别细致,毛发成簇由根根细线勾勒,通过分组与淡墨在底层的分染,突出了厚重的层次感。毛发边缘处以更淡的黄色染出轮廓,使毛发蓬松质感细腻逼真。整体来看,这只狮子无论是身体比例、结构还是局部特征,都十分准确。画中背景树木枝干的画法值得留意,画家在画较粗枝干时以重色晕染暗部,以西人“凹凸画法”突出了枝干的立体感,这件作品的作者应该接触过西方绘画。
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余省、张为邦曾奉旨按照《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中百兽形象绘制《清宫兽谱》,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动物图志。《清宫兽谱》始绘于乾隆十五年(1750),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图文并茂,具有重要的史料、科学及艺术价值。图谱分瑞兽、异兽、神兽以及各种普通类动物共180幅,画法兼工带写,动物形态以工笔画法细致描绘,从动物骨骼、肌肉结构的准确性、使用分染晕染法画边缘与转折处阴影以及画面取景的透视效果来看,绘制画谱的画家们运用了部分西画写实技巧,背景则以小景山水画法为主。经王祖望依据文字说明和图像做物种考证,《兽谱》中现实存在的兽类有61种,包括狮(图4)、虎、豹、狼、犀牛等猛兽⑦。
作为供皇室宗族使用的“工具书”,此图谱对兽类动物的介绍与描绘,出发点是希望具有客观的知识性,但实际却有许多虚构的内容,如“麒麟”“獬豸”“白泽”等瑞兽,另外有部分动物的名称介绍虽基本准确,但图画与实际的形象却有较大出入或文不对图,如“熊”“貘”“恶那西约”等,这些模糊的认识反映出当时人在动物学方面的认知情况。而若不计较此图谱实用的功能,在绘画表现方面图谱中的作品展示了清乾隆年间宫廷中流行的糅合了部分西画技巧的画风,整体细腻精致,虽然在生动性与笔墨意味方面有所欠缺,但在动物具体形态的描绘上,《清宫兽谱》中已经出现了类似我们在晚清以后见到的写实风格。
四
明代韩昂撰《图绘宝鉴·续编》中录明代画家擅画题材中有走兽类者三人,包括戴进、谢宇、陈喜,但均没有具体画狮、虎等猛兽的记载。而在传世作品中可见到一些零散的作品,如戴进画《罗汉图》(图5),画中罗汉手持法杖端坐于山石树下,左手伸出抚摸座下老虎额头,门后有一侍童面露惊恐之色。这件作品中所见老虎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完全驯服的,而类似这样的驯服与和气也是宋元之后我们在猛兽与人共同出现的一类绘画作品中可见的狮与虎最常表现出的状态。
清代徐沁撰《明画录》中记载四人擅画虎,即陈希尹、商喜、赵廉、何雪涧,清王原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中记有“赵廉湖州人,善画虎,人称赵虎(《画史会要》)”,《石渠宝笈》中录明人画猛兽题材的作品除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明宣宗《狮子图》、明人画《狻猊图》《驺虞图》外,还有明赵汝殷《风林群虎图》及明沈周《虎》。据《石渠宝笈》“养心殿”部记明赵汝殷《风林群虎图》(图6),画林泉间或行走、或坐卧、或饮水、或嬉戏等姿态各异的老虎共计28只,这些老虎同样有躯干粗壮、头大颈短且虎额花纹刻意绘成对称图案的统一特点,画家虽以工笔丝毛法画老虎皮毛,但处理条纹时墨色与用笔粗细缺乏变化,略显呆板。明沈周画《虎》在《石渠宝笈》中被列为明人画之上等,记:“素笺本著色画,款题云‘西山人家傍山住,唱歌采茶上山去。下山日落仍唱歌,路黑林深无虎患。今年虎多令人忧,绕山搏人茶不收。墙东小女惊涕流,村南老人空髑髅。官司射虎差弓手,自隐山家索鸡酒。明朝入城去报官,虎畏相公今避走。’沈周下有‘启南’一印,轴高一尺七寸五分,广九寸三分。”这件作品的主题在题跋诗文中得到说明,讲述虎患害人,但暴戾贪婪的官吏比老虎还更加凶恶。而典故中包含猛兽且成为绘画主题的作品在明朝还有仇英画《二十四孝图》册页中《杨香搤虎救父》一页(图7),表现的是杨香搤住老虎使其趴伏在地,进而使他父亲逃脱虎口的场景。画家使用较简单的线条勾画人物与虎,老虎头大身粗、眼小鼻短,条纹较短近似斑点,额部花纹聚拢像花朵,并不显得十分凶恶。由以上明代画虎作品看,越来越多画家开始有重复前人图式之嫌,画中老虎头大颈短、额纹图案似花等特征都十分接近,并且在清代画家笔下被继续沿袭。

图6 [明]赵汝殷 风林群虎图(局部)

图7 [明]仇英 二十四孝图·杨香搤虎救父(局部)

图8 [清]陈农 太师少师 27×19cm 绢本设色
清马负图画《虎》一轴,图中一只老虎蹲坐于画面最前端,远处山崖耸立,间有瀑布流水,老虎头部比例较大且没有画出脖颈,使这只蹲坐的老虎身形轮廓浑圆,虎面部刻画较细致,虎额与脸颊的纹路、口鼻须发的位置比例关系基本准确,表情温顺,但因脖颈较短而显得好像微微耸起的肩膀使它看起来有些胆怯、滑稽。老虎虽相对于因产地遥远令人感到神秘而陌生的狮子来说更为国人熟悉,但毕竟是凶猛可伤人甚至食人的野兽,在明清画家的作品中除了主题较单一外,也显示出了对虎的形象描绘程式化、简单化的问题。
古代官制太师为三公之首,少师为三孤之首,所以“三师”与“太师少师”以及群狮样式都有祝福一个家族代代为官的寓意。明清时以“三师”“太师少师”等寓意吉祥主题的猛兽题材作品较多流传于民间书画市场中,在活动于扬州、上海等地区画家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少群狮、群虎式样的作品。清中期画家华嵒有三张《三狮图》传世,陈农、黄小裳、童衡、张灏几人各作有同题为《太师少师》的作品,任预作有《五狮图》。这些寓意祝福、祥瑞的作品中狮子的形象,不论画法工细或放逸,通常被画成色彩斑斓、鬃毛成卷、神态祥和、雌雄不分、成群戏耍的样子(图8),与真实的狮子形象相差甚远,但却与民间工艺如石雕、年画、布偶甚至舞狮形式中狮子的形象一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客观条件所限外,明清时逐步兴起的书画市场中购买力主要来自富庶的市民阶层,对吉祥寓意的喜好以及认识上相同的局限性使购画者并不在意画中动物形象“写实”与否,他们与画家一样可能更加熟悉官宅门前头顶发卷、脚踩藤球的石狮,以及工匠缝制的额头有“王”字图案的布老虎,因此,画家以美好祝愿的寓意为题画出张嘴微笑的彩色“狮子”的作品并不会遭到拒绝。
清郑绩撰《梦幻居画学简明》中对“畜兽”一门的讲解则是宋元以后画论中最详细的一篇,《畜兽总论》解释“畜兽”为“四足为毛之总称。野产者谓之兽,豢养者谓之畜。其性善走,亦名走兽。凡走则四蹄双起,前蹄跳,后蹄踢,飞奔作势,如车之转轮,如舟之拨棹。行则前右足退步在后,后左足亦在后,前左足进步向前,后右足亦向前。谚云‘左上右落,前进后退’,此天生自然之理也。”论画畜兽需认识清楚不同种类的特点,否则易出错误,“其错处画者固不自知,看者亦常不觉。故画学与格物之工,均不可少。”又言古人画虎者之代表为赵邈龊与辛成,最终说出画畜兽的标准为“凡画兽故须形色认真,不致画虎类犬,又不徒绘其形似,必求其精神筋力。盖精神完则意在,筋力劲则势在,能于形似中得筋力,于筋力中传精神,具有生气,乃非死物”⑧。
《畜兽总论》后《论畜兽》则详列狮、虎、象、狐、牛、马等具体动物的形象与习性特征,如:“狮为百兽长,故谓之狮。毛色有黄有青,头大尾长,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闪电,巨口耏髯,蓬发冒面。尾上茸毛大如毬,周身毛发松猱如狗。虞世南言其拉虎吞貔,裂犀分象,其猛悍如此。故画狮徒写其笑容而不作其威势,非善画狮者也。”“虎为山兽之君,状如猫而大如牛。毛黄质而黑章,锯牙钩爪,四指不露甲,须健而尖,舌大如掌,满生倒刺,项短鼻齆,眼绿如灯,夜视则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白虎曰甝,黑虎曰虝。伏则尾垂,昂立尾竖。先写其形影,次用黑点斑而后渲染赭黄,俟干加须点睛,以取威势。”⑨作者虽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他所知道的狮子的形象特征,但显然“毛色有青有黄”“目光闪电”之类描述并不是来自亲眼目睹的真实经历,而是拼凑前人文献中的说法而成,虽然末句强调表现“威势”才是画狮子最重要的要求,但也认为“笑容”是画狮时应当具有的特征。这一说法既体现出作者所见同时代画家画狮作品的普遍特征,同时也说明了他对狮子形象的陌生与误认。这样的理论与作品同样说明了,缺乏驯服、豢养或其他使人能够充分观察凶猛野兽尤其是异域物种的技术手段,画家实在难以完成细致描绘其形象的任务,而普通民众对它们的认识更是长期停留在模糊、夸张及概念化的阶段。
注释:
①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5页。
②[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01页。
③邱世华《虎踞鹰扬——元归真〈画虎〉小探》,《故宫文物月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10年2月第323期。
④[宋]米芾《画史》,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214页。
⑤[明]文震亨《长物志》,重庆出版社,2010年3月,第65页。
⑥[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209页。
⑦故宫博物院编《清宫兽谱》,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⑧[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第1199页。
⑨[清]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第1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