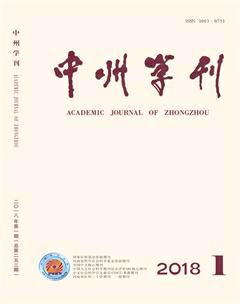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色及其意义
武鹏
摘 要: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相较于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在与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进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参考。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渐进式改革;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1-0014-06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其间,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不迷信,不盲从,从而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方式方法和经验策略。这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逐渐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打破了自东欧剧变以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终极神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一套新的、富有吸引力的模式选择。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色及其成功实践的国内、国际意义加以归纳总结,有助于我们更广泛深入地理解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道路:激进与渐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欧亚大陆上相继诞生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起初,这一体制加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战后恢复进程,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历经10年左右的实践后,其也逐渐显露出一系列的问题,如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生活用品供应偏紧、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为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试图有限度地引入市场的调节作用。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始终未能达致合意的效果。历经了长期探索后,“建立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获得了广泛认同,绝大多数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步入了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这一进程涉及了30个国家,覆盖了全球近30%的人口,堪称20世纪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浪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东欧剧变的发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以我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即在不骤然打破原有体制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引入、培育市场经济因素,以最终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常被称为“中国模式”;另一种方式是以俄罗斯等多数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改革,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时推进产权私有化、契约自由和宏观经济紧缩,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常被称为“休克疗法”。各个国家无论选择何种改革方式,其目的都是要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繁荣富裕。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来审视改革的效果,渐进式改革要明显优于激进式改革。借助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我们对此可以获得一些直观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至2015年,中国以10%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仿照中国模式进行渐进式改革的越南,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了6.8%的较快水平。相比之下,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作为理论指导,选择走激进式改革道路的东欧各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大多不到2%,不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也只是达到了3.7%,表现最差的乌克兰甚至未能恢复至改革前的水平,俄罗斯则仅达到0.5%。两种改革方式的成效呈现如此巨大的反差,以至于很多顽固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激进式改革是失败的。
事实上,激进式改革给当事国带来的创伤还远不止经济增长数据所呈现的那么简单,部分负面影响甚至持续至今。
第一,“休克疗法”所引发的突如其来的经济社会秩序大混乱,给当事国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即使是在号称激进式改革“优等生”的波兰,“休克疗法”也曾导致了1990年到1991年工业品产值下降40%,GDP下降近20%,失业率从0%蹿升到1994年春的17%,1990年末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50%,并且到1991年底还处在70%的高水平上,1992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6%。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贫困不断蔓延,企业间的拖欠不断上升,大量的养老金补偿没有得到支付,银行资产组合中的坏账在增加,黑市经济和逃税行为横行并且日益泛滥(科勒德克,1999)。有鉴于此,曾亲身经历了激进式改革的波兰前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科勒德克将“休克疗法”讥讽为“没有疗法的休克”(科勒德克,1999)。
第二,激进式改革导致多个当事国的民族资本被西方国家剥夺控制,曾经较为发达的、独立的工业体系趋于瓦解,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国家核心竞争力丧失殆尽。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经济较发达的东欧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美籍波兰裔学者波兹南斯基(2004)提供的资料显示:2000年,西方资本在工业和银行业中的比重,波兰为40%和75%,捷克為35%和65%,爱沙尼亚为60%和80%。私有化过程中,波兰的工厂和银行资产被仅以相当于其实际市场价值10%或20%的价格卖了出去,多年累积起来的资本约有90%左右蒙受损失,成为主要来自西欧国家的买主们的利润。最后,激进式改革过程中,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民族资本虽然避免了被西方剥夺,但却集中到了国内寡头的手中。据统计,俄罗斯500家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只卖了72亿美元,许多大型企业的售价仅相当于西欧一个中型面包作坊的价格(金雪军和杨晓兰,2002)。在财富分配高度不公的同时,强大的寡头利益集团还与政客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从而严重恶化了国家治理能力,加剧了政治腐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典型的如乌克兰,经济寡头化导致了寻租泛滥,政治成了大资本控制的“提线木偶”(张弘,2016)。寡头及其政治代理人之间的竞争乃至争斗,极大地恶化了政治稳定,割裂了国家认同,成为近年来该国内乱分裂的重要诱因。endprint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实践
与弊端丛生的激进式改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赞许。2004年5月,英國著名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的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在否定“华盛顿共识”的同时,通过总结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北京共识”,并指出,中国模式不仅适合于中国,同时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仍有少数激进式改革的支持者在极力地为其失败进行辩护,力图将以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归于某些特殊的客观条件,进而弱化乃至否定改革方式与改革绩效之间的关联。其最主要的辩护理由包括两点:一是中国在转轨之初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低于苏联解体前的苏东各国,那么,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推论,其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较小,更易于吸收前沿国家的技术外溢,进而其经济增速快于大多采用了激进式改革方式的苏联解体前的苏东各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将两者间转轨绩效的差异过多地归于转轨方式的选择。二是与苏联解体前的苏东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中包括典型的城乡分割特征,体制改革后劳动力在城乡部门间进行再配置将会显著提升社会的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无非是发展经济学早已阐述了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而已(Sachs & Woo,1994; Sachs et.al,1994)。然而,通过对比各国(或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述两点辩护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经不起实践推敲的理论观点为自身经不起实践推敲的理论观点来辩解。进一步来讲,对这些辩驳的分析,恰恰印证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实践检验是十分成功的,具体来看有下面几点。
第一,二战后除了“亚洲四小龙”外没有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或地区成功跃升为发达国家,国家或地区间贫富差距的固化、扩大而非收敛,才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常态。如Pritcherr(1997)的研究显示,1870—1990年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和最富裕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扩大了5倍;Maddison(2001)的研究显示,1950—1998年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了1.75倍。收敛的证据即使存在,也主要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之间或其内部各区域之间,这意味着实践中的收敛是有条件的,呈现出“富国俱乐部”的特征。作为新古典增长理论创立者的索洛便曾指出,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可能呈现经济趋同,但更大范围内则没有趋同的趋势(Solow,2009)。
第二,在转轨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也并未呈现出收敛特征,即使是条件禀赋更为相近的苏东各国,其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维持乃至强化了改革之初的差异格局。如Rapacki & Próchniak(2009)对1990—2005年苏东27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不仅未呈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甚至还表现出了发散性;侯铁建和王威(2013)对1991—2011年苏东27个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受制于经济转轨各国初始禀赋条件的差异和不同路径选择,其相互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这一差异目前依旧存在,甚至有所扩大。
第三,二元经济结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并非中国所特有,但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跳出了贫困陷阱,实现了经济的赶超式发展。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很多时候它可能只是作为经济不发达的一种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因而出现的。二是二元经济结构至多只能解释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能够达到的经济增长水平,而无法解释高速增长的部分;或者说,二元经济结构只能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一般性的经济增长,但要用来解释中国这般的奇迹式增长则是明显不够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古典主义的二元经济增长理论①,都无法从实践上否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相较于经济缓慢增长的乃至陷入了转型陷阱和贫困陷阱的大多数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顺利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时还从低收入国家快速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即成功地完成了“双重过渡”②。正是在这种“万马齐喑,一马当先”的事实基础上,“北京共识”成功取代了“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赶超式发展的世界性范本。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色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国民经济基础差、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度不均,同时又缺乏理论和经验指导的背景下起步,不断克服国内外一系列艰难险阻,走出了一条举世瞩目的成功道路。其在与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鲜明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先易后难,从薄弱环节打开突破口。由于渐进式改革没有骤然打破原有的利益关联格局,为尽快开辟局面,需要从利益关联少、改革阻力小的环节率先入手。比如,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然后再推进至城市部门。一方面,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分割制度使广大农民在旧体制中获益最少,被“挖得太苦”;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过剩、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导致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过低,生活普遍较为穷困。这使得农村内部积聚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农村和农业改革所面临的助力要远大于阻力,改革易于得到施行。农村改革过程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增强了城市部门全面改革的信心,为城乡商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打下了基础,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扩展。
第二,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逐步展开。这种俗称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一方面降低了改革中的学习成本和适应成本,另一方面避免了个别决策的失误演化成系统性、颠覆性的重大错误。典型的例子如我国对外开放在空间范围上的逐次推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先在南方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加了天津、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同时还将经济开放区扩展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胶东半岛、辽东半岛等片状区域;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将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扩展到内陆和边境口岸城市。近几年来的自贸区建设也充分彰显了这一特色。2013年,我国率先成立了上海自贸区;2015年,在东部沿海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2016年,新批准的辽宁、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重庆、陕西等7个自贸区,在分布范围上从东部地区逐渐拓展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逐渐覆盖了全国四大区域板块。endprint
第三,增量改革先行,带动存量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僵化的资源配置体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具有极强的刚性结构,推动其改革的难度很大。为此,我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基本没有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基础,而是采取一些修补的办法来暂时维持其运转,以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将主要的注意力转移到增量上来,允许并鼓励私有经济和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渐引入市场调节作用。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国有经济和市场力量逐渐壮大,与国有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时,一方面,国有经济面临着非国有经济愈益紧迫的外在竞争压力,改革开始形成倒逼机制;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对国有经济改革的物质补偿能力,稀释了改革成本。最终,国有经济改革的阻力被层层弱化,市场化改革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顺利推进。
第四,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首先,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改革都是以发展为最终目标和根本出发点的。其次,要实现发展与改革的目标,需要长期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我们开拓一切事业的根本前提。最后,改革是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根本动力,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繁荣都离不开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简明言之,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非常注重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较好地实现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有机统一。
第五,绕开争论抓紧干,先干再说不怕错。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有着极强的紧迫感,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曾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现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③然而,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差异,观念转变有先后,改革积极性有高低,加之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将大家意见统一起来的难度非常之大,迁延不决地争论在所难免。对此,绕开争论,抓紧时间推进改革与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争取时间干,不要争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④进一步地,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⑤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参考书,没有活案例,“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蹚错一步,在所难免。如果因为怕犯错误、怕担责任而畏葸不前,靠“不干事”来保障“不出事”,则难免会得不偿失,最终耽误改革进程。为此,只要出发点契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中国的改革事业对先行先试者一贯秉承“允许犯错、宽容失败”的态度。
四、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实践的意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改革的“中国模式”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第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重大挫折,陷入了低潮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借机放言社会主义的失败,妄谈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顶住了压力,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来逐渐引导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打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局面,用事实回击了西方反动势力的猖狂攻击。中国模式的实践证明,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苏联斯大林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只要找对方向走对路,社会主义必定能够重新焕发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如今的中国,犹如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灯塔,照亮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前途,引导并鼓舞着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继续追求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第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令中国人民怀着前所未有的信心踏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近现代的中国曾饱受侵略与压迫,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族自信心,使部分人滋生崇洋媚外的心理。然而,正是由于国家身处逆境,激励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地探索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道路。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苏式”计划经济等一系列尝试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终于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正确的道路,用不到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00多年走过的发展历程,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文化影响力迅速扩大,彻底改变了积贫积弱的旧面貌。改革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凝聚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围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目标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大好局面。
第三,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然而在改革之前,我们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将社会主义教条地理解为计划经济,将资源配置的手段等同于社会性质,未能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走了不少弯路,耽误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鉴于此,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注重解放思想,结合中国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厘清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做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伴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成果相继问世,持续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强化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参考,“中国模式”逐渐成为推动经济起飞与实现现代化的学习样板。二战后,除了“亚洲四小龙”没有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或地区能够成功跻身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经济赶超和实现现代化成了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面对如何快速提升人類福祉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难题,全世界都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对此,西方国家开出的所谓“自由民主”的药方,不仅没有成功地指引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分裂和动荡,让那里的人民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像近来的叙利亚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子。目前,除了越南等体制转轨国家外,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学习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中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近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星——埃塞俄比亚,从政府到民间都在积极、认真地学习“中国模式”,“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区”“五年计划”等中国概念、中国符号被大量吸收进其国家发展战略中。相应地,埃塞俄比亚经济在最近的10年里保持了11%的高速增长,摘下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国家的桂冠。⑥放眼当今世界,中国模式正在逐渐取代西方国家宣扬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模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选择。endprint
注释
①古典主义范式是指边际革命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和劳动力无限供给。尽管刘易斯的论文中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刘易斯自己的说法,他的文章仍是建立在古典框架上的。参见邵晓、任保平:《古典主义范式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述评》,《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此后,刘易斯模型经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发展,形成了古典主义框架下分析二元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②“双重过渡”的概念最早由陈宗胜在1995年提出。
③上述讲话内容未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邓小平年谱(1975—1997)》和《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参见中央电视台、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7年联合摄制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12集。
④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⑤参见《视察上海时的谈话》(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7页。
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分国家或地区2004—2015年GDP增长率数据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1]Maddison, A.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ECD, Paris, 2001.
[2]Pritchett, L. Divergence, Big Time[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3), pp.3-17.
[3]Rapacki, R. and M. Próchniak. Economic Growth Accounting in Twenty Seven Transition Countries: 1990-2003[J].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Volume 47,Number 2/March—April 2009, pp.69-112.
[4]Sachs, J. and W. Woo.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Experience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C]. in Lee, C. and H. Reisen eds. From Reform to Grow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ECD, Paris, 1994.
[5]Sachs, J., W. Woo, S. Fischer and G. Hughes.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J]. Economic Policy, 1994, 9(18), pp.101-145.
[6]Solow, R. M. 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C]. in J.B. Taylor and M. Woodford eds.,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Vol.1a.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pp.637-667.
[7][波]科勒德克.從“休克”失败到“后华盛顿共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2).
[8][美]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陈宗胜.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双重过渡[J].天津社会科学,1995,(6).
[11]侯铁建,王威.《转轨国家的经济收敛特征:再检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12]金雪军,杨晓兰.转型经济国家的管理层收购——以俄罗斯及东欧国家为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3).
[13]邵晓,任保平.古典主义范式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述评[J].福建论坛,2009,(6).
[14]张弘.乌克兰政治稳定中的腐败问题[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4).
责任编辑:浩 淼 思 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