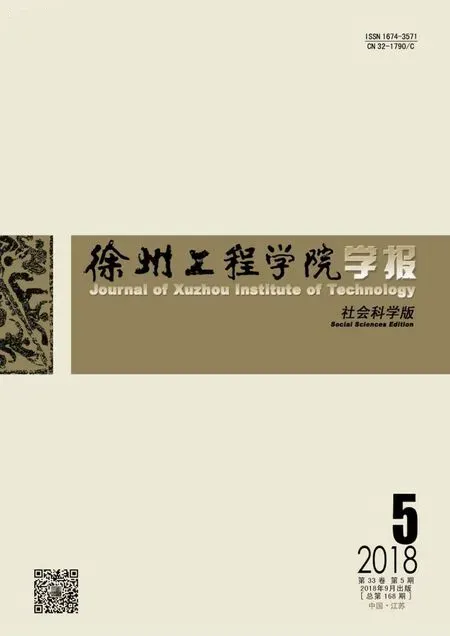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活动六议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政治暗杀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对于革命党人宣传、实行的暗杀活动,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的认识与评价是不尽相同的。某些当代学者之所以对暗杀活动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其理由不外乎是:部分革命党人存在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不愿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悲观绝望,存在着侥幸取胜的心理;从事个人暗杀不但不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反而打乱了革命党的起义部署,危害了反清革命大业;政治暗杀活动导致大量革命骨干的无谓牺牲,大伤革命的元气。甚至称政治暗杀为恐怖主义,指责从事暗杀活动的某些人是革命的投机分子。
近年不少学者在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指出了其不足与局限。对此,笔者基本上是认同的,但仍想就以下六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不是实行恐怖主义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进行的武装斗争与政治暗杀,很多时候是可以明确区别的,但有时则表现出兼而有之、混而合之的特点。例如,1911年4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黄花岗起义时,革命党人林时爽即曾明确表示,如果武装起义“举事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1]310。事后有人记述这一起义时也说,在起义前的一次会议上,尽管革命党人的热情高涨,“热度可沸”,但却“非复(有)军事布置”,皆“认定此处为大暗杀”[1]310。革命党人对政治暗杀活动利弊的认识虽有所不同,但却基本上形成了反清斗争“主流曰革命,支流曰暗杀”[2]282的思想共识。
辛亥革命前,部分革命党人认为,正是因为历史上的刺客绝迹,才使得君主们无所畏惧,实行野蛮的专制主义。为此,他们或极力宣扬革命者应“沐浴于腥风血雨之中,壮游于炮雨枪林之际”,学习“张良之大铁椎,荆卿之利匕首”精神,仿效历史上侠义之刺客,“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吴魂:《中国尊君之谬想》,《复报》,第1期。。或大声疾呼,“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人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极力宣传如西方的无政府党那样,“左手挟唯心论,右手掷爆裂弹”,对清廷大员进行“十步之内,血火红飞”*无首译:《帝王暗杀时代》,《民报》,第21号。政治的暗杀。他们认为,采用“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3]53的暗杀方式,“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的武装起义,实是更具实效性,两者“不可同日而语”[3]24。为此,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党人对清廷重要官员先后进行过数十次政治暗杀。但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绝不是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在宣传和实行恐怖主义*对此,有些人表述的较为隐晦、含糊,如有人说,革命党人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暗杀活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有的人则明确提出,部分革命党人从事的是“个人行动和恐怖主义的暗杀活动”;有人认为革命党人的暗杀,是“幻想通过一些英雄行为和个人恐怖主义手段唤起人民的觉醒”。更有人非常明确地说:“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当时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这种暗杀行为,我们曾经称之为‘革命义举’,但要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这就属于典型的‘恐怖主义’了。”。理由有四。
其一,革命党人自始至终,仅仅是“把组织暗杀作为重要的革命手段之一”[4]98,而不是革命的全部或唯一形式。除吴樾一人之外,几乎所有的革命党人皆将武装起义置于各种革命形式的首要位置,而将暗杀置于次要位置。
其二,部分革命党人认为,革命初期的思想先知先觉者,为了“寒奸贼之心,醒国民之梦”,首先需要对广大国民进行思想宣传鼓动工作,但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我有笔墨,敌有刀斧”,革命“志士之血终不足饱民贼之刀也”。在革命者“欲图大举,又苦羽翼未丰”的情形之下,革命者“不得已而先之以暗杀”。他们遍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后发现,在“堂堂正正之国民军出现以前,未有不以如鬼如蜮之侠客壮士为先锋者”,先行从事暗杀,“苟能循序而进,吾知其必有功也”*竟庵:《政体进化论》,《江苏》,第3期。。其后,也不断有人重申这一思想认识。他们说,革命党人对清廷大员进行政治暗杀,“狙人不备,收其大勋”,若就其方法与手段而言,不免有些“蜮之射影,则又近乎阴险”。但是,此又为“不得已而用之,所谓济变之术也”,因为在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中,“人之于雠敌,心欲去之而力不足以显然相攻,则尝出于暗杀”*寄生(汪东):《纪清贝勒溥伦来东后事》,《记事栏》,二页,《民报》,第18 号,总2927-2928页。。也就是说,人们采取政治暗杀之法,乃是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得已而为之的计出中下之举。
然而,也有部分革命党人认为,实行政治暗杀乃是反清革命的光明正大之举。如温生才谋炸广州将军孚琦被捕后,犹“侃侃谈主义”。两广总督张鸣歧审问其“何故暗杀”,温生才胸怀坦荡地回答说,非暗杀,实为“明杀”。张鸣歧又问其“何故明杀”,温生才再次正色回答说,“杀一孚琦,固无济于事,但借此以为天下先”[5]1326,可以唤起更多国人的革命意识。
其三,有相当多的革命党人意识到实行政治暗杀,乃是“匹夫提剑”的个人行为,“屠恶有限”,因此不能成为“吾党之专策”*揆郑(汤增壁):《崇侠篇》,《民报》,第23期。,只能作为革命“要求之发韧,而不足以尽要求之成功”*鸿飞(张钟瑞):《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河南》,第4期。。湖北的革命志士更是认识到,实行个人的暗杀活动,“不足以摇撼全局”,经反复认真地研究后,“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6]11。
即使是鼓吹暗杀最力的吴樾,也并非完全排斥武装起义,他一面高倡、践行个人暗杀的方法,一面高张革命的旗帜。他说,采用暗杀的方法杀掉慈禧太后,是为了“去其主动力”,杀掉铁良等清廷大吏,则是“去其助动力”,但是要想取得排满革命的胜利,则必须同时实行“革命主义”“不得不出以革命”,并大声疾呼“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愿吾同胞一行之”*吴樾:《暗杀时代》,《民报》增刊,《天讨》。。
纵观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宣传、从事暗杀活动的同时,又在千方百计地联络会党、策动新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最终以武昌起义和各省的独立响应而彻底推翻了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建立了共和国。
其四,当时的进步人士对暗杀的内涵有过认真的分析与论述。他们认为,真正的暗杀,应是为了除害而不是为徇私;是为了伸公理而不是为名誉;是为了排强权而不是为报复。“使为徇私而暗杀,则暗杀不得为暗杀,而为谋杀;使为名誉而暗杀,则暗杀不得为暗杀,而为好杀;使为报复而暗杀,则暗杀不得为暗杀,而为妄杀”。因此,“非有正当暗杀之目的者,不可言暗杀之言”,“暗杀诚出于至诚至公而不可假借者也”*民:《普及革命》,《新世纪》,第23期。。尽管鼓吹实施暗杀的革命党人未必都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但就其政治暗杀的社会实践来看,革命党人进行的大小数十次的政治暗杀对象,都被严格限制在清最高统治者及顽固反对、镇压革命的清廷权贵或地方大吏范围内,并未对其他一般的满族无辜平民或普通清军士兵进行血腥杀戮。
二、暗杀活动是否给统治者提供了反对和镇压革命的口实
有学者针对史学界有关部分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的种种“有害无益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谓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但他同时又说:“毋庸讳言,暗杀活动确实有它消极作用的一面。如果打击不准,殃及无辜,就会不得人心,容易脱离群众。如果滥施恐怖手段,影响社会治安,就会引起人们反感,甚至把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推到敌人的怀抱里。”他举例说,1900年史坚如谋炸德寿之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一轰不中,反而使后楼房地方倒塌房屋八间,压毙男女六人,压伤男女五人”。于是,“德寿在告示中抓住这一点来挑拨人们对革命党的不满”。史坚如从事暗杀活动时,“轰塌民房,毙伤无辜的后果给了敌人诬蔑革命,煽惑群众的口实。这是史坚如事先没有料及的”[7]210-211。其他学者,亦有同样的认识。他们认为,“政治暗杀活动,如果筹划不周全,技术不熟练,可能会造成打击不准,殃及无辜的恶劣后果”。史坚如行刺德寿,李沛基行刺凤山等等,都“为敌人煽惑百姓、镇压革命提供了口实”[8]。
笔者认为,上述的观点从某一方面来看是对的,然而却只谈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人们是否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人类的政治社会领域内,革命与反革命,双方在政治立场、政治利益方面是根本对立的,无论革命者采取暗杀的方式,还是武装起义的方式,都会遭到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与反对。不但革命者进行的政治暗杀活动会给统治者提供反对革命的口实,革命者进行的武装起义,同样也会给统治者提供反对革命的口实。即使革命者仅仅从事反清革命的文字或思想宣传,同样也会被统治者罗织以诸如“无君无父”“谋乱叛逆”“大逆不道”“异端邪说”等罪名。清统治者要想反对、镇压革命,无论革命者采取怎样的方式,统治者都会寻找口实,没有口实,也会无中生有地制造口实,在政治斗争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若不想为清统治者制造镇压革命的口实,方法只有一个,即不再宣传和从事革命,转而为封建统治的专制制度和清统治者大唱赞歌。
革命党人进行暗杀活动,的的确确存在着种种不足与局限,但所谓暗杀活动为敌方反对革命提供了口实的论点,则其所依论据不足为凭,尚需认真研究,详慎推敲。
三、暗杀活动是否打乱了革命派武装起义的部署,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革命党人曹亚伯曾指出,温生才的个人暗杀行动,“促虏之提防,而为我之障碍”[9]233。黄兴也曾多次谈到,“温生才则不谋于朋友众人,一击而杀孚琦”,“使彼惊骇而预防,真吾党之大不幸也”[10]76。曾参预密谋广州起义的应德明在其回忆录中也说过,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实基于三月初九日刺孚琦太易也”[11]323。
当代学者根据上述史料断言:“暗杀活动不仅动摇不了封建统治基础,而且往往牺牲许多革命骨干,暴露革命组织,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如1911年黄花岗起义之前,温生才枪杀孚琦,引起清政府的严密戒备和大肆搜捕,打乱了原来的起义部署,使筹备已久的广州起义不得不改变计划仓促发动,终归失败。”[12]还有的学者认为,温生才的个人暗杀活动,“引起了广州官吏的严密戒备和大肆搜捕,结果使筹备就绪的广州起义不得不改变原划计而仓促发动,因而各方面力量来不及联系,起义不能顺利进行,终归失败”[13]。另有学者也说,温生才刺杀孚琦之举,“引起了广东地方当局的高度恐慌,广州城内因此‘防日严密,侦探四出。旗界戒严,按户查诘’。结果使革命党人筹备就绪的广州起义不得不改变原计划而仓促起事,各方面的力量来不及协调,起义未能顺利进行,终归失败”[8]。
若按上述观点的逻辑分析,如果没有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武装起义就应该取得成功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自1900年至1911年10月,除武昌起义外,革命党人发动的十余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每次起义失败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在此,我们姑置不论。但有一点应是确定无疑的,即决非是因为部分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而导致了这一系列起义的失败。
革命老人吴玉章在《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运送军火的失事,叛徒的混入以及陈炯明、胡毅生等人的临阵脱逃等等”,都是造成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因素”,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单纯军事行动”,则是此次“广州起义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14]63。在同一篇文章中,吴玉章又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了革命党人历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共性原因。他说:“要举行武装起义,必须首先作好艰苦的群众工作……只有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动起义,起义才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反之,任何脱离群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是冒险行动,而一切军事投机和冒险行动,总是要遭到失败的。”[14]45
对于吴玉章先生的结论,笔者是认同的。不过,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与武装起义,除此因果关系外,还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另一种关系。
如果就某一次具体的政治暗杀与武装起义的表面因果关系,或是其时间的先后逻辑而言,温生才暗杀孚琦的行动,似乎是导致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就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而言,某一暗杀活动的出现,却又恰恰是武装起义失败的产物,是部分革命党人转变斗争方式的表现。对此,革命党人刘揆一曾有明确的表述“时党员因屡次倡义,中途失败”,故此革命党人才“多持暗杀主义,而私自觅师学习炸药者”[9]292。
我们以同盟会的第二和第三号领导人黄兴和汪精卫为例试析之。
据章士钊记载,华兴会在讨论革命计划时,大多数人皆认为“当然以暴动为主,而暗杀亦在讨论之列,特后者(指暗杀)克强不甚赞成,而笃生认为必要”[15]140,也就是说,黄兴本人最初并不十分赞成采用暗杀的革命方式。1911年4月,孙中山等革命者决意“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16]242,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结果却是再次遭到失败,革命力量损失殆尽。刘揆一在其所作《黄兴传》中说,黄花岗起义惨败后,黄兴因“悲痛吾党殉国之惨,牺牲之大,即欲俟伤愈后,躬自暗杀最为仇敌之人,以报死难诸友”[9]299。黄兴本人也说,自己“痛此役之失败,同志之惨亡”,于是欲行个人主义,准备采取暗杀的方式,“狙击张(鸣岐)、李(准)二凶,以报同志”[9]170。
汪精卫最初对暗杀活动也持怀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他曾说:“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可得,直小儿之见而已。”但是后来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屡起屡败,革命形势陷入低潮。“这一切刺激了年轻脆弱的汪精卫,使他决心为暗杀而献身,‘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希图以此挽救革命”[17]11。
孙中山先生也说,正是由于革命党人发动的十数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4]102,才导致了1910年3月的汪精卫、黄复生谋刺摄政王载沣之举。
四、政治暗杀是否导致大量革命骨干的牺牲,使革命元气大伤
从事政治暗杀是十分危险的活动,无疑会死伤许多坚定而激进的革命志士,对此,革命党人有所反思,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但是若据此而认定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导致大量革命骨干的牺牲,使革命元气大伤,则似属偏见,至少是片面的。
在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运动中,无论是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还是采用暗杀的手段,都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都是要有较大伤亡与牺牲的。如果仅就数量而言,牺牲于武装起义中的革命骨干,要远比暗杀活动更多。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即开始筹备新的起义。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秘密会议,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16]242。
为此,革命党人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以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总筹此次起义的各项工作。革命党人总结了以往参加起义人员复杂、起义时不易统一指挥的教训,分别从南洋各地及国内南方各省抽调革命党人,组成“选锋队(即敢死队)”,初为500人,后增加到800人。按照革命党人刘揆一的说法,此次起义是同盟会“集全力为最后之奋斗。在东本部党员被派赴香港与各省,几为之空”[9]295。
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既是同盟会筹备策划时间最长、决心和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同时也是革命骨干牺牲最为惨重、革命元气伤害最为巨大的一次起义。据曾参预密谋黄花岗起义的应德明说,“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同志,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实际上,此役死难的革命党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11]324。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其发动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虽“踬踣者屡”,但“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对此,孙中山颇为痛惜,“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16]50。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孙中山再次沉痛地表示,此役“死事者七十二人,皆国之俊良也”[18]65。黄兴于失败之余,欲直接暗杀清廷大吏张鸣岐或李准。赵声因深感此后举事大难,愤而成疾,临死前痛吟“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句,“目闭而泪出不已”[9]315。而主张暗杀最烈的杨毓麟亦因此次起义失败,使得革命党“同志精华,澌灭殆尽”[9]322,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于同年的7月8日,在英国蹈海而死。
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原因很多,也许如有人所说,温生才私自行动,刺杀孚琦之举,过早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但此次起义,同样存在着事前准备不足,“非复有军事布置”;革命党人意见纷纭不一;力图依靠少数选锋队员突袭等军事冒险的思想。事后有人指出,革命党人在此次起义中,“可谓绝无耳目,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彼”,“一切行动,无殊盲斗”,“以此少数而敌多数,无殊白供牺牲”[1]310。
其实,在辛亥革命的初期,在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牺牲一二革命志士从事暗杀活动,比发动武装起义损失要小得多。为此,汪精卫与胡汉民发生过一次同志式的争论。
1908年前后,由于革命党人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一些同盟会领导人主张改变革命策略。如胡汉民认为,“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否则,必将使革命元气大伤,“使吾敌之魔力反涨,国民愈生迷梦”。但汪精卫则坚持认为,从事暗杀活动“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只有那些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发动的武装起义,才“是伤吾党元气”*《汪精卫与胡汉民书》,《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双照楼1939年校印本,第1页。的错误行为。
政治暗杀和武装起义,是当时革命党人反清革命的两种主要斗争方式。多次政治暗杀活动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多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共性原因,如果说政治暗杀活动导致了大量革命骨干的牺牲,使得革命元气大伤,那么武装起义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人们厚此薄彼,看来是存在着先入为主的认识偏见。
五、革命党人对暗杀活动的反思与清廷官吏对暗杀活动贬抑之分析
辛亥革命时期,既有许多革命党人积极宣传并从事对清廷大员的暗杀活动,同时,也有不少的革命志士反思暗杀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究竟如何。例如,1908年汤增壁提出,革命党人从事的暗杀活动,“屠恶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反动政权,因此不能成为“吾党之专策”*揆郑(汤增壁):《崇侠篇》,《民报》,第23期。。曾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林天羽,曾赋诗殷切希望革命党人改变暗杀这一手段,“吾侪既救国,舍生殉主义……生固我所欲,死亦安得避”,尽管革命志士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生死了不关”,但是,必须考虑所作所为,要“期于事有济”。革命党人“狙击复暗杀,前仆后者继。究其所结果,不与自杀异。此辈宁尽诛,徒令丧壮士。我今语同志,播然大变计。古今英伟人,其妙在任智”[19]208。1911年,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社论说:“革命党者,必当以大起国民军,组织军队为唯一之方针。”“吾党之所求者,在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事业伟大,断非区区暗杀一二元凶大恶所能有济者。”*《光华日报》,1911年3月8日。
革命党人内部有关实行暗杀利弊的反思,是必要的,他们是在探寻推翻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在这一探讨摸索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意见分歧也是正常的。有的学者认为部分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不仅丝毫动摇不了统治阶级的基础,而且往往牺牲许多革命骨干,暴露革命组织,以致使革命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的论断,或亦可为一说。但是,若根据1911年4月温生才枪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审讯时所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20]294来论证,“即使统治者也很明白,暗杀了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物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统治秩序”[21],则不能令人信服满意。
革命党人汪东有关武装起义与政治暗杀的作用及局限问题的分析论述,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汪东在其《刺客校军人论》中说,对清廷官吏实行“怀匿炸药而投”的暗杀方法,存在着诸多的局限。其一,所投掷之炸药或炸弹,“砰轰散击”,杀伤力有限,不但“中敌与否不可知”,而且常常使“己身则先裂为灰尘”。其二,采用政治暗杀之法,“杀其一人,代之者如其人,尽杀满朝,明日又周布矣”,杀不胜杀。清统治者“彼之蠹无穷”,而从事暗杀活动的“吾之俊民有限”。因此,他认为,“今计革命之业,断不能以破碎灭裂”,仅仅依靠暗杀一法,希冀“侥幸其或成矣”,而必须“鸠集群力”,武装起义与政治暗杀并行共举,才能“各致其用”,取得较好的结果。他把当时的反清革命运动“喻同伐桑”,认为实行暗杀仅是“拔其叶而敌落其实……不拔其根,开岁复萌叶结实如故”,而进行武装起义,则是“并其根而尽拔之”的彻底办法。
表面看来,汪东“杀其一人,代之者如其人,尽杀满朝,明日又周布矣”之说,与两广总督张鸣岐“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之说,似乎意思相同。其实,两者不仅立场不同,即是其根本命意亦迥不相同。
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汪东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有人持“专恃刺客”,仅仅依靠暗杀之法,即“可以集事”成功的想法,这当然是错误的,必须“有以矫之”,必须加以澄清和改正。但他同时又特别强调,无论是身为刺客的政治暗杀,还是身为军人的武装斗争,无不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作用,皆为“乾坤不毁,三光不灭”的正确方法之一,革命事业“实维其赖”。因此,就其实现反清革命事业的手段与途径而言,“刺客之与军人,相须为命,何有缓急之分”*汪东:《刺客校军人论》,《民报》,第16期。,政治暗杀与武装斗争都是必要的、正确的。
六、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可钦可佩
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人们可以见仁而乐山,亦可见智而乐水,可有自己的分析与认识,亦可与他人讨论或商榷。但对于革命党人在践行革命理想过程中的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则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称赞。
首先,革命党人倡导实行暗杀,其理想与最终目的至公而高尚。
革命党人是由成分较为复杂的各个阶层组成的,他们对清廷大吏进行暗杀的原因各有不同。或许如有人所说,存在着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不愿对人民大众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等。有的人如汪精卫,后来甚至堕落为可耻的汉奸。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对清廷大吏实行暗杀的最终目的是至公而高尚的。
对此,汤增壁曾有深刻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中国古代的确有许多令人钦佩的侠义之士,如刺杀王僚的专诸、刺杀庆忌的要离、刺杀韩傀的聂政、刺杀秦王的荆轲等等。这些人皆具有“亢厉无畏,恒人难能”的勇气,其“不畏强御,不好缘饰,不为阿谀,率真而行”的斗争牺牲精神,实为“凡民铮铮者”。但是,这些人却皆是为某些人的私利而为,或是因“忠于其主,以知遇之隆,而效彼身命”;或是因“食人之禄”,而“不顾其患”。还有些人则更是等而下之,为他人以金钱收买,于是“乌兽锵锵,感激涕零,思得当以报,则惟有陨首捐躯,私恩授受,不自尊贵”。
而革命党人效仿古之侠士,不惜“弹药猛烈,析骨为烬”,暗杀清廷大员于“轮蹄之下,宫寝之内”,“此非个人之觖望,亦非承命驱策,感怀德义”,而是为了“使四万万众恍然惊觉”;是为了“公理之日倡”;是为了使“民知有革命”,使“民知革命之切”;是为了“种族之思,祖国之念”;是“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揆郑(汤增壁):《崇侠篇》,《民报》,第23期。。
由此可见,革命者的政治暗杀与古代侠客之刺杀,虽同为舍生取义之举,但其“义”之内涵,却有公义与私利的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李建军[1]认为,农业研究与开发体系大致包括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私人公司和其他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以及各个国际化农业中心等,而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以农业科研院所为主体,以农业大学为主干的农业研究与开发体系和独特的农业自助体系,这些体系的职责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农业技术推广在内的多个环节。本研究的农业科研人员指的是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学内从事农业技术创新的人员,其工作职责包括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农业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
其次,革命党人践行革命的精神可嘉可尚。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明确提出实行革命的方法是:“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在反清革命的过程中,进行革命的思想宣传工作,当然是极其重要而必要的,但还必须付诸“起义”和“暗杀”等实际行动。我们应该看到并承认,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些人仅仅是一个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却并非真正的实践者。
革命志士在宣传对清廷大员进行暗杀的时候,颇为推崇古代的侠义之士,更是特别提倡“任侠”的精神。他们说,凡是能够做到“白刃可蹈,而坚持正义”者,可谓之“侠”,而“投之艰巨,不懈其仔肩”者,是谓之“任”。
当时反清革命的中心或策源地,并不在国内,而是在日本的东京。一些激进的留日学生在此激烈地鼓吹革命,但他们却大多停留在舆论或思想的宣传方面,很少有人回国直接投身革命。例如,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钮永键即曾指出,多年来,“中国志士,激昂慷慨,徒有空言”。留日学生往往也是喜欢头头是道地写文章、慷慨激昂地发议论,但却“事事不自图担当,徒责望于人”,往往是希望“人任其艰,我议其后”*《留学记录》,《湖北学生界》第4期,第122页。。黄中黄(章士钊)有感于诸多的留学生在海外倡言革命,而只有沈荩等少数人回到国内实行革命的现实,发出了留学生“虽然高标其主义,而不思所以实行之,又何取乎无谓之空谈乎”的质疑,衷心称赞只有沈荩才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实践家”。对此,他不禁大发“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22]295-296的感慨。1905年9月,吴樾之所以甘冒生命的危险,谋炸出洋考察政治清吏大吏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因为他“痛四方口舌排满之辈”,有言论而无行动,深以“不得一人之实行为耻”[23]689。
正是在此情形之下,许多激进的同盟会会员,或以革命活动“运动员”的身份回国,投身于武装起义的策划之中;或以暗杀活动“执行员”的身份回国,从事于暗杀的实践。无论是策划武装起义,还是实行暗杀活动,都是不惜以血肉之躯,沐于腥风血雨之中的可贵实践者,皆应得到人们的嘉尚与称赞。
革命党人汪东从意志品行、实行难易等方面,分析了刺客与军人、政治暗杀与武装斗争的异与同。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评价革命党人从事政治暗杀的高尚精神,颇具启示意义。
汪东虽然也充分肯定作为一名军人所应具备的不畏艰苦、不惧牺牲的精神,但他却更为称赞刺客。在他看来,军人的冲锋陷阵,很多时候是“身迫严令,非其心之所欲,徒出于不得已焉”,而刺客则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轻于生死,但使荷戟戎行,绝无拦道牵衣,哀离惜别之态”;军人于战斗之前,皆是“欲陷敌于必死之地,而予己以可生之路”,“军人之所求者生,而刺客之所求者死也”;军人可有身经百战而肤发完好者,战胜归来,不仅会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啧啧赞叹”,还可以受到“政府策勋,使者慰劳,铜柱标其功名,簿金肖其丰采,爵列通侯,禄封万户”,万一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而还,“则勿问朝野,举相钦礼”,而“刺客之道,非直危道而已,怀敢死之心,行必死之事。其事不成,菹醢其骨而无所悔,幸而遂成,则亦与敌骈戮”,“以不榖之身,出必死之道,无军人荣誉可法”*汪东:《刺客校军人论》,《民报》,第16期。。因此,相较之下,刺客较军人更加难能可贵,就此而论,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更应得到人们的尊重与景仰。
再次,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可钦可佩。
暗杀活动是最激进,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斗争方式之一。
古代侠客行刺,皆持短兵器、冷兵器,为铁椎博浪,图穷匕首见之举。革命党人认为,张良击杀秦始皇之铁椎误中副车,荆柯刺杀秦始皇之匕首误中廷柱,暗杀失败,皆因其所用器物不够精良所致。“倘使那时候有炸药,有手枪,任你有十个秦始皇,都要死得干净了”。相比之下,“炸药比手枪更好”*白话道人(林懈):《国民意见书·论刺客的教育》,《女子世界》,第3期。。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志士为确保谋刺清廷大员的杀伤效果及成功率,除采用手枪外,更多的是采用炸药或炸弹等爆烈的热兵器。
当时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因无法得到炸药或炸弹的制成品,只能依靠学到的有限化学知识及简陋的工具自行研制,因而经常发生意外爆炸。往往轻者炸伤双手或眼睛,如杨毓麟即因此而炸伤眼睛,致“一眼失明”[9]319;刘思复亦曾多次因试验炸药而“击伤脸部”,“炸伤面部及左手下部,五指具废”[24]146-147。重者则可能致死身亡。
那些宣传,特别直接从事“怀藏利器、流血五步”*揆郑(汤增壁):《崇侠篇》,《民报》,第23期。之内暗杀活动的人,无不深知此行无论成功与否,大多将有去无回,或是玉石俱焚,与敌人同归于尽,或是被俘后惨遭杀害,甚至是“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矣”*《彭家珍致赵铁桥、黄以镛书》,转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册,第1484页。。
因此践行于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或许存在着一定的悲观情绪,但绝非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悲观主义者,而是革命的英雄主义者,充满了彻底革命的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陈天华、杨毓麟、姚洪业等人蹈海、蹈江而死的自杀行为,或可谓是其悲观绝望情绪的表现。于此,汤增壁虽隐晦其辞,但意思甚明,“长沙有两士,葬清芬于鱼腹,沉幽怨于沧流,志行荼苦,而不可以为训”。揆郑(汤增壁):《崇侠篇》,《民报》,第23期。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88页。然而,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仇鳌,仍是认为陈天华之蹈海,姚洪业之蹈江,乃是“不惜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进行革命”,吴玉章也认为,陈天华之所以蹈海,是“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坚持斗争”。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第35页。故此,人们对辛亥时期的仁人志士,理应给予充分的理解,更应对他们表示尊重与敬仰。。这些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既不是出没于绿林的草莽英雄,也不是浪迹江湖的飞侠剑客;既不是图财舍命的村夫莽汉,又不是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而是一些平日穿长衫、戴眼镜,稍稍带有些洋气,几无缚鸡之力的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日本人池亨吉曾形容并称赞史坚如“容貌妇人风骨仙,博浪一击胆如天”;称赞汪精卫虽年仅23岁,“为蒲柳弱质之美少年”,却是“能当大事故”,闻鸡起舞的革命“实行之人”,真乃“奇世之豪杰也”*《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4月版,第208、210页。。
这就更使人对其油然而生钦服、感佩、景仰之情。试问,那些认定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是悲观主义者的人,是否具有这些志士大无畏牺牲精神之半?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从事暗杀活动前,大都表示出慷慨赴义的必死决心,不但具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还”的义侠悲壮,更是颇具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
例如,1905年9月,革命党人决定赴北京谋炸即将出国考察政治的清廷五大臣时,杨毓麟以自己身为北方暗杀团领导,毅然决定亲自执行这一危险任务。但吴樾亦是当仁而不让,坚决表示“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25]432。结果,炸弹未曾投掷之前发生意外爆炸,“轰然一声,铁片四散”,在炸伤清廷大臣的同时,吴樾本人“下半身先震碎,肠腹崩裂,手足皆断,即重伤死”[26]197。另据吴铁城回忆,为了预防万一,“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然后“伺机行事”,称赞其“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湾三民书局1972年版,第14页。。1907年7月,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后被俘,结果被处以“割头剖心”[27]40的酷刑。1911年4月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前,下定必死决心,在其给同盟会同志的信中表示,自己的“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温生才致孝章、源水、螺生函》,转引自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327页。。正因如此,尽管黄兴对温生才擅自刺杀孚琦而影响了广州起义有所不满,但他仍然称赞温生才这一大无畏牺牲精神,“其志行真属高卓”[10]76。
1909年11月,汪精卫在入京谋炸摄政王载沣时曾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成与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但“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汪精卫与胡汉民书》,《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第5页。,憧憬着革命的最后胜利。汪精卫被捕后,面对死亡,慨然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燐光不灭,夜夜照燕台。”后来,在当时国内多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作用下,汪精卫虽未遭受杀害,而是被判终身监禁,但这实属个别例外,更属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党人的意料之外。
七、余论
笔者认为,时人“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寄生(汪东):《纪清贝勒溥伦来东后事》,《民报》,第18号。的有关政治暗杀的评判标准,至今仍然适用。首先,革命党人政治暗杀的对象,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及其权贵大员,皆属革命的对象。其次,革命党人政治暗杀的志向与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是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既然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完全符合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尽管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局限,但仍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和称赞。
当然,作为一百年以后的现代史学工作者,对于革命党人从事的暗杀活动,可以有自己更为正确的认识,但这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或是“马后炮”式的聪明。还是吴玉章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得更为客观,当时,“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吏,哪里知道暗杀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不能动摇它的社会基础呢”,对于这些现代似乎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则“是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才能理解的”[4]98。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学者,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批评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活动,非但有苛求先烈志士之嫌,且有违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