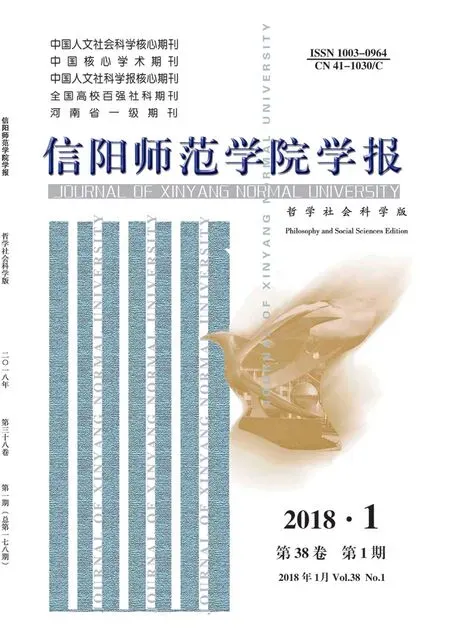当代美国一般管辖权发展的收缩表现及其反思
——以戴姆勒案为例
姜帅合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当代美国一般管辖权发展的收缩表现及其反思
——以戴姆勒案为例
姜帅合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与美国司法程序一样,美国对人管辖权应当是公平、统一以及具有可预测性,并要求平等对待原被告双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戴姆勒案引起了美国学界的广泛讨论。该案缩小了法院长臂管辖权的范围,不仅没有厘清法院先前在固特异案中确立的“实质在家”标准的含义,而且在意图缩小一般管辖权的范围时也忽视了美国民事管辖传统原则“公平与实质正义”。从戴姆勒案判例分析来看,目前美国法院一般管辖权收缩倾向的出现则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和政策考量而非法理因素。
一般管辖权;实质在家;戴姆勒案
对人管辖权是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美国联邦法院及州法院主张对人管辖权的标准问题是学者们讨论和关心的重点。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国际鞋业案中确立的“最低联系”标准含糊不清,以致下级法院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这使得美国管辖权可预测性这一基本原则无法得到实现,也引起了众多美国学者们的批评。
与美国司法程序一样,美国对人管辖权应当是公平、统一以及具有可预测性,并要求平等地对待原被告双方。不仅如此,对人管辖权也应当给非本州居民的被告就如何避免进入外州的影响范围加以指导。这就表明,一个意欲在外州或外国进行大规模销售的公司应当有能力知道或者最起码有明确的规定指导它的行动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导致它受到外州或外国法律的规范。此外,对人管辖权也同样应当保证原告在不必负担过度责任或延期的情况下享受到一个方便法院的管辖。在刨除美国对人管辖权的这些基本政治考量因素后,我们发现即使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戴姆勒诉鲍曼案(Daimler AG v. Bauman,以下简称“戴姆勒案”)中意图阐释一般管辖权的适用范围,但仍然存在着概念含糊不清和标准不一的问题。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一得之见。
一、美国一般管辖权发展的历史溯源
美国法院的属人管辖权要求诉讼当事人必须与受诉法院具有充分的最低限度联系,它主要分为一般管辖权和特别管辖权两种。一般管辖权指的是法院对与本地有密切或持久联系(住所和国籍等)的被告所行使的管辖权。“根据一般管辖权,法院可以审理针对该被告的任何诉讼请求,包括与法院地完全无关的行为所引起的诉讼请求”[1]。因此,一般管辖权也可以被称为“全能管辖权”。而特别管辖权则是指法院根据被告与法院地之间的特殊联系而行使的管辖权,那么法院便仅能在与该特殊联系有关的诉讼请求中行使管辖权[2]。
美国对人管辖权的判断标准源自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判断标准可分为“传统”标准和“最低联系”标准。在彭诺耶一案(Pennoyer v. Neff)中,法院将传统的对人管辖权判断标准描述为:国籍、自愿出庭、同意受其司法管辖以及出现。随后,在1945年的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International Shoe Co.v.Washington)中[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放弃了此前的属地主义原则,提出了“最低联系”标准,即使被告并未实际出现在法院地,但他仍有可能与法院地有最低联系,在不违背公平和实质正义的传统观念的情况下法院可对其实施管辖权。在该上诉案中,上诉人主张其活动不构成在华盛顿州的存在,因此华盛顿州法院无属人管辖权。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须与一州有某种最低限度联系,使该州法院能够行使管辖权而且不违背传统的公平与实质正义观念”[1]82。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后续的一系列的判例法中继续强调并发展了“最低限度联系标准”,持续地奉行长臂管辖权原则。无疑,这种长臂管辖权原则为随后特别管辖权与一般管辖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后,特别管辖权愈发受到关注,而相较于对特别管辖权讨论的热衷程度,美国法院仅仅在铂金斯案(Perkins v. Benguet Consolidated Mining Co)和哥伦比亚直升机案(Helicopteros Nacionales de Colombia v. Hall)中对一般管辖权提出了两种观点。在铂金斯案中,美国法院认为其对在俄亥俄州设立办公室而在二战中被日本人占有公司总部的公司董事长享有一般管辖权。而在直升机案中,美国联邦法院则排除了德克萨斯州法院基于直升机供应商在德州银行有存款且偶尔往德州运送公司人员参加培训而对直升机供应商行使一般管辖权。
然而,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默和判决戴姆勒案后,仅仅间隔一个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固特异案中(Goodyear Dunlop Tires Operations v. Brown)提出了第三个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实质在家”标准的观点。固特异案涉及一般管辖权问题。该案争议的问题是:法院是否拥有针对固特异外国子公司的管辖权?北卡罗来纳州法院认为自己拥有一般管辖权,因为固特异外国子公司所生产的轮胎在北卡罗来纳州大量出售,所以符合“商业流通”原则。而联邦最高法院则以全体一致的形式驳回了州法院的裁决。金斯伯格大法官在撰写的判决书中首先对一般管辖权进行了定义,即只有当外国公司与某一州之间具有“持续而系统的一般商业联系”,以至该州已经成为该公司“实质上的家”时,该州才可以对该外国公司拥有一般管辖权,从而可以受理针对该公司的一切诉讼。金斯伯格认为在固特异案中作为被告的外国子公司与北卡罗来纳州之间不存在持续而系统的一般商业联系,北卡罗来纳州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被告的家,那么,北卡罗来纳州法院便不能行使一般管辖权[4]。
尽管法院在审查一般管辖权时提出了这个新的标准,但是它并没有充实这个标准。固特异案并没有就“决定商业联系的程度是否足够使得一个外国公司受到法院的一般管辖”[5]给下级法院以指导。该案认为一个主要营业地或者注册地在外州的公司可能会在法院地达到“实质在家”标准,但并没有为下级法院提供任何例子。相关评论者更认为,这样一个限定性的用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法院对外国公司行使属人管辖权[6]。
二、美国一般管辖权发展的收缩表现
从“最低联系”标准到“实质在家”标准,美国法院更像是在进一步细化前者的适用范围,越发注重被告对于法院地是否具有利用法院地利益的“故意”存在,一旦被告被视为有针对法院地利益的行为存在,法院方可对其实施对人管辖权。美国法院的这种较之以往更为收缩的态度在戴姆勒案判决意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戴姆勒案件基本情况
2004年,22名原告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位于阿根廷的梅赛德斯奔驰分公司在阿根廷肮脏战争期间与阿根廷政府勾结,绑架、拘留、折磨和杀害原告及他们的亲属,要求被告依照美国《外国人侵权法》(the Alien Tort Statute)及《酷刑受害者保护法》(the Torture Victim Protection Act)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事情发生于阿根廷的冈萨雷卡斯卡坦岛,而当时原告们也在那里工作。原告从未声称梅赛德斯奔驰阿根廷分公司与阿根廷政府的勾结行为发生在加州或者美国的任何地方。
被告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是一家德国上市公司,其在德国生产制造奔驰汽车并且总部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该公司诞生于1998年的一次合并,当时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被合并成为德国戴姆勒公司的子公司。在诉讼之初,戴姆勒公司声称“在加州没有办公室或持续经营”[7],而与加州的联系之一是在旧金山的法律顾问,而该法律顾问也仅受雇负责代表处理戴姆勒公司在该州涉及清洁空气法的诉讼。此外戴姆勒公司也有针对加州市场的制造产品行为,其与加州的全球自然基金会有着合作伙伴关系。原告认为戴姆勒公司应对其全权控制的阿根廷子公司的行为负责,然而戴姆勒公司以缺乏对人管辖权为由提出抗议。原告拿出了一系列意图证明戴姆勒公司与加州有联系的证据,同时作为代替方案,原告要求将美国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与戴姆勒公司的联系也放入法庭的考量因素之中。
一审法院支持了戴姆勒公司的抗辩理由,认为戴姆勒公司与加州的联系并不足以构成美国法院对人管辖权的标准[7]。此外,因为原告无法证明美国戴姆勒公司与被告是“代理”行为,法院拒绝基于“代理”理论将美国戴姆勒公司与加州的联系归于被告德国戴姆勒公司的联系之中。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过程中,原告没有反驳一审法院所认为的戴姆勒公司与加州的联系不充分的判决,而是提出美国戴姆勒公司与加州的联系能够归于被告与加州的联系,从而使得加州法院拥有一般管辖权。
起初,第九巡回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7],但在关于判断美国戴姆勒公司与被告之间是否构成“代理”关系的问题上,法院认为原告的证明不够充分。但莱因哈特法官提出了反对意见,不仅认为美国戴姆勒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关系满足了“代理”的要求,而且认为考量“合理性”标准并不排除对人管辖权的行使。最终,第九巡回法院收回了最初意见,判决“最起码在决定一般管辖权的最基本的目标时,美国戴姆勒公司是德国戴姆勒公司的代理商”[8],因此,美国法院对戴姆勒公司有对人管辖权。第九巡回法院在其结论中指出,像德国戴姆勒这样的公司法人设立类似美国戴姆勒子公司仅仅是为了获取美国市场利益但不需要承担任何管辖权的后果。莱因哈特法官指出,这就像是虽然该公司在加州制造出售了大量奔驰汽车,但它仍不能被地方法院强制要求出庭。而这显然并不合理。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4年1月14日提审了该案,并做出了终审裁决,推翻了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认为戴姆勒公司因为其在阿根廷境内实施的行为而不受美国加州法院的管辖[1]。
(二)法院的推论
在戴姆勒案中,法院试图通过回溯一般管辖权的发展历史来回答遗留在固特异案中的问题,并进一步定义一般管辖权的边界问题[9]。法院在国际鞋业案(International Shoe v. Washington)中确立了对人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在此之后,特殊管辖权在现代法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在国际鞋业案后,其仅仅在少数案例如铂金斯案、直升机案和固特异案上讨论了一般管辖权的问题,同样,一般管辖权问题的研究也并不受法院的重视。
随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讨论了第九巡回法院将美国戴姆勒公司与法院地的联系归于被告德国戴姆勒公司的论证部分。法院拒绝了第九巡回法院的分析,因为这将会导致“一般管辖权的蔓延式扩张”,而这是在此前固特异案中法院就已经申明了的[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强调在固特异案中,仅有一小部分情形才能使得被告人受法院的一般管辖,比如公司主要营业地或者公司注册地在本州。然而,法院强调固特异案的判决并不意味着仅仅只有公司主要营业地或者注册地在法院地时才能受到法院的一般管辖。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其实扩大了一般管辖权的基础,但是并没有为下级法院提供任何的指导。相反,它仅仅重申了固特异案所确立的标准,即法院所在地能够视同一个自然人的居所,这就可被视为“实质性在家”[9]。
其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简单地论证了戴姆勒公司与加州的联系,断定不论是戴姆勒公司还是美国戴姆勒公司都没有在加州合并或者维持主要营业地,因此对其实施一般管辖是不妥的。正如索托美亚法官所说:“问题并不在于戴姆勒公司与加州的联系太少,而是它与其他州的联系太多”[9]。法院在戴姆勒公司全球经营活动行为的背景下审视了戴姆勒公司与加州之间的联系,由此完善了此前的“实质在家”标准,且更加考量实践操作的可能性,即需要衡量公司州内与州外联系对比是否符合这一标准。
显而易见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严密考察戴姆勒或美国戴姆勒公司与加州联系后并没有得出该结论。相反,它忽略了在回答司法管辖权问题时需要充分的事实论证而非更多地考虑政策问题这一要义。根据法院判决,如果戴姆勒公司的经营活动足以构成一般管辖权的基础,那么“在美国戴姆勒公司销售额相当大的其他任何一个州,都可能受制于法院”[9]。如此,无限扩张的一般管辖权将会使美国国际经济贸易投资活动受到巨大阻碍。法院比较了第九巡回法院的意见与欧盟国家的标准,欧盟对于管辖权的法律规定是只有公司主要活动地在法院地,法院方可行使管辖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得出结论,美国法院对戴姆勒公司行使管辖权是违背传统“公平与实质正义”观念的。
三、总结与反思
由上述可知,针对对人一般管辖权,美国法院较之以往采用了更为严格的判断标准。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似乎都陷入了“制造恶法”的境地。如果支持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这将会大大地扩张一般管辖权的范围。原告依赖于美国戴姆勒公司与加州之间的联系,尽管被告德国戴姆勒公司与所诉暴行有关,但它与加州却没有联系。如果母公司是基于子公司的关系而被一般管辖权所约束,那么一般管辖权的范围显然将无限扩大。反过来说,如果推翻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戴姆勒一案将进一步限制了在固特异案中所确立的一般管辖权的标准。虽然,在戴姆勒案中法院并没有明确限制一般管辖权范围为公司注册地或主要营业地,但在这两种范式基础之外建立一般管辖权,这对于原告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法院希望缩小以往对形成实质性、持续性且系统性商业活动的公司行使一般管辖权的范围,或者说抑制这种倾向。尽管法院看起来并没有排除虽然注册地或主要营业地在外州,但构成本州的“实质在家”标准的少数情形,而戴姆勒案的判决似乎表达了这是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的一个例外。
此外,相较于此前教科书般的铂金斯案,戴姆勒案所确立的标准则似乎与之有所出入。在铂金斯案中,法院认为能够行使管辖权,即使被告在俄亥俄州没有主要营业地或注册地。与俄亥俄州能够构成联系的因素是公司董事长在其俄亥俄州家里保存了文件,拥有活跃的银行账户,派发薪水和组织主管们的会议。而在该诉讼提请之时,该公司实际上在菲律宾恢复运营。法院没有关注该公司与菲律宾的联系,仅仅聚焦于它与俄亥俄州的联系。由此可见,调和铂金斯案与戴姆勒案的判断标准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法院并没有明确推翻铂金斯案的判决,但它在戴姆勒案中的论证推理实际上是破坏了铂金斯案的法理基础,而这却是先前审理有关一般管辖权案件的判断标准。
法院的试验产生了不公平的结论且破坏了传统观念上的“公平与实质正义”,这会使戴姆勒案产生深远影响。第一,该判决将会带来司法权披露范围的扩大。尽管法院声称这份判决不会改变披露范围,但实际上在下级法院层面上却是做不到的。如今,下级法院除了鉴别州内联系外还需要鉴别州外联系的范围。这无疑是增加了下级法院的司法负担,显然与美国简便司法规则保证更好的预见性相冲突。第二,这种新的规则使得个人和小企业更有可能承担管辖责任。比如,一个自然人被告,他与法院地的联系仅仅是一次旅游,如果在此期间被送达传票,那么他就会受到法院地法院的管辖。然而,一个在法院地有自己的财产、人员和实质性商业活动的公司却有可能免于管辖,因为它有可能与其他地方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同样,一个小型企业即使经营活动或者注册地在外州也有可能被加州法院管辖。不同于戴姆勒这样的大公司,根据小企业的整个经营,它在加州的销售量很有可能视为足够多而受到管辖。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并不公平,尤其是在衡量对人管辖权与正当程序要求的关系之间。第三,戴姆勒案使得原告在起诉一个跨国公司时难以选择法院地,它将应由被告所承担的败诉风险转移给了原告。正如索托美亚法官所说:“孩子由于一个跨国企业名下的外国医院的疏忽而受到伤害,家长却不能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起诉,即使这家医院在美国多个州内都有联系。”[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份判决的主要意见会使得原告无法在美国任何地方法院获得救济。
更为重要的是,戴姆勒案将会适用于有关美国公司的判决。尽管该案涉及的是外国原告和外国被告,但是法院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适用于外国公司。因此,戴姆勒案所设立的标准将会造成一个注册地或者主要营业地在美国其他州的美国公司免于受到一般管辖权的约束。
综上分析,戴姆勒案不仅没有厘清法院先前在固特异案中确立的“实质在家”标准的含义,而且在意图缩小一般管辖权的范围时忽视了美国民事管辖传统原则“公平与实质正义”,并更多地考量了政策因素。收缩一般管辖权的倾向对于一直诟病美国长臂管辖的学者们来说,他们认为它是一种进步,但这种收缩的背后更多的是法院对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至少从目前的判决来看,法理因素是不够充分的。虽然,从原先的“最低联系”标准再到现在的“实质在家”标准,法院依然无法能够就判断一般管辖权给出清晰的衡量标准,但庆幸的是,新标准的提出和践行推动了美国一般管辖权研究的发展进程,为法律工作者们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1] 杜 涛.美国联邦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收缩及其启示[J].国际法研究,2014(2):82-95.
[2] MEHREN V, ARTHUR T, TRAUTMAN, et al.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a suggested analysis[J]. Harvard Law Review, 1966, 79(6):1121-1179.
[3] International Shoe Co. v.Washington[EB/OL].(2017-06-27)[2017-08-10].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tional_Shoe_Co._v._Washington.
[4] Goodyear Dunlop Tires Operations, S.A. v. Brown[EB/OL].(2017-06-27)[2017-08-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odyear_Dunlop_Tires_Operations,_S.A._v._Brown.
[5] TARIN D, MACCHIAROLI C. Refining the Due-Process Contour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over Foreign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Law,2012,11:52.
[6] BORCHERS P J J. Mcintyre Machinery, Goodyear, and the Incoherence of the Minimum Contacts Test[J]. Creighton Law Review, 2011,44:1245.
[7] Daimler ag v. bauman et al.(11-965) [EB/OL].( 2014-01-02)[2017-08-13].http://www.doc88.com/p-3817636567131.html.
[8] Daimler Chrysler Corp. v.Cuno. [EB/OL].( 2011-06-27)[2017-08-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imlerChrysler_Corp._v._Cuno.
[9] Daimler ag v. Bauman [EB/OL].( 2014-11-02)[2017-08-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imler_AG_v._Bauman.
TheContractionofGeneralJurisdictioninContemporaryAmericaandItsReflection——Taking Daimler AG v. Bauman as An Example
JIANG Shuaihe
(College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fair, unified and predictable, and require equal treatment of the original defendant, a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Daimler,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American academic circles. The scope of the case reduced the court long arm jurisdiction, the court did not clarify previously the meaning of the standard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at home"established in the Goodyear case; meanwhile it ignored the American civil jurisdi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justice" in the scope of intent to narrow the general jurisdiction. The contraction tendency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n American courts lays more emphasis on economic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rather than the legal principal.
general jurisdiction; essence at home; Daimler case
吉家友)
10.3969/j.issn.1003-0964.2018.01.010
2017-11-08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CFX031)
姜帅合(1992—),女,河南信阳人,硕士,主要从事国际私法研究。
D997.3
A
1003-0964(2018)01-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