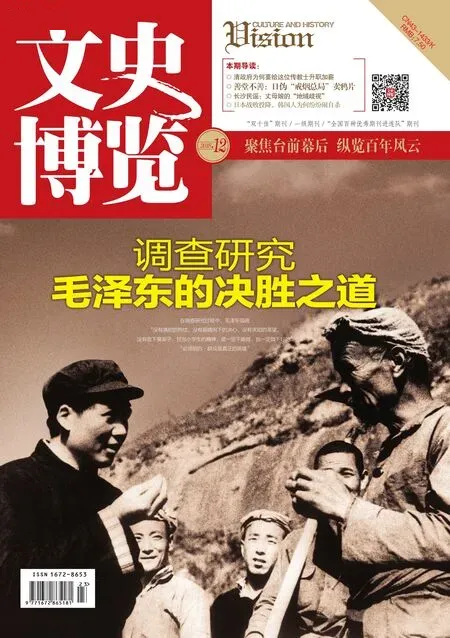华北大汉奸押解南京受审前的丑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人民的压力,在华北抓了一批汉奸。但法院公开审理的都是些三流小汉奸,大汉奸一个未见解送法院。对此,社会上传说纷纭,说大汉奸迟迟不送法院,是因为办理人员受贿,企图藉此释放。北平当局为应付舆论,一方面枪毙了两个“受贿”者,另一方面匆忙宣布押解王荫泰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
1946年5月26日晨5时,当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的王荫泰等汉奸像往常一样检查血压时,才知道即将被解往南京受审,他们立刻慌作一团,有的匆忙给家人写“遗书”,有的急急打点自己的行李。汪时璟、余晋和平时都被软禁在汪的家中,也临时被提到了监狱,集合出发。王荫泰被编为第一号,与江亢虎铐在一起。群奸被押出监狱时服饰各异,表情狼狈,构成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兹录群像于后——
王荫泰(1886—1947),山西临汾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娶了一个德国太太。曾当过律师,做过法官。“七七事变”后,他做了8年伪官,做过伪临时政府实业部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伪实业总署督办等。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新民会长。他为敌招募劳工,供敌情报,搜刮民食,发行伪币,包庇赌场,甘做敌人统治中国的鹰犬,罪大恶极,被列为平字汉奸第一号。从监狱起解时,王荫泰一直低着头。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他最初不肯回答,后来很狡猾地说:“我的事华北都知道,无何感想。”“相信政府的裁处也会公平的。”在监狱门口临近开车的时候,他对记者苦笑说:“别矣北平,恐怕我不能回来了。”囚车过灯市口,他的德国太太和三个女儿夹在唾骂汉奸的人群中望着他落泪。

齐燮元
齐燮元(1879—1946),河北宁河人。在这批大汉奸中,他算是资格最老的军阀了。“七七事变”前,这位“息影津门”的将军就与日本特务机关眉来眼去。事变后,他与王克敏等组织伪临时政府,任常委兼治安部总长,其后历任伪军事首长,先后成立11个集团军分驻华北各地,扰乱华北,破坏抗战。当记者问他起解的感想时,他手拍着胸傲气凌人地说:“我没有对不起老百姓的地方,这次我一定听国家法律制裁。”“从未做坏事,蒋主席也说我资格老。”随后又像安慰又像自嘲地对和他铐在一起的伪北京市长刘玉书说:“市长也没有对不起人民的事。”押解兵对他很客气,他用训话的口气告诉押解兵他跟吴佩孚的“光荣历史”,厚脸皮上不时浮出些强笑。
殷汝耕(1883—1947),浙江平阳人。早在1935年11月,他便乘日本企图侵略华北之机,公然窃取冀东22县,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他曾接受日本指挥,出卖柳江煤矿,设立冀东银行,包庇日韩浪人输运白银出口。后又应汪精卫的邀请,充任汪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是个老牌汉奸。当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只笑笑:“没什么话讲,没什么话讲。”他强作镇静,但不时脱帽,用手帕擦汗。他显得苍老,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气劲。
汪时璟(1887—1952),安徽旌德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财务总署督办,是这群汉奸队伍里穿着最漂亮、最阔绰的人物,与衣着陈旧的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围观的人说:“做汉奸也还是长财政的(意为干财政最吃香)。”在飞机场检查时,发现他手提包里的东西最齐全,除各种补药、用品外,还有一密裹的小包,里面放着一卷自白书。他的身份很神秘,当局对他一直很客气,并没有把他关进监狱,而是把他软禁在自己家中,直到起解前25分钟,才用小汽车把他押解到狱。记者问他话的时候,他装聋作哑,老让余晋和作翻译,余用手放嘴上对准汪的耳朵说:“这位先生问你还有什么话说?”他笑了:“没有什么,谢谢你,只是惭愧,应当,应当。”
余晋和(1887—?),浙江绍兴人。曾历任伪北京市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伪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等职。他对记者说:“在北平我没有对不起民众的事。”“国家惩治汉奸、肃正纲纪是对的,但对我们几个人,似乎还要考虑。”在囚车上他四处张望,他看见事变前许多自己的部属(“七七事变”前他曾任北平警察局长)又回到北平,有的做了押解官,感到很不是滋味。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1939年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不久即在汪精卫怂恿下参加了“和平建国运动”,历任伪考试院副院长、院长,伪国府委员等职。江亢虎在离开监狱时,老态龙钟,面色苍白,好像非常害怕。他对记者的发问默不作声,但可以看出他内心异常恐惧。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这位知堂老人在北平沦陷后,忽然耐不住苦雨斋的寂寞,热心做起伪官了。他曾任伪北大校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他光着头,神态颓废。记者问他时,他说:“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说话声音很低,苦笑着。被捕前,他在苦雨斋中向记者辩解说:“我做官做校长,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在押解南京的这批华北大汉奸中,他最瘦,行李也最简单,一个不足10斤的小包,里面有两本书:《谈龙集》和《朱子》。登机后周作人以文人姿态不时吟诵,并亲书七绝一首以示押解官。诗云:“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
潘毓桂(1884—1961),河北盐山人。“七七事变”后,他负责主持北平维持会,借口维持治安,引导日军进驻市内,并焚烧民间所藏孙中山等的书籍,以后任伪天津市长,完全听从日军指挥。押解时,他面色发青,手提包裹,除糕点外都是补药。对记者的发问,他没有答复。
邹泉荪(1902—1975),山东福山人。是沦陷期伪华北商会联合会及北平商会的会长,操纵金融、物价,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抗战胜利后,他拿着数年搜刮来的钱财到处送礼,拉关系。他对记者说:“我相信我还会很自由,因为……”他张着镶满金牙的嘴大声笑着,似乎满不在乎。
刘玉书(1885—?),四川遂宁人。做过伪北京市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从陆军监狱到南苑机场的路上,他在载有14人的大卡车上乱嚷嚷。他答复记者的询问:“我没有话讲,所犯的罪行也不容自己申辩,我的一切,北平的老百姓会代我说话的。”此时,一位记者问他:“你拿混合面让北平人吃,还记得吗?”他红了脸,不吱声了。
唐仰杜(1888—1951),山东邹县人。当过伪山东省省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等职,在群奸中堪称“羊群之驴”。他还想活,不知羞愧地拿他自己的儿女做护身盾牌:“我大儿为抗战死在昆明,二儿为抗战死在重庆。至于自己呢,老朽了,死去了没有什么,早就准备着了,没开始捉我们的时候,我就自愿到行营自首了,请政府公平处断吧。”
陈曾栻,河北青县人。当过伪河北省省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农务总署督办,到飞机场后,他说:“快完了,还坐一回飞机。”汪时璟狠狠瞪了他一下,似乎说真晦气。
文元模(1890—1946),贵州贵阳人。是这批押解南京的华北汉奸中两个文化汉奸之一,另一人是周作人,他俩都做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文元模原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研究过地质,曾出版过颇有名的世界地理书籍。他说自己是个穷教书匠,这次去南京,带的款子很寒酸。押解途中的他衣衫不整,形极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