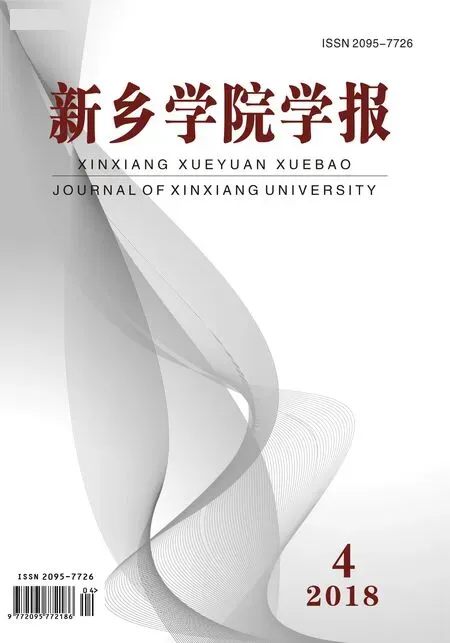明嘉靖时期祥瑞文化探析
吴华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25)
祥瑞又称符瑞,是一个与灾异相对的概念。古人将自然界中出现的一些奇特现象神秘化、谶纬化,宣称它们是君主施政有德、天下太平的象征。祥瑞文化是中国古代极其特殊的一种政治文化。它“伴随着殷周之际天道观念的形成而逐步出现”[1]。到了汉代,经过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改造[2],成为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政治工具。到了元明清时期,受到宋学的冲击,祥瑞文化日渐式微。不过即使到了这一时期,祥瑞文化仍然对封建统治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3]。
明嘉靖时期,祥瑞现象频频出现。今天的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与嘉靖皇帝对祥瑞的喜好有关。南炳文先生指出,嘉靖皇帝是“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的人”,他“喜欢祥瑞,目的是为了粉饰太平”[4]。胡凡先生认为嘉靖皇帝对祥瑞的喜好甚于其他帝王,原因是嘉靖皇帝想用祥瑞来美化自己的统治,同时也认为出现祥瑞意味着上天对他修道行为的嘉许[5]。
一、嘉靖时期祥瑞现象概述
嘉靖七年(1528年)三月,灵宝县境内黄河河水忽然变清①。消息传到北京后,嘉靖皇帝立即派遣官员前往灵宝县祭告河神,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上疏请贺。“黄河清”现象古已有之,本属自然现象②,因极少出现,故被视为祥瑞。虽然“黄河清”的景象在嘉靖朝只出现了一次,但之后与“黄河清”类似的祥瑞现象③大量出现,借呈献祥瑞来颂扬皇帝施政有德成为嘉靖朝的政治奇观。
嘉靖时期出现的祥瑞现象较多,笔者分四个阶段来分析祥瑞文化对嘉靖朝政治的影响。
祥瑞文化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自嘉靖七年灵宝县发生“黄河清”[6]1451事件始,至嘉靖十一年(1532 年)发生宋沧献白兔[6]1500-1551事件终。 《明通鉴》与《国榷》所记载的这一时期出现祥瑞现象的次数均为7次,这一时期出现的祥瑞现象包括黄河河水变清以及出现甘露、白兔、白雀、瑞麦、嘉禾、盐花等。《明通鉴》和《国榷》所记载的事件略有不同,后者未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汪鋐献甘露一事,而多了嘉靖十一年靳水产嘉禾[7]3460一事。在这一时期,廷臣自发呈献祥瑞,祥瑞的政治寓意多为 “王者德至大”[8]813“王者德盛”“敬耆老”“爵禄均”[8]827-874等。当时也有人对祥瑞提出质疑,如御史周相、兵部主事赵时春等正直臣子就多次上疏反对呈献祥瑞。此时,嘉靖皇帝对祥瑞的喜好还未达到狂热化的程度,在“廷臣请表贺”时,他有时也“以灾异止之”[6]1467。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呈献祥瑞对朝政的影响相对较小。
祥瑞文化迅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自嘉靖十二年(1533 年)发生吴山献白鹿[6]1506事件始,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发生西苑进嘉谷[7]3880事件终。 文献所记载的这一时期出现祥瑞现象的次数为21次,这一时期出现的祥瑞现象包括出现白鹿、白兔、景云、旋风、白鹤、瑞麦、嘉禾、灵黍、醴泉等④。在这一时期,祥瑞现象的出现逐渐频繁化。嘉靖皇帝移居西苑后,以西苑嘉禾为代表的祥瑞现象每年都会出现。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态度也趋于狂热,每遇祥瑞,必告太庙、世庙。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醴泉出承华殿后,“自是遇庆贺斋祀,辄停常封奏事以为常”[6]1506。廷臣也多热衷此事。“河南巡抚都御使吴山献白鹿,群臣表贺。自后,诸瑞异表贺以为常”[9]。杨爵等人曾劝嘉靖皇帝要正确对待祥瑞,待到杨爵、刘魁言等人下狱后,“中外争献符瑞,焚修、斋醮之事,无敢指及之者矣”[10]7896。 总体看来,在这一时期,呈献祥瑞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祥瑞文化鼎盛时期。这一时期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八月发生宛平县民张巨佑献芝[6]1696事件始,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发生淮王厚焘献白雁[7]3968事件终。文献所记载的这一时期出现祥瑞现象的次数为13次,这一时期出现的祥瑞现象包括出现瑞芝、白兔、白鹿、嘉谷、白龟等⑤。在这一时期,祥瑞现象的出现多与嘉靖皇帝个人意志有关。瑞芝是具有代表性的祥瑞,共出现了7次之多⑥。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人多次呈献祥瑞的情况。例如,胡宗宪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一岁二瑞”,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复献芝草和白龟”[11]5413。此时,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态度由利用转为依赖。例如,嘉靖三十九年胡宗宪所献白龟死后,嘉靖皇帝竟发出了“天降灵物,朕固疑处尘寰不久也”[12]792这样的哀叹。
祥瑞文化衰落时期。这一时期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发生严嵩、孙严鹄献玉兔[6]1744事件始,至嘉靖皇帝去世终。在这一时期,不同文献记载的祥瑞现象基本相同,包括严鹄献玉兔和灵芝、蓝道行献瑞龟、玉兔生子、天降仙桃等,文献所记载的这一时期出现祥瑞现象的次数为13次⑦。在这一时期,伪造祥瑞的情况十分普遍。例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王金、陶世恩伪造五色灵龟、灵芝[12]795。这一时期廷臣献瑞的目的十分明确,都是为了获取利益。献瑞者严鹄、蓝道行属严党,陶世恩为陶仲文子[12]795。
二、嘉靖时期臣民献瑞的目的
既然祥瑞是自然界中的反常现象,就应当十分罕见。然而,嘉靖朝出现祥瑞现象竟达54次之多。嘉靖皇帝在位时间较长,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嘉靖朝祥瑞现象出现次数如此之多。不过,就嘉靖皇帝统治后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人造祥瑞”这一情况来分析,嘉靖朝祥瑞现象大量出现还应当有其他原因。
嘉靖年间,世人对呈献祥瑞抱有极大的热情。虽然人们献瑞的时间、地点以及方式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目的却有高度的一致性。
嘉靖时期宗室和高层官僚献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嘉靖三十七年春,浙江倭乱再起,嘉靖皇帝下旨责备时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抗倭不力。胡宗宪上疏嘉靖皇帝,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胡宗宪“失内援”,“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两献白鹿于嘉靖皇帝。胡宗宪的投机行为使嘉靖皇帝“大喜”,嘉靖皇帝遂“加宗宪秩”[11]5413。这样的事情在嘉靖年间绝非个例。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交城王表得白兔于藐姑射山,“撰颂以献”。至于表献瑞的原因,《国榷》是这样记载的:“表本孽宗,贿严氏袭交城王。至是颁宗藩条例,惧革爵,故希宠自固。”⑧
嘉靖时期中下层官吏和平民献瑞主要是为了升迁。这部分人对献瑞最为积极。例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黄冈生员刘文煜进瑞兔[7]3666,嘉靖三十五年宛平县民张巨佑献灵芝[6]1696。这些人献瑞之后,嘉靖皇帝多是“贲金赐钞”。只有王金在献瑞之后受到重用。嘉靖皇帝相信服食灵芝能够益寿延年,便让人采集灵芝。“四方来献者,皆积苑中;中使窃出市人,复进之以邀赏”。王金本为罪人,他“厚结中使,得芝万本,聚为一山,号万岁芝山,又伪为五色龟”[10]7900-7901。他将这些所谓的祥瑞献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大喜,谕礼部:“龟芝五色既全,五数又备,岂非上元之赐? ”[13]732-733随后授王金太医院御医之职。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献瑞者都为了谋取私利。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五月,“帝夜坐庭中,获一桃御幄后,左右言自空中下”[10]7901。 天降仙桃令嘉靖皇帝十分高兴,他决定斋醮五日以谢天意。“明日,复获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未几,白鹿亦生二子”[6]1765。几日之内连降祥瑞,令嘉靖皇帝开心不已。那么,这些祥瑞究竟是怎样来的呢?史书中道出了实情:宦官看嘉靖皇帝“邑邑不乐”,于是“诈饰以娱之”⑨。
三、嘉靖皇帝对祥瑞态度的变化
嘉靖时期,诸臣乃至百姓纷纷呈献祥瑞,出现此种现象与嘉靖皇帝本人对祥瑞的态度有着直接关系。
在封建时代,祥瑞被视为皇权合法性的证据。我国历代皇帝对祥瑞文化都十分重视,嘉靖皇帝也不例外。然而,在南宋灭亡后,由于受到宋学的冲击,祥瑞文化证明皇权合法性的作用大大弱化了[3]。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还比较理性,每当出现祥瑞现象,他虽会告之宗庙,但对百官请求庆贺一事均予以制止。例如,嘉靖七年,灵宝县境内黄河河水忽然变清,御史鄞人周相上书劝谏:“愿罢祭告,止称贺,诏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时以闻。”嘉靖皇帝听了以后虽然感到不高兴,但还是采纳了他的意见,“诸庆典亦止不行”[6]1451。 汪鋐献甘露一事发生后,嘉靖皇帝也阻止了庆典[6]1467。 可见,此时嘉靖皇帝虽喜好祥瑞,但还没有达到狂热的程度。
后来,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时灾异现象频频出现。灾异本是“自然灾害或反常的自然现象”[14],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却将灾异与君主失德联系在一起。嘉靖九年(1530年),真定府等处大旱,嘉靖皇帝除了派遣官吏祭祀诸神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应对办法。既然天降灾异可以被解释为君主失德、民不聊生,那么天降祥瑞就可以被解释为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基于这样的认识,“河南、四川等处献瑞麦”。嘉靖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令荐之奉先等殿”[6]1482。《宋书》云:“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于周德,三苗共穗。于商德,同本异穗。于夏德,异本同秀。”[9]827-874由于嘉禾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受到了正承受着政治压力的嘉靖皇帝的重视。自嘉靖十一年八月开始,“彗星连月不灭”。出现彗星在古代被视为凶兆,而彗星“连月不灭”则更令嘉靖皇帝担忧。此时,四川巡抚宋沧“希旨献白兔,诡称祥瑞”[6]1505。 宋沧的这一举动令嘉靖皇帝十分欣慰。在明代诸帝中,嘉靖皇帝在位时间较长,他在位的时间仅次于万历皇帝。受到“小冰期”的影响[15],嘉靖皇帝在位期间自然灾害频繁。当时科技不发达,人们无法解释为何自然灾害频频出现。面对这些所谓的灾异,嘉靖皇帝除了“修省”之外,没有其他的应对办法,他利用祥瑞来粉饰太平也就不足为怪了⑩。
嘉靖皇帝后来热衷祥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借祥瑞现象证明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依“祖制”而论,嘉靖皇帝以藩王世子身份入继大统是具有合法性的[16]。不过,他还想通过确立自己生父兴献王的地位来证明自己即位具有合法性。嘉靖七年六月修订《明伦大典》时,张璁、桂萼等“标(汪)鋐所献甘露于卷末,以为此上孝感之应”[13]732。 《宋书》言:“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见敬,则柏受甘露。竹受甘露,王者尊贤爱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8]813嘉靖九年十一月,甘露降显陵。嘉靖十五年(1536年)冬十月己亥,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辛巳,奉太宗文皇帝为成祖,皇考献皇帝为睿宗[12]759-760。嘉靖皇帝不断提高生父兴献王的地位,目的就是向世人证明其即位具有合法性11。
嘉靖皇帝对祥瑞现象从利用走向依赖,始于嘉靖四十三年的“天降仙桃”事件。此时,嘉靖皇帝已届中年,他信奉道教,希望长生不老,因而对祥瑞现象日渐依赖。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世宗起自藩服,入缵大统,累叶升平,兵革衰息,毋亦富贵吾所已极,所不知者寿耳。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缘长生而冀褕举。惟备福于箕畴,乃希心于方外也……方其前星未耀,玄鸟方来,瑶筐诞祥,高禖有应,世宗信之,欣然以天神可降焉。于是命道士邵元节为致一真人,金银象印,陪祀南郊,风雨灵坛,职司秘蓚……继又召真人张彦,设金蓚大斋。则有白鹤降庭,卿云捧日。去天尺五,几于呼吸可通矣……而世宗之意,冀遇其真。复召陶仲文者,拜为神仙高士。徐市既去,更用卢生;混康以还,复征灵素。即蓬莱之想愈殷,祈年之观益丽矣。乃若旋风四绕,则行宫果灾;疑狱初平,即春霖早霈。以至白鹿一双,献于浙地;紫芝千本,贡自荆州。又且云气降于祈坛,绥桃来于御幄。比之建章宫中,芝房露掌;玉津园里,幡节楼台。”[12]798-799嘉靖皇帝中年以后,为求长生开始赞玄修道,他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获得上天的回应。早年道教方士为获宠信而呈献的祥瑞此时被嘉靖皇帝视为上天对自己的回应,在这一时期他对祥瑞的喜好逐渐狂热化。
由上述分析可知,嘉靖皇帝对祥瑞的特殊喜好直接导致了嘉靖时期祥瑞现象频繁出现。
四、嘉靖朝祥瑞现象频现的影响
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群臣挖空心思迎合皇帝的意旨。“嘉靖惑于瑞应,惟以粉饰治象为心。一时诸臣,迎合意旨,纷纷讳饰,具表称贺,导谀贡媚,相习成风,几不可胜责”[17]。祥瑞现象大量出现,一方面给帝国带来热闹和喜庆[18],另一方面也导致仕风日趋谄媚化。
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抚吴山献白鹿,“为大臣谄媚之始”[13]733-734。 从嘉靖十二年到嘉靖三十五年,史书中记载的祥瑞达现象竟达21次之多,祥瑞现象几乎每年出现一次。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嘉靖皇帝“诏有司采(芝)于元岳、龙虎、三茅、齐云及五岳,仍访之民间”,“自是臣民献芝者踵至”[6]1696。从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祥瑞现象一共出现了26次,其中瑞芝就出现了9次。嘉靖廷臣之谄媚,由此可见一斑。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诸臣及礼卿为贺表”[19]。嘉靖九年六月,河南、四川呈献瑞麦嘉禾,内阁大学士张璁上《嘉禾颂》,此为群臣献贺唁鸟兽文字之始。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郑王厚烷献白雀,廷臣作《献白雀颂》《献白雀赋》等。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出现景云,群臣作《庆云赋》《大礼告成颂》等。嘉靖三十七年胡宗宪献白鹿,同时献上其幕府宾客徐渭所作《代初进白牝鹿表》和《代再进白鹿表》。《代初进白牝鹿表》云:“臣谨按图牒,再纪道诠,乃知麋鹿之群,别有神仙之品,历一千岁始化而苍,又五百年乃更为白,自兹以往,其寿无疆。至于链神伏气之征,应德协期之兆,莫能罄述,诚亦希逢。必有明圣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乃致仙麋,遥呈海峤,奇毛洒雪,岛中银浪增辉,妙体搏冰,天上瑶星应瑞,是盖神灵之所召,夫岂虞罗之可羁。”[20]《代初进白牝鹿表》文采斐然,内容却无甚可取之处,不过是一篇借赞美天降瑞物来迎合嘉靖皇帝赞玄修道心思的文章。在嘉靖朝,诸臣所献贺唁鸟兽文字在语言上日益骈俪化[21],在内容上则渐趋谄媚化。
随着嘉靖皇帝对祥瑞的喜好程度一天天加深,敢于对皇帝进行劝谏的人越来越少。祥瑞现象古已有之,被一些人视为上天对君主统治的肯定。在明代,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不少大臣对皇帝崇信祥瑞的做法进行规劝。嘉靖七年,当灵宝县“黄河清”的消息传到京师后,御史周相以“诏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时以闻”[11]5525-5526来劝谏嘉靖皇帝。嘉靖九年七月,兵部主事赵时春针对河南、四川献瑞麦的事情上疏劝谏嘉靖皇帝。在执政初年,嘉靖皇帝对祥瑞的态度相对理性,故而虽然对周相、赵时春等人的扫兴行为感到不满,但也能够体察他们的赤诚之心,对他们的处罚也相对宽缓。对周相的处罚在《明史》中有记载:“帝大怒,下(周)相诏狱拷掠之,复杖于廷,谪韶州经历。 ”[11]5525-5526对赵时春的处罚则是“下狱掠治,黜为民”[6]1696。
后来,因言官在“大礼议”“更定祀典”等事件中冒犯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对言官极为不满。嘉靖十年,监察御史喻希礼、石金借天降祥瑞劝谏嘉靖皇帝赦免“护礼派”[6]1496-1497, 这件事进一步加深了嘉靖皇帝对言官的不满。随着“大礼议”“更定祀典”等事件尘埃落定,嘉靖皇帝开始崇奉道教并祈求长生。在这种情况下,嘉靖皇帝对劝谏其停罢地方呈献的言官态度也日趋强硬。
嘉靖二十年(1541年),监察御史杨爵上疏劝谏嘉靖皇帝:“左道惑众,圣王必诛。今异言异服列于朝苑,金紫赤绂赏及方外。夫保傅之职坐而论道,今举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乱莫以加矣。陛下诚与公卿贤士日论治道,则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诞邪妄之术,列诸清禁,为圣躬累耶!臣闻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盗繁兴,诛之不息。风声所及,人起异议。贻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讥,非细故也。 ”[11]5524-5525此番言论激怒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立下诏狱搒掠,血肉狼籍,关以五木,死一夕复畡。所司请送法司拟罪,帝不许,命严锢之”。“既而主事周天佑、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后蓨死狱中,自是无敢救者”[11]5526。
此后,工部员外郎刘魁、给事中周怡也先后因言获罪。从嘉靖二十年杨爵下狱到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上疏之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外相戒无敢触忌讳”[11]5526。
敢于对嘉靖皇帝喜好祥瑞之风进行直谏的人越来越少,致使呈献祥瑞的风气大盛,由此导致嘉靖官场风气日益谄媚化。
五、结语
嘉靖皇帝喜好祥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想利用祥瑞维护自己的统治,二是他因崇奉道教而对祥瑞产生依赖心理。嘉靖廷臣或是为个人利益所驱使,或是为了效忠皇帝,积极回应嘉靖皇帝的这一喜好。在这样的背景下,嘉靖朝大量出现祥瑞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人在献瑞时还特别附上贺唁鸟兽文字,嘉靖仕风逐渐趋于谄媚。由于嘉靖皇帝严惩了一些劝谏其停罢地方呈献的官员,敢于对嘉靖皇帝喜好祥瑞之风进行直谏人越来越少,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嘉靖官场的谄媚风气。嘉靖仕风谄媚,从表面上看是嘉靖廷臣“媚上”所导致的,但嘉靖朝皇权高度强化才是祥瑞现象频频出现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谄媚的政治风气反过来又促进了嘉靖朝皇权的强化。
注释:
①不同文献对于灵宝县“黄河清”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述不一。《明会要》(卷六十八)指出此事发生在嘉靖七年四月,而《明史》(卷二百九)、《明通鉴》(卷五十四)均指出此事发生在嘉靖七年三月。笔者采纳后一种说法。
②灵宝县即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地处黄河中游。每年农历三、四月份,黄河中上游地区降水较少,黄河径流量相对较小,黄河携带的泥沙较少,故灵宝段有时会出现黄河变清的现象。
③本文所讨论的祥瑞现象,以《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记载的为主。至于《明史》等史书中记载的因嘉靖皇帝祈祷而出现的祥瑞现象,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④文中数据为文献数据的汇总。数据来源主要有:《明通鉴》卷五十六至卷六十、《国榷》卷五十五至卷六十、《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明史》卷十七至卷十八。
⑤文中数据为文献数据的汇总。数据来源主要有:《明通鉴》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二、《国榷》卷六十二至卷六十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明史》卷十八。
⑥《明史》记载:“帝于秘殿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明通鉴》卷六十一也有类似记载。可见,嘉靖朝后期诸臣呈献祥瑞,主要是遵照皇帝的旨意行事。
⑦文中数据为文献数据的汇总。数据来源主要有:《明通鉴》卷六十二至卷六十三。
⑧这段文字见于《国榷》(谈迁.国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4016),《明通鉴》也有类似的记载(夏燮.明通鉴:中[M].长沙:岳麓书社,1999:1777-1778)。
⑨原文见《明史》:“当是时,陶仲文已死,严嵩亦罢政,蓝道行又以诈伪诛,宫中数见妖孽,帝春秋高,意邑邑不乐,中官因诈饰以娱之。”(张廷玉.明史: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7901)
⑩古人对于天降灾异十分重视。在“大礼议”事件中,“护礼派”就是利用灾异事件抵制嘉靖皇帝提高生父兴献王地位的。嘉靖元年(1522年)春正月,杨廷和、蒋冕等人利用“清宁宫小房灾”迫使嘉靖帝“称孝宗为皇考,慈寿皇太后为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复加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742-743)。
11嘉靖皇帝利用祥瑞现象来证明其即位合法性的例子还有很多。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本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宁藩后,至庐山刻石纪功,末云:‘嘉靖我邦国。’明年,世宗龙飞,遂用二字纪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731)
:
[1] 龚世学.中国古代祥瑞文化产生原因探析:以周初天道观的形成为基点[J].天府新论,2012(5):133-138.
[2] 金霞.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视野中的祥瑞灾异 [C]//张金龙,王炜民,张军,等.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 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6(6):177-190.
[4] 南炳文,汤纲.明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74.
[5] 胡凡.嘉靖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1-472.
[6] 夏燮.明通鉴:中[M].长沙:岳麓书社,1999.
[7] 谈迁.国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沈约.宋书: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张廷玉.明史: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5.
[10] 张廷玉.明史: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张廷玉.明史: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37.
[15]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6.
[16] 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48-62.
[17]张廷玉.御定通鉴纲目三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
[18] 卜健.明世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77.
[19]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54-55.
[20] 徐渭.徐渭集: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3:430-431.
[21]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D].上海:复旦大学,2009: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