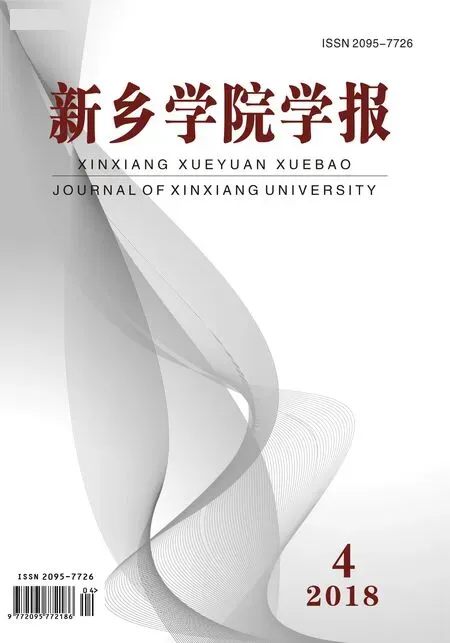论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重复叙事
王青军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小说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上半部讲述主人公杨百顺为寻找一个 “说得着”的人,一路走出故乡延津;下半部讲述杨百顺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一句话”走回延津。一出一回,延宕百年,也牵连出了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曲折复杂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关于“说话”的作品,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将语言运用到了极致,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事语言,刘震云力求洗练精简、叙事直接,没有大量的修饰语言,平实的语言背后承载着巨大的叙事张力,特别是“折绕”修辞的运用,使语言极富韵味、耐人咀嚼。刘震云将这种语言特点称为“拧巴”。在一次被采访时,他曾说“我要把拧巴的世界再拧巴一下”。这种语言的“拧巴”成了刘震云小说的一种明显特征。而这种“拧巴”使语言呈现出了重复的特征,在表达主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一句顶一万句》重复书写着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爱情的破裂,人物的经历正是这些情感消失的过程,而孤独正是来自这种情感剥落后的焦虑和无奈。从这点来看,《一句顶一万句》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关系的消解。从《我叫刘跃进》到《一句顶一万句》以及后来的《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小说中一直重复着一个“寻找”的主题,小说以“寻找”钩连故事情节,这种“寻找”向我们展示了平凡生活背后的荒诞。
关于“重复”,美国批评家劳治认为,“对重复的察觉是阐释语言在像小说这样的长篇文学作品中的作用的第一步”[1]153。他强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对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成分进行全文追踪,考察语言重复在上下文中的作用。而批评家米勒认为,小说中的重复并不仅限于语言的重复,他将“重复”分为三种模式,即文字成分的重复、场景和时间的重复、作品之间的主题重复。不论是语言还是情节或主题,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在叙事中都体现了重复的特征。
一、叙事语言的重复
美国批评家劳治在《小说的语言》开篇中说:“小说家使用的媒介为语言,作为小说家,无论做什么,均需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来做。”[1]155语言作为叙述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小说中发挥着重要的叙事作用。劳治强调对小说语言重复的关注,并在全文内对其进行追踪,探讨其与小说主题之间的关系。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也多处体现了语言的这种重复特征,而在这里语言的重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示作品主题的作用,同时也形成了刘震云“拧巴”的语言风格。
(一)人物称呼的重复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对小说人物的命名带有重复的特征。作品中的人物多采用“老×”的形式,如老马、老杨、老曾、老裴、老汪等等,这既是刘震云对小说人物的命名,同时也是作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称呼。从作者命名的意图来看,刘震云试图通过“老×”的命名方式来消解人物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延津的平凡的生命个体。为了更好地体现人物的这种平凡性和无差别性,刘震云赋予了笔下人物平凡的职业。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没有人干着宏图伟业,大多数人物都是小商小贩,每个人都在为日常琐碎的生活奔波。如老马是赶大车的,老杨是卖豆腐的,老裴是贩驴的。刘震云在小说中剥空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刘震云之所以要彻底地剥离掉小说中的社会政治因素,正是为了能够更加集中笔力来展开对于乡村世界日常言语活动的描写”[2]。《一句顶一万句》以“老×”的命名方式则是剥离了人物的阶级、地位、年龄上的差别,将人物还原为乡村经验中平凡的生命个体,从而探讨乡村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言语关系。
从作品中人物间的称呼方式来看,“老×”的称呼与人物间疏离的关系产生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在乡土日常生活经验中,“老×”的称呼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在叙述杨百顺与老杨由于老马产生的冲突时写道:
卖豆腐的老杨听后,现实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
“老马决不是这意思,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 ”[3]3
若将第二句话改为:“马××决不是这个意思,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效果就不一样了。
从感情经验出发,老杨对老马不同的称呼体现的是老杨心中自己与老马之间的亲疏关系。“老马”这一称呼从老杨口中说出带有一种较强的情感色彩,也符合老杨一直将老马当做自己最好的朋友的特征。但透过作品后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知道两人之间并不存在亲密的朋友关系,老马从没有将老杨当做朋友。所以,老杨对老马的这称呼便带有了一种反讽意味。这种天然的亲近、亲密的称呼背后,掩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人与人之间的“面和心不和”。
(二)词汇的重复
劳治认为,考察重复在上下文中的作用,特别是它与总体结构的关联,有助于阐释作品的意义。据统计,《一句顶一万句》中“说话”一词出现了316次,“说得着”出现了33次,“喷空”出现了61次,“喊丧”出现了42次。小说一直都在围绕着“说话”的问题展开。前半部主人公杨百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背井离乡,与家乡渐行渐远。后半部牛爱国为了寻找一句话,从陕西一路寻回河南延津。因而,“说得着”“说话”“喷空”“喊丧”这些关键词一再出现,从不同层面上起到了提示和强调主题的作用,也具有极大的阐释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如果说寻找“说得着”的人是主人公人生的终极追求,那么“喷空”和“喊丧”就是寻而不得的一种变相的心理宣泄。
以“喊丧”为例。“喊丧”一词在小说中共出现了42次,而且全部集中于上半部“出延津记”中。对于上半部主人公杨百顺来说,“喊丧”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理解小说的主题,“喊丧”也有着重要作用。
小说中,“喊丧”的罗长礼是杨百顺心里最羡慕、最钦佩的人。年少的杨百顺曾一度想要离开卖豆腐的老杨,追随罗长礼喊丧,却因喊丧无法维持生计作罢。虽然杨百顺一心倾向喊丧,然而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喊丧”一出场,带给杨百顺的却是痛苦的经历。为了看罗长礼喊丧,杨百顺弄丢了家里的一只羊,生着病被父亲打了一顿皮鞭,撵出去找羊了。在这里,“喊丧”所引发的故事是对乡土社会中家庭伦理的解构。作品中描写,面对挨打的杨百顺,哥哥和弟弟都在“捂着嘴笑”,老杨在把儿子的头上打出几个血疙瘩后,将生病的杨百顺撵出去找羊。可见,在老杨的心里,羊比儿子还要重要。由此,在这个家庭中,父子、兄弟之家的亲情荡然无存,这是一个无爱的家庭。正如陈晓明所说,“小说中没有看出他的家庭有多少友爱,那只是一个乡村的自然的经济单位,家庭不是友爱的场所,只是生产作坊”[4]。“喊丧”自出现起,便与杨百顺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杨百顺无论是跟老曾学杀猪,还是到县衙种菜,甚至结婚娶了媳妇,心里始终保持着对“喊丧”的痴迷。经历了种种波折,离开杨家庄后,杨百顺杀过猪,染过布,破过竹子,种过菜,蒸过馒头,却始终找不到一个“说得着”的人,此时的他愈发觉得“喊丧”对生活的必要。就像杨百顺自己所说,“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喊丧”与“喷空”一样,能够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两者都有“虚”的特征。杨百顺心中对“喊丧”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或者说是随着生活的发展逐渐认识到其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年少时的杨百顺对于“喊丧”仅仅是羡慕“喊丧”的罗长礼长脖子、声音响亮,而多年之后,感觉生活太“实”的杨百顺则是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了“喊丧”。他从家乡一路走来,是要寻找能够说得着的人,最终却寻而不得,内心巨大的孤独只能寄希望于“喊丧”来发泄出来。小说中 “喷空”一词的重复出现有着同样的意义,这些“虚”的行为,都是人物内心无法言说的孤独的宣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日常生活经验当中,“喊丧”这一行为并不是一种为人所尊崇的职业,“喊丧”人的地位并不高,从某些层面来说,甚至比一般的职业更显卑微。因而,当吴摩西告诉吴香香自己喜欢“喊丧”时,吴香香“气笑了”。显然,在吴香香看来,“喊丧”并不是一件值得喜欢的事情,吴香香的笑带有嘲笑的意思。而这一笑,杀猪的老曾也曾有过。但就是这使人显得卑微的“喊丧”,让杨百顺在历经多年的奔波仍难以忘怀。杨百顺苦寻说话的人,却始终求而不得,心中的孤独与苦闷无从诉说,最终将自己化身“喊丧”的罗长礼,借“喊丧”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楚。“喊丧”这一为人所轻视的职业,最终却代替了人与人交流的最好方式——说话,成了吴摩西倾诉情感的最好方式,这样的一种转变同样使文本产生一种反讽的意味,也体现出了生活的荒诞性。
(三)句式的重复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将语言运用到了极致。他大量地使用重复的句式来讲述琐碎的故事,用重复的语言带领读者在小说中绕来绕去,最终将读者带回到原点,这样的一种重复使得语言既有耐人琢磨的韵味,同时在故事情节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小说中,刘震云大量使用了“不是……不是……也不是”或者“是因为A,也不是因为A,而是因为B,也不是因为B而是因为……”等类的句式,几经转折之后,将读者的思绪带回到开始,接着叙述故事。如在写到牛爱国他妈应该姓什么的问题时,小说是这样说的:
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应该性姜;本也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该姓吴,应该姓杨。[3]226
一个人的姓氏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在小说中,刘震云并不直接说牛爱国他妈姓杨,而是带领读者转了一个大圈子,以“本不该……应该……”的重复句式,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样的一种重复句式使语言产生了一种幽默的效果。然而,这种“重复”的深奥之处还在于,刘震云正是通过这种“重复”将牛爱国妈妈的身份复杂化了。姓曹—姓姜—姓吴—姓杨的姓氏转换体现的正是牛爱国母亲身份的复杂,作者也正是通过这种转换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种转换背后的原因,从而引出了姓氏背后一个又一个复杂的故事。由此可见,“重复”在这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二、故事情节的重复
在小说中,情节是叙事的一个重要元素,为增强文本的可读性,情节的设置一般追求传奇性和神秘性,追求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但是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故事的情节却极为特殊。刘震云十分注重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的情节设置也紧紧围绕着人物之间的关系展开。而贯穿其中的是“孤独”的主题。《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通过“重复”这一叙事手段,将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的亲情、爱情、友情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将人的情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地剥去,最终留给人的是无法言说而又无穷无尽的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采用了两段式结构,讲述祖孙两代人出走和回归的故事。但通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上下两部分的情节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两人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一“出”一“回”,因为一个“找”字,延宕百年,钩连出了几代人的恩恩怨怨。
《一句顶一万句》中“出延津记”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杨百顺为寻找“说得着”的人离家出走的故事。透过杨百顺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刘震云在大量的情节“重复”背后对中国乡村传统伦理关系的解构,或者说,刘震云看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精神孤独的本质,是情感被抽空后的空虚与无奈。
在“出延津记”中,刘震云写到了几对父子关系:卖豆腐的老杨和杨百顺,杀猪的老曾和他的两个儿子,弹棉花的老姜与姜龙、姜虎、姜狗。父子之情本是一种亲密高尚的情感,中国自古以来极为注重家庭伦理中的父慈子孝。但在这几对父子关系之中,我们看不到儿子的孝道,也看不出父亲对于儿子的慈爱。老曾与自己的两个儿子之间,因为自己续弦和儿子娶妻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老姜与自己的三个儿子因为一只鸡腿最终分家。而对于主人公杨百顺来说,父与子的冲突则更加明显:杨百顺因为看罗长礼喊丧,弄丢了家里的一只羊,回来后遭到了父亲老杨的一顿鞭打,在生着病的情况下被赶出家找羊。显然,在老杨的眼中并没有对儿子的关注,丢失的羊比杨百顺更加重要。如果说“对家庭伦理的表现一直是中国乡土社会叙事的独特价值所在”[4],那么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则对家庭伦理进行了激烈的挑战,他对血缘关系进行了戏谑、嘲讽,赋予其荒诞性。父子之间的相互猜忌、兄弟之间的冷漠无情,“在这部作品中,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再次被解构,遭到深刻的质疑”[4]。亲情的消亡迫使杨百顺走出家庭寻找新的情感寄存之处,这就是对友情的追寻。
人物摆脱家庭和家族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建立全新的社会关系。离开老杨的杨百顺开始跟着老曾杀猪,杨百顺与老曾是师徒关系,也是朋友关系。在这里,杨百顺与老曾之间建立了短暂的友谊关系。跟随老曾杀猪的日子对杨百顺来说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但即使是这样短暂的友情依然被解构了。杨百顺因为自己的牢骚被以讹传讹,最终与老曾之间断了来往。他们因为有话可说才成了朋友,建立了友情,也是因为说话断送了友情。在小说的后半部“回延津记”中,刘震云重复写到了牛爱国与冯文修、老丁与老韩、小温与小周等几对友情关系,但友情最终都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宣告破裂。
《一句顶一万句》中还反复出现婚姻关系的裂变的情节,如吴摩西与吴香香、牛爱国与庞丽娜以及李昆与章楚红。婚姻关系的裂变源自婚姻双方对爱情的背叛。杨百顺以“嫁入”的方式与吴香香结合,甚至将自己改姓吴,婚后却发现吴香香早在结婚之前就与老高偷情。吴香香对婚姻的背叛,最终使得吴摩西在寻找她时丢掉了与自己“说得着”的巧玲,吴摩西又一次成了孤独的个人。
陈晓明称刘震云为 “最激进挑战家庭伦理的当代作家”,他指出刘震云用“友爱伦理代替了家庭伦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句顶一万》中,刘震云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温暖的记忆,他在用友爱伦理代替家庭伦理之后的叙事中,再一次无情地解构了这种友爱。在“出延津记”中,当主人公杨百顺身上的亲情、友情、爱情关系逐渐被抽离之后,剩下的只有一副被掏空的躯体,只有无以言说的虚无与孤独。刘震云正是通过不断的重复,将一段又一段情感破裂的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而造成这些情感消亡的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馒头、几斤牛肉,甚至是一句话就足以击溃人们之间的情感,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人与人缺少沟通与交流。因为“说不着”,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每个人都成了孤独的个体。刘震云正是以《一句顶一万句》展示和剖析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这种精神孤独。
三、文本间的主题重复
希利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说,作者在一部小说中可以重复其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5]2。他通过对哈代作品《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的对比分析,指出了两部小说在主题与形式上相互呼应。对照刘震云近些年创作的几部作品,我们也能够发现其作品中有一个贯穿着的“寻找”主题。
小说《我叫刘跃进》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寻找”。无论是寻找钱包,还是寻找载有重要秘密的U盘,刘震云正是通过“寻找”的过程,将一串串故事、一场场闹剧联系在一起,展现的是权力与欲望交织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倾轧,以及面对这一切无法挣脱的无奈。《一句顶一万句》中“寻找”的主题则更为明显,杨百顺“寻找”说得着的人,走出河南延津,一路走到了陕西。牛爱国为了“寻找”一句话,从陕西一路寻回河南延津。从《我叫刘跃进》到《一句顶一万句》,“寻找”的主题一直贯穿在作品当中。如果说《我叫刘跃进》寻找的是物欲社会中人性的温暖,那么 《一句顶一万句》则是寻找孤独境遇下人的精神慰藉。《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寻找”不仅仅是作为故事的线索,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种哲学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家大多关注人的存在状态。刘震云的小说中渗透着存在主义因素。他也曾承认自己读过很多萨特的书,读后觉得还不错[6]239。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曾用 “存在的精神分析”来分析人的存在状态,如人们经常感到的烦恼、恐惧、孤独和绝望。而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感到孤独和绝望,是由于“人总是向着确定去生存”[7]。当人们失去这种“确定性”,处于迷茫的状态时,人们便能够减少心理的恐惧、孤独与绝望。因此,“寻找”成了人们用来逃避孤独的价值选择。《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和牛爱国都处于焦虑与孤独之中,所以二人都选择了“出走”,寻找说得着的人,寻找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但是,在小说中,这样的一句话并不存在,或许生活中也不存在顶一万句的那句话,而牛爱国却苦苦追寻着,也正因此,小说最后的那句“不,得找”才具有了震撼心灵的力量。
从某种层面上说,刘震云是为他的人物杨百顺和牛爱国设定了一个不存在的追寻目标,读者跟随着牛爱国的脚步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最终同样寻而不得。所以,当牛爱国明知道找不到时仍然坚持要找,这时候的“找”就不再是之前的“找”,此时的“找”不再是找一句话,而是在寻找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寻找”的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甚至“寻找”本身已成了一种人生的状态,即对人的生命和生存状态的寻找。套用余华《活着》自序中的一句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8],或许可以说“人是为了寻找本身而寻找”。
《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安波舜在编者荐言中给予了其“千年孤独”的评价。从“孤独”这点来看,《一句顶一万句》可以说是探寻中国底层民众精神孤独的史诗。就像评论家李敬泽说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中,人在苍茫大地上奔走,这个人也不是知识分子,也没有揣着作者塞给他的一脑袋思想,他的问题是家常日用,是千万人、亿万人在生命中都要面对的结实、具体的选择和难局,他一次次奔走,只为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这次或许能说出一句说到他心里、他自己就偏偏想不到的话。就这样,人间烟火竟苍茫了,咫尺间琐碎人事中竟有个浩浩天涯。”[9]为摆脱孤独,人们开始了寻找。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寻找成了解救孤独的最好方式。由此,刘震云赋予了“寻找”以哲学的意义——生命本身就是寻找,其意义也在于寻找。
四、结语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在用最浅显的话来讲述底层人民最平凡的故事,却写出了生活不平凡的意义。小说展现出刘震云精湛的语言功力,不断重复的语言展现的是乡村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刘震云对乡村伦理社会无穷尽的解构,道出了底层民众精神孤独的原因。情感的消失使人仅剩一副空洞的躯体,但人并没有放弃对摆脱孤独的向往,在持之以恒的坚持寻找中,人们重新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所在和生存的意义。“寻找”成了摆脱孤独的理想方式。
: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王春林.围绕语言展开的中国乡村叙事: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2):82-87.
[3]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4] 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5-14,24.
[5] 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
[6] 张英.文学的力量·刘震云访谈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239.
[7] 科萨克,王念宁.存在主义的大师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3.
[8] 余华.活着·自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7.
[9] 王晓旋.孤独的精神还乡: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式寻找[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