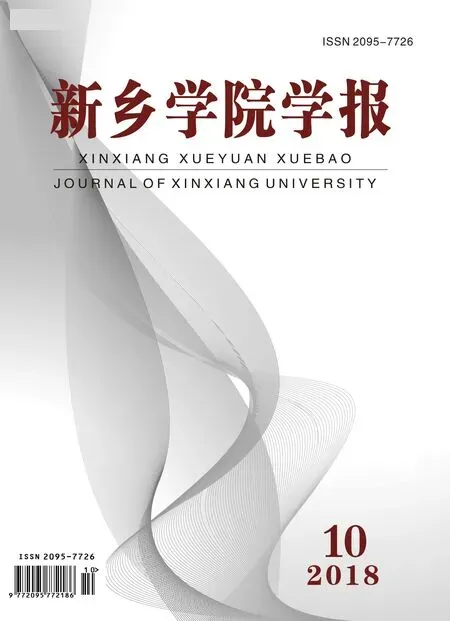荒诞的叙述现实的孤独
——对《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一种阐释
梁 宇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刘震云自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以后陆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系列“官场”题材的作品。此后评论界对刘震云小说创作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刘震云于2017年出版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再次牵动人心,作者用朴实幽默的语言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种种荒诞。“吃瓜群众”种种荒诞行为的背后掩藏着永恒孤独的生存本相,流露出刘震云对现实存在的独特思考。
一、荒诞的内涵
“荒诞”在西方词典中的解释十分简单笼统,意指不合乎情理或不恰当。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将“荒诞”具象为一个英雄的身姿。他指出:“荒诞指述现代人普遍面临的基本生存处境。现代人被抛弃在这种处境中无路可逃,他唯一可做的只是如何面对荒诞并在荒诞中生存。”[1]马丁·埃斯林在《论荒诞派戏剧》中用“荒诞”指一系列荒诞剧作家在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共同倾向:人的异化特点与意义的虚无,从表现形式到主题内容一以贯之的荒诞特性[2]。在中国本土,“荒诞”一词也有类似的定义,如《辞海》中对“荒诞”的阐释:“不近情理,虚妄不可言,如荒诞不经。 ”[3]
本文所运用的“荒诞”概念是指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一种生存困境。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身处在一个热闹喧嚣的世界之中,同时人人又被冷漠、孤独的感觉包围。当这种表面的繁华、内在的孤独被一个喊“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孩子揭穿之后,所有“正当”的言辞和崇高的“意义”就会立刻瓦解,世界会遁入虚空的境地。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幅幅场景,表面看似繁华,人人位高权重,实则背后落寞,拼命挣扎之后结局仍是一片荒凉。
二、荒诞的主题表现
刘震云的小说有他独特的“荒诞”风格,从早期的小说《一地鸡毛》开始,他就致力于书写一个人与身边的几个人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呈现出人在生活中发生异变的过程。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由“不可知”力量推动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瓦解又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毫无逻辑、毫无规则的联系构成了小说主题的“荒诞”性。
(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靠种种“不可知力量”
刘震云小说中从来没出现过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要么是单位中的“小林”,要么是“剃头的老裴,杀猪的老曾,传教的老詹”。这些小人物“带着乡间麦秸秆的味道,带着活泼生动的生活气息而来,不是那么高大,不是那么无私无畏,但更真实,更可爱”[4]。小人物之间的连接组成了刘震云的小说世界,有意思的是,小人物之间关系的建立完全是种种“意外”的组合,关系的聚散与离合完全靠“不可知”的力量所推动。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围绕牛小丽寻找逃跑的宋彩霞展开故事情节,找的过程中结识了苏爽,由此引出公路局长杨开拓、某省副省长李安邦、某市副局长马忠诚等人,这四个人原本是互不认识的,但由牛小丽外出找人,故事逐渐演变成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就这样四个陌生人最后反倒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任何一人暴露,其他三人都逃脱不了,冥冥之中他们就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捆绑在一起。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也有类似情况,由李雪莲一人引出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等人,这些人物故事都是围绕李雪莲的上访展开,他们原本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甚至不知“李雪莲”是谁,可就是李雪莲的上访,让他们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人与人之间“不可知”力量的呈现,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改变了人的命运,使人存在的目的性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因果关系给主人公留下了“意义的虚无”,从而表现出这个世界惊人的荒诞色彩。
(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瓦解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小说中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体现在宋耀武被双规这一事件上,由李安邦一手提拔起来的市长宋耀武被双规后,公安厅厅长又背着公安局局长段小铁复查车祸案,紧接着杨开拓被调查,继而在杨开拓手机上发现了苏爽,通过苏爽又发现了牛小丽,由牛小丽又牵扯出李安邦。小说中一人出事就牵连出一大串人,这些人原本可以互不干扰,可就在宋耀武被双规后“真相”便一一浮出水面。作品表面叙述波澜不惊,但由一人而牵连出众人,这种骨牌效应的背后是对世界“荒诞”性的深刻认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人物命运的发展呈现出多序性与不确定性,最终堕入加缪所说的现代人被抛弃在无路可逃、无处可跑的境地。
(三)荒诞的叙事结构与情节设计
刘震云的一系列新写实小说都是典型的荒诞叙述,以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来书写各式各样的荒诞,可以说“荒诞”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继续用自己的独特方式书写着不同阶层的人物的荒诞命运。
1.结构上的荒诞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我不是潘金莲》在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前言,仅用为数不多的文字去写正文,这种序(前)言和正文颠倒的结构安排打破了读者正常的阅读习惯,同时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全书共297页,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讲述前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你认识所有人。前两部分共271页,而第三部分,也即正文,仅26页。前两部分围绕牛小丽、李安邦和杨开拓三个人物展开全文的叙述,正文部分仅用少数的文字写马忠诚误入洗脚屋,通过一个看似滑稽、戏谑的事件揭示出人生的荒诞不经。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亦是如此,整部小说也是三部分,第一、二章序言:那一年,二十年后。第三章正文:玩呢。前两部分写李雪莲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上访,想要摆脱自己“潘金莲”的罪名,折腾了连同自己在内的一批又一批人。最后一部分写史为民受李雪莲上访的启发,利用所谓的“上访”,顺利返乡和老友打上了麻将。
这种用大量篇幅对序(前)言进行铺设,而用为数不多的语言来写正文的构思,凸显了刘震云对小说结构的精心安排。这种反常规的写法,相较之前传统小说故事叙述的开头、高潮、结尾这种起承转合式的写法大不相同,他独特的反常规写法,解构了历史上的正史写法,脱离了写作的主旋律,悖离了世界的规整,这种写作背后其实掩藏着刘震云对世事的认识与看法。结构上的反叛暗含着他对现成秩序的反叛,现实世界是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景象,可这热闹景象背后又有多少无可奈何?又有多少人生困境?又有多少孤独不为人知?刘震云小说中结构的反常规化正是本文所要阐述的荒诞意识的真实显现。
2.情节上的荒诞
刘震云小说虽然较多采用写实的手法,但许多故事情节,包括一些很小的细节设计都颇具戏剧特色,虽然是源于生活的真实但是也充满了调侃与戏谑的意味。
全书在正式开篇前引用了一句“我”三舅的话:如有巧合,别当巧合。作者开篇明言别把巧合当回事,但这些巧合却不容忽视。牛小丽去西南某省寻找嫂子宋彩霞,途中又丢了老辛老婆,二人都未找到,自己却被一个叫苏爽的女子骗去当了“良家妇女”,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宋彩霞”。一切皆由宋彩霞开始,丢了宋彩霞,去找宋彩霞,最后自己倒成了“宋彩霞”。这种情节上的设计令人匪夷所思:原本自己是一个人,到最后自己又成了另外一个人,那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这种不可思议的情节设计是对人生崇高理想信念的解构,人到最后还是一种无意义的存在。
小说中李安邦和朱玉臣原本是好朋友,但在市长考察期间两人产生嫌隙,结下怨恨。十八年后李安邦被选为省长候选人,两人恩怨重新展开,在李安邦觉得四面楚歌时朱玉臣竟然被查出癌症晚期,自然无暇顾及其他,李安邦就这样顺利地当上了省长。说来更巧的是,就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马忠诚也当上了市环保局局长:环保科的十一位科长,为争夺局长之位互相举报,所以任谁也不放在眼里的马忠诚倒因祸得福了。
整部小说中这样的“巧合”情节还有很多,情节设计的荒诞性为文章增添了戏剧性色彩,饱含着幽默与嘲讽。
三、荒诞的艺术表现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5]我们要想充分了解这部新作的文学内涵,就必须对它的语言进行探讨分析。
(一)重复的语言风格
刘震云小说的语言一贯朴实简洁,多口语、俗语,而在这部小说中,重复的语言现象格外凸显。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有好几处词语和语义上的重复。
1.关于牛小丽“长得像个外国人”
(1)出自王京红和李柏琴之口:“你长得像个外国人。 ”[6]68
(2)出自傅总之口:“你的好看,和别人不一样,你长得像个外国人。 ”[6]73
(3)出自省长李安邦之口:“果然长得像个外国人。 ”[6]87
(4)出自镇派出所的男警务人员之口:“长得是有点像外国人。”[6]252
(5)出自中年女警察之口:“可能你长得比别人漂亮吧,可能你长得像个外国人吧。”[6]261
2.关于“口渴”
(1)对杨开拓被“双规”后接受调查时口渴的描写:“现在觉得渴了比饿了还要难受十倍。千万只虫子不但在噬咬他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还在拼命吸吮他身体里最后一点水分。”[6]213
(2)牛小丽得知丈夫出轨与丈夫冯锦华对质时,对冯锦华口渴的描写:“冯锦华觉得千万只干渴的虫子不但在噬咬他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还在拼命吸吮他身体里最后一点水分。 ”[6]247
在这部小说中前前后后一共五次出现牛小丽长得像外国人,此外关于“口渴”“知人知面不知心”“傻×”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越想说话,越急于表达,结果表达得越不清楚,甚至越表达越糊涂。这种重复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 “吃瓜时代”背后的孤独本质,揭示出人类在言语沟通上的一种困境。
(二)“拧巴式”幽默
刘震云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他最幽默的一部小说。生活本身就是幽默的,这毋庸置疑,只是我们缺少发现幽默的眼睛,难以看到幽默背后的现实。小说中“表哥”“微笑哥”杨开拓的故事是有生活原型的,作者有意将生活本来的面貌如实呈现,以文学形式表达生活幽默背后的生活真实。
小说中最突出的是“拧巴式”幽默。“拧巴”一词出自《我叫刘跃进》这部小说,他说这个词是他从生活中学到的,“拧巴”的同义词叫“别扭”,而生活中最大的别扭就是对别扭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处,环保局局长马忠诚的一段话令人若有所思。“啥叫荒唐?事情荒唐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做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做也不叫荒唐,联防队员把钓鱼执法的钱拿回家,他老婆又拿这钱去过日子才叫荒唐。你也荒唐,我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常?”[6]296何为“荒唐”?荒唐原本是离谱,不符合常规,让人感到奇怪的意思,而在这里,经过马忠诚对于“荒唐”的理解,让我们明白世上任何事都是荒唐的,荒唐即合理,因此荒唐反而成了天经地义之事。这种“荒唐”的解释中既有“话”的拧巴又有“生活”的拧巴。从修辞上来讲,拧巴是反讽,反讽的内容是对世界的不满,凸显现实世界的可笑。这种“含泪式的微笑”对揭示荒唐世界是非常有力量的,它是刘震云理解世界的一把锐利的解剖刀,通过这种“拧巴”式幽默也促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清醒的认识。
四、“荒诞”的背后
“吃瓜”是一种网络用语,网络上将“吃瓜”和看热闹、围观联系在一起。“吃瓜时代”原本是一个轻松、惬意、诙谐的时代,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竭力向我们展示了“吃瓜时代”背后的孤独虚妄的本质:“吃瓜时代”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时代,是一个想象大于现实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夸饰渲染的时代,但这个时代说到底还是一个永恒孤独的时代。
孤独是刘震云小说的永恒主题。一个人遇到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亲人、朋友能说得上话。小说对李安邦翻阅一千二百二十三个手机联系人才找到一个自认为“靠谱”的朋友这一细节描写,真实而详细地描绘出李安邦的孤独无依。没有一个真正交心的朋友,就连自己的妻儿也不能信任,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牛小丽与丈夫冯锦华、老辛与老婆朱菊花亦是如此。牛小丽丈夫在五年前就与齐亚芬有染,可牛小丽五年后才从他人之口得知;老辛与老辛老婆两人也是互相防着,老辛怕媳妇逃跑不敢多给零花钱,老辛老婆为取得老辛信任对他事事依顺,可一旦抓住机会就一逃了之。小说用“吃瓜儿女”来揭示这个孤独且异样的时代,人生活在这种隐瞒、欺骗、互不信任的环境中,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任人摆布,这种孤独本身也是“荒诞”的一种外化,是作者揭示的隐藏在“荒诞”背后的现实孤独。
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将生活中的幽默搬到文学中,用“荒诞”的书写方式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这个孤独的“吃瓜时代”。“吃瓜时代”的大众虽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人,无时无刻不与他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实则都在承受着孤独的压迫。“吃瓜时代”表面看似是一个热火朝天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荒诞不经、无以言说的世界,要想在这个“吃瓜”时代洁身自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就要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