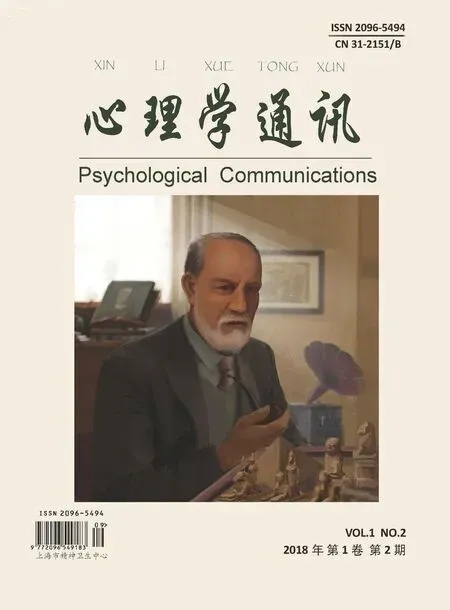关于心理治疗的六个疑问
谢斌
本期的主题,是各路专家从各自的专业或学术领域,讨论“心理治疗”有关的研究或观点。
与这些年在中国大陆日趋火爆的心理咨询(psychological counseling)相比,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无论从专业还是法律角度看都要求更高,实际处境也显得颇为尴尬。比如执业场所,对前者几无明确要求,后者则被限制在有极高准入门槛的“医疗机构”,而如果学历教育不是医学相关背景,在许多地区又存在入职医疗机构的重重障碍;比如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实行的是市场化定价,收费没有上限,而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心理治疗服务则受到严格的价格管制,技术优势和劳务成本无从体现。从各自吸引到的人数(尽管相关证书的证明效力并没有可比性)看就是:自2002年启动证书考试到2017年人社部将心理咨询师从职业资格目录取消,取得该职业证书者已达130万之众;而同年启动中级职称(初级职称直到2015年才启动)考试的心理治疗师队伍,迄今才仅有约0.5万人,且许多还是兼做治疗师的精神科医生。
由是观之,作为学术的“心理治疗”也好、作为职业的“心理治疗师”也好,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还能否好好生存下去都值得存疑,更毋庸侈谈发展了。
要解决好一个专业的生存发展问题,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根本上还是要从专业内部着手。心理治疗领域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如果在专业内部无法形成共识,要去外部影响公众、影响政策必然困难重重。
以下六个问题,虽然不全与专业的困境有关,但对于思考当前“尴尬”的原因以及将来如何破解,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这些问题迄今尚无标准的答案,在此抛砖引玉,期待学者们在相关学术、管理、政策等研究中不断提供真知灼见。
1 心理治疗是独立的专业领域吗?
心理治疗作为专业技术、心理治疗师作为专门职业,应该均无异议。但在我国的毕业前教育体系中,心理治疗是单独作为一个专业设置,还是纳入某个或多个已有的专业领域,目前大概还没有定论。既有在心理学中纳入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也有归入临床医学的医学心理学方向的,还有专家呼吁参照境外的做法,为其新设临床心理学专业开展统一培养。
即便专业的定位解决了,其应该设在心理类院校还是医学类院校、或者两者均可,也需进一步明确。
这类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涉及心理治疗从业人员的基础来源。目前不问专业出处,只需医疗机构证明在从事心理治疗相关工作即可参加初级职称考核(从而进入卫生专业技术通道)的做法,相信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策。
2 心理治疗属于“治疗”范畴吗?
站在医疗卫生的角度看,“治疗”往往与用药、手术等相关,即便如康复治疗等,也会联系到相关康复器械的使用上去。因此心理治疗进入医疗机构的另一大障碍,便是要明确其“医疗属性”。
回答清楚此问题,实际上有助于厘清上文提到的心理治疗专业设置是否一定要在医学院校的问题。
中文的“治疗”其实来自英文的两个单词:一是“therapy”,指的是那些耗时较长、通常不使用药物或手术、以改善整体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状况为目的的方法。另一个“treatment”,才是偏重于为治疗某种特殊病症而采取的、通常使用药物或手术的医学疗法。诸如理疗、音乐治疗、按摩治疗、运动治疗等,均为therapy 而非treatment,其专业设置大多不在医药院校,但专业实践却都已为医疗卫生领域所广泛接纳。(非医学背景心理治疗师提供的)心理治疗在我国只不过是其中新的一员而已。
3 心理治疗是否确实需要这么多理论流派和技术方法?
医疗卫生服务中一个敏感的问题,便是费用支付。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方式,都离不开围绕“安全”和“有效”提供的循证证据。心理治疗如能像药物治疗那样,经过临床验证明确疗效与疾病或症状的对应关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则无论存在多少种技术流派,都是合理的。
但现状却是,至少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老的流派和技术尚未完全阐明疗效机制及临床必要性,新的理论和技术又蜂拥而至。而且针对相同的临床问题,不同流派之间还各执己见、并不完全包容,或者不能在不同理论取向的治疗师之间规范化地“通用”。
这方面形成共识对于本专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质量监管、人力和技术成本的测算(与科学的定价有关)等等,都要以此为前提。可资借鉴的,是在起步较早的一些国家实行的“技术准入”制度。比如德国(钱铭怡等,2010)不仅设立“联邦心理治疗科学顾问委员会(Federal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for Psychotherapy)”对不同流派的疗法按循证标准进行科学审定,还通过社会保障系统的“联邦联合委员会(Federal Joined Commission)”对心理治疗方法开展是否纳入保险支付的评审。在诸多技术中,目前纳入保险支付的仅有最早获得科学审定的精神分析治疗及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行为治疗等少数几种,而第二批获得科学审定的系统治疗则尚未得到保险公司支付(Fydrich, 2018)。美国则是通过专业学会,对已有循证依据的各种治疗技术具体可应用于哪些疾病或问题加以明确认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Cook, Schwartz, Kaslow,2017)。
4 心理治疗的疗效如何评价?
相较于药物等治疗,心理治疗的安全性具有较大优势,但有效性却时常受到质疑。因此科学评价的重点,即是其临床疗效。
简单地评价某疗法对某病患有效或改善了其心理健康状况,是远远不够的。严格的临床评价应参照药物试验的方法,遵循随机、对照、盲法等基本原则。这方面也有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WHO曾以单行本推荐团体形式的人际心理治疗(IPT)作为抑郁症可能的一线治疗(WHO, 2016)。2015年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Fonagy, et al., 2015)显示,与常规抗抑郁治疗相比,长程精神分析治疗(LTPP)在远期随访观察(24月至42月)中的疗效更佳,且患者社会适应能力改善更大。最近还有研究(Dunlop, et al., 2017)探索存在于某些抑郁症患者中的对认知行为治疗较对药物治疗更敏感的生物标志。
类似的还有关于治疗成本效益的证据,也需要科学设计的研究加以论证。比如近期的2项研究(Altmann,et al., 2016; Altmann, et al., 2018)就分析了门诊心理治疗在降低保健费用等方面的作用。
5 心理咨询师可以做心理治疗吗?
我国现行的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三条对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治疗设置了禁止性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此规定的合理性可以存疑,但仍需严格遵守。实践中最好将其理解为监督管理上的设限。因为首先,在专业技术上这两个领域难以明确区隔,其次,目前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活动尤其是培训活动,主题都离不开各种心理治疗方法。
心理咨询师在其咨询服务中经常会运用到心理治疗技术,但其本质上仍是提供的“心理咨询”而非“心理治疗”。好比某精神科护士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可能会熟练地运用到认知行为技术,但从行政管理、甚至是纠纷处理的角度看,其行为仍然只是精神科护理,不能认定为心理治疗。但如果该护士以“心理治疗师”自居,并以“心理治疗”项目提供服务甚至收取相关费用,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相似的问题还涉及心理咨询师可否在医疗机构从业?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即可理解为“不禁止”。事实上各地的医疗服务项目中,大都有“心理咨询”。除治疗师外,心理咨询师应当也是提供该服务的合格人选。
6 心理治疗师队伍要多大才够?
考察某职业“是否有发展前途”时,一个最直观的关注点就是其人力资源供需差距。我国目前专职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底数并不十分清楚,即便以在职全部约0.5万人计,供需差距仍然巨大。按照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的统计,全球每10万人口中,“服务于精神卫生体系内的心理治疗师”的中位数为0.88名,高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属于此列)为1.89名(WHO,2018)。以此推算,要达到2016年的全球或者高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位水平,我国当前仅在精神卫生服务系统内就大约需要1.3万到2.6万合格的心理师,人数缺口达60%~80%。
如果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正是社会心理健康需求剧增的时期,心理治疗师数量的短缺恐怕还要更大些。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