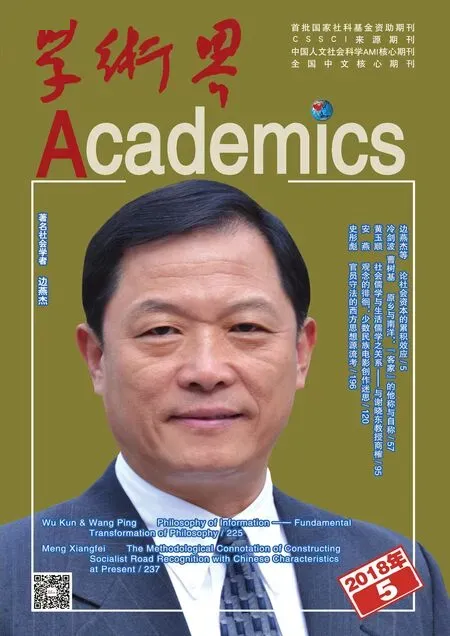观念的徘徊: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迷思〔*〕
○ 安 燕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在我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历史上,除了十七年时期的艺术辉煌被反复提及、浓彩重墨书写,似乎再难有任何一个时段的创作能与之比肩。即便在当下艺术观念极大自由、艺术手法无限多样化、题材类型高度多元化的语境中,也难在整体上比肩“十七年”。众所周知,“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无一例外服务于政治,无论是类型特征突出的《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姐》《神秘的旅伴》等,还是秉承左翼文艺片传统的《农奴》《边寨烽火》《哈森与加米拉》等,“政治”是其共同的大写主题。事实上,“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就其思想诉求而言,是极其单一的,政治大于一切,无论是语言、形式、表现手段和美学风格,还是主题表达,与当下充满多元化、多样性、艺术观念日趋丰富复杂、表意更为宽广的创作实难一拼高低。然而,“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的煽动力、感染力直到今天,依然无比强悍,其政治与美学会通的近乎自然主义的经验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政治与美学的会通使“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找到了它自己的“最终形式”,如同特吕弗对希区柯克悬疑惊悚片“最终形式”的认定,一部电影“不仅应是找到它的完美形式,而且要找到它的最终形式”。〔1〕而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整体上未必创造出了“完美形式”,但一定找到了它的“最终形式”,无限贴近它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受众审美气质的形式。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最终形式”的秘密在于“会通性”的建立,即主流意识形态、故事、形式、风格、文化、民俗风情等政治的、文化的、审美的、商业的诉求完美相融,润物无声。故事始终居于主导性的链条上,语言、形式、民俗风情乃至意识形态话语皆有限度地贴附剧情而生,缝合于故事链。其电影形态恰似我们今天对主流电影的期待,“我们现在要建构的是一种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我们提倡、建构的这种主流电影就是要使中国的主旋律电影走向商业化的制片体制,同时使中国的商业电影体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精神。”〔2〕“我们要提倡的主流大片,就是要把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精髓与艺术化追求、商业化运作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道理是一样的。”〔3〕今天,在主流电影领域,确然出现了一批主流价值、艺术性、商业性有机统一的优秀影片,如《集结号》《云水谣》《烈日灼心》《白日焰火》等,但少数民族电影依然远未进入主流电影的行列,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依然徘徊在边缘,苦苦挣扎。自“十七年”之后,少数民族电影为何无缘主流无缘市场,无缘进入大众视野,为何“被”边缘或自甘边缘,归根结底,是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观念出现了问题。受创作惯性、文化认知、市场大气候的影响,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在小众化与文艺片、原生态与民族志、类型化探索等观念中摇摆不定或各执一端,难以达成平衡,更难走向会通。
一、“小众”与“文艺”
“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因其政治、文化与美学的会通,整体上呈现出较为典型的文艺片特质,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秉承了新中国成立前文艺片的“大众化”“通俗化”追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从奴隶到将军》《傲蕾·一兰》《孔雀公主》等影片同样继承了“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通俗好看的文艺片风范,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认可。那么到了1980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松绑,阶级斗争、民族团结的主题失去了其时代有效性,中国电影进入全面探索期,要求电影语言、电影观念、电影叙事手段现代化,向传统戏剧电影观念挑战的呼声响彻电影知识界。第四代、第五代纷纷加入这场极具革新力量的探索电影的新浪潮运动之中。轻叙事,重描写,淡化情节,渲染环境,重视造型和人物塑造以及鲜明的导演意识,形成了这一时期探索电影的独特面貌。
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也呼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张暖忻的《青春祭》,田壮壮的《盗马贼》《猎场扎撒》,李小拢的《鼓楼情话》《神女梦》等,均体现出与“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重传统技法、重故事冲突的迥异面貌。“《青春祭》以一种散文化的电影语言,完成了对‘文革’及其少数民族生活的另类反思。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盗马贼》,几乎完全淡化了故事情节,把镜像语言的表达推向了极致。”〔4〕《盗马贼》更是大量呈现送鬼、敬神、天葬、祈福等宗教仪式场景,“具有民族文化学及其人类学的价值”。〔5〕《猎场扎撒》《盗马贼》这类影片主要通过走国外评奖的艺术路线为人所知,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为少数民族电影开创出一种新的格局,然而,其故事的极度弱化和叙事的寓言化只能将观众拒之门外。广西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鼓楼情话》,表现的是侗族人民的风情习俗和历史传统,“它既非风情纪录片,也不似纯粹意义上的情节片,倒更象是一首电影散文诗。这散文诗情节很散,但民族风味醇厚,象缓缓淌流的山泉、象静静湖面上的一泓清水、象淡淡的月色……”〔6〕《鼓楼情话》彻底淡化情节弱化故事,依靠精致的画面和民俗景观来吸引观众,使得影片遭遇零拷贝的尴尬命运。广西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另一部少数民族电影《神女梦》,其“神话+爱情”的题材虽有天然的吸引力,但导演李小拢抛弃原著《百鸟衣》反抗强暴、争取自由的核心故事,而对人的原始欲望和人性的本能欲求进行了大写化书写。这一改编既是80年代人文精神背景下探索、实验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西方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导演雄心勃勃,试图探索少数民族电影汇入80年代艺术片开拓的洪流,但由于他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上不够务实,盲目西化,导致水土不服,难以为本土观众认同。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因其大众化、通俗化的追求和兼容会通的品质,实现了艺术与市场的双赢,相较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探索片,其整体上呈现出来的艺术性较为持中平和,并秉承传统叙事法则,可以称之为“弱文艺片”的话,那么以《盗马贼》《猎场扎撒》《青春祭》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电影则可称为“强文艺片”,其核心标志是导演意识鲜明强烈,轻故事和情节,重描写和情境,重造型、象征和人物塑造,总体特征是内容与形式上反传统常规叙事。从新中国成立前《瑶山艳史》《塞上风云》《花莲港》“开化启蒙”或“民族团结”的主题,到“十七年”近乎整一性的“阶级斗争”“民族团结”主题,到1980年代中后期探索电影多样化的人性、信仰、生死等主题,再到当下更加多元化的创作,少数民族电影形成了自身从“弱文艺片”到“强文艺片”及其并行发展的轨迹,它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流电影”框架下文艺片、类型片的二分格局截然不同,它始终框定于“文艺片”范畴之中。虽然全球性的电影产业化浪潮不断刺激着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商业神经,但由于创作思维和文化认知的惯性,其在类型电影的生产上依然未有质的突破,这使得它迄今仍保有文艺片的单一格局。尽管当下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日趋多元化,但仍然显得黯淡寂寞,一方面是由于“十七年”辉煌群落的参照;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弱文艺片”摇摆在艺术、文化、商业之间,或为原生态文化左右,或为商业诉求把控,或为陈旧的经典叙事禁锢,难以在一个扎实丰满的故事中贯注、平衡少数民族电影必需的多样化表达,呈现出少数民族电影应有的“最终形式”。这一类“弱文艺片”主要指的是原生态电影、民族志电影或有类型化意识的影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承袭“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大众化、通俗化的传统,但往往故事、人物、形式、立意较为陈旧老套、简单肤浅,或以原生态文化、民俗风情的展呈来支撑叙事,或以简单的类型框架来敷衍剧情,既缺乏故事的厚度,更缺乏精神的厚度。难怪郑洞天先生直言批评“少数民族电影太肤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庚胜先生更是严厉批评少数民族电影“对少数民族风情和民俗表现庸俗化”、“缺乏历史厚度”、“盲目地唯美化”、“形式大过内容”、缺乏“内在的文化精髓”〔7〕。如果说“十七年”少数民族“弱文艺片”因对“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强度聚焦而应和了时代之需,又因其对文化、美学、商业等附加值的平衡处理而获得了对应于所处时代的“最终形式”,那么今天的“弱文艺片”在主流文化、地域文化、美学观念、市场语境全面改变的情境下,在曾经的附加值实现了对等的情况下,不管是照搬“十七年”的经验,还是基于一种简单的整合思维,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获得其“最终形式”的。
1990年代置身于市场经济语境中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一方面保留了自80年代以来的艺术探索、崇尚人文精神的经验和趣味,一方面又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尽管如此,创作者的个人艺术趣味还是起着主导性的作用。《黑骏马》《益西卓玛》《红河谷》《悲情布鲁克》《东归英雄传》等一批少数民族电影,仍在整体上彰显出“强文艺片”的格局,并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由此奠定了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中国文艺片中坚力量的地位。较之自“十七年”以来的“弱文艺片”,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挖掘与理解显然更为深入、准确。谢飞执导的《黑骏马》《益西卓玛》不仅在形式和风格上以诗意化的抒情、大色块的写意、远景空镜的大量使用、民族音乐的高扬、情绪情调和意境的营构等手段有效地替代了叙事与冲突,更在主题上凸显了对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背离,对毫无掩饰的人性欲望、生命的韧性和强度的礼赞。对欲望、生命、精神自由的书写远远超越了“十七年”时期的单一主题,显示了少数民族文艺片对传统的一种超越性追求。
新世纪以来,在日渐高涨甚至势如破竹的产业化浪潮里,类型电影的开拓和繁荣成了时代之急需,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在水土不服中一边陷入焦虑,一边却难以克服对少数民族电影的认知惯性,在类型开发的无力中,只能继续徜徉在文艺片的理想里远离商业大潮。蒙古族导演宁才就认为:“少数民族电影不能走市场路线,至少在今天它走市场没有意义,也走不了。少数民族电影应当深入民族的心灵,表达民族的精神,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8〕对于很多少数民族电影导演来说,是否能占领市场并非少数民族电影的使命,而表达民族内在精神的艺术追求才是它的生命力所在。拍摄《马背上的法庭》和《碧罗雪山》的导演刘杰也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就是小众的,不可能有太大的商业市场,民族题材电影更多是一种文化的担当,他甚至认为艺术片天经地义就是背离于主流的。万玛才旦在采访中多次表示,自己在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中,会考虑更充分的个人表达,因为自己的影片大都是小成本制作,投资方往往不会有具体的票房要求,自己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压力。更多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以实际行动呼应着少数民族电影的“文艺片”使命。
陆川执导的《可可西里》以强烈的纪录片风格、真实的情节、节制内敛的叙述,呈现了一种充满力量感的真实震撼,对人类的生存危机给予冷静而深沉的观照。“象晨风一样清新”的《诺玛的十七岁》以抒情的笔触和散淡的叙事呈现了哈尼族少女对“外面的世界”的怦然心动,表现了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落差。王全安执导的《图雅的婚事》讲述的是一个蒙古族女子图雅“嫁夫养夫”的故事,置身于男性、现代文明重重包围与压力中的图雅凝聚着微观性别权力政治的典型化书写:勤劳善良、坚韧独立、精神强大的女性不仅是男性的知遇者与拯救者,也是她所置身的文明、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影片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包裹的却是充满戏剧性张力的情节和人物的精神强力,是一部在艺术、文化和商业之间平衡较好的作品。
如果说上述影片因较为强烈的导演个人风格、深邃的精神诉求和精良的制作而具有“强文艺片”的特质,那么万玛才旦的创作则在整体上集中体现出新世纪少数民族“强文艺片”在困境中的坚守。其代表作《静静的嘛呢石》以平淡自然的笔触,去“奇观化”的生活流叙事,描绘了一个偏僻山村的藏族寺院里,一个小喇嘛在藏族新年回家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本土文化和外来文明之间的奇特体验,由此深入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万玛才旦以平静、平和、包容的态度表达了对传统本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文明的深入思考。新作《塔洛》则在现代性的探索上更为冷峻,通过一个没有自我身份认同的牧羊人试图从传统走向现代,寻找身份认同并彻底失败的故事,呈现了当下藏区青年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的真实精神生态。该片在语言、形式、风格上的考量显然更为精细,更具隐喻性。较之少数民族“弱文艺片”中规中矩的表现手法、老套的故事和表意,万玛表现出对散文化叙事、纪实手法、黑白影像、长镜头、远全景、日常性、去奇观化的个人化偏爱,这使得其作品具有“强文艺片”的突出特征。万玛才旦的创作提供的重要启示在于: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如何克服对那些表层的、生动的内容的追寻,不再将那些至关重要的细节、意味深长的仪式当作奇观来展示,而注意到它们丰富的符号性和叙述性,及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特性的关联,从而真正走入少数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内部与深处,并赋予其时代新思维。
此外,诸如《季风中的马》《碧罗雪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长调》《清水里的刀子》等少数民族电影虽然不得不继续面对市场的压力和难以进入院线的尴尬,但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功却毋庸置疑。“少数民族较之于主体民族对于文化流逝、语言消亡、社群崩解及道德断裂等问题有着更为切肤的体验。”〔9〕或许正是由于少数民族对现代性危机更为直接和多重的体验,才使得一些优秀艺术影片的创作与生产成为可能。
二、“原生态”与“民族志”
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界和学术界,有一些创作者和学者不约而同地视少数民族电影的文献价值、文化志价值、民族学和人类学价值为其最重要的价值,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即使不卖座,也因具备这些价值而显得意义深远。韩万峰以拍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著称,他拍摄的《尔玛的婚礼》《我们的嗓嘎》等都是母语拍摄。他坚持认为,少数民族电影即使不卖座,作为文献资料也有巨大价值,“我始终认为拍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是艺术家一种良心和责任,哪怕我的电影现在没有人看,但在若干年以后,它能成为专家研究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这也是值得的。”〔10〕民族学意义上的母语电影“都以独特的创意、鲜活的少数民族风情,显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别样光彩。而其在民族文化及民族学层面上的深远意义,更是让人们满怀期待”。〔11〕有学者直接将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一种文献来考察,认为,“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较之于主流题材与类型的电影有着题材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是在审美、认识、娱乐、感发、教育之外,还有文献记录的价值。”〔12〕有学者肯定少数民族电影“文化软实力”的价值,认为“这些少数民族电影,势将在中国与世界电影的对话中焕发出一种清新而启迪人心的‘文化软实力’”。〔13〕更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文化意义上,更倾向于称其为‘文化志’电影,即记录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探讨电影的意义,更多不是在电影艺术本体意义上,也不是在产业意义上,而主要体现在文化意义上。”〔14〕
事实上,早在“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神秘的旅伴》等影片中,少数民族的边地风光、民俗风情、文化景观已有大量展现,并天然成为少数民族电影的标签之一。这一“文化志”特征在以后的创作中,尤其新世纪以来,更是被无限放大,乃至成为一种独立题材。少数民族电影区别于其他电影的标志之一,本就是展现出本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面向,这种特征的揭示和表达并不与它的艺术性、商业性相悖。而创作者和学者对民族志、文化志特征的刻意强调,似乎是为了回避民族题材电影同样需要面对市场逻辑的困扰。在21世纪遍及全球的产业化语境中,少数民族电影依然如同海市蜃楼,可以不食人间烟火,或为文化或为艺术率性生存。而它的一些创作者或学者们,亦认可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存方式,认可其作为“文化志”或“民族志”的原生态价值。令人奇怪的是,当人们面对普通电影时,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艺术的、文化的、思想的表达与商业的、娱乐的诉求可以且应当兼容,而在面对少数民族电影时,则不再持有如此理性。“文化志”观念得以盛行的原因主要是少数民族仍然被置于一种特殊的、非主流的、他者的视野中,少数民族文化被想象为静态的、孤立的、封闭的、凝固不动的、等待被发现和被表述的,它自外于现代世界和主流社会,所以它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发展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而是维持其凝固不变的文化形象。
1987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鼓楼情话》,展示了大量的侗族民俗:滚泥田、斗牛、抢花炮、卜寨、打油茶、坐妹、对歌、涂黑面、抢亲等。然而民俗奇观的荟萃并没能挽救该片零拷贝的命运。张暖忻继《青春祭》后,1993年拍摄了哈尼族题材的《云南故事》,该片扩大、张扬了对哈尼族民俗生活的展现,以致遭遇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真实感的人物和故事。因此影片的存在,主要依赖大量哈尼族民俗生活的包装”。〔15〕事实上,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奇观的表达与故事的讲述并不矛盾,应该是互为促进、内生相融的关系,但在很多创作中,由于故事、情节、人物的单薄,便大量诉诸民族原生态景观的展览来支撑叙事,替代故事和情节。《云南故事》的民俗展览之所以成了影片的累赘,正是因为它是孤立的景观,没有有效地融入到影片的叙事和表意中去,影片故事的单薄、情感的空洞和表意的老套概念化也很难有效吸纳民族民俗景观。因此,原生态文化本身并非少数民族电影“肤浅”“虚假”“盲目”的“原罪”,而是对原生态文化过度的、畸形的消费或脱离于叙事的空洞展览,才是造成少数民族电影“肤浅”的“原罪”。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电影具有天然的“悦目”性,正是因为少数民族有着与主流文化迥然不同的民族性格、民俗风情、民间习俗、生活方式、自然风光等,它们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在性结构,电影以特有的方式将它们呈现、表现出来,是必要和必然的事。
一向颇得业界和学界认同的塞夫、麦丽斯的蒙古族题材电影,也仍然有大量的民俗风情的表现——蒙古族婚礼、赛马、围栏、祭敖包、除夕夜的祭神等。民俗、仪式、风光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与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少数民族电影的叙事,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都是他们精心从蒙古民族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和心灵寄托的典礼,没有这些支撑又怎能使其民族性凸显出来?”〔16〕只要准确处理好少数民族电影的叙事与原生态景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将原生态景观的表达置于叙事的需求中,使其成为叙事的动力学机制,原生态景观就不再是肤浅的、空洞的、孤立的,而是影片血肉与共的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电影为寻求多样化发展,在对民族文化的表现上较之上世纪80、90年代,则更为激进,原生态影像的风格化与命名的真正完成其实发生在新世纪。如果说上世纪“十七年”以及80、90年代少数民族电影对民族民俗文化、异域风光的呈现主要是基于一种“唯美”“悦目”的考量,新世纪的原生态影像则真正具有了一种强烈的“文化志”“民族志”意识。
整体来看,当下我国少数民族原生态电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影片往往被定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播”,充斥着对原生态文化的大书特写和密集展示,故事、人物、冲突、表意或被挤压或被忽略。拍摄《爱在廊桥》的陈力说:“这部电影对于宣传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常重大。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整个文化元素集中,观众会不知不觉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贵,唤起抢救保护传承这些文化的意识。”〔17〕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展览始终占据着叙事的核心位置。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原生态”电影为了完成原生态意识形态的传输,故事、情节、人物和艺术手法往往建立在陈旧的文艺片观念之上,内容和形式都过于老套甚至生硬,其“弱文艺片”的平庸特质难以进入当下观众的接受视野。《云上太阳》《马奈的新娘》《我们的嗓嘎》《爱在廊桥》等大量原生态影片都存在故事、人物套路化概念化的致命问题。“文化志”电影在展览、呈现原生态文化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思考被忽略了,即如何通过电影,创造抢救、保护和传承原生态文化的更好通道?如何通过更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原生态文化,从而激发起真切的文化认同,以及抢救和传承的责任感?答案是显然的和唯一的,那就是电影的充分市场化,一部“原生态”电影只有凭借自身的独特魅力为广大观众接受、认同,才能谈得上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原生态文化只有真正落地于电影的内在属性,融会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在表象上不自满、不饱和、不喧宾夺主,才反而具有更充实、更饱满、更内在化表达的可能性,原生态电影也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性。
三、类型化探索
“十七年”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电影的放映都取得了成功,吴永刚执导的《哈森与加米拉》在乌鲁木齐公映时,各影院在公映前一天就售出两万两千多张票,影片仅47个拷贝,却在全国的放映场次高达12326场,观众达到6290819人次,超过了当时风靡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18〕《神秘的旅伴》也盈利近30万。白桦编剧、王为一导演的《山间铃响马帮来》是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惊险片,表现的是云南边境的斗争。影片在惊险气氛的营造上虽有很大欠缺,但却为惊险片的类型开创奠定了基础。在人民群众与敌对者的阶级斗争中,贯穿着苗族青年蓝劳与黛乌的爱情经历。影片渲染了美丽神秘的边疆风光,插入了对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习俗的展呈,由此奠定了少数民族惊险片、反特片的经典叙事模式。《神秘的旅伴》《冰山上的来客》《羊城暗哨》《古刹钟声》《英雄虎胆》等“十七年”反特惊险片皆延续了这一模式。较之《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在惊险气氛的营造和紧张的叙事方面做得更为成功,观赏性娱乐性更强,强化了反特片的娱乐功能和类型化特质,建构了反特惊险片的成熟样态。该片“从1956年2月至7月映出场次15263,观众人次9086513,平均每场人次595次,盈利298225元。”〔19〕“《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神秘的旅伴》的成功操作带动了1956年至1959年间的反特惊险片创作的高潮。”〔20〕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类型片,无论是惊险、反特、喜剧,还是音乐,几乎无一例外遵循下述叙事模式:敌我阶级斗争+浪漫爱情+少数民族风光+民族音乐,多元化视听娱乐元素的融会极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大众化诉求,成全“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找到了其“最终形式”。
1996年冯小宁执导的《红河谷》,是90年代少有的在类型化探索上较成功的作品。影片离奇的故事和悬念、跌宕起伏的情节、紧凑的节奏、壮美的雪域风光、强烈的情感冲突、热烈奔放的人性、激情燃烧的思想主题,尤其是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情节结构,有效地支撑起影片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使它成为少数民族电影较为罕有的高票房影片。新世纪以来,《花腰新娘》《别姬印象》《红河》《怒江魂》《这儿是香格里拉》等影片或在故事、情节、冲突,或在类型融合,或在广告营销方面下功夫,试图探索出一条少数民族电影的市场化之路。2005年傈僳族题材《怒江魂》是云南首部按照市场化商业模式进行运作的少数民族电影,故事的内容融合寻宝、复仇、爱情等商业元素,讲述了傈僳族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敌入侵的英勇故事,穿插了两个民族男女青年的爱情;在民俗奇观方面更是精心设计了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的惊险仪式;在明星效应和市场推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怒江魂》上映后票房并不理想,收入远未达到预期,令创作团队很沮丧。该片导演表示,虽然少数民族题材很吸引自己,但鉴于其票房的不理想,以后接拍这样的题材会更谨慎。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有着较强商业类型意识的少数民族电影,也往往很难取得理想的票房成绩,究其原因,《怒江魂》的失败主要还是受制于“十七年”文艺片的陈旧观念和“团结对敌+爱情”的老套故事模式,即使注入诸多类型元素,也难以挽救主叙事链所框定的乏味故事格局。
《怒江魂》市场探索的失败对少数民族电影的市场化之路所造成的阴影,是可以想象的。无独有偶,张杨2017年执导的《皮绳上的魂》,也是一部在类型叙事上有较充分准备的作品,却依然遭遇票房的滑铁卢,票房收入远不及他同期的另一部纪录片式的故事片《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恰当地以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藏地文化,融合了西部、公路、奇幻、夺宝、复仇、爱情等类型片元素。它的魔幻,不光在故事本身,更在讲故事的方法,也许正因为它时空错乱的手法,让观众分不清虚幻与现实,增加了观看的难度。这再一次证明:类型片对艺术电影手法的借鉴,对艺术性的追求,需要进行适应性改造。张杨试图在影片中表现的形式与内容都太多了,在多类型杂糅和藏地异域风光的包裹下,是一个关于善恶、救赎、复仇、重生,以及西藏从蛮荒到现代文明的多面向故事。如此大信息量的填塞说明艺术思维的惯性仍然左右着他,令他取舍困难。过多类型的杂糅本身就意味着对明晰类型的消解,增加了观看、辨别的难度,而形式的过度拼接又弱化了故事消费的快感,也许这正是《皮绳上的魂》遭遇市场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家瑞以执导少数民族电影见长,他的“云南三部曲”《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红河》都是试图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谋求良性平衡的作品。但三部影片的票房收入也并不理想,仅处于不亏本状态。如果说《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基本按照文艺片的路径来创作,《红河》则进行了类型化探索,集黑帮、枪杀、动作等商业元素于一身,“爱情+黑帮”的类型杂糅构成了影片的故事内核。《红河》是“云南三部曲”中院线放映规模最大的一部,但也仅仅收获了不到一千万的票房。票房不理想的原因主要还是类型架构不彻底,故事的主线不在类型的链条上,而在纯真情感的链条上,这条主要故事链上的“爱情”又恰恰是非常态的、内敛节制的。黑帮老大沙巴真心喜欢阿桃欲收其为义女的情节,也大大跳脱于常规类型化情节设计,因此影片看似冲突强烈、戏剧性十足,实则情节散淡、个人化风格强烈。其气氛、人物、情节、形式、风格等方面的设计很难为习惯于常规类型片的观众接受。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在类型探索上最集中的片种还是歌舞片,这得益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内生性文化传统,歌舞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最特别的艺术瑰宝,也是最直接可见的文化资源。《寻找刘三姐》《吐鲁番情歌》《大东巴家的女儿》《鲜花》等,在歌舞片类型上进行了某种探索,歌舞作为类型策略贯穿于整个叙事链。此外,还有较为少量的其它类型,如体育片《阿米走步》,以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背景,讲述法籍教练与本土自行车手从冲突到对话、和解的故事,表现了中外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以及团结、宽容、奋进的励志主题;《风雪狼道》则是一部主旋律灾难片,以百年罕见的暴风雪为背景,讲述了解放军指战员救援灾区的故事。相较于当下主流电影轰轰烈烈的类型发展态势,少数民族电影不仅离真正的全面的类型建设相距遥远,即便是类型化探索也仅仅处于尝试阶段,其数量、质量都令人堪忧。
这些类型化探索的影片存在的巨大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是创意贫乏,故事、人物老套,叙事中规中矩,表意肤浅平庸,故事设计上往往不约而同借助外来视角,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猎奇式展览。如《寻找刘三姐》《大东巴家的女儿》《阿米走步》《云上太阳》等,借中外文化、理念的碰撞和冲突表达对民族文化的赞美或宽容、奋进的励志主题;或如《吐鲁番情歌》《美丽家园》等通过主人公的情感纠葛,表达父辈与子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或如《鲜花》《风雪狼道》等,表达对真善美的弘扬。显然,无论是关乎文化的表面冲突,还是励志主题,都是颇为陈旧甚至肤浅的,难以引人共鸣,此为这一类类型化探索电影的致命伤。其次,类型叙事的主轴没有建立起来,类型轴线成为枝蔓,类型元素匮乏,受“弱文艺片”平庸理念的制约,四平八稳,没有真正完成类型叙事。再次,这一类影片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理解过于肤浅和表面化,仍然停留在猎奇展览的层面,由于文化内涵缺乏,导致故事和人物空洞浅薄。整体而言该类影片体现出与原生态影片、“弱文艺片”一样的症候,也是少数民族电影的通病:轻人物、轻故事、戏剧性不强、冲突软弱,叙事、主题策略上体现出较为严重的趋同特征,如对文化冲突、代际冲突、英雄塑造、励志的普遍性表达,在故事和主题上没有创造出明显的差异性格局。这导致少数民族电影成了一个给人以“刻板印象”的封闭系统,缺乏鲜活的生命力。
显然,少数民族电影再也回不到与市场无关,以边缘、另类、无功利性自居的时代,而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化之路。其在类型化探索的过程中势必应当有效避免“故事综合症”困境,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开创鲜活生动、富于真切生命体验的故事。同时,由于其创作观念的历史痼疾,它的市场化探索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勇气、意志。虽然《怒江魂》《吐鲁番情歌》《花腰新娘》《红河》《皮绳上的魂》等有一定市场意识的少数民族电影,在市场探索上遭遇了或彻底失败或不尽如人意的命运,但无论如何,市场化探索都势在必行。只有一次又一次迈出市场化的步伐,少数民族电影才会逐步克服、化解内生性的、结构性的、习得性的问题和痼疾,走上市场化的大道坦途,真正实现从“小众”到“大众”,从“原生态”到“讲故事”,从“边缘”到“主流”的转变,也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有效建构与传播,成为能够代表国家、民族形象的中国电影家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注释:
〔1〕〔法〕弗郎索瓦、特吕弗:《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郑克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2〕贾磊磊:《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与价值体系》,《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第21-25页。
〔3〕赵实:《中国特色电影发展道路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78-381页。
〔4〕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5〕〔10〕饶曙光:《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变化及其评价维度》,《电影艺术》2013年第2期,第52-57页。
〔6〕张国凡:《别具一格地表现侗民族风情——看电影〈鼓楼情话〉随笔》,《民族艺术》1988年第2期,第34-37页。
〔7〕王婧姝:《民族电影应注重内在文化精髓——与白庚胜谈〈大东巴的女儿〉》,中国民族宗教网,2009年3月3日。
〔8〕李博:《民族电影凝聚民族精神》,《中国艺术报》2011年5月4日。
〔9〕〔12〕刘大先:《一部丰富的情感文献——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怀旧与思索》,《中国民族》2012年第2、3期合刊,第57-63页。
〔11〕郑莹莹:《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大有可为》,《文艺报》2010年6月2日。
〔13〕黄式宪:《以自身“民族母语”拍摄电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人文原生态与现代性的交融》,《文汇报》2012年12月22日。
〔14〕俞灵:《民族题材电影:支撑中国电影的文化精神》,《中国民族报》2010年7月23日。
〔15〕王迪:《民俗:电影叙事话题——兼论影片〈青春祭〉、〈云南故事〉》,《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16〕韦朋:《从“他者观望”到民族意识的复苏——蒙古族题材电影的流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14页。
〔17〕朱雅秀:《电影〈爱在廊桥〉专访》,宁德网,2011年6月23日。
〔18〕袁文姝:《坚持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驳文艺报评论员的“电影的锣鼓”及其他》,《中国电影》1957年第1期,第20-25页。
〔19〕《面对事实 克服缺点——有关讨论国产影片问题的几份资料》,《中国电影》1956年第3期,第3-5页。
〔20〕陈山:《红色的果实——“十七年”电影中的类型化倾向》,《电影艺术》2003年第5期,第2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