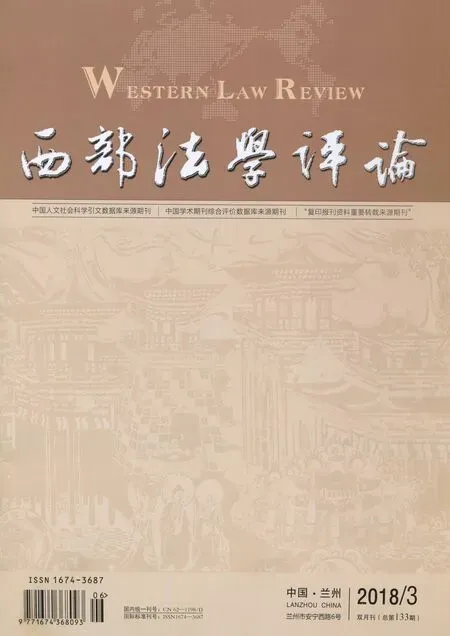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
——一个经验性守法研究的新路径
吴云梅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法治建设,特别是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监管基本涵盖了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为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立法只是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仅仅给出法律规范,说明哪些行为不允许、哪些行为允许并不能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真的按照规范的良性运行,而是需要法律规范监管的对象实实在在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事,也就是监管对象能够遵守法律规范才是法治建设成功的保障。然而,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存在很大的守法危机。在很多法律领域都出现很多违法事件和违法现象。简单列举几个,如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震惊全国的开胸验肺事件暴露出的职业健康问题、天津港爆炸所暴露出的虚假环评问题、屡禁不止的假发票问题、“中国式过马路”集体闯红灯问题等等。频繁出现的违法问题不仅会扰乱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容易动摇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信心,是我国在建设法治国家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面对中国的守法危机,我国很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也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思考和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要。而且已有守法研究中暴露出抽象讨论的文章过多,而经验性实证性研究过少;已有为数不多的经验性研究缺乏对所使用和可使用的守法研究路径的系统思考,因而不利于彼此进行对话和交流等。本文旨在针对这些问题对中国和国外现有的守法研究进行梳理,特别是总结和分析国外三种守法研究路径的关注点、优势和局限性,并在分析这三种守法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适用于现阶段中国守法研究的新路径——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该路径兼顾国外三种守法研究路径的研究兴趣,又规避了部分局限性,实现了对三种研究路径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采用该路径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我们积累对中国守法实践的认识,同国内丰富的守法讨论相互支持和相互验证,又可以让我国的守法研究有效地与国外守法研究进行对话和交流。
一、中国的守法研究
中国面临巨大的守法危机,但是系统的守法研究成果很少。虽然中央提出守法是进行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很多法学,包括社科法学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立法问题、执法问题和司法问题上。一个原因可能是源自于对守法研究重要性认识的误读。如李娜指出,守法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一种法律适用的结果,好比一个自动售货机,只要国家投入了法律,就能期待产出的是守法行为和结果”。*李娜:《守法作为一种个体性的选择——基于对建筑工人安全守法行为的实证研究》,载《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忽视了“纸面上的的规则”和“实际的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和动态的转化、冲突和协调的过程。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视角都容易把守法的主体(个人或组织)看成是被监管对象,将其放在了“客体化”的位置上,而忽略了他们在守法实践中的主观建构作用及其作为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前引[1]。因此,人们很容易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去讨论守法问题而忽视一个核心问题:要实现守法,守法行动的主体必须做出某些行为或者改变某些行为,所以,进行具体行动的行为主体的观念和行动是关键。第三个原因可能是守法研究本身的要求超出了传统法学的研究,需要与来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进行合作。但是中国社科法学的研究刚起步不久,其研究力量和研究的领域还很有限。采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是中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可能最早是由苏力教授在2001年提出来的,*侯猛:《社科法学的传统与挑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但在近几年才开始得到重视和发展。并且大部分社科法学的研究都关注与法律机构有关的主题,如法庭和律师,而对法庭之外法律如何塑造着守法主体的行为的关注相对较少。
幸运的是,中国学者对守法问题的研究在近十年来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讨论守法。不过很多此类的守法讨论和研究缺乏一个恰当的经验性研究焦点,研究实际发生的行为,而往往陷入一种脱离经验性研究的空泛论证和思辨的境地。比如很多学者的文章主要是指出守法的重要性,*刘杨:《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曹刚、吴晓蓉:《守法的必然和应然:一个道德心理学的视角》,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守法的伦理,*刘同君:《守法伦理的理论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守法和其他概念的联系,如信任、形式正义、道德、个人福祉等,*冯粤、缪斌:《德福相同的守法之路》,载《新远见》2008年第7期;向仕明:《论守法的道德基础》,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3期。*王晓烁:《论法的形式正义与守法》,载《河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卫守宇:《论道德建设与守法意识的形成》,载《邢台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向仕明:《论守法的道德基础》,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3期。或者指出一些促进守法的一般性激励措施。*丁启明、赵静:《论企业环境守法激励机制的建构》,载《学术交流》2011年第3期;占茂华:《法理学视角下的守法概念解读》,载《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一些学者主要对西方的守法理论进行引进和介绍;*丁以升、李清春:《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上)——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论的理由》,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丁以升、李清春:《公民为什么遵守法律?(下)——评析西方学者关于公民守法理论的理由》,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1期。还有不少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集中关注守法当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王峰:《守法的经济分析》,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吴亚辉:《论守法的逻辑:基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游劝荣:《守法成本及其控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陈和芳:《守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以甲企业对劳资关系的处理为例》,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这是西方守法理论中认为对守法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例如,吴亚辉认为守法行为的内在逻辑是法律的守法成本和收益比较。他把社会成员分为两类,*同前引〔16〕。一类是对法律漠不关心的一般人,一类是乐意接受法律的好人。对于第一类一般人来说,他们的行为逻辑是当守法成本小于违法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守法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考虑守法。对于第二类好人来说,他们本身愿意支付一定的成本来遵守法律,因此其中又有一个预期支付因素影响他们的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说当他们因遵守法律所支付的成本与违反法律所支付的成本之差超过自己的预期支付时,好人才会考虑选择违法。王峰认为效益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也是守法的一个价值、价值取向、标准和根据。守法效益是多层次的,如总效益、平均效益、边际效益、个人守法效益、群体守法效益和社会整体效益、守法的实际效益、可能效益和潜在效益、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等等,不仅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伦理效益等。守法首先是理性化的,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实现,能够带来效益,人们就会选择遵守法律或者规避法律,甚至违反法律。因此他认为要促进人们遵守法律,那么法律应该有益于人们权利的维护、保障和实现。*同前引〔15〕。游劝荣强调守法成本对守法行为选择的影响,提出要通过制度设计,比如提高生活水平、制度设计符合社会正义、建立对守法者的救济机制和奖励制度,以此来降低守法的成本,从而促进守法。*同前引〔17〕。
除了关注守法的成本收益之外,一些学者也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守法。比如,姚俊廷指出除了理性选择外,感性选择也是选择守法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姚俊廷:《感性选择视阈中的守法可能性及其限度》,载《唯实》2009年第7期。守法中的感性选择是一种基于法律或关于法律知识基础上的情感、态度、偏好或反应性行为。他认为任何基于理性的知识都是由具体的人感性地认知和接受的,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体验比知识更能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因此,他认为要促进守法,法律必须要注意公民法律情感的养成,提升法律自身的亲和力和公信力。
国内有关守法的经验性研究远远落后于以上的理论性研究。国内早期进行守法的经验性研究的是来自医学领域的学者。他们调查了医务人员对有关临床操作规定的遵守情况以及影响医务人员遵守规定的因素。*尚少梅、王宜芝、郑修霞、孙玉梅、黄靖雄、何愿如:《促进护理人员洗手行为依从性的研究》,载《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3年第6期。*Luo,Yang et al.,2010,“Factors Impacting Compliance with Standard Precautions in Nursing,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 14.然而,这些经验性研究并没有和守法理论相连接,对守法理论的贡献也微乎其微。陆益龙可能是最早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守法进行经验性研究的学者。他用问卷调查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守法倾向,比如支付电费和农业税,使用假币或者假证书。他的研究从守法的两个理论范式出发,即工具主义范式和规范内化范式,分析了影响农民守法行为的因素。他的研究发现两种范式共同作用于人们的行为选择,但是仅仅从法律工具性因素和行动者主观意识因素来解释农民的法律行为是不够的。影响农民守法行为倾向的因素嵌入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相对独立的法制系统。*陆益龙:《影响农民守法行为的因素分析——对两种范式的实证检验》,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010年以来,国内有关守法的经验性研究逐渐增多。王晓烁和刘庆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守法行为倾向。*王晓烁、刘庆顺:《守法行为的心理因素分析》,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他们发现在行动者知道某种法律规则的前提下,法律行为的正向体验程度、守法知识的可得性感知程度、守法体验的印象深刻程度以及违法行为惩罚的确定性程度与守法倾向性呈正相关关系。陈和芳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某企业出现的几个法律纠纷案例中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企业做出违法行为选择的根本原因是其自身对成本收益的考量,而法律只是影响其成本收益的一个变量。*陈和芳:《守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以甲企业对劳资关系的处理为例》,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她认为对企业守法行为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立法瑕疵、执法投入有限、新法律的适应过程以及法律主体之间力量的不均衡。余伟铿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了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香港制造企业对中国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他们发现企业守法的最基本原因是为了避免执法人员对企业提出无理要求。被监管企业越容易理解实际执行的法规,它们就越可能采取守法行为。他们认为在中国还不健全的法治环境下的守法机制与拥有健全法制的西方国家的相关机制不同。*余伟铿、邓穗欣、卢永鸿:《脆弱法治下的守法行为:来自中国环境改革的经验》,秦寅霄译,载《中国治理评论》2014年第2期。李娜通过观察和访谈调查了建筑工人的施工安全守法行为。她尝试从三个分析视角,即法律规范、社会规范和个人规范,对建筑工人守法行为进行解释。她发现法律规范对建筑工人的威慑作用很有限,威慑并不是其守法的必要条件,即使没有法律规范的威慑存在,守法者依然能够遵守法律。建筑工人对社会规范的认知,即建筑工地其他人的行为模式,也并非影响其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而个人规范,即对自身安全的关注、职业习惯、惯常实践、对危险的认知等是解释建筑工人安全行为实践的主要因素。因此,她认为无论守法者还是违法者的行动逻辑主要受个体规范的影响,法律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很弱。*同前引〔2〕。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对守法的研究不断增多,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了守法研究的重要性;然而,现有的研究还很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类型来看,经验性研究远远少于思辨性的讨论,思辨性的讨论缺乏经验性研究的支持而容易流于空洞。其次,从研究路径来看,现有的经验性研究几乎都是外源性研究而没有内源性的研究,即并不讨论相关利益群体对守法概念的解读和守法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建构,而是在研究之初对守法进行或明确或模糊的界定,然后根据各自的界定来寻找影响这个“守法”变量的因素。但是内源性研究,即对守法概念的解读和分析,为外源性的守法研究提供核心的概念支持,是守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从外源性路径研究中守法概念的操作化来看,不同学者研究的“守法”缺乏统一的基础,他们研究的“守法”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比如陆益龙、王晓烁和刘庆顺研究的“守法”实际上是“守法的行为倾向”,而李娜、陈和芳、余伟铿等人研究的是“守法的具体行为”。在“守法的具体行为”中,有的采用的是直接观察法,有的则采用的是自我报告式的问卷调查法。不同的数据采集方法中实际的守法行为概念又存在差异。最后,从现有研究与国外已有守法研究的对话上来看,国内的守法研究还很缺乏与国外相关研究的交流和对话。国外的守法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无论从参与的学科,还是从涉及的法律领域以及研究的路径来看,国外在守法方面的研究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是国内对这些研究成果的了解还比较局限。如不少研究者主要局限于几个经典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如工具主义范式、规范内化范式、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威慑理论等,而对后来国外守法研究关注的主观威慑力、动机姿态、描述性社会规范、守法能力、一般性守法责任意识、执法风格、过程研究等缺乏了解。部分研究和国外的守法研究不在同一个讨论体系中,既难以向国际守法研究呈现中国的智慧,又难以与国外守法研究交流,吸取有益的养分促进自我的发展。
二、国外守法研究的路径和局限性
与国内有限的经验性研究相比,国外对守法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两个研究路径,即内源性路径和外源性路径。*Parker,C. and V. Nielsen. 2009. "The Challenge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Business Compliance in Regulatory Capitalism."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5:45—70.内源性路径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守法概念本身,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监管实践中的守法的含义,即守法是什么,它是如何被阐释和建构出来的。一方面,内源性研究旨在发现在监管领域中各利益相关群体对守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和解读;另一方面,内源性研究还意图发现造成这种认识和解读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各利益相关群体背后的权力关系。简言之,让内源性研究者感兴趣的不是人们是否遵守或者违背法律规定,以及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而是监管者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有关法律的知识,以及他们如何界定什么是守法。
相反,外源性研究关注是什么导致人们遵守法律,人们遵守法律的原因和效果,试图理解是什么因素影响着人们做出守法的决定和行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外源性研究者必须事先界定守法的概念。外源性研究具有实用性倾向,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可以促进守法的影响因素,如执法、组织特点、社会规范或文化。换句话说,外源性研究者关注如何促进法律的实施而不是反思法律是什么。
(一)内源性守法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守法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容易理解的概念。当提到守法的时候,人们似乎都知道是遵守法律法规或某些规定。字典里有关守法概念的解释也比较简单。在牛津英文字典中,守法被定义为“遵守或满足规则或标准的状态或事实”。在汉语成语词典里,守法被解释为遵守法律法规,办事守规矩。然而当“守法”成为一个研究概念或者研究对象的时候,其概念当中的复杂性、变化性和动态性就呈现出来了。
首先,守法是相对于一定的法律法规而言。要界定什么是守法,必须先明确守法的对象,即相应的法律法规。理想状态下,这个法律法规必须非常清楚明确,可以与守法行为进行一一对应。然而,很多研究者却指出,法律法规永远不可能足够具体和清楚到可以根据条文就来判断一个行为是守法还是不守法,而必须根据真实的情景进行具体的解释。警察和其他监管者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守法或者违法时总是拥有一定的自由量裁权。Huising和Silbey在研究美国东部大学基层安全监管员的监管实践时发现,根据城市建筑管理规定,“建筑物的所有出口和主要走廊必须保障畅通”, “如果监管员认为出口或走廊里的物品会阻碍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或者消防人员的通行,那么监管员可以要求清除这些物品”,而美国东部大学基层安全监管员在实践中需要具体解释和明确“什么是畅通的走廊”。*Huising,Ruthanne and Susan S. Silbey. 2011. “Governing the Gap:Forging Safe Science Through Relational Regulation”,Regulation & Governance,5:14—42.被监管的建筑物内的各实验室人员不断向安全监管员索取具体可衡量的标准,而安全监管员也必须根据每一栋楼甚至每一层楼的情况来确定具体衡量的指标。我国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三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其中,什么是“相适应”和“合理的”都需要根据真实的情景进行具体的解释。
其次,守法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在实践中会具体沟通和协商到底什么行为可以被接纳为守法或不守法。例如Lange对垃圾处理厂的研究发现,监管人员如果发现虽然某个垃圾处理厂具有合法的资质证书,也在其证书许可的处理能力范围内运转,但是其实际运作时显然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了明显的压力,那么监管人员就会与垃圾处理厂负责人进行沟通,要求其进行整改。*Lange,B.1999. "Compliance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ocial & Legal Studies 8(4):549—567.反之,如果某个垃圾处理厂实际上超出了其资质证书所允许的处理负荷,但是并没有给周围的环境造成压力,那么监管人员也会和垃圾处理厂负责人进行沟通协商,不判定其违法,但要求其更换新的资质证书。Talesh对消费者保护法的研究揭示了汽车制造商会在监管之下发展出自己的消费者纠纷处理方式,并最终让监管者认可和接受他们的方法,修改了相应的法律条款,从而改变了汽车制造商是否守法的界定方式。*Talesh,Shauhin. 2009.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Legal Rights:How Manufacturers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Consumer Law”,Law & Society Review,43:527—562.除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外,第三方群体,诸如对监管内容有利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普通群众等也可能参与到守法的建构中。因此,“什么是守法”是各社会群体在互动中建构出来的,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第三,守法是一个抽象概念,不同行动者对这个概念存在不一样的理解。监管者很可能以一次检查的结果来判定监管对象是否守法,而被监管对象则可能以另外的标准来理解守法。如Fairman 和Yapp的研究发现,小型食品企业认为在下一次检查到来之前,只要他们做到了监管者上一次来检查时所要求的内容,他们就是守法了,而不管期间他们是否违背了其他的法律规范。*Fairman,R. and C. Yapp. 2004."Compliance with Food Safety Legislation in Small and Micro—Businesses:Enforcement as an External Motivator",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3:44—52.
因此,从内源性研究路径看来,“什么是守法”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内容。它可以通过研究“守法”如何建构、不同群体对“守法”有着怎样不同的理解以及“守法”具体有怎样不同的含义,来理解有关法律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即“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更好的监管和更好的社会”。*同前引〔30〕。例如,Lange就提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保持相对透明的信息交流将会是实现更好监管的一个途径。
然而,内源性研究路径有一个较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很难回答一个实用性问题,即“如何促进人们守法”,而这个问题是很多关注守法研究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同前引〔30〕。对于内源性研究者来说,守法的定义根本是不确定的,每一个对守法的界定都是针对具体情境和具体对象的主观建构,而当评估守法与否的标准是变动的、不确定的时候,研究者也无法对一个具体的行为进行守法与否的测量和评估,无法比较不同的守法行为,也就不可能去进一步研究类似“如何促进人们的守法行为”的问题。
(二)外源性研究路径及其操作化问题
与内源性研究路径不同,外源性研究者并不追问“什么是守法”,而是在研究开始就设定好一个确定的守法定义,在这个守法定义的基础上来研究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守法,以及如何促进守法等问题。
以Winter 和May的研究为例,他们想分析影响丹麦农民守法的动机,“守法”作为研究的因变量被界定为农民的生产行为对四个农业环境指令性法规(有具体的技术性数字标准)的满足程度。*Winter,Soren C. and Peter J. May.2001. "Motivation for Compliance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0 (4):675—698.他们根据农民自我报告的四个具体行为,如储存肥料/粪肥的空间大小,喷洒肥料/粪肥的时间、硝酸盐的使用量以及牲口的数量来对照指令性法规中的技术性数字标准,然后以三分法的方式来判定农民守法的程度,包括没有守法、基本守法、完全的守法。在根据事先确定的守法概念对丹麦农民的行为进行测量的同时,他们利用问卷得到的信息测量了几个守法的动机,如计算性动机、规范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守法能力。通过分析这几个动机与守法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计算性动机、规范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守法能力与守法均呈现显著的关联性,但是几个因素合起来对守法的解释度却不足10%。
然而,外源性研究路径仍然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挑战,那就是对守法概念的操作化和数据收集。对守法概念的操作化是指明确哪些数据是研究者所界定的守法概念的过程。在守法研究中,守法通常被操作化为守法倾向、守法态度、政策目标的实现等,仅有很少一部分研究者会把守法概念操作化为具体的守法行为,如李娜、*Li,Na. 2016. “Compliance as process:Work safety i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PhD thesis,Faculty of Law,Amsterdam University. http://dare.uva.nl/document/2/176952Gray、*Gray,Garry C. 2006. “The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Violations:Punishment,Compliance and the Blurring of Responsibility”,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46(5):875—892.Burby & Paterson*Burby,R.J.,and R.G. Paterson. 1993. "Improving Compliance with St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2,no. 4 (1993):753—72.的研究。
Valerie Braithwaite及其合作者研究监管对象的四种*Braithwaite,Valerie,John Braithwaite,Diane Gibson,and Toni Makkai. 1994. "Regulatory styles motivational postures and nursing home compliance",Law & Policy 16(4):363—394.(后来增加到五种*Braithwaite,Valerie. 2003. "Dancing with Tax Authorities:Motivational Postures and Non—Compliant Actions",in Valerie Braithwaite (ed.) Taxing Democracy,Ashgate:15—40.)守法的动机姿态,实际上就是把守法概念操作化为监管对象的守法态度。前面介绍的中国学者陆益龙、王晓烁和刘庆顺研究的“守法”实际上也是“守法的行为倾向”。守法态度和倾向本身有自己的研究价值,但是Parker和Nielson提醒守法研究者必须清楚认识到守法态度和倾向并不必然带来守法行为。*同前引〔30〕。把守法操作化为政策目标的实现,即测量监管对象是否满足了具体的监管目标,如环境排放是否达标、*Andrews,R. 2003.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Do they improve performance? Project Final Rep.,National Database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Univ. N. C.,Chapel Hill. http://ndems. cas.unc.edu. cited from Parker,C. and V. Nielsen. 2009. "The Challenge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Business Compliance in Regulatory Capitalism."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5:45—70.雇用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比例、*Braithwaite,Valerie.1993.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ffirmative action legislation:achieving social change through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aw Policy 15:327—54.较少的工人受伤和死亡率*Mendeloff,John and Wayne B. Gray. 2005. “Inside the black box:How do OSHA inspections lead to reductions in workplace industries?”,Law Policy 27:219—237.也是很多研究者采取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可以来评估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但是研究者应该清楚这个方法实际测量的是监管对象对具体法规目标的遵守,而非对法规本身在行为上的遵守。
Parker和Nielson认为,守法研究者的最终目标是要评估人们是否遵守法律规范,以及他们的这种遵守行为是否带来法律规范所预期的具体目标。*同前引〔30〕。所以他们认为把守法操作化为守法行为非常重要,但也非常不容易做到。首先,研究者将直接参与对行为的评估,如前面内源性研究路径所揭示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守法有着不同的界定,那么研究者是应该选择哪个群体的视角呢?有关这一点,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应该选择立法者的视角,*Winter S,Elmore RF,and Abelmann C. 1994. “Youth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SA and Denmark:political culture,policies,and implementation”. Presented at Annu. Res. Conf. Assoc. Public Policy Manag.,Chicago,Oct.有的则认为研究者作为局外人的视角也同样重要。*Guba E,Lincoln Y. 1981. Effective Evaluation:Improv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Responsive and Naturalistic Approaches,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选择哪个视角与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和信念有关,不过无论选择哪一个视角,研究者都必须在他们的研究中清楚明确地阐述他们的视角和评估标准。其次,研究者还需要解决如何获取数据的难题。理想状态下,把守法操作化为守法行为,研究者需要直接去观察监管对象的行为,然后评估这些行为是守法还是不守法。但这一方面需要注意研究者的观察行为对监管对象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的观察将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时候是不现实的,所以很少有研究采用这种直接的观察法。再次,即使研究者可以采用直接观察法观察监管对象的行为,他们也还面临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需要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识别哪些是守法行为,哪些是违法行为。
(三)过程性研究路径及其局限性
除了主流的内源性和外源性研究路径外,国外的守法研究中还存在第三种研究路径,那就是过程性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的使用还不是很多,但是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可以整合内源性和外源性研究路径的一条中间路径。*Van Rooij,Benjamin. 2013. “Compliance as Process:A Micro Approach to Regulatory Implementation.” on file with the author.过程性研究路径与前两种研究路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上或者用一个静态的评估标准来研究守法,而是认为守法是历经了一系列的步骤或者过程而产生的。过程性研究路径就是要研究产生守法的这些步骤和过程。如Henson和Heasman提出守法过程包括几个步骤:识别规则、解释规则、识别变化、做出守法决策、指出守法的具体方式、交流、执行、评估/监控。*Henson,S. and M. Heasman.1998. "Food Safety Regulation and the Firm:Understanding the Compliance Process",Food Policy 23(1): 9—23.Chemnitz认为守法的过程包括几个阶段:知识阶段、态度阶段、决策阶段、执行阶段和监控阶段。*Chemnitz,C. 2011. "The Compliance Process of Food Quality Standards on Primary Producer Level:A Case Study of the EUREPGAP Standard in the Moroccan Tomato Sector",Food Policy January 06.Van Rooij认为守法是一系列非线性的可循环过程,具体包括学习过程、协商过程、传播和翻译过程、操作过程、验证和激励过程、机制化和内化的过程。*同前引〔50〕。
过程性研究路径规避了外源性研究路径中有关评估和测量守法行为的风险,因为它把守法的评估和测量分散到了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中,而不是依赖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此外,这样的评估和测量与守法的产生环境和过程联系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守法的建构过程,融合了内源性研究路径的视角。然而现有的过程性研究路径也有很大的局限,其研究的逻辑是试图描绘一个从外部的法律规范如何导致监管对象的守法行为甚至内化为内部规范的单向式图景,也就是法律规范→守法行为→内部规范。这个逻辑很好理解,但是对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在实际生活当中,守法行为的产生不一定遵循这个逻辑,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法律规范,但是受内在规范的驱动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了守法行为。法律规范不一定是所有守法行为产生的起点,生活中还可能存在很多其他的可以触发守法行为产生的因素。因此,现有的过程性研究路径不能真实地反映守法产生的过程,容易错失影响守法行为产生的因素。
此外,现有的过程性研究路径大多设定监管对象为个人,所采用的也是和个人决策有关的模型,但是实际生活中,监管对象除了个人还有组织。组织的守法既包括组织层面的守法行为,也需要最终落实到个人的守法行为。除了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如组织特点、组织文化、组织规范等,这会对组织和个人的守法产生影响,而现有的过程性研究路径不能处理这种嵌套式的守法。
三、新的研究路径尝试: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
如前所述,中国现在面临巨大的守法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立法只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法律制定出来之后对法律的遵守。反观我国现在普遍存在的各种违法现象,笔者认为为什么人们不遵守法律,以及怎样促进人民遵守法律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除了理论思辨之外,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经验性研究,探索中国正在发生的守法实践,影响人们守法的因素,找到促进人们遵守法律的的途径。基于这个原因,本文认为我国的守法研究首先有一个实用主义的倾向,希望解答“什么因素促进或阻碍着人们普遍的守法”,“如何促进人们遵守法律”等实用性问题。此外,中国的法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还在不断的探索完善当中,因为传统文化和长期形成的“人治”模式的缘故,人们对法治和守法等概念可能还未形成基本的共识,我们对人们守法的理解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不注意去理解人们对守法的认识,对守法概念的建构,而只用事先设定的守法概念去研究影响人们守法的因素,很有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错失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根本走错方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深入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参见王启梁教授的文章“进入隐秘与获得整体:法律人类学的认识论”(《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他认为法律研究者需要重视在具体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实践,需要对法律实践有一种嵌入到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整体性的考察,这样才可能洞悉法律实践的隐秘和法律的暗面,缩小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鸿沟。,去理解守法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去分析守法概念是如何被人们建构、使用的。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守法研究既要注意研究和理解守法概念(内源性),又要解答什么因素影响以及如何促进守法等问题(外源性)。想要实现这样的研究目的,内源性和外源性研究路径在回答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均存在重大的局限,而第三个过程性研究路径也面临同样重要的问题。
在总结分析这三个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下面笔者将提出一个新的适用于中国守法研究的研究路径,即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它从三个研究路径中提取了部分要素,既兼顾内源性研究需求,也兼顾外源性研究需求,还承接了过程性研究路径的过程性视角。
首先,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路径把守法概念操作化为守法行为,并且把守法行为定义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对法律规范的行为回应。监管对象的行为是该路径下守法研究的起点,即研究者要能够清楚地描述出与相关法律有关的监管对象的具体行为。例如,如果研究餐馆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者可以选取食品安全法中的几个具体条款(如有关餐具消毒的条款),识别出这几个具体条款所对应的餐馆行为(如消毒设备和方法、消毒行为、消毒记录、消毒结果等),然后具体的描述这几个行为,识别这些守法行为的特性,把握不同守法行为的区别。已有的守法研究已经发现,生活中的守法行为远远不能用守法/不守法这样的两分法进行概括,而是存在多样化的守法类别,比如象征性守法、*Edelman,Lauren B.,Stephen Petterson,Elizabeth Chambliss and Howard S. Erlanger. 1991. “Legal Ambiguity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liance:Affirmative Action Officers’ Dillemma”,Law & Policy,Vol. 13,No.1:73—97.协商性守法、*Langbein,L.,and C.M. Kerwin. 1985. "Implementation,Negotiation and Compliance in Environmental and Safety Legislation",Journal of Politics 47(3):854—880.自愿性守法、*Scholz,John T. 1984. "Voluntary Compliance and Regulatory Enforcement",Law & Policy 6(4):385—404.超越性守法、*Prakash,Aseem,2001. “Why do Firms Adopt ‘Beyond-Compliance’ Environmental Policies”,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10:286—299.创造性守法、*McBarnet,Doreen,and Christopher Whelan. 1991. "The Elusive Spirit of the Law:Form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Legal Control",Modern Law Review 54:848—873.虚假性守法*Noutcheva,Gergana. 2009. “Fake,Partial and Imposed Compliance:the Limits of the EU's Normative Power in the Western Balkans”,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6(7):1065—1084,DOI:10.1080/13501760903236872.等等。
其次,在描述具体守法行为的时候,该路径强调研究者要遵循过程性视角,不能只描述某一个时间点上监管对象的行为是什么,而是要追溯监管对象的这些行为是如何产生的,要加入时间的维度去看监管对象的行为起因、发生、发展和变化。这里的过程性视角是以行为为中心,把行为看作一个事件,试图描述这个“事件”如何开始、发展、变化等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研究者把监管对象的守法/不守法的行为纳入到其发生的情景中,联系情景来讨论守法行为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特有的或尚未被发现的守法影响因素,而不是局限于已有的影响因素理论。由于是以行为为中心,这种过程性视角可以涵盖行为发生的不同情景和层面,因此可以分析触发守法行为发生的不同场景及其中的场景因素。比如不少研究,特别是内源性研究路径的研究认为守法是通过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互动、协商而建构出来的。即守法行为可能是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过程性视角可以对监管者与被监管的互动进行描述,分析影响的因素。此外,组织里的个人在没有直接接触监管者的前提下,也会因组织因素的影响而采取守法行为,过程性视角就同样可以对这种守法行为发生的组织情景进行描述,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采用行为主体的视角是被监管者的视角。在现有的大部分守法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容易采用监管者的视角,询问“为什么监管对象会守法”以及“如何让监管对象守法”,却忽略了被监管者作为守法的行为主体所具有的主体视角,即守法行为是“我”日常行为中的一部分,哪些因素影响着“我”采取守法行为。守法行为的发生与被监管者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被监管者的视角来描述守法行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有助于发现与守法行为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守法行为。例如Garry Gray从一线生产工人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工人的安全行为,发现法律上为了保护工人而赋予工人拒绝危险工作的权利(反过来说,工人被迫通过行使自己拒绝危险工作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但是在实践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工人通常都不会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拒绝危险的工作。*同前引〔39〕。在一项有关餐馆从业人员的守法研究中,*Wu,Yunmei.2017. Compliance Pluralism and Processes:Understanding Compliance Behavior in Restaurants in China,PhD Thesis,Faculty of Law,Amsterdam University.研究人员采取餐馆从业人员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他们的守法行为,发现有的从业人员虽然知道办理健康证是从事餐饮行业的基本要求,自己对办理健康证的必要性和益处也持积极的看法,到某些大型或高档餐馆求职的时候也愿意主动办理健康证,但是在某些小型餐馆工作时却不愿意主动办理健康证,其原因就是他们觉得所在小餐馆的老板并不重视健康证,而且认为办理健康证是餐馆老板的责任,不是自己的责任,认为只要老板要求就去办,不要求就不办。虽然食品安全法要求所有从事食品生产的人员都必须取得健康证,但是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并不会受到处罚,而是餐馆老板受到处罚,所以部分餐馆从业人员并不认为获取健康证是自己的责任,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这条法律的规范对象。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那么任何试图分析影响这些从业人员的守法因素的尝试将注定会有所偏颇或不得要领。而这正是通过采取被监管对象的主体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守法行为与其日常生活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守法行为的主观看法而发现的。
与相对成熟的国外守法研究相比,中国有关守法的经验性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应对目前的守法危机,我们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在现阶段,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路径有几大益处。通过描述具体的守法实践行为,我们可以积累对中国守法实践的认识,描绘出中国守法实践的真实情景。从而一方面可以让中国的守法研究者在与国外守法研究者对话或者分析国外守法理论的时候更好地明晰不同理论所根植的社会情境和守法实践,另一方面也可以和国内丰富的守法理论讨论互相支持,互相验证。此外,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是在现有国外守法研究路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对现有三种研究路径的一种整合,兼顾了三种研究路径的兴趣和视角,部分处理了相应的局限性。因此使用该路径的研究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守法研究的前沿实现与现有国外守法研究的对话,促进中国守法研究与国外守法研究的对接和相互促进。
当然,描述性守法行为分析路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该路径把守法概念操作化为具体的守法行为,为了获取具体守法行为的资料,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观察监管对象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进行规模化的定量研究。其次,采用该路径研究时,研究者会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是否能与监管对象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以便近距离接触监管对象,获取真实的数据资料。如果不能建立起充分的信任关系,研究者或者难以接触到监管对象,或者即使接触到也不能获得真实的数据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