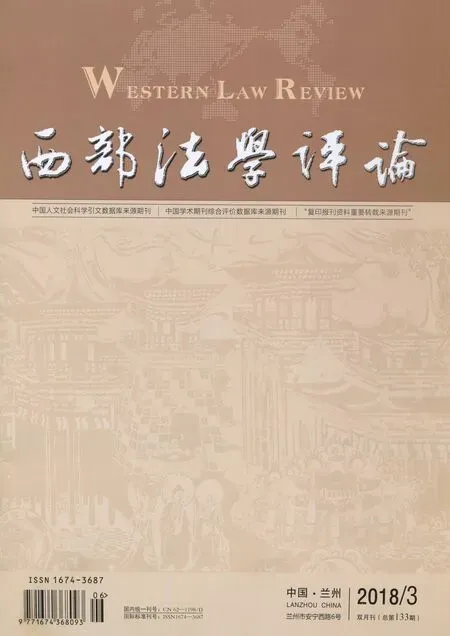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融合
——以提升司法的正当性为目标
张 华
一、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缺陷
法律修辞通过说服听众来提升司法正当性,指导性案例则通过同案同判来彰显司法正当性。〔1〕不过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他们提升司法结论正当性的功能却总是由于被歪曲、被漠视或被抑制而难以有效发挥。
(一)法律修辞:可接受性荫庇下的主观主义难以被有效规制
运用好法律修辞是保证语义的准确传达与理解以及对实现听众的有效说服的重要路径。但修辞的主观主义特质也让人们深深忧虑,〔2〕存在于可争辩性领域的法律修辞在很多时候都暗藏着恣意裁判的可能,诉诸感性而不诉诸理性。修辞术(学)在古希腊时期曾极盛一时,但后来由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观念的兴起而日渐式微,甚至被认为“是希腊罗马思想的恐怖变异”*[比]CH.佩雷尔曼:《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杨贝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总第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而遭遇厌恶与抵触。不过现代司法不是按图索骥,在理性说服逐渐埋葬蛮力压服的法治潮流中,“司法活动需要证明:其据以推理的前提是正确真实的,其推理过程是符合逻辑的,其结论是合理合法的。”*任海涛:《中国古代司法修辞的合理性及启示》,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修辞学最终还是高调复兴了。与传统修辞学相比,新修辞学更加注重说服效果,“听众”成了新修辞学的核心概念。正如佩雷尔曼所认为的那样,“对话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听众的信奉”,*M.Maneli,Perelman’s New Rhetoric as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Next Century,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pp.51—52.也即可接受性。可接受性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其过分在意获取听众的接受而不可避免地融入具有迷惑性的情绪因素,即便是脱法而为的主观主义修辞也在所不惜。有些修辞者甚至试图通过直观、旁观、通观等修辞视角的转换, 来造成客观的假象,掩盖其视角在本质上的主观主义性质,从而达到所谓的“说服目的”。不论是为了暗度陈仓抑或是仅仅出于好意,“歪嘴和尚”们很可能已经把法律的真正含义与是非曲直给念歪了,把司法的正当性给念丢了。修辞放大了适法行为的随意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本来就迷雾重重的司法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所以说,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固然是意见整合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但纷繁多变的司法实践却导致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进化过程充满了变数,法律修辞的理性话语力量在跨越历史的栈桥上变得风雨飘摇。法律修辞对司法的正效应只能由此而付之阙如。而这一切出现的原因不仅仅是法律修辞的主观主义再次蔓延开来,更直接的原因是缺少语用学规则的有效制约。基于此,有人提出了规则的约束、法律思维的引导等以规制主观主义为目的的各项措施。其中,规则的约束是指谨守程序化的修辞范式,包括逻辑的限制、程序的规范;法律思维的引导是指把法律规范用作思维判断,包括理性主义的引导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培养等。这些措施合称为法律修辞客观化转向。*客观化的特征:趋向法律与事实的真实原貌,排除外部不当干扰。客观化转向的范畴包括但不限于陈金钊教授所言的“把法律作为修辞”。参见武飞、王利香:《法律修辞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衔接——司法民主的视角》,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笔者对此十分赞同,因为“司法裁判要成为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结果,必须具备客观性。”*王晓:《法律论证客观性的寻求——以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点》,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1 期。法律修辞的客观化转向能否实现不仅是修辞本身存在样态的问题,而且是司法能否做到客观公正、不枉不纵等攸关判决正当性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规则的约束之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谨守合法性原则来把修辞者服帖地约束在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在法治社会,判断个案裁判之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是裁判依据的合法性,法律才是司法行为正当性的最重要理由。尽管合法的不一定是可接受的,但是于法无据的可接受性只会导致主观主义的妖颜祸种再度肆虐。
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客观化原则的各项措施并未奏效。所谓“规则的约束”由于可操作性不强而经不起实践的拷问,“法律思维的引导”也由于太笼统而只是处于初期阶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便有些修辞者认识到了“在合法性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可接受性”*陈金钊:《多元规范的思维统合——对法律至上原则的恪守》,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的重要性,还可能会由于法律仅划定了一个宽泛的裁量区间或者法律本身就是不完善的而依然无从知晓特定修辞行为是否符合抽象法律条文的规定。法律修辞因此而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的怪圈”,正当性命题也由此而失却了其正确性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修辞者们可能会由于找不到正确性标准而陷入无尽的争论,进而影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可是我们又找不到一个无可易移的衡量标准来终止喋喋不休的争论。法律修辞成于主体间共识,而共识则基于规则的主体间有效性。在规范与标准缺位的情况下,论辩与商谈可能会凝聚共识并发现真理,也可能会加深分歧并淹没真理。但又不能因此而排斥修辞,否则就等于因噎废食。贡塔·托依布纳认为,“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专家语言的增长”。*[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可惜的是作为专家语言或专业语言的法律修辞却由于得不到规则的有效约束与法律思维的正确指引而难以恰当地展现其实践价值。迄今为止,法律修辞学会议已经连续召开了八届,几乎每届会议上都会有人问法律修辞存在的意义何在。这并不是说我们之前一直所秉持的修辞规则的约束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也不是说法律思维的引导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是说这种表面上十分美好的制度蓝图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构建层面,亟需被推广、被完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即便修辞学人已经在学术共同体中达成了不少共识并初步建构了法律修辞的学科范式,但修辞学体系之外的人仍然对此知之甚少并且由于无知而对修辞学人指手画脚,甚至盲目地为法律修辞确定具体标准。
另外,法律修辞提升司法正当性的前提是其本身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法律修辞在很多时候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强者面前更显得力有不逮。当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还受着实质思维的制约,张扬着所谓“依法裁判”的司法传统而难以摆脱只注重实质审判的窠臼,法律修辞被充分运用的情况微乎其微。这从目前简短的裁判文书就可见一斑。尽管有些裁判者正在逐步摒弃这种观念并有志于通过理性说服来获得胜败皆服的结果,却又由于不谙修辞技艺而不知从何说起。是故,季卫东教授在上世纪就已经倡导的“判决理由高于实质判断的原则”*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至今仍未被确立。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认真对待修辞、重视修辞,却总是很难在短期内看到实效,法律修辞保证裁判正当性的功能一直没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二)案例指导制度:说服力欠佳且拘束力微弱
虽然有人相信作为裁判规则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拥有了不容置疑的正当性”,*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但是也有人在怀疑案例指导制度整体或部分的正当性。*牟绿叶:《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李森:《新一轮司法改革背景下案例指导制度的新问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张伯晋:《案例指导制度不是判例法》,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29日。而按照拉兹的观点,规则的合理性与规则所服务的目的证明了规则的正当性。*[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尽管当前人们对设立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目的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对具体规则合理性的批判却不绝于耳。理论上的非议也并非无理取闹,毕竟指导性案例的实践效果常常不尽人意。例如,科层制下的“案例遴选机制没有摆脱行政化的内部操作运作传统”,*牟绿叶:《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为案例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埋下了隐忧。针对此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从比较法的视角,学习域外经验将案例援引完全付诸“司法市场”,让诉讼参与人自由与自主地选择案例。这实际上是要完全抛弃或推翻现有遴选程序本身,已成为激进的制度革命而非渐进的司法改革而不太切实,况且西方判例制度也由于摆脱不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约束而具有不少缺陷。第二种方案是仍然采用目前的遴选方式,但应当对之加以完善。不过应当如何完善?倘若当事人原本就不服生效判决,那么该判决荣膺“判例”的地位就只会招致更大的不满,由此产生的第二次伤害甚至会超过第一次伤害。指导性案例若想成为司法正当性的依据,就必须首先满足自身正当性的要求,也即必须将最合适的案例遴选为指导性案例。不过如何遴选出这样的案例却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遴选之后,对原始案情的追忆与再现、对原始文书的裁剪与加工俨然成了一种惯例。这些形式上客观的叙事方式是否也能在原始当事人那里“说好法治话语、讲好法治故事”并获得原始正当性却不得而知。民法法系国家最多只是通过案例挑选以形成司法先例,而我们则还通过案例加工以形成指导性案例。当然,对案情的裁剪与加工并不等于说理得到了强化。当前指导性案例文本所涉及的事理、法理、学理、文理乃至情理都缺乏说理,以至于时常出现类似于指导案例27号“本案结论是正确的,关键之处在于本案法官没有将正确的结论论证清楚”*李森:《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中国问题与德国经验——以“癖马案”为视角》,载《湖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3 期。的尴尬局面。最高院也承认,“案例推荐和编选水平有待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所谓的“水平有待提高”也就是修辞论证水平需要被提高。包括指导性案例文本在内的“文书改革面临的问题首要是说理不充分。”*曹志勋:《论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及其裁判技术——基于对已公布的42 个民事指导性案例的实质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指导性案例能够真正规范司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例本身的说服力和质量,那种寥寥数语的“超级先例”*“超级先例”一词并非笔者首创,其由格哈特首先提出。参见[美]迈克尔·J.格哈特:《先例的力量》,杨飞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79页。虽然不易遭受攻击,但是却由于失之粗糙而有碍于后人准确、完整地理解先例,导致指导性案例很难灵活应对多变的司法现实。时间点变量的应然作用在案例指导制度中得到了昭示,但关联性变量的缺失却使得案例指导制度的实然运行变得十分不畅。
其实,比案例遴选中的那些问题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司法中的案例拘束力问题,也即同案同判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问题。同案同判是对司法结论正当性最原始、最基本、最直接的诠释。*Richard Wollheim, Isaiah Berlin: “Equ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56, No.1, 1955, pp.301—326.我们也整天打着“同案同判”的旗号,但实际上又不允许前案对后案形成约束力。这是多么矛盾的思维,幻想着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类似问题类似处理,却又不允许把同等条件作为处理同等情况的依据,甚至为同等情况的不同等对待寻找种种借口……制度设计在逻辑自洽性上出了问题。虽然指导性案例具有通过提供约束性规则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强大功效,可是如果这种规则连最基本的强制力都没有,可以随意僭越,那么指导性案例的规范作用、可预期功能就只能沦为空谈。没有规范拘束力的理性说服只能被置若罔闻,缺乏强制约束力的指导性案例在复杂而残酷的实践面前定会变得苍白无力,更遑论在此基础上提升裁判的正当性了。
虽然主流观点认为指导性案例应当具有规范拘束力,最高院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指导性案例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实证考察发现指导性案例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只是沧海一粟,判决理由参照指导性案例的比例不到0.002%。*笔者在中国审判文书网上,将时间限定为从最高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2011年12月20日到2017年1月22日,共有裁判文书25763599篇。之后分别以“指导案例”或“指导性案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除去其中的重复文书、实际所指为公报案例的文书,共录得裁判文书2174篇。其中,当事人提出参照要求但是法院未予以回应的文书共431篇,也即只有0.0017%的裁判文书按照最高院的要求在判决理由中引用了指导性案例。检索结果还显示,当事人提出援引要求的文书数量与法官作出回应的文书数量的比例是5:1。笔者也检索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下文简称《细则》)颁布之日的2015年6月2日至2017年1月22日的文书,发现各项数据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与之相印证的是有人经过统计发现,截至2016年8月,最高院发布的64个指导性案例中仅有19件被正式援引,大部分指导性案例处于沉寂状态。*向力:《从鲜见参照到常规参照——基于指导性案例参照情况的实证分析》,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实践中的低迷与理论界的热议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到底是因为指导性案例被刻意规避了,还是被遴选的案例如此不具有代表性以至于难以适应实践需求?恐怕最为根本的还是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正如某判决书所言的那样“我国非判例法国家……指导案例对本案的审理仅有参照意义。”*“青岛东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姜宝琛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编号:(2014)青民五终字第1628号。因此可以不参照。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案例指导制度推行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当事人,而是来自法院或法官。检索结果显示,当事人提出援引要求的数量是法官回应数量的5倍,背离指导性案例的约束实际上已经成了很多法官的默认选项。作为花瓶制度的指导性案例并没有在关键时刻以强有力的手段来促成结论正当化的实现。有论者认为指导性案例援引率低迷的原因还包括相关制度可操作性的缺乏,特别是《细则》的内容“多数为指导性案例的管理工作,包括规范结构、遴选条件等程序化要求……而非操作性规定。”*赖江林、李丽丽:《类案识别:指导性案例适用技术的检视与完善——基于最高人民法院52件指导性案例适用现状的实证分析》,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2016年4月14日,第389页。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与常态化、周期性的遴选工作相矛盾的是,有关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保障机制与相关技术支撑都尚未建立起来。
即便解决了约束力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有待解决。我们知道,案件不可能完全相同,援引指导性案例的前提也并不是两个案件完全相同,否则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范围就太过于狭小。只要案情相似即可援引也早已成为共识。而且相似性的判断一般通过凯斯·孙斯坦的“类推思维典型形式”*[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胡爱平、高建勋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或者安德雷·马默的“强类比”与“弱类比”方法即可完成。*Andrei Marmor,Should Like Cases Be Treated Alike, Law in the Age of Plu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0.但问题是,相似的案例可能并不止一个。司法场域中解决方案的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形形色色的案例之间难免会出现冲突、矛盾、间隙与张力。尤其是当两个案例都可以被用来解决问题甚至产生了不和谐、矛盾乃至对立但又找不出轩轾冲突的方案或者即使找出了方案却难能令人信服时,就会发现达致正当的过程是如此艰难。而且当事人的类型往往是多元的与不确定的,一部分当事人可能会为援引结果拍手称快,另一部分当事人则可能会对援引结果嗤之以鼻。此时,共识与制度性权威再次变得脆弱不堪。处于历史与现实交汇点上的指导性案例对于当事人而言所具有的连贯性、确定性与可预测性也变得不连贯、不确定与琢磨不定。马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倘若仅仅只能找到唯一的一个案例但该案例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此时仍应遵从所谓的“同案同判”原则?*同前引[26], p.5.
二、消除缺陷: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融合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法律修辞的提升裁判可接受性的功能、说服听众的功能,指导性案例提供裁判规则的功能、实现同案同判的功能……这些有利于提升裁判正当性的功能都已经受到了极大遏制。“修辞与判例”这一对法学范式必须得寻求突破了。其实,只需发现修辞与案例的潜在价值并促成二者的功能融合,即可压制主观主义并促成法律修辞的客观化转向、保证指导性案例的同案同判功能能够发挥出来并且发挥得好,从而真正提升司法正当性。
(一)在修辞中运用案例:提供标准、强化规则
前面说到,客观化原则所要求的各项措施由于可操作性不强或太笼统而经不起实践的拷问,仍处于初期阶段。特别是,法律规范在很多情况下规定的都是一个具有裁量可能性的司法区间,缺少修辞论证的统一尺度或具体可比的参照范本,为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与主观主义的失控提供了契机。但案例指导制度却有很大的不同,具体的指导性案例比抽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更强的准确性与确定性。指导性案例提供的情景化类比进路会更好地限缩修辞者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一个可供比照的衡量标准或示范性指引,为修辞论证悬以准绳,从而有效解决修辞标准模糊化、抽象化问题。虽然法律修辞不能荡涤掉与生俱来的主观主义特质,但至少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来稀释其主观主义色彩。案例指导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模板,防止修辞者在主观主义的驱使下裁剪法律。因此把指导性案例作为修辞论证的标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制度权威缺乏的现实问题,防止修辞者在没有翔实可鉴的样板可供参考的时候就自行其是、任意运用法律外因素进行法律评价、为枉法裁判寻找托词和借口。这些做法看似束缚了法官的手脚,实际上却构建完成了一个抵制干扰的修辞情境,把法官从体制内的行政压力与体制外的舆论压力中解放了出来,降低法律外因素对司法审判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助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甚至可以矫正长期以来备受批评的案件请示制度,保证审判活动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具体地说,指导性案例提供标准、规制主观主义的方式大致如下:
AD9833的核心是28位的相位累加器,它由加法器和相位寄存器组成,每个小时来临,相位寄存器以步长增加,相位寄存器的输出与相位控制字相加后输入正弦查询表地中[5]。Sine ROM的作用是把相位信息转换成正弦数值,从而可使用NCO输出。数模转换器是10位的DAC,可从Sine ROM中接收数字,并将其转换成相应的模拟电压。稳压器的作用是调整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所需的电源,此电源的范围为2.3V~5.5V。
一方面,修辞者(尤其是代表当事人利益的修辞者)的目的是通过将待决案件的基本事实T={α,β,γ}涵摄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T’’={α’’,β’’,γ’’}之下,来实现自己的主观目的P,并获得听众的认可。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却总是面临着种种问题,例如,当T’’的某个要素α’’缺失或模糊不清之时,修辞者通过法律实现诉求的最初想法就会难以实现,即使勉强实现了也难以获得广泛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修辞者很可能会为了实现结论的可接受性而抛弃过程的正当性——抛弃法律。虽然修辞者不应当轻易去寻找非法律因素来屏蔽法律与事实之间的沟壑,非法律因素往往裹挟着太多的主观主义成分,但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而在另一方面,与抽象的法律要件T’’={α’’,β’’,γ’’}相比,指导性案例的要素T’={α’,β’,γ’}在很多时候与待决案件的案情T={α,β,γ}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只需相对简单的类比即可实现主观目的P。此时应当把指导性案例作为达致修辞者目的依据与标准,防止修辞者通过其他手段M来达致主观目的P。当然,如果通过法律与通过指导性案例都不能实现主观目的P,那么修辞者所欲实现的主观目的P很有可能是不正当的,应当被另一方的正当的修辞压制下去。
以上的论述可能会让某些读者误以为指导性案例发挥作用的前置性条件是法律无法涵摄事实,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更为复杂。例如,法律规定某个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是或命题R= X∨Y,即法律评价可以是R=X,也可以是R=Y,指导性案例的结论是R=X。假设不考虑先例,那么不论待决案件的法官最终作出R=X或Y的裁决,对听众来说均是可接受的、正当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先例R=X是存在的,而后案法官仍作出了R=Y裁判,利益相关者显然会感到不公。虽然两个案件都是依据法律作出的合法决定——事实涵摄于法律之下,但是最终却致使听众对后案结论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此时只要法官还想说服听众,谨守同案同判原则就成了法官的应然义务。指导性案例最直接的功能即在于实现同案同判,限制包括法官在内的修辞者的自由恣意,这正是法律修辞一直梦寐以求却始终难以实现的效果。把指导性案例确定为修辞论证的标准是对修辞现状的回应与纠偏。不论何时,与基于自身对正当理由要素的直接评价而行事相比,如果依据实践权威提供的理由来行事更能满足正当化的吁求,那么此时接受实践权威就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拉兹所谓的“常态证立命题”。*[美]朱尔斯·L·科尔曼:《原则的实践:为法律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辩护》,丁海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该命题在修辞论证场域中的表现就是倘若作为实践权威的指导性案例更能满足司法正当性的吁求,那么就应将其作为修辞论证的标准或理由去发挥作用。这也是指导性案例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之一。
当然,修辞者把指导性案例作为论证依据的先决条件是指导性案例具有规范效力。任何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案例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横向说服力,而指导性案例不同于其他案例的关键并不在于横向说服力而在于纵向拘束力。此前的公报案例几乎功能尽失,关键就在于没有拘束力。从域外经验来看,在民法法系里面尽管判例表面上不如成文法重要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甚至创制了“新法”,尽管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所以比利时法学家胡克说,“这是新的现实,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比]马克·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虽然英美法系把先例中的“判决理由”的拘束力与“附带意见”的说服力相区别——英美人并没有笼统地承认先例任何部分都具有拘束力,但关键在于先例本身早已具有了拘束力。具有拘束力的案例才能更好地夯实合法性基础并压制住主观主义,进而提升司法正当性,修辞者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案例。而对于文章第一部分所论述的“合法性危机的怪圈”,解决方法其实也就是此处所讲的把指导性案例作为修辞者运用法律修辞的制度性依凭。
另外,作为修辞依据与标准的内容不能囿于高度原则化、抽象化的裁判要点。原因在于若只引用抽象规则,修辞者还需额外负担把抽象规则具体化的任务。对于某些案件而言,相比于引用抽象性规定,引用生动具体的裁判事实和理由的论证压力则小得多,只需要把案情加比以对即可。而不必费神去解决哈特所说的把特定事实涵摄于抽象规则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问题。*[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也即,若指导性案例对基本案情T的法律评价为X,而待决案件基本案情含有T’,那么只要T=T’,待决案件的法律评价X’就直接等于X。而不是在L为裁判要点的前提下,由T=T’,到L涵摄T’,再到X’=X那种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复杂过程。这也是我们的近邻日本法院虽然也编辑了裁判要点但并未赋予其排他性拘束力的原因所在。如果通过第一种直接方法即可达致目标,则不必迂回前进采用第二种间接的方法,否则就有悖成本原则。而且裁判要点和抽象法律过度相像,可能会抹杀指导性案例精准化限制修辞者恣意的独特功用。指导性案例中可以被作为标准与依据加以援引的内容应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这样的理念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且得到了详细论证。*参见郭明瑞、瞿灵敏:《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与适用问题研究》,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或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大学联合课题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3 期;或参见孙海龙、吴雨亭:《指导案例的功能、效力及其制度实现》,载《人民司法(应用)》2012 年第13 期。甚至在上世纪郭道晖前辈就明确指出先例之成为法,是以其在裁判理由中所宣示的法理为基准,*郭道晖:《提高判例的法理质量》,载珠海市非凡律师事务所编:《判例在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而非某些人所固守的“只有裁判要点才能……加以援引”。*黄泽敏、张继成:《指导性案例援引方式之规范研究——以将裁判要点作为排他性判决理由为核心》,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当然究竟是指导性案例的任何部分均可以被修辞者援引,还是应当把关键词、法条等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排除在外,需要尽早筹谋策划。
尽管前面说到,客观化原则所要求的法律思维的引导与规则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学术研究的界域,亟需被推广、被完善,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些目标也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在修辞论证中运用指导性案例则会大有不同:一方面,把指导性案例作为修辞标准或依据的做法本身就是在完善与充实修辞规则,强化修辞规则的约束。另一方面,具体可感的修辞标准更易于被修辞共同体所接受,也更易于被普及与推广。而且修辞者在说服听众接受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与发现修辞规则,从而更好地去学习修辞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推广修辞规则。随着客观化原则的推广与完善,主观主义得到抑制,可接受性得以升级为正当性。这样,法律修辞不仅包括了逻辑三段论的涵摄思维,还蕴含着从彼案件到此案件的类比思维。尽管只通过提供一个单薄的修辞标准难以保证法律修辞客观化转向的必然实现,但是在修辞中运用先例却为法律修辞提供了一片成长的沃土,零碎的修辞规则会随着案例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完善并逐步组合起来。
(二)在案例中运用修辞:搭建平台、提升效力
虽然最高院垄断了指导性案例的生成,却阻止不了“案例市场和法学理论的竞争”。*李森:《新一轮司法改革背景下案例指导制度的新问题》,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培育出一个更好的案例生成环境。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充分重视法律修辞的作用,通过法律修辞的催化作用来激活与助推多元意见与观念在生机盎然的司法沃土上自由角逐,让最具公信力的案例通过真理性辩驳脱颖而出并上升为指导性案例。更具体地说,就是用修辞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多种观点与多项选择对阵的平台,从若干个备选案例中筛选出最具说服力的案例并赋予其正当法律效力。唯有当某个案例的理由最终击败了多个与之相冲突的理由之时,才最终赋予其法律上的“指导地位”。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排他性理由,在嗣后的案例援引过程中对指导性案例正当性的怀疑就会一次次出现,修辞者很可能会通过背离性论证对之加以规避,司法也将难以做到兼听则明。这其实也是前面所讲的第二种方案的完善办法:把修辞论证作为筛选案件的过滤装置。用修辞方法来保证遴选程序所选择的都是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案例,使听众相信选择此案例而非彼案例的决定是合理的,解除听众对指导性案例本身正当性的疑虑或不信任。
当然,一个活跃与有序的案例市场仅仅依靠进化理性可能要走很多弯路,建构理性亦应加以凸显。应当基于建构主义的理性,把案情信息的透明与公开、案例平等性的假设、竞争过程的充分与对等、案例筛选结果的市场化评价等基本吁求付诸规范化与体系化的制度实践与规则实践,让修辞者们能充分地表达意见。还可以授权原审法官从裁判理由原文中提炼裁判要点,最高院在编撰指导性案例时亦应采用该裁判要点,否则即应做出明确、详细、充分的正当性论证,用“原汁原味”来保证案例的亲历性、真实性与准确性,从而使裁判要点获得更多的原始正当性。此时原审法官对修辞的使用也应当强调,毕竟“一份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裁判文书更容易上升为指导性案例”,*黄现清:《裁判文书说理的法理分析》,载《政法论丛》2016年第1期。形成法律修辞与案例指导制度的良性互动。而对于发布体系过度多样化问题,*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体系过度多样化,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以及围绕当前热点问题都不断有案例发布,而且各地高院甚至中院也都在发布“指导案例”。除了法院系统,检察系统、公安系统也在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那些效力不明而层出不穷的案例弱化、稀释了指导性案例的层次体系和内在逻辑。以及案例编号的结构等问题,*案例编号设置过于简单,难以保证表述的准确性,不方便检索等。除了应当通过制度性建构加以回应,还应在修辞用语上加以充实与完善,让修辞者明白不同案例的类型、性质、效力以及援用规范,从而有效降低后案修辞者在司法中滥用法律修辞而歪曲指导性案例原意的概率。当然,究竟是改善文书本身的说理还是增加类似于产品说明的“指导性案例说明书”,这需要决策者来决定。
至于司法中的案例引用率低迷问题,原因很多,例如指导性案例拘束力不足、对基本案情与法律适用的相似性都加以证明的论证负担过重等。*参见孙光宁:《反思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方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或参见郭明瑞、瞿灵敏:《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与适用问题研究》,载《江汉论坛》2016年第2期。不论原因为何,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支持性论证、区别性论证与背离性论证等规定为裁判者选择遵循先例、区别先例与背离先例的一项强制性义务。法官是否应当主动发现、引用案例尚且不论,对诉讼各造所引用的案例予以回应的义务则必须通过程序控制来加以实现。正如艾森伯格所言:“法院没有义务服从律师,但是他们有义务对律师的必要请求予以回应。”*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Nature of the Common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92.前文已述,指导性案例援引的最大阻力来自法院或法官。而修辞义务化的效果就是即便不能确保法院援引案例,至少可以迫使法官作出不援引的回应以提升其结论的正当性。最高院也认识到了这点并在《细则》中要求裁判者应当对诉讼各造所提出的援引要求在裁判理由中予以回应,但由于缺乏不援引的法律后果而且还因为此前规定指导性案例不得作为裁判依据而破坏了该项规定的规范效力。目前似乎只能通过责任追究机制等强制性手段——违背修辞论证义务将产生判决被推翻的风险以及对法官的消极评价——来迫使法官对此做出论证与说明了,让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法官在成本-效益规则的驱使下做出理性选择。至此,法律修辞不受重视的问题也被化解于无形之中。
对于案例之间的竞合或冲突问题,必须运用修辞方法在不断的说服与论证中逐渐排除多样化的方案,直至寻找到一个最具共识性的指导性案例,保证正当性基础不至于因为一点点的冲突与矛盾就黯然消逝或被掩饰。人们信服先例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权威性,还因为它所具有的逻辑自洽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具体到个案,对于多个可供援用的指导性案例之间相互抵牾的问题,修辞者需要证成所选案例的合理性。例如指导性案例A的基本法律事实是T={α,β,γ},指导性案例B的基本法律事实是T={α,β,δ},而待决案件C的基本法律事实是T={α,β,γ’},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修辞的方式来说服听众何以援引了案例A而不援引案例B,让听众理解为何γ与γ’之间的差异足够微小而可以忽略不计,δ与γ’之间的差异则太过于显著而必须加以区别对待。而强化法律修辞的说服作用,要求修辞者对A案件与B案件的法律事实作出实质性对比并必须加以说明,则有助于加深修辞主体对案情的精细理解与把握。真理最终还是越辩越明。另外应予注意的是需要援引指导性案例的案件大多是疑难案件,*本文的疑难案件既包括单纯事实认定存疑的案件、法律适用存疑的案件以及包括二者皆存疑的案件。简单三段论推理很难让听众相信你所做出的选择是正当的、正确的,因而需要采取复杂的双层证立模式来完成论证任务。修辞者不仅需要证成结论的正确性,而且还需要让听众明白何以作为前提的指导性案例A的必要事实只能被认定为{α,β,γ},而不能被认定为{α,β,ε}或其他。而当多个可供援引的指导性案例是聚合关系时,修辞者则需要从这些先例中析出一个普适规则∀(T→R)来处理待决案件,较为典型的如指导性案例4号与12号的综合情势权衡规则,对被告人与被害人家属的利益诉求予以综考量。这种情况必须用尚不完美的客观化原则来保证援引的客观与公正,防止法律修辞的主观主义缺陷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歪嘴和尚”所利用。
不难看出,法律修辞在指导性案例适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就是为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提供一个对话与博弈的司法竞技场,通过修辞平台的搭建把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彻底释放出来。而且强化法律修辞在指导性案例中的运用对修辞的推广也颇有裨益。一份普通的判决文书的听众往往只限于特定的当事人,修辞的示范效果也局限于此。但指导性案例的影响范围则大得多,在指导性案例中运用修辞的示范效应将至少扩大至以后所有类似案件的当事人,这为修辞规则的普及提供了绝佳的实践进路。而且这个过程还可以让法律人更好地去学习蕴含其中的修辞规则、技巧与思维,从而更好地去实现修辞规则的约束与法律思维的引导。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在加强修辞论证的过程中须正确使用修辞,把法律修辞的文义射程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将修辞破坏力转化为建构正当性的动力。与偏重法律效果的消极修辞相比,着墨于社会效果的积极修辞隐藏着更多的“法律越轨风险”,也更容易使得修辞者从正义的法治诠释者沦落为骄纵的法治破坏者。因此应尽可能多地使用理性的消极修辞,尽可能少地使用感性的积极修辞,在最大的程度上保持客观法律与客观事实的原本面目。这是一个前置性问题,如果不能把法律修辞的主观主义控制在客观的范围之内,修辞定会给司法带来无尽的灾难,功能融合所欲实现的正当化目标亦将烟消云散。
三、功能融合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作为说服艺术的法律修辞是主体间有效沟通的重要途径,能够为指导性案例的遴选与适用提供正当化手段;而指导性案例作为生动易懂的“活教材”对法治的宣传与对社会公众的普法教育能够更好地促成法律的内化,为法律修辞作用的发挥奠定社会法治基础。但是功能融合尚不完整,在融合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功能分化等其他问题。
(一)注重根据案例类型的功能分化
我们一直着眼于功能互补意义上的融合,却可能忽视了功能分化意义上的融合。司法实务中案件的类型林林总总,而最高院却只是笼统地要求“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查询相关指导性案例”,*《细则》第11条。并未交代清楚指导性案例发挥作用的场域。难道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援引要求的极端简单的案件,仍要强迫法官去查找案例?这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知道,实践中的大部分案件都是相对简单的案件,实现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等置易如拾芥,援引指导性案例只是画蛇添足而已。况且在司法供给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现实情况之下强加给法官查询、对比并决定是否引用案例的工作是不得人心的,承受巨大工作压力的法官显然不会对此表示赞同甚至与改革相龃龉。特别是自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指导性案例在此时成了法律人的负担,正效应竟不敌其负效应。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对于简易案件,只要法官进行必要的修辞论证即可免除其案例援引义务。这类案件交给效率较高的法律修辞反而能更迅捷地达致正当。“修辞可以使得判决的合法性得到较小成本的灌输”。*洪浩、陈虎:《论判决的修辞》,载《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第5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而且此种做法也是在推介修辞,改变修辞不受重视的窘境。被修辞魅力深深折服的诉讼两造更有可能服从判决,减少上诉或申诉的概率。而对疑难案件或重大案件,法律除外因素太强大,再完美的说辞在暗流涌动的行政势能和汹涌澎湃的舆论势能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任何一个被证明为合理的权利皆不得受到忽视”,*[比]CH.佩雷尔曼《法律与修辞学》,朱庆育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但是现实表明再有力的修辞论证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也同样会力有不逮,只能弃听众的理解性接受于不顾。此时,必须用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性权威去抵制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司法不仅仅需要发自内心的信服,还需要庄严肃穆的慑服。
其实,在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屈指可数的今天,划分疑难案件与简易案件其实并不具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司法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例可循,修辞者连任何一个相关的案例都找不到。我们每年有超过2300万个案件需要审理,*周强:《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3月20日。但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却不足百件。现在,美国那种判例数量太多所导致的“卷宗危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当前确实应当不断增加指导性案例的供给,足够多的案例才有可能建立起来同案同判所需要的巨大数据库。*尽管由于司法传统、法律技术、法律文化以及法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在短期内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案例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但质变的纵深维度的难以跨越正是我们加快量的积累的理由。但更切实也更为紧迫的任务则是将待决案件分为有例可循的案件和无例可循的案件。前者以援引为常态、以不援引为例外,但是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援引要求的简易案件可以不援引。这也体现了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能更好地满足多样化需求而提升司法的正当性。对于后者,则应当再次发挥修辞者主体性优势,将类型化的抽象规范活化为案件裁判的标准以填补规范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正是指导性案例的不完备性为修辞的运用创造了更大的空间,让法律修辞去解决某些看似很难解决的问题成了一种可能。不过此时修辞者的主观主义缺陷进入了最容易爆发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降低这种可能性。法律修辞具有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双重属性,但此时其教义法学的属性应当得到昌明而社科法学的属性则不应过分强调。
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功能分化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对于无例可循的案件,让法律修辞去发挥作用、填补空白,去“施展才华”,增强裁判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也即当制度性理由的权威不足以应对听众对正当性的怀疑的时候,实质性理由就应当去证成司法结论的正当性。其二是对于有例可循的案件而言,让指导性案例主导疑难案件或重大案件的正当性证明任务;对于除却疑难、重大等变数较大案件之外的大部分案件而言,援引指导性案例并非必要,强迫法官去查询案例更非明智之举,让法律修辞主导简易案件的正当性证明任务即可。根据客观化原则的基本立场,法律修辞要做的就是把法律的正当性输送到每个司法裁判的每个终端。恰如其分的表达不仅有助于说服效果的大幅攀升还有助于实体问题的解决,提升裁判的实质正当性。
功能分工的核心在于,让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去填补对方的功能盲区,两者各有分工和侧重,分别负责不同类型案件的正当性证明任务。如果二者中的某一方去解决司法中的法律漏洞、文义模糊、价值权衡、权威性规则相互冲突等问题更具优势,其即应当去填补漏洞、明确含义、斟酌轻重、决定顺序。只有寻找到最佳切入点并进行正确的、相洽的功能衔接,才能在实质上提升裁判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完成法治中国的巴别塔。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内在价值均在于贯彻正义、实现法治。可是两者也会产生分歧。法律修辞的基本目标在于区别对待、因案而异,而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追求则是同样对待、同案同判,在实现正义、追求正当裁判的过程中竟然也产生了偏差与分歧。“携手共进,并行不悖”似乎成了一句空话。但是二者并不能因此而分道扬镳。应当把法律作为修辞论证的核心素材,坚持法律修辞的客观化转向;把指导性案例的运用控制在法律的界限之内,坚守法的规范属性与教义学属性。保证修辞与案例始终是围绕法律、围绕法治发展规律在运行,尽量用法律的融贯性来凝聚共识、消除隔阂。
(二)其他需要警醒的问题
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融合其实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相互合作与融合,在对方的场域中发挥己方的优势与作用。其二是法律修辞与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分工与分化,各自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坚守住各自的阵地。可是这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并担保裁判正当性的必然实现,很多问题依然要通过完善自身来加以解决。法律修辞仍应一如既往地秉承客观化原则的限制,通过规则的约束、法律思维的引导来保证法律修辞在一个统一的范式内运行;指导性案例同样要一如既往地提升自己的规范拘束力与说服力,通过案例遴选方式的优化、案例适用标准的统一、法官适用案例技能的培训、案例库的丰富扩充、案例生效后评估等手段来把“软约束力”升格为“硬约束力”并保证案例的正确适用。部分性能的提升有助于整体性能的提升,修辞与案例必须“修炼内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法律必守的观念,把主权者的自由裁量权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否则施密特式的主权决断论将不可避免地在现代社会中再度疯狂肆虐。*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64—69页。对法律的忠诚与恪守是实现法律治理秩序的前提。“要想建成实质法治社会,必然要经历形式法治建设的阵痛与苦难。”*杨铜铜:《法治思维下的论题学思维——理念、问题及其规制》,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19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以法律为代表的裁判规范绝不能被边缘化,否则法治就只能被束之高阁,而建设法治国家的美好理想也将变得遥不可及。
前面总是在论述如何融合与衔接却可能忽视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作为修辞标准的指导性案例在法源谱系中的具体定位问题,这也是一个将会对修辞策略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现有法律体系不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以例破律显然是违背法治必守的基本原则的——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显然弱于基本法律。不过关于如何处理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竞合的问题则聚讼不已。有的认为最高院有权将指导性案例吸纳为新的司法解释类别,指导性案例应当与现有的司法解释具有同等效力;*参见陆幸福:《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法律效力之证成》,载《法学》2014年第9期;或参见谢彩凤、赵鸿章:《从“柔性参考”到“刚性参照”:指导性案例应用现状探究及完善——以52个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情况为分析视角》,2016年4月14日,全国法院第27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第421页。有的则认为指导性案例不具有法源的地位因而效力弱于司法解释;*蒋安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载《法制资讯》2011年第1期;或参见王利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2012年第1期。还有的认为虽然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弱于正式法源但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参见雷磊:《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性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1 期;或参见宋京逵:《对案例指导制度的再审视》,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毕竟作为“个案解释”的指导性案例与作为“规范解释”的司法解释拥有共同的发布主体与相似的规范目的,都是司法解释权运行的结果。它们之间的效力问题则只需要遵循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基本原则即可加以解决。而修辞者在此时则应当确保自己所做的选择契合于法律修辞的客观化原则。不论是做出司法解释优先还是案例优先的效力判断,均应当通过详细、完整的修辞论证来获得听众的认可与接受,达到法律与案例之间的有机融合而非决然对立。另外需要澄清的是,这里只是说效力上相等,指导性案例是否属于司法解释则有待商榷,毕竟案例指导制度在性质、特点、构成以及适用方式上与法律规范具有显著的区别。
另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问题是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界域大小的问题。一方面,作为裁判依据的指导性案例本身就是修辞论证的论据之一。就是说,指导性案例是被包括在广义的法律修辞范畴之内的,指导性案例是修辞者达到说服目的的工具之一。但如果仅这样认为,法律修辞的体系就不免变得过于庞大而难以触摸。另一方面,在指导性案例适用的过程中,法律修辞也成了诉讼各造所使用的技术性工具,他们要用法律修辞来证明己方所选择的案例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与优先性(priority)。其实指导性案例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为修辞者提供“司法决斗的工具”来提升裁判的形式正当性,还在于通过提供裁量标准来保证结论的公平与公正等实质正当性。也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不能贸然把指导性案例仅仅作为法律修辞的工具,指导性案例的独立性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若无睹的。申言之,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看来,指导性案例仅仅是说服论证的一个工具,并未对结果公平性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从指导性案例的运用者的角度来看,法律修辞更多的是遣词造句与词藻润饰意义上的文学修辞,其存在的意义只是辅助指导性案例更好地发挥作用,忽略了说理程序的重要性。根据司法正当性的基本立场,不注重公正的单纯说理容易沦为诡辩,而将说理视如敝屣的裁判则容易沦为专断。应当从裁判正当性的角度看,既注重裁判的公正性,又注重裁判的说服力。不偏不倚,把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作为双引擎去推动裁判的正当性。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修辞抑或是案例,任何单一的方法革新或制度微调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司法实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改革者必须注重与审级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其他制度的配合。譬如,注重案例指导制度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衔接。与抽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相比,具体的指导性案例更容易被人民陪审员所认知和接受。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将成为人民陪审员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契机。再如,注重法律修辞与庭审方式改革的关系,通过完善争点整理技术来保证修辞主体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提升修辞论证的针对性。概言之,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项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都需要一系列制度的保障与配合。如果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还需要立法的完善。法律修辞与案例指导制度是从需求侧提升裁判结论的正当性,而立法的完善则是从供给侧为司法正当性的提升提供基础与保障。
结 语
司法判决既需要制度性理由的拘束力,也需要实质性理由的说服力;需要权威性论证,也需要正确性论证。当实质性理由缺乏力量的时候,用制度性理由去补强;当制度性理由缺乏或互相冲突的时候,用实质性理由去填补或权衡;当两个理由都完备的时候,那就基本完成了提升司法正当性的任务,此时制度性理由的主要功用是对结果的权威性论证,实质性理由不仅包括对结果的正确性论证还包括对制度性理由缘何具有权威这一前提性命题的正确性论证。而当实质性理由与制度性理由相互掣肘的时候,应当综合考虑,在约束力的前提下实现约束力与说服力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