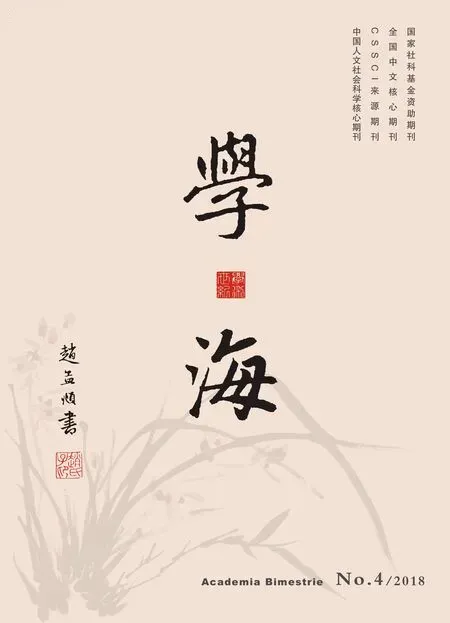在惩治与服务之间*——试论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双重特性
内容提要 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互动关系兼具单向性与主体性的双重特性。单向性是主体性得以展开的前提,亦即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依法惩治、监督管理与教育矫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追逐自由、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并同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良性互动,重建自身的主体性身份。主体性则是行刑社会化、社区服刑人本化与再社会化的体现,是社区服刑人员寻求主动性、能动性与自主性的真实反映。承认两者互动关系的双重特性,必将走出“准监狱化”与“福利化”的认知困境,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矫正关系,最终实现社区矫正惩罚性、预防性、社会化、人本化等复合性目标。
引 言
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因行刑社会化过程而在两者之间所形成的权责关系以及协商互动关系。从刑罚执行目标上说,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处于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关系的核心,是社区矫正的基础性关系。因此,两者关系的和谐共生直接关涉到社区矫正的效果与矫治目标的实现。在社区矫正实践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拥有法律制度所赋予的权力,肩负着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的重任。社区服刑人员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必须服从社区矫正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惩治的相关管理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管理、矫治与教育的客体,而是力图寻求自身自主性,尽可能在法律制度框架下扩展自身自由与权利,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因此,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出单向性与主体性的双重属性。这种互动关系的双重性质决定了社区矫正常态化的运行轨迹与发展方向。对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双重属性进行系统认识,有助于澄清一直以来对两者关系的属性进行辨识时所形成的“准监狱化”或“福利化”的认知困境。本文将对处于实践中的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双重特性及其认知困境展开讨论,进而认清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真实样态,探索优化社区矫正互动关系的治理之道。
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双重属性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单向性与主体性是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互动时所呈现的基本关系特征。单向性是主体性得以展开的前提,亦即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与依法惩治,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享有自由、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寻求社区矫正机构的指导和帮扶,并同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良性互动,重建自身的主体性身份。主体性则是行刑社会化、社区矫正人本化、民主化与再社会化的体现,是社区服刑人员寻求主动性、能动性与自主性的反映,是社区矫正这一刑事执行工作追求的重要目标。
(一)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单向性互动关系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依据正式的法律制度规范而产生,具体表现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即司法所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具体的刑罚执行关系,亦即前者具有对后者依法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励惩处等方面的权力。在行刑过程中,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和矫治,两者之间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中。国家制定与执行刑罚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对罪犯相关权益的限制或剥夺,使其感受到国家对其危害社会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制裁,从而安抚受害人并确保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社区矫正虽较之监禁矫正更为轻缓,但惩罚性依然是其基础性前提。为达到管理与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目的,法律赋予社区矫正机构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一系列强制性权力,如要求社区服刑人员服从社区矫正的各项日常管理制度,接受社区矫正机构的不定期核查,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教育与社区服务活动,等等。同时,为了体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惩罚并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开展,根据刑罚执行活动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制社区服刑人员的部分自由权利。
在这种关系结构中,社区矫正机构代表的是国家利益,是担负刑罚执行任务的国家机关,由此彰显国家法律的威严,突出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社区服刑人员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与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则是刑罚执行和被改造的对象,是处于相对弱势和被动的群体。因此,在社区矫正实践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在同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互动时理所当然应处于相对主动且强势的地位。由于触犯了国家法律,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要履行相应的义务或遵守相应的禁止性规定。从这个层面说,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为刑事执行法律关系,呈现的是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与个人的服从性义务关系。因此,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间的刑罚执行法律关系属于不平等主体间的刑罚执行互动关系,虽然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矫正的过程中仍享有不被剥夺或限制的部分权利与自由,但更多地体现为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与被监管、矫治与被矫治、帮扶与被帮扶、主体与对象的单向性关系。
在社区矫正期间,社区矫正机构有权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定期向其报告自身生产生活情况,有权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各类教育学习活动,有权要求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一定时限的社区服务活动等。与此同时,社区服刑人员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对涉及自身的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必须按要求完成社区矫正机构交办的各项任务,遵守社区矫正制度性规定。倘若社区服刑人员不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日常管理,故意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范,社区矫正机构有权对其做出相应的处罚,轻者给予警告、治安管理处罚;重者可提请裁决机关对其撤销缓刑、假释或收监执行。
社区矫正机构正是通过限制社区服刑人员的部分自由,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违规行为的惩处来保证刑罚惩罚性目的的顺利实现。由此可见,社区矫正行刑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终止,与法律赋予社区矫正机构的行刑权力密切相关,罪犯自身无权选择是否承受这种强制性的刑罚处罚,更不能改变或逃避处罚的内容,此时的社区矫正法律关系更多体现社区矫正机构单向的行刑意志,而不是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双方的平等协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处于一种管治与被管治、主动与被动、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关系结构中,两者的互动关系呈现鲜明的单向性特征。①
(二)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主体性互动关系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为缓和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间不对等的、相对被动的单向性关系,社区服刑人员会利用各种机会、制度供给与社会网络等扩展自我权能,尽可能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基本权益进行合理化表达,并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同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沟通协商,主动表达自身的各种诉求,特别是民生诉求,尽可能降低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拓展自我的自主性空间,重建自身的主体性社会身份。社区服刑人员主体性身份的重建成为该群体与社区矫正机构围绕焦点问题而展开互动时所呈现的基本特征。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在互动过程中所呈现的主体性特征,主要体现的是社区服刑人员所试图扩展的主体性而非社区矫正机构本身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相对于单向性的权力义务关系而言的。因为在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公权力的拥有者和执行者,前者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的主导性和主体性不容置疑,而后者由于触犯国家法律而成为被管治、被矫治和被改造的对象,该群体在同社区矫正机构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得较为被动,主体性缺失或不足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扩展和重建社区服刑人员的主体性,成为理解与建构社区矫正关系的重要内容。
社区矫正是将社区服刑人员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中进行教育改造,矫正该群体的偏差行为和思想观念,预防和减少犯罪,恢复他们的社会功能,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活动和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社区矫正工作本质上具有惩罚性与预防性、社会性与参与性、人本性与服务性等复合性特征。②它并不是放纵罪犯,相反是在惩罚犯罪行为的基础上,使社区服刑人员同家庭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进而重建该群体的社会人格,增强他们重新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该群体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③,促进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回归社会。
一方面,国家通过对罪犯及其行为与心理的监管矫正来实现针对他们的特殊预防,尽可能使其不再实施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行刑社会化的方式使罪犯与家庭、与社会链接起来,并最终融入社会之中,实现罪犯的参与性再社会化,使其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实现从犯罪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要实现这种社会身份的转变,社区矫正机构必须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坚持以社区服刑人员的需求为本④,充分激发社区服刑人员的主动性,恢复该群体的社会功能,使其由被动适应社会转变为主动融入社会。重建社区服刑人员的主体性,既是行刑社会化的需要,也是社区服刑人员的现实诉求。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必须要尊重社区服刑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主体性诉求,应当“以肯定罪犯的主体性为前提。”⑤社区矫正机构在制定矫正方案、开展教育学习、进行职业培训等过程中,要给该群体提出个人想法、表达自身需求、诉说个人愿望创造机会,充分发掘与调动社区服刑人员接受教育改造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在此基础上,社区矫正机构要将以往以行刑干警为中心的教育改造模式转变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与罪犯双向互动的教育改造模式。唯有如此,社区服刑人员才可能从外部的强制和威慑、被动服从社会规范和监狱机关要求的状态中走出来,进入一种主动认同并自觉追求和践行的境界⑥,进而重建自身的社会人格,提升自身适应社会的主体意识和能力。
社区服刑人员作为社区矫正互动关系中的参与主体,应当改变自身的客体化身份,将自身视为具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视为对家庭、对社会有责任担当的守法公民。该群体只有积极主动地同社区矫正机构开展良性互动,逐步改变自身“被改造”“被管理”“被教育”的角色定位,努力减少“罪犯”标签的负面影响,才能重新发现自我,重新找回自我,重新拓展适应社会的能力。而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本质上也是实现自我再社会化的过程,是社区服刑人员积极参与矫正教育,主动实现自我改造和自我人格身份再造的过程。同时,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服刑人员主体性的重建,往往还表现为该群体积极主动地将自身面临的生存困境、民生诉求、就业意愿等各类生存发展的权利向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合理化表达。社区矫正机构应当认真倾听社区服刑人员的所愿、所思、所想和所求,及时回应社区服刑人员的主体性诉求,并同该群体一道协商解决他们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样,社区服刑人员在进行社区教育改造的同时,逐渐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身份重建,进而逐渐修复自我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自我的社会认同本身是该群体顺利回归社会的前提,也是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复合型制度在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中的真实体现。
总之,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互动关系兼具单向性与主体性的双重特性。这种双重特征表明,社区矫正既不是完全限制或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监狱矫正的翻版,也不是无条件地将罪犯放在社区而放任自流,而是强调监管教育与再社会化、行刑社会化与民主化、惩罚性与预防性、开放性与社会性、人本性与人道性并重⑦,强调在教育矫正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主体性重建与社会功能的修复并成功融入社会的过程。
澄清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认知的两个误区
当我们理解了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角色定位及其双重特性后,便能澄清两者互动关系的两个认知误区,即“准监狱化”与“福利化”误区。事实上,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关系的认识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深刻理解两者关系间所呈现的单向性与主体性的双重属性。
(一)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准监狱化”认知误区
所谓“准监狱化”认知误区,便是社区矫正机构将社区服刑人员等同于监狱囚犯,将社区矫正视为监禁矫正的翻版,用监禁矫正的理念管理社区服刑人员,并尽可能限制或剥夺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或其他社会权利。这种执法观念由于片面强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治和惩罚,过度突出惩戒性,将社区服刑人员视为刑罚执行的被动对象或工具。由于忽视了行刑社会化和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的现实需要,因此难以实现修复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功能,达到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活动的复合性目标。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一些社区矫正机构由于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及其目标没有形成清晰认识,社区服刑人员的罪犯身份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便成为他们进行监管教育的起点。他们将社区服刑人员所居住的社区空间简单地等同于“没有围墙的监狱”,将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定位为“便衣警察”,将社区矫正工作目标归结为“管得往,跑不了,不出事”。同时,这些基层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类型及其性质一概而论,过分强调社区矫正的管控性、惩罚性而忽视社区矫正的人本性与社会性,在管理方式上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与处罚措施,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严密的监督与管理,在执法方式与执法态度上对社区服刑人员形成一种高压态势,使社区服刑人员逐渐成为被驯服的客体,使该群体丧失基本的自由和表达自身诉求的权利。
在监禁执法理念的影响下,一些社区矫正机构无视社区矫正内含的教育、帮扶与社会关系修复的功能,不愿意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帮扶、促进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关系融合等方面承担责任。部分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工作缺乏明确的工作计划,而且管理和沟通方式十分刻板,甚至在很多方面直接侵犯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权益。例如,有些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无视社区服刑人员面临的现实困难,不愿为他们在社区中遇到的生存问题提供必要帮助;有少部分工作人员甚至借为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困难的契机牟取好处。
因此,部分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间的互动关系呈现监管有余而帮扶缺失、惩治过度而预防性较差、漠视权利而社会化不足等倾向。也就是说,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权力和刑罚惩罚的权力得到充分释放,但其承担的教育帮扶职责则明显弱化。与之相对应,社区服刑人员得到适当教育培训或社会救助的权利则难以切实保障,导致该群体在社区服刑期间的处境更加艰难,再社会化和重新返回社会的能力更加弱化,社区服刑人员的客体化、边缘化地位更加明显。在社区矫正实践中,这种“准监狱化”的刑事执行理念将会使一些社区矫正机构人员形成“宁左毋右”“宁重毋轻”的思维惯性⑧,从而直接强化了他们同社区服刑人员的惩治性关系,并最终导致社区矫正初衷与目标的偏离,使社区矫正的执法工作变得更加封闭保守,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关系因此会变得渐趋紧张并难以维系,行刑社会化与社区服刑人员重返社会的目标更是难以实现。
(二)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福利化”认知误区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福利化”则站在“准监狱化”的对立面。这种错误观念认为,社区矫正是一项社会福利的供给服务,社区矫正机构是社会福利的供给者和福利资源的链接者,而作为弱势群体的社区服刑人员则可以无条件地向社区矫正机构索取福利资源,最终成为社会福利的依赖者。依照这种逻辑,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关系被简化为福利供给与被供给、依赖与被依赖、帮扶与被帮扶的关系。这种“福利化”的认知观念由于一味强调福利救助而忽视社区矫正惩罚的本质,不但会培养大量的福利依赖者、懒汉和无能者,弱化社区服刑人员的责任担当,而且放纵了社区服刑人员的违法行为,降低了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和回归社会的可能性,扭曲了社区矫正的初衷和目标。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部分社区矫正机构将社区矫正视为社会福利的转化形式,他们对刑罚轻缓化与执行方式社会化等措施的认识较为片面。这些工作人员认为,社区服刑人员犯罪行为相对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特别是一些偶犯、初犯、老年犯、过失犯重新犯罪的风险较低,加之有些罪犯是因为不懂法才走上犯罪道路的,因而过于强调对这些人的监督管理措施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有些不合情理。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面对的主要是失业、失学、失地及生活困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当极易导致其在矫正期间违法犯罪。此外,社区矫正机构现有的执法手段与措施还十分有限,若一味严格管理,很可能引起社区服刑人员的不满与抵触,进而影响日常监管与矫正效果。
在这种执法理念的影响下,这些社区矫正机构将珍贵的执法资源过量投入到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思想教育与社会适应性帮扶上,过分夸大心理问题与生活困境对社区服刑人员违法犯罪的影响,将维护社区矫正的正常管理秩序等同于“花钱买平安”。最终,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间的互动关系呈现福利有余而惩罚缺失的倾向,导致实践中出现社区矫正机构“帮扶过了头,罪犯得好处”或“罪犯反而享受特殊照顾”的奇怪现象。因此,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便是过度重视“教育矫治和帮扶救济,社区矫正的惩罚功能严重缺失。”⑨社区矫正机构把无原则的人道主义作为借口,将本处于不同性质的工作职能混淆,轻视社区矫正的惩罚性,不仅导致自身监督管理权力运行受阻,而且从长远看来也不利于社会公众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接纳与认可,不利于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并重返社会。部分社区矫正机构这种职能定位上的偏差,使得其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关系走向“福利化”陷阱,并逐渐偏离正常轨道,最终影响社区矫正目标的实现。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过程中所出现的“准监狱化”与“福利化”的认知困境,反映出人们对两者关系的实质或属性缺乏基本认识。准监狱化将社区矫正视为监禁矫正的翻版,过度强调刑事执行的惩罚性而忽视行刑社会化的必要性和再社会化的重要性,而福利化则过度彰显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救助性和社区服刑人员对矫正机构的无限依赖性而忽视了对罪犯的惩戒性,单纯将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关系简化为福利供给者与接收者,从而否定“社区矫正的惩罚功能。”⑩显然,无论是“准监狱化”还是“福利化”,都无从体现行刑社会化的本质,都无法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治的基础上实现该群体的主体性身份重建进而达至回归社会的目标。要走出这两种认知误区,就需要全面把握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深入理解单向性和主体性这一双重属性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呈现方式与展开过程。
结 语
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的关系介于惩治与服务之间,是社区矫正的基础性关系。如何准确界定和理解两者关系的基本属性,是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常态化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社区矫正实践中,两者之关系定位是否明确,边界是否清晰,都会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的实践效果。笔者从单向性与主体性两个维度,对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双重属性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辨识和澄清了两者关系的“准监狱化”与“福利化”的认知误区。尽管社区矫正工作经历了先行试点、扩大试点、全面试行到整体推进等阶段,但迄今为止对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特征还未形成共识。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由于缺乏基本共识,致使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常常在“准监狱化”与“福利化”之间左右摇摆,进而直接影响到矫正方式的抉择与行刑社会化目标的具体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认清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互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不仅有助于澄清当前两者关系的认知误区,而且为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矫正关系,实现社区矫正惩罚性、预防性、社会化、人本化等复合型目标明晰了方向。伴随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常态化运行,从理论和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晰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服刑人员之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①王志亮:《论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特点》,《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②张昱:《论复合型社区矫正制度》,《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
③郑杭生、程琥:《法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④张昱、费梅苹:《社区矫正制度的社会学视野》,《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⑤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法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⑥李畅:《论罪犯自我改造的主体性》,《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⑦屈学武:《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设计及其践行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⑧郭星华、李飞:《制度移植与本土适应:社区矫正本土化面临的困境》,《中州学刊》2013年第8期。
⑨武玉红:《社区矫正的惩罚性不容忽视》,《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
⑩武玉红:《社区矫正管理模式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