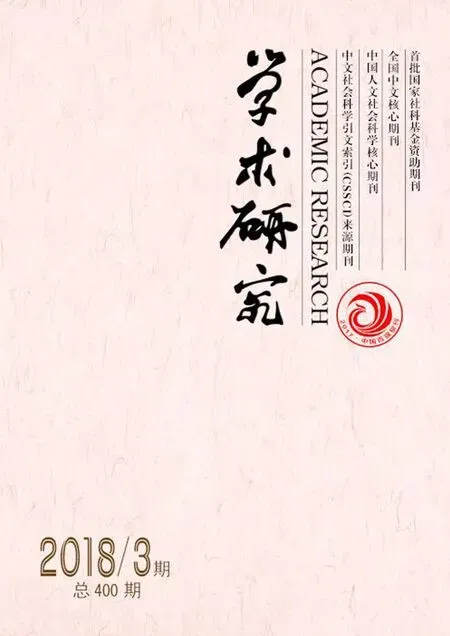医术的本质:亚里士多德与现象学传统*
陈治国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及其支配下的一般科学技术观念中,医术往往被奉作与数学、物理学等理论学科等量齐观的精确科学;医术的对象是疾病,其任务是控制、抵御疾病对身体的入侵和伤害;作为医疗主体的医生和医院则是不容挑战和质疑的专业性权威;医术水平的进展是无止境的,一切身体上的病变最终都有完全被攻克的医学可能,如此等等。针对这些广泛流行的医术“常识”或“命题”,本文拟从亚里士多德以及有其深刻烙印的现象学传统——这里以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为重心——的视野,重新探究医术的真正本质,以期激发各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并逐步扭转诸多医术理解与认知上的重大偏差。首先,围绕《形而上学》《物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等基本著作,揭示亚里士多德对作为自然物的身体及其健康的定位、对医术活动的学科性质及其特征的理解;其次,通过考察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灵魂观、身体观和自然观的重新解读,以及身体问题在其哲学中的主要发展线索,阐明他在现象学视野下对现代医术的深刻认知和界定;再次,进一步探究处于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双重影响下的伽达默尔,在诠释学的现象学视域下对医术及其与身体健康之关系的分析和反思。
一、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物的身体与作为创制科学的医术
毋庸讳言,医术在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哲学探究中从未成为直接而明确的独立主题。可是,无论在《形而上学》《物理学》,还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灵魂论》等作品中,医术却一再映入哲学家的眼帘。个中原因,不仅在于医术——同今日情况一样——与每一人类个体的安康福祉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一种特别的含混性:一方面,医术对象乃是作为自然物的身体;另一方面,探究并看护这一自然性身体的医术在根本上又属于创制科学的范围,而不是理论科学或实践科学。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所有现实世界的事物可分为两类,一者是自然物(phusei onta),另一者是技术(技艺)物或人工物(poioumena):“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的本原。反之,床、衣服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事物,就它们接纳了这些名称规定而言,亦即,就它们是技艺产物而言,都没有这样一个内在的变化的冲动力。”(Physics, 192b12-20)a本文所引亚里士多德原始文献主要依据:Aristot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192b12-20。凡出自该文献的引文,仅以夹注形式标注作品名称及贝克标准码。这就是说,是否在自身之内具有动静的本原(arche)和原因(aitia),构成了自然物和技术物相区分的基本依据。这里,亚里士多德似乎特别强调生成意义上的“动力因”这一非人力、非技术的“自然”特征。实际上,自然物作为“由于自身”(kath hauto)、“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它的“自然”(phusis)包括四重含义:作为质料的自然、作为形式的自然、作为动力的自然以及作为目的的自然。(Physics, 193a10-b20, 194a28-29)所以,就“人”这种自然性实体而言,他是灵魂(形式)和身体(质料)的复合体。b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写道,作为“拥有器官的自然物的第一现实性”,“灵魂不是身体,但它是与身体相关的某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在身体之中,并且在某种特定种类的身体之中”。参见Aristotle, De Anima, 412b5-6,414a20-22。可是,就活的身体(lived-body)本身而言,它也是一种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实体:血液、骨骼等器官是质料因,各器官及其组成部分或元素之间的天然平衡结构是形式因,c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将身体的健康看做身体内部冷和热、干与湿等自然元素之间的一种平衡或中道状态(meson)。参见 Aristotle, 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334b22-30。趋向于作为这种平衡的健康或积极存活状态是动力因,而健康或积极存活状态的实现是目的因。在此意义上,身体显然属于在一种“由于自然”而存在的自然物。
不过,作为自然物的身体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它的平衡状态有可能被打破,从而失去健康。在此情形下,医术的介入就必不可少。医术的介入旨在通过治疗来恢复身体的健康。在此过程中,身体及其健康的根据就出现一种新的变化:身体健康的动力看起来不再是身体的内在“趋于健康”,而是外在于身体的“医术”。医术通过一系列操作程序或中介性事物在身体中重新产生健康。并且,由于医术的功能就是研究健康或如何恢复健康,作为动力因的医术与作为形式因的健康就是同一的:“健康、疾病、身体;动力因是医术……砖头,动力因是建筑术……在某种意义上,医术就是健康,建筑术就是房屋的形式,而人是人所生。”(Metaphysics, 1070b28-33)
当亚里士多德把失去健康的身体的动力因——以及形式因——归结为外在于身体这一自然物的医术,他也就把医术推入了创制科学的范围。根据研究对象以及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确定性程度,亚里士多德将所有知识划分为三类: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Metaphysics, 1025b1-1026a32)理论科学主要研究必然、永恒的事物,或者在其自身内拥有运动静止之源泉的事物,这种研究能够获得高度确定性,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思辨活动,包括数学、物理学(自然哲学)、神学(形而上学)。实践科学主要探究人类可变的行为(praxis),即伦理性、政治性的实践事务,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等,这类探究的目的虽然蕴含在行为之中,但只能获得一定意义上的确定性知识。而创制科学主要包括文学艺术、技艺制造等模仿性或使用性的活动,其目的是外在于活动过程的产品,这类科学知识确定性最差。
创制性知识突出的不确定性特征大致可归结于三个原因。第一,创制科学尽管也涉及普遍的东西,但是,主要研究模式是普遍性知识的具体运用,对具体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声称,作为创制科学的技艺(techne)——相比于单纯经验——与理论科学具有更多相通之处,即“知道原因”“可以传授”(Metaphysics, 981a26-b10)等。可是,他也明确认识到,“除非在巧合的意义上,医生并不治疗人,而是治疗卡利亚斯、苏格拉底,或者通过这般个体名称来称谓的其他人,他恰巧是一个人。那么,如果一个人只有理论而无经验,知道普遍而不懂其中的个别,他就要屡遭失败。因为,正是个体有待于去治疗”。(Metaphysics, 981a17-24)由于医术这样的创制科学主要适用于具体的对象,具体对象总是千差万别,所以它的真实效果就会多样不一。
第二,创制科学所依据的灵魂能力是制作理性,即与制作(poiesis)相关的逻各斯(logos),(Nicomachean Ethics, 1140a9)这种理性能力——其德性就是所谓的“技艺”——的运用与发挥,同意见、情感、想象等非理性能力紧密相关,较少受到现实世界之必然性或自然性事物的制约,所以它所获得的知识就具有较高的偶然性。“技艺同关乎真实的推理过程的制作之品质是一回事情。所有的技艺都涉及生成,亦即,涉及构想和思考如何去生成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并且这些事物的始因处于制作者之中而不是处于被制作物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运气和技艺是相关于同样的对象……正如阿加松(Agathon)所言:‘技艺钟爱运气,运气钟爱技艺。’”(Nicomachean Ethics, 1140a8-20)
第三,由于在创制科学中,技艺活动不是自足的,即技艺活动的目的(telos)一般是外在于其过程本身,并且达到这一外在目的是其所有的价值所在,因此,技艺活动的手段就多种多样,甚至“不受约束”——除了目的。这一点再次突出地体现于身体的健康这一医术主题上。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三章阐述“目的因”时写道:“在目的或所为者的意义上,例如,健康就是散步的原因……同样,由别的行为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而施行的一切中间措施,例如,肉体消瘦法、倾斜法、药物或外科器械等等,都是达到健康的手段。尽管它们彼此有别,有的是行为,有的是工具,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目的”。(Physics, 194b33-195a2)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失去健康的身体之动力因“转移”到了医术,并且在医术专门研究健康的意义上,它也是身体的“形式”,可是,医术绝不是自主的、自足的,不能凌驾于始终作为目的的“健康”之上。它必须服务于身体的健康,而不能以健康为手段或者向健康发号施令。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多个地方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说:“健康的主体不能说是一个失健的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人”,(Metaphysics, 1033a12-13)“医术并不优越于健康。因为,医术并不役使健康,而是为健康的生成提供服务。它为健康,而不是向健康,发布命令”。(Nicomachean Ethics, 1145a8-10)
让我们重述一下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医术及其与身体和健康的关系。首先,医术的对象是作为自然物的身体,但是在知识类型上,它作为技艺,属于创制科学。其次,属于创制科学的医术这种技艺,在本性上鉴于其作用领域、能力依据以及活动特征,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再次,医术虽然构成了失健之身体的动力因、形式因,但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服务于“人的健康”这一根本目的,而不是与健康讨价还价或向健康发号施令。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医术以及身体的健康这种理解,后来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代表的当代现象学传统中得到了重新的关注、运用以及适当的更新。
二、海德格尔:身体的自身康复与医术治疗之交叉运动
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在其承继胡塞尔现象学并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阅读和研究而发展出一种此在的现象学或基础存在论的十年(1917—1927)努力中,海德格尔并没有专门讨论医术问题,但是以相当特殊的方式涉及“身体”问题。首先,在1924年夏季学期讲稿《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明确把“身体性存在”看做人类此在之基本存在方式的一种核心规定。而这种思路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灵魂理论中的nous(理智、纯粹理性)和pathos(情感、感受)这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展开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中,“灵魂的活动”与“身体的活动”无法分割,而作为人的灵魂中特有部分的nous却被认为是“分离的”,不过,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人的思考(noein)并不纯粹。设想我在此并不真实拥有的某物,这植根于想象力(phantasia),并且只有立足于再现(Vergegenwärtigen)才是可能的,而再现不过是曾经当前之物的重演(Wiederholung),是对一种过去了的当前的重演。”由于想象或想象力属于我们的一种感知能力,并且感知(aisthanesthai)“不是理论思考,而是对围绕我的某物敞开”,是“此在拥有世界意义上的感知”,所以,海德格尔推论说,“想象是思考(noein)的基础。就思想(noesis)是之人存在的最高可能性而言,人的全部存在是规定了的,以至于这种全部存在必须理解为人的身体性‘在世界之中存在’”。aM. Heidegger, Grundbegrif f 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2, S.202,199, 199.
就pathos(情感、感受)而言,海德格尔也采取了一种扩展性的解读策略。情感或情绪作为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结构中非理性部分的重要内容,其活动方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可变性、被动性,不同于出自理智能力的主动性之行为(praxis)。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有些时候当我们陷入某种情感、情绪之际,明显受到了在世界中所照面的事物或境遇的强力牵动,但有些时候并不全然如此。譬如,当我们陷入某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之际,并没有真正碰到令人可怕的具体事物,这表明,一定程度上,恐惧是在我们自身之内涌现出来的,恐惧和和焦虑的可能性是在我们的存在中被共同给予(mitgegeben)的。进而,海德格尔断言说:“实际上,身体性也在情感活动(pathe)之生成(genesis)中有所言说(mitspricht)。”bM. Heidegger, Grundbegrif f 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2, S.203.
依据这种解读,具有感知性以及部分原生主动性的身体,就不能被拒斥于此在的生存论建构之外,即“源初的身体性之此在功能(Daseinfunktion)为人的完整存在奠定了基础”。确实,依据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野,富有意义的身体并不是心理/生理二元区分中的机械性物体,一般所谓的焦虑、愉快等“身体状态”也不是内心状态的外在附随表现,而是作为有生命之物的存在者一种整体性情状,属于人的“特殊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出自我们的身体性存在的情绪或感受(pathos),或多或少总是同我们已经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之其他事物相关联,人类此在本身就产生了“其着迷(Mitgenommenwerden)的可能性和方式”。换言之,由于情绪或感受就是“作为人类此在之在其全部身体性的在世界之中存在(in seinem vollen leiblichen In-der-Welt-sein)的着迷”,cM. Heidegger, Grundbegrif f 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2, S.199,198, 197, 198.人类此在就总是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包含着其他存在者的共同世界,并且不可避免要通过自身来筹划它自己的安置方式、交道方式等。
海德格尔对身体(Leib)或身体性(Leiblichkeit)在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层次上的这种分析,在稍后的《存在与时间》中却发生了不声不响的一种“变化”。一方面,与身体息息相关的pathos(情绪、感受)通过“现身情态”(Bedf i ndlichkeit)这一概念得以保存,作为实际的被抛状态,现身情态既是此在的生存论结构的三重基础性环节之一——其他两者分别是理解(Verstehen)和言谈(Rede),同时作为此在的“着迷”也是其非本真存在的源头。另一方面,“身体”这一概念本身却很少再被公开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情形。一者是海德格尔经常在消极的意义上,批评笛卡尔式无生命的、机械的、单纯空间性的自然化身体,一者是他频繁地使用“上手之物”(das Zuhandene)、“在手之物”(das Vorhandene)、“倾听”(Hören)等具有明显身体意象的概念。这种含混的身体图景,已经引发了海德格尔学界内外的各种争论。偏于批评性的解释是,《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纯粹是一种无身体的、形式化的先验主体,这既反映了海德格尔在身体问题上的“盲目”,也是其基础存在论无法最终完成下去的重要根由。aTina Chanter,“The Problematic Normative Assumptions of Heidegger’s Ontology”,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Martin Heidegger, ed. by N. Holland and P. Huntingt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73-108.偏于同情性的解释是,由于身体现象从属于世界现象,在世界结构得到阐明之前,“此在身体本性的整个问题框架就依然是隐蔽着的”。b参 见 David R. Cerbone,“Heidegger and Dasein’s‘Bodily Nature’:What is the Hidden Problematic?”,Heidegger Reexamined, Vol. I, Dasein, Authenticity, and Death,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Hubert Dreyfus and Mark Wrathall,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85-106.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尤其是基础存在论中身体问题的相关争论,可进一步参见Dider Frank,“Being and the Living”,Heidegger Reexamined, Vol. I, pp.107-120; J. Derrida,“Sexual Difference, Ontological Difference”,Heidegger Reexamined, Vol. I, pp.157-176; David F. Krell, Daimon Life: Heidegger and Life-philosoph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Kevin A. Aho, Heidegger’s Neglect of the Bod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基于这里的探讨主题,我们无暇深度介入这场争论,可以概略地给出以下三点理解,从而允许我们继续回到当前主要问题上来,即海德格尔现象学视野中身体与医术的关系以及医术的本质等。
第一,由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完全专注于从时间角度来阐释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并且渗透着浓厚的康德式先验主义气息,所以,在其明显形式化的此在之生存论结构中,无论如何总是具有某种场所或位置特征的身体,很难继续占据一种显著的存在论地位。c刘国英:《肉身、空间性与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肉身主体的地位问题及其引起的困难》,《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四):现象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53-77页。
第二,逐渐被虢夺了存在论地位的身体,在存在者层次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分量。一方面,毫无疑问,《存在与时间》中的上手、在手、手势(Gebarde)等概念仍然预设或蕴含着一种必然的身体性存在。不过,这种“身体性存在”不能从一种单纯现成实体的角度来理解,而是要从一种生成的、运动的角度来审度。海德格尔在1972年同瑞士心理学家鲍施(Medard Boss)的一次交谈中,曾这样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能在《存在与时间》中主题性地探讨“身体”这一最大难题:“因为我们具有眼睛,我们不能‘观视’,毋宁说,由于按照我们的基本本性,我们作为可以观视的存在者到场,我们才具有眼睛。同样,我们不能在存在方式上是身体性的(leiblich),除非我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向来已经在根本上蕴含着对临访我们的东西之感知性/接受性的关联,这种东西出自于我们世界的敞开域,我们就是作为敞开域而生存着。”dM. Heidegger, Zollikoner Seminar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S.293-294.按照这种解释,关键不是先行刻意地直接瞄准给定的身体进行解析,而是在它一系列自然而然的功能性活动中,“身体”才真正“存在起来”。
另一方面,“身体”这种不容事先觉察的隐匿性存在方式,同作为用具(Zeug)的技术物具有很大相似之处。e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用具”概念虽然也包含自然物,但主要涉及的是技术物,并且明显按照制作模式来谈论自然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区分了此在于周围世界中所照面的存在者的两种存在方式,即在手之物和上手之物。所谓上手之物,是指事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通常以“用具”的方式在某种隐匿中围绕着我们。“上手之物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的……切近的上手之物的特性就在于,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隐退起来(zurückzuziehen),以便于真正地上手。日常切近地打交道的东西也并非居留于工具本身。”f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76, S.69.在这里,海德格尔虽然主要描述的是一般工具或器物等技术物的上手存在,实际上这也适用于身体。亦即,当我们的“身体”正常地发挥其适当功能之际,它就是作为用具透明不显的。相反,当我们不能清楚地看见事物或无法自然地扭动脖颈之际,我们的身体才会格外醒目地作为现成对象进入视野。所以,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在海德格尔那里,身体和工具一样,在其日常致用中都有一种自身隐匿的倾向。gDavid R. Cerbone,“Heidegger and Dasein’s‘Bodily Nature’:What is the Hidden Problematic?”,Heidegger Reexamined, Vol. I, Dasein, Authenticity, and Death,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Hubert Dreyfus and Mark Wrathall, New York:Routledge, 2002, pp.85-106.
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身体或身体性也构成了此在的存在论层次和存在者层次两种状态之间的枢纽。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作为此在的生存论建构的基本环节之一,现身情态在生存状态上的重要表现就是同身体相关的诸种情绪,而各种具体情绪现象不仅表明此在本身总是已经被抛于世界中的某个此(Da)处,而且也把世界中其他存在者作为对此在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东西揭示出来。这种情形从存在论上来讲就是,“现身情态包含有一种不断开展着的对世界的托付,从这种托付中我们才能与关系着我们的利害的东西相照面”。a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76, S.137.当然,就我们的身体性此在总是有其处境、具体的感情以及作为遭受性或反应性的情绪而言,它实际上蕴含着无尽的生存可能性。同时,由于此在在存在论状态上的特殊存在方式乃是“超越”(Transzendenz),即通过理解性的筹划向着这种或那种生存可能性去充实自身,并且这种超越既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一种有限的选择活动——在某种确定的可能性领域进行筹划永远无法涵盖整个的可能性领域。所以,这就意味着:以身体性存在为起点和依据的此在,其生存论上的超越行动,要不断回溯到它试图逾越的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身体性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承认的那样,“只要此在存在,此在作为操心就总是它的‘它存在且不得不在’。此在托付给了这个存在者,它只有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才能生存,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此在生存着就是它能在的根据,虽然此在不曾自己设置这根据,但它依栖在这根据的重量上,情绪把这重量作为负担向此在公开出来”。b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76, S.284.关于这一点,他在《赫拉克利特研讨课》(1966/1967)中讲得更为直接而清晰:“人迥异于所有其他存在者……就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而言,他也具有另一种存在品格,通过这种品格,他嵌于幽暗的根基。他拥有双重的品格:一方面他是把自身置于澄明之中的存在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被闭锁在澄明的深渊根据(underground)中的存在者”,而“这一点只有首先通过身体现象才是可理解的”。cM. Heidegger & Fink, Heraclitus Seminar, trans. C. Seiber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5.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海德格尔开始着力在“后存在论”(Metontologie)的名义下,从存在者层次来进一步阐明此在在存在问题上的优先性根据,并更为公开而广泛地讨论身体问题。
不过,虽然此在现象学或基础存在论之后的中晚期海德格尔哲学多处谈及身体,基于这里的主题限制,我们主要把目光瞄准他1939年的著名论文《论Φύσις的本质和概念——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在这篇文章中,鉴于他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主体形而上学的亲缘关系的深刻体味,以及对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希腊自然观的重新解读,海德格尔明确地阐述了自然性身体与作为现代技术的医术之间的牵连与区分。如上所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固然也在一种生成的意义上论及身体的隐匿性,但是很大程度上以类比方式隐约地将它与一般的技术物相提并论,现在他坚决地要求承认作为自然的身体之不可还原和替代的自主性。换言之,任何时候,作为技术或技艺的医术都不应无节制地去支配身体,而是要顺应、配合身体本身的自然运动。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再次涉及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解读。
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亚里士多德曾讲到一种医者自医的特殊现象。“自然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我说‘不是由于偶性’,是因为(譬如)一位医生或许本身就是他自己康复的原因。不过,他并不是作为患者而成为具有医疗技艺的人:医生和患者同属一人纯系偶然。正因如此,这两种属性常常难以一起出现。其他所有的技艺产品也是如此。没有一件技艺产品在其自身中拥有它自己的制作本原。然而,尽管有些情形下(譬如房屋和其他手工制品),本原外在于事物,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即在事物自身中偶然地引发一种运动变化,本原就处于那些事物本身之中(但是并非由于它们自身)。”(Physics, 192b22-32)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即一个正常的身体“由于自然”而拥有健康,但是,当他失去健康之际,医术的介入就是必要的。并且,尽管他在其他地方曾强调,健康这一形式的“缺失”(steresis)也可能构成身体的一种特殊形式,(Physics, 193b19-20)身体的健康这一目的也必定位于医术这一技艺活动之外,可是他仍然很大程度上把失去健康的身体之动力因归结于医术。而海德格尔基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在“机巧”(Machenschaft)模式下对身体之类自然物的强力控制和主宰,格外强调医者自医活动中作为自然(物)的身体之不可随意支配和驾驭的内在特质。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在医者自医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相互交叉的两种运动方式:作为技术(技艺)的医术治疗和作为自然(phusis)的康复活动。染病的“医生”在自身之中具有健康的本原,但这不是按照本身(kath auton),不是因为他是医生。换言之,“是—医生”(Artsein)不是康复的真正开端支配(ausgängliche Verfügung),即自然或本原,开端支配乃是在于“是—人”(Menshein)。“是医生”或者说“医生之存在”,虽然是医疗活动的开端支配,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具有抵抗能力的自然(Natur),它才是身体康复活动的真正开端支配,没有这种内在的本原(arche),一切医疗活动都是徒劳无功的。就医疗活动中医生需要精通医术和健康知识而言,这也完全是后天习得的,不会像树木或身体那样自然生长,并且具有偶然性;它在身体康复中的作用,主要是辅助具有抵抗力的身体去阻抗不利因素的干扰,而不能完全无视身体自身那种趋于健康的内在能力。所以,海德格尔断言说:“techne只能迎合phusis,能够或多或少地促进康复;但作为techne它决不能代替phusis,决不能取而代之成为健康本身的arche。也许只有当生命本身成了一种技术上可制作的技术物,才会发生那种情形。然而,在那一时刻,也就不再有健康这一回事情了,同样也没有什么生和死了。”aM. Heidegger,“Vom Wesen und Begrif f der Φύσις. Aristoteles, Physik B, 1”,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 S.257.另外,由于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中晚期作品中,海德格尔经常直接将“自然”看做“存在”,而存在乃是自行遮蔽着的解蔽(das sich verbergende Entberegen)之二重性运作,b关于这一点,可进一步参见陈治国:《论海德格尔的“四重体”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5期。所以,作为自然物的身体任何情况下也都有其自行遮蔽的一种面向,它是任何高明的医术都无法彻底照亮的和解蔽的,尽管医术之技艺也是一种事物的解蔽方式。
三、伽达默尔:实践理性之反思框架下的医术与人的健康
同样以亚里士多德为重要思想源泉并深受前期海德格尔影响的伽达默尔,在其诠释学的现象学或辩证—对话的现象学脉络中,一方面承认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重要部分的医术在现实生活中的明显成就,另一方面也坚决要求深刻反思近现代医术无法自我觉识的盲点和误区。
首先,立足于亚里士多德在身心观上的形式质料说(hylomorphism),伽达默尔重申身体对于人类个体的存在论地位,以及人类个体性存在的整体性特征。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现代技术的医术,它的知识来源于科学实验,而科学实验总是以量化研究的模式来处理身体,并且这种身体乃是一种机械的、非个体的(impersonal)“物体”。当这种科学性的医术知识直接运用于“此时此地”面临生与死的人类个体情形之际,它的风险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每一人类个体,就其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而言,他或她从来都不是自我分离或分裂的存在。伽达默尔写道:“我们也许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没有将身体同时经验为某种活的事物和趋于衰退的事物,有关灵魂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对灵魂的任何讨论——是否可以涌现出来。也许,即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亚里士多德仍然是正确的,当他讲道:灵魂不过是身体的生命特征,所谓entelecheia之充实的自我实现的形式。”这就是说,在任何状态或条件下,作为有生命之物,我们人类个体既不是单纯以“灵魂”在世,也不是单纯以“身体”现身,而是“完全地在场”。cHans-Georg Gadamer,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 i c Age, trans.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1, 149.按照这种人类存在方式,我们就必须坚决地追问,仅仅以无差别的对象化之物——不管它是无生命的人类躯体还是大批的医学试验动物——为根据的医术知识,再次以无差别的方式运用于每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类个体之际,它的效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充分保障的?
其次,伽达默尔接续海德格尔在此在现象学或基础存在论中对身体隐匿性特征的洞察,进一步阐述了身体之健康的隐匿性品格。如前所述,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很大程度上似乎倾向于把人类此在的身体作为一种用具来经验,并且这种用具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具有明显的隐匿性特征。伽达默尔虽然没有接受此一时期海德格尔从技术物角度理解身体性经验的具体方式,但是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身体——或者更直接地说,身体之健康——的自我隐匿品格。他讲道:“毫无疑问,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我们本性的一个构成部分就是,我们自觉的自我意识很大程度上保留在背景中,以致我们对良好健康的安享不断地从我们这里隐匿不见。然而,尽管有其隐匿特征,健康恰恰在对安康(well-being)的总体感觉中显示自身。它首先在这样一种事态里显明自身,即如此这般的安康之感受意味着,我们向新的事物保持开放,准备开展新的事业,忘却了我们自身,几乎没有注意到加于我们身上的诸种要求和压力。这就是健康的实质。”aHans-Georg Gadamer,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 i c Age, trans.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2.
身体的健康之隐匿性品格,决定了我们很难将它作为一个现成对象来予以恰当把握:当身体之健康进入我们的视野之际,也就是我们的健康消弭不见从而成为“有问题的”东西。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深刻地体现了身体以及身体之健康同自然或世界整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旦那种不受干预的、自在而顺畅的联系发生失衡或遭受过度干预,身体就会发生“颠簸”,其健康状态就会成为问题。所以,当医生对失去本然的平衡或节奏的身体展开治疗之际,必须认识到,健康首先不是与某种实在性的疾病有关,而是与我们身体那种原始的“适当平衡或协调”有关。同时,我们自身也必须认识到,“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一个部分,并通过受自然支配而与自然对立”。bHans-Georg Gadamer,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 fi c Age, trans.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7, 116.这就是说,无论是病人自身的自我痊愈,还是医术的辅助性治疗活动,都不能企图以完全对抗的姿态去控制身体的诸种运动和变化,而是以更恰当的方式去促进身体的节奏或平衡之重建。伽达默尔曾以轻松而又意味深长的笔调写道:“健康不是一个人在其自身中内省地感受到的状态。毋宁说,它是一种在此(Da-sein)状态,一种在语词中存在的状态,与人类伙伴一起存在的状态,积极馈赠地参与日常事务的状态,它就是生命的韵律,一种重建平衡的持久过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想一下呼吸、消化和睡眠的过程。”cHans-Georg Gadamer,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 i c Age, trans.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3-114.
再次,基于人类此在之存在方式上的统一性(有生命的人类存在者总是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体),以及每一个体性此在与自然整体或世界整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人类总是属于自然或世界的一个内在构成性部分),伽达默尔进一步要求把医术活动置入实践理性的反思模式之中。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在把人类知识划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的过程中,为三种知识活动分别指派了不同的人类官能及其德性,即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创制性技艺。其中,实践理性的功能方式是考虑或慎思(bouleuesthai,deliberation)。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考虑有时候被简单地看做对达成某种目的的正确手段的计算或推算(logizesthai),有时候又涉及对目的本身以及人类生活中各种成分的秩序之安排。而伽达默尔在阅读亚里士多德之际,明确地直接将bouleuesthai译解为更宽泛意义上的反思(Überlegung,ref l ection),d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VI, herausgegeben und übersetzt von Hans-Georg Gadamer, 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1998, S.27.这种反思既是对具体处境中各种要素的敏感把握,也能够把目的知识和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作为这种实践性反思活动之德性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也不仅仅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单纯属于实践理性的德性,甚至次于理论理性的德性即理论智慧,而是说,它就是理智德性总体,或者说,是人之一般德性(virtue of the human being in general),乃至最高的人类德性。与此相比,作为“精通某事”(Sachkundigkeit)aAristoteles, Nikomachische Ethik VI, herausgegeben und übersetzt von Hans-Georg Gadamer, 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1998, S.29.的技艺,由于是制作上的理性能力状态,并且其目的外在于活动本身,所以它不是自主的,不能成为一种德性,而是必须受到德性即实践智慧的指引和制约。
按此情形,作为技术(技艺)的医术必须纳入实践理性的反思模式之下。第一,由于健康属于整体性人类此在的一种身体性经验,医术治疗过程中医生对问医者的感知,就不能仅仅限于物质性身体的某些症状,而是要扩充到对其一般性的个人生活方式与生存经验的感知和把握。后者显然属于实践理性的活动范围。bHans-Georg Gadamer,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 i c Age, trans.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9.第二,由于每一人类个体都具有某种不可还原的自主性和差异性,医术治疗过程中医生还必须真正尊重问医者或求医者的他在性,即不是将他或她看做一个无关痛痒的“病例”(case),而是看做一个真正自主、独立的人格(person)。伽达默尔写道,医生想要很好地治疗一个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他者的他性(otherness),而不是与之相反,去寻求受现代技术推动的标准化的倾向、学校的权威,或者盲目坚持教师或家长的权威的专制控制。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有希望提供名副其实的指导,帮助他人找到他们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每一人类个体自身首先对自己的健康始终具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的进步一直伴随着我们不断降低对健康的普遍关心和对预防医学的日趋忽视”。cHans-Georg Gadamer,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 i c Age, trans.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9, 106.第三,鉴于健康深深地涉及身体性此在与其所从属的自然以及世界整体之间的微妙平衡和协调,这也多少意味着,自然本身的安宁,以及社会—世界的康宁,都必将以某种不可避免的方式牵涉或左右着人类此在自身之健康。而这些问题,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作为中立性技术的现代医术的能力范围,它们更多地属于实践理性之反思活动的任务。正是在上述三点意义上,伽达默尔明确地主张,“要把技术及其能力划入并归属于实践知识以及实践之中”。dHans-Georg Gadamer,“Burger zweier Welten”,Hermeneutik im Rückblick,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5, S.234.
总之,从亚里士多德以及深受其哲学恩惠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现象学传统来看,基于近现代一般性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技术观念的医术理解与认知,在很多方面都是大可追问的,或者说具有十分严重的褊狭倾向。概略而言,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医术的对象是作为自然物的身体,但是由于医术本身作为技艺属于创制科学,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健康这一根本目的。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技艺的医术和作为自然的身体,在人的康复活动中具有某种交织性,但是前者永远无法代替后者,医术对于在根本上具有运动尤其是自我遮蔽之倾向的自然性身体,只能发挥一种配合与支持的功能。伽达默尔在综合性继承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不仅继续强调医术相对于自然性身体的服务性、参与性地位,强调医术远不止于对医学知识的简单运用,而且要求在实践性反思的框架中来运用医术,即医术属于一种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人类生存经验。总之,按照亚里士多德和现象学传统,人类身体的健康虽然关乎医术,但是首先关乎自然、关乎整体性的人之存在,乃至我们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实践性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