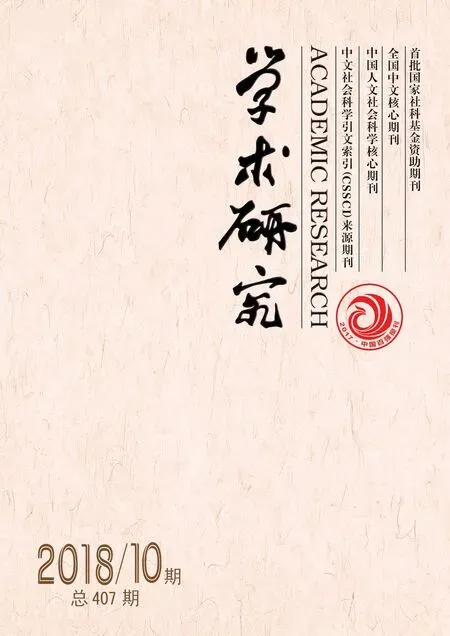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家庭伦理观对比刍议*
黄其洪 姚 亮
目前学术界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家庭伦理观的关系的研究,往往站在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抽象对立的立场上,只关注二者在宏观上的一般差别。例如有学者提出,黑格尔在考察家庭伦理问题时,只是提出一套抽象的家庭伦理生活观,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家庭伦理观是颠倒与抽象的,必须在唯物主义世界中获得改造,确立科学的家庭伦理观,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是家庭生活而不是家庭概念。a吴苑华:《家庭伦理:黒格尔与马克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7年第1期。诚然,从本质上看,二者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是造成其家庭伦理观相差别的根本原因。但如果仅仅关注体系上的对立,而忽视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婚姻家庭伦理各环节上的相同点、细微差别以及造成这种差别的客观原因,那么,基于这种抽象对立的论证,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确定不移的,实际上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并无益处。为了解决当代的家庭危机,需要的是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而不是僵化的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因为实践问题遵循的是一种复合的逻辑,而非单纯的理论逻辑。
一、黑格尔与马克思家庭伦理观的异同
在具体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家庭伦理观的异同之前,首先应摈弃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即认为黑格尔只承认概念上的家庭伦理观,而没有包含实践意义上的家庭生活本身;而马克思的家庭观,则是放置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中来讨论的,只有马克思的家庭伦理观才具有现实感,才与物质世界相关联。我们应该看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家庭伦理观都是具有现实感的,二者之间真正的差异绝对不是所谓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差异,而是表现为一些具体原则和观点的差异,而且二者之间的相同点可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多,这些异同需要我们结合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细致的比较。
(一)“爱”与婚姻:主观性环节的异同
黑格尔认为,“爱”是家庭这个直接性伦理实体的关键性规定,它有三个重要内涵。首先,爱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作为精神主体对自身统一的感觉,但这种统一感觉又只能通过放弃自身的抽象独立性、在追求与他人统一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这种放弃就是自主的、有意识的让渡,并在与对方的交往中获得与自我统一的感觉:所谓爱,“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a[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5页。其次,爱以客观关系为对象,爱这种自我意识不是抽象与空无内容的意识,它是对“自我与别一个人在团结、协作与义务等客观关系上”的自觉意识。这种通过抛弃抽象自我的外在个性、独立性、自由与权力等,在与他人的统一中获得自我确证与存在意识的爱,体现出“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层次跃迁,它扬弃了那种“特异化”、“主观任意”的爱慕,上升为一种“伦理性的爱”。再次,这种伦理性的爱作为一种直接实体,本身统摄了各种行为并体现在具体的相互统一、相互关爱、相互成就的行为与实践中。家庭成员的爱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它在家庭实体中表现为恩爱、信任、互助的行为,以及个体在家庭生活中的实存,而这正是家庭与婚姻的本质方面;婚姻是具有法权意义的伦理之爱,而婚礼则是完成家庭这个伦理实体的神圣环节,是婚姻升华为伦理关系的确证。
马克思认为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与最自然的关系,要建立起作为真正人的伦理之爱,就应当尊重个体独立人格:“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b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另一方面,人的感觉与爱,都是通过对象性关系来实现自身的感性占有,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人只有在对象中才不致丧失自身,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正因如此,“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c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6页。这种对象化逻辑与黑格尔主张的爱的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同样,伦理之爱也应统摄互助、互爱、信任与自觉履行义务等行为:“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d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6页。黑格尔认为,伦理的爱是其概念及其现实化的过程性统一,个体抛弃抽象独立性去追求与他人统一的过程中,精神的主体就能够自在地与自身统一起来。而马克思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之爱,被私有财产关系及抽象个人意识所阻断,无法形成“完整的回路”,即在放弃个体抽象独立性追求与对方统一过程中,精神主体无法获得与自身统一,也就无法获得互爱互助、信任与个体实存感。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家庭建立的基础是私有财产,从表面上看似乎全民拥有建立、保护与延续家庭的“平等权力”,然而实质上只有资产者拥有建立、保护与延续家庭的“实际能力”,即充分的经济实力与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家庭关系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间实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家庭成员之间主观环节的爱,被客观环节的财产私有这种异化关系所遮蔽:这才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家庭的客观性环节上的真正分歧。
(二)财产与权力:客观性环节的异同
在黑格尔看来,财产与权力是家庭生活中所包含的客观性维度。物质生活中包含的那些客观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家庭统一与解体阶段,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自由的定在”:一是在由爱维系的家庭统一阶段,财产与权力表现为个人在统一体中的物质生活,共同分配权,它是一种积极自由(free to)与肯定性的义务;二是在家庭解体阶段,财产与权力演变为“特定单一性的抽象环节”,并对统一体采取一种外在对抗的形式,它是一种消极自由(free from)与否定性的权力,表现为对地产、生活费与教育费等的分割。aDavid James,“Subjective Freedom and Necessity in Hegel’s‘Philosophy of Right’”,Theoria: 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2012(3).家庭因为前一种定在维护着它的统一性与排他性,反对家庭的解体与成员退出;但是,一旦丧失了“爱”,家庭必然走向解体,财产与权力这种定在将无能为力,因为爱才是维系家庭实体的本质方面。黑格尔不主张用“客观家庭权力所要求的统一”来束缚“作为基础与主观感觉的爱”,而是主张以婚姻来实现两个个体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通过“爱”来统摄物质关系:“对夫妻共同财产加以限制的婚姻协定……只有在婚姻关系由于自然的死亡和离婚等原因而消灭的情况下,才有意义”。b[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6页。此外,黑格尔认为,把财产、门第、政治目的等考虑作为缔结婚姻的决定性因素,实质上是把婚姻当做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这可能导致“情感的解体”,从而使家庭面临巨大困难。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对财产保护的出发点并不是以家庭实体为目的,而以保护单个人的财产与权力为目的,这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成员间关系成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连接家庭成员的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偶然需要和私人利益。他指出,资本主义家庭中妇女可以用来交易与出卖,子女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资产阶级家庭以工人阶级的独身或者寡居为代价:“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私有财产权使每个人对立起来。因此,马克思强调财产在家庭生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伦理的爱沦为了偶性方面,服从“个性需求、欲望与富人的兴致”。无论是家庭统一还是解体,甚至在婚姻前状态中,财产与权力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d《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马克思始终将家庭放置在市民社会中而反观之,认为家庭产生演变和发展受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家庭生活中物质关系贬低与压抑了伦理的爱,资本主义“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形式,是“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既然这种婚姻中关注的内容同样是财产与权力,那么它在本质上同契约关系就没有多大区别:现存婚姻中财产与权力的重要地位早已动摇了婚姻的本质,因而对于资本主义家庭来说,“情感的解体”成为一种必然,表面的和睦却是偶然的和虚伪的。
(三)教育与解体:主客观统一环节的异同
在黑格尔看来,夫妻对子女的教育体现了家庭伦理中最主要的部分,因为对子女的教育是家庭中主观性维度与客观性维度的“肯定性统一”。黑格尔认为,“子女有被扶养和受教育的权力,其费用由家庭共同财产来负担。父母……有矫正子女任性的权力”,教育的含义“就在于破除子女的自我意志,以清除纯粹感性的和本性的东西”。e[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7、188页。这表明,子女教育的肯定性目的在于“灌输伦理原则”,教会他们领会作为伦理生活基础的爱、信任与互助;而否定性目的则在于“培养独立自由人格”,以便获得脱离家庭统一体的能力。至于家庭的解体,黑格尔认为,家庭作为统一权力和实体性人格虽然反对成员的退出,但实存婚姻如果依存的只是主观的、偶然性的感觉,它当然是可以离异的,只不过作为伦理性实体,这种离异不能主观任意,只能通过伦理权威来裁定。黑格尔认为由于夫妻感情破裂造成家庭的“情感解体”与成员亡故造成家庭的“自然解体”并不能对家庭伦理方面有所增益,只有子女成长获得独立自由人格并组建新共同体,原有家庭走向解体,才具有伦理意义。f黄其洪、于永成:《黑格尔的家庭观及对当代和谐家庭建设的启示》,《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家庭必然解体是因为它作为独立人格完成了对子女的教育这一伦理使命,需要向市民社会过渡。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家庭教育是异化的,在家庭的自然生活环节人才自觉是人,而在谋求发展时因为从事异化劳动反而觉得自己是动物,教育成为一种制造奴役与培养剥削的手段。资本主义教育实质上是一种阶级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具有某种单一技能的机器。“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8页。关于家庭的解体,马克思认为成员死亡带来的家庭解体不具有伦理意义:“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b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4页。人作为类存在物,总能不断绵延传承下去,因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子女成长造成家庭解体,是家庭复归社会、个体复归总体的必然形式,因而具有社会伦理意义。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情感解体”具有伦理意义,主张离婚自由。恩格斯在依据马克思手稿摘要和批注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明确指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家庭必然解体是因为家庭建立早已基于市民社会的一切原则,只有消除这种原则,变生产资料为社会公有,一夫一妻制才能抛掉其虚假形式,成为真正的情感现实。
二、黑格尔与马克思家庭伦理观相异的原因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家庭伦理观之所以有差别,首先是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其次,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各自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家庭伦理观的生成过程必然服从体系的逻辑要求;最后,这种差别的生产还由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
(一)现象: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作为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组成部分的家庭伦理观,也具有历史时代的现实基础。它是从“时代的十字架”中获得的“作为蔷薇的理性”,是“伦理现实和自然现实的实体性本质的那种理性”的内容与“反映它的概念”的形式的统一,因而它才能摆脱“私见”的桎梏。黑格尔生活的时代,一方面妇女不从事社会工作,不与市民社会和国家产生联系,因而妇女的实存感只能在家庭中获得;另一方面,出于历史的独特性,那时的西方执行“一夫一妻制”。因此,黑格尔关于“爱与婚姻、财产与权力、子女教育与家庭解体”等方面的伦理规定都基于这个现实条件与历史传统,并获得合理性。例如,他主张“婚姻的本质方面是在家庭生活中恩爱互助与相互信任等精神纽带”、“婚姻按本质说是一夫一妻制”、“女子委身事人就丧失了她的贞操”、“女子的归宿本质上在于缔结婚姻”、“男子在家庭之外有另一个伦理活动范围”等等。从这个角度看,黑格尔关于家庭成员在伦理关系的保守性质,就显得极为合理。
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欧已经普遍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通过法律的手段取消了对妇女只能从属于家庭的限制,妇女不仅可以走出家庭到资本主义工厂中工作,而且还具有了部分的政治参与权。可以说,资本推动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波妇女解放运动,但是,这种解放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解放,妇女走出了家庭,同时又进入资本的奴役之中。马克思的家庭婚姻观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的深刻控诉,例如,家庭关系下降为权钱关系、社会大工业的发展使女性与儿童走出家庭并大量沦为雇佣工人、妇女参与到社会大生产过程中从事商业活动、资产阶级家庭建立在工人阶级单身与妇女公开卖淫的基础上、夫妻之间的从属关系依据谁占有生产资料而定等。dMartha E. Gimenez,“Capital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Marx Revisited”,Science & Society, 2005(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夫一妻制是片面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往往对女性严格地执行专偶制,而男性并非如此。这样的情况下爱情所具有的坚贞和忠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中极为罕见。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生产资料及其继承权集中于男子之手,婚姻形式、择偶观以及家庭内部分工受现实经济状况所支配,伦理之爱与婚姻自由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之后,才能普遍实现。由此可见,对受资本逻辑统摄的社会存在的批判,是马克思构建其家庭伦理观的现实基础。
(二)过程:方法服从体系的逻辑
黑格尔的家庭伦理观构建当然运用了他的思辨方法。他认为思辨辩证法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意识的唯一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方法,它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也是知识范围内的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从上位概念或属概念的角度看,黑格尔使家庭隶属于客观精神的第三个环节——伦理,并作为它的第一个直接实体;它是自由意志经历了抽象法这个客观自在的精神阶段,再经过道德这个主观自由的精神阶段,进而第一次达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自在自为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下位概念或种概念的角度看,黑格尔认为家庭经历主观性环节的婚姻,再经历客观性环节的家庭财富,最后经过子女教育与家庭解体,进而过渡到市民社会。他用思辨方法描述了家庭这个伦理实体的生成、发展与消亡过程。然而黑格尔革命性的思辨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是温和与保守的,这种保守性从始至终贯彻于他的家庭伦理中,并表现为对传统伦理精神的珍视与致敬。在黑格尔那里,家庭伦理作为伦理精神运动的环节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是为了历经市民社会而论证最完美的国家形态,即威廉三世许诺的那种等级君主制。因此,“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格尔哲学中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占主导地位,辩证的方法终究服从于绝对真理的体系。a刘福森、黄其洪:《论思辨辩证法的称谓、对象、动力和开端问题》,《理论探讨》2006年第6期。
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意志”这种实践态度,却扬弃了“思维”这种理论态度。他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关系“一开始就很倒霉,不可避免地受到物质的纠缠”。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在家庭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它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仍然由社会存在决定,因而只有通过“武器的批判”即“物质实践”来扬弃它,通过革命来改变生产方式,进而改变由它所决定的家庭伦理关系。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所主张的过程,不是家庭概念或精神自发运动与回归的过程,而是经由实践批判最终达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过程,它服务于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最终目的,即“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而真正具有伦理意义的家庭在于:使家庭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初场所,因为这是与人的解放相一致的个人自由的充分表现。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本身就不合乎伦理,因为它建立在资本与私人发财的基础上。“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b《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418页。如同黑格尔的家庭伦理观体现其“思辨辩证法”从属于“绝对理念自我回归”的理论体系一样,马克思的家庭伦理观同样表征了其“实践辩证法”从属于“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体系。
(三)本质:精神与实践的关系
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家庭伦现上的差别,从本质上看,取决于二者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经典哲学问题上的重大分歧。黑格尔认为,概念不仅是我们的思维,而且也是事物的本质,实在的事物只有当它符合自身的概念时才是实体性的东西,思维与存在是自在自为的统一的,它们在绝对理念的自在自为的回归运动的过程中实现同一。从内容上看,黑格尔的“思维”是绝对精神的概念化存在形式和自为形式,黑格尔的“存在”是绝对精神的现实显现和自在存在,二者统一于绝对精神之中。从形式上看,黑格尔的思想客观性问题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现实性,思维不断地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与自己相符。因此,黑格尔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存在向思维的生成过程”。在具体家庭伦理观中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精神的纽带提升为实体性的东西”并使之具有合法性地位,而把财产与权力等环节下降为次要地位,认为实存婚姻在这方面的缺陷无害于婚姻的本质;二是认为实存家庭虽然具有多样表现,只要经过了主观性环节与客观性环节,并通过婚姻仪式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统一,就仍然符合家庭的概念,并作为伦理实体具有重要地位。家庭生活中现实的矛盾与纠纷、情感的破裂和痛苦,这些都不在黑格尔考察的范围,仿佛只要有了婚礼的保证,只要曾经有爱,具体婚姻家庭生活动的冲突、矛盾、纠纷、痛苦、伤害,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未免过于理想化。
与黑格尔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统一于绝对理念自我运动过程”不同,马克思认为“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过程”。这种“同一”需要实践的帮助,是基于实践辩证法的现实发展的过程,因为世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在实践过程中,在无数次“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中思维与存在不断趋近同一,实践辩证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过程,也是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过程。基于此,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服从于解放全人类的理论体系,他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出发考察实存的家庭,得出了财产与权力环节是影响家庭与婚姻幸福的本质原因,认为家庭伦理重建,应诉诸对社会存在的革命性实践。因此,家庭伦理是组成市民社会伦理的部分,而家庭解放则是理解社会解放的一把钥匙。在具体家庭伦理观中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基础的缺失、家庭伦理关系的破裂与家庭生活的异化;二是致力于改变这种家庭关系,即通过彻底的实践来使现实的家庭符合家庭的概念,恢复平等的婚姻关系、伦理权利与义务。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现实的婚姻实践中的矛盾、冲突、纠纷、破裂、痛苦,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的婚姻家庭观更具有现实感。
三、综合这两种家庭伦理观之后的当代建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作为男女经过必要环节自愿组建的共同体人格,家庭具有自我发展、追求解放与自由的愿望,具有维护统一与反对分裂的现实诉求,也具有自我约束、自我限制的伦理精神。因此,构建和谐的家庭,要以伦理之爱为基础,以自我保存与发展为目标,以传承家庭伦理精神为导向。
(一)个性独立:以伦理之爱消解主观矛盾
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强调两个人放弃各自的抽象独立性,在对方中找到自己,通过差别达到统一,通过放弃获得实存等,这并不等同于各自完全抛弃个体独立性,而是将个体独立性在对方身上实现出来,通过这种双向对象化,最终形成“家庭共同体”这个统一人格的个性诉求。无论是主观性环节的爱与婚姻,还是客观性环节的义务、财产、权利都必须通过家庭成员来承担。因此,这个共同体表现出来的自我发展、追求解放与自由等愿望,必然寓于家庭成员的自由发展的诉求中。这就涉及重要的实际问题,即由于夫妻在家庭生活中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地位各不相同,彼此放弃个人抽象独立性、狭隘自由与平等的过程必然不能一帆风顺,因而家庭中的矛盾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在黑格尔看来,家庭的基础与前提应当是“伦理的爱”,夫妻双方在主客观环节方面应具有平等地位,在家庭生活中互助互爱与相互信任,反对一种奴隶式的夫妻关系或将妇女与子女排除在家庭财富之外等。但是基于男女在自然分工的差异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存条件,男女双方在家庭伦理中扮演的道德角色不同,aEdward C. Halper,“Hegel’s Family Values”,Review of Metaphysics, 2001(4).他指出女子的归宿本质上在于结婚,而男子在家庭之外有另一个伦理活动范围,其现实的实体性生活是在国家与科学中。马克思也从实践角度主张“解放家庭”或“妇女的解放”,推翻资本私有制下家庭生活中丈夫对妻子的压迫,父母对子女的剥削。他从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真正占有人的类生命的角度,提出“人从家庭中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警惕马克思所批判的两种异化的现象。一是“拜金主义择偶观”。这种婚姻观认为:我是丑的,但是我能买到最美的女人,“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b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5页。以金钱的特性取代人的个性,于是人与自然等整个世界,都可用货币来交换,把物质条件作为婚姻考量的前提或唯一标准,而“爱及其统摄的伦理行为”,则作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被抛弃,或寄希望于所谓“后期培养”。这违背了和谐家庭的本质要求,必然会增加家庭矛盾,甚至引发家庭解体与社会问题。二是那种所谓“自由恋爱”。即认为既然爱是婚姻中实体性的东西,那么就应当抛弃对财产、仪式甚至贞操的考虑,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非必要的环节,甚至被认为会降低爱的自由与真挚性。正如黑格尔所言,这种看法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诱奸者的论据,因为家庭与婚姻主观环节上需要以爱为基础,客观环节上需要财产和仪式等形式的肯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实体。因此,也要重视黑格尔的家庭伦理观中蕴含着的合理主张,如举行婚姻仪式,反对婚前性行为,夫妻双方在家庭中自觉履行伦理义务,对子女进行共同教育。夫妻双方在家庭共同体中的伦理地位,应当以男女的自然分工差异为依据,而不应以经济地位的差别为转移。此外,在妇女已经与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伦理关系的前提下,妇女可以平等参与国家、科学、艺术等活动。这又需要依据现实情况来处理好“家庭私法”与“国家公法”之间的关系,a福吉·勝男:《家族の倫理と論理. G.W.F.ヘーゲルに関わって》,《人間文化研究》,2004(2)。因为作为社会意识的家庭伦理关系,一旦脱离“社会存在”而走得太远,家庭乃至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理论与实践困难。
(二)自我保存:将对立权益转化为共同增益
黑格尔认为,家庭的定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维护统一的权力。家庭的实体性应该具有定在,因此它是反对外在性和反对成员退出这统一体的自在的客观的权力,正如斯宾诺莎指出的,“自我保存”并不仅仅是人格作为自然形态的本能,而是理性形态的德行和一切伦理的基础。同样,家庭共同体人格作为一种伦理精神对个体成员进行约束,恰恰是共同体进行“自我保存”的理性行为。因为无节制的情感和欲望并不能给自身带来“自我保存”,不但不能增进自身的存在,反而会沦为极端个人主义,最终导致自身毁灭。b王腾:《斯宾诺莎的德性观:自我保存即德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28日A07版。二是家庭的共同财富。“家庭作为人格来说在所有物中具有它的外在实在性。它只有在采取财富形式的所有物中才具有它的实体性人格的定在。……家庭不但拥有所有物,而且作为普遍的和持续的人格它还需要设置持久的和稳定的产业,即财富”。c[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5页。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家庭共同体面向社会时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的物质保障,因而需要对家庭共同财产进行合理的分配、管理与保护,从而实现其增殖。
无论家庭统一权还是家庭财富,本身都具有一种排他性。在这种排他性中,个人的特殊需要这一任性环节以及自私的欲望,就转变为对一种共同体的关怀和增益,就是说转变为一种伦理性的东西。因而在家庭还维持着统一的阶段中,财富属于共有,但管理者却可以是达成协议的任何一方,此时,伦理性的爱,能将双方原本对立权益转化为共同增益。而当遭遇家庭成员亡故、夫妻感情破裂、子女成长分离,共同增益便无法维持下去,进而又回到相互对立的状态,这就是家庭的解体。这里同样也涉及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既然家庭解体是必然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处理家庭成员的各种财产关系?黑格尔认为,“由于家庭的解体,个人的任性就获得了自由。……他愈加按照单一性的偏好、意见和目的来使用他的全部财产”,d[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1页。这就必然要诉诸“婚姻协定”、“法律上的辅助”等保障性措施,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各自从共有物中取得应有的部分。因家庭成员死亡带来的自然解体,会产生家庭财产分配与管理变更问题,则需要诉诸实在法关于遗嘱、捐赠与继承的相关规定。因夫妻感情破裂产生家庭情感解体时,则需要诉诸实在法对婚姻共同财产认定、过错方的行为认定来判别。因儿女成长重新组建家庭,原有家庭趋于消逝,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伦理关系的延续与伦理精神的传承,是家庭概念与实体的新生,是另一组对立权益转化为共同增益的过程。
(三)精神传承:直观家庭生灭的客观过程
家庭无论是作为黑格尔伦理实体的一个环节,还是作为马克思市民社会的一个细胞,在主观、客观以及二者相统一的层面与社会发生关系。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从根本上符合个人回归社会的必然逻辑,这也从理论上证明了家庭走向解体的必然性,这使得家庭“伦理上的解体”成为文化进化与精神传承的物质载体。aDoyne Dawson,“The Marriage of Marx and Darwin”,History & Theory, 2002(1).在马克思看来,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家庭异化从实践上助推了家庭解体。他认为,新家庭的生成与旧家庭的消亡,是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式,它组成一个连续的、运动的、客观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与教育,实现家庭伦理精神的延续与传承。因而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马克思同黑格尔都赞同家庭中子女的教育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因为家庭教育也具有社会属性,家庭精神又必然蕴含着社会、国家与民族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普遍意识”与“类生活”才能得以延续下去,这便是家庭生灭过程中的理性结构。正如黑格尔所说,以抽象形态出现的家神、家礼与家法等,象征着某种对家庭成员进行约束与限制的伦理精神,在家庭统一阶段,对未成年子女“灌输伦理原则”,使其“在爱、信任与服从中度过伦理生活”,从而在家庭生灭的客观过程中实现伦理精神的传承。
黑格尔认为,实存家庭虽然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陷,但却体现着伦理精神与自由意志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理性结构。因此,家庭成员应意识到家庭实体中存在的理性结构,“意志的过程本身即是通过意志活动将有限性和有限性所包含的矛盾予以扬弃的过程……意志知道,目的是属于它自己的,而理智复确认这世界为现实的概念。这就是理性认识的正确态度”。b[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2页。实际上,这种理性结构,便是蕴含在家族延续中的客观伦理精神,只有对这种精神保持一种冷静直观的态度,才能在现实家庭生活中对其进行扬弃。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除了教会子女生活技能与科学知识外,更应当重视伦理精神、国家精神甚至民族精神的教育,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教给他们伦理生活的基础,在客观的伦理之爱中,使子女脱离原来所处的自然直接性和感性,达到独立性与自由人格,进而获得脱离家庭的自然统一体的能力。子女的客观知识与伦理精神两方面的教育,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同时也是为形成一个新的家庭做准备的客观过程。民族和国家的伦理精神就是在这种家庭的生灭进程中得以延续和传承,这是人类发展铁的规律,任何伤心和痛苦都无以阻挡这种规律,我们应该自觉地适应它,微笑地面对和推进一个个新的伦理实体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