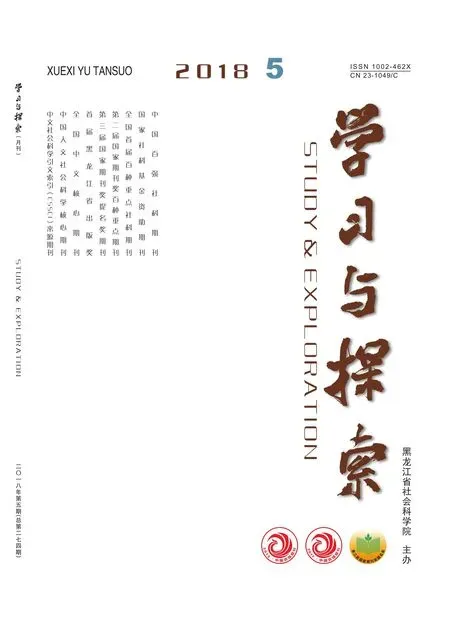阐释公共性的生成要素探究
张 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张江先生在2017年《学术研究》第6期发表的《公共阐释论纲》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即“公共阐释”。他指出:“公共阐释的内涵是,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一提法对于目前流行的阐释学理论构成了一种挑战。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阐释活动自古就存在。阐释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指对《圣经》教义的解读,19世纪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才将这门学科方法论化。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为代表的当代哲学阐释学成为显学。它的突出特点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强调阐释的当下性和此在性。张江先生提出的公共阐释,以“公共”作为阐释的限定语,重视阐释的普遍性和公共有效性,强调阐释的社会性和责任意识,因此是对当代阐释学的一种反拨。由于张江先生此文名为“论纲”,因此很多论点是以纲要形式呈现,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上,将其论文中的关键术语限定“公共性”作进一步细化。具体来说,则是从阐释主体出发,探究“公共性”的生成要素。
一、阐释主体的个人性及其在阐释活动中的核心意义
学者洪汉鼎曾在其著作中提到西方学者通过对“阐释学”的词义考古,认为它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指向:“1.说或陈述,即口头讲说;2.解释或说明,即分析意义;3.翻译或口译,即转换语言。”“因此,诠释学既可能指某种事态通过话语被诠释,又可以指被说的话通过解释被诠释,同时也可能指陌生语言通过翻译被诠释。”[2]但这只是对阐释学解读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对阐释的理解,需要回到阐释活动中去,审视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不是单纯探究从其语义出发归结其可能具有的指向内涵。
阐释活动至少包括三方面要素:阐释者即阐释主体、文本即阐释客体、创作者意图。在这一构成中,存在着阐释的三种可能的意义归属:归于创作者意图、归于文本自身独立生成的意义、归于阐释者试图达到的目标。在阐释学发展的历史中,究竟该将意义归属何方的争论一直存在。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阐释活动中,具有优先性的是阐释者。他的价值认同和选择决定了意义归属的方向。
阐释者的优先性给阐释活动带来了独特的面貌。从直观层面来看,阐释活动是一种阐释者本人的个体阐释。它是由个体来完成的,是作为个别的、具体的人阅读文本,对其做出翻译、解释以及评价。这种解释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
阐释者的个人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阐释活动的个人性,这一特质体现在很多方面。从阐释者与创作者意图或观念的关系来看,阐释的个人性表现在可能会带来评价或理解的错位。例如,欧阳修曾在其文章中说:“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若吾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3]欧阳修的这段话是感慨“知之”与“好之”之间是很难一致的。但这段话恰好说明,阐释者的阐释相对于创作者本人的意图或喜好而言具有独立性和个人性。欧阳修与梅尧臣都认可了欧阳修对梅诗理解的权威性,然而欧阳修所称许者却与梅尧臣完全不同。同时代的好友与知音,又都是作为当世的著名诗人,尚且出现这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那么存在着时空间隔的阐释活动,其个人性无疑会更加明显。
从阐释者本人与文本关系来看,由于前者处于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因此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文本的解读也会存在不同。黄庭坚曾谈到自己阅读陶渊明作品时的体会:“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力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4]少年时读陶诗读不出味道,待到经历过一些世事,有了超拔闲旷的心境后,方能读出味道。这是黄庭坚阅读陶渊明作品的个人体会,也是很多人的阅读体验。阐释活动是阐释者的个体人生与文本里描绘的人生的相遇,是阐释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参悟和感受他者人生,并将这种领悟传递给他人的过程。年龄与阅历的变化,体现出的是阐释主体的未确定性和流动性,它增加了阐释活动的复杂性,也增加了阐释活动中的个人化色彩和偶然性。
更重要的是,阐释者本人是处于具体历史中的人,时代的文化、政治、社会等具体历史语境,都会直接影响阐释活动的内容指向和价值判断,成为阐释者的特质规定以及个体阐释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美国学者乔治娅·沃恩克曾在其著作中征引伽达默尔的一段话:“当某个文本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5]9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阐释者对本文的阐释,并不依赖于作者以及其他读者的阐释;第二,作者与其他读者的阐释也都具有个人性;第三,阐释者的阐释受到具体历史语境的制约,这是其个人性的基础。在征引了这段话之后,乔治娅·沃恩克又以实例的方式将伽达默尔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明确:“我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理解可能被联系到我对心理学问题和存在主义论点的理解。这些可能并不是促使莎士比亚自己创作这一剧本的问题和论点;它们既不是过去他的公众必定意识的问题或论点,也不是今后将必然指向理解这一剧本的问题和论点。然而这些问题和论点既有助于规定我规定该剧本可能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又有助于规定我得以理解莎士比亚意图的方式。”[5]91伽达默尔强调前见对个体的规定性,注重前历史对阐释者的影响,而从沃恩克的观点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发现阐释活动的个人性特征。这种个人性体现在它与创作者意图可能无关,与过去的读者观点可能无关,也与未来对该作品的理解可能无关——它只对阐释者本人有意义,这展现了阐释者本人的阐释方式和兴趣点,也体现出文本对阐释者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阐释主体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阐释的个体性是阐释活动的出发点,任何一种阐释都是由个体出发的。阐释者的个人性是阐释活动的起点,因此当我们讨论阐释的公共性时,也需要从阐释主体出发,从阐释主体以及阐释活动的个体性中发掘出公共性的辩证内涵。理论的吊诡在于,个体阐释的多样性在赋予了阐释活动的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条件。张江先生指出,个体阐释不是私人阐释,某种程度上,这是个体阐释具有公共性的关键节点所在,也是个体阐释的公共约束和责任担当的结点所在。个体阐释是建立在人类共通性基础之上的,阐释主体是处于具体历史中的人,他受具体历史时空的制约,因而在具有历史具体性和个性的同时,也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公共属性。因此,“阐释的公共性决定于人类理性的公共性”,这道出了阐释活动具有公共性的关键所在。
二、人的心理结构与阐释公共性的形成
从阐释主体来分析阐释活动公共性的形成,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是阐释主体的内在要素,其二是其外部要素,其三则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因素。所谓内在要素,即人的本质的共通性,在此我们主要从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来考察。所谓外部要素,在此是指语言和话语体系。所谓介乎两者之间的要素,则是指具体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等。这些方面虽然具有属于外在于人的客观性,但又是规定了人的社会本质的重要方面。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为了解释审美判断力的普遍性,提出了“共通感”这一概念。“人们必须把sensus communis(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的)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将会从主观私人条件中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有可能会被轻易看作是客观的。”[6]对这一概念,康德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共通感是康德基于他自己理论推衍的一种假定;第二,它是一种评判能力和一种理念,即属于人类理性范畴;第三,它具有客观性,但这种客观性主要是指它在人类本质中的普遍存在,而并非是指具有物质实体性;第四,它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使其与主观私人条件截然分开,即它存在于人的主观与精神世界,但又不属于某一个具体人的纯粹个人经验。张江先生提出的“公共阐释是共度性阐释”“公共阐释是反思性阐释”、个体阐释不是私人阐释等观点,是与康德主义的这些美学观念有联系的。然而在康德之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又有了很多新的思路,他的“共通感”的假设也可以获得更多、更充分的解读,而这些对于我们理解阐释主体的内在本质联系也十分必要。
20世纪初期以来,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荣格等学者对人本质的理解在此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质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意识,即理性;其二是无意识,即非理性。人的深层心理构成是一个类似冰山的结构,理性仿佛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只是人类本质的一小部分;决定人类行为的是人的深层本质,即无意识部分,它仿佛深藏于海底的冰山主体。学界一般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称之为个体心理学,因为他强调个体童年创伤对无意识的构成作用。在这种个体心理学的背后,其实暗示出了人类共通性的可能。人类的无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主要是性的欲望;而童年创伤也主要是指童年时性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以及阉割恐惧等。因此个体无意识其实主要是由童年的性意识创伤组成。尽管每个人的创伤经历不同,但却都是童年性意识,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荣格在这方面比他的老师更加明确。在他看来,人的无意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体无意识,一部分是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是私人童年经历,而集体无意识则是深埋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原初记忆,它并非个体经验,而是人类远古记忆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回响。它虽然存在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但却不属于每个个体,而是一种他者存在,是一种客观普遍性存在。
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观点使我们对人类的心理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可以借此达成对阐释活动和阐释主体更多的认识。作为阐释主体,他不仅仅具有理性,同时还具有感性,甚至在心灵深处还有属于无意识的非理性层面。这些拒绝理性分析的东西,是人类的重要属性,也是人类彼此之间可以分享的世界,同样也是阐释活动得以进行、阐释主体分享阅读体验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桑塔格以其女性独有的敏锐指出:“我们现在需要的绝不是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7]16她的观点虽然有偏颇之处,但却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阐释中,我们不能通过阐释将艺术转变成一种思想,或者文化的传达工具。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的主张,力倡去感受作品。与桑塔格不同的是,我们不反对阐释,但在阐释活动中,阐释主体通过自己的阐释,不仅要传达思想,传达文化等观念,同时,也要传达感受。正如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论证的,人类的感受和经历同样具有共通性,可以实现共享。桑塔格还指出:“现在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必须学会去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感觉。”[7]17虽然这是她反对阐释的理由,但同时也提醒我们,阐释活动是一种由感觉和感性出发的活动,感性和感觉是我们阅读活动开始的地方,是阐释活动得以进行的动力之一。因此,在阐释活动中不能忽视感受和感性。同样地,阐释的公共性不仅体现在理性和观念方面的共享性,同时也体现在人的感受甚至非理性层面的可分享性之中。
三、人的社会存在与阐释公共性的形成
人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先天与后天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才形成的。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而言,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这一定义主要着眼于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人本质建构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这一系列关系的综合体现。这些社会关系不仅构成了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形塑了人的观念和思想。伽达默尔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克思对人本质规定的具体化版本。他在评述维柯时说:“维柯认为,那种给予人的意志以其方向的东西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表现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共同性的具体普遍性。因此,造就这种共通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9]35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对人的社会属性可以做如下理解:其一,人的普遍性不是理性的抽象品,而是具体普遍性,它落实于具体的集团、民族或国家等人类具体的社会性和普遍性上;其二,对于生活而言,起到决定性意义的是这种人类具体普遍性;其三,这种社会属性同样属于人类共通感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四,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理念,我们可以将这种具体普遍性作一延伸,即这种具体普遍性体现于时间性之中。无论是一个集团,还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都具有时间性和时代性,都存在于具体时空之中,它规定了具体人的集团属性、民族属性或国家属性。并且这种普遍性以两种情形展开自身,第一是作为传统,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它表现为一种先在;第二是个体自我的历史性,它表现为一种同时性,即规定了个体的具体时间性。在阐释活动中,它们交汇在一起,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基础。
在阐释活动中,传统具有双重性。海德格尔曾经讨论过历史意识的此在,非常符合对这种双重性的描述。他说:“过去的‘已经在此’,而且是以形式生动多样的‘已经在此’与逗留照面的,这种逗留以一种规定的方式看它并这样去看它的指引联系,以至于一种关联从其自身、从其预先规定的事情内容中产生出来,这种关联不断将比较的逗留纳入到追踪的看和共同的看,而且它必须从自身出发以这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10]58-59也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或传统)在阐释者出现之前“已经在此”,它已然获得了自身的存在形式,是具体阐释者的先在。但是,当阐释者审视它的时候,又是“追踪的看”和“共同的看”的结合。“追踪的看”是一种还原,它不是还原到历史本身,而是尽可能地与此前出现的所有有关此一历史事件或文本的诠释知识的一致。“共同的看”则强调了一种公共性。海德格尔说:“历史意识这样存在着:它将自己纳入到一种公众状态中规定的自我解释,以这种公众状态的方式来把握自己,并这样普遍地支配自己。”[10]59历史是一个不断在公众中展开的过程,公共性的阐释成了历史把握自身的方式。并且在看(阐释)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关联,这种关联中最重要的就是阐释者的当下,即生活的此在,它引导和规定了看(阐释)的方式和方向。也就是说,传统一方面作为解释出来的传统而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当下与传统的结合而存在。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思考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去追逐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是学会在对象中认出自身的他在性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是一种关系。”[11]80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都强调阐释主体,强调从阐释主体出发来审视阐释活动的本体性。阐释的公共性在这里可以获得合法性依据,传统或过去的历史及文化作为规范主体的他者,在阐释活动中为阐释的公共性提供了可能。它不仅规定了阐释者主体,使之处于历史链条之中,而且提供一种类似于客观知识的东西,规定了阐释者的阐释不可以是私人阐释,而是可分享的知识。
阐释者的当下性由于与传统的结合,因而在阐释活动中也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一方面,它赋予文本解释以时代性,使文本不是历史幽灵的复活。阐释活动并不仅仅追求历史的还原,而是在解释中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这种新意义的获得,就在于阐释者根据当下的时代语境和需求,因而对历史事件或文本做出新的解读。这种新解读将会随着时间距离,而汇入文本或历史事件的解释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当下性来自时代和社会,而不是来自个体,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可以使阐释者的阐释获得同时代接受者的同情和理解,进而使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双重维度,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四、语言系统与阐释公共性的生成
阐释活动的存在形态,一般以语言为其表现形式。洪汉鼎在《真理与方法》的“译者序言”里说:“理解的实现方式乃是事物本身得以语言表达,因此对事物的理解必然通过语言的形式而产生,或者说,语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9]XI阐释以语言为完成形式,语言的特点必然会制约阐释活动,因此讨论阐释,语言的特质是不能忽略的一环。
伽达默尔在《人和语言》中对人的本质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言的特质等问题做了简单阐释。在他看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借助语言来思考。语言具有三方面的特点:“首先是讲话具有本质上的自我遗忘性。”[11]188即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很少对讲话本身有意识,人们不会注意到自己所说的话的语言结构、语法和句法等。“语言存在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它的无我性。”[11]189“无我性”是指语言存在潜在的听话者,即主要用于一个人讲给其他人听,因此,它不能只是指向言说者自己所意指的对象,而是需要听话者也能够了解正在言说的事件。所以伽达默尔说,讲话不是属于“我”的范围,而是属于“我们”的范围,是一种无“我”。“第三个因素”是“语言的普遍性”[11]191。这一点是由第二点引出。正是由于语言的无我性,所以语言才具有普遍性。它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所有听话者的语言。伽达默尔的语言普遍性还强调了一点,那就是语言的包容性。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免于言说,而所有的言说借助的只能是语言。伽达默尔在其著作中对语言还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即语言具有陌生性和约束性。前者体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之中,后者体现在谈话中。谈话中,会设置问题和回答问题,每一种陈述都需要根据设置的问题,即动机来组织,因而受到设置问题的支配。
伽达默尔对语言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于阐释活动公共性问题的理解。阐释活动需要借助媒介,即语言来进行。根据伽达默尔,语言具有无我性和普遍性,这种“我们”的特点注定了借助语言来呈现的阐释活动是一种公共性的活动,而不能只是对自身发言的私人活动。语言用来传达,同时也是用来交流,因此,语言要求公约性,能够被他人所理解,因此它必然有着公共规则与内涵。伊瑟尔也认为,“语言活动的成功决定于用约定俗成的常规与传统和真诚的保证来解决未定之处”[12],是语言的公共规则和自身包孕的传统维度确保了语言活动(包括阐释活动)的顺利进行。
语言的特点在确保了阐释公共性的同时,也给阐释活动的公共性带来新的生机。首先,语言本身具有多义和模糊等特点,这可以使公共阐释变得更有张力和弹性空间。由于语言的这一特质,就使阐释本身包含了两个部分,明确阐释出的与隐含着的。理解,不仅是对已经阐释出的内容的理解,同时也包括对隐含着的部分的填充和解读。因此,这对阐释的公共性实际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如果缺少公共性,则可能导致阅读者无法理解阐释中的隐含部分,因而最终导致阐释活动无法完整进行。其次,借助语言,就使阐释活动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交流的方式呈现。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伊瑟尔对接受和阐释活动的理解,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交流”。在他看来,阐释意义的生成,产生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中。读者阅读文本,是与文本之间的情感或思想的交流。我们认为,除此之外,阐释意义的生成,也存在于阐释者与阐释文本的阅读者之间。这仍然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以传统和时代特质为先在语境,以阐释者个体经验和认知为前提,构成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交流构架或范式。文本的意义以及阐释的意义都在这一构架中得到重新组织。
某种程度上,阐释具有公共性是一个自明命题。然而,在当代阐释学语境以及文学批评活动中,强调阐释的公共性自有其现实意义。伽达默尔等人重视传统在阐释活动中的价值,但却因为将传统视为一种流动性的历史生成,进而将阐释活动带入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理论深潭之中。公共阐释所强调的公共性,用康德主义视角来理解,是一种主观普遍性,也即一种源自主体的客观性。这种公度性基础赋予了阐释活动以确定性,使之在具有个体多样化的灵动空间和巨大的包容性的同时,也具有了极其广泛的共享性。因此,在阐释活动中,倡导阐释的公共性,确立阐释范式,遵循共同的阐释规则,是获得良好阐释效果,使阐释活动得以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2]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 于民:《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4] 《黄庭坚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4页。
[5] 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6]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
[7]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Ⅰ卷),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0] 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Ⅱ卷),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12] 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