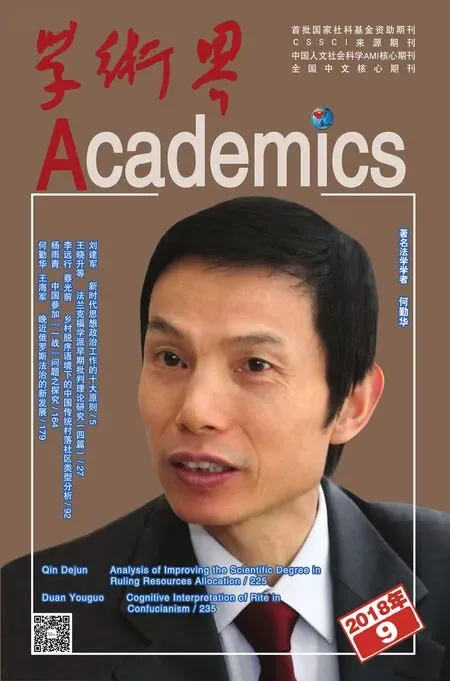“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波洛克与诺伊曼之争
○ 高红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自霍克海默执任所长,就在前任所长格律恩堡(Carl Grünberg)所规定的超党派学术立场、跨学科研究方法基础上,将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从致力于社会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研究转向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理论批判,并将它称之为社会哲学(与一般哲学相对)的研究路径。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够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文化”〔1〕,这为社会研究所后来吸收诸多不同学科背景(如哲学、法学、国民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的学者加入,进行跨学科合作式研究奠定基调,同时也为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研究路径和学术观点埋下伏笔。
一、法兰克福学派极权主义研究的两条路径
霍克海默之所以改变研究所任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在于1930年的德国日益紧迫的社会现实,1929年由于生产过剩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德国和德国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更加衰败和堕落,大量“中等阶级”和失业工人开始涌向希特勒,垄断资产阶级转而支持纳粹党,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运动却陷入分裂乃至停滞状态。〔2〕正是在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社会研究所团结在霍克海默周围,以“批判理论”为武器开启了深度解剖和对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极权统治的救赎路程。这种“理论批判”并非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意义上的纯粹概念性的批判,而是青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批判,又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3〕,霍克海默在1937年《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就明确与以笛卡尔《方法谈》所奠定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传统理论划清界限。〔4〕
然而,在对法西斯主义极权的典型代表纳粹政权的分析上,法兰克福学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种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他们站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带来普遍异化现象的论述,韦伯对资本主义合理化与合法化危机的揭露以及卢卡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等基点上,批判式地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进行整体的理论或文化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作的《启蒙辩证法》就对启蒙概念进行了深刻解剖,认为启蒙已经丧失原本祛魅的功效而走向新的麻痹和神秘化,同时又对资本主义所践行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霍克海默在1947年的《理性之蚀》中对现代理性的工具理性片面发展的批判,马尔库塞1955年的《爱欲与文明》从心理分析学角度对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受压抑进行批判,以及阿多诺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对传统本体论哲学(包括海德格尔所谓的新本体论或存在本体论)同一性思维的否定式批判,以致最终趋向瓦解的逻辑,陷入为批判而批判、为拒绝而拒绝(马尔库塞主张的“大拒绝”)的局面。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他们这一总体性批判的研究路径对动员革命主体、凝聚革命力量、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很大的鼓动效应,马尔库塞后期甚至成为“3M”(其他两者为马克思和毛泽东)之一。但从长远看,随着阶级矛盾和缓、革命热情的衰退,势必影响到批判理论自身的发展,损害其理论的有效性和对现实的解释力。〔5〕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还有一条以深入现实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批判相结合的“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路径,以波洛克、格罗斯曼、诺伊曼、基希海默、古兰德等人为代表,具有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等专业学科背景,他们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建构相关理论,对社会问题开出自己的救赎药方,而当时纳粹极权势力蓬勃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日渐沉沦,尤其是1933年纳粹上台所实行的恐怖主义极权统治,几乎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其中关于纳粹主义性质的问题,还出现了以波洛克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观和以诺伊曼为代表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观的争论。
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观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起因于波洛克的一篇准备刊发在《社会研究杂志》上题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与限度》的文章。
1929年波洛克前往苏联,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回国后撰写了一篇题为《苏联的计划经济试验(1917年—1927年)》的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里,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怀疑主义乃至悲观主义态度得到了系统说明。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看到服务行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从而使剩余价值的生产获得了新的途径,他认为这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1932年《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资本主义的当前状况与计划经济新秩序的概览》的文章,他认为,尽管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崩溃,现状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将以新的属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形式出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撰写《国家资本主义:其可能性与限度》一文。波洛克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6〕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甚至美国文化工业社会等都呈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构成了对原有西方文明的总体威胁。在波洛克那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与私人资本主义即自由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一定的政治因素(如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克服经济或市场的自发状态,协调、组织经济进程,以期获得稳定社会结构的效果。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服从于政治。二战之前的德国、意大利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波洛克认为,计划相对于市场来说是另外一条出路,通过政治的力量限制市场的作用,可以使资本主义保持活力。〔7〕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读完波洛克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和疑虑。霍克海默对波洛克能够敏锐地关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深感赞同,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认同波洛克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但对于波洛克将“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用于分析纳粹主义持有异议,即有美化纳粹主义之嫌,阿多诺甚至认为这篇文章对纳粹主义的分析过于简化,而且充满了盲目的乐观。〔8〕由于霍克海默、阿多诺与波洛克在研究所内部是自第一任所长之后最核心的三位人物,同时又是关系最亲密的朋友,因而他们更多的是站在维护波洛克的立场而给出的忠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建议波洛克对这篇文章进行改写。
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意义重大。波洛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批判性地考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前景问题,使得批判理论调整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即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日渐消沉,而预言中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如期垮台,使得批判理论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再反思,进而推动了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型。〔9〕根据美国学者费舍尔的说法,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至少从三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10〕具体说来主要有:首先,根据霍克海默的说法,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抓住了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为同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进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11〕事实上,此后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逐渐成为20世纪30、40年代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共同的理论关注点,如诺伊曼、基希海默、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都讨论过此问题;其次,波洛克从历史哲学层面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和非工具理性的本质区别,从而激发了霍克海默等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同期发表的《理性的终结》一文中,霍克海默更是深化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性认识,而他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工具理性批判的拓展;再次,波洛克对社会主义迅速实现所持有的实地考察后〔12〕的怀疑,以及他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持久存在的新形式的分析等都极大地影响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事实上,后期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社会发展的悲观主义态度很大程度上和波洛克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有很大关系的,如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等整体上都呈现出悲观主义色彩。〔13〕总体而言,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争、逻辑分析,以及他将这一理论用于对纳粹主义的分析都持有异议,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一理论进行全盘否定,毋宁说,这一学说只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的理论。
三、诺伊曼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观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用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成员诺伊曼那里则是另一种态度。诺伊曼之所以被称为研究所的边缘性或外围人员,除了诺伊曼与研究所核心领导人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等人的关系不甚亲密之外,更多的是理论旨趣和观点的巨大差异。〔14〕尽管波洛克在研究所是诺伊曼行政职务的上级领导,但他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维护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立场不同,他坚决反对波洛克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分析纳粹主义,而主张法西斯主义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15〕,认为波洛克的分析含糊其辞、结论带有概念性,既缺少应有的实证分析,也没有阐明推论的过渡环节。〔16〕在他看来,波洛克要么不了解纳粹主义的本质,要么就是有意美化纳粹主义。他认为,纳粹主义从其权力组成的多极化但缺乏核心的统一性而言,它根本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家的特征,而它所实施的高度集中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方式,本质上是“极权+垄断”相结合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是反自由、反民主,甚至是反理性的,因而并不具备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
尽管诺伊曼与波洛克研究路径相似,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和批判纳粹主义,但波洛克更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而诺伊曼的分析更突出经济基础在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诺伊曼在《巨兽》一书的第二部分中的“极权式垄断经济”章节中专门批判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用法,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经济学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公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家”的特征。〔17〕诺伊曼认为,纳粹主义的政治结构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非统一的组织,唯一统一的力量是由维和部长级理事会代表的官僚主义和武装力量,他们在畏惧民众和排斥社会主义方面具有相对一致的目标,他们根本的意识形态是种族主义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根本上说还不具备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纳粹主义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同时,诺伊曼还认为,纳粹主义时期,德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中失业的消除、生产的增长、工业产值的增加等,都完全归结为战时经济的需要,完全的配给制度和价格控制,使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假象,一种类似布尔什维主义的假象,即好像自由市场被国家行政管理取代了,资产阶级也消亡了。然而,实际上,正如诺伊曼此前对纳粹主义政治结构多极化的分析,纳粹主义政权是由四个权力中心(纳粹党、国家官僚、军队和大企业)构成的,他们的关系是各自为政、相互牵制的,因而从根本上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本质上也不可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共通性。
诺伊曼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在对比分析纳粹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展开,其文本内容主要集中在《巨兽》一书中。该书以三个问题截稿,分别是:一是德国有政治理论吗?二是德国是一个国家吗?三是这个结构(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什么?〔18〕事实上,正如诺伊曼在该部分的书稿中指出的,这三个问题是对整本书的总结,即对纳粹主义决定性方面的集中阐述。〔19〕诺伊曼认为,每个政治系统都以其政治理论为特征,体现其结构和目标,而当它用以分析纳粹主义时却遇到了困难,在诺伊曼看来,纳粹主义本质上是反民主、反自由,甚至是反理性的,而该书稿的书名之所以取为“Behemoth”(巨兽),根据诺伊曼本人的说法,它源自霍布斯的另一本同名著作,它象征一个无国家、无法无天的状态,〔20〕是与霍布斯另外一本更众所周知的著作《利维坦》所提到的怪兽“Leviathan”相对。尽管“利维坦”也吞噬了社会,使得社会很可能演变为一个暴君统治的战场,但这个“暴君”的上台是人们达成一致的选择或妥协的结果,因而它本质上还是理性的,其权力的运行也是基于法律范围内的,诺伊曼借用“Behemoth”这一概念来分析纳粹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诺伊曼认为民族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了理想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活力论、相对主义、普遍主义、制度主义等要素,但这些要素之间无法融为一体,而是彼此充满了矛盾,他们的使用都遵循于人的意志或需要,〔21〕因而如果一个国家〔22〕是以法治为基本特征,那么根据诺伊曼对纳粹主义的描述,显然,纳粹德国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具体说来,首先它不符合作为现代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和目标的统一性,希特勒尽管在纳粹德国民众中的声望很高,表面上代表了最高的权威,但其实际掌控的权力却被四个权力中心分割,因而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他所确立的策略也经常被下级打折扣式处理或有意篡改。〔23〕其次是纳粹德国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都是以备战为需要,社会的高度整合以及建立一套类似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也都是便于调整战略;再次是与纳粹德国社会高度整合相关的特征,即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较大,法治的建设被统治阶级意志取代;最后是纳粹德国大肆屠杀国内犹太族,实施种族清洗政策违背了国家作为全民利益代表的原则。甚至纳粹主义时期最著名的律师赫恩和奈瑟也拒绝使用国家的这个概念,在他们看来,如果将纳粹德国视为一个国家,那么国家在这里就成了一个自由构想的东西,而行使权力的人则成了国家本身,〔24〕而在诺伊曼看来,纳粹德国除了希特勒的魅力之外,没有可以有效合并四种权力的力量,甚至没有落实妥协的普遍的有效基础。〔25〕诺伊曼认为纳粹主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新的社会形式。
这个新的社会形式是什么呢?这是诺伊曼在批判国家资本主义,否定纳粹主义是国家之后紧接着要回答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新的社会形式尽管还不能完全把握,但却可以从其发展趋势中把握其政权的本质,〔26〕即以极权为基础的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具体而言,诺伊曼首先认为纳粹主义的产生是出于利益、权力,尤其是对被压迫群众的恐惧等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的各个中心彼此防备,甚至吞噬,进而使得原本就不协调的力量中心最终倾向于“驻军国家”(garrison state)的方向发展,拉斯维尔〔27〕称之为暴力行为人执掌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可能会执掌国家政权,但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呢?
诺伊曼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纳粹党掌权的德国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是进入一个新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依靠党和军队达成妥协后所实施的暴力和恐怖而实现,而新的资本主阶级的出现将与党的意志为依据的政治权力充分地嵌合在生产过程中,〔28〕即这里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从而产生了极权式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其次,另一个趋势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诺伊曼认为,这两大阶级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深刻的对抗,这种对抗深刻地体现在纳粹魔幻性的宣传与社会的完全理性和人格解体〔29〕之间,即纳粹不允许产生一种与劳动理性过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是不断灌输式的宣传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化纳粹主义并掩盖真实的社会局势。诺伊曼认为纳粹主义的这种努力是得不偿失的,反而会激起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对纳粹的蔑视和逃避;〔30〕再次,诺伊曼认为纳粹主义的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其本质上的极权式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瓦解纳粹本身,即纳粹一面大肆进行着反资本主义和反国家的宣传,在行动上却通过暴力和恐怖(如国会纵火案)实行权力的高度集中、中小企业收归个人等。纳粹上台以后,德国出现一批新的垄断巨头,这就是纳粹领袖,像希特勒(希特勒本人不重视甚至轻视经济发展,而更多地通过暴力掠夺的手段夺取资源和财富)、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典型的是戈林。1933年以前,戈林同生产资料占有毫无关系,1937年建立“赫尔曼·戈林工厂”以后,因不断合并德国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夺取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外国工厂而日益扩大。1943年初,“戈林工厂”已拥有177家工业企业,69家采矿业和钢铁联合企业,156家贸易公司,15家建筑公司,〔31〕而另一面却不赋予民众应有的平等、自由等权利,从而加剧了纳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甚至是社会整体性的冲突;〔32〕最后,诺伊曼认为纳粹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必定以失败收场,但他认为要战胜纳粹德国,不仅仅依靠军事经济行动,还应配合着心理上的行动。在诺伊曼看来,纳粹之所以能够在民众中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一方面除了与纳粹所实施的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关,另一方面还和纳粹进行的魔幻性的宣传有关,这种宣传很大程度上蒙蔽或遮盖了对现实真相的认知。
四、小 结
诺伊曼的《巨兽》一书之所以对纳粹分析具有如此权威性地位,不仅在于该书于1942年纳粹统治仍处于上升期就科学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战争必然失败的结局,更在于该书通过对纳粹主义实证的结构主义分析正确把握了纳粹主义政权的性质及其本质,即以权力为基础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诺伊曼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伪社会主义,它所主张的阶级平等、取消阶级斗争,不过是为了凝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拿犹太人和共产主义做“替罪羊”,以转移国内矛盾,其根本目的是为加强自身统治而非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纳粹政权内部充满了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权力中心的四重分割使得统治阶级既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又缺乏长远的施政目标,以致后期纳粹党领导人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成为典型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认为纳粹统治依靠的是暴力恐怖与阴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依靠的是领袖的个人魅力而非现代法治,因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此基础上,诺伊曼就有理有据地批驳了以波洛克为代表的,将纳粹主义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为正确把握纳粹政权的性质和理解现代国家提供有力依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诺伊曼对纳粹政权的基本分析框架来源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即外在地考察纳粹政权的组织结构及其实践意图,这种分析路径的好处是可以较快地把握该组织基本性质及其发展趋势,但其不足在于忽视了这种政权的群众产生根基以及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处境及其感受,而这正是纳粹政权得以产生及其对世界产生强大破坏性的力量所在,这也是诺伊曼《巨兽》被诟病最多的问题所在。诺伊曼似乎也意识到问题所在,他后期转向对政治异化、权力认同及其焦虑问题的关注就是很好的证明,然而还未等到诺伊曼进一步拓展其在1954年《焦虑与政治》一文中所呈现出的创造性观点,他就于当年因一场车祸逝于瑞士,同时也使这一研究思路留下了一段空白。
注释:
〔1〕〔德〕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
〔2〕〔31〕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29、347页。
〔3〕王凤才:《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
〔4〕Vgl.Max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Frankfurt/M.Suhrkamp,2005,S.205-259.
〔5〕笔者认为第一代主要批判理论的研究路径在阿多诺走向瓦解的逻辑,很大程度上迫使以哈贝马斯、霍耐特为代表的第二、三代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理论进行反思、重构和转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主要问题发生改变的必要,而这种批判理论得以成功转型的可能性又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如波洛克、格罗斯曼、诺伊曼、基希海默等人侧重以经验研究与理论批判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具有密切关联,只是目前这些理论家往往被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理论“光芒”遮蔽而缺乏深入研究。
〔6〕这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英文即National Socialism,是在波洛克意义上使用的,即波洛克首先将纳粹帝国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纳粹帝国组织和管理模式,而诺伊曼恰恰否认这一点,他认为纳粹帝国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将它视为经济垄断在高度极权支撑下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他这里一般被称作“民族社会主义”。
〔7〕柴方国:《波洛克与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1期。
〔8〕Emil Walter-Bush.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Theorie und Politik.Wilhelm Fink Verlag, 2010, S.83.
〔9〕〔13〕陈湘珍、张亮:《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形成及其效应》,《理论探讨》2009年第3期。
〔10〕〔美〕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93页。
〔11〕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 Fischer: Frankfurt a. M., 1985-1996(17). S.116.
〔12〕 这里所谓的实地考察,即波洛克于1929年前往苏联,并撰写了一篇题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1917-1927年)的考察报告》,这篇报告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全面参与经济生产、分配等环节的组织模式,它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
〔14〕苏尔纳认为,诺伊曼的风格是枯燥的,几乎是沉默寡言的;而且他对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等人的文献并未给与太多的承认(〔德〕A.苏尔纳:《F.L.诺伊曼是谁?》(上),《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4期)。
〔15〕〔德〕A.苏尔纳:《F.L.诺伊曼是谁?》(下),《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5期。
〔16〕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314-326.
〔17〕〔18〕〔19〕〔20〕〔21〕〔23〕〔24〕〔25〕〔26〕〔28〕〔30〕〔32〕Franz.L.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m1933-1944. Frankfurt/.M.Suhrkamp. 2009:pp.221-228,459-470,459,459,464,468,466,470,470,470,471,473-474.
〔22〕这里所谓的“国家”是指现代国家。
〔27〕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美国著名的政治科学和传播学理论家。
〔29〕所谓“完全的理性与人格解体”,更多指的是纳粹主义施行的高度集中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完全是以备战需要而无视人的个性综合发展需要,这种完全量化的理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反自由、反民主,甚至是反理性的。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