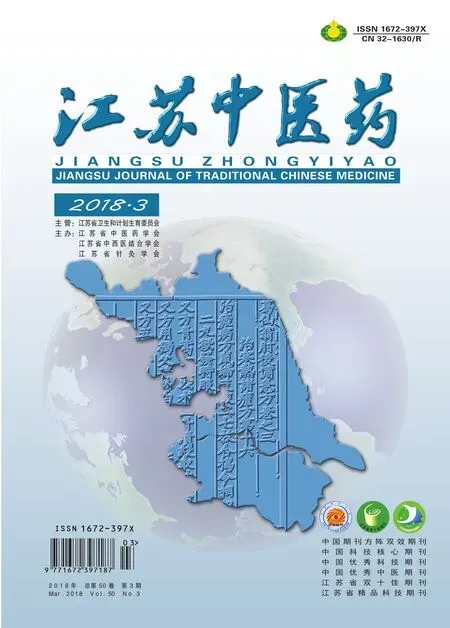《洞天奥旨》疮疡治疗思想概述
解广东 白克运 王本军 周永坤
(1.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济南250014; 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济南250014)
《洞天奥旨》[1]是清代名医陈士铎编撰的一部外科专著,全书共十一万余字,分16卷,首载经络图,涉及外科疾病一百余种,奇方近三百首,书中首论疮疡,次述病症,后叙方药,是一部代表清代以前外科学成就的重要著作。其对外科疮疡的描述内容占有4卷,系统阐述了疮疡的证治经验,集历代疡科之大成,辨证精当,用法神妙,处方屡试不爽,为后代医家所重视,现将其疮疡证治思想探讨如下。
1 辨标本,别脉之有余及不足
标本理论是《内经》治则治法篇的核心内容,其本意是指草木的枝叶与根茎,就疾病而言,引申为疾病的表象与本质[2]。陈氏在此专著中首论疮疡之标本,可见其在外科疮疡中的重要性,“苟不知标本,轻妄施药,不中病情,往往生变”;外生疮疡,通常皆因脏腑内毒发越于外,故忽略脏腑发病的本质,而治疗疮疡之标,往往难以奏效。对于复杂疾病的辨证,更需要标本分明,如果阳病出现痒的症状,此为阴虚,故治疗应“补阴以化毒,而不可损阳以耗气”。《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因营气根于胃气,胃气影响营气的顺逆,而营气之逆直接导致疮疡形成,故无论疮疡属阳病或阴病,其治则皆需固护胃气,“有胃气则本病阴而能生,无胃气则标病阳而亦死”,此理论亦是陈氏对《外科枢要》中元气理论的发展。
疮疡多生于体表,然与之相连的脏腑之毒难以触及,因此需要察色诊脉以辨别脏腑的虚实,在通常情况下,疮疡病脉象亦有规律可循,“未溃而现有余之脉”“已溃而现不足之脉”皆为顺之象,反之则逆,并把浮脉、芤脉、滑脉、实脉等七种脉象归为有余之脉,把微脉、沉脉、缓脉等六种脉象归为不足之脉。根据标本和脉象,治疗亦有所阐述,针对疮疡未溃而出现的不足之脉,宜重用人参、黄芪急补元气,以托毒外出,即所谓“补阳以发其毒”;而对于已溃而出现的有余之脉,宜多用熟地、当归,骤充其血,以散毒于内,即所谓“补阴以化其毒”;当有余不足之脉难以分辨时,则可用大补气血的药物,佐以善消火毒之品,亦能发挥疗效。
2 审阴阳,明疮疡肿溃与虚实
疮疡有阳证、阴证之分,通常情况下,阳证表现为皮肤红活发赤,灼热,肿势高起局限,软硬适度,阴证表现为皮肤不热或微热,肿势平塌下陷不局限,红肿散漫,坚硬如石或柔软如棉[3]。陈氏在书中尤其注重疮疡阴阳辨证,“阴阳不分,动手即错”“阳症必热,阴症必寒”,根据疮疡的不同临床表现,从形、色、初起感觉、溃烂、收口情况,加以区分,“阳症之形必高突而肿起,阴症之形必低平而陷下”,“阳症之色必纯红,阴症之色必带黑”等。又对疮疡阴症与阳症从热、寒、滞、陷四种不同的病机加以对比,如“阴热者,夜重而日轻;阳热者,夜轻而昼重”,同时阐述了病机的变化过程中所伴随的临床表现,“先阳变阴者,始突而不平,初害痛而后害痒;先阴后阳者,初平而溃,始患热而后恶寒也”等。对病机变化的原因也有独到的见解,阳病转化为阴病,多为阳虚湿重的胖人或服用寒性的药物所致,阴病转化为阳病多为阴虚火多的瘦人或服用热性药物所致,并反对世俗以气血或痈疽分阴阳的一些观点。在治疗方面,勿论阴证阳证,必用气血兼补而佐之消毒的方法,区别在于金银花等化毒之品的用量上。
陈氏认为疮疡的治疗虽然皆用补益的方法,但若不辨明证之虚实,则难以速效,而在辨明虚实阴阳时,又需结合疮疡的肿溃情况,疮疡未溃,肿块有肿而高突、焮赤作痛的表实证和坚硬深痛的里实证之分,治疗应有所区分,“表实可散,里实可攻,攻散之中,略兼用补”;亦有疮疡肿块焮赤作痛而少衰的表虚证和痛不甚深的里虚证,其治疗亦有不同,“表虚不可纯散,里虚不可纯攻,攻散之中,重于用补”。疮疡溃后,亦可出现两种情况,“肿硬焮痛,发热烦躁,大便秘结,疮口坚实,此阳毒未化,乃邪实也”,“倘脓大出而反痛,疮口久而不敛……乃正虚也”,前者治疗宜补而兼散,后者则戒散而必补。
3 知经络,识疮疡内外及顺逆
经络布散全身,运行气血,经络闭塞不通,气血津液输布障碍,则易生疮疡。陈氏在书中卷首载经络穴位图14幅,足见其对经络的重视。根据疮疡所生之部位,判断其所属何经络何脏腑,“生于面,即属足阳明经之病,面乃胃之部位也。生于颈项,即属足厥阴肝经之病,盖颈项乃肝之部位也”,并根据经络气血多少,施以补气、补血、消散之法,“若胃经,则气血俱多,初可用消,而终亦必佐之以补气血”,肝经又属血多气少的经络,故“非补气,则未溃不能散,已溃不能生也”。又疮疡之生由营卫气血瘀滞引起,陈氏认为引起营卫气血瘀滞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即外感、内伤及不内不外之伤,“外伤者,伤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内伤者,伤于喜、怒、忧、思、惊、恐、悲之七情也”,三因素之所以引起疮疡,亦离不开气血虚衰。治疗疮疡之前,亦需判断疮疡的顺逆,即所谓“阳症多顺,阴症多逆。顺者生,逆者亡。”顺逆知晓以后,则能有助于病情的预测,陈氏在书中亦详细描述四种顺逆情况的临床表现,“疮疡之初起,顶高根活,色赤发热,焮肿疼痛,日渐突起,肿不开散者,顺也;若顶平根散,色暗微肿,不热不疼,身体倦怠者,非逆而何?”等。
4 顾体质,分贫富肥瘦及孕产
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4]。陈氏在书中主要从后天获得方面,对贫富、肥瘦、孕产之人加以区分,照顾到不同人群的体质状态,分析疮疡形成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的不同,即体质不同,发病倾向也不同。疮疡生于富贵人家,则常因多食燔熬烹炙之物,思淫享乐,致肾水亏涸,难以伏火,热而化毒,变为疮疡,而贫穷人家所生疮疡,常为感受外邪,致脏腑经络气血瘀滞,化火化毒,变生疮疡,“故贫贱之人所生者,半是阳毒,而富贵之人所生者,尽是阴疮”,而又“阳毒易消,阴毒难化”,故治疗有所区分,及时治疗,前者多清补,后者宜温补,即“阳易清补以消毒,阴宜温补以化毒也”。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曰“肥人多湿,瘦人多火”,陈氏认为疮疡的发生与治疗亦与肥瘦体质相关,“湿多则痰盛而气虚,火多则液干而血少”,故瘦人患疮疡之症,多因阴血亏虚,肥人多因阳气亏虚,其治疗亦应有所差异,又因气血相互依存,“气非血以相养,则气虚不能遽旺也;血非气以相生,则血虚不能骤盛也”,故肥人疮疡的治疗应重补其气而轻补其血,瘦人应重补其血而轻补其气,佐之消火败毒之品,疮疡之症则能速效。因孕妇、产妇的体质与常人不同,如孕妇本已是气血半荫其胎,有患疮疡者,其治疗宜护其胎,而不得用败毒之药重伤气血,然疮疡亦需治疗,故应于补气补血之中,少佐泻火败毒药,才能取得满意的疗效,“则在腹之胎无损,而在肤之疮亦易散也。”产后体质多为亡血过多,气血衰少,产后疮疡之生,多为血亏,“血亏而阴愈亏”,故产妇所生疮疡多为阴疮,“阴疡在常人,尚纯用补剂,产妇阴虚,更无疑也。”治疗当补阴以生血,兼补阳以生气,而补阳药中当用温性之物,而不必佐之泻火败毒之品,“使荣卫通行,气血流转,则毒气不必攻而自散矣”。
5 慎火灸,佐刀针敷药兼调护
陈氏在书中继承了《外科正宗》的火灸法治疗疮疡的思想,疮疡的火灸疗法可发挥独特的疗效,应用得当,可现速效。“盖毒随火化,自然内之火毒,随外之艾火而宣散也。”灸治部位亦有所禁忌,如头面部及肾腧穴部位不宜灸,而阴虚之人亦不宜灸;对于灸治的壮数不加统一限制,但应有所参照,即“初灸即痛,必灸至不痛始止。初灸不痛,必灸至痛始止……不可半途即撤也”,“若初灸麻痒者,亦必灸至痛而止”。然而其在火灸论中亦有自己的见解,“大约阳疮之痈疽不宜灸,而阴症之痈疽必亦灸也”,若为阳证疮疡施用火灸,火毒通入于内而不出,变生诸多他症,与《外科正宗》所述“不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均可灸”的思想相异[5],也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及发展。陈氏亦阐明了使用针刀治疗疮疡的态度,“见有脓,急用针而不可缓”,“见瘀肉,急用刀而不宜徐”,既反对滥用刀针,也反对畏用刀针,且使用刀针治疗的同时,主张外用药、内服药同用,“然后外用膏药、末药,呼其脓而护其肌,内复用汤剂,散其毒而还元”,以求全效。其外治疗法中,陈氏推崇敷药的使用,“敷者,化也、散也。乃化散其毒,使不雍滞耳”,然敷药的选择亦需合乎病症,如阳症疮疡,用寒性化毒败火之药敷,后期用热药消散;阴症疮疡,用温性化毒败火之药敷;半阴半阳症疮疡,则用和解化毒败火之药敷,杂用温性药物散毒。
在疮疡调护中,陈氏列举诸多疮疡期间饮食的禁忌,并主张禁恼怒与色欲,尤以色欲为重,“一犯色欲,多至暴亡”,治疗多重用人参、黄芪、白术、当归、熟地黄、附子、肉桂、金银花等,对金银花的使用,陈氏设有专论,尤其重视,“盖此药为纯补之味,而又善消火毒”。
6 结语
《洞天奥旨》作为外科专著,体现了陈氏在疮疡论治方面的卓越思想和高超医术,虽在自序中称其医术为岐伯所亲授,为后世医家所诟病,然而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对疮疡的治疗有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疮疡病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陈士铎.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洞天奥旨[M].柳长华,刘更生,李光华,等,点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2] 赵伟红.标本理论的临证应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5,13(13):7.
[3] 王磊,李峨.外科疮疡的阴阳辨证解析[J].江苏中医药,2009,41(8):9.
[4] 邸洁,朱燕波,王琦,等.不同年龄人群中医体质特点对应分析[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4,34(5):627.
[5] 姜徳友,淡平平.《外科正宗》学术思想初探[J].中医药信息,2011,28(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