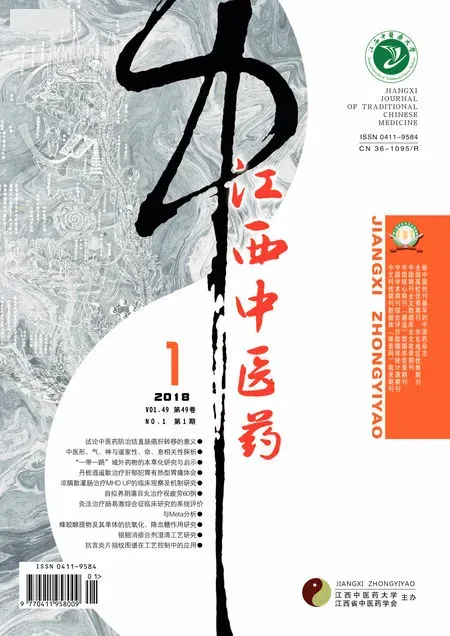江医家陈自明崩漏证治思想探析
★ 罗侨 李丛 冯倩倩(江西中医药大学 南昌 330004)
陈自明,字良甫,南宋临川( 今江西抚州) 人,约生活于公元1190年—1270年。他出生于世医之家,曾任建康府明道书院的医谕(教授),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妇产科专家。陈氏自幼聪慧,怀有济世活人志向,博览历代医家著述,遍行东南各地,汲取诸家之长,并继承家传良方,因而医术高明。他尤精于妇、外两科,撰有《妇人大全良方》和《外科精义》二书,在中医妇科和外科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妇人大全良方》对妇科急症崩漏辨治具有独特经验,对现代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述于下。
1 崩漏的病因病机
崩漏是指经血非时暴下不止或淋漓不尽,暴下如注谓之“崩”,淋漓不尽谓之“漏”,是月经周期、经期、经量发生严重失常的病证。《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1]405。《说文解字》:“冲,要道也”[2]。《集韵》:“冲,要也”[3]。即言冲脉为十二经气血通行之要冲,为“十二经之海”,能调节十二经脉之气血,与五脏关系密切,对月经的行止起重要作用。任脉为“阴脉之海”,《难经》杨玄操注:“任者,妊也”[4]。指出此脉与妊养胎儿有关。陈氏《妇人大全良方》认为: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血气之行外循经络内荣脏腑。若无伤损,则阴阳和平而气血调适,经下依时。若劳伤冲任,冲任二脉亏损,气虚不能制约其经脉,就会出现经乱无期,出血量多,势急如崩或量少淋漓累月不尽,或停经数月后又暴下不止的症状。“崩”为忽然暴下,称之“崩暴下血”,病势急重;“漏”为淋漓不尽,病势较缓,谓之“崩中漏下”。崩与漏的关键病机同为冲任气虚,不能制约其经血,但亦有不同之处,“崩”病势危急,常为外感风邪或内伤发热伤及冲任所致。《妇人大全良方·崩暴下血》曰:“然风为动物,冲任经虚,被风所伤,致令崩中暴下”[5]23。亦载:“若经候过多,遂至崩漏……此由阴阳相搏,为热所乘,攻伤冲任”[5]22。“漏”病势迟缓,多为虚寒相搏,冲任不固所致。《妇人大全良方·崩中漏下》:“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其脉为牢,妇人即半产漏下”[5]26。
2 崩漏的辨证论治
崩漏是妇科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也是疑难危重症。徐春甫《妇科心镜》云:“妇人崩漏最为大病”[6]。该病病因多端,病机复杂,历代医家不乏对其细究。陈氏汲诸家之长,承家传良方,对崩漏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其临床辨证可归纳为风伤冲任型、阴虚阳搏型、虚寒相搏型等,相应处以不同治疗方法。
2.1 祛风止血以止崩风为阳邪,百病之长,其性主动,善行数变,易兼他邪乘虚而入。手太阳小肠经和手少阴心经相为表里,此二经在妇人平素时期,气血循经下行调节月水,在妇人有胎之时,气血循经上行分泌乳汁。《良方》有云:“夫妇人月水不调者,由劳伤气血致体虚,风冷之气乘也”[5]14。风冷之气客乘于胞内,伤于冲任之脉,损手太阳、少阴之经致冲任虚损,冲任气虚不能固其经血而致崩中漏下。此外,《伤寒脉歌》有载:“脉浮而大,风伤荣。荣,血也”[5]23。陈氏参悟古人见识,认为“风为动物,冲任经虚,被风所伤,致令崩中暴下”[5]23。风性主动,血随风动,且冲任经虚,不能固摄,血不得藏,流不归经而致出血,陈氏组方五灵脂散、荆芥散、独圣散祛风治妇人血山崩不止。虽然五灵脂散、荆芥散及独圣散皆以五灵脂、荆芥、防风单药成方,但是,陈氏谴方有道,五灵脂、荆芥、防风性偏温,皆是风药。风药是李东垣继承其师张元素关于药物气味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具有升发、疏散特性的一类药物[7]。《素问·调经论》曰:“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1]651。陈氏药用五灵脂、荆芥、防风不仅可以宣畅气机,而且可以祛除风冷之气。气机通畅,统摄血液运行有序,风冷之气祛除,胞宫可以恢复正常生理功能,血亦可自荣,则冲脉、任脉气盛,太阳、少阳所生之血宣流依时而下。
2.2 滋阴凉血以止崩早在《素问·阴阳别论》中有载:“阴虚阳搏谓之崩”[1]472。阴虚,阴血不足;阳者,火也,阳火偏旺;搏者,动也。崩漏为血病,营血有热,营热如沸,血热则溢。唐代王冰《黄帝内经·素问》释:“阴脉不足,阳脉盛搏,则内崩而流下。”陈氏《妇人大全良方》有载:“若经候过多,遂至崩漏,色明如水下,得温则烦,甚者至于昏闷……此由阴阳搏,为热所乘,攻伤冲任”[5]22。阴虚则内热,血得热则流散,譬如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阳伤于阴,令人下血而成血崩,甚者使人昏闷。陈氏认为“阳伤于阴,令人下血,当补其阴”[5]22。故当滋阴凉血,以代表方小蓟汤为例,方中小蓟为君,臣以生地,辅用白术以滋阴凉血止崩。小蓟性凉,入肝经血分,凉血止血,兼可清热,配以生地,清热养阴,兼以凉血,两药相伍,清热凉血力增,且可凉血止血,止血不留瘀。辅以甘温的白术,使小蓟及生地不至寒凉太过,伤及脾胃,并且,白术有补气健脾之功,可以升发脾胃之气生血补其阴。
2.3 温肾祛寒以止漏陈氏认为“淋漓而不断,谓之漏下也”[5]26。漏下之病,病程缠绵难愈。女子以血为本,脏腑以血为用,长期慢性失血以致精血不足,脏腑虚损,不能抵御外邪,寒邪乘虚客入胞宫。从而影响胞宫行月经、泌带液、主胎孕、司分娩、排恶露的生理功能。《素问·五藏别论》云女子胞“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1]492。寒邪客乘胞宫以致胞宫不藏反泻,这是导致漏下的主要原因。故陈氏说“脏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其脉为牢,妇人即半产而漏下”[5]26。此外,《素问·奇病论》说“胞络者,系于肾”[1]637。且寒邪易伤阳气,胞宫寒冷可耗伤肾之阳气。故陈氏以温肾祛寒之法以止漏下,方以鹿茸圆。鹿茸圆方中以鹿茸为君大补肾阳、固冲任,赤石脂、禹余粮、柏叶收敛止血为辅,配以熟地、当归补血,艾叶、附子、续断温经暖宫共奏温肾祛寒,固冲止漏之功。此外,陈氏亦常用龟板、鳖甲、牡蛎、熟地、当归等血肉有情之品,峻培本源,温肾暖宫。
3 治疗特色
3.1 急则治标,善用止血药崩漏属于出血性疾病。《备急千金要方》指出,如果崩漏“去血多未止”,则可引起“心中悬虚,心闷眩冒,头重目暗,耳聋满塞,举头便闷欲倒”等症[8]。“崩”为忽然暴下,病势急重,陈氏认为崩症应紧急治疗,控制出血。同为旴江医家的万全《万氏妇人科·崩》亦指出:“凡妇人女子,初得崩中暴下之病者,宜用止血之剂,乃急则治其标也”[9]。纵观《良方》中陈氏止血用药多为小蓟、茜根、蒲黄等凉血止血药或赤石脂、禹余粮、棕榈炭等收敛止血药。然而,陈氏非常善于用止血药治疗暴崩下血,常用单味止血药就能控制病情。如神应散中单用桂心,不拘多少,甘锅内煅,微存性,为末,每服一二钱,米饮调下治疗妇人血崩不止;又一方以黄芩,不以多少,为细末,每服一钱,霹雳酒调下治崩中下血;又如用新缩砂仁,不以多少,于新瓦上炒香,为细末,米饮酒调下治血崩。
3.2 治疗重补脾胃、调肝肾补脾胃、调肝肾是陈氏治疗崩漏的又一大特色。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崩漏为出血性疾病,故当补脾胃以益气血。且气血为人身之阴阳,阳主升,阴主降,阳根阴,阴根阳,一升一降,循经而行,无崩漏也。陈氏认为崩漏的主要病机为冲任虚损,冲脉为血海,肝藏血,冲脉隶属于肝,任脉主胞胎,属于肾。陈氏药用当归、白芍、香附、龟甲、龙骨、牡蛎等以补脾胃、调肝肾,脾气健则冲任二脉充盈有度,肝气条畅则冲任血海溢止有时,肾气盛则任脉通,冲脉盛。陈氏通过补脾胃、调肝肾以达到调理冲任的目的,使经行依时有度。
4 结语
崩漏作为妇科危重症候,历来受到重视。陈氏《良方》分“崩暴下血不止方论”和“崩中漏下生死脉方论”两篇加以细致阐述,提出崩暴下血和崩中漏下主要病机是冲任虚损,但在病因上稍有不同,崩暴下血有风伤冲任和阴虚阳搏,热伤冲任,崩中漏下主要为虚寒相搏,并且在治疗上以祛风止血和滋阴凉血止崩、温肾祛寒止漏分别对待。用药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善用止血药急则治标,重视补脾胃、调肝肾以固冲任,这些治疗思想对后世医家具有一定的影响,是旴江医学妇科崩漏治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陈氏晚近300年的另一旴江代表医家龚廷贤,在妇科学术上也造诣颇深,其崩漏的诊疗思想相较陈自明各有千秋。在病机上,龚氏主要责之于脾胃,强调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损而致冲任失调;在治疗上,龚氏擅化裁四物,重补血理气[10]。并强调“升阳”法在治疗崩漏中的作用,龚氏在治疗崩漏上还有联合酒方,配以灸法及熏法,这些治疗思想上的异同体现出旴江医学随着历史的更迭在不断的向前发展。江西旴江医学自秦汉发端以来,历代多有发展,尤其是宋代以后,因本区域社会文化的崛起而得到迅速壮大,明清两代达到鼎盛[11]。旴江医学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后世努力发掘,这有利于传承和弘扬江西地方医学特色,升华和拓展江西地方医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