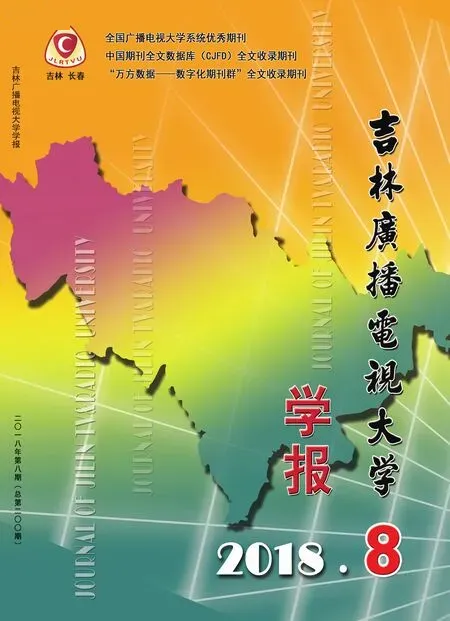论《爵士乐》中的母性缺失与自我构建
李可一 刘晓露
(明德天心中学,湖南 长沙 410004;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作为美国当代黑人女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作品始终强调主体自我获得承认、肯定和爱的需要,始终关注黑人主体是如何在以白人文化为主宰的美国文学中被构建起来的。在一次关于小说《爵士乐》的访谈中,莫里森指出女主人公维奥莱特其实是在沉睡的状态中死去。“没有什么能让她复生,除了那个拥抱生命的灵魂或精神,那个当我们说“我”时所意味的东西。它是如此被忽视,如此沉默,如此不被统治世界的力量所接受……那是自尊诞生或毁灭的地方……我们需要释放,以自我的那部分为荣……这对人类而言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寻找那种人、那样的理念和思想构成了我的大部分作品。”自我必须获得爱和认同,用莫里森的话说,就是得到尊重和释放。当我们无视或疏于照顾真实的自我时,我们会丢失、忘记我们原本的样子,就会像维奥莱特那样陷入沉睡。
莫里森指出自爱取决于自我首先被另一个自我所爱。在一个孩子学会爱自己之前,他必须经历自我被爱,从而证明自我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这份感情的。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强调了母爱对一个孩子情感健康的重要性,因为正是母亲首先爱孩子,赋予他一种被爱的自我认知。那些被遗弃的,从未得到母爱关怀的孤儿,在成年后通常有心理创伤。失去母爱的孩子从未学会如何去爱他们自己,没有这种自爱,自我会迷失、被遗忘。因此,正确的过程是母爱——自爱——自我。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说《爵士乐》即讲述了一群母爱缺失的孩子们的故事,他们没能完成从母爱到自爱的旅程,因此也从未真正认识自我。
一、维奥莱特与罗丝·蒂尔:源自母性之殇的裂缝
《爵士乐》以二十世纪初美国大迁徙运动为历史背景,讲述了黑人夫妇乔与维奥莱特离开南部乡村融入北方城市的经历。叙述者用“头脑里的裂纹”“黑暗的缝隙”“粘得很糟的接缝”来描述维奥莱特主体意识的分裂和破碎。她很小的时候,母亲罗丝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重担而自杀。小时候,外婆总是给她讲一个金发小孩的故事。这个金发小孩叫戈尔登·格雷,是白人路易斯小姐和一个黑人小伙所生的儿子。从外婆关于金发男孩被溺爱被崇拜的故事中,维奥莱特得知拥有白皮肤和成为男性,就能获得爱和快乐。她同样从那些故事中得知她的母亲,外婆的其中一个女儿,在外婆追随主人路易斯小姐去巴尔的摩时被留在了身后。本该属于女儿们的母爱被慷慨地赠予了长着黄色卷毛的白人男孩。可外婆并不恨这个把她从女儿身边夺走的男孩,相反,她爱这个“美丽的年轻人”,这个让外婆忘了自己女儿的男人也同样迷惑了维奥莱特的心,并且毁掉了她的自我价值。她的欲望不仅仅是得到戈尔登的爱,更是要成为他。小说结尾,维奥莱特告诉费莉丝她的脑子里住着一个爱耍花招的金发小孩,她又是如何把生活搞了个一团糟:
“现在我想做我妈妈没能活着看到的女人。那一个。她会喜欢的那一个,我以前也喜欢的那一个……我外婆老把一个金发小孩的故事灌给我。他是个男孩,可有时我把他当作一个女孩,当作一个兄弟,有时当作一个男朋友。他活在我的脑子里,像颗痣一样沉默。可直到我来到这里才知道。我们两个,必须摆脱它。”
……
“你是怎么摆脱她的?”
“杀了她。然后我把那个杀了她的我也杀了。”
住在脑子里的金发小孩是导致维奥莱特心理创伤和伴随而来的自我错位的根源,也是死去母亲的替代品。美国学者黛博拉·麦克道尔(Deborah McDowell)指出对死去母亲的回忆是小说《爵士乐》的原动力,更确切地说,文本的原动力是对替代母亲的追寻。一系列错位,一系列替代推进着维奥莱特的叙事。无论是对金发男孩戈尔登的迷恋,还是对丈夫乔的爱,亦或是后来对死去女孩多卡丝的着迷,对母亲的饥渴像重锤敲打着她,她试图填补因母亲去世而产生的自我空洞。
维奥莱特对母亲身份的抗拒也与母亲的缺失有关。“维奥莱特从中得出的重大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孩子。不管发生什么,决不要有一双小黑脚叠在一起,一张饥饿的小嘴叫着:妈妈?”维奥莱特后来经历的三次流产,“与其说是丧失,还不如说是不便。”流产似乎是自我诱导的,象征着维奥莱特对母亲身份的抗拒,更确切地说,她拒绝变成她母亲那样。
尽管维奥莱特拒绝母亲身份,她却不断地把自己置于母亲的角色。小说中,维奥莱特“盯着小孩子看,在圣诞节展销的玩具前面踌躇不前……渐渐地,热望变得比性爱更难对付了:一种令人心跳气短、不能控制的饥渴”。维奥莱特用一个藏在床下的娃娃安抚自己,甚至企图把别人的孩子抱回家。日常生活中,她也表现出与其她女性的母性认同。维奥莱特靠给人烫头发谋生,烫头发代表了一种母性行为,顾客是她的替代孩子,她从未有过的女儿们。通过打扮这些女士,维奥莱特获得了母亲身份,向她的孩子们提供养育和咨询。一看到多卡斯的照片,她就想要把她的发角修修。就如那些顾客是她的女儿们一样,鸟也是,乔曾对邻居玛尔芳抱怨“维奥莱特对她的鹦鹉比对我照顾得更好”。
试图通过养育别人找回失去的自我——对多卡斯、洋娃娃、抱走的孩子、做头发的顾客、鹦鹉——维奥莱特实际上试图成为她失去的母亲。更重要的是,通过像母亲一样抚育他人,她渴望发现作为女儿的原来的自己。她把自己投射在她照顾的人和动物上,这样,成年的维奥莱特抚育了作为孩子的维奥莱特。她自己抚育了自己。通过这种养育,维奥莱特既可以成为她失去的母亲,也同时是曾经作为女儿的自己。
最终在年长女性爱丽丝的开导下,维奥莱特认同了她的母亲罗丝,理解了母亲的人生。维奥莱特终于理解母亲为什么没有养育她。罗丝当不了女儿的母亲,因为她自己从未被当作女儿养育过。维奥莱特意识到了母亲身上缺失的母爱,这种认识使女儿—女儿之间的认同成为可能,反过来又强化了母女间的联结。当维奥莱特记起作为母亲、作为女性、作为女儿的妈妈时,维奥莱特也找回了自我。她心中死去的那个女孩复活了。用莫里森的话说,“她现在就在这儿,活生生的。我看到她,命名她,索要她——她是一个多么好的陪伴啊。”与母亲的认同将维奥莱特带回她的自我,内心里狭窄、黑暗部分关闭了,粘得很糟的缝隙得以修复,自我变得圆满完整,在寻找母亲的秘密花园时,她找到了自己的花园。
二、乔与“野女人”:追寻母亲的痕迹
《爵士乐》中另一个缺席的母亲是“野女人”(Wild)——乔的生母。“这人脑筋彻底毁了,连最差劲的母猪都能办到的事也不会做:给自己下的崽子喂奶。”戈尔登第一次看到野女人是在树林中,他描述她是“一个莓子一样黑的裸体女人,浑身粘满了泥浆,头发里净是树叶”。她的肚子又大又紧,他被吓住了,他想这不是一个真的女人,而是一个幻影。野女人居住在一个典型的女性空间——子宫一样的洞穴中,存在于法律、秩序、理性的男性世界之外。她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是粗暴、原始、被放逐的女性自我。野女人嚎叫、大笑、撕咬、歌唱,但她从不说话。当乔第一次听到野女人唱歌时,他错误地认为她的歌是天地奏出的音乐,是流水和高高的树中间的风共同发出的声音。当乔在灌木丛中寻找野女人以确认她就是他的母亲时,他所想要的只是一个信号,“他不需要语言,甚至没想过要语言,因为他知道语言是会说谎的,会烧得你热血沸腾然后就无影无踪了……她要做的只不过是给他一个表示,把手从树叶中间一下子伸过来”。野女人通过触摸交流,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说,她是用身体写作。通过笑声、歌唱、触摸,野女人讲述了前俄狄浦斯母性空间的前话语语言。
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了主体表达在表意过程中出现的符号界(the semiotic)和象征界(the symbolic)两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她那里,象征界是指语言学家所认定的意义本身,而符号界则是语言中的动力因素,它与节奏、音调等相关,是非语言或先于语言的,不能化约为语法和逻辑结构。这种用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前俄狄浦斯语言,是一种特别的标志、痕迹和索引。澳大利亚女学者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把这种符号定义为“前指义的能量。”她认为符号界是内在性冲动无序无形的循环,以无束缚的方式在孩子的体内循环。这种多形态的,不合常情的冲动无视现实法则,仅靠自身的力比多驱动。符号界在象征界中爆发,它表现得如同中断,是文本的不和谐音,是不受文本逻辑和叙述控制的节奏。这种记号既是象征界功能的前置条件,又是不受控制的放纵,可以为话语使用,但不能发声。
野女人代表了符号界不受控制的放纵。她的大笑、歌唱、触摸构成了符号界叙述语言。克里斯蒂娃解释了符号界是如何打断象征界并以节奏、文字游戏、曲调、大笑等形式回归。野女人同样存在于象征界之外,用她女婴般的笑声,指甲的轻敲瓦解了作为象征界的男性世界。克里斯蒂娃把符号界定义为痕迹,同样的,野女人的儿子给自己取了“特雷斯(痕迹)”这个姓。野女人的家也是作为前俄狄浦斯母性空间而呈现的。她住在如同子宫般的洞穴里,乔第一次寻找母亲时,他“找到了石洞的入口,却无法从那个角度进洞。他得爬到它上面,再从它的口里滑进去”。几年后,乔再次试图进入洞穴,他“爬进了一块低得能擦到他头发的空地……他不能够在里面转身,就拖着整个身子一路爬出去,好让头朝前再进来……然后他看见了那个裂口,他屁股着地滑进去,一直滑到了底儿。就好像掉进了太阳里面”。这里描述了回归母体的场景。乔顺着产道,穿过子宫颈,进入子宫,婴儿的出生通道被反转过来,一个成年男性寻求重新进入母亲的子宫。乔进入了“野姑娘那间金色的房间”,回到了初始之地。乔渴望发现他来自哪里以便他最终可以知道他是谁。对光线的指代,“就好像掉进了太阳里面”,颠覆了柏拉图洞穴的黑色虚无。这个通道暗示了黑暗是光,洞穴——子宫——则是原点之锚。
不同于同时代男性作家的“父爱饥渴”主题,莫里森的《爵士乐》则讲述了一个关于男性的伤痕和治愈完全不同的故事。乔遭受的不是父爱饥渴,而是作为一个得不到母爱的孩子的忧伤。母爱缺失导致了乔的心理创伤。乔从未哀悼到时生物学上父亲的缺席,事实上,乔从未想知道亲生父亲是谁,文本也没有推测他父亲的身份。
乔曾三次动身寻找野女人。乔想证实“她千真万确就是他的母亲,就算得到证实将让他感到耻辱,他还是会成为弗吉尼亚最幸福的孩子……是。不是。两者都行。其中一种也可以。但不要这样一声不吭啊”。当他的乞求得不到回应时,他带着愤怒和耻辱转身跑了。“那种内心空虚,从此被带在了身上”。乔不断从一种身份转向另一种。“在认识她(多卡丝)之前,总共改变过七次”。多年后,情人多卡斯的出现填补了乔内在的空虚。乔在多卡斯身上找到了他从未见过的母亲,她脸颊上的雀斑成为寻找母亲的痕迹:
她要我买的护肤品我都买了,可令人高兴的是没有一样管用。把我脸上那些小蹄印去掉?一点痕迹也不给我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唯一的东西,就是找到那条路,决不放弃。我在弗吉尼亚追踪我的母亲,那条路引着我找到了她。
在乔的意识中,野女人和多卡斯合二为一,因为多卡斯“头脑冷静,甚至很野”。乔开枪射杀移情别恋的多卡斯,叙述者承认“直到此时此刻我也拿不准他的眼泪到底为了什么而流,不过我敢肯定那不仅仅是给多卡丝的。当时,他顶风冒雨地满街乱跑,我一直以为他是在找她,而不是找‘野姑娘’那间金色的屋子”。
野女人才是那个被乔打中的女人,是她的死让乔哀悼。作为一个男孩,乔从未和母亲的达成和解,他费尽一生试图忘记他的母亲,试图成为别人而不是自己母亲的儿子。当他第二次失去母亲时,乔重新经历了作为孩子被否认、被压抑的痛苦和缺失。只有当乔真正承认并体验到失去母亲的情感伤害时,治愈才成为可能。随着多卡斯的死,乔最终能够哀悼母亲的死,并学会和过去和解,重新找回曾经丢失、错位的自我。
三、结语
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认为语言永远地把我们从母体分离。语言是无限衍义之链,无止尽的差异运动,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寻找着想象中的自我完整和统一。美国学者麦迪龙(Madelon Sprengnether)在《幽灵母亲》中写道:欲望永远无法获得它的客体,能指无法捕捉或包含所指;主体必须永远对他和她自己保持未知。这种欲望创造了语言。我们不断地更换替代物,用隐喻替代隐喻,却从未能恢复我们想象中的纯粹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完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语言把我们从母体分离,乔不断变换的身份和对母亲的追寻模仿了替代物无限衍义的过程。正如《宠儿》以数字124作为开头,《爵士乐》用声音开始叙述:某个声音——女人穿针之前添湿手上的线时嘴上发出的动静。这样,我们不是通过语言进入文本,而是通过非语言、前话语的声音,这个声音是舌头和嘴唇接触时发出的,是身体原始、本初的语言,在话语之外循环。《爵士乐》的叙述以典型的母性话语开始,把乔和维奥莱特对失去母亲的记忆联结在一起。《爵士乐》肯定并赞美了母性。没有得到母爱的孩子身上深刻的心理创伤提醒读者母爱对自我认知和情感健康是多么重要。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治愈才有可能发生,自我改变和重生的希望开始于母亲。也许那双推动摇篮的手不会统治世界,但它们却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并为我们指明未来的道路。在追寻母亲的秘密花园时,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