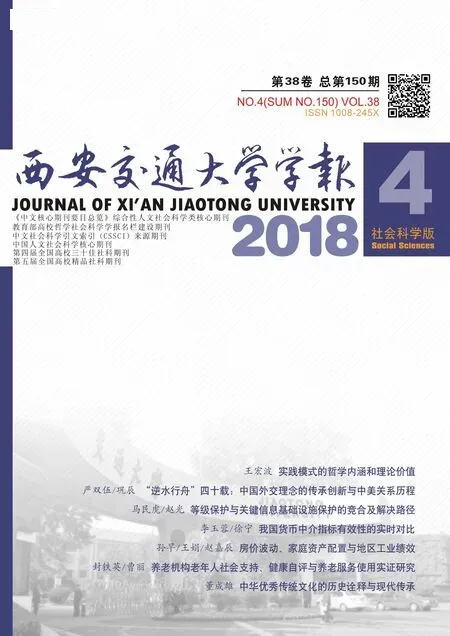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诠释与现代传承
董成雄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自从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构建优秀传统传承体系的重要部署,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就这个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科学的传承体系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已无须赘述。2017年1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再次强调当前“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迫切需要加强政策支持,着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三个“迫切需要”说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应围绕“体系”二字展开,重点是做好“两个体系”的构建与衔接,即整理出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体系构架及现代传承体系构架,再把二者有机地衔接起来,才能高屋建瓴地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前,已经有研究借助文化的结构功能理论尝试性地梳理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架构[1],因此,本文将借助哲学解释学理论深化对文化传承的理解,并根据文化学理论梳理传承体系的构建。
一、华夏传统的源头与活水:从前轴心期到轴心期的精神觉醒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Landman)[2]4认为人类是历史和文化的创造物,所以人的本质不能靠生物遗传继承,代替遗传保存祖先的现实形式便是文化传统。祖先文化的传承是人类社会早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创新的基础。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Meader)[3]28-29在其所著的《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曾把人类文化的传承分为三种类型,即“前塑”“同塑”和“后塑”文化(Pre-figurative;Co-figurative;Post-figurative)。她把“前塑”文化定义为老年文化,认为它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在当时社会落后封闭又尚未有文字传承的环境中,前辈经验几乎就成为后辈在知识、技能、价值等方面的唯一来源。由于前辈通过教育把他所掌握的东西晓谕、传授给晚辈,因此,前辈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礼仪准则和生产技能皆为后辈的楷模,即使祖先死后,其教诲也成为子孙应该遵奉的准则。由于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在各家庭、家族、氏族中具有普遍性,于是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习俗,社会成员借助习得的文化模式或行为而产生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也可以说,以祖先教诲、社会习俗、先王(实为氏族部落首领)传说为主的“前塑”文化既是原初的传统,也是后来传统文化的源头,即使原始社会进入“农业文明”后,“前塑”文化仍然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模式。在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长期延续,于是“前塑”文化又通过“法古”“法圣”“法先王”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来,《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云:“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可见早在夏初,祖宗与先王的典则已成为传统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应该说古人对这种传统合法性的承认并非盲目的迷信,因为它本身就是经过许多先辈长期的社会实践筛选、检验才获得合理性认证的。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视传统的国族。在古人看来,所谓“传统”就是指先王先圣所创立的帝业学说被后人世世相传并转化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正统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墨子·贵义》也说:“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这表明古人对先王先圣留下来的政治文化遗产有自觉的传承意识。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对先王之道、祖宗之法就表现出高度的推崇和虔诚的敬意。《尚书》中的《商书》《周书》诸篇经常提到“稽古”“承古”“师古”之类的话,声称“学于古训乃有获”[4]253“不由古训,于其何训?”[4]525“前塑”的价值取向极其明显。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主义者。在古代,“述”与“作”是一种表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对举关系,《墨子·耕柱》说:“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可见“述作”所含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其指向皆为“善之益多”。《礼记·乐记》云:“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这是把圣人与贤明看作文化创新与传承的承担者。孔子虽然从不以圣人自居,自称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还是认为传统是在传承和损益中发展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看到正是由于“周监乎二代”,才发展出“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化。而西周文化又一直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后学所景仰。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以说正是有了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传统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但如果我们要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就应该重点关注先秦文化。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5]14的“轴心期”理论对我们今天理解先秦文化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依然深有启发。他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寻找一种超越西方基督教历史而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假若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轴心的话,它要能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由此,他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定为历史的轴心,因为在这一期间,世界上三个地区(中国、印度和西方)都出现了精神的觉醒,形成三个“精神辐射中心”,并建立了精神传播运动。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哲人们探询根本性的问题,并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在雅斯贝尔斯(Jaspers)看来,“轴心期”奠定的世界历史结构表现在:第一,它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被融化、吸收进入了“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第二,直到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为我们提供精神动力;第三,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要么与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隔绝而保持原始状态,要么与其中一个接触而被拖进历史(如东方的日本人、马来人等)。总之,“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5]15。由此可见,他已敏锐地看到“轴心期”的文化创造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即精神的觉醒使哲人懂得反思人类的历史以探寻根本问题;精神的创造奠定了人类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精神的传播带动其他民族的发展;精神的传承使后世的飞跃获得了这一文化遗产的滋养。西方的文艺复兴从它们的“轴心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便是一个范例。在中国,“轴心期”同样奠定了(近代以前)中华民族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思想框架,这就是我们强调把传统追溯到“轴心期”文化这一源头活水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轴心期”文化还有它更原初的源头。雅斯贝尔斯(Jaspers)提到中国“轴心期”时只讲到诸子百家,但在诸子之前中国已有三代礼乐文明。作为一种“早熟”的文明,古人甚至将自己的文化源头追溯到三皇五帝的《三坟》《五典》,即使它并非信史,但作为口述传统亦有可信之处;而有文字记载的三代文化典籍《六经》基本可信,因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轴心期”之前还有一个“前轴心”时代,它就是孕育中华文明的“苗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认为古希腊和希伯莱是世界文明演化的“苗床社会”(seedbed societies),中国和印度文明却不在其列。显然,这种观点带有偏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提出一种原型文化理论,认为一切文化都是由其原型文化所决定的,人类的创造性行为无不受到给定的文化系统的制约[6]398。其实,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在中国,三代先王先圣创造的文化便是华夏的原型文化,《六经》则是先王文化的结晶。“轴心期”的诸子百家均出于“王官”,并受《六经》影响,《庄子·天下篇》指出:古之道术其在《诗》《书》《礼》《乐》者,除了“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外,“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后来黄宗羲也说:“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但诸子百家并非简单地继承“前轴心”期的原型文化,而是在列国竞争、思想多元的时代推进了哲学的突破和文化的繁荣,因此,从“前轴心”到“轴心”时代,华夏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与核心命题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立君为民”“为政以德”“允执其中”“兼爱尚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循道而为”“缘法而治”“世异备变”“穷变通久”等均已出现。与此同时,华夏的文化精神如道家的哲学精神、批判精神、自由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正义精神、中和精神;墨家的博爱精神、平等精神、务实精神;法家的进取精神、变革精神、法治精神;民间的功利精神、商业精神等,也在诸子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关怀中自发地展现出来。由于“轴心期”文化的哲学突破“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前后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因此,它也包含着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无论是中古儒生的“述圣”“述孔”,还是明末三大家与清末康、梁等唤起的启蒙思潮,甚至现代新儒家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都在这个古代文化宝库中汲取精神资源,所以雅斯贝尔斯(Jaspers)说:“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5]11即使“西化派”的重要代表胡适也不敢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他说:“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胡适也非常肯定诸子百家的思想价值,认为“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7]773。我们今天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必要唤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
二、传统的诠释与传承:从自在状态到从自觉建构的时代转化
任何传统文化都是时代的产物,以满足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因此,回归“轴心”时代不可能述而不作,而需要通过创造性诠释与时代性转化来实现古今对接。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古为今用”的道理,通过诠释传统而超越传统本身就是他们的一贯“传统”。在古代,所谓“道”,既是圣贤对社会理性的高度凝练,又是传统的载体;它既可以是口述传统,也可以是经典文本。“祖述尧舜”中的“述”就是没有文本依据的尧舜传统。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说明三代未有典册之前的述作也有部分在口述传统的基础上“损益”。到“天下无道”的东周乱世,诸子百家为解决“救世”的时代课题,几乎皆“挟古自重”或“挟圣自重”,连最有变革精神的法家也不例外。李明辉先生说:“西方思想家往往透过批判前人的学说来建构自己的学说,而中国思想家即使提出新说,也要强调自己只是‘道’的诠释者。”[8]442孔子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看出,战国时代出现许多托名“黄帝”的著作,其实均是思想家自己主观诠释黄帝思想的产物。黄帝的思想是什么虽然没人知道,但人们知道他是华夏传统的象征,托名黄帝即是在祖述传统。秦汉大一统后,经过汉初统治者弃法入道的摸索,到汉武帝时再次以“更化”的名义回归三代礼乐传统,重建礼制,独尊儒学,并以“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9]275一语来强调“更化”的指导思想。汉末经学衰落,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通过“祖述老庄”建立清新简约的玄学体系,但“名教本乎自然”的结论扭曲了老子的思想而迎合了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隋唐是外来佛教兴盛的时代,国人先是用“格义”之法对它作了中国式的诠释,接着又用本土宗法文化把它改造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使佛教实现了“洋为中用”的转化。此后,宋明理学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根本,采纳佛教的思辨哲学诠释“天理”,重新确立了儒学在理论上的主导地位,也被认为是在继承“道统”。直到近代西风东渐后,思想家们更是以西学来解释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甚至以古代“大同”理想与舶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接,意在以“托古改制”之名行“托西改制”之实。由此可见,所谓传统,长期以来就被“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所解释和创新。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古人对传统的创造性诠释基本上还属于自发产生或处于自在状态,缺乏自为的意识和自觉的理论建构。就后者而言,西方近现代解释学在方法论哲学上解释传统经典方面是颇有建树的。一般来说,近代以来解释学大致可分为“以作者为中心”的客观路向和“以读者为中心”的主观路向。前者比较“坚持忠实于原典”,例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把解释学理解为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其任务为“主观地重建客观过程”,即重建文本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把握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原意[8]18。另一个重要代表狄尔泰(Dilthey)也主张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解释要对历史文本作出客观的理解。他认为我们与他人、古人与今人之间存在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这就使我们不仅可以和他人对话,也可以和历史对话。理解文本就是通过对话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再现他人内心体验和作品的意愿。但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也看到“诠释者对作者的理解,应该胜于作者对自己的理解”[10]107,狄尔泰(Dilthey)则认为“理解就是在你中重新发现了我”[8]57。可见客观主义的立场也只能是相对的,这就为后一种解释学的发展作了铺垫。
倾向于“读者中心论”的现代解释学的特点是不坚持忠实于原典,而认为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还是一种更新历史文化的创造。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理解活动有赖于理解的“先结构”[10]122,即一些在理解前便已存在并决定理解的因素;而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又有一个“认识预期”,它也是待解释的意义的一个部分。于是理解活动便成了“认识预期”、解释者的“情境”与“前结构”之间的“循环”。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Heidegger)主张解释就是“要冒犯文本”(doing violence to the text)才能将一部文本的意义比较完整地释放出来,这就承认解释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的色彩。其后,伽达默尔(Gadamer)又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他的哲学解释学[10]218。其理论有几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它揭示了解释经典不只有方法论的意义,更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他看来,理解活动是活生生存在的人去认知,类似“我存故我思”;但我存与我思并非毫无先入经验而完全客观地去观察理解客体对象;能理解文化,就一定是生存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受其塑造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课题对象的人。所以必须以人精神活动中的“理解”现象为探讨对象。第二,它强调解释的主观性和“偏见”的合理性。由于不同历史情境下不同认知主体有各自的特殊视界,因此他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往往是不同的,这就带来了理解者的“偏见”。有学者认为“经典不说话,除非我们发问”印证了伽达默尔(Gadamer)解释学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诠释者有问题意识且问题提得好,就能把蕴藏于其中的微言大义发掘出来。第三,它指出理解过程就是经典文本的作者之视界与解释文本的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一个理解活动好比经典文本作者在特定视界内向解释者提出若干问题,理解这个本文就是理解它所提的那些问题;而为了理解本文所提的问题,就要超出本文的历史视界,从而使文本作者的视界与理解者自身的视界相融合,于是理解者也超越了自身的视界而得出了新的答案,一个答案意味着又一个问题,推动理解者和对象本文之间产生新的互动。
三、传承的返本与开新:从“原始”到“要终”的逐步推进
应该承认,西方解释学无论是“以作者为中心”还是“以读者为中心”,对经典的解释均有各自的价值,其合理成分也值得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承借鉴吸收。克罗齐(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敏锐地看到:“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他们的坟墓里,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才被欧洲精神新的成熟所唤醒……历史的伟大论著现在对我们说来是编年纪录,许多文献目前是默默无声,但是等到时来运转,生命的新的闪光又会从它们的身上掠过,它们又会重新侃侃而言。”[11]9在我们看来,今天的中国要唤醒传统的文化生命,重点是把握好解读传统文化几个环节的内在关系,在分梳传统文本的“含义”及其“意义”的问题上,要掌握好二者的平衡。任何经典文本当然有其固有的“含义”,但在经典的解释者看来它也可能包含比本义更进一步的“意义”,甚至可以发掘出原作者未必意识到的意义。傅伟勋曾把创造性诠释分为五个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8]434,分别探讨了原作者实际说了什么;其意思是什么;还可能蕴含什么;诠释者应当为原作者说出什么;为解决原作者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性诠释现在要做什么。有学者认为前三个层次相当于“解释”,后两个层次相当于“诠释”。显然,“以作者为中心”的解释学侧重于揭示文本的“含义”;“以读者为中心”的诠释学着眼于发掘文本的“意义”。弄清文本的含义虽然是发掘其意义的基础,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弄清含义的层面上而不进一步发掘其意义,那么文本就成为僵死的东西,与后人面对的时代课题就出现了断裂,使用只有激活文本才能接续断裂、传承传统。在这方面古人对先圣“微言大义”的发明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出色的范例。另一个反例则是,清代朴学的训诂考据极其发达,学者们对经典“含义”的解释纵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这方面现代学者也比不上),但却未能推动中国社会汇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与此相反,康有为却通过发掘经典的“意义”揭示了变革的时代课题。
在创造性地诠释经典文本“意义”的基础上,又要防止“过度诠释”与“不足诠释”两种极端倾向。意大利教授艾柯(Eco)[12]83曾提出,诠释文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诠释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一种是“使用文本”(using a text)。前者把诠释停留在文本的语义学范围内,可造成“不足诠释”;后者把自己的主观意愿打扮成作者的原意,这就是“过度诠释”。如果文本解释未能在文本的客观性与解释者的主观性之间保持适度的均衡,就可能出现“过度诠释”或“不足诠释”的情况。例如,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犹如“过度诠释”和“不足诠释”的两种典型:古文经学派解经忠实于圣人原意,致力于字斟句酌的训诂,被今文家讥讽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而今文经学派释经则迎合现实需要,致力于附会其中的“微言大义”,被古文家斥为“为学疏略,难以应敌”[13]3189。但“过度诠释”和“不足诠释”都不是好的诠释,因为圣贤的“中道”思想已揭示了“过犹不及”“允执其中”的道理,前者可能导致望文生义,信马由缰;后者则可能造成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最终都没有达到传承的目的。其实,古人早有“原始要终”“原始反终”之说,即考其本始而要约其终,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应该是前者的目的。但就我们今天的经典诠释来说应该有合理分工,即整理国故者应以“原始”为据;发扬传统者以“要终”为本。
在对待“过度诠释”与“不足诠释”两种倾向上,我们仍要正视一个现实,即绝对忠实于文本作者的原意是不可能的。例如《六经》只是一些朝廷的文书档案,其原作者则是一些无名的官吏,根本不知他们留下的这些文书对后世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伽达默尔(Gadamer)[14]383认为,当初这些文本的原作者“并不需要知道他所写的东西的真实意义,因而解释者常常能够而且必须比作者理解的更多些”。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即已指出,“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同样,“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15]457诚然,这种无头公案无人判得了,甚至没必要清楚判明谁真谁假,因为古人早就懂得“《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道理,故主张“从变从义一以奉人”[16]95“道无求备,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也”[17]1549。既然通过“原始”仍不能穷尽其理,故有必要拓展诠释的空间。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返本”与“开新”问题上,必须把握好几对辩证关系。一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任何传统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它的“前结构”,而后人的传承则有后人的“现结构”。诠释传统文本不仅是诠释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对话和视界融合,还是历史“前结构”与当下“现结构”之间的全面交融,而传统的价值与时代的课题则是它们的粘合剂。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9]275,汉武帝在准备推行“更化”时对贤良文学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18]1912,可见“征于人”“验于今”更重要,诠释应服从现实的需要。二是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关系;由于先人的智慧是可以被后人传承的,任何传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任何文本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必定有其合理性。但由于社会在进步,历史的合理性不等于当下的合理性,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它同样存在时代的局限、环境的局限、个人的局限等,即使圣人圣王也受制于这些局限,所以夏、商、周之间的文化“损益”可以视为对前代文化局限性的认识与扬弃,这就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三是包容性与选择性的关系;传统的形成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丰富自身、发展自身的过程,因此,包容性是发展自身的必要前提,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诸夏与四夷文化的聚合过程。即使是异邦优秀文化,中国也善于包容、吸收与转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期间对来自印度的佛教的包容和吸收,使佛教最终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由于西风东渐的影响,中国又形成了以进步、竞争、创造、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近代精神传统[19]75,包括以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础的红色文化传统,极大改变了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但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并不是不加选择地通盘接收,而是像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那样,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有一个“认识预期”,当主体带着认识预期对认识对象进行理解诠释的时候,对不符合自己价值取向(或利益取向)的东西必然有一个选择、过滤、防御、拒斥的过程,毛泽东所说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其实就是主体对古代文化及外来文化的防御机制与认同机制。四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传统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是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无法简单切除的文化基因。文化结构理论认为,一个民族经共同的历史、语言、传统形成的固定心态,是该文化中最稳定、最不容易产生律动和发生突变的心理层次,属于该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民族性的体现;相对而言,宗教、哲学、道德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则是文化表层结构。从空间上看,同一个民族群体中可以兼容多种宗教、哲学、道德和风俗;从时间上看,这些表层结构的文化成分又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近代以来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宗教、哲学、道德和风俗等表层结构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化学理论同时认为,“民族潜意识”在无形中制约着表层文化的变化,任何文化表层结构的变迁都只能向文化深层结构意向回归,这就是民族性的力量。例如,近代日本人在表层文化上几乎被欧化,但在深层文化上仍然保留着“菊与剑”的民族性。又如,胡适、鲁迅都是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者,但在个人婚姻上的保守性又表明他们骨子里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另一方面,在五洲大通的时代,不知世界变化的大势,不愿汇入时代的潮流,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逃脱不了自我淘汰的悲剧的。从19世纪中期到后期,拒绝变革的清廷和积极维新的日本两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新中国建立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巨变同样也表明了这一点。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如百舸争流,文化的民族性必须与世界性对接才有出路。
四、传承的途经与目标:从体系构建到文化更新的实践举措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既要有对历史遗产的把握,又要有对当下情势的认识,还要有对未来趋势的展望。这就需要从文化学理论中提炼一些基本概念,建立一个由“文化反思”“文化选择”“文化诠释”“文化重组”“文化更新”诸环节环环相扣的学理分析框架,由此组成一个由“传承缘起”“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途径”“传承目标”诸要素有机结合的传承体系。
“文化反思”是“传承缘起”的媒介。所谓“文化反思”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对自我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再思考和再估计。它通常由内外两种原因促发,或由于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及政治制度发生变化引起了社会文化的不适;或由于与外来文化发生持续地接触、碰撞,受到一个与自身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的刺激,都会引起该民族的文化反思。在中国,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反思也不一样,近代因西方入侵、民族危机带来的维新派、革命派的文化反思自不必说;即使是“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反思与近年来的正面反思也完全不同。因为一个民族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通常会因缺乏民族自信而妄自菲薄,而当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际地位提高的时候,又会回顾追寻昔日的荣光,并引发不同于往昔的文化反思。当今中国经过二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出现了大国崛起、民族自信的新气象,时代的课题是呼唤文化自信的回归,中央也不失时机地作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西方文化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商品经济冲击导致精神家园荒芜的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这就是“传承缘起”。
“文化选择”与“传承主体”有关。所谓“文化选择”是指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变化后,原有的文化也要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新旧文化更替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文化不但将成为今后社会的主流文化,而且还将成为今后几代人(甚至更长)先天的文化环境,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掌握文化选择权的权力主体,即“传承主体”对文化选择负有特殊的历史性责任。一般来说,合理性较高、适应性较强的文化元素更有机会脱颖而出,而不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要求的文化则比较容易被淘汰,或被边缘化。例如,秦汉之际,中国治国思想经历了由法家经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变,文化选择的主体都是官方,特别是经过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传承了两千余年,这个选择与传承维持了中华文明两千年的稳定。当前,中央率先向全国人民发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学者应该主要承担文化选择的任务。中央的《意见》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这是对党中央作为传承主体地位的确认。
“文化诠释”对“传承内容”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也解决着那个时代的课题。但由于其中包含着民族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思想框架,被视为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又要通过文化诠释来开发其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例如民族精神、优秀思想、和谐伦理、文明礼仪等内容*笔者认为,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可包括“道”与“器”两大类,就“道”而言又可包括“天道”和“人道”,并由此展开[1]。虽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理性,但也不可能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现代,而需要经过民族文化精英对它们进行哲学上的新诠释或文化学上的再解释。所谓哲学再诠释主要是把它由“以古人为中心”的“含义”解释推进为“以今人为中心”的“意义”诠释;所谓文化再解释,则是把某些古代(或外来的)文化元素放在现代(或中国)社会环境中,作出与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相契合的解释,以实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无缝对接,并使古代的优秀思想、和谐伦理、文明礼仪等传统文化在现代获得新生。
“文化重组”与“传承途径”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为文化传承并不是纯粹的“返本”与诠释,它还要根据现实需要通过文化采借引入新元素、开创新局面,以实现古今中外的文化融合。所谓“文化重组”,就是把采借来的文化元素纳入现有的文化系统中重新组合,从而为现实服务。中央《意见》要求“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可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与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此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现代化建设也多有助益,因此,中、西、马历来被看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三大来源。然而,即使是优秀文化也需要适当的传播途径来付诸实施,对此,可以通过政府主导、精英推进、教育协同、社会熏染、外交推广等来贯彻。古人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20]639无形的“道”需要有形的“器”来实现,经过适当的化裁、变通,并推行、举措于天下,才能成就伟大事业。
构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主观上要实现“传承目标”,客观上要完成“文化更新”。所谓“文化更新”,是指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文化体系进行的更新,即新质文化取代原有文化的过程。但这种更新又分为“自主更新”和“非自主更新”两类,前者是指没有外来因素介入而靠社会自主发展产生的文化更新,如原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就发生了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的文化变革与更新;后者是指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下,双方经过长期的文化冲突而使弱势文化非自主地发生变革与更新,如清末民初的中国在西风的扫荡下发生的文化更新。当前中国完全是在高度的文化自信基础上进行的自主更新,文化传承的目标是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就是中央《意见》所指出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也就是说,它把本来、外来、未来三者结合起来,目标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