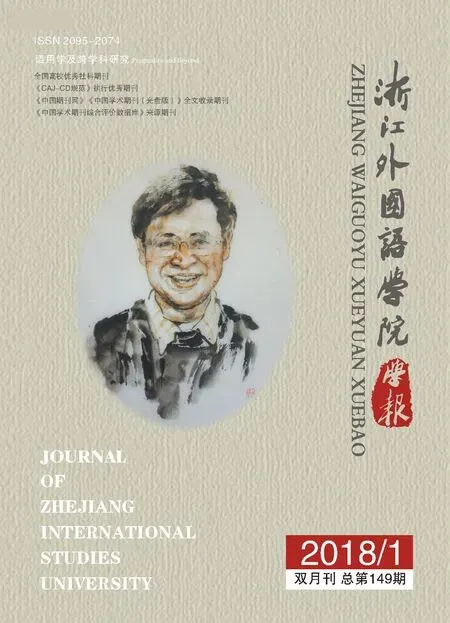中产趣味、人际隔阂与自然的拯救
——解读安·贝蒂的《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
黄姗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440100)
一、引言
安·贝蒂(Ann Beattie,1947— )是当代美国短篇小说家,与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齐名,二十多岁起开始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撰稿,笔耕不辍四十余年。贝蒂向来被认为是其所处时代中产阶级的代言人,善于书写此类人群的困境与挣扎,因而评论家常将其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相提并论。2011年,贝蒂精选其过往刊登于《纽约客》的短篇小说,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序,出版了合集《纽约客故事集》(The New Yorker Stories),并声称“其中收录的故事无疑都是她的最佳作品”(qtd.in Cox 2011:58)。该合集深入对比了贝蒂的前期与后期作品,很好地展现了其创作风格的演变过程。这种对比不仅体现在主题的变换方面,而且彰显于创作手法和看待问题的角度方面。对于部分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她作品的评论家,贝蒂公然表示抗议:“许多人在某个时间点后就不再阅读我的作品了。对这些人而言,我仍然是1976年他们所认为的那个样子。”(qtd.in Cox 2011:79)贝蒂的创作是流变发展的,虽然同样是书写中产阶级的迷茫,但她后期作品中的不少主人公似乎被编织进一个复杂而无形的网络之中,无法挣脱,只能寻求某种自我解脱的途径。贝蒂的后期作品也因此比前期更为苍凉而无奈。短篇小说《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The Last Odd Day in L.A.,以下简称《洛杉矶》)发表于2001年,为《纽约客故事集》所收录,是贝蒂后期的成熟之作。相较于她的前期作品,这部作品出现了诸多变化。比如困境的产生不再归咎于夫妻中的某一方;对人物情感的刻画愈加细腻、深刻,因而人物形象显得更加立体、丰满;笔触所及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而是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大环境等。在《洛杉矶》中,贝蒂刻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趣味区分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隔阂,揭示了此种趣味区分并非仅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habitus)和“场域”(field)形塑的结果,更是消费社会中大众媒体操控的产物。在“上帝已死”的后现代社会,贝蒂将拯救中产阶级精神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人与自然的重新联结之上,她的这种自然观呼应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历史悠久的超验主义思想。
二、趣味区分与人际隔阂
“趣味”(taste)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理论关注与辩论的焦点。康德及其之前的哲人皆把趣味看作是某种纯形式审美的主观偏好,而布迪厄摆脱了前人形而上的传统,从社会学角度看待趣味区分与阶级区分的关系,将趣味与客观的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他认为“趣味(也就是表现出来的偏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差别的实践证明”(2015:93),这种差别的实践与“必然的客观距离”越大,便“愈发成为韦伯称之为‘生活的风格化’的东西的产物,这种风格化是有系统的决定,它支配和构成各种各样的实践,如选择一个酒类制造年份和一块奶酪,或装饰一座乡间房屋”(2015:91)。贝蒂笔下的《洛杉矶》也正是以详细呈现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中产阶级的趣味区分来展开叙事的。
《洛杉矶》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按照趣味以及生活实践,他们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凯勒,曾经是大学教师,热衷于金钱与权力。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他认为“深刻改变过他人生的事”是几年前投资了微软的股票,这使他得以成为富贵闲人(134)。尽管住在波士顿郊区,但凯勒“从不读本地报纸”,在其眼中《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方能满足他的阅读趣味(144)。第二类是凯勒的妻子苏·安妮,热爱绘画与园艺,大学时就读艺术史专业,对卢浮宫和现代美术馆情有独钟。但是,她对艺术的审美趣味伴随着对物质与权力的拒斥,并使她走向了凯勒趣味的对立面。第三类是凯勒的女儿琳,住在坎布里奇,是一个白领。因为觉得“实属屈就”,所以琳与汽车机修工男友分手了,之后,换了一个又一个男友,她与后面的男友们有着“白领的职业和白领的渴望”(116)。琳的小资文艺偏好徘徊于物质与艺术之间,以一种“媚俗”(kitsch)的形象出现。第四类是凯勒姐姐的双胞胎儿女理查德和丽塔,他们住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山,都是股票经纪人,开宝马敞篷车,是时尚与享乐的追逐者,沉溺于欲望的解放之中,彰显了好莱坞式的纵欲与疯狂。
趣味的多样化本无可非议,但是在一个竞争性的现代社会,此种多样化不可避免地被人为地赋予了价值和等级的比较,正如布迪厄所言:“当趣味要为自己提供充足的理由时,它就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这并非偶然……审美的排斥异己具有可怕的暴力。”(2015:93-94)小说中,此种趣味的竞争体现为价值观的竞争。凯勒与妻子在趣味方面并不相投:他对妻子的兴趣不太上心,总把她最爱的那幅水粉画叫作水彩画,而妻子的纠正基本无效。不仅如此,凯勒依仗着自己的渊博知识,时常对家人冷嘲热讽,肆意贬低他人的趣味。“他擅长言辞的恐怖才华”(156)不可避免地给家人带来了情感创伤,最终导致妻子离他而去。他与女儿的相处也不那么愉快,琳“不想听到(凯勒)对她光鲜生活的任何批评”(122)。就连双胞胎在美国西海岸的时尚生活,在凯勒看来也是光怪陆离,“没个正经”(128)。小说中的四类趣味呈现冲突态势,从而成为凯勒等人彼此之间产生隔阂的直接原因。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叙述者凯勒是孤独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谁又会在乎他回不回家呢?他妻子不关心他住在哪儿,只要方向与她相反就行;他女儿也许会松一口气,他终于搬去了别处。”(129)正如贝蒂的大部分作品那般,《洛杉矶》同样将描写的重心放在中产阶级的精神“异化与解体”上(Centola 1990: 411)。
如果仅仅停留在此种人际隔阂与孤独感的描述上,那么《洛杉矶》与贝蒂前期的作品之间也就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了。事实上,该小说往前跨了一步,这一步凸显了贝蒂后期作品的主要特征,即把目光投向人物生存的社会环境,将情感状态的捕捉与社会无形之网的描述紧密交织在一起。
三、趣味区分与消费社会
贝蒂笔下的中产阶级缘何如此疏离而孤独呢?史蒂芬·R·森托拉(Steven R.Centola)给出了如下答案:“因为富人的生命几乎全部消耗在对物质目标的追逐上。”(1990:411)然而,他只道出了部分原因,物质固然是中产阶级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因为这关系着阶级的定位,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于是,贝蒂把更深层次的原因指向了此类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洛杉矶》中穿插了一段凯勒前往洛杉矶看望双胞胎的经历,这段旅程呼应了小说的标题“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足见其在整篇小说中的地位与意义。笔者认为,凯勒游览洛杉矶的所见所闻揭示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即由大众媒体所构建与操纵的消费社会。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趣味不仅受到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和“场域”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遭到媒体话语的操纵。
凯勒在洛杉矶逗留了几天,在“最后的古怪一日”来临之前,他参观了充满戏谑调侃、“旨在嘲讽所有博物馆的博物馆”,去了充斥着性欲色彩的寿司餐厅,入住了双胞胎在好莱坞山的房子,品尝了意大利熏火腿、意大利汽酒、“梅洛”葡萄酒、马斯卡帮尼乳酪以及有机李子(128-130)。凯勒沉浸在物欲的世界里,不能自拔。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The Consumer Society)一书中描述了当代社会中这种物的泛滥:“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2008:1-2)这里的物代指所有能够投入到消费(包括文化消费)市场的事物,而不仅仅是实体物品,还包括服务。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不会再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全部意义上去看全套的物。”(鲍德里亚2008:3)鲍德里亚认为物具有符号学象征意义,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解与布迪厄关于趣味与阶级区分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人们根据偏好购买同一系列的物,以物的象征功能对自身进行界定,而反观此种偏好的雷同又可以管窥他们的生活实践与思想倾向。双胞胎拥有光鲜的职业、宝马敞篷车、坐落在好莱坞山的房子,他们的“冰箱里有马斯卡帮尼乳酪,而不是农家鲜干酪,水果盒里塞满了有机李子,而不是皱巴巴的超市葡萄”(130),这一切清晰地展示着他们的品味倾向:金钱、时尚、享乐。这些物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趣味,也是他们界定身份的依据。
洛杉矶之行前后的强烈对比让凯勒产生了“顿悟”,冲洗水桶时他“在水槽边哭了起来”(132)。“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以及泳池边的《时尚》杂志象征着双胞胎所追求的品质生活,两者之间具有某种隐性的关联。凯勒独自一人站在露台上时,发现泳池边有一本被淋了雨的杂志,他觉得“这本《时尚》在绿色的瓷砖上瓦解腐烂,像高速公路上的垃圾一样恶心”(131)。正是这时,他意识到大众媒体对双胞胎生活风格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大众媒体正是在背后操控他们趣味的无形力量。他嘲讽女儿的趣味为“白领的渴望”(116),但他自己何尝不是这种无形力量操控下的产物?正如“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和《时尚》杂志之于双胞胎,《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同样形塑了凯勒的趣味、催生了他的欲望,他热衷于金钱与权力,并以此为标准对身边人作出居高临下的品评,这是多么可笑和无知。
四、“上帝已死”与自然的拯救
在贝蒂后期的创作中,宗教意象频繁出现。但是贝蒂笔下的宗教却无力拯救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宗教意象更多地是象征着业已丧失的传统价值观或集体精神信仰,通常暗示着“上帝已死”的内涵,比如《玛丽的家》(Home to Marie,1986)结尾处设置的基督诞生场景,《霍雷肖的把戏》(Horatio’s Trick,1987)中的柯南神父,《兔子洞是更可信的解释》(The Rabbit Hole as Likely Explanation,2004)中出现的教堂,抑或是《压顶石》(Coping Stones,2005)描述的名画《亚伯拉罕的祭献》中天使的双手。
《洛杉矶》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宗教意象。洛杉矶承载着“天使之城”的美誉,在此,凯勒明确地感觉到“什么东西正在注视着他”(133)。这里存在着对“上帝之眼”的映射与戏仿,凯勒在“天使之城”遭遇的“上帝之眼”是来自一头鹿的注视。然而,那头消失在好莱坞山中的鹿毕竟不是天使,它的“蹄子紧紧地抵住地面,而没有轻如薄纱的翅膀将它向上托举”(156)。上帝与天使已然死去,能将大部分人联结在一起的精神信仰也已不复存在。无怪乎凯勒在去洛杉矶机场的路上,脱下白色T恤举到空中说:“我在此屈服于天使之城的疯狂。”(135)
贝蒂对宗教意象的描写,既是对传统的怀念,也是对现状的揭露。在媒体话语盛行的消费社会,维系人际间关系的传统价值观已然丧失。媒体话语塑造着人们多样化的趣味,造就了一个从未如此多元和分裂的世界。在一个主体已然丧失、每个人都想通过物来重新定义自身之独特的社会,在一个过度强调差异性以凸显存在感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置身于孤岛,孤独、疏离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情感体验。
尽管贝蒂对现状的描写带有悲观色彩,但她也暗示了精神拯救的可能。在“最后的古怪一日”,也就是凯勒洛杉矶之行的最后一日,他独自待在双胞胎的房子里,拯救了一只在游泳池里溺水的负鼠宝宝。当凯勒漂到泳池尽头,想要爬上岸时,他发现“一头鹿高高在上,从梯台上往下看”(134)。眼神交汇的那一瞬间,凯勒“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在这出现无数启示的一天——那头鹿投来的是一种仁爱的目光,仿佛心怀感激。他感觉到了:一头鹿认可了他,在向他表示感谢”(134)。正是在这一瞬间,凯勒重新发现了自身与自然的联结,并获得了心灵拯救之感。于是,他放下了成见,最终在故事结尾时尝试重建与女儿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凯勒和一头鹿眼神交流的场景,是直指小说主题的核心意象,反映出贝蒂将拯救美国中产阶级精神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自然的想法。贝蒂的这种自然观呼应了新英格兰地区历史悠久的超验主义自然观,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爱默生、梭罗等先驱者。早期的超验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是上帝的化身、超灵(宇宙精神)的外衣,人可以通过直觉(或悟力)从自然中感知上帝的神启……与自然环境直接、瞬时的交流能(长远地)作用于人的灵魂,使之逐渐得到净化和升华。”(转引自张雪梅 2005:65)贝蒂让凯勒从与一头鹿的眼神交流中获得心灵的净化和重生,表现出了明显的超验主义自然观倾向。然而,与爱默生等人不同的是,贝蒂所处的后现代社会奠基于“上帝已死”的客观现实,剥除了宗教的外衣,自然在贝蒂的笔下成为人们摆脱消费社会的媒体操控、打破趣味区分导致的人际隔阂,并最终实现人际联结重构的关键之所在。
五、结语
郭颖与王中强曾撰文探讨贝蒂的前期小说《换挡》,并指出:“小说人物空虚、迷茫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之一。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笔下,人物表现出空虚、迷茫的原因各有不同。”(2016:46)同样的,贝蒂前期作品与后期作品中的迷茫亦不尽相同:前期作品的主人公大多年轻,因为尚未认清自身发展的方向而迷茫,大多仍有逃离的可能性;后期作品的主人公则不仅年岁较长,更重要的是已然深陷社会与制度所编织的无形之网中,肩负得更多,他们的迷茫来源于一种无法逃离的困顿感。
从表面来看,《洛杉矶》描写的是凯勒所处的人际隔阂的孤独世界,但正如苏珊·加内特·麦金斯蒂(Susan Jaret Mckinsty)所言,贝蒂笔下的叙述者总是“同时讲述着两个故事:客观的、细琐的当下构成的公开故事,以及主观的过去构成的隐蔽故事,而后者通常是叙述者所要极力隐藏的。两个故事之间的空隙,便是故事的意义之所在。”(1987:112)在表面碎片化的叙述之外,我们观察到了凯勒作为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凯勒用自己的趣味对身边的人施加精神压迫,同时他自己的趣味却也受到媒体话语的操控。贝蒂将对男权的批判与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交织在一起,将眼光投向了整个中产阶级所处的社会环境。洛杉矶之旅既是小说主人公凯勒的顿悟之旅,使他重新审视自身所犯下的错误,并由此获得了重生的勇气,同时也是作家贝蒂将拯救人类精神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人与自然的重新联结的希望之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安·贝蒂小说中的食物政治”(项目编号:17GWCXXM-36)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经费资助,特此致谢!
Centola,S.R.1990.An interview with Ann Beattie[J].Contemporary Literature31(4): 405-442.
Cox,C.2011.The art of fiction No.209:Ann Beattie[J].The Paris Review196(1): 47-84.
Mckinstry, S.J.1987.The speaking silence of Ann Beattie’s Voice[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24(2): 111-117.
安·贝蒂.2014.《纽约客》故事集Ⅲ: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M].周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郭颖,王中强.2016.存在空虚、身体政治和女性主义——安·贝蒂短篇小说《换挡》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1):44-51.皮埃尔·布迪厄.2015.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M].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让·鲍德里亚.2008.消费社会 [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雪梅.2005.艾米莉·狄金森对超验主义自然观的再定义[J].外国文学研究 (6):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