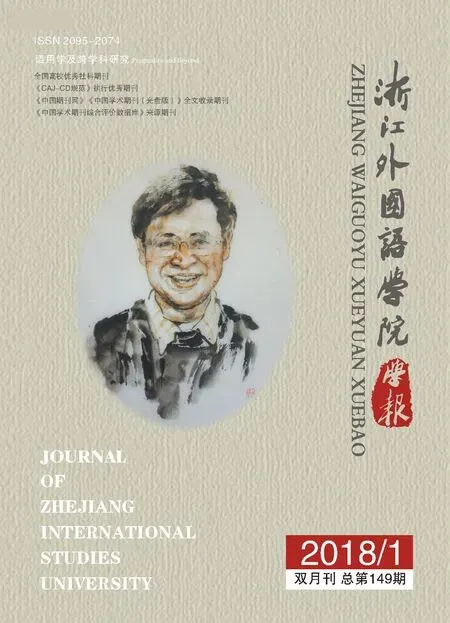他者、自我与真相: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旅行
袁小明
(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一、引言
1988 年,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发表了小说《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得到了读者的普遍好评,并获得了“布克文学奖”。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从英国管家史蒂文斯(Stevens)的视角,探讨了“伟大”“尊严”“职业精神”“英国性”“历史与回忆”等主题。叙事过程中,作家穿梭于历史与当下之间,精准地把握住了20世纪80年代弥漫在英国社会中的怀旧情感,在展现史蒂文斯内心彷徨的同时,也影射了英国民众的失落心理。小说中,史蒂文斯六天的旅行经历形成了回忆的框架,而回忆又不断形塑着旅行的心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早期旅行文学是殖民历史的产物,杨金才曾在《英美旅行文学与东方主义》一文中专门探讨了该类作品的政治意蕴,认为旅行文学通常是指那些具有较好文学修养的人对自己旅游经历的记录,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旅行者的国家意识、文化优越感等(2011:79)。20世纪初期,随着汽车文化的兴起,旅行文学再次繁荣起来。在英国国内,驾车旅行渐成风尚,由此而伴生的文字作品也成为了重构国家身份、重新发现英国“伟大性”的重要途径。先行研究已注意到旅行对于《长日留痕》叙事的重要性,如:蒋怡(2013)认为石黑续写了游记文学传统,通过史蒂文斯旅行中的风景这一文化符号唤醒了帝国记忆,进而批判了20世纪80年代的怀旧保守风潮;刘璐(2010)则认为该小说是石黑对隐喻性叙事的一次尝试,他沿用英语文学中的朝圣叙事结构来展现史蒂文斯在二战前、后的两段经历。这些研究都关注了作家的旅行书写与英国国家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并从宏观上结合社会语境对作品中的政治意识进行了有效阐释,因此为解读小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石黑一直进行着对个体面对社会整体时的心理困境与心理调节机制的思考。通过书写史蒂文斯的旅行,石黑试图呈现的不单是英国国家意识下的个体心理变化,更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和困惑。基于此,本文拟围绕小说中史蒂文斯的六天旅行经历,来探讨旅行者是如何不断调整自身身份定位,与他者建立平等的交流模式,并最终实现与生活的妥协。
二、遭遇他者
旅行中,旅行者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各种异质性文化。通常情况下,体验这些迥异于自身的风土人情也正是旅行者所追求的。旅行者将此作为个体的特殊经历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早期旅行文学,该文类经常采用纪实性的手法。然而,旅行者对所见所遇的纪实性书写是在自身文化知识和文化立场下进行的,旅游目的地的人和物通常会被纳入到他的认识体系中,因此难免会受到其自身情感、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所说的那样,早期西方旅行文学书写中,一系列东方文化被形塑成他者或异类文化,并遭到贬抑,最终沦落至边缘地位(1979: 65-67)。苏珊·巴斯奈(Susan Bassnett)在《翻译、文化与历史》(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中同样指出:“地图绘制者、翻译家和旅行文学作家看似从事的是纯粹的文本制造,而且作品也被标榜为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但是实际上这类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却蕴涵了一种文化态度的生成,他们正是通过此种方式来操控读者对某种文化的态度。”(1990:99)
上述研究揭示了旅行文学创作背后的权力话语体系:在权力话语构建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在遭遇他者时,形成怎样的文化记忆,以及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长日留痕》中,尽管史蒂文斯遭遇的并非是早期旅行文学中的那种异域风情,但是对于长居达林顿庄园的他来说,也堪称是陌生环境中的一次新奇体验。根据史蒂文斯的叙述,这是他第一次到英国西部旅行,这种旅行方向的设定响应了20世纪初旅行文学的特征。当时,旅行者往往从现代生活的中心伦敦出发,那是“书籍、报纸和杂志出版商的集散地,由此可以到达广大读者”(Featherstone 2009:68),他们故意避开工业污染严重的北方城镇,向西南乡村进发。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曾对当时的旅行方向作过这样的叙述:“我们要么往西旅行,要么往南”,“往西便是去凯尔特文明的古代中心——康沃尔郡和爱尔兰”(qtd.in Burden 2006:138)。在踏上行程之前,史蒂文斯特意找来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英国旅游手册《英格兰的奇迹》(The Wonder of England)。史蒂文斯开着雇主的福特汽车驶出了庄园,刚开始,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激动或不安,但是没一会儿就意识到:“周围变得陌生,我知道我已驶离了以前熟悉的地方。我曾听过关于航海中最终看不见陆地时的情景描述,那个时刻,人会感到不安与兴奋。现在,我开着福特车,周边环境变得陌生,心里同样产生了这种感觉。”(24)再次拐弯时,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山边行驶,左面就是悬崖。当“确实感觉到已经离开了达林顿时,我全身一阵紧张,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警觉起来”(24)。旅行正式拉开了序幕,如同那些早期异域旅行者一般,史蒂文斯不安的感觉中也夹杂着一丝莫名的兴奋。
六天旅行中,史蒂文斯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经历了从排斥到完全接受的变化。旅行初始,史蒂文斯对所见到的人心存警觉,且有意识地进行排斥。在路边休息时,当一个当地老人建议史蒂文斯登山观景时,他“一时认为他是个流浪汉”(24)。而且,史蒂文斯根本不愿意接受那个老人的建议,他答复道:“如果事实如你所说(山上看到的景色是英格兰最好的),那我也宁愿呆在这儿,我不能刚踏上旅途就把最好的看了。”(25)尽管最终上了山,史蒂文斯还是觉得那个老人冒犯了自己,“上山只是为了证明他的话愚蠢至极”(25)。当晚的住宿中,史蒂文斯同样表现出高高在上的身份优越感,“在登记住宿信息时,我发现她(女店主)一阵惶恐”(26)。在问及盥洗室在何处时,史蒂文斯感觉她回答的语气是“诺诺的”。然而,在对白天山上的景色进行回顾时,史蒂文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承认,景色的确壮丽,而且远比旅游手册中描绘的大教堂更加值得记忆,这也促使他在结束第一天的旅行后,“第一次调整自我,开始以正确的心态对待此次旅行”(26)。虽然石黑没有直接阐明究竟何为正确的心态,但很明显,如何对待他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二天的旅行中,史蒂文斯对待他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当地一个庄园的管家帮助史蒂文斯检查汽车时,他认为这个陌生人(他者)“愉快”“非常开心”“乐于助人”“友好”(118)。汽车问题解决后,史蒂文斯心怀感激,对于别人的参观建议,也一改第一天的态度,当即接受,甚至主动去旅馆楼下的酒吧,顺着其他人的谈话,插上一句自认为很机智的言语。
随着旅行的深入,史蒂文斯对他者表现出越来越愿意接受的姿态。旅行的第三天晚上,尽管已经很疲倦,但他还是主动与当地人一起探讨时下的政治问题。在此之前,出于心理上的优越感,史蒂文斯眼中的人与物纯粹是缺乏主体性的被观察对象,自我与他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而第三天的经历则表明,史蒂文斯开始接受当地人,并按照他们的理解方式来表达自己。在谈及“尊严”问题时,尽管意识到当地人观念的不同,但是史蒂文斯还是回答道:“当然,你的观点非常正确。”(186)
旅行的最后一个晚上,石黑将场景设置在海边的一个小镇上。值得注意的是,海边通常被视为一种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镇上到处都是和史蒂文斯一样的旅行者,不再有之前视他为贵族的崇拜者,这儿充满了巴赫金(Bakhtin)所谓的狂欢化特色,个体的身份等级被搁置,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改变之前孤独行走的状态。夜晚的码头上,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码头上到处是人,我身后,登上甲板的脚步声络绎不绝”(231)。在和一个老人的交谈中,史蒂文斯摆脱了之前的优越感,敞开心扉,坦诚交流,不再有所保留。
就这样,旅行中的他者不再是异己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其可以转变成促进自我成长的积极力量,自我与差异性他者之间实现了和解,双向交流模式得以诞生。这种模式正是当下多元社会亟需建构的交往模式,族裔身份也促使石黑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中,除了利益因素以外,对待差异性他者的姿态往往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书写史蒂文斯对待他者态度的变化,石黑探讨了多元文化环境下如何处理异质文化的国际性话题。
三、发现自我
身份认同是由一系列被社会承认的差异所构建而成,这在当代身份理论中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论断。正是因为差异,我们得以界定自我。同样,旅行多以遭遇差异作为目的,由此便给个体的身份构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这也是西方早期旅行文学的研究中之所以采用后殖民角度关注旅行者确立文化优越心理的原因。然而,这种视角较多关注的是身份认同中的“异”,而往往忽略了“同”。其实,身份认同既是一个划定自我与他者界限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同类归属的过程,而同类的经验往往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因此,在旅行中,旅行者不但能从他者身上发现自我的特点,而且也能在与他者的相处中,实现情感的共鸣,从而得到启发,进而深化对自我的了解。另外,自我与他者之间一旦形成了平等的对话机制,他者也就能主动地对自我施加影响,并进一步形塑自我。
《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对自我的发现,起初本是基于“异”的,但随着旅行的深入,“同”逐渐代替了“异”。通过回忆,过去的经历与现下旅行的经历不断形成参照,沿途的人和物等他者性存在逐渐渗入到史蒂文斯的固有认知框架之中,促使他对自我认识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正。可以说,六天的旅行经历构成了史蒂文斯不断发现自我的外部要件:
首先,通过旅行中与他者的交往,史蒂文斯逐渐承认了自己对肯顿小姐的爱恋,这标志着他对自己情感的认同。旅行前,史蒂文斯一直暗恋着肯顿小姐,但他自己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史蒂文斯为自己旅行中拜访肯顿小姐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肯顿小姐原先是达林顿庄园的女管家,他想顺道去了解一下,她是否愿意重新加入这儿的雇员队伍。当美国雇主故意就此事进行调侃时,史蒂文斯觉得“这太令人难堪了,达林顿勋爵是绝对不会这样对待员工的”(14)。随着旅行的逐渐深入,史蒂文斯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回忆视角,肯顿小姐在回忆中的出现也变得愈加频繁。
石黑将旅行的第三个晚上设置在泰勒家也可谓用心良苦。在旅馆中,每个人都只是恪守着自己的职责做好分内的事,而在家中,一切活动便获得了温馨的亲情色彩。在泰勒家,史蒂文斯回忆起肯顿小姐离开前的一幕情景:“我独自站在肯顿小姐紧闭的门口,我半对着她的门,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敲门进屋,我知道,肯顿小姐肯定在哭。”(212)“一个早上我都在回忆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件事中的一部分,这个时刻多年来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当中。”(212)这是一段关于肯顿小姐一直希望史蒂文斯能够对她表白,但史蒂文斯直到她离开都没有表达出来的记忆。可见,旅行前的史蒂文斯一直努力压抑着个人情感,而正是这次旅行促使他觉醒,他终于开始逐渐正视这段微妙的情愫。
以往的史蒂文斯认为,在职责面前,个人的情感微不足道。即使当父亲去世时,史蒂文斯也一直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悲伤或去看一下父亲,他甚至为自己的表现而感到自豪。旅行第二天的上午,石黑在史蒂文斯的回忆中穿插了一段关于他在乡村道路上行驶的情节。为了避让一只母鸡,史蒂文斯停下了车,此举得到了母鸡主人的感谢。在聊天过程中,母鸡主人顺便告诉史蒂文斯以前她家的乌龟就是在这个地方被碾死的,为了此事,她的儿子哭了好多天。这个情节看似无关紧要,但显然唤醒了史蒂文斯对善良的感知能力,以及长期压抑在内心的对父亲的情感。
其次,通过旅行中与他者的交流,史蒂文斯对自己的职业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不难看出,史蒂文斯之所以开始这段旅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在的美国雇主,他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时空来对“职业精神”“伟大”等问题进行思考。在沉迷于英国过去辉煌的史蒂文斯看来,英国的景观远非其他国家所能媲美。英国的景观平静、含蓄,而美国和非洲国家虽然也有一些“令人兴奋”的景观,但因“过于炫耀,而显得低级”(29)。进而,史蒂文斯认为这其实与问题“何为伟大管家”类似,因此,他开始重新审视伟大管家的定义。此前,他深信海恩斯协会(Hayes Society)对伟大管家所作的定义,即一个伟大的管家应“具备坚守自己岗位的尊严”(3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史蒂文斯一直坚信尽管自己为了实现职业上的“伟大”而未能很好地对待父亲,但是父亲肯定是支持他那样做的。正如先行研究所发现的那样,石黑作品中充满了自我欺骗(不可靠叙事),史蒂文斯觉得“毫无疑问,伟大的管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了伟大的绅士,通过伟大的绅士,伟大的管家为人类作出了贡献”(117),而事实上达林顿勋爵根本算不上伟大,甚至可以说愚蠢,且具有明显的种族偏见,于是,史蒂文斯关于伟大管家的认识也就变得不那么可靠了。尽管第一天的平静旅行没能打破史蒂文斯对伟大管家的固有认知,但是接下来几天旅行中出现的人和物却促使他产生了自我修正意识。
旅行第四天的下午,一个医生识破了史蒂文斯的身份,并直接询问他何为“尊严”,而他却只想到了“不在公众场合脱掉衣服”(210)这种苍白无力的说辞。无疑,这个提问直击要害,彻底粉碎了史蒂文斯对伟大管家的认识。旅行的最后一天,在与一个具有相同经历的老人交谈时,史蒂文斯对自己的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服务于那些绅士,我们没有选择,担心自己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当然你我都会为自己认为有价值或真实的事尽上微薄之力,但是如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牺牲太多的话,能获得的无非也就是自豪和满足。”(244)就这样,史蒂文斯六天的旅行结束了,同样他的心理旅行也结束了。史蒂文斯对自己的职业有了重新定位,他放弃了对诸如“伟大”“尊严”等远大价值目标的追求,而将自己置于当下现实之中,并努力过好生命中余下的光阴。
四、接受历史真实
在旅行中,旅行者总是带着自有的认知模式进入旅游目的地。作为观察者,在对目的地的人和物进行呈现时,旅行者利用固有认知框架对观察客体进行整合,而就像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惯习”①布迪厄在《区隔》(1984)一书中较为详细地阐释了“惯习”,他认为“惯习”是由个体生活环境调节而生成的一种持续且可变化的性情倾向系统,是个体实践的内驱力,既具有被动性,又具有主动性。概念一样,认知框架是个体的生活经历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时,人的认知框架也并不完全是被动地按照既有的模式运行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刺激会促使大脑进行自我调整,从而形成新的认知心理机制。除了涉及上文所论述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这种认知心理机制还涉及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界定所属团体的问题。同样,在小说《长日留痕》中,除了思考如何界定自我与他者的问题,石黑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自然景观是如何映射并改变主人公国家意识的:自然景观一方面映射并加强了史蒂文斯原有的“伟大英国”的国家意识,另一方面又促使其不断修正对“英国性”的理解,并最终得以摆脱对“英国性”的本质主义解读,而接受英国辉煌不再的现实。
史蒂文斯对“英国性”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他之前在达林顿庄园的服务经历。从回忆可知,他在达林顿庄园的服务时间主要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座著名的庄园历史悠久,可以说是英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和代表。由于庄园主人达林顿勋爵的声望和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政治精英汇聚于此,这里成为许多国际会议召开前的谈判基地。对于几乎足不出户的史蒂文斯,庄园的辉煌代表着帝国政治的辉煌与鼎盛。此外,阅读也是个体认知的重要来源。小说中,《英格兰的奇迹》和《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之类的旅游书籍,也为史蒂文斯认识“英国性”提供了重要素材。上述书籍充斥着对英国景观的赞美,从而使得史蒂文斯固执地认为英国必然保持着昔日的辉煌,而这显然与当时英国的国情不相吻合。从小说内容推算,史蒂文斯旅行的时间大概是在1956年夏天,那一年,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英法联军对埃及进行了武装干涉,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抵抗,最终埃及政府宣布与英法断交,而且阿拉伯世界也纷纷效仿,对英法实施石油禁运,最终英法迫于压力,不得不从埃及撤军。这次事件对英国帝国自尊心的打击极大,使其在国际舞台上颜面尽失,标志着英国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②金万峰在文章《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时代互文性》(《日本研究》,2011年第2期,94-98页)中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早在2000年,唐岫敏就曾在《历史的余音——石黑一雄小说的民族关注》(《外国文学》,2000年第3期,29-34页)中指出,石黑一雄作品中渗透着对英国民族问题的思考。。
同时,理想的“英国性”通常被认为存在于乡村之中,因此乡村景观成为了最能代表英国文化的符号之一。特别是19世纪晚期,尽管乡村文化逐渐衰落,但其符号意义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这个国家(英国)的过去、情感结构和文学,无不与它的乡村相关。即使在进入20世纪后,悠闲的生活方式、简洁的屋舍等代表传统英国文化的符号也是不减反增。”(1975:248)这种理想化的认知框架直接决定了旅行第一天史蒂文斯对英国乡村景观的态度。当史蒂文斯登上山顶、俯瞰远方时,映入眼帘的是“延绵不断的英格兰乡村,场面极其壮观……这种品质只能用‘伟大’来形容”(28)。然而,好景不长,旅行第二天的下午,由于汽车缺水,他来到一所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前,这个庄园是风光不再的英国的缩影,“一半的窗户框上沾满灰尘”(118),只有一个人看管整个庄园。其实,达林顿庄园和这个破落的庄园一样,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耀,此物此景进一步触发了史蒂文斯认知视角的改变。于是,在别人推荐下来到池塘边进行游览时,他对景物的描述便失去了旅行第一天所见的那种此起彼伏的壮观,“这儿充满了平静,池边的树木靠水很近,使得河岸看起来让人心情愉悦……岸边路面上一层深深的泥泞,一直伸向远方”(121)。旅行第三天的傍晚,史蒂文斯因为汽车没油而深陷田野之中,天色已黑,四处无人,他只能摸索着沿泥泞的田间小道直行,以便到附近的村庄寻求帮助。此时,史蒂文斯觉得大片田地失去了曾经的壮丽而变成了荒野,固有认知框架中的伟大英国变得虚无而遥远了。在第六天的旅行中,尽管旅游手册告诉史蒂文斯其所在的小镇有好多有趣的旅游项目,但他却只是静静地坐在长凳上,享受着此次旅行的最后时光,这也象征着他终于接受了英国不再辉煌的现实。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小说《长日留痕》的创作,石黑一雄深刻地揭示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失意的现状,对人类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进行了一次心理探幽。在六天的旅行中,史蒂文斯不断调整着对待差异性他者的姿态,这不但帮助他实现了心理上的修复,也使得他能够逐渐认识和修正自我,最终得以正确处理自我与他者、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这种书写改变了早期旅行文学那种发现英国“伟大性”的叙事传统,旅行产生的效果不再是对英国的自豪,而是对国家现状的失望。
Bassnett, S.1990.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Burden, R.2006.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in D.H.Lawrence’s Twilight in Italy(1916) and other travel writing[C]//R.Burden & S.Kohl(eds.).Spatial Practices:An Interdisciplinary Series in Cultural History,Geography and Literature,Vol.1:Landscape and Englishness.Amsterdam: Rodopi Press,137-163.
Featherstone, S.2009.Englishness:Twentieth Century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Forming of English Identity[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Ishiguro, K.1993.The Remains of the Day[M].New York: Vintage Books.
Said, E.1979.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
Williams, R.1975.The Country and the City[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蒋怡.2013.风景与帝国的记忆——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视觉政治[J].外国语言文学(2):124-131.
刘璐.2010.隐喻性话语和“朝圣”叙事结构——论《长日留痕》的叙事特点[J].外语研究(1):108-111.
杨金才.2011.英美旅行文学与东方主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 (1):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