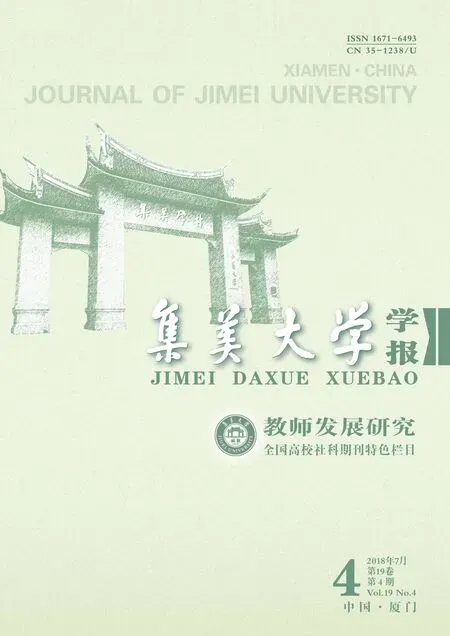从民国时期的识字教育反观今天识字教育
张 帆,张哲英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 民国时期识字教育概况
(一)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识字教育
中国传统识字教学以集中识字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课本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一方面我们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为了摆脱被殖民、被侮辱的境地,一群有识之士开始在教育方面改革,逐渐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随着教育模式的改变,教材、教法也产生改变。识字教育作为语文教育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变化是值得考量。晚清时期,一些语言学家关注到儿童识字教学方面改革,因此,在分科之前,就有不少人研究蒙养教授。1846年,文字学家王筠的《文字蒙求》一书问世,1850年,其又编著《教童子法》,对当时的儿童语文教育做了初步建设,他倡导童子集中识字,教师要进行知识讲授[1]60。当时的识字教授方法仍旧为“集中识字”,这是延续了传统的识字教学,而其中的变革是教师对文字的教授不再是不假思索式的灌输,而是要向学生传授文字的形音义等相关知识。
晚清时期,为了更好地传播文化和启迪民智,白话文运动兴起。首先在白话文教育方面做出贡献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倡导白话和与之相适应的平民教育。在识字教学方面,太平天国成就卓越。1852年,洪秀全和卢贤拔编纂《三字经》,该书是太平天国时期重要官书之一,也是一种儿童教育课本,1854年,洪秀全又下旨颁行《御制千字诏》一书,作为儿童识字教育和太平天国革命教育的课本[1]55。
之后,晚清有识之士均开始倡导白话运动,施崇恩等以简明的方式普及白话文知识。19世纪90年代,与白话运动相适应的国语运动已经开始,它包括“切音”“简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等,其中最早提出这种运动的是卢赣章在《切音新字序》中,谈到“国语统一”的问题。1891年宋恕提出了汉语拼音的主张。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王照在变法失败后,也积极投身于拼音文字工作[1]58。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均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受到西方冲击这一背景下产生,不论是从普及白话到普及教育,还是借鉴西方的拼音字母解决汉字识记困难这一问题。最后殊途同归,从识字教学的创新达到“启迪民智”的作用,使得国家摆脱列强钳制的困境,走向富强,这是一种带有鲜明社会意识的教育运动,这也是民国教育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识字教学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清王朝被推翻,但并未迎来真正的民主社会,文化精英们开始从思想文化角度进行变革,五四运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五四时期的教育以“民主”“科学”这两个方面进行。20世纪20年代初期,现代语文教育家吴研因著《文字的自然教学法》,反对往日“由教师做主支配,学生跟着机械做”的所谓“不自然”的教学法,提倡以“学生的自觉需要”“学生已具的动作和经验”“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三者为依据,实行“自然”的教学法。[1]74之后,尤其在高校和现代学堂中,“自觉”“自然”的教授蔚然成风。文字教学不再是过去那种“先生教一撇,学生学一撇”的机械形式,在师生交流互动的前提下,对字义的理解与运用成为教学的主流,我们如今所倡导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模式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寻求借鉴。
科学地运用语言并促进语文教育的发展这一重任落在了五四时期的语言学家身上,黎锦熙的《新著国文语法》是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著作,也是较早的语文教育著作,语言学家出身的黎锦熙在其著作中强调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将识字教学、语法教学摆在突出位置。虽然其思想很快被“五四”先驱所提倡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所取代,但黎锦熙重视字词的“工具性”等教学理念为我们的识字教学留下宝贵的经验。
(三)20世纪30年代识字教学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否定了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开始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共产党经历长征之后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中国此时形成了国共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的教育也是在这两个政权的对峙中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区域推进其政治化的教育,并形成较完备的教育体系,最早的课程标准就是这一时期制定,这一课程标准以国家级文件的形式规定了识字教学的具体细节,识字教学从自觉、自发性地组织教学成为我国近现代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并且出现了很多官方普及性的教材,这些语文教材都以不同的方式促进识字教学的进步。如陈鹤琴与盛振声合编的初级《儿童国语教科书》,这一套教科书在识字方面的特点是不以单字或单词起首,开始的第一课就学成句的话,便于与儿童原有能力相适应[1]183。这与现今普遍使用的的“随文识字”是基本一致,即儿童不是仅仅孤立地学习语言文字,更要学会运用语言文字。由于儿童受年龄限制,其抽象思维能力较差,将文字放在固定的句子、语段中进行识记,更易于儿童掌握字义、词义。1936年,马若谷、李訾不、程粟一等三人合写过一题《三种现行国语教科书的评论》的文章,对当时商务、中华、大东三家出版社的三种小学国语教材进行分析评价,文章中,作者所提到“编好国语书”的13条建议基本是公允的。第7、8、9、10条均针对儿童识字教学,要求在文字编排上要由易到难,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将字尽量在词语中进行识记,为文字加拼音标记,达到形音义学习的统一。这些都为现代识字教育做了较好的铺垫。
(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识字教学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侵略,大片国土被侵占,政治文化显示出特殊的地区特征,即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而不同的地域也因为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况有其特殊性。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再次走向对峙,国统区与解放区在语文教育方面有着鲜明的政治特征。这十二年的识字教学以地域为坐标,从国统区、解放区两个区域为向度进行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南沿海地区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转移到西南、西北地区,在大后方的国统区,由于资源、时间等限制,为了配合这种特殊情况,政府便开始试行小学国语常识分科合编本。即以图画配有趣的文字进行识记,在有限的纸质资源和紧张的教学时间内,学生学习最多的文字和日常知识,达到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合二为一。但是这种课本过于重视“党化教育”再加上材料的缀余,因而受到诟病。这一时期国统区(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学者和教员在艰苦的环境下并未放弃教育教学研究,反而针对当时的条件,不断充实教法研究。识字教学由于战争的特殊性,以“工具性”“效率性”为主,即“随文识字”中的“文”不再是名句名篇,而是常识性的文章,这使得学生在战争这样一个物质和人力匮乏的时期,用最少的时间学最多的基础知识,即字词和常识。
这一时期的解放区教育整体上也是和国统区类似的“战时模式”,即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人力、物力向广大群众普及知识,陕甘宁边区历经三次编写的《中等国文课本》正是将基础知识与识字教学相结合,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解放区的语文教材编写呈现“社会化、政治化、劳动化、实际化”[1]303的特点。由于解放区的农民占其人口主体,所以教育必须与农业生产劳动相结合,故《农民识字课本》《看图识字课本》应运而生,这样的识字教学模式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干部是贫苦百姓出身,受教育程度较低,很大一部分是文盲,对干部的扫盲和普及教育成为解放区识字教学的又一重点,《干部识字课本》正是针对这一现状所编撰的。全书60课,用生字7000多,供干部扫盲学习用。从内容看,除了对识字具体指导之外,对学习态度、工作作风、思想方法、政治认识以及简易应用文等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课文[1]314。这些课本仍旧是“随文识字”这一模式。而“文”均改成政论时文,这一选材方式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甚至多次教学改革之后的今天。时文的选入是配合战争的复杂环境与特殊情况产生的,时文中的文字都是常用字,而时文的文章语境又适合战争这一风云际会的时代,而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语境下,语文教育应该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这样的模式不适合今天的语境是必然的。
著名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他的“自觉学习法”“思想教育”等,为解放区的教育建设立下功劳。徐特立对苏区的识字教育建设立下实际建树,他曾说:“‘识字运动的办法’其基本点是:老公教老婆,儿子教老子,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他认为:“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2]由于苏区人民大多为底层农民,其对教育学习并不重视,以强制性的指令普及教育并不现实,通过小先生制这一灵活的方式,既可以不耽误农事生产劳作,又可以使苏区教育最大化普及。徐特立还对苏区语文教材编写提出建设性意见,认为语文教材不仅与政治相结合更要与实际生产生活相结合。除徐特立外,对解放区语文教育建设贡献卓著的就是程今吾,程今吾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在识字教育方面,他提倡阅读、写字和写作的有机结合,即当学生有不会写的字时,可以暂时隔开,教员给他补上,学生在之后的阅读、写作中加深学习。这样便同时有效提高了识字、阅读和写作能力。现在的语文教育,识字、阅读和写作是重难点,教师可以从程今吾的教学中汲取养分,丰富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识字教学方法的梳理可以看到,识字教学一直是语文教育家关注的重点,是不可忽略的。这些专家学者或一线教师的识字教学并不是凭空想出,而是传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并结合现代西方的教学方法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产生的。这些宝贵的经验也会为现今的识字教学提供丰富的借鉴。
二 对我们如今识字教学的启示
(一)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相配合
集中识字是我国传统的识字教学方法,代表作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识字教材将基本的文字以一定顺序排列。在儿童进行开蒙的时候用一段时间集中识记。晚清时期,王筠等关注儿童识字教育的语言学家仍旧使用这样的方式。根据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阐述,集中识字的产生是基于汉字为表意文字这一特性,由于汉字不像英语等,学生识记基本字母就可以进行拼读、阅读。学习汉字必须每一个字扎实认识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读写教学。[3]但是,因为集中识字只是单一的识字,导致学生可能对字的用法等不能深刻理解,语境意模糊不清。近代以来,很多专家和教师引入随文识字,即在具体语境中识记文字。但随文识字可能会造成对文字的读写记忆不牢固的弊端。故在识字教学法上,应该使得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相结合。
进入新课程改革的今天,为了减负,新课程标准减少了规定识字的字数。例如2016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识字与写字”这一模块相比旧版而言,第一学段(1-2年级)认字数量删减。第二学段减少约400字,到第四学段(7-9年级)删除“会写3000”字这一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实用文体阅读。纵观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要求明显提高,这样有助于开拓学生思路,适应信息化社会时代信息爆炸、阅读资料较多这一特点。而很多专家和教师却曲解了这一含义,认为识字教育并不重要,如今新课程重在凸显学生能力培养,因此,现今语文课堂忽视识字教学的现象很严重,学生写错别字(尤其初高中)的现象也随之严重。“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如果基础的字词掌握成问题,那么后期的读写和更高的能力要求——“核心素养”都堪比空中楼阁。重视识字教育才是语文教育最基本也是最必要的开端。根据前人的语文教学经验,将集中识字与随文识字相结合,一面让儿童集中掌握基本汉字,一面将常用字编入教材,在课文中理解其意义。
(二)识字教学要与生活实际和思想教育相结合
识字不是一项单一的活动,其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认识文字和简单的读写,而是从文字中学会文化内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所以,我们的识字教学不是刻板地逐字教授,而要在文字教授中渗透思想教育。无论是国民政府的“部编”教材还是解放区苏维埃政府的相关教材,均是在语文教育中渗透思想教育,在识字教学中结合政治思想、日常生活和价值观的教育,这样的识字教育才是丰满的。
杂字是传统古代流行的针对底层劳动群众的识字教材,杂字内容一般是将识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民国时期,国统区如陶行知等很多教育家将识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社会大学,达到知识的普及。而在解放区,由于解放区群众大多为底层农民,文化素质较差,文盲占大多说,但由于忙于农事,大部分农民群众又不能脱离生产劳作进行全日制学习,并且共产党内很多干部也是农民出身,文化素质偏低,为了提高解放区人民和共产党内部的文化素质,徐特立等人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念、进行“群众培训”“干部培训”等。这些识字方式其实与古代的杂字有一定传承性,将识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如今的学校教育中,因为提倡学生“核心素养”,注重知识的迁移应用,所以在识字中让学生联系社会实际,拓展综合能力便显得十分重要。例如识记一些关于草木花卉的文字、词语,可以让学生到大自然中,不仅形成形象思维,更能亲近大自然。而在识记一些关于人的情绪的字词时,可以渗透社会公共礼仪知识。
(三)从汉字的构成规律与儿童学习规律进行识字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所以在汉字识字教学中要考虑形音义三要素的关系进行教学。正如王宁教授所说:“生理学与心理学对汉字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表明,认知过程要经过‘字形的精确确认’与‘字义与语音的加工’”[4]。例如在讲解占汉字很大比例的形声字时,教师应该注意声旁、形旁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形、音、义的内在关系,从而活学、活用汉字。儿童的认知接受具有一定规律性,如果违反规律,反而会产生不良效果。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人对编订完成的教科书的字汇、词汇、编写规律等都提出了相关要求,即需要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编写。并建议儿童识字课本应该放置于一种儿童的识字语境中进行。但反观今天,一些老师、家长片面追求学习的量,让孩子过度超前识字,其实这样是违反教学规律的,可能会造成儿童学习负担过重,造成身心的双重伤害。
综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可以知兴替”,在对于语文教育某一时段的学科史的探究中,可以反观今日语文教育的得失。从民国时期这一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动荡变革时期的语文教育,可以为我们今日的语文教育提供很多养分,从历史的角度,立足当下,构建更加完善的语文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