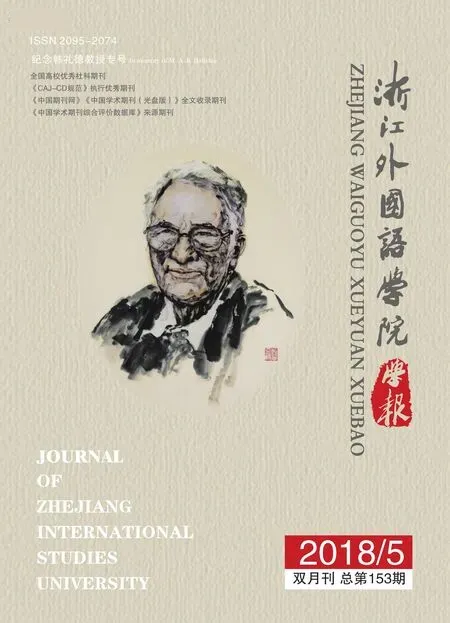生态话语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阐释
苗兴伟 , 赵 云 ,2
(1.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2.山东大学 翻译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一、引言
生态和环境的恶化已经为人类的生存敲响了警钟,生态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1990年,Halliday(1990/2001:199)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指出,物种的毁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不仅是生物学界和物理学界的问题,同时也是应用语言学界的问题。生态语言学将语言和生态联系在一起,研究语言如何影响人类与其他有机体和物理环境之间有利于生命持续的关系(Alexander & Stibbe 2014:105)。生态语言学以生态问题为导向,研究语言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资源,语言的社会符号观、话语建构论和意识形态观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视角。国内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辛志英、黄国文 2013;何伟、张瑞杰 2017;黄国文 2017),本文将探讨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阐释生态话语如何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揭示生态话语背后的生态观念和意识形态。
二、从生态语言学到生态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语言学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其实由来已久(Fill & Mühlhäusler 2001:1)。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洪堡特已经开始关注人类语言的多样性问题。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探讨了语言与其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正式将语言与生态联系在一起并开创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是Haugen,他在1970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阐述了“语言生态”的思想,与之前有人提出的“语言生态”这一概念相比,Haugen的语言生态思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Haugenian approach)应运而生,并在语言习得、双语和多语、语言多样性、语言消亡和恢复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Fill 2001;Steffensen 2007;黄国文、赵蕊华 2017:586)。豪根模式主要研究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双语现象、语言规划、语言及使用语言的社团、语言的生态类型、语言地位、语言使用者及其社会阶层、宗教背景和宗教因素(Haugen 1972:325;Boguslawska-Tefelska 2016:16)。因此,Haugen所说的环境指的是使用某一语言的社团及其社会因素。豪根模式把语言生态看作是一个隐喻,语言被比喻为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语言与其环境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Alexander & Stibbe 2014:107)。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生态的另一个维度,即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特别是语言在环境问题的发展和恶化中的作用(Fill 2001:43)。由于Halliday在1990年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强调了语言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一研究范式被称为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模式(Hallidayan approach)(Fill 2001; Steffensen 2007;黄国文、赵蕊华 2017:586)。在韩礼德模式中,生态是非隐喻的,指的是生物环境(biological environment),即有机体之间及其与物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Stibbe 2015:8)。Halliday(1990/2001:198)指出,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经济和社会的无限增长对环境造成了威胁。语言建构了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使其体现在语法系统中。例如,在语言的对立范畴中(如big-small),表增长或积极意义的词是无标记的中性词,比如我们会习惯表达“How fast is the car? ”而不是 hows low; “How high is the building? ”而不是 how low; “How big is her income? ”而不是how small(Fill 2001:48;Halliday 1990/2001:194)。这样的语言特征就会使人把经济增长看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追求,把萎缩和减少看作是不可取的现象。
Halliday(2007:14)提出了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与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的区分,前者关注语言的表意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后者研究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区分与前文所述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生态语言学的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表面上看有着本质的差别,但二者都体现了“和平共生”“相互依赖”和“小就是美”等生态原则,因此,这两个模式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Fill 2001:43;Steffensen 2007:8)。同时,“隐喻的”和“非隐喻的”区分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悖论:豪根模式的“生态”是隐喻的,因而是虚拟的;韩礼德模式的“生态”是非隐喻的,因而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语言可以用来谈论生态,却不是生态的一部分(Pennycock 2004:217)。因此,生态语言学应抛弃和消解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的区分,并将二者融合到一个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中(Steffenson & Fill 2014:16)。虽然Halliday区分了系统生态语言学和机构生态语言学,但 “多样性”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关键 (Alexander & Stibbe 2014:107)。Halliday(2007:13)在谈论语言消亡的后果时指出,人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类比:正如物种多样性对于环境和生态的健康是必要的,语言的多样性对文化和生态—社会的健康也是必要的。虽然他认为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类比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这一类比无疑对打通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具有启示意义。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是有联系的 (Mühlhäusler 2003;Fill & Penz 2007),如果本地语言被像英语这样占优势地位的世界语言取代,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话语的损失,这些话语包含了人们已经学到的关于如何在本地环境中可持续生存的所有知识。取代这些话语的是不可持续性社会所推崇的经济增长话语、消费主义话语和新自由主义话语(Alexander & Stibbe 2014:107)。
生态话语分析在生态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关注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如果把生态看作是人与他人、其他有机体及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就在于人如何建立与他人、其他有机体及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生态语言学并不是研究语言在建立各种关系中的作用,而是聚焦语言如何建立有利于生命持续的关系(Alexander & Stibbe 2014:104-105)。生态话语分析大都关注生态话语,即关于环境和生态的话语,聚焦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阐释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对生态话语进行分析有助于揭示生态话语中人类中心主义、物种主义、消费主义、增长主义等意识形态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利影响。Alexander & Stibbe(2014:108)主张,生态话语分析不仅仅是生态话语的分析(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而且是在生态框架内开展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也就是说,生态话语分析不只是分析生态话语,而是分析任何对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响的话语。所有话语都会对人类的行为造成影响,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会对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生态框架内对所有话语进行生态分析。
三、生态话语分析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角
Halliday在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就语言与环境的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语言学和语言学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他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视角探讨环境问题,这充分体现了Halliday所提出的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思想,也证明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性。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路径,是一个全面的、理论上强大的语言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语言使用者在现代社会中所遇到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Halliday 2008:7)。就生态话语分析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为阐释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把语言看作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社会行为潜势,并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语言将人们的“行为潜势”编码为“意义潜势”,然后通过词汇语法系统编码为“话语”(Halliday 1978:21)。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语言使用者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语言是在人类与生态-社会环境(eco-social environment)的互动中通过实施某些重要功能进化而来的(Halliday 2013:15)。生态-社会环境与词汇语法系统的界面是语义。语言的表意能力是通过我们的选择激活的(Halliday 2013:35-36)。根据语言系统的层次观,语言系统体现为选择关系,语境激活了语义选择,继而激活了词汇语法选择。任何选择都是由语言所要实施的功能来决定的。
在生态话语中,语言选择具有目的性,许多破坏话语需要在一定的生态-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解释。例如,人们为了达到砍伐森林的目的,将primary forest(原始森林)称作decadent forest或over mature forest;将砍伐(logging)美化为 harvesting,或者表述为 foresters cull trees, remove pest species。有些模糊话语也是有意图的。例如global warming被climate change替代后,前者所传递的生态危机感被模糊化,变成了语义宽泛的气候变化。同样,economic growth把经济增长表达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和现象,模糊了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有些模糊话语需要改进,如将seal pup称作seal baby,可以增强人们对野生动物的认同,减少猎杀行为。语言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有益话语的空缺。例如,英语和汉语中都没有被词汇化的表达“垃圾分类”(to separate garbage)的独立词语,也缺乏一个表达“将一种物品运送到其他盛产该物品的地方”的词语,英语中虽然有carry coals to Newcastle这一短语,但并没有一个被词汇化的词语(Harré et al.1999:31)。汉语中也是如此,比如某瓶装水的广告把自己称作“大自然的搬运工”,很少有人质疑为什么要把水运到不缺水的地方,瓶装和运输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我们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描述这种为了商业利益而多此一举的行为。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观把语言看作是用来表达意义的社会符号和资源。从生态的角度看,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在意义潜势中的选择表达在生态-社会环境中的经历,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其他有机体及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识形态观
意识形态是对现实世界的表征,是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支配和剥削等社会关系的手段(Fairclough 2003:9)。意识形态通常借助语言手段隐含在话语中,话语通过灌输、维持或改变意识形态产生意识形态效应。系统功能语言学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Martin & Rose 2007:314)。在某种程度上,一切为意义所作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动因,一切以意识形态为动因的选择都具有意识形态效应。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法不是中立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语言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力量 (Halliday 1990/2001;Halliday 2003;Halliday & Martin 1993)。Halliday(1990/2001:179)指出,语法既是人类经验的理论,也是社会行为的原则。某些语言表达的频繁使用使人们对它们所表达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意义已经变为常识进入人们的潜意识,Fairclough(1992)把这一过程叫作意识形态的“自然化”。 例如,英语中用来表达自然资源的名词water、coal、oil、air、soil、steel等为不可数名词,这就容易使人将自然资源误解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存在。语法识解现实的方式可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并对人类的健康和自然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语法在识解我们的经验过程中建构了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增长主义的意识形使人们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却忽略了增长背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
生态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影响人类和其他物种生存与健康的重要因素,生态话语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而有些话语在建构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同时生产和再生产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和物种主义(speciesism)的意识形态。生态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示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生态话语中的运作机制以及语言选择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应。人类中心主义与物种主义以各种方式体现在话语中。例如,语言不接受其他物种的施事者(agent)地位,因此不会有“What’s the forest doing?”这类表达。即使存在这样的表达,人们一般会把它理解为“Why is the forest there?Remove it!”,而不会从森林保持水土和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Halliday 1990/2001:194)。人类通常运用距离化(distancing)策略将自己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一方面,语言常常使用不同词汇系统来指代和描写人类和其他物种,如代词的区别以及skin—hide、flesh—meat、胖—肥、长胖—长膘、舌头—口条、吃饭—吃食儿、手—爪、脚—蹄、食品—饲料等对应词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词汇的搭配也表现出排他性,比如think、know、believe、amiable、sympathetic等词汇一般不与表示动物和植物的词汇搭配。
就生态语言学的意识形态分析而言,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是否正确,而是意识形态是否鼓励人们保护或破坏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生态语言学所做的就是衡量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是一致的还是相违背的(Stibbe 2015:23)。
(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
受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把语言看作是建构现实的手段和途径,即语言在表征我们的经验时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经验,而是以词汇语法为动力主动地建构各种范畴和关系。换句话说,语法识解经验并建构由事件和事物构成的世界(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xi,17)。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建构论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建构观是一致的。Halliday(1990/2001:179)指出,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创造现实。批评话语分析的建构观认为,语言作为具有高度建构性的媒介不是中立的,因而不存在中立的现实表征。话语不是被动地反映或仅仅描写世界,而是一种行为,不同的话语建构的是不同的世界(Fowler 1991:4)。话语建构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选择实现的,不同的语言选择所产生的建构效应(constructive effect)是不同的。
生态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揭示话语如何建构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Stibbe(2012:20)指出,动物被社会建构的方式影响人类社会对待它们的方式。无论是英语的“animal”还是汉语的“动物”通常是不包括人类的,这种语义上的区分拉开了人与动物的距离,强化了人与动物的差别。在英语中,表达肉类的词语(如beef、pork)与表达动物的词语(如bull、pig)是没有联系的,这就隐去了人类在获取这些肉食时动物所承受的痛苦及背后的杀戮。Stibbe(2003)通过对主流话语和猪肉产业话语的分析,揭示了话语是如何建构人与猪的关系的。工业化使人与猪的关系越来越远,除了出现在侮辱性语言中,人们很少有机会与猪面对面地接触,猪肉产业话语将猪构建为机器和物体,从而将人类对猪的某些残忍做法合法化。
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建构效应。动物在人类的生活和整个生态系统中充当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发挥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但语言的选择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the Earth community、 the greater community of life、a unique community of life、a magnificent diversity of cultures and life forms、 the joyful celebration of life(Newman 2009:101)之类的表达方式把人类、动物和其他生命形式建构为同一个社团的平等成员。
四、结束语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阐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就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而言,无论是语言多样性还是生物多样性,都是生态话语分析应该关注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语言生命力与危机》的报告中指出:每一种语言的消亡都会导致独特的文化、历史和生态知识的消失。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对世界的体验的独特表达。因此,对任何一种语言的了解都可能是回答未来一些基本问题的关键所在。每当一种语言消亡,我们在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模式和功能、人类史前文明以及世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持时,证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UNESCO 2003:2)。Wodak & Meyer(2016:12)将“分析、理解并解释气候变化以及围绕可替代能源生产等诸多争论”列入当前批评话语研究的议程。对于生态话语分析来说,研究世界所共同面对的语言和生态问题,更是生态语言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生态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建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