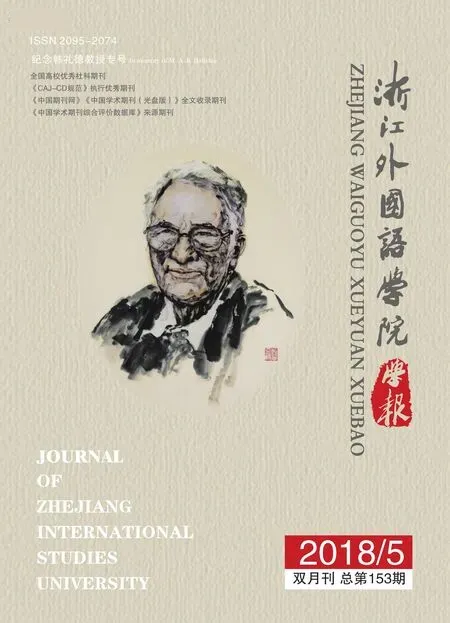为了那些与韩礼德先生交往而难以忘却的回忆
——记与大师的几次近距离接触与启迪
黄会健
(浙江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一、引言
今年4月16日下午,我从手机里看到朋友转发的微信,得知韩礼德先生于2018年4月15日晚上8点左右,在悉尼的一家养老院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微信中还说:“迈克尔临终时,意识到即将离世,而能坦然以对……一棵大树在森林里崩然倒下了。”当时,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涌现出一股对失去这位语言大师感到悲伤却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惋惜。这种感情来自我与韩礼德先生二十多年来难得的几次交往和接触。应《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之约,谨以本文,追述与大师亲密接触的往事,畅谈聆听大师教诲的启迪,表达对大师的深深缅怀。
二、与韩礼德先生结交的缘起
我与韩先生交往的缘由,要从我的同事钱淞生老师说起。1979年8月,我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浙江化工学院工作。当时的外语教研组里,老教师特别多,总共只有十二三名教师的队伍中,掐指一算,老教师就有六七位,而且有些是从俄语或其他语种“改行”过来的。钱先生更为特别,据说他是从中文“改行”过来教英文的。在与钱先生共事的岁月中,我从他那里得知,他与韩礼德先生曾经是同学。1945—1948年间,他俩在北京大学师从王力先生,并住在同一寝室。钱先生的年龄与韩先生相仿,两人的关系很不错。但从北大毕业后,直到钱先生2011年4月18日去世,他们竟然连一次面都没见过。钱先生是一个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学者,他曾经在王力先生的指导下,开展过对闽南方言的田野调查,并和王力先生合作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如《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广东四邑方言语法研究》和《台山方言》等。我还记得,1982年的一天,他拿出其中的一篇给我看,当时我对他的研究感到既新鲜又惊讶,更佩服。1982年夏,我所在的学校开始逐步向杭州搬迁。到了杭州后,我准备再次考研(1979年初夏,我曾参加过武汉大学的英语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取得过复试资格)。但考研的难度在逐年加大,许多学校要考语言理论知识了。由于大学里没有开设语言学这门课程,我当时觉得,那将是我考研路上的一道坎。于是,我常向钱先生求教。记得有一次,我登门向他讨教有关语音学的知识,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个[m],然后问我,语音学上那是个什么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个“鼻音”。他摇了摇头说,只对了一半。看我有些困惑,他便解释说:“这是个双唇鼻音。”这时我才知道,描写一个辅音,必须从其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着手,有的还要考虑其清浊差异。在这之后,我校外语教研室为了提高教师的语言学理论水平,专门请钱先生开设了语言学这门课,用的教材是高名凯先生编写的《语言学概论》。钱先生讲课很风趣,我现在还记得,他在最后一堂课的最后几句话:“知识分子一辈子跟书打交道,生活在书里,最后死在书里,这叫作,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记得钱穆先生也有类似的话。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生活在书籍中的人。由于钱先生与韩礼德先生曾是北京大学的同学,而我又是钱先生的同事和朋友,在随后与韩先生的接触中,我心中便有了一种更加亲近的感觉。
三、与韩礼德先生的六次亲密接触
1995年7月18至22日,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第四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会议与第二十二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会议之前,浙江省外文学会任绍曾会长向省内各高校发了通知,要求各校外语教师把相关论文上报给学会,以便遴选能够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之前,我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留学回国不久,手头有点材料,觉得可以拿得出手,于是,就按照学会的要求,提交了论文提纲,此后得到回复,通知我准备参加这次会议。为了确保这次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的顺利举行,方琰教授在清华大学组织举办了为期三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短训班”。在讲习班上,我第一次遇见了韩礼德先生和他的夫人韩茹凯(Ruqaiya Hasan)。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韩先生学问做得大,但没有架子,非常随和。讲习班期间,我主动找他聊过一些问题。记得我俩坐在清华园一个花坛边的石板上,我问他,他的系统功能语法与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是否有联系,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有什么区别,对于前一个问题,他没有作正面回答,而对于后一个问题,他说:“These two theories are totally different!”。说实在的,当时的我,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解还很肤浅,并没有把握其理论的深度。后来的讲习班里,我在聆听韩先生的讲课中,有三点现在仍记忆犹新:一是语句的难度可以根据内容词(content words)的密集度与语法结构的复杂程度来计算;二是语篇信息的包装(information packaging)很像我们生活中处理垃圾的过程,由小包的家庭垃圾,到垃圾桶,再由垃圾桶到环卫车,再到垃圾填埋场,是步步升级、积累的过程;三是语法隐喻是语言学习者对语言驾驭比较成熟的表现,儿童在九到十岁之前,语言中一般没有这种现象。
正式的学术交流大会,在暑期讲习班之后进行。我记得,在学术交流活动期间,韩先生来到任绍曾教授发言的分会场,任先生发言的题目是“Jespersen’s Functional Approach to Grammar”。该发言谈到,叶斯柏森在对语言作语法分析时,始终坚持以意义和语篇为取向的特征,认为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致的。韩先生听完发言后非常谦虚地说,对叶斯柏森的语言学理论,他了解得不多。当时的我,对韩先生那种虚心好学的态度感受非常深刻,同时,也为他能选择在任先生发言的分会场与大家一起研究语言理论问题感到高兴,因为任先生毕竟代表了浙江省外语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这次学术交流会上,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Robin Fawcett向与会者展示了如何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计算机上生成语句。这使我认识到,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懂得语言的意义是依靠系统中的词项选择来实现的。
1999年8月15至18日,复旦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会议在上海召开。韩礼德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记得韩先生在主旨发言中说,进入21世纪之后,语言研究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起主导作用。会议期间,我有过一段与韩先生面谈的时间。当时,我得知韩茹凯患了直肠癌,动过手术,便向韩先生建议,劝他与韩茹凯来杭州讲学。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浙江省外语界培养年轻学者,另一方面可以常和阔别已久的老朋友钱先生一起叙旧,一起搞研究,虽然当时的钱先生已经退休,但思维还很敏捷。更重要的是,韩夫人可以在杭州找个有经验的老中医,用中药逐步调理身体。他听了后,表示可以考虑我的建议。他说:“I like the word‘gradually’.”。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够落到实处,我建议他先去杭州看看,会一次老同学,再考虑是否要来讲学。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而且,与会的Matthiessen也要伴随他一道来杭州看看。
我将他们安排在杭州大厦住宿。晚餐由我出面在楼外楼宴请,任先生和俞东明先生也一起陪同。第二天,我们几个陪同他俩一起在西湖边游览,之后在山外山饭店吃了中餐。记得在点菜的时候,我们问韩先生想点什么菜,他看了看菜单,然后说,来个“bitter melon”(苦瓜)。但遗憾的是,厨房里没有备苦瓜。这里要提一下,比没有吃到苦瓜更遗憾的事是,我打电话给韩先生的同学钱先生,却没有人接电话。我跑到他家一看,是铁将军把门。后来才知道,钱先生已与夫人一起到美国的儿子家了。这次韩先生来杭的遗憾远不止这些。当我问他俩住得是否舒适时,韩先生向我抱怨了两件事:一是杭州大厦房间里供饮用的袋装咖啡是受潮的,很可能是时间长了,没有更新。二是床头柜上放着的警示牌上用中英文分别写着“请不要在床上吸烟!”“No Smoking in Bed!”,韩先生看了非常生气。他说,自己作为一名外国游客,难道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知道,还要这样来提醒?我听了后,心里也不好受,只怪我们一些宾馆管理水平不高,同时也怪自己把他俩安排到此处住宿。假如时光能倒流,就算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俩安排个好一点的宾馆。另外,我想,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让韩先生与他的老同学见一次面。
2008年8月18至22日,第十一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韩先生在和与会者拍集体照时戴了一副黑色墨镜,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眼睛不太好,怕强光照射。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他,身体还是很棒的。韩先生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在会议结束的晚宴上,他坐在我们浙江学者一桌,频频与大家拍照留影。
2009年8月14至18日,第三十六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暨第十一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我与马博森以及绍兴文理学院的几位教授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在一个分会场里,我聆听了韩先生的发言,话题是“汉字的表意结构”,他列举了汉字“書”“畫”的构字特点,用以说明汉字独特的构字方式,让外国学者大开眼界,同时,也让中国学者眼睛一亮,汉字里有语言研究的重要素材。本次学术会议结尾时,组委会安排了中国学者与韩先生对话的活动。其间,有学者问起“话语”与“语篇”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韩先生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语篇”,“discourse”也好,“text”也好,都可以叫作“语篇”。
2010年11月12至14日,同济大学承办了国际语篇分析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在此之前,我得知韩先生将参加本次研讨会,就特地跑到钱淞生先生家,请他说说他最想与韩先生说的话,钱先生当时已经有点行动不便了,于是就坐在藤椅上,说了些惦记韩先生以及向他问候的话,并将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韩先生。当时,我用手机将钱先生的话录了下来,然后转到U盘上,带着它去参加会议。在研讨会开始前,我跑到主席台上,把录音拷贝到姜望琪教授的电脑上,并请他将录音转交给韩先生。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在自己的学校里有事,需要赶回杭州。这次会议上,我没有与韩先生说上几句话,就匆匆离会了。2011年春,学校开学的那天,我在办公室意外发现桌上摆着一封韩先生寄给我的亲笔信。信中大致的意思是,我给他的录音已经收到,他与钱先生已经通过电话了,对我促成他和钱先生的联系,表示十分感谢。这封信,因我多次办公室搬迁和住处变动,一时还无法找到。
四、与韩礼德先生交往的启示
缅怀大师的事迹,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韩先生平易近人的为人作风,学习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领会其精髓,并学会应用其理论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服务。
在我与一些语言学大师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人处世非常随和。这在韩先生身上尤为突出,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开山鼻祖,他到哪儿都没有一点架子。从来没有看到什么前呼后拥的情景。在我以往与外国朋友的交流中,与韩先生拍照合影,次数最多、最自然,他就像我的父辈。1999年请他来杭州时,他和Matthiessen是同住一个房间的,房费是他们自己支付的。让他点个自己喜欢的菜,他点的是苦瓜,而不是大鱼大肉。当然,喜欢点什么菜,这与人的年龄大小也有关系。他俩从上海到杭州下榻的宾馆,途中坐火车、打的,都是他们自理。现在回忆起来,那次他俩来杭,接待方面有许多地方没考虑和照顾周到。但是,除了对宾馆的服务质量提出异议外,他没表示过一点抱怨,这让我感到既愧疚又感动。
在学术理论的追求上,他不含糊,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定力和独特的智慧。前面提到,当我问到,他的理论与乔姆斯基的理论有何不同时,他说:“These two theories are totally different!”。声音之铿锵,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
为什么这两个流派是完全不同的?在哪些方面不同?哪一家比较符合语言的事实?哪家对语言现象更有解释力?现在看来,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西方语言学理论学派林立,但主要还是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两派。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别是两派的代表。生成语法理论从理性主义的语言观出发,认为语言受一组有限的句法规则制约,并可以根据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合乎语法的句子。它关注的焦点是句法的逻辑性,乔姆斯基自己说过,生成一个句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堂逻辑课。他所做的工作是,研究一个合乎理性的普遍语法,即对所有自然语言共同的语法属性(原则)和不同语言之间有差别的参数的研究。乔姆斯基假定,人类有一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先天的语言官能(an innate language faculty),它在基因上预先决定了语言习得的进程。人类的语言官能吸纳了普遍语法原则 (universal grammatical principles)。 乔姆斯基(Chomsky 1972:102)说,“There are very deep and restrictive principles that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human language and are rooted in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 human mind.”。 那么,什么是普遍语法原则呢?拿个例句来说明,如“Memories will fade away.Will memories fade away?”。
英语的陈述句变为一般疑问句,句子需要倒装,其方法是将助动词提到主语之前,语调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书写上是将句号变为问号。但是,并非简单地把语句中的第二个词提到句首。这种语言操作是按照“结构依存原则”(structure dependence principle)进行的,即“所有的语法操作都是结构依存性的”(Radford 1997:12)。普遍语法原则讲的就是语法操作或结构潜在的普遍属性,除结构依存性原理外,还有“中心词移动条件”“最短移动原则”“经济原则”“充分解释原则”等。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普遍语法原则不是学得的,而是自然所得的。儿童学习语言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具体语言中词汇和设定该语言独特参数(parameter setting)。这些参数是不同语言之间语法差异的一个方面。语序就是一个参数,有的语言的语序是SVO,如英语;有的则是SOV,如日语。参数也可以是同一语言中的不同变体,例如,英语陈述句变为疑问句,语序就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主张,自然语言语法的普遍特征反映在一组普遍语法原则的操作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差异特征是由一组有限的参数所显示的。
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比,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将人类语言知识的本质表述为某种与生俱来的、抽象的、自主的规则系统,但完全忽视了人类语言的社会性。语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使用语言的人是社会人,因此,语言具有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属性,忽视这一特征的语言学,将失去对于语言的解释力。乔姆斯基所缺的,正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所特有的。或许可以说,这两种理论可以互补,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乔姆斯基的理论存在严重缺陷。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韩先生说,他喜欢“gradually”这个词。不搞极端,不搞二元对立,主张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些思想都对他的研究方法具有重大影响。在阅读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的语言学著作时,我们会发现,乔姆斯基喜欢用“either...or”,韩礼德喜欢用“more or less”。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级阶理论,将语言单位分为语素、词、词组(短语)、小句、复杂句、语篇。“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是韩礼德提出的独特术语,“A language is a complex semiotic system composed of multiple LEVELS,or STRATA...the central stratum,the inner core of language,is that of grammar.To be accurate, however, we should call it LEXICOGRAMMAR, because it includes both grammar and vocabulary.These two,grammar and vocabulary,are merely different ends of the same continuum—they are the same phenomenon as seen from opposite perspectives.”(Halliday 1985/1994:15)。词汇中有语法,语法中有词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相辅相成,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在遣词造句(wording)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要对语言系统中各次系统的成分作选择,并将其置于相应的句子结构位置内,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在处理聚合关系时,语言使用者可供选择的词项是呈现系统排列的,选择是从不确定到确定渐渐精准的过程。
韩先生喜欢“gradually”是有道理的。渐进性、系统性、整体性,是我们理解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把钥匙。
韩先生非常重视语言的实际使用,对滥用语言的现象深恶痛绝,这也是我与他接触中所感悟到的启示之一。在宾馆,他看到床头柜上的警示语“No Smoking in Bed!”,非常反感。一个语言大师,对此反应之强烈,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细想一下,其中不无道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文明程度,反映了社会的文明水平。在旧中国,或许有人在床上吸烟,床上吸烟的危害主要在于容易引起火灾,因此,一般旅店里,以此作为警示,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到了当今的社会,一般的公共场合,都禁止吸烟了,在床上吸烟的情况,恐怕已经少之又少了。更何况,在对外开放城市杭州的大宾馆里,还有如此让外国友人大跌眼镜的警示语,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软实力,而语言正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媒介之一。但这一点,往往被许多人所忽视。近些年来,杭州在创建文明城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在语言使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例如,前几年,我刚退休时,办了一张公交卡,每次上车刷卡后,就听到“老人卡”;现在刷卡,就会听到“敬老卡”。年龄比我大十来岁的刷卡,听到的是“爱心卡”。以往公交车专座上写的是“老、弱、病、残者专座”,现在是“爱心专座”。但作为一个全国文明示范城市,杭州在语言文明方面,还是做得不够到位,尤其是遇到要将汉语译成外语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例来说,在一所省内较有名气的高校内,笔者依然能看到诸如将“无烟楼”译成 “Smokeless Floor”,将“请节约用水”译成“SAVES THE WATER USED”的现象。在杭州的公交车上,将“爱心专座”译成“SEAT FOR THOSE IN NEED”,算是不错的翻译。但遇到稍微复杂的内容,翻译有时就乱了方寸,如将“公交车上严禁携带如汽油……爆竹、有害物品……和有碍其他乘客安全健康的物品。”翻译为 “Bus prohibited such as gasoline...firecrackers, toxic substances...and impede other passengers safe and healthy items.” 。 这样的译文,如果让外国友人看到了,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对于想提高软实力的杭州来说,是一种缺憾。我想,现在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根本就不重视语言的作用,尤其是外语在软实力培育中的作用。有些人以为,翻译仅仅是一种语言,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事情。
总之,大师虽已仙逝,但他把具有独创性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留了下来。我们应该认真阅读他的语言学著作,继承和发扬其人类社会语言研究的思想传统,掌握和使用好本国语言与外语,使语言能更好地为社会生活服务,尤其是为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大师生前给我们的谆谆教诲,才能让大师在九泉之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