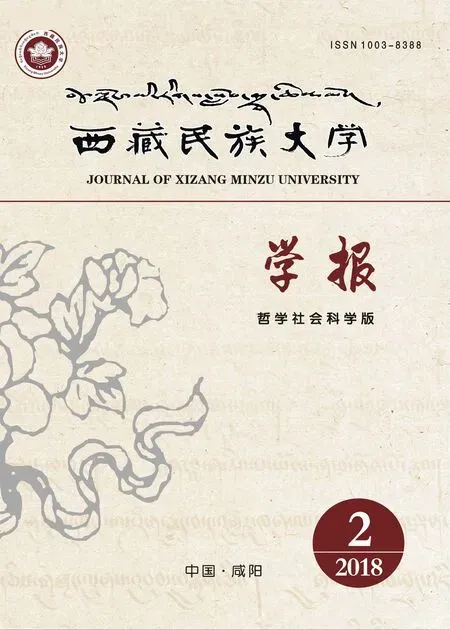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顾祖成先生的藏学研究访谈
陈鹏辉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顾祖成,江苏兴化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35年出生在旧中国一个破产的知识分子家庭,1960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志愿建藏,一直在西藏民族大学(前身为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西藏自治区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方志专家组成员;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等职。退休后返聘为《西藏民族大学学报》主编(1999-2013)、学术顾问(2015至今)和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顾祖成先生一直从事西藏历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他主持整理编纂的明清实录藏族史料获得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9)、《清实录藏族史料》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合著《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五届入选著作奖(1996),主编教材《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十讲》获西藏自治区教委“全区优秀教研成果奖”(1997),专著《明清治藏史要》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个人曾荣获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83),西藏自治区优秀专家称号(1991),“全国敬业奉献模范”提名奖(2017)等。
受《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委托,笔者对顾先生的学术人生进行多次访谈。
笔者:顾老师您好!今年是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学报特设了学者访谈栏目,现委托我对您作一个学术访谈。您一直从事西藏历史研究,为藏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藏学研究之路的。
顾祖成(以下简称顾):好的。我生于旧社会,实际成长于新中国。1956年是我以后专业学习、研究的第一步。当年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我原来是小学在职教师,就在这一年,经过上级教育部门批准,我报考高等学校,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当年我们县批准报考的有六十多人,当时第一志愿也是最高志愿,大家都想到华东师范大学,北师大当时不在我们县的招生计划之内。最后考上华东师大的只有我一个,这就增加了我的自信心。以前倒是很努力,但是增加自信还是很重要的。
大学四年,华东师大的学术氛围一直很浓,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学术造诣很深的。像李平心、吴泽是两位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很有名的。老一辈的像吕思勉,是一级教授。那时他们几位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课,但是历史系给我们上中国史课的像戴家祥教授,这位老师是王国维的学生,精通钟鼎文。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经常到华东师大来讲授历史地理方面的若干研究观点或新的成果,这样我在华东师大就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当时,我也无法规划好自己是主攻中国史、还是世界史、还是历史地理。为什么我说这三个方向,我们老师中像戴家祥他们,在我们这样本分、勤奋的学生心中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谭其骧做历史地理研究,当时接受了一个国家任务,像现在的国家立项科研项目一样。南京当时要修建长江大桥,长江在南京江段出现几个永久性的江中大桥墩以后,可能引起主航道改变,这样就可能影响下游江流走势,所以要摸一摸历史上长江下游江岸的变化。谭先生组织复旦和华东师大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参加这项研究任务。我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正是大跃进、全国大炼钢时期,我就不参加这些运动了,专门做长江历史地理资料的辑录整理。当时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是历史文献、方志方面的图书馆,谭先生把馆里所有长江南京以下各地的方志都调出来,有宋代志、明代志、清代志等,由我们来辑录长江下游江岸及吴淞口到杭州湾海岸线的变化方面的资料。我们有专门的工作室,每个人有个小桌子,每天都安排得很满,就是从各类方志中将相关史料摘抄成卡片。谭先生亲自来检查指导,他叮嘱我们一定要把卡片归类放好,不要混淆。我和其他同学摘抄的卡片他亲自看,予以表扬,这是一个引导,调动起了我这方面的兴趣,我想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做历史地理研究。这一段任务完成以后,谭先生让我们写报告,也就是阶段性论文,从中挑选几十篇印成一个册子,为后续研究准备资料。这一段经历就打下了我从历史文献中摘抄资料的基础。为了世界史的学习,我在华东师大期间,努力学习俄语。其他同学大都是高中应届毕业,有外语基础。我是中等师范毕业,没有外语基础,但是我决心要赶上,劲头也就来了。当时全年级有一百二十多名同学,结果我的俄语成绩排在前列。俄语老师当时有个大盒子的录音机,他就把录音机和磁带交给我,放给感兴趣的同学听。
1960年大学毕业后,碰上困难时期,全国高等学校减员,我们这一届重点分配到边疆地区,我一开始被分到了新疆。系里领导找我谈,说新疆学校教育以新疆大学来说,比较吃香的是维吾尔语,尤其是俄语。你俄语基础好,就到那儿去吧。虽然远一点,但我也愿意去。可是有一个偶然的原因,我不是党员,我眼睛里看着党员应该都是模范,当时我们毕业的有4个班,其他一个班的班长是党员,分到了西藏。这个同学不愿去,要求换一个其他地方。所以最后就把我换到了西藏,我志愿建藏。分到西藏,但是没有进藏,留到了咸阳西藏公学①。当时还有从华东师大、北师大、东北师大分配到西藏的毕业生,全都留到了西藏公学,为公学办高等学校储备人才。
笔者:您参加工作的时候,国内藏学研究尚处于新生时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学术著作也不多。您到西藏公学后,是怎样选定研究方向的?
顾:当时公学的学生,不要说汉语汉文,就是藏文都是文盲半文盲,汉语文从拼音开始学。所以我们所学的专业用不上,也没有历史课。在这种情况之下,经过很短一个时间的彷徨,我觉得做世界史研究不现实。民院所在地咸阳,倒是周秦汉唐故地,那就做中国史研究。但当时学校没有条件,很重要的没有图书资料。学校的图书馆只有现在一间阅览室那么大,只有几百本书。所以我觉得应该做民族史、藏族史研究。这个方面过去也知道一点,比如松赞干布、吐蕃王朝、达赖、班禅、格鲁派都是知道的,但是详细历史当时就不清楚了,所以就决心自学。先去西安看看有没有西藏史方面的书,在钟楼附近的科学出版社门市部,看到了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②,这在当时是一本高水平的西藏史著作,我就马上买了。在咸阳的书店又买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沂暖翻译的《西藏王统记》③,这是西藏文献中很有名的。我把这两本书当作至宝。可是《西藏王统记》看来看去不像一个历史著作,不是按现代史学体例来写的,王先生的翻译也带有文学性。我就想西藏历史撰述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还大有研究。王忠先生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当时看不太懂,书里提到的敦煌资料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越是看不懂还越是要看,跟王沂暖的《西藏王统记》对照起来一看,有些意思就明白了,只是译名不同。我也请教民院一些文化水平高的老同志,也几乎都说不清。在这个期间又想办法借到了30年代出版的荣赫鹏的《英国侵略西藏史》④。这本书中把糌粑说成“大麦粉团”,噶伦写成“协摆”,还有译得很古怪的人名、地名,问老西藏同志也都说不清,于是我就埋头研究。
几个月后,我们被安排进藏去搞中心工作,就是锻炼,当时叫实习。1961年初到西藏后,我才了解到了真实的西藏。当时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杨东生,后来继张国华之后担任民院院长。他跟我们讲,西藏要办高等学校,你们这一批60人是我到教育部从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三所重点院校专门要来的。现在你们的专业用不上,你们不要荒废,西藏要发展,今后一定能够用得上。我想西藏公学要提升成西藏高等学校,中国史、藏族史专业一定是少不了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就专攻藏族史。如果说华东师大是为以后打下了基础,那这段时间我实际是在“转型”。
转型期也作了一些尝试,当时师范专业要开设历史课,就找到了我。历史课不能只讲中原王朝的历史,还得结合西藏地方史讲一点。我当时和教研室同志编了一本3万字的西藏史教材。这是怎么编的呢?就是之前学的基础知识,再加上当时《藏族简志》《藏族简史》⑤征求意见稿,就是到80年代正式出书的那两本书。这在当时是征求民院意见的,放在阅览室也没有人看,我就借了这两本书,我到哪儿就带到哪儿。讲课基本按照那个框架,当时还没有那么多考古发现,从林芝人讲起,讲猕猴变人传说,然后吐蕃王朝、萨迦王朝、帕竹王朝,直至甘丹颇章王朝,当时称之为“黄教全藏政教合一政权”,这么讲下来。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术研究谈不上,但还是进入学科领域认真学习。对某一时段,如吐蕃王朝的汉藏文资料基本上都接触到了。当时《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⑥没有整理出版,只能从王忠那本书中看到一些片段的翻译,我觉得非常珍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在民院,在西藏搞社教。当时有人写了一篇批判西藏史研究方面的文章,说西藏史研究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个事情后来有深刻教训。在揪反动学术权威的氛围中,有人告诉我,你要小心,你编的那本教材也被拿来展览了。我们教材中的松赞干布不是帝王将相了吗?文成公主不是才子佳人了吗?好在我不在校,在校肯定会被揪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文革”期间我基本上是逍遥派,大有时间来学习藏文、看二十五史,特别是其中的吐蕃传,所以这10年没有荒废。
改革开放以后,条件好了,西藏要恢复高等学校,民院筹建历史系,分工的时候,我不想驾轻就熟,就到西藏史教研室,中国史教研室不进了,世界史教研室更不去了。“文革”后期学校恢复招生,第一次系统地开设历史课,学校安排我来上课。这些学生中后来成就大的有汉族班的肖怀远、牛治富、刘洪顺等,藏族班的洛桑江村等。当时我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通史》以及陆续出版中的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我在这个范围里备课,经常晚上备课到一点钟,饿了就把馒头用纸包着放到被窝里暖暖吃。一些同志晚上上厕所看见我屋子的灯还亮着,就关心说要早点休息。这样坚持下来,写了好几本完整的中国通史提纲式的讲稿。
笔者:您在西藏史研究中,一直坚持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总体框架中,系统地阐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您这一学术视角不仅为深刻理解中原王朝与边疆政权的关系、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也从学理上为反分裂斗争的现实需要提供了依据。请您谈谈您是怎样形成这一学术观点的?
顾:“文革”结束后,在藏族史的教学研究方面,我感到一根主线必须搞清楚,就是西藏在整个中国历史演进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中国史就好像一片森林,西藏史是森林中的几棵树。如果看不到森林,只看到几棵树,这样讲西藏历史不可能是全面的。“四人帮”粉碎后,1978年我就尝试着做一些研究。当时写了一篇《西藏原始文化同黄河流域的密切联系》⑦的文章,投给了《历史教学》,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刊发在了1979年底一期的第二篇。因为当时“红专”问题上仍心有余悸,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成昌文这个笔名。后来知道,这篇文章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藏族史研究室的常凤玄同志审的稿,以致后来见面他直接喊我的笔名。当时全国历史类只有两个杂志,一个是《历史研究》,一个就是《历史教学》。这篇文章的发表,增加了我的学术研究的信心。在这之前,我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评近代俄国侵略中国西藏中的德尔智其人的文章⑧,后来周伟洲教授给我说是他审的稿。再早些,我给《西藏日报》投了一篇文章。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我们在西藏开门办学,有人对桑结加措过于推崇。我觉得这个不对,对清王朝来说,桑结加措不能说是爱国的。当时讲爱国主义、卖国主义,我就从这个角度把桑结加措匿五世达赖之丧及与准噶尔拉紧关系写了一篇长文投给了《西藏日报》。他们非常重视,转给自治区革委会主管文教的领导审稿,他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联系实际写得很好,但是他也拿不定主意,最后给予推荐的是王辅仁先生。王先生看了后说对桑结加措的评价应该是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给予了肯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在《西藏日报》正式刊用,最后刊发在了《西藏历史研究》,这个是《西藏日报》编辑部把学术研究和政治结合起来搞的一个内刊。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一些同志发表不同意见。所以,藏学研究一定要与现实紧密结合,要有学术性和思想性,思想性不是空的。要从学术性里面体现思想性,其中史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把传统教法史放到中国史的总体框架中,如何去伪存真,是要下很大功夫的。
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您主持整理的3辑《明实录藏族史料》⑨与10辑《清实录藏族史料》⑩两部书,不仅是国内有关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资料专集,而且为海外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和藏学研究机构所收藏,为学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两部史料集分别是从卷帙浩繁的《明实录》与《清实录》中辑录、整理出的有关藏族历史的史料专集,工作量非常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完成这项工作十分不易。请您介绍一下相关辑录、整理的过程。
顾:历史系“西藏史”开课稍晚,为我专做这方面的资料工作赢得了时间。当时学界很重视古籍整理,我在之前的学习过程中认识到历史研究中文献资料的重要性,知道了明实录、清实录藏族史料的整理的重要性。我从报纸上的一则消息看到,国内从台湾购进了7套明清实录,我想陕西可能会分到,就通过援藏的陕西师大、西北大学的同志打听。最终打听到陕西省图书馆进了一套,但是不能外借。我说用西藏的介绍信能不能借,结果还是不能外借。但陕西省图书馆答应给我们创造条件,给了一个阅览室作为我们专门的工作室,这样每天一大早从咸阳乘火车去西安,晚上再回来。1980年在陕图整整摘抄了一年的时间。当时学校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党委书记、院长主持学校科研会议时,都要叫我去列席,专题汇报进展情况,对我们提出的困难,领导都会马上解决落实。比如当时的复印条件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们规定30字以内的内容手抄,30字以上的复印,复印费用很贵,学校领导大力给予了经费支持,也批准同意我们遇到下雨、下雪天可以找旅馆住宿,不用来回跑。在当时条件下,辑录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确实很辛苦,但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同人正处于年富力强之际,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些同人如今大都进入老迈之年,有几位竟成了古人。整个1981年至1982年上半年,我和中国史教研室马驰同志,还有退休返聘的王观容老师整理辑录藏族史料,不论寒暑与节假日,分类编纂《明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共六册,由学校内部印行,对外交流。
1982年8月至1983年8月,我和藏史教研室的琼华(藏族),还有马驰,来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因他们那里有台湾影印出版的明清实录,与社科院同志结合,以民院辑录整理的实录资料为基础,每天工作不少于15小时,用编年体整理汇编《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这两部大型藏族史料集1982-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笔者:《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问世三十多年来,屡屡获得学界和同行专家的称誉。出版之初,著名藏学汉文文献专家吴丰培先生即特在《西藏研究》刊文评介[1];1991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在其《西藏的教育》一书中评介说“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2](P125);2003年,王尧、王启龙、邓小咏所著《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评价说:《清实录藏族史料》“史料翔实,是研究17到20世纪初叶藏汉、藏蒙民族关系和西藏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以近代帝国主义侵藏史等重大藏学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3](P44)。请您介绍一下这部史料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顾:《清实录藏族史料》记事起自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延聘五世达赖喇嘛、推崇黄教,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迄于宣统三年(1912)藏乱终末,历时二百七十多年。《清实录藏族史料》是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初叶两百多年间藏族社会历史,尤其是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形成、发展以及藏汉、藏蒙等民族关系史的不可或缺的汉文原始资料。对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亦辑录有若干重要资料。
历史有它自己的本来面目。《清实录藏族史料》以其丰富的史实,充分展示出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全面行使国家主权的原貌。这些基本史实主要是:
1、清朝中央设立专门机构理藩院,钦定则例,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几次颁行藏事章程,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进行治藏的立章定制。皇帝以旨谕直接过问、处理西藏地方政教大事。
2、正式派遣大臣驻藏。中央政权在藏设立官署。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办西藏地方事务,任免地方重要官员,监制铸币,调遣营伍,赈灾济贫,巡阅边防,抗击外寇,安辑地方,等等。
3、大力扶植和优崇达赖、班禅,以册封确立其政治和宗教的地位,推进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的确立。建立“金瓶掣签”制度,颁行有关活佛转世章程,将西藏各大呼图克图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转世灵童的认定、坐床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和国家典章法制之内。
4、推动西藏地方政权系统的历史演进,改定西藏行政体制,设立四名噶伦,组建噶厦,明定噶伦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督领下,会同办理西藏地方事务的制度。
5、清朝中央规定西藏地方文武官员品级、员额和升补次第程序。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员噶伦、代本,由清朝中央直接任命,年俸由中央政府照例发给。
6、西藏地方定期向清朝中央朝贡,缴呈“丹书克”,以效职方之贡。逢朝廷各种庆典,派人进京朝贺,履行地方对中央必须承担的政治义务。
7、清朝中央调遣军队进藏,处理突发事件,安定边疆,绥靖地方,并在西藏地方常驻军队,以尽守疆戍边之责。定制组训地方正规军队,担负保藏卫国的任务。中央驻军和藏军统由中央派驻的官员管辖。
8、明定外事集权中央,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处置权统归驻藏大臣行使。达赖、班禅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由驻藏大臣为之酌定回信。摄政、噶伦等地方官员不得擅自与外方通信,违者乃遭追究。
9、清末,在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侵略中国西藏地方,严重损害清朝治藏主权的情势之下,清朝中央力图“整顿藏事”,派遣大臣进藏查办藏事、推行新政,希冀抵御外侮、“挽回主权”,维护国家的统一。
笔者:您的学术研究旨趣一直在西藏地方史方面,尤其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见长,先后出版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⑪《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简明教程》⑫《明清治藏史要》⑬等著作。请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确立这个研究领域的。
顾: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的整理为我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1984年,我担任了历史系的负责工作后,相当多的时间、精力投入系务管理,但始终坚持西藏史教学与科研。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三个大的科研任务,一个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的研究,这个是合著,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立项,1996年正式出版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一个是西藏启动了方志编纂工作,要我参加,西藏主要领导对这项工作很重视,亲自开会安排。其中“教育志”明确让我担任第一副主编,主编是教育厅长,但是这个工作后来因为接受其他重要任务而要求退出了;最后一个就是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陈奎元书记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陈书记很赞成把西藏史放到中国史研究的框架中研究编纂,而不是像之前将西藏按一个王朝一个王朝那样的体例来写。当时我已经退休,但是我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也不愿意离开民院。这样我就接受学校返聘,担任学报主编,同时投入这一重要的特别委托项目的研究之中。
在参加编写《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中,我在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的基础上,将“关系史”研究扩展到了元代,清代我反倒不搞了。清代部分由中国社科院的姚兆麟同志完成。我在完成元代部分的过程中,充分运用陈庆英等翻译的《萨迦世系史》⑭、赞拉·阿旺、佘万治翻译的《朗氏家族史》⑮等藏文资料,这就更加扩大了学术视野。元明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确立阶段,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角度而言,也就是中央政府对藏治理阶段,这是狭义上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出版后,教育厅委托我院编写“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教材。由我组织了民院的陈崇凯、宋秀芳、史工会等几位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编写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十讲》,后经过自治区教材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正式作为教材,由我负责全书的修改统稿总编撰,交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简明教程》。在编写本简明教程过程中,我继续扩展“关系史”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远古时期,从西藏考古发现阐述西藏远古文化与中原深刻的渊源性联系,在论述唐王朝与吐蕃王朝的关系中,突出阐论“甥舅关系”。在这之前,面对《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数百万字的翔实史料,不由得产生了系统阐述明清中央王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的愿望。1993年我申报的“明清治藏研究”课题,获得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的资助立项,1999年出版了《明清治藏史要》。
退休以后,我继续思考“关系史”问题,2008年发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总体演进与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形成——兼批达赖集团篡改历史、鼓吹“西藏独立”》⑯一文。
说到“关系史”,藏文资料十分重要,汉文资料尤其不可或缺。现在有一个不太辩证的观点,搞民族史、藏族史,不通民族文字、不通藏文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是不能简单说不通藏文就不能搞藏学了,看你做哪一个专题,如果是作“关系史”。反之,不通汉文是绝对不行的。恰白先生的《西藏通史》在阐述藏族历史自身方面非常精到,但在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这个方面,恰白先生亲口跟我说过,他没办法运用明清实录藏族史料,他只能转引一点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里所引到的汉文资料。所以,年青一代的学者一定要汉藏文结合。
笔者:您从事教学科研将近60年,为西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私奉献,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青年学人树立了榜样。请您为青年学人分享一下您的宝贵经验和学术心得。
顾:我一直认为学校的发展人才是关键。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中做了一点工作,但是我们在人员素质、结构上受“文革”影响很大。新时代我们民大有一支学历层次高、年富力盛的学术队伍,可以说是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愿年轻同志珍惜自己的成长,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处理好教学科研的关系。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等学校教员,没有科研是不行的。科研是什么,科研立项是科研,没有立项也应该有自己一以贯之的研究。坚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夯实好基础。科研方面要锲而不舍,广积薄发。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不能过急、过于疲劳;就我感觉,如果身体好,就算退休了,专业研究也不一定就能停下来。
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学术道路和人生道路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方面应该坚持理想不动摇,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有梦想,专业上持之以恒、一以贯之,排除干扰。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功经验的话,还是敢于碰硬。比如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的整理、投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研究等,这在当时,无论是条件还是学术勇气,都是挑战。
今后只要身体健康,大脑清楚,我会无条件配合年轻同志,也就是不需要立项,不需要经费方面的支持,也不需要把我列为什么课题成员之类等等,只要能为我们民大藏学研究有新的更大的发展,我愿意做一些工作。
笔者: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注 释]
①西藏民族大学的前身,1958-1965年校名为“西藏公学”;1965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2015年4月28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见西藏民族大学校园网“学校简介”。
②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③索南坚赞著,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④《英国侵略西藏史》是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头目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el)于1910年出版的侵藏回忆录,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孙煦初的汉译本,1983年西藏社会科学院将其列为《西藏研究参考资料》丛书第三卷,在拉萨重印出版。
⑤《藏族简志》《藏族简史》两书是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少数民族史志丛书”中的两种,1963年完成初稿后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藏族简史》于1985年作为“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作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二由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⑥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⑦顾祖成先生当时以笔名成昌文,发表的《西藏原始文化同黄河流域的密切联系》一文,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
⑧该文名为《评沙俄特务德尔捷也夫在西藏的活动》,见《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⑨顾祖成等:《明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⑩顾祖成等:《清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⑪黄奋生,顾祖成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⑫顾祖成,陈崇凯主编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简明教程》,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出版后,2005年再版。
⑬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1999。
⑭《萨迦世系史》成书于1629年,著者为萨迦派款氏家族传人阿旺贡噶索南,原书名为“瞻部洲北部执掌佛法之大德具吉祥萨迦珍贵世系—满足诸愿之奇异宝库”。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本,1989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庆英等的汉译本,2002年再版。
⑮《朗氏家族史》又名《朗氏灵犀宝卷》,为大司徒·绛求坚赞(1302-1371?)著,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西藏社会科学院藏文古籍编辑室整理的藏文版,198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赞拉·阿旺、佘万治等的汉译本,2002年再版。
⑯顾祖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总体演进与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形成——兼批达赖集团篡改历史、鼓吹“西藏独立”》,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吴丰培.为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编印问世而欢呼[J].西藏研究,1984(2).
[2]多杰才旦.西藏的教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3]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M].北京: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