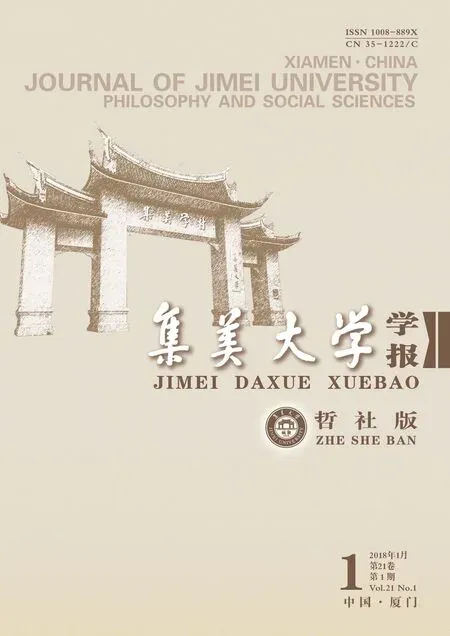挥着翅膀的“伊卡罗斯”
——《怕飞》的女性成长分析
曾 玲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小说《怕飞》是艾瑞卡·琼的自传体式小说,1973年发表于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期间,是作者的第一部文学小说。自发表之初,这部作品就广受争议。早期的评论令人喜忧参半,有的评论热情似火,有的评论惊恐万状。后来约翰·厄普代客在《纽约客》上赞扬了它,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亨利·米勒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热情的赞美文章,称这部作品是“自己的《北回归线》的女性版”[1]415,并预言这本书会改变美国的创作。截至20世纪初,这部作品销售了2 000多万册,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籍。
小说的主要脉络是女主角的各种逃离,从家庭逃向恋人,被恋人伤害后又逃回家庭。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该作品是女权主义风暴后的代表,其言语大胆前卫,对女性欲望极致凸显。作品自然地把男性的语言融入到自身的书写中,反映出女性在争夺话语权上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地位。然而正如书中女主角伊莎多拉在幻想一部电影里女主角在受伤后进行手淫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死去”[1]145,女性的自我追求被男性忽视,继而冠上“生育工具”的代号。以往的大多数评论家都仅仅把该作品视为女权主义代表,也认同其语言表现力度之强烈,忽略了主人公逃离背后的心理原因。笔者试从心理层面出发,探索作为文中连接各种关系主体的媒介——“飞行”及其背后所引申的内涵,指出“怕飞”是作者用来显示女主角各种不安全感的绝佳体现。而在看似对精神分析各种讽刺的掩盖下,艾瑞卡·琼刻画了一名因为心理安全感缺失而不断寻求亲密关系又逃离亲密关系的犹太女子,在反复挣扎、紧张焦虑下最终通过镜像反省找到自我之爱的成长之路。
一、恐惧症与安全感
保罗·G在《安全感》一书中提到,对于安全感,人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定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心理学各个流派里,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学派里讨论安全感较多。精神分析学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研究中,认为安全感是指一种心理氛围,即个体的工作、学习环境对其幸福影响的心理感知。弗洛伊德假定当个体所接到的刺激超过了本身控制和释放能量的界限时,个体就会产生一种创伤感、危险感,而伴随这些感觉出现的体验就是焦虑[2]29。社会文化精神分析的代表霍尼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认为儿童在早期有两种基本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和满足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父母,当父母不能满足儿童这两种需要时,儿童就会产生基本焦虑。武志红认为婴儿是从妈妈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存在。“若注目时妈妈与婴儿有共鸣,且带着接纳与喜悦,婴儿就会感觉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妈妈这面镜子若打开得很少,而且打开时都是儿童极力讨好母亲,就易导致一个结果:一个人对别人的反应极度在意”[3]62。人本主义者认为安全感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长的核心内容,是仅次于生理需要的地基。“当有人无条件关注你、接纳你、尊重你,慢慢地你就有了安全感”[2]28。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当生理需要被大体满足之后,第二层次的需要就出现了。个体变得越来越对寻求环境的安全、稳定和保障感兴趣,可能产生了发展某种结构、秩序和某种限制的需要。个体变得忧虑不是与饥渴这种需求有关,而是与他的恐惧和焦虑有关。马斯洛指出:“心理的安全感指的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4]1马斯洛认为心理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根据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的理论,父母(尤其母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客体,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如果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爱,持续、稳定、前后一致、合理的爱,孩子就会体验到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并且感觉到自尊、自信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伊莎多拉的童年经历和原生家庭的状况恰恰是完美的“示范”。这是伊莎多拉一直渴求爱、渴求性、渴求关怀的深层原因,是她成长的真正推动力。伊莎多拉的原生家庭总是充斥着各种争吵,父母没有明确的精神追求,也无法给予孩子追逐梦想的鼓励,甚至根本无法理解她的感受。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主张,“父母的职责是尽最大可能让孩子充分地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让孩子以后能够应付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用玫瑰色的美好色彩来美化现实,也不是用悲观的态度给他们描绘这个世界”[5]79。伊莎多拉的母亲是个矛盾体,她拒绝“平凡”,把它当成是瘟疫一般尽力回避。但她“声称她把创造力看得高于一切,可是真正看重的是赚钱与获奖”[1]198。伊莎多拉对怀孕充满了恐惧,因为母亲不断告诫她说正是由于孩子的拖累,她才没有办法成为一名艺术家。而父亲在做什么呢?母亲的说法是,父亲为了做他的酸奶黄瓜生意跑遍了世界各地,母亲则留在家里生孩子。这种被迫留在家里得不到自由的冲突引发了她的怨恨,但是她却合理化的解释为“女人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当艺术家,要么生儿育女”[1]52。被阉割的欲望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母亲的解释把女儿们引向两个极端,一类是不断的生儿育女,被生活折磨得忙乱不堪,而另一类就是拒绝生育后代。
在亲密关系中,伊莎多拉受到母亲这种相互矛盾心理的影响极大,尽管她个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与丈夫争吵的过程中,伊莎多拉指责他让她窒息,而丈夫贝内特则认为是伊莎多拉的母亲让她感到窒息,并且提到“不管(你)承认与否,你总在重新体验你的童年时代”[1]182。伊莎多拉也承认,“贝内特谨慎的、强制的以及令人讨厌的稳如泰山刚好是她对变化的恐惧、对孤独的担心、对安全的需求”[1]95。这种感觉实际是伊莎多拉对童年缺失母爱的一种诉求。母亲本应该给孩子提供这种安稳的感觉,让孩子感觉不用担心恐惧,不必害怕危险,感受自己的安全。阿德里安则象征着本我对欲望的追求,这是心理医生认为的“寻找我的父亲”,因为父亲在伊莎多拉成长过程中是缺失的,几乎无法给她力量。在伊莎多拉的梦中,阿德里安与贝内特坐在一个她童年常去的游乐场的跷跷板上,一上一下,相互博弈,并且就她的问题进行争论。这个意象很显然贴近了她童年的环境,两人分别代表她的父母,在争夺内心的力量。这种争抢,正好引发了她对周围环境的焦虑和内心的不安全感。对亲密关系和家庭之爱不太了解的伊莎多拉在婚姻中无所适从,母亲的“不能平凡的理论”让她在第一次走向亲密关系的时候潜意识地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布赖恩。与布赖恩的婚姻是她第一次尝试认识自己、寻求自我。在他的最后通牒下,伊莎多拉“一方面害怕失去他,一方面又想离开家,而且即将大学毕业,也不知道究竟还有其他什么事可以做——于是就嫁给了他”[1]253。可是她和布赖恩的爱情是美好的、精神性的、充满童稚气息。他们缺乏经济基础,同时缺乏关注彼此的成长和自身的成长,最后布赖恩甚至疯狂到要卡死伊莎多拉,让她进入天堂。得救后的伊莎多拉认识到自己被这段不幸的婚姻困住,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失去了创造动力,也迷失了自我。第一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伊莎多拉并没有审视自己的力量,而是希望依靠他人的力量获得自己的解放。“我就像一艘船,总要有一个停靠的港口。我就是无法想象自己没有男人”[1]104。在布赖恩被送进精神病机构后,伊莎多拉的父亲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引燃了她心中对于高大的父亲形象的追求——尽管在实际生活中,父亲并没有给予伊莎多拉多少关注。对父亲的需求,促使她迈出了成长的脚步,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并且找了一位咨询师的丈夫。
二、飞行与逃离
小说开头描述了女主角用谨慎而悲观的心态努力跟踪飞机飞行的整个过程时,并由飞行恐惧联想到一系列恐惧。这种种幻想,在一个不缺乏爱、不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身上都极少发生,但女主角恰恰觉得这种恐惧无所不在。“飞行”在作品里连接了很多重要的突破,比如创造力、性高潮及独立能力。在德国海德堡的时候,伊莎多拉感受到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时刻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监狱里。当时贝内特因为外公的去世变得沉默,无法顾及伊莎多拉的感受,伊莎多拉就开始运用她的写作能力,带自己脱离被封闭的生活,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我的写作就是将我带到我脑海里的未知世界的潜水艇与宇宙飞船……如果我学会建造适当的交通工具,那么我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领域”[1]277。伊莎多拉希望能够借助写作的翅膀,自由翱翔,自在生活,然而因为只有幻想而没有实际生活的体验,内心缺乏力量,她只能依赖贝内特和一些心理治疗师,创作的作品也局限在某些固定的领域,无法接触更新鲜的素材。“飞行”的潜寓意还体现在伊莎多拉的性幻想和性高潮里。叙述者铺天盖地地使用性语言,描绘自己的性幻想以及与多个男人之间的性行为,看似追求性高潮,其实是想摆脱女性被压抑的地位,获取和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在释放了欲望之后,并没有填补女主角内心的空虚和无助。在她经历了真正的成长后,当现实中遭遇陌生男人想要勾引她与她发生速交体验时,她发现“它非但没有激发我的激情,还让我感到恶心”[1]394。
伊莎多拉的第二任丈夫,贝内特·温(wing)完美诠释了一个典型的稳健的父亲形象。温(wing)这个名字里,wing代表翅膀,可以一飞冲天。在贝内特·温身上,伊莎多拉想要实现对于飞行的渴望,她希望自己能够“在一个男人身上把自己彻底忘了,不再成为(我)自己,想乘着借来的翅膀升到天堂上去”[1]392。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段婚姻中,伊莎多拉开始体验她在写作中的乐趣,看到自己的真实欲望和幻想。贝内特赞同伊莎多拉的写作行为,“在(我)相信自己之前他早就相信我能写作”。在这段婚姻里,伊莎多拉接触到很多心理咨询师,学会停止讨厌自己,开始爱自己。与此同时,她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缺失的安全感并不能从丈夫身上获得,相反,她陷入了一种对丈夫的批判、反抗中,似乎这样她就能实现潜意识里对自己的父亲的反抗。正如后来引诱她离开的阿德里安所指出的,“你终生都在寻觅一位导师,后来你找到了他,你就深深地依赖他,过度的依赖又使你开始憎恨他”[1]115。当伊莎多拉没有力量承载自己的成长时,她转而责怪贝内特,责怪这种依赖,然后试图逃离这种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莎多拉遇到了来自英国的咨询师阿德里安,受他的引诱离开了丈夫贝内特,离开假象的舒适区域。伊莎多拉在是否离开贝内特的念头间挣扎的背后,也是她在独立还是依赖之间抉择的纠结。阿德里安声称他们的旅途能够让伊莎多拉发现自己,“你的计划是要弄清楚,你有多么坚强。你的计划是要开始相信,你可以独立自主”[1]174。当伊莎多拉害怕这种独立行为时,阿德里安嘲笑她,“我给你提供一种生活体验,它能真正改变你,你确实可以对此进行写作,而你却逃跑了”[1]183。逃离的起因是由于性诱惑,可深层原因则是伊莎多拉对于自我的审视,对于自己写作素材的质疑以及对于自我独立的追求。她一直以为自己在追寻爱,阿德里安直接戳破她的谎言:“你嘴上说爱,但你的意思却是安全感。”[1]186她知道自己无法从阿德里安身上获取安全感,却仍继续这段旅程,原因是来自心底成长的需求,她希望自己能够“学会如何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存在下去,学会如何承受自己的生存,学会如何关怀自己,而不是始终转向精神医生、恋人、丈夫、父母求助”[1]329。随阿德里安离开德国后,她感觉自己抛弃了以前的角色,并且下定决心勇敢跟着感觉走。“我不再是胆战心惊的家庭妇女,我正在飞”[1]227。阿德里安开车很疯狂,这种疯狂到近乎于追寻死亡的感觉刺激了伊莎多拉的感知觉,极大地冲击了她的安全感,让她有了飞行般的体验,轻松自在,“想象着自己滑翔穿过羊毛状的云彩,进入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满怀着你最心爱的童年记忆”[1]235。她开始觉醒,知道所有的恐惧背后都有难以遏制的逃避的冲动,而她需要“忍受这颗疯狂乱跳的心,一直到……找到一个谁,也许找到我自己”[1]355。
三、自恋——走向成熟
引路人的缺失使伊莎多拉的成长尤为艰难,在这样的心境下,自我审视成为她自发成长的有效途径。镜子在作品中承载了伊莎多拉的自恋情结,激发她探索分析自己,走向整合之路。霭理士(Havelock Ellis)说,“这种类似自恋的倾向,在女子方面原有其生命的种子,而这种种子的象征便是镜子”[6]178。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自恋正是与一个镜子的故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在《莱昂纳多·达·芬奇和他的童年的一个记忆》中首次提到了自恋(Narcissim)。后来,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一个导论》中,运用力比多理论分析自恋现象,并且指出了自恋理论的前提假设——本能理论。对于儿童性欲的研究,弗洛伊德假设,“人最初有两个对象——自己和养育自己的女人,就此而言,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有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7]255。个体离开了原初自恋,并以理想的形式将其恢复,他为自己树立的理想只是童年失去的自恋的替代,这种自恋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
拉康发展并批判了弗洛伊德的两种自恋,并论述了“镜子阶段”的文章,通过描述婴儿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他论述了认同和理想的产生。镜子阶段存在三个环节:在镜子面前的儿童表现得像是看见了一个真正的人或者是一个其他的形象;然后儿童不断地想控制或者找到在镜子后面的这个人;人类的儿童认出了这个“像”(image)就是他自己。婴儿在镜中看到的“像”并不与他自己实际的经验完全吻合,镜中的“像”是需要解释的,是“我”的最初表现,也是自己要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镜子阶段是从不充分到预期的急速发展的内在冲动的戏剧,是落入空间认同圈套的图谋着幻想的戏剧。这些幻想将身体的破碎形象与我们称为它的整体的矫形形式连接在一起,将身体的破碎形象与由异化同一性所确定的保护机制连接在一起”[8]15。在《两种自恋》这篇文章里,拉康进一步提到:“在人身上,镜子中的反射指示了一个原初的智力的可能性,并引入了一个次级自恋,它的基本模式就是与他者的关系”。“他者,这个另一个自我,依据生命阶段的不同,或多或少与自我理想混淆在一起……自恋的认同,是与他者的认同,在正常情况下,使人能够精确地定位他与世界的想象和力比多的联系”[9]156。镜子阶段的来临即是孩子形成主体意象的那一刻,而孩子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自我意象,让自我意象内化,是孩子自我整合自己的形象,形成类似于格式塔一样的完形。正是在这种完形中,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意象完成了一个从部分到整体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作品中镜子充当认识了解自己并产生自恋的媒介是具有普遍性的。
在伊莎多拉刚认识阿德里安后不久,她和贝内特及阿德里安一起参加宴会,却被许多相通的镜子厢间以及隔间弄迷糊了。他们“不断地朝自己走去,如同在梦里一般,辛苦地寻找,心里的恐惧不断增加”[1]108。这个时候的伊莎多拉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弱小,也无法找到坚定的信念,所以避讳看到镜子,避讳自我审视和自我探索。与阿德里安逃离贝内特身边后,她离开了相对温暖舒适的生活,开始了自我冲击和自我成长之路。在她习惯性依赖男人的时候,阿德里安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她只能独自一人呆在巴黎一家小破旅馆,孑然一身、孤立无助,好像回到了孩提时代最糟糕的黑夜恐惧症。在恐慌中,她求助了成人的自我,开始了理性的自我批评。回想起心理咨询师哈佩医生给她的分析,她意识到自己的恐惧跟她的犹太身份及母亲对她的不当保护有关系。当恐慌过去后,她明白潜意识里的恐惧只能通过自我成长克服,于是静下心来审视自己。
伊莎多拉自我审视的过程也是她通过自恋进而达到自信的心理成长历程。她仔细地看着镜中裸体的自己,有批判,有赞同,她“不再自我责备……也许(我)最终的逃跑并不是因为我的邪恶……也许那正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忠诚。一个改变(我)生活的强烈而必需的手段”[1]376。在阅读自己以前的笔记时,她梳理自己的思维,认识到自责无法改变事物的现状,自己总是混淆依赖与爱,并且想到了解决混乱婚姻的方法——“如果我与贝内特再次言归于好,情况必须完全不同。如果不能言归于好,我知道我也能挺过去”[1]377。镜子里的自己拥有完美女性的形象,柔弱而又刚强,恐惧而又坚韧,种种美好浮现在她心头,女性的自恋帮助她稳定情绪,克服恐惧,冷静思考。她认识到自己这四年来的进步,不再像以前那样恐惧不可控制的事情。她了解自己并不能掌控不可知的事物,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接受事物的发生,而不是让无端的想象扼杀自己的行动力。坐在圣米歇尔广场的咖啡馆,伊莎多拉享受了平凡生活中的快乐,强烈意识到活着所能享受到的一切微不足道的快乐。她意识到,她对性“飞行”的盲目追求,严重影响了她认识自我和接受自我;这种所谓的飞越和飞离并不是来源于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借来的“翅膀”飞行。她讽刺自己就像是伊卡罗斯借助父亲达罗斯给他建造的蜡翅膀飞行,并且试图用这借来的翅膀脱离父亲。但是由于离太阳(梦想)太近,蜡融化,翅膀散落,独立的梦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借来的翅膀是靠不住的。她应该继续写作,找到自己的核心力量,摆脱对过去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真正展翅高飞。
浸入浴缸,洗涤自己的动作是很多成长小说都有出现的仪式。在作品的结尾处,伊莎多拉找到贝内特住的酒店后,进行了这一仪式。在深深的浴缸里,她感觉自己漂浮起来,觉得有什么东西是陌生的。向内探索后,她抱住自己,发现“我的恐惧消失了。二十几年来一直在我心里的那块冰冷的石头消失了。不是突然不见的,并且也许不是永远消失,但是它不见了”[1]402。她知道自己能活下去,最重要的是她会继续写作,壮大自己的内心力量。正如英国学者鲍曼所说:“两个分离的、自我包裹的存在,每一个的存在都通过守护自己的自我性、自我的同一性、自我的边界、自身的空间得到实现。”[10]81成长起来后的伊莎多拉认识了爱与依赖的区别,不断肯定了自我价值,维护了自我的发展,只有在此基础上,她才能跟他人建立健康、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肯定的亲密关系。
[1]琼. 怕飞[M].石雅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保罗·G,孙向东. 安全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3]武志红. 为何家会伤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4]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 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5]阿德勒. 儿童人格教育[M].戴光年,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6]霭理士. 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7]JEAN LAPLANCHE, J 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M].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1973.
[8]LACAN ECRITS. A selection[M]. ALAN SHERIDAN, trans.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
[9]拉康.拉康选集[M]. 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0]鲍曼. 后现代伦理学[M]. 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