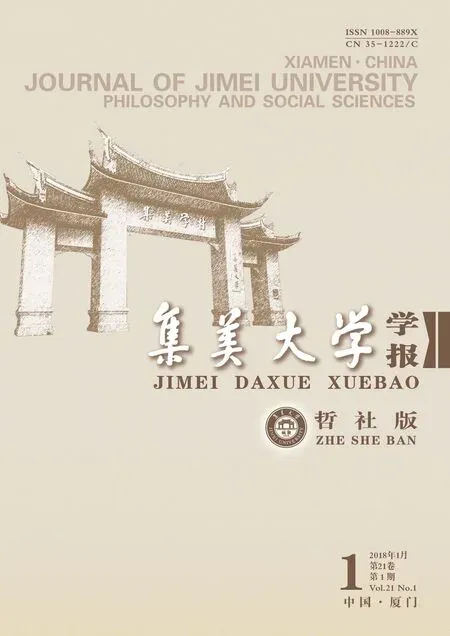我乃声音之名,名之声音
——新奴隶叙述《爵士乐》中的“声音”与非裔主体建构
王 斐
(1.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引 言
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继承了非裔奴隶叙述(the slave narrative)的书写传统的同时,又将其创作融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彰显非裔族群的文化、种族和性别的话语场域,从而表达对非裔族群的受难史、身份认同、精神世界和历史命运的关注。
《爵士乐》(Jazz,1992)作为莫里森撰写的美国非裔历史三部曲之第二部,与之前的《宠儿》(Beloved,1987)一样,依然根植于美国非裔历史,以巧夺天工的叙事框架和恢弘瑰丽的想象,重新检视与诠释美国非裔离散史。莫里森在该小说创作中模仿爵士音乐即兴演奏技法,集结调用了多种叙事手段和策略,以跳跃转换的时空、迂回交错的情节,演绎了非裔族群的多舛命运。这部带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新奴隶叙述犹如一部爵士乐即兴演奏曲,情节不依照线形发展,也无甚高潮起伏,而是在开头紧锣密鼓地交代出故事的大致轮廓:20世纪20年代美国非裔“大迁徙”背景下的“大都会”,50岁的男主人公乔爱上了一个奶油肤色的少女多卡丝,终因怀疑她不忠而将其枪杀。乔的妻子维奥莱特,在少女的葬礼上企图用刀子划破其死去的情敌的脸庞。接下来,这场婚外情、葬礼混乱的波澜搅起了死寂的往事。乔想起了自己一生中的七次蜕变、回忆起自己的母亲——一个精神错乱的野女人;维奥莱特回忆当年与乔的相识、自己家族在蓄奴制废止前后的血泪历史;少女多卡丝历经种族骚乱痛失双亲的童年、爱丽丝姨妈身世背后的创伤记忆,乃至故事赖以发生的宏大社会现实在回忆叙述中一一呈现,展演了南北战争以来半个世纪美国非裔族群在奴隶制、南方重建、大迁徙历史变迁中的苦难史以及精神状态的困境。最终小说中所有人物能坦然面对过去与自我,达成对非裔社群的认同,并同时经由回忆叙述对抗白人的官方书面历史,得以在非裔心灵荒原中获得救赎与自由。
可以说《爵士乐》以繁复的叙事策略与爵士乐即兴演奏技巧,使非裔族群用身体所铭刻却被官方书写的语言暴力所规训和隐藏的受难史,在后现代的叙事碎片中得以重现。因此,本文试图探讨莫里森如何通过戏仿奴隶叙述的“说话书”(the talking book)以及爵士乐的即兴演奏(Jazz improvisation)这种另类的“种族言说”去修正被白人权威话语书写的历史记忆,打破在暴力制度下一个族群的沉默,对非裔遭受压制、被遗忘以及边缘化的惨痛历史进行召唤、重建与疗伤,进而实现个人与群体的救赎。
二、新奴隶叙述的定义
新奴隶叙述(the Neo-slave narrative)滥觞于奴隶叙述(the slave narrative)。根据戴维斯和盖茨(Davis & Gates)的定义,奴隶叙述尤其指废除奴隶制前即1865年前出版的关于“非裔群体惨遭奴役迫害的书写证言”[1]。可以说,奴隶叙述以罄竹难书的奴隶制以及对黑奴惨绝人寰遭遇的揭露在解放黑奴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奴隶叙述更体现了在开始摧毁西方文化加诸于其身的客体身份与商品身份之前,非裔所作出的确立自己为 “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s)的大胆尝试。正如盖茨所言:“奴隶叙述是奴隶对主人把自己变成商品的企图的表现和倒转,同时也是奴隶同样拥有欧洲人所拥有的人性的佐证,这种交错配列也许是奴隶叙述以及后来的黑人文学中最普遍使用的修辞象征。”[2]146然而,历史记录总无法逃离官方权力的运作,因此官方权威决定了奴隶叙述中的何种事实该被保存乃至美化、何种事实该被屏蔽乃至曲解。例如相当一部分的奴隶叙述由前黑奴撰写,依然有许多文本却是由前黑奴口述再由白人进行记录整理,于是就存在白人记录员所记载的奴隶叙述能否忠实于黑奴口述内容的争议。[3]159
虽然奴隶叙述在重建再现非裔族群历史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为新奴隶叙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当代非裔文学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以非裔族群为代表的边缘群体书写的历史逐步动摇了官方历史叙事的本质主义的诉求,传统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被解构。在此背景下,新奴隶叙述大量涌现,为非裔族群提供另类的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和对抗的记忆(counter memory),为重新诠释历史事件提供了对话场域而且还“成为足以颠覆白人官方历史书写的潜在力量”[4]。拉什迪 (Ashraf H. A. Rushdy) 认为新奴隶叙述是“现代或当代那些以描绘新世界蓄奴制经历及蓄奴制贻害为主的虚构作品……将蓄奴制当作一种具有深远文化含义和挥之不去的社会影响的历史现象加以再现”[5]。因此就主题内容而言,当代新奴隶叙述“在套用奴隶叙述时……就是通过对历史书写的干预,再现多元异质的黑人主体;通过刻画蓄奴制这一古怪的体制下黑人痛苦的同时,重新唤起人们对当下美国语境下自由的概念和美国黑人整体命运的关注与思考”[3]159。换言之,新奴隶叙述通过重塑过去断裂、零落、破碎的历史记忆成就文学与历史的见证,让被噤音消声的非裔族群历史重新发声,实现非裔族裔的身份认同与社群建构。
就叙事手段与策略而言,新奴隶叙述有明显互文性特征,即抓住传统主题与转义并给予修正从而构成了文本之间奇特的形式谱系上的延续性,[2]129与此同时杂糅了如后现代叙事技巧以及非洲口头艺术形式(oral art forms)于其中。新奴隶叙述“其潜在的力量就在于刻意改造、嬉弄前文本或文类,批评或审视‘赢家’书写的历史,并通过虚构,提出自己版本的历史,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注”[3]159。概而言之,新奴隶叙述以其独有的叙事策略与白人历史观、官方话语以及知识权力网络颉颃交锋,瓦解白人以知识与权力所建构的各种论述。
三、戏仿奴隶叙述的“说话书”——重塑非裔的言说主体
身为美国非裔女作家,莫里森是种族语境下以及性别话语语境下的“他者”,其言说的话语空间必然遭遇白人强势文化话语权系统性的掠夺、规训和压制。因此,莫里森所面临的叙事困境在于如何以新的“种族言说”方式开拓非裔族群的言说空间,使非裔族群在种族主义的桎梏中获得解放。莫里森对语言有着极为卓著的驾驭能力,其创作的新奴隶叙述《爵士乐》以爵士乐风的即兴叙事手法智慧地将后现代叙事技巧与非洲口头艺术形式(oral art forms)以及非洲音乐完美的集结,挑战了西方文学传统,撼动了白人主流话语霸权,在重写非裔族群历史的同时更呈现出离散主体寻求身份文化定位的过程。
在《根性》(Rootedness)这篇文章中,莫里森指出她在小说中致力于结合印刷文字与口述文学,使得小说不仅可以被安静阅读也可以在阅读中被听见。[6]58-59因此,她的叙述文体向来具有口语化及音乐性的口述文学特色,而该特色则是继承了西非部落故事讲述者(Griot)*故事讲述者(Griot)原来指代西非部落中传统的说故事者,他们用歌唱形式表演口头史诗,因而被认为是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口头知识宝库,社会传统和价值观的源泉。在非洲散居族裔的语境下,故事讲述者这一术语被广泛用来指代实行这一功能的艺术家,如非裔小说家、非裔诗人、西印度洋流行歌手,他们都被视作非洲语言艺术家。在后殖民语境中,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Chinua Achebe)认为非裔艺术家承担着近似于故事讲述者的社会责任——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重建以及对民族历史进行重述。的说唱传统。通过融合美国黑人口头习俗和音乐创作的声音效应而形成的“视听文学”,[7]莫里森挑战了西方主流文化与历史中以书面话语书写的典律,解构了西方霸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关系:中央/边缘,优/劣,主体/客体,理性/神秘。
在这部极具爵士乐特质的新奴隶叙述中有一性别与身分不详的匿名叙事者贯穿于小说始末。为此有些评论者将爵士乐视为小说之匿名叙述者,[8]11而莫里森则在访谈中表示此书中的叙述者其实为无性别与年龄的叙述声音*《爵士乐》中的叙述者“声音”可以看做是莫里森对非裔作家赫斯顿所创造的叙述声音的致敬式的戏仿。盖茨评论赫斯顿创作的叙述声音是“一种抒情性的、游离于身体之外的但又个体化的声音。[……]一个响亮的真正的叙述声音能呼应并且追求黑人口语传统的非个人性、匿名性以及非权威性地位。黑人口语传统无名无姓无自我,它是集体性的,有很强的表现力,并忠于共同的黑色性未曾写下来的文本。(the unwritten text of a common blackness)”。详情参见:GATES, HENRY LOUIS.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M].New York:Oxford UP,1988:202.,并指明这是一本“说话书”的“声音”。[9]94事实上,莫里森的“说话书”指涉了自奴隶时期起就存在的黑人方言与文学化的白人文本之间、口语语词和书写语词之间、文学话语的口头形式与印刷性质之间的一种奇特的张力。自奴隶叙述开始,非裔作家便致力在文本中建立属于自己族裔的声音,声音在其文学传统中便与主体的“现存”相关连。[2]131换言之,非裔只有通过将他们的声音铭记在书写下来的语词中,他们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盖茨在《意指的猴子》(TheSignifyingMonkey,1988)中阐述“说话书”的这个比喻时,援引黑奴伊奎阿诺(OlaudahEquiano)的奴隶叙述《伊奎阿诺的人生记趣》(TheInterestingNarrativeoftheLifeofOlaudahEquiano,1789)中的一个片段揭示黑奴在面对白人书写时所经历的“主体阉割”。伊奎阿诺看见主人看书时,误以为主人是在对书说话,所以也就常拿起书来对之说话,然后耳朵紧贴着书尝试倾听书的回应,然而书始终保持沉默,令他十分不安。这名黑奴认为书对他的主人说话,他的主人也对书说话,二者之间有声音交流,而他身为黑奴所得到的只有沉默。可以说,这段轶事可以理解为丧失主体性的伊奎阿诺在和同样为客体的书说话的时候,出现的当然只能是无生命的两个客体之间死寂般的沉默。事实上,伊奎阿诺的这段“趣事”隐喻了在白人社会符号体系之中,非裔的面部特征和话语在西方文本中是缺席、无效与空虚的符号。非裔没有声音,也听不到回应,被隔绝于以白人主体性为中心所建构的知识体系、话语及书写之外。在此莫里森运用“说话书”指代新奴隶叙述《爵士乐》,戏仿了伊奎阿诺的文本,重复延续了该奴隶叙述的传统并将之修正转义(trope)*根据盖茨的定义,转义(trope)是一种黑人话语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在类似语言游戏活动中自我产生或创造意义,不再受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这种修辞手段衍生出具有鲜明非裔民族话语特质的表意方式——“喻指行为”(Signifyin(g)),实现对白人的“表意”(signification)的再构与重排、重复与修正。转义(trope)由修辞层面将曾经被语义层面压制的语词意义释放出来,从而赋予了非裔言说的主动权。详情参见:GATES, HENRY LOUIS.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M].New York:Oxford UP,1988:46-47.——只有在西方文化中运用“声音”这个终极符号方能赋予自身的主体性。
盖茨就叙述声音作用于主体建构意义做过如下阐释“声音演绎了一种独特的渴望和言说,在声音中出现了一个远远超越个体的自我,出现了一个超验的、说到底是种族的自我”[2]202。于是莫里森试图在她的创作中以非洲音乐以及口述传统重塑非裔历史,使爵士乐音(the sound of Jazz)转义为叙事声音(the narrating voice),从而超越文字,承载文字无法表达之事。她的这个企图在小说扉页所引用的于1945年在埃及纳格哈马迪(Nag Hammadi) 出土的诺斯替教(Gnosticism)*诺斯替教(Gnosticism),其意为真知派。Gnostic源于希腊词汇Gnosis,意为“真知”。在基督教的早期诸教派中,它迫使早期基督教会为了反对它而汇编成《圣经》。文献中的一首长诗 《雷霆, 完美的精神》(Thunder,PerfectMind)中的第一诗行所彰显:“我乃声音之名,名之声音。”
四、爵士乐的异质书写:颠覆西方叙事传统的即兴曲
这部新奴隶叙述小说的背景设置于爵士乐蓬勃兴盛的20年代,正是非裔迁徙到北方都市期间开始认知到他们需要属于自己的音乐的时候。[10]273新兴的爵士音乐无疑代表非裔文化身份,甚至也包含对西方白人文化的反抗,挑战传统西方白人音乐的创作模式。芬克斯坦(Sidney Finkelstein) 认为爵士乐是“黑人解放后遭受监视和镇压之下赖以述说不幸遭遇、抗议种族歧视压迫并表达自由渴望的声音”[11]。可以说,爵士乐跳脱出传统音乐规则的限制隐喻了非裔族群对抗文化霸权时不屈与充满活力的声音,“保存并传达了塑造身份认同的真理”[12]。进一步说来,爵士乐化的文体亦起到了对抗西方文学叙事传统的作用,带有爵士乐质感的书写无需借助于西方经典文学的权威和范式,以“声音”凸显非裔力图反对压制黑人声音和情感的主流文化霸权的毫不妥协的“歧异”(Differend)。于是由爵士乐音(the sound of Jazz)所转义并彰显的“声音”(voice)在小说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音乐之声与叙述声音交相辉映,铭刻了非裔族群的异质文化与族裔身份,也再现了非裔主体在迁徙过程与城市漫游中的迷茫与追寻。
这种爵士乐化的叙事风格以迥异于传统叙事的谋篇布局,以正在说话/书写、即兴/雕琢的错列并置,时而重复用字,时而改变节奏,时而呼叫应答,使“声音”随兴所致,游走于沉默与言说之间。在排篇布局上,莫里森首先糅合了爵士乐的乐谱章法使文本所产生的独特视觉效果转化为“乐音”,使其成为能够被安静地阅读,同时也能让读者聆听的“说话书”。《爵士乐》共十章,与西方文学传统迥异的是,各章节之间并非以文字或数字做标题,而是以一页空白间隔开来,构成爵士乐节奏所必须的休止符,形成某种静默的意象,视觉上的行进与停顿在听觉的层次上便转化成叙事声音或音乐的进行与中断(静默)。吉尔罗伊 (Paul Gilory)认为,黑人音乐保存某种与黑奴历史相关的“本体论状态”(ontological state),即“痛苦的存在”(the condition of being in pain),透过如切分音等节拍的变化与时间的断裂表达出黑人文化的特殊性,也展现出其身份上的认同。[13]可以说,小说文本中声音(现存)与静默(缺席)的交替出现,恰好隐喻非裔离散主体在大都会身份认同过程中所经历的居间性(in-betweeness),表达离散主体迁移进入大城市后认同的困顿与文化环境上错置(dislocation)的状态。易言之,这种另类的排篇布局将传统的符号体系陌生化,反映了莫里森试图重新题写并重新阐释非裔族群现状的另类语言空间。从各个章节的关联来看,莫里森还运用爵士乐中的滑奏(glissando)效果,如前一章的最后一个字(音)是后一章开始的第一个字(音),构成既中断又持续的韵律感。[14]252例如,第四章以“春天来到了大都会”[15]120。一句做结,随之第五章则以“当春天来到了大都会”[15]123起头。此外,莫里森又试图仿拟爵士乐呼—应(call-and-response)的音乐模式衔接各个章节,每一个章节结尾的一句话或者意象都是下一个章节的开始,营造出即兴与互动氛围,从而邀请读者展开与书的“对话”和即兴创作。例如,在第七章以叙事者的发问“可是,她在哪里”[15]226做结,随后第八章就给予回答“她在那里”[15]228。又如在第九章结尾以“这能让痛苦减轻些”[15]235。第十章则随即以“痛苦”起头最为对于上一章节的回应。由于声音本身赋予主体实存(substance),这种藕断丝连的文字安排于是呈现了声音(主体)与现存之间的关连性。因此莫里森这本“说话书”使读者在两个章节之间的空白节点展开缥缈深思并进而触动读者聆听到书中的声音并给予回应,曾经遭到噤音的非裔族群之声音从而得到聆听与回应,主体性得以辨识。
爵士乐的曲式结构不仅体现在小说文本布局上,亦通过小说叙述内容而彰显。 在爵士乐演奏时,通常有一段基本素材,乐队的每个成员包括领衔演奏者都要围绕这段素材,在和声框架的范围内于重复中进行大胆、自由而又随心所欲的即兴创作。《爵士乐》基本的音乐素材在小说开头便已交代,接下来围绕着这场婚外情与葬礼的基本情节,匿名叙事者(“声音”)时而犹如乐团首席爵士歌手独自浅吟低唱尘嚣过往,时而与其他小说人物(乐团成员)的叙述声音展开了交互轮唱与即兴演奏,从而打破遵循原因结果、时空顺序、逻辑秩序和层次关系的传统叙事规约,代之以非线性的、断层的、碎片化的后现代叙事模式,从不同角度解构故事本身。于是,多重叙述视角的循环叙述使情节与主题犹如兜兜转转的枝蔓缠绕,在过往与当下穿入斜出,在梦呓与现实混沌中交错层叠。可以说,这种打破时空、现实与虚幻的叙述策略亦隐喻了被白人暴力改写后的非裔族群所产生的的时空倒置感。叙述者与小说人物各自的独白相互交织,角色各自的疑问从他人得到回应,犹如爵士乐曲中的“呼-应”(call-and-response)形式,反映离散主体祈求回答或回应的欲望。散落于时空的故事碎片在各个人物的即兴演唱中得以拾掇拼贴。他们关于苦难的叙述声音同时也得以直抵读者肺腑,奴隶制的暴虐与贻害以及非裔族群的多舛命运随之尽收眼底。可以说在爵士乐的即兴表演中,文本中近乎疯狂虚妄的声音中无不隐含着族群创伤记忆,无不充斥着奴隶制贻害下的痛苦与阴霾、彷徨与迷惘。概而言之,爵士乐风的叙事文体不仅彰显了非裔主体的文化身份,并且回应了历史与种族创伤的痛苦与梦魇,更呈现出离散主体寻求符号定位的过程。
埃里森(Ralph Ellison)认为,爵士乐中的独奏与即兴表演既是在界定个人的身份,也是在界定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以及与历史传统之间的一个连结,爵士乐的生命在于把历史传统作即兴的表现。[16]因此,在文本中众声喧哗的爵士即兴曲里,爵士乐般的叙事声音塑造了离散主体,救赎其脱离白人种族主义论述中非裔静默的黑色身体所表征的空缺状态(blankness),进而使官方的非裔历史论述也得以被颠覆与重构。奥斯坦多夫(Berndt Ostendorf)认为爵士乐从白人与黑人的民间传统中杂揉了异质的对话,[17]396即爵士乐本身是呈现离散主体寻求身份界定的杂揉文化产物。因此“说话书”是莫里森借“爵士乐”谱写而成的新奴隶叙述,凸显了其在语言表达权、文化再现、族裔历史和历史脉络之间进行某种积极的尝试。可以说,小说中爵士乐化的族裔叙述彰显了非裔语言在英文语言符号背后的合法性,非裔口头艺术与音乐传统的叙述方式通过介入到英文文本中,以“相互演出”(interplay)的方式解构宗主语言,在黑人文本中确证其黑色意义。此外,如爵士乐即兴表演般的零散化和拼贴化的叙事手法一反传统的叙事结构,消解西方宏大叙事,使非裔族群的历史记忆得以重构。
五、结 论
可以说,《爵士乐》扉页引用的古埃及诗“我乃声音之名,名之声音”极为精妙地概括了莫里森创作该文本的意图与修辞策略。爵士乐为莫里森的族裔叙事提供了足够的结构隐喻,其颠覆了西方结构严密、逻辑紧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符号系统,多重叙事技巧的反复奏鸣以及复调式的咏叹之“声音”重新题写并开辟了非裔美国人另类的言语空间。融汇了黑人口头习俗和音乐传统书写成的“说话书”,逾越西方经典文学典律进而消解颠覆西方的宏大叙事,使非裔离散主体的历史得以在爵士乐般的叙事声音中被重新书写与聆听,这恰恰是新奴隶叙述的目的所在。
[1]DAVIS, CHARLES T, HENRY LOUIS JR GATES. The slave’s narrative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XII.
[2]GATES, HENRY LOUIS.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M]. New York : Oxford UP, 1988.
[3]林元富.历史与书写 —当代美国新奴隶叙述研究述评[J].当代外国文学,2011(2):152-160.
[4]MCQUIRE, SCOTT. Visions of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 memory, time and space in the age of the camera [M]. London: Sage, 1998:169.
[5]RUSHDY, ASHARF H A. Neo-slave narratives: Studies in the social logic of a literary for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22.
[6]MORRISON, TONI. Rootedness[M]//MORRISON, TONI,CAROLYN C DENARD.Toni morrison: what moves at the margin.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08:56-65.
[7]DAVIS, ANGELA Y. Blues legacies and black feminism : gertrude “ma” rainey, bessie smith, and billie holiday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0:148.
[8]ECKARD, PAULA GALLANT. The Interplay of music, language and narrative in toni morrison’s jazz.[J].CLA Journal,1994,38(1): 11-19.
[9]CARABI, ANGELS. Nobel laureate toni morrison speaks about her novel jazz[M]//DENARD, CAROLYN C.Toni Morrison: Conversations. New York: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3:91-97.
[10]LEWIS, BARBARA WILLIAMS. The function of jazz in morrison’s jazz[M]//MIDDLETON, David L.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Manchester UP, 1998:271-82.
[11]FINKELSTEIN, SIDNEY. Jazz:a people’s music[M]. New York:Citadel,1948:28.
[12]MORI, AOI. 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 [M].New York:Peter Lang,1999:113.
[13]GILORY, PAUL.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consciousness [M]. New York: Harvard UP, 1993:203.
[14]RODRIGUES, L EUSEBIO. Experiencing jazz[M]//PRTERSON, NANCY J. Toni Morrison: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7:245-66.
[15]MORRISON ,TONI. Jazz[M].New York: Knopf, 1992.
[16]ELLISON, RALPH. Living with music:ralph ellison’s jazz writings [M].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36.
[17]PICI, NICHOLAS F. Trading meanings: the breath of music in toni morrison’s Jazz[J]. Connotations,1998,7(3):372-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