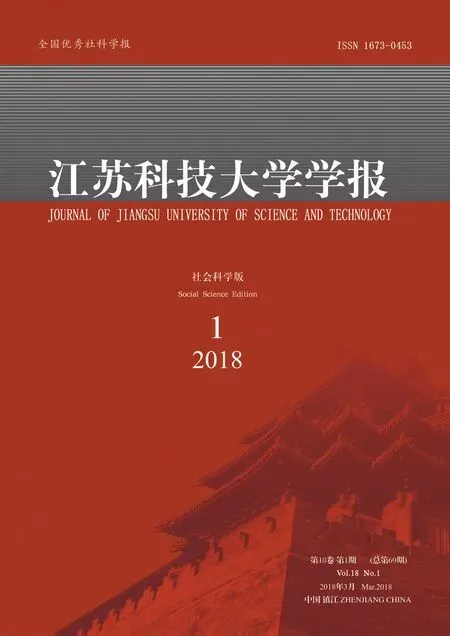武则天与进士科关系考辨
——从武则天人才理想的角度
卢 娇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00)
在武则天与进士科的关系上,现代人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武则天的干预下进士科更重文词,甚至开始“诗赋取士”;在用人方面,武则天则压制明经而特重进士一科。此种观点以陈寅恪、尚定、胡可先等人为代表,分别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1年版)、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胡可先《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陕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初唐进士科并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赋取士”,武则天对进士科也并未特加重视,认为当时无论从录取人数还是高级官员的出身来看,进士、明经两科的比例与此前相比均无明显变化。此种观点以岑仲勉、傅璇琮、吴宗国、陈飞等人为代表。分别见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吴宗国《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璇琮《武则天与初唐文学》(《燕京学报》新7期)、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岑仲勉先生虽认为武则天时进士科已开始试诗赋,但乃偶然改革,非刻意而为,并未体现出对进士科的青睐。可见,两种观点分歧很大,因而极有必要深入探讨武则天对进士科试项的具体改革*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一章《朝廷考试及其试诗——进士科“以诗取士”的确立与调整》对唐初进士试项的沿革变化有比较详细的考述,但多致力于在现象层面的还原,而没有探讨改革背后的原因,特别是与统治者的关系。另,该文对当时进士试项沿革过程的描述与本文也略有不同。,在此基础上才能厘清武则天与进士科的关系。笔者拟从武则天的人才理想入手,结合其对进士试项的具体改革及实际选拔结果、当时的现实形势需要,探究武则天对进士科的真实态度。这对武则天研究、唐代科举史甚至唐代文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一、 武则天的人才理想
关于武则天的用人喜好,历代史书所述颇多,最常见引者则莫过于《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所曰: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1]357-358
即武则天爱好文学,喜用文士,在她的影响下,公卿百官都是因文章而显达之人。由此,文史并重特别是善于作文便被看作是她的人才理想。这段记载影响很大,它确实反映了武则天用人的一个重要侧面。比如她前期所重用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不仅善于逢迎,也熟悉经史并文采灿然,在龙朔年间与上官仪一起成为最重要的宫廷诗人。稍后的“北门学士”,更是武则天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的一批才学俱佳的人选,并被引入禁中,特许从北门出入,“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2]2846,更是表现出她对文学人才的器重。晚年的武则天,身边聚集了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等大批文学之士,并留下了杜审言因赋《欢喜诗》而被重新擢用、郭震因赋《宝剑篇》而免于责罚、崔融因撰《启母庙碑》而受褒奖等众多奖掖文学人才的佳话。对此,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曾热情歌颂: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3]
文学才能确实是武则天人才理想的重要方面。
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审时度势及对人才的充分利用,而她用人的出发点则是基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比如许敬宗等人的文学才华恰好适应了特殊阶段宫廷斗争的需要,由其起草的诏敕文书总能替武后的活动找到历史依据而使其合法化*如许敬宗起草的《立武昭仪为皇后诏》,将高宗与武则天的乱伦行为偷梁换柱成“事同政君”,即谓武则天像汉代的王政君一样,是先帝的宫人,然后由先帝赐给太子。这一典故不可谓不巧妙。,并且能用华美的文词来粉饰渲染。她对“北门学士”的任用也是极大地发挥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不仅修撰了《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书,而且还根据需要适时地编纂了《少阳正范》《孝子传》去规劝太子李贤顺从武则天,帮助武则天密谋临朝称制,又助其建成明堂,是武则天的“智囊团”,在她夺权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武则天临朝后,“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2]2847。可见,武则天并非只重文学才能,而是越来越认识到政治识见所反映的经世之才也是治世之所必需,这些用人实践让武则天相信,文学与政事的结合是最完美的人才模式。
嗣圣元年(684)徐敬业起兵,武则天在读到骆宾王的檄文时深加赞赏,其赞的不仅是骆宾王的文采,也包括他的政治胆略和智慧:
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4]
“狐媚惑主”之类不过是对武则天的一般人身攻击,展示了骆宾王的文采和胆略,武则天的欣赏仅体现在“微笑而已”,但后文则抓住了武则天的要害——在先帝尸骨未寒之时就将其子迁于庐陵,这分明是“窃窥神器”,于是打出“匡复庐陵”的旗号,这无疑非常具有号召性,再加上铿锵有力的语言极具煽动性,这反映的不仅仅是文采更是智慧,因而武则天非常赞赏。这都表明武则天的人才理想是文学与政事相结合。
然而在现实中,很多时候有文学才能者未必在政事上表现突出,政事出众者又未必拥有文才。在文学与政事不可兼得时,武则天选择的标准首先倾向了政事才能,而对文学之士亦不废弃,不过任用多限于重要政事之外的活动。
长安中(701-704,狄仁杰于久视元年九月病逝,故《资治通鉴》系之久视元年—700),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杰曰:“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李峤、苏味道足矣。岂文士龌龊,不足与成天下务哉?”后曰:“然。”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才也,用之必尽节于国。”[5]
这里武则天明确赞同狄仁杰所说的文士拘泥小节、不足以辅佐治理天下大事,她期待的是有胆略、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治世人才,李峤、苏味道之类的文词人才已经不能满足政治需要。这都说明她在用人时已不再倾向于倚赖文学人士来理政,而是将政事与文学区别对待。这从另一些细节也可见出:
长寿三年(694,《新唐书·王求礼传》《历代名臣奏议》均谓久视二年701)三月大雪,凤阁侍郎苏味道以为瑞,修表将贺。左拾遗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降雪,此乃灾也,乃诬为瑞,若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乃止。[6]792
则天尝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景俭独曰:“……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渎阴阳也。臣虑陛下布教施令,有亏礼典……”于是再拜谢罪,则天曰:“卿真宰相也。”[2]2912
很明显,在晚年的武则天看来,像苏味道那样出身进士的文词之臣,可以用他们的文采和言论来歌功颂德,娱乐身心,或者营造祥瑞气氛,但在政治上她无疑更钦佩和信赖耿介的吏治人才,并听从他们的建议。
总之,武则天的人才理想可以归结为:文学与政事结合,以政事为本。这样的人才理想,必然会在人才选拔制度——科举中有所体现,换言之,能够体现其人才理想的科目就必然为武则天所重视。
二、 武则天对进士试的重要改革
唐代科举分常科、制举,常科中公认的主干和代表是明经科和进士科。其中明经一科,始终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前后变化不大。而进士科在武则天时期(显庆元年656——神龙元年70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页。神龙元年,武则天退位。还是经历了较大的变革。
调露二年(680)刘思立建言与永隆二年(681)的《条流明经进士诏》(以下简称《条流诏》),向来被认为是武则天时期进士科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刘思立建言,学者一般都注意到以下记载:
至调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1]354
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6]1379
前者谓其建言进士、明经两科并加帖经而不及杂文一事,后者则曰建言进士加试帖经和杂文两项而不及明经科一事,区别甚大。不过无论刘思立的建言是什么,次年《条流诏》的规定是很明确的:
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徵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拣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辨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惟许通六经,进士文理华赡者,竟无甲科。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属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每经帖试,录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日仍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升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恒式。[7]
即明经在试策外加试帖经,进士在试策外加试杂文。至于此时进士试有无经史内容及经史的具体考核方式,众说纷纭,所可确定者,“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1]354;上元元年十二月(674),武则天下诏:
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6]1373
于是上元二年(675)正月敕“明经加试《老子》策二条,进士加试帖三条”[8]。可见,最先在进士试中加入经史内容的不是武则天,而武则天对进士试经史内容的改革是与明经科同时进行的,因而经史内容不是武则天对进士科改革的重心所在。
另一方面,《条流诏》在次年即开耀二年(682)真正推行,若将诏令与有关刘思立建言的记载相联系,则一般认为开耀二年是唐代进士科试杂文的开始。关于“杂文”,徐松的解释是:“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9]70徐晓峰则考证出杂文除徐松所言之箴、铭、论、表、诗、赋外还包括笺、议、颂、檄[10]。又,宋《四明文献集》明确说“唐显庆四年(659)试《关内父老迎驾表》”[11](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亦引《词学指南》云显庆四年试《关内父老迎驾表》《贡士箴》),即在显庆四年就有了明确试杂文的记录,这与开耀二年始试杂文的结论是相矛盾的。陈飞先生也据显庆四年所试表、箴认为,在开耀二年杂文——试策“二项试”制度以前,已经存在实际上的二项试,只不过不经常、不固定,杂文时有时无而已,而诏书的意义在于,将试杂文固定化、制度化*见陈飞《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兼及“三场试”之成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邓小军也认为诏书“只是将由来已久的考杂文定为常规”,参见其《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572页。。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进士科自隋建立至此已有七八十年历史,特别是在唐代,其每一次变化几乎都以相应的诏敕来下达,如前引“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明经加试《老子》策二条,进士加试帖三条”,故在考试试项这一重大问题上,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便时而一项时而两项、或者最高统治者频繁干预增加或减少试项,可能性都不大。如果进士科试杂文“由来已久”,那么多少会引起举子的留心,不至于至此“不辨章句,未涉文词”还是普遍现象。再者,显庆四年至开耀二年之间也不见任何进士科试杂文的记录,很多资料都表明刘思立建言之后才是进士科正式试杂文的开始*如《旧唐书·刘宪传》:“父思立……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请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6页)《旧唐书·杨绾传》也引其上疏:“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旧唐书》卷一一九,第3430页)。所以,显庆四年的试杂文很可能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偶然行为,之后一直到开耀二年几乎再未出现过,以致后来史家将这次偶然的行为忽略不计。
无论是显庆四年还是开耀二年,无论是特例的加试杂文还是制度化的加试杂文,都是在武则天柄政时期。在她的影响下,进士试又经历了其他改革:
(一) 五代王定保:“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 所试皆答策而已……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12]1582即在武则天革命改制(690)前后进士科又停试杂文,直到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后才恢复。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认为此说不确,并引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神道碑铭》为证:“君讳秀……年十五,为崇文生,应举。考功员外郎沈佺期再试《东堂壁画赋》,公援翰立成。沈公骇异之,遂擢高第。”[13]3481又曰《登科记考》列徐秀为长安二年(702)进士,“则可知即使天授(690)前后武则天曾停试杂文,至迟长安二年已恢复。事实上时间应该还要早些”[14]。此说证据不足。从《碑铭》“再试《东堂壁画赋》”的行文来看,应是徐秀应举考完了常规科目之后,沈佺期出于个人爱好对本已看好的徐秀加试一篇赋,目的为验证徐秀的才能、一睹其风采,这很可能仅是临时的个别行为,不是针对所有考生的。如果是恢复试杂文的制度,则杂文是在试策之前的科目,不可能“援翰立成”之后就马上“遂擢高第”。因此,在没有发现进一步证据之前,王定保的说法不宜否定。
(二) 长寿二年(693),“太后自制《臣轨》两篇,令贡举习业,停《老子》”[1]354。
综上,武则天时期对进士科考试的改革有:显庆四年,首次并且临时加试杂文;上元二年在经史考核内容中加入《道德经》;开耀二年明确规定加试杂文;改制前后,停试杂文;长寿二年,明经、进士试都停试《老子》,改考《臣轨》。在这些改革当中,经史内容的改革每次都与明经科同时进行,体现不出对进士科的差别对待,只有加试“杂文”一项是武则天对进士科的最大创新,也是进士科主文词的核心表现,正是加试“杂文”,折射出武则天的人才理想及对进士科的态度。
三、 武则天对进士科的态度
在武则天对进士科态度问题上,陈寅恪先生主张,进士科主文词,“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驱之鹄的”[15]。即武则天重文词、重进士科,于是天下士人竞相考进士一科。而当今不少学者认为,虽然武则天时期进士科录取总人数和年平均人数远远高于太宗时期,但停举的年份多,录取人数起伏也很大,特别是改制之后录取人数较之前有大幅跌落,并且“明经所取人数不仅比进士多,而且在中唐以前,在官位的升迁速度上,有时也并不在进士之下”[16]205。又,高宗、武则天擢拔的宰相当中,明经出身的有十数人,也不能轻易地说重进士而轻明经,特别是狄仁杰、李昭德等重臣均为明经出身,所以武则天并非特重进士一科*详见傅璇琮《武则天与初唐文学》、贾丹丹《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江淮论坛》2009年第2期。。实际上,若结合武则天的人才理想,则会发现其是否重进士科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其中既有程度问题,又有时间问题,不能笼统以“重”或“不重”言之。
前文说过,武则天对进士科的最大创新是加试“杂文”。其实在未加试“杂文”的贞观年间,科举用人已经出现了尚文词的倾向,但时或受到太宗本人的调整和限制,如贞观十八年(644)下诏要求“奇伟必收,浮华勿采”[13]68,时或受到有识之士的刻意扭转,如贞观二十二年(648)王师明之黜张昌龄*当太宗问昌龄被黜原因时,师明曰:“此辈诚有词华, 然其体轻薄, 文章浮艳, 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 恐后生相仿效, 有变陛下风雅。”见《通典》卷一七《选举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2页。,反映了“尚儒”与“尚文”两种思想的矛盾和较量。而至“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2]4942的武则天时期,整个文化环境已由儒学化转变成文学化,即便没有加试“杂文”,作为决定去留最重要因素的对策,其衡量标准也主要是词华而非其内容。如刘希夷上元二年(675)中进士,《唐才子传》谓其“射策有文名”*辛文房撰、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4页。这也说明当年定无杂文试项,否则不会以“策”来证其文名。,文词水平直接成了公认的对策优势,而完全不顾及其反映的政治见解。《条流诏》对进士科最大的不满也是那些凑足人数之进士的“不循史传”“不辨章句,未涉文词”,也没有言及对策中的识见问题。不过,虽然《条流诏》针对举子现状强调了文词,但它并没有废弃政治识见,其对人才的最高期许仍然是“文理华赡”,即文词和政治识见并重。然而实际操作中重文词表现往往会影响到政治识见的表达,以政治识见为首就难以顾及文词水平,以致满足“文丽华赡”者“竟无甲科”*对此,通常理解为“文理华赡”者不能录取到甲科,而只能录取到乙科(如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实际上,据《通典》, “按令文……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杜佑《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也就是进士无甲科,一般说的“登甲科”只是及第的美称而已,“竟无甲科”不是说没有录取到最高等次,而是没有及第。,即及第者中无人做到“文理华赡”。其根源在于单纯的试策很难做到人尽其才,举子们或像刘希夷一样专攻文才,或像《条流诏》中所举虽凭政治识见及第却“不辨章句”。在这样的背景下,诏令加试“杂文”,则能让“杂文”承担对文词才能的考核,让对策承担对政治识见的考查*并非如普遍认为的只为提高应试者的文词水平,因为是加试杂文,而非改试杂文,试策仍然是不能忽视和代替的,此时还没有出现后来的“以诗赎策”的情况。,其初衷正是为了在文学和政事间寻找平衡。
杂文中包括赋的最早记录是垂拱元年(685)*傅璇琮先生据颜真卿所作《颜元孙神道碑》发现,垂拱元年登进士第的颜元孙所试杂文两首是铭和赋。《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页。,包括诗的最早记录是垂拱二年(686)*陈铁民先生据梁屿墓志考证出其在垂拱二年(686)首次应进士科考试,当年所试杂文题为《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见《梁屿墓志与唐进士科试杂文》,《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断梁屿当时参加的是制举试,不能据此认为当年进士科已试诗。或更晚,天宝之前杂文并非专以诗赋,不能说完全开始了“诗赋取士”。但杂文的文学因素被大大突出了,评价杂文的唯一标准即其文学性,如《颜元孙神道碑》:“考功郎刘奇乃先标榜君曰:‘铭赋二首,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词高理赡。’”[13]3457这“丽且新”即主要是对语言的要求。这样就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在进士科以文词之美取人,不用再像太宗时代那样既爱好华美文词又担心有舍本逐末之嫌,毕竟试策的初衷本是为了咨询时政——“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文心雕龙·议对》),以文词来选策,总是名实不符。另一方面,她又试图让试策回归到最初咨询时政的功能,所以对对策的衡量标准自然少不了“理赡”,即政治识见的表达言之有物、言而有理。并且她于对策抱有较高的期待,希望有补于时事,如光宅二年(685)在策进士第一道问后即曰:“伫闻良算,明言政要,朕将亲览。”[9]78最终吴师道等27人及第,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12]1582可见对试策的重视。因而加试了杂文的进士科实际上反映了武则天文学和政事兼重的最高人才理想,武则天当时对进士科是寄予厚望的。
武则天时期贡士停举集中的时间是咸亨二年、三年(671-672)、仪凤元年、二年、三年、调露元年(676-679),这都在颁布《条流诏》的永隆二年(681)之前,自颁布之始到载初元年(690)称帝期间从未停举,这更可见出对新规下的进士科满怀期待。但事与愿违,尽管武则天想通过加试杂文选拔文学政事相结合的人才,可杂文是试策之前的试项,又每场定去留,必须通过杂文考试才能进入到下一环节,因而文词水平成为举子的首要用功之处,进士科选拔的仍多是偏于文学而疏于政治识见的人才。光宅二年(685)对吴师道等人对策的敕批就多少折射出武则天的一丝失望。“循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由于革命改制,进士科的考试科目恢复到《条流诏》颁发之前,停试杂文。即便如此,天授中(690-692)薛谦光上疏论举人之弊时仍谓:
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今之举人,有乖事实……只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归,以此收人,恐乖事实……伏愿陛下降明诏,颁峻科……断浮虚之饰辞,取实用之良策。[2]3138-3140
很明显,即便取消了杂文,举子们在对策中还是习惯性地多在辞采上下功夫,此时不用再担心“不辨章句,未涉文词”,而是为只追求“文擅清奇”而忧虑,试策不能很好地起到咨询时政的效果。所以,改制前后进士科停试杂文,或许就是出于武则天“断浮虚之饰辞”的预见,只不过结果却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取到“实用之良策”,进士科吸引的仍旧是文词之士(这才有了薛谦光的上疏),于是录取人数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在长寿三年(694)又出现停举,其根源正在于进士科不能满足武则天当时首要的人才需求,她对进士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在改制前后还发生了几件事关举人的大事。一是之前重用的“北门学士”在改制前夕被一一流放和诛杀,这或可预示武则天将要调整之前的用人政策,最起码是需要起用一批新型人才来助其共理大周。二是武则天扩大了制举规模,并亲自临试。永昌元年(689),诏称:“宜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13]990,并在制举策问后属明“朕将亲览”,以示特别重视。《大唐新语》卷八亦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17]制举与常科善选拔一般的案牍人才相比,更能选拔那些有胆识有才华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特别是那些可以应付复杂局面的人才,并且可以立即授官。在常科与制举的天平上,武则天更加倾向了制举。三为开试官之制。《资治通鉴》载:
(天授三年692)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18]
即对存抚使所举之人不加测试和淘汰,一并试用为官,视其在职表现再定去留。这与常科及制举以言取士不同,而是以政治实绩取人,重吏干之才;也与通过科举考试、守选若干年月再等待吏部授官的常科入仕渠道不同,而是大大缩短了人才从被选拔到被任用的周期,是武则天的一大创举,与其大开制举一样,反映了其在革命初期欲“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同时也体现了其为守天下而求吏干之才的迫切心情。至此,她已不需要许敬宗那样满腹文采的文士来帮助自己打击政敌,因为她已经能够调动一切她愿意调动的力量(譬如酷吏)来打击反对派;也不需要“北门学士”那样以文学为掩护来分“宰相之权”、扩大和巩固自己地位的政客,因为她已大权在握,并起用武氏子弟来强化政权,李唐宗室至此殆尽。此时,她急需的是能使大周长治久安的吏治人才。事实亦是如此,改制后武则天最倚重的正是狄仁杰、李昭德、徐有功等耿介的吏干人才,即便是进士出身的娄师德,其受到重用不是因为他“颇有学涉”,而在于“兼怀武略”[2]2975。在文词之才和吏干之才之间,武则天选择了后者。
一切都在表明,武则天革命之后,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以最快的速度来发现、选拔、任用吏干人才,以期在垂暮之年尽早呈现大周盛世。她对仍以文词为主的进士科的政治期待,显然已经大不如前。但这并不代表她对文词人才已经完全弃之不用,而是一方面利用他们来娱乐身心,一方面通过笼络他们来引领舆论,在一些大型的礼仪场合,也总是少不了文学之士的献诗献赋和应制之作。如明堂建成时,刘允济有《明堂赋》;拜洛受图时,李峤、苏味道、牛凤及有《奉和受图温洛应制》,陈子昂有《为程处弼应拜洛表》;武则天登帝位时,李峤、陈子昂有《皇帝上礼抚事抒怀》;天枢造成时,武三思为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记,李峤《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僚应制》冠绝当时;嵩山封禅,宋之问有《扈从登封途中作》《扈从登封告成颂》《扈从登封告成颂应制》……这些诗文都渲染和强化了明君形象和盛世氛围。此时武则天已经不需要文学之士过多地发挥他们并不是很擅长的理政之才,而是让他们回归到以文词侍君的地位。圣历二年(699)她成立控鹤府,后又将其改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几乎集结了当时宫廷所有的一流文学之士,让他们做的却常常是“嘲戏公卿以为笑乐”[2]2706,后为掩人耳目又令其修《三教珠英》,但他们“日夕谈论,赋诗聚会”[2]3175,亦可见他们当时一般公务清闲,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也确实无甚建树。
总之,武则天晚年已将政事主要委托给值得信赖的吏治人才,并通过制举、试官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明经科来加强对各级吏干人才的选拔,而那些进士出身的文士则多从事与文化创造相关的工作,他们已不再是武则天政事上倚赖的重心。
应该说,高宗朝前期大幅扩大进士科录取规模,可能出于新帝即位之初笼络天下人心的初衷[16]207,并非出于对进士科的自觉选择,因而皇权巩固后就多次出现停举的情况。但随着武则天的柄政,对许敬宗、李义府、“北门学士”等人的使用经历,使她对文学和政事相结合的人才十分青睐和渴求,于是在本重文词的进士科进一步加试杂文,让杂文和对策分别承担对文学和政治识见的考核,且每年开考,期待选拔出文学与政事并重的人才,这是她对进士科的自觉倚重。但事与愿违,进士科吸引的仍多为文词之士,即便是对策中也常充满了“浮虚之饰词”而少“实用之良策”,很难发现理想的人才。到改制前夕,武则天根据形势需要大力调整用人策略,在文学与政事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将用人的重心倾向了政事,于是一方面在进士科停试杂文,以期通过“断浮虚之饰词”来更好地发现“实用之良策”,无奈仍然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借制举、试官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明经科来选拔吏治人才,对吏治人才委以重任,进士科已非其选拔政治人才的重心,故录取人数大幅下降,甚至再度停举。当然,武则天对进士出身的文学之士仍十分欣赏,只是不重用,而是基本停留在任其发挥文学才华的层面上,或让其纪述盛典、讴歌盛世、颂扬圣德,或让其侍奉酒宴、诗曲娱乐、游赏赛诗。
在武则天与进士科的关系上,简单地说“重”或“不重”都是不够准确的,而是不同时期对进士科有不同期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时人渐重进士一科。故有薛元超的“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19]、王定保的“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12]1578-1579的说法。但这皆非出于统治者的倾斜和举子个人升迁的考虑(因为薛元超说此话时已经贵为宰相,其他缙绅们也已“位极人臣”),而很可能是出于贵难贱易的社会心理。《封氏闻见记》载:
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20]32
(进士)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徵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20]34
《通典》:
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1]357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对进士的认可度自然要高于明经。
[ 1 ] 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2 ]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 彭定求.全唐诗(卷二一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2307.
[ 4 ]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58.
[ 5 ]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23.
[ 6 ]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7 ]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六)[M].洪丕谟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549.
[ 8 ]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7388.
[ 9 ] 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0.
[11] 王应麟.四明文献集[M].民国四明丛书本.
[12] 辛文房.唐摭言[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3]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 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93.
[1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02.
[16] 傅璇琮.武则天与初唐文学[M]∥唐宋文史论丛及其它.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17] 刘肃.大唐新语(卷八)[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90.
[1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6477-6478.
[19] 刘餗.隋唐嘉话(中)[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3-104.
[20] 封演. 封氏闻见记[M].张耕,注评.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