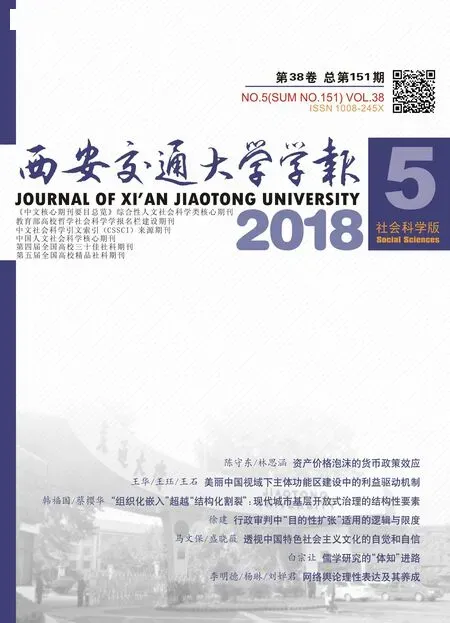中国当代诗篇中的“长安”书写
——以“半坡”和“大雁塔”为中心
张英芳
(1.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433;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文系,陕西西安710054)
长安,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空间”的中心,文人墨客从多个视角对其进行着“历史激情”和“文化想象”的书写*代表性的诗作如《秋兴八首》《帝京篇》《谒大慈恩寺》《登科后》《长安古意》《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丽人行》《长恨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慈恩寺塔》《菩萨蛮》等。。当代诗歌中,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书写长安的诗篇并不是很多*代表性的作品如冯至的《登大雁塔》《半坡村》等。。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抒情诗的热浪逐渐退却,朦胧诗继之崛起,但是,“令人气闷的朦胧”[1]并没有为中国新时期的诗歌发展提供持久的理论资源和现实动力,因此,诗歌何去何从成为80年代乃至当代文学前行的一个重要问题。带有历史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的是,1983年围绕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从诗歌内部到文学的外部发生了一场“震颤式”的有关诗歌美学观念的争论。与此同时并在此之后,中国当代诗坛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如海子、杨炼、韩东、于坚、李小雨、浪波、侯马等。相继以“长安”这个地理空间为坐标,围绕“大雁塔”和“半坡”,创作了一系列与“长安”有关的诗歌*代表性的作品有《大雁塔》(杨炼,两百多行,组诗,1983)、《半坡》(杨炼,组诗,1983)、《有关大雁塔》(韩东,1983)、《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海子,1985)、《大地上》(韩东,1988)、《半坡的雨季》(韩东,遗失,1985)、《半坡》(李小雨,1985)、《又见长安》(浪波,1983)、《望长安》(侯马,1990)、《大雁塔》(南人,2002)、《长安行》(于坚,组诗,2003)、《大雁塔》(李聿子,2007)、《长安》(孤雪,组诗,2009)《百度大雁塔》(雨荷风,2015)等。。从这些围绕长安的诗篇的意象、主旨和精神气质来看,其内部之声与当代诗潮和鸣之时,又有着鲜明的“自我的声音”。由此,以“大雁塔”和“半坡”为中心的“长安”书写诱发了有关中国当代诗歌从观念、实践到范式的诸多争论。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围绕“长安”书写的典型文本进行分析,在追问“长安”这个历史实体和精神空间的“诗意”象征中,再一次呈现中国当代诗歌的嬗变轨迹和美学追求。
一、由“大雁塔”诱发的论战:从历史的“赋形”“变形”到个体的“实感”体验
对当代诗歌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变奏”是一曲多声部的交响乐。与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80年代的诗歌写作既在省醒“历史”中不断与“过去”发生着断裂,又在断裂中寻求着与“历史”新的连接点,试图在“断裂”与“黏连”中实现新的突破。1985—1986年新时期的诗歌发展就是在这种“断裂”和“延续”中探索着新的美学观念,因此可以说,80年代中国诗歌“走过的路”,其实是多种问题的交织和多元观念的交汇,这种“复杂”而并不明晰的多元背景为诗歌寻求各种可能性的“实验”提供了契机。基于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答案的急切冲动,“长安”这个富有多重意味的“地理空间”再一次浮出地表,成为80年代诗歌理论论争的一个起点和“焦点”。
80年代初期,在有关朦胧诗潮的争论尚未平息的间隙,“被命名”为朦胧诗人的杨炼*朦胧诗潮起的时候,杨炼作为群体中的一个诗人也被命名为朦胧诗人,但是杨炼本人并不认可这种带有时代印记的泛指的命名。在1983—1988年间相继写下了《大雁塔》《半坡》《诺日朗》《敦煌》《西藏》等具有“史诗”意味的大型组诗,其中,《诺日朗》在发表之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回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诺日朗》的被认可不同,几乎同时同步发表的《大雁塔》,却引发了诗坛内外一场“地震波”。缘由大概在于《大雁塔》是“历史的物”,而《诺日朗》是“自然的物”。1983年,《大雁塔》发表后不久,当时在诗坛还处于相对“无名”状态的韩东,发表了《有关大雁塔》,这两首诗的客体虽然都是大雁塔,但是由于历史态度的分歧,从语言、情感、观念到审美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质地和表征。之后,围绕着这两首诗争论的“晕波”,1985—1986年在诗坛乃至文坛开启了一场影响较大且意义深远的有关“诗歌美学观念”的论争*1986年,《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100多位诗人,60多种“诗派”,有关朦胧诗派与第三代诗群的分化在此形成一个界标,各种各样的流派通过各种渠道宣传着各自的文学主张。。
《大雁塔》与《有关大雁塔》的交锋,既交织着“诗歌写作观念”的冲突,同时又是以《今天》为代表的“第二代诗群”与以《他们》为代表的“第三代诗群”的一次公开对峙。从表面来看,他们之间的分野和分歧是语言的“隐”与“显”,“朦胧”与“直白”的区别,但是内在的分歧还是关于对待“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态度的分歧。在这场论争中,最大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子其实源于“大雁塔”这个历史的遗物和面对历史遗物的“历史态度”,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对此,杨炼认为:“这一代人的思想和写作,曾经被我概括为‘噩梦的灵感’:从‘文革’的现实,向历史幽暗的深处追问,再进一步反思(注意:从来不是浮泛煽情的‘寻根’!)埋藏在每个人深处的传统思维方式,直到再次触摸中文 ——那作为苦难和力量的源头。”[2]12-13对于“大雁塔”这个物以及据此物写作的《大雁塔》,杨炼的态度是在对“历史物”的追问、反思中,寻找与历史新的连接点,从而为历史“赋形”。因此在《大雁塔》中,杨炼赋予了“大雁塔”历史的激情,从“位置”“遥远的童话”“痛苦”“民族的悲剧”“思想者”五个层次展开对“历史”深层次的追问:“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象一个人那样站立着/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地一动不动/墓碑似地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生于60年代的韩东(杨炼生于1955,韩东生于1961)则不同,1983年韩东创作《有关大雁塔》的时候22岁,彼时对于宏大的厚重历史的态度相对较“轻”,对历史而言,他更注重个体的“重”——强调个体的实感“体验”:“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在韩东的历史体验中,宏大的历史作为一种压抑和留有巨大阴影的“物”,对个体形成了一种遮蔽,因此在他的诗歌中表现的态度是在逃亡中积极地“对抗”:“我们爬上去,然后再下来”。韩东的这种对历史的逃亡、叛逆和对抗的姿态,构成了对于历史的一种“变形”和“消解”。之后,以韩东、朱文为代表的第三代诗群又发起了一份以“断裂”为中心的诗歌调查报告*1998年,朱文发起了“断裂:一份问卷和56份答卷”的挑战,宣告与现存的文学秩序决裂。见《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通过与“历史”的断裂来彰显第三代诗群的“民间化”“个人化”“日常化”立场。但是别有意味的是,无处不在又无法逃逸的历史关联性不断地为第三代诗群“逃离历史的企图”设置“障碍”,因此在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中,他的野心是“颠覆”历史,但实质上在《有关大雁塔》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的变形”,而非“颠覆”。
《有关大雁塔》之后,1984年韩东又创作了《你见过大海》,在这首诗中,个体的“实感”经验被再次放大,成为诗歌表现的“中心”:“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过了大海/并想象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你想象过大海/你见过大海/也许你还喜欢大海/顶多是这样/你见过大海/你也想象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就是这样,顶多是这样,人人都这样”,这种消极的“对抗”,无论是面对巨大的历史物——大雁塔,还是巨大的自然物——大海,他的叙述都显得“平静”而“无所谓”,呈现出与宏大的事物包括历史的“间离”感。因此,在1985—1986年诗坛激烈的论争之后,就形成了以《今天》和《他们》各自为中心的诗歌群体以及两种不同的诗歌写作观念:“官方与民间日常”“政治与个人”“诗意化与口语化”。这种诗歌观念的“紧张”和“冲突”直到90年代才有所松弛。
当我们以“大雁塔”为透视点在回顾80年代以及90年代诗坛的“来时路”时,有关诗歌写作的“大”与“小”、“轻”与“重”的探讨是核心。那么在“政治·历史·个体”“官方·民间·日常”中孰为核心?孰为“大”?孰为“重”呢?我们还需继续回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50与60年代去寻找“线索”。从历史时序来看,80年代围绕“大雁塔”引发的论争,是诗歌“革命”“反抗”的使然,但是这场“诗歌革命”的前奏是什么?内在的动因是什么?1949年11月,胡风创作了具有“史诗”性质的“政治礼赞诗”——《时间开始了》,在这首诗中,“北京”被作为一个空间的“中心”,对应着一种“政治的想象”和“浪漫的抒情”。之后,围绕着“政治抒情”的礼赞诗成为诗坛的主流,20年后,1968年食指创作了同样以“北京”为想象中心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指向还是北京,但是诗歌的“情绪”却悄然发生着变化。《时间开始了》是激荡式的:从“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到“又一个欢乐颂”,以5个乐篇,长达4 600行的“史诗”书写着对政治的热情和赞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却是迷惘式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以这两首诗为代表,“北京”作为一个隐喻,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时间起点上承担着“政治的抒情”与“抽象的想象”。继之而起的“文革”,更多是空白。到了80年代之后,文化、文学都在剧烈地“反弹”,企图超越政治的狭隘和抽象抒情的虚伪,既能寻找到历史的“根基”,又能寻找到现实的依托。在这样的际遇之下,被考古的“长安”在80年代的诗坛引发热烈的交谈和论争其实是一种必然。因此,1983年那场《大雁塔》和《有关大雁塔》的论争在80年代成为一个话题的中心,似乎是两代诗群的美学观念的争论,但是其缘由和影响却绝不止于此。“长安”回归到书写的视野并且被放大和凸显,暗喻着中国文学文化有关历史传统、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的内在冲突与平衡选择,这场论争的背后其实是有关中国文化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观念的一次交锋,而在“大雁塔”引发的这场论争之外,围绕“长安”的另一个“历史的遗迹”——半坡,在80年代中期同样成为诗歌书写关注的焦点。
二、更远古的“半坡”神话:原初的历史、大地及现实日常
当代诗人对长安的“历史”认同或者“消解”,肇始于辉煌的“历史遗迹”——大雁塔,却不止于此,要更深刻地“理解”和“领悟”历史,还需要到历史的“更深处”去,到那些纯粹的“历史物”中去理解“传统”与“现代”,甚至“前传统”与“后现代”。因此,在对“大雁塔”书写的同时,诗人们还将目光投射到指代“长安”历史的更深处,人类文明的源头——“半坡”,试图挖掘更多有关“长安”的原初形态和原始意义。在《大雁塔》中,杨炼将其比喻为“遥远的童话”,在《半坡》中,杨炼则直接从“神话”开始,对远古“半坡”的“人类之谜”进行探索,杨炼选择了代表“半坡”的几个物象:石斧、陶罐、火、太阳、光等这些原始的“自然之物”来叩问,倾听历史的“回声”。杨炼在一次采访中回答了他书写“半坡”的缘由:“所谓朦胧诗人之中我可能是唯一一位诗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中国历史层次在现实和生活中间的存在,我的自选集中第一部作品是《半坡》,西安的半坡,这个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期遗址,那是一部总诗,由六首长诗组成,这样一种古远的历史文化怎么和当今的生活相衔接,怎么样能够在当代生活里活生生的存在?它和我在开始的写作状态有关,我插队的三年,学会最基本的感受是人和大地之间这种既爱又恨的纠结,爱来自于祖祖辈辈对大地的依附,像对母亲的依附一样,但是其中也有恨,因为祖祖辈辈被锁定在大地上,犹如囚徒一般。我关注历史,关注六千年前半坡人,在他们小村子里通过他们的墓地,穹庐,小屋子,祭司,通过神话片段等等所感受生存处境,和插队时的感受是完全贯通的。所以,从一开始,历史对我来说就不是另外的东西,不是在我之外的东西,历史始终在我之内,我的每一首诗都在进行我当下人生的考古学,要掰开我自己呼吸的每一秒钟看到屈原,看到杜甫,听到曹雪芹,听到兰陵笑笑生,听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但是这些都发生在2014年,所以这样的历史感,我认为是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家、文化人或者一个普通人必须拥有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财富。”[3]杨炼将“半坡”作为“神话”,更多地则赋予其“大地”的意义。那么韩东呢?在韩东的诗歌中,“半坡”是什么样的存在?
与对“大雁塔”的消解不同,韩东在1983、1984年《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的写作之后,于1986年写下了《半坡的雨季》*此处的《半坡的雨季》不是《半坡的雨》,《半坡的雨》中的“半坡”指的是南京的“半坡酒吧”,《半坡的雨季》指的是长安东郊的“半坡”,韩东在2002—2008年间写下了《半坡即景》5首,《半坡即景》的“半坡”指代的都是南京的“半坡酒吧”。,遗憾的是这首以“半坡”为对象的诗后来遗失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2003年,时隔近20年后,此时的韩东不再年少,是一个典型的“中年人”,而且此时也不太写诗,更多地转向小说创作。在接受楚尘文化记者专访的时候,他说道:“1982年,大学毕业分到西安,最想去的地方不是碑林、大雁塔,甚至也不是兵马俑和华清池,而是半坡古人类遗址。往那儿一站,当真有宾至如归之感。复原的房舍泥墙草顶,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家下放的那个村子。我觉得此番感动和我早年的生活有关,其实并不尽然。访问半坡以后,我写了一首叫《半坡的雨季》的诗,可惜已经遗失,只记住了这个名字。幸好1988年,我又写了这首《大地上》,算是了却了一个情结”[4]。不知道韩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意指什么?他的“情结”又具体指什么?这些都无从考证了。但是明显的是自《有关大雁塔》的写作过去22年之后的2015年,他又重提了“长安”,还提到了他有幸留存的有关半坡的诗《大地上》:“大地上/只有两个人的时代/或者稍后大地上的人类/仍然稀疏/生长在山谷间/而让另一些山谷空着……那时候的每一根光线都不弯曲/牵动下巴/使我们向往天上的事物/离战争还有一万年末日还有两万年/我在大地上行走/跟着牛不超前”。从1982年到1984年,韩东在“长安”生活工作了两年,1983年创作《半坡的雨季》遗失,1984年底1985年初回到“故乡”南京,成立《他们》文学社,倡导“日常化”“口语化”写作,1988年离开“长安”四年后写下与半坡有关的诗《大地上》,2015年在离开“长安”20年后,他又重提了“长安”,以“大地”为“半坡”命名,而且“那时候的每一根光线都不弯曲”“使我们向往天上的事物”,此时的“长安”在韩东的笔下更多的是一种“本源性的历史”,因此,“叛逆”的韩东在1988年写到“半坡”的时候,却是无限“温柔”,对“半坡”保持着最天然的致敬。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清晰而直白地触摸到了作为第三代诗群代表的韩东对待历史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再一次验证了30年前的《有关大雁塔》并非是简单地“反历史”或者“虚无历史”,恰恰证明了在《有关大雁塔》中他对于历史的“变形”,即在宏大的历史中必须包含个体的历史的真实体验,历史的历史和个体的历史融为一体,历史才会富有意义。更有意思的是,《大地上》这首诗和杨炼的《半坡》以及杨炼在采访中提及的“半坡”之于“大地”的意义一样,韩东同样认可赋予“半坡”以坚实的“大地”的意义,在《大地上》这首诗中,韩东对杨炼《大雁塔》的那份“消解”消失了,对历史和文明他也保持了敬意。韩东与杨炼对待“半坡”的“同一”,似乎传达了他们对“原本性”文化的崇高敬意。与这种敬意相同的,还有李小雨写于1985年的“半坡”系列。以《陶罐——半坡之一》这首诗为例:“我披发的母亲/裹着兽皮的母亲啊/她指向/最纯粹的泥土、水和火焰/世界就这样诞生/诞生成一个有孕的曲线/一个婴儿在腹内蠕动/一枚果实正在成熟……”,在这里李小雨赋予“半坡”母亲、泥土的意义与韩东、杨炼赋予半坡“大地”的意义是相通的。
如果说杨炼、韩东、李小雨等诗人对“半坡”的“大地”“母亲”的认同,是对人类更原始的历史认同的话,中国当代诗坛另一位重要的诗人——海子,在他的“半坡”影像中,却呈现出一些“别样”。1985年,也就是《大雁塔》和《有关大雁塔》争论不休,诗坛处在“众生喧哗”的那年,中国当代诗坛另一个重要的诗人海子,在他第一次“西行”*海子有过两次西行,第一次是1986年,第二次是1988年,在正式的文章中海子对自己的西行都没有直接表述,但是通过《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敦煌》《日记》《西藏》等诗篇,可以追踪到他的“西行”踪迹。途中默默地经过长安,但是他没有写“大雁塔”,而是躲在西安东郊的“半坡”,以“吊半坡”的方式回到了“现实日常”。在《吊半坡并给擅入都市的农民》中,诗歌以“吊”起笔:“我/径直走入/潮湿的泥土/堆起小小的农民——对粮食的嘴/停留在西安/多少都城的外围/多少次擅入都市/象水、血和酒——这些农夫的车辆/运送着河流、生命和欲望……父亲是死在西安的血/父亲是粮食/和丑陋的酿造者/一对粮食的嘴/唱歌的嘴、食盐的嘴、填充河岸的嘴/朝着无穷的半坡/粘土守着粘土之上小小的陶器作坊/一条肤浅而粗暴的/沟外站着文明/瓮内的白骨飞走了那些美丽少女/半坡啊——再说——受孕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果实/实在需要死亡的配合”。在这首诗中,海子突出了“泥土”,潮湿的泥土,“泥土、大地、神话”这些在杨炼、海子、李小雨笔下的东西与海子笔下所要表达的那个“历史”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在海子这里,他提出了“父亲”,“父亲”的血,这点与李小雨笔下的“母亲”不同,他在“父亲是死在西安的血”“这些农夫的车辆运送着河流、生命和欲望”中从历史回到了“现实日常”,并在回到“现实日常”中又远眺到“受孕”,回到“生命的起源”。《吊半坡》之后,海子继续西行,到达了敦煌、青海湖和西藏,并写下了《祖国(或以梦为马)》《敦煌》《九月》《日记》《怅望祁连(之一)(之二)》《西藏》等诗篇。追溯海子的西行踪迹,无论在“长安”还是“敦煌”,他往返穿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替中,在历史中为现实写着“寓言”。但为何在对“长安”的书写中,海子没有写“大雁塔”,而是选择作为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半坡”,且以“吊”这种悼念的方式来写呢?他在这首诗中究竟要传达什么?在海子的“诗学”观念中,既有中国传统的魅影,又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因而在海子的诗歌中,更能直接地触摸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因此在透视吊半坡这首诗的时候,海子不断地提及了“血”“父亲的死亡”“受孕”,通过这些意象来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1985年,在那个注定喧嚣与迷茫并存的时代,杨炼、韩东、海子、李小雨等诗人在重返“半坡”的诗歌写作中,对“传统”与“现代”的纠缠,以“母亲”“父亲”“大地”“受孕”“陶罐”“火”“光”等“物”赋予“半坡”以“历史”与“现实”意义,试图联接“历史”与“现实”的通道,并在返回“历史”之途中为迷茫的“诗歌”寻找一条“现实”出路。这一点其实与《大雁塔》的争论“异曲同工”,由此以“大雁塔”和“半坡”为指代的有关“长安”书写之于诗歌审美观念、写作实践的意义更加明晰:“长安”作为历史之物和现实之象征,对于诗歌如何面对内在的写作动力——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平衡传统与现代在现实中的表述,其影响绝不止于80与90年代,直到当下,这种影响还一直在,且未停息。
三、重塑:“人类的集体回忆”与对长安的“精神赋形”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价值观念指向“实用性”和“功利性”,“文学失落”“诗歌失落”已然成为一种显在的事实,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诗群的分化、流派的散失与重回“史诗”的激情在衰减中时时又有“波浪”涌动。2002年8月6日,第三代诗群的代表人物于坚在《诗江湖》发表了组诗《长安行》,再次以《大雁塔》《半坡》等“地理空间”为标的,表达着新的“历史迷情”:“大雁塔/在长安/天气就是紫气/鱼贯而入、买了票/我们钻进雁塔/要看看大唐朝的肚子里/凌空高蹈的都是什么……千年过去了/不动/尊重/上窜下跳之后/空虚/……收起乖戾的羽毛/我跟着古代的老百姓/跟着皇帝/跟着僧人和使者/跟着李白/跟着长安/默默地跪下来”。在“默默地跪下来”中,那个曾经对历史“不屑一顾”的于坚在对历史的敬畏中,返回了“传统”。那个写作《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还原生活“粗糙真相”的于坚,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发生了这样的写作转向呢?更进一步地,这只是于坚个体的写作调整,还是一种整体转向的风向标呢?
关于《长安行》组诗的写作缘起,或者说写作情境,于坚在《致伊沙》中表白道:“今年7月27日,我第三次来到西安,我终于看到了长安,我是有福之人啊,我不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外祖母是一个文盲而知道敬畏李白的人。”[5]于坚在承认“我不是喝狼奶中长大”中确认了自身生命的来源。也许这是他在20年间对历史“温故知新”之后的“自我历史意识的觉醒”吧。但是意外的是,直到2007年,他的知己“伊沙”,看到于坚的诗并在于坚的解释中却“有点出离愤怒”,缘由就在于那个写作《车过黄河》的伊沙认为于坚是个“叛徒”,背叛了他们共同的写作信仰,认为于坚是“伪民间”,背弃民间就是向作协体制的妥协,向“人民大会堂”进发*见长安伊沙的博客《沈浩波、伊沙与于坚的决裂经过》,原文最初发表于2007年6月7日的《诗江湖》,在博客中伊沙对这场“口水”战有详细的描述。。
在于坚和伊沙等人的争论开始之后,作为一个“时代和诗歌的话题”,更多的诗人加入到对于坚的“讨伐”和“声援”中来。这些“讨伐”者大多来自于曾经与于坚并肩的“内部群体”,而这些“声援”者多来自于批评界。为此,在这些“事端”和争论“白热化”之时,《作家》杂志社在2002年第10期推出了围绕《长安行》的讨论,讨论的中心不外乎三类问题:于坚为何会“叛变”?于坚叛变了什么?于坚的叛变对未来诗歌的发展有何寓意?先看看“内部”的争论:按照伊沙、沈浩波等人的看法,于坚回归传统是向“体制”的妥协和投降,失去了其“先锋性”,但是也有的诗人认为,“《长安行》曾在网上引来轩然大波,我要说这是最具于坚魅力的诗篇,是……自然之诗、历史之诗、生命之诗完美结合”[6]。诗歌评论家姜耕玉对于坚的“变化”则认为:“与其说于坚的《大雁塔》及《长安行》是对韩东《大雁塔》的背反,不如说是‘反叛’20年诗歌过程(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必然或归宿,是第三代诗歌20年的叛离与回归的实现,具有世纪之交诗歌的终结与开始的意味。”[7]
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场争论,韩东以及韩东所代表的“第三代诗群”在1985年崛起之后,诗歌的日常化、民间化写作形成此后十余年来诗歌发展的主潮。于坚在《长安行》之后,在各种质疑和争议中,于2003年获得南方都市报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授奖词如下:“他在2002年度发表的一系列新作,有着诗人性情的天真流露,并将接续传统的情怀和风尘仆仆的个人魅力结合得完美无缺,他的语言,也因挣脱了底层的土气而获得真正的诗性光辉。于坚的写作提醒我们,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6]“接续传统的情怀”大概是于坚写作《长安行》最为直接和核心的缘由吧,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接续传统”的努力在对“自我”颠覆的挑战中使得诗歌重回“庄严”,这是他《长安行》最大的贡献,也因此,于坚再次获得了“新的认同”。一个有勇气的诗人,敢于对过去的写作“矫枉过正”,重新面对历史,这种“自我修正”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风平之后,回眸这场论争,源头就在于《长安行》向历史的回归和敬畏引发了“第三代诗群”中某些诗人的愤怒,而且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无法避免的争论,就像80年代《大雁塔》和《有关大雁塔》的那场围绕“历史”与“反历史”的争论一样,《长安行》既是80年代那场论争的延续,更是经过时间的洗涤之后深深的反思,这场反思从回到过去开始,面向的却是中国诗歌的未来。
《长安行》之后,2011年于坚继续追随历史的“遗物”,抵达了敦煌,并写下了散文《圣敦煌记》:敦煌是历史,但是为什么当代人潮水般地涌去?这种历史不是书本上少数人的历史,而是活着的大众的历史。这是神性使然。大多数历史缺乏神性,仅仅是解释。但敦煌不仅仅是历史,它是神性的载体,神性是无法被历史化的,它会隐匿,某些时代它不在场,但无法被历史化。敦煌曾经被流沙吞没,但只要一旦重见天日,就依然神性熠熠,因为它已经神灵附体[8]。在《圣敦煌记》中,于坚对敦煌的膜拜与对“长安”的“默默地跪下来”是一致的,通过《圣敦煌记》,可以再次确认于坚对“长安”的“朝圣”的那种历史的迷情是真实的、真切的,叛变的“于坚”重新确认了那个宏大的历史的存在。在时间的廊道回转中,于坚把被韩东“变形”的《大雁塔》重新归到“历史”的“庄严和肃穆”,并在这种返回中为历史进行“精神赋形”。
2009年经过长安的诗人孤雪同样写下了《长安》组诗,在《空》中诗人写道:“进入之前/先要掏空自己/做一名长安门徒”。之后,还有更多的“门徒”抵达“长安”,在诗歌中叩问“历史”,有类似《大雁塔》,也有类似《百度大雁塔》的,但更多是致敬,在诗歌中赋予“长安”以庄重严肃的历史价值。在这种“赋形”中,时光在退却中似乎又回到了1982年。1982年杨炼在《传统与我们》一文中强调:“传统,一个永远的现在时,忽视它就等于忽视我们自己;发掘其‘内在因素’并使之融合于我们的诗,以我们的创造来丰富传统,从而让诗本身体现出诗的感情和威力;这应成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我们占有得越多,对自身创新的使命认识得越清晰,争夺的‘历史空间’也越大。”而为此需要思考、实践的则包括“必须进行新的综合”、必须进行“重新发现”,使我们的诗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9]153。20世纪80年代至当下,在对书写“长安”诗篇的透视和聚焦中,中国当代诗歌要走过的路在《传统与我们》中就已经被预言。也如评论家所言:诗歌“西安”,最古老也最现代。我们走得再远,背后仍是“长安”[7]。此处的“长安”,更多指代传统和历史。海子在自己的诗学理论著作《诗学:一份提纲》第四章“伟大的诗歌”中,给予了人类的一些历史地标最高的敬意:“在诗歌王子与诗歌之王之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创造性诗歌——这是一种诗歌总集性质的东西——与其称之为伟大的诗歌,不如称之为伟大的人类精神——这是人类形象中迄今为止的最高成就。他们作为一些精神的内容(而不是材料)甚至高出于他们的艺术成就之上。他们作为一批宗教和精神的高峰而超于审美的艺术之上,这是人类的集体回忆或造型。”[10]“长安”在这些诗人的笔下,也许就是海子所认为的那个“人类的集体回忆或者造型”,是一种超越于材料而作为精神的部分。
自20世纪80年代,在众生喧哗中,被淹没的“长安”被重新发现、激活。“长安”,作为一个具象和抽象的地理历史文化空间,作为一种风向标,诱发了诗歌从内部到外部、从个人的“乌托邦”到一个民族精神的宗教、从庄严的史诗写作到民间的口语化写作等诸多“诗潮”,呈现并隐喻着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的河流”。在历史的喧嚣之后,穿越当代诗篇中的“长安”书写,当我们再次回眸并眺望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嬗变轨迹,在这些书写长安的诗篇中,可以清晰地追索到中国当代诗歌演变的轨迹,从“气闷”的朦胧到写作视点的“民间化”,从拒绝华丽的“口语化”写作到重回史诗,中国当代诗歌在摸索前行中再次回归了中国古典的“史诗”传统和“民间”传统,当我们通过这些变奏去眺望中国当代诗歌涌动的“暗流”之时,我们已经打开了面向未来的诗歌将要走的路。2017年4月27日、6月1日、6月29日,《文学报》分三期推出了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如何写出史诗性作品”的讨论,讨论邀请了于坚、哈金、吴亮、郜元宝等诗人、作家、批评家来重新讨论有关诗歌、有关文学的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 ——史诗书写,这种讨论本身再一次显示了“历史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实感,历史对于诗歌,既是一种写作的资源,又是一种理论的‘资源’”。于坚在这场讨论中再次确认了他对历史的态度:“规避历史最终取消的是私人生活的深邃和独立”[11],因此,“长安”书写作为当代诗歌书写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在历史的回眸和现实的穿梭中既为过去的文学经验提供着“历史”的经验,更作为未来诗歌写作的“灯塔”,指引着诗歌前行的方向。
-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儒学研究的“体知”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