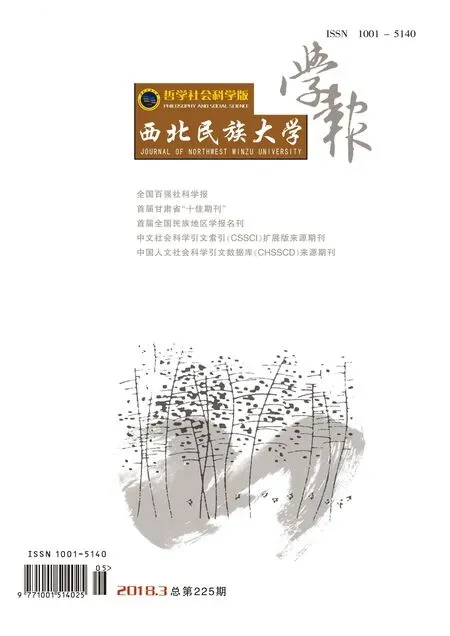英诗汉译中的折射:再探译诗的修改
王 杨
(兰州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但凡译文,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改进余地,相对短小的译诗更易留有遗憾,修改亦更为常见。对于译者在译作中出现的林林总总的“错误”,传统的翻译研究势必会“迁怒”于译者,但实际上,将翻译作为文学事实加以接受,则研究路径便会发生建设性的变化。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误解和误释’而获得曝光并产生影响。”[1]即他所称之为的“折射”。对“折射”之本质进行深入分析,不难看出其反映的是文学作品为应对不同读者所进行的改编,作为显性改编形式的翻译则在确立原作者及原作声誉的过程中极具影响力。
首先,翻译连接了原作和译作这两套文学系统,可看作是两套文学系统边界上产生的文本,作为文学系统行为准则的行为观念在多样化的系统碰撞中,不同的文学观念相互竞争,都试图控制整个系统。作为“折射”而存在的翻译试图将一部文学作品从一个系统带入另一个系统,就表现为两种系统间的妥协,由此,它必定会同时显现出两种系统中的约束机制。其次,翻译所体现出的不只是意义上的对等,而是分别支撑原作与译作的两种文学观念的妥协。原作从最初的不大被接受到被“确切”翻译,这个类似“进化”的过程将一直继续,由于支配接受系统的操控因素在不断变化,新的折射和改写势必会不断发生。
一、基于形式的“折射”:因译法改变而作的修改
英诗汉译初始阶段所普遍采用的“民族化”译法,逐渐演进为“兼顾顿数与字数”的译法,二者相较,足可见差别极大。以雪莱(Percy ByssheShelley,1792—1822)的短诗Awidowbird为例,早期的“民族化”译法将其译为五言或七言,如苏曼殊所译的第一句是“孤鸟栖寒枝”,郭沫若的是“有鸟仳离枯树颠”;而“兼顾法”重译后则是“丧偶的鸟为她的爱侣而悲痛”。由此可见,将高度浓缩的文言体现形式为主导的“民族化”译法改为“兼顾法”,实则得另起炉灶,基本等同于重译。究其缘由,“民族化”译法有相对封闭的体系、稳定的节奏范式、固定的语言规范和审美标准,故而有译者对同一原作使用文言与现代汉语夹杂的做法,然却鲜有改先前的“民族化”译诗为语体译诗的。
英语格律诗最终演进为按“兼顾”法要求进行汉译,正是看中了“形神皆似”这一实现效果,形式作为诗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得译作自动向原作靠拢,连韵式也改得同原作一致。英国诗人哈特利·柯勒律治(Hartley Coleridge,1796—1849)的SheIsNotFairtoOutwardView[2]前两句的汉译,正是“自由化”译文改为“兼顾法”译文:
她的外貌并不能算妖娆, 可现在她眼光冷淡娇羞,
没其他许多姑娘俊; 没对我眼光回一眼;
再以美国诗人尤金·菲尔德(Eugene Field,1850—1895)的LittleBlueBoy[3]为例,原作的韵式为ababcdcd,单行和双行的音步分别是四音步和三音步,虽然基本沿用此范式,但由于三音节音步相对较多,相较于三音步两音节的诗行就会多出不少音节,下面对比修改前后的原诗第一节两句的译文:
小小的玩具狗身上蒙着灰尘, 小小的玩具狗满身蒙着灰,
可仍旧雄赳赳傲然肃立; 仍雄赳赳在傲然肃立;
小小的玩具兵满是红色锈斑, 小小的玩具兵生锈又发霉,
发霉的步枪还握在手里。 那支枪还握在它手里。
先看原译,单行没有做到押韵,且每行还增加了一顿,但采用“兼顾法”的改译则还原了原作的韵式和音步数,且用十一字与九字区别了四顿行和三顿行所惯常采用的十字与八字。
以来自英国诗人道森(Ernest Christopher Dowson,1867—1900)的短诗TheyAreNotLong[4]下半首的末句为例,最末行仅为两音步“Within a dream”,且与第二行以同一词“dream”收尾。初译将此行译为“在梦中又失去了影踪”,修改后的译作则将其译为“消失在梦里”,在不损失内容的同时,充分地体现了原作的音步特点。
上述几例皆是“字数相应法”改为“兼顾法”,也有将“自由化”译诗改成“以顿代步”的,且看以下这一例。英国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的Sea-Fever最初是译成了自由诗的形式,原作的韵式也做了改变,尽管每行音节数不一,却都遵循着齐整的七音步,而这在初译中是被忽略的;修改后采用了“以顿代步”泽法:“我得重下海去,去那寂寞的大海和长天,……我得重下海去,因为奔流海潮的召唤,……我得重下海去,生活像漂泊的吉普赛人一般,……”。
从最初的“民族化”译法,到“五四”前后出现的“自由化”译法,再至“字数与顿数兼顾”法,在原译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修改,实则正是“折射”的体现,即译作所不断进行的改编,其意图是对读者阅读该作品的方式产生影响,原作借“折射”进入目的语所在的文学系统,读者最终由“陌生疏离”到“逐渐接受”的应是原作的本来样貌,而最开始抹杀原作呈现形式的译法从译诗的长远发展来看仅是一种“过渡”。
二、基于细节的“折射”:针对“韵”或“律”所作的修改
先看一例,美国女诗人韦尔考克斯(Ella Wilcox,1850—1919)的LaughandtheWorldLaughswithYou[5],以原作第一节为例,原作的音步数依次为四、三、四、三、三、三、四、三,原译文第五行“你歌唱,山丘把你的歌应和”和原作的“Sing,and the hills will answer”顿数不一致;修改后译为“你歌唱,山丘会应和”,达到了和原作相吻合的三顿。在押韵上,原作的第二、第四和第六、第八行分别押尾韵,第二、四行为“alone,own”;第六、八行为“air,care”,原译作未能体现出押尾韵,原译将第二、四行结尾译为“哭,多”,第六、八行译为“失,却”;修改后的译作则关注到了押尾韵的效果,第二、四行结尾译为“泪,堆”,第六、八行译为“走,后”。
再来看Rubaiyat[6]第四版第一首,原先的两种译作都符合“兼顾法”的要求,韵式也能达到与原作一致,但从韵脚上来看仍不够理想。原作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行皆押尾韵,分别是“flight,Night,Light”,原先的两种译文将其分别处理为“田园,飞散,塔尖”和“星星,院庭,塔顶”;修改后的译作则是“星斗,田畴,塔楼”,实现了对原作韵脚的贴合。虽说改动了韵式,但对全诗的牵动却并不大,而有时的改韵则会涉及较大的牵动面,例如美国诗人奈哈特(John Gneisenau Neihardt,1881—1973)的LetMeLiveoutMyYear[7]的第一节,原作的第二、第四句,第一、第三句分别押尾韵,以第二、第四句为例,原作的第二句是“Let me lie drunken with the dreamer’s wine!”,原译作将此句译为“让我在醇酒般的幻梦里醉沉!”,修改后的译作则是“让我酣饮了美梦之酒后醉卧!”;原作第四句为“Go toppling to the dust——a vacant shrine.”,原译作是“倒下时以空虚的躯壳归尘泥。”,修改后的译作为“跌落尘土时只是空虚的躯壳。”,改动的不只是韵脚,整个句式结构及语义重点都做了调整。
“韵”和“律”的修改同等重要,但相较于改动后表现更为明显的“韵”,“律”的改动却往往易被忽视,虽然改动“律”时常伴随译法的改变,但有时仅是词序的调整,不会牵动全诗,尤其从“字数相应”改为“兼顾”,不会出现像由“民族化”和“自由化”改为“兼顾”时那般大动作。以Rubaiyat第11首为例,原作的第三、第四行分别含六顿和四顿,原译为“奴隶、苏丹之称在此已被忘怀:愿马穆德在他的宝座上安泰!”,改译将这两句都处理成了五顿:“奴隶、苏丹之称在这里被忘怀:但愿马穆德在其宝座上安泰!”。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Rubaiyat第32首中,以原作第三句为例“Some little talk awhile of ME and THEE”,原译是每行六顿:“片言只语,你我被人谈及片时”,改译的效果为“片言只语,我和你被谈及片时”。
对采用“字数相应”译法的原译,改为“兼顾”译法时,有时仅是每行删去一二字,最为典型的请看美国女诗人Marianne Moore的ATalisman,以原作中的一小节为例:“of lapis lazuli, a scarab of the sea,with wings spread”,早先的译文是“那是天青石琢的海鸥,是海上的甲虫形石符;它张着翅膀,”,改为“兼顾”法后的译文为“那是天青石的海鸥,是海上甲虫形石符;它张着翅膀,”,再改的译文则是每行缩短了一音步,就成了:“那是个天青石海鸥,这航海人用的护符;展开着翅膀,”。原作中,长行皆是三音步六音节,按1:1.5的“字数相应”译法译成长行九字,顿数有三也有四,每行精简一字后就达成了“兼顾”的三顿一行。
再来看看英诗中常见的四音步诗行,最初多译为十一字四顿,在“兼顾”译法的关照下,改译成了十字四顿。以美国诗人Longfellow的TheRainyDay的第一节为例,第三句原作是“The vine still clings to the mouldering wall,”,原译为“藤蔓依然攀附着旧墙破壁”,修改后的译文为“藤蔓仍攀附着旧墙残壁”,此种修改贯穿于第一节的五句中。同此例相近的是美国诗人J.R.Lowell的Aladdin,原作全篇遵循三音步,多数是三音节。原译则是单行十字,双行九字,单行为四顿,双行为四顿、三顿兼有,其中四顿占多。且看原作第一节的后四句的原译作和修改后的译作之对比:
有时我冷得觉也睡不着, 脑海的眼睛千千万,
可脑海中火样的热情 心灵的只半双
追着缥缈的西班牙城堡, 但整个儿生活将黯淡,
堡上有美丽的金屋顶。 当爱情已死亡。
这例的修改所改动的不只是字数与顿数,内容呈现及表现重点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动,原译作在内容贴合度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修改后的译作对此进行了调整。
三、“折射”的发展:重译与借鉴
原作通过翻译的“折射”而进入新的文学系统所最先采取的一种策略是,将新的诗学概念翻译为更熟悉的旧的诗学术语,将新的诗学并入旧的诗学。随着新文学系统对来自外来语的原作的接纳程度的渐次放开,原先的策略发生了演化:解释新的诗学,并说明目的语文学系统实际上可以容纳它,可以允许它成为自身诗学的必要组成甚至是功能成分。此间,目的语文学系统对外来语原作从最初的情感疏离逐渐发展成为情感的卷入。故最初英诗汉译所采取的“民族化”、“自由化”译法就慢慢凸显出接受修改的必然,而不少译作仅是修改还显不够,有追求的译者会对其进行“重译”来适应已逐渐接受原作的当下文学系统。
著名的诗作多是重译所优先考虑的对象,以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短诗Coward[8]为例,至少有过下例几种已发表的译文:
1)我认识死,我不能面对死,
人们领着我去死,盲目的,孤独的。
2)恕我未能正视死亡,尽管当时惊险备尝,
只因把我双眼蒙住,人们让我孤身前往。
3)我不能清醒地面对死神,
而且人们把我一个人蒙住眼睛
引向了死神。
三种译文中,第一种出自1986年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诗”的条目;第二种出自郭沫若(1987),第三种则出现在1995年。
译家对自己所做的原译进行重译的情形也颇为常见,如许渊冲先生对Herrick的UponHisDepartureHence在《外国语》(1993/4)上刊出了译作,而后又在该刊(1994/4)上刊出了重译。
我如此 这样
Thus I 就消逝 死亡
Pass by 而去世, 下葬,
And die, 像一个 无名
As one 无名者 幽灵
Unknown, 死去了; 归阴,
And gone; 我变成 像是
I'm made 一个魂 影子
A shade, 被埋进 消失,
I'th grave, 坟墓里, 坟墓
There have 我有穴 有如
My cave, 在此地。 归宿。
Where tell 这地点 悠悠
I dwell, 我长眠, 永久
Farewell. 哦再见。 分手。
这首原作极为特殊罕见,称其为“短到不能再短”亦不为过,每行仅有一音步两音节,在此基础上遵循三行一韵,实则大大减少了翻译中可供回旋的余地,而诗人有意采用这样格律的目的就是从形式上使整个诗作的排版效果颇似墓碑。原译作已经从格律、韵脚、形式感等方面做到了与原作极大程度的贴合,许渊冲先生的重译力求在“字数相等”方面达到与原作的一致。
而有些重译既不是因原译对原作格律的反映仍存在可供提升的余地,亦不是需对内容进行某种“更正”。如1993年版的一本英汉对照诗集中,有一首玛丽·柯勒律治(Mary Coleridge,1861—1907)的Slowly,原作是英诗中不常见的“回文诗”,原作和译作《意迟迟》如下:
Heavy is my heart, 我心儿多沉郁,
Dark are thine eyes. 你眼光多暗淡。
Thou and I must part 你和我得分离
Ere the sun rise. 在太阳升起前。
Ere the sun rise 在太阳升起前
Thou and I must part. 你和我得分离。
Dark are thine eyes, 你眼光多暗淡,
Heavy is my heart. 我心儿多沉郁。
后齐云对于原译又给出了重译《意迟迟》,另一译者罗若冰也出了重译《依依情》,只选第一节作对比:
我的心多抑郁 我的心情忧郁,
你的眼已黯然 你的眼神暗淡。
我和你要分离 你和我得分离,
在红日升起前 在太阳升起前。
这样的重译,应当归于“借鉴”的范畴了。对于他人的译作有参考或借鉴在译界时有发生,有时是因对该译作印象太深,在自己的译作中会留有他人译作的影子,如1999年《希腊哀吟》中的“永夏尚滔滔,斜阳照荒岛”,读来总不免想起苏曼殊所译之“长夏仍滔滔,颓阳照空岛”。
对比上文的两种重译,齐云的重译在格律上与原译一致,内容也几近相同,却有半数以上的字进行了更换或改动了位置,所采取的译法仍是“兼顾”法。而后一种重译,改动过的便只有标题了。对于已被反复重译的诗作,若后来之译者只是作一些低水平的所谓“重译”或极为浅表的借鉴,对翻译资源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同样的心思、精力和时间,何不花在那些尚未译过的新作上,又或者,做一点更深层次的借鉴,按更高的译诗要求做些有质量的重译?
四、“折射”的反思:关于逆向修改
前文所论之“修改”,同英诗汉译的翻译要求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基本趋势是由低向高,所谓“逆向修改”,指的是与正常发展趋势相逆,甚至有译者将诗体移植的原译“修改”为“自由化”译文的,完全不了解英诗汉译的发展。遗憾的是,很多印数较大且流传颇广的英汉对照诗集不断进行再版后,不少诗作都进行了实为“逆向修改”的“重译”。
以《柔巴依集》第四版第49首为例,这一版的译文是:
如果你愿意去探索这个奥秘——
耗去你生命的珠片无所顾惜,
那就赶紧!正误也许只差毫厘——
但请问,什么才是生活的真谛?
细分析下,这译文存在一些问题,如第三行没有做到“字顿兼顾”,只做到了基本的“字数相应”。而编辑对于此译作的修改却是第二行,将其改为“即使耗去你生命的珠宝也无所顾惜”,这样一来,该行成了十五字,连“字数相应”都丢弃了,成了彻底的“自由诗”。之所以会有这般尴尬的“逆向修改”,大抵只是因为编辑的认识不够;而以下两个“逆向修改”的译文却被当作“新译”而发表,究其缘由,还是译诗的要求未能被更广大的群体了解所致。原作是美国诗人拉尼尔(Sidney Lanier,1842—1881)的短诗Struggle:
My soul is like the oar that momently
Dies in a desperate stress beneath the wave,
Then glitters out again and sweeps the sea:
Each second I’m new born from some new grave.
拉尼尔的作品之前鲜有译介,而在1989年却同时出现了两种译文。《美国抒情诗选》、《美国诗选》分别以题为《拼搏》和《斗争》收录如下:
我的灵魂宛如桨,在波涛之下 我的灵魂如一支桨,在一刹那间,
因为死命地奋力,而短暂陨灭, 死于骇浪之下的绝望的压力,
接着又闪烁而出,在海上一划: 然后又闪出波涛,且掠过海面,
每秒钟,新生的我跳出新墓穴。 每秒钟我复活,自一个新的墓里。
这两篇译文,前者采用了“兼顾”法,后者为余光中的译文,采用了“以顿代步”法,尽管译法之侧重点不同,但两者都注重了对原作格律的反映。而在1994年版的一套大部头译诗系列的美国诗歌卷中却出现了下面这篇所谓的“新译”《拼搏》:
我的灵魂仿佛一支桨,斩浪劈波,
因为奋力过猛,在刹那间毁灭;
而后又一闪而出,在海面掠过,
每一秒钟,复活的我,跳出新的墓穴。
所谓的“新译”明显是将两首“旧译”稍加拆解,再用拆后“零件”拼装而成。在译法上为了避免与旧译太过相近,改用了“自由化”译法,此外,还增添了原作中不存在的“引申”,如添加了“斩浪劈波”,还有用同义词进行置换,如以“毁灭”换“陨灭”。这种程度的“修改”正是“逆向修改”,与为提高翻译质量而进行的“修改”是大相径庭了。
英国诗人多恩(John Donne,1572—1631)的短诗Daybreak也遭遇了此类境遇,以原作前两句为例:
Stay,O sweet,and do not rise!
The light that shines comes from thine eyes;
The day breaks not: it is my heart,
Because that you and I must part,
这首原作的原译《破晓》出现在1992年:
躺着吧,亲爱的,请别起身!
这个光出自你那双眼睛;
天没破晓,是我的心破碎了,
因为你和我将不得不分离,
原译所采用的是“以顿代步”法,但韵式却与原作差别不小,原作的韵式为aabbcc,而译作的韵式为aabccb;原作是第一、第二行,第三、第四行分别押尾韵,而译作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实现。再来看看这首原作的“新译”:
躺着吧,亲爱的,千万别起身!
这一缕光亮之源是你那一对美眸;
天并没破晓,破的只是我的心,
因为我不得不与你分手。
不难看出,这位译者为了与原译“撇清”,分别用“美眸”、“分手”等词置换了“眼睛”、“分离”,而“千万”、“一缕”等词完全是凭空添加,这样一番“加工”之后,就成了“自由化”译诗,正是完全不看原作而在原译基础上进行“逆向修改”的译文。为何能断定这篇“新译”是抛开原作呢?原作中有这样一个关键词“Stay”,新译的处理方法和原译几乎完全一致,倘若真的读过原作,就不会完全照搬原译的做法。再看诗行排列:旧译的排列明显与原作不同,而新译的韵式为ababcc,单就这一点和原作较为接近,既如此,为何不采用原作的诗行排列,而还要沿用旧译的做法呢?
“逆向修改”的译诗存量不少,且形式多为自由诗,究其原因则是不少译者对英诗汉译的发展规律及其可企及的高度未能有足够的了解,进而对译作的优劣难以辨别。甚至于认为格律和内容不是统一而是对立的关系;所出版的译诗集,书名是越来越“美”,而处理也大胆到令人瞠目,有甚者竟将格律诗原作改为无韵诗。形式为诗作不可随意割舍的重要部分,对形式的任意丢弃,这样的译作其内容怕也无法准确反映原作之内容。在中文的语境中,形式主义多少都含有贬义之意味,而反映格律的译诗恰又是处于“自由化”译诗所包围下的“少数”,在此情形下,若是格律译诗对内容的反映还不及后者,岂不成了“因形害意”。
译诗的改进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逼近“真相”,尽可能地接近原作本身,原作通过翻译的“折射”在全新的文学系统中得到了认可和接受,而文学系统也由于外来原作的加入变得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