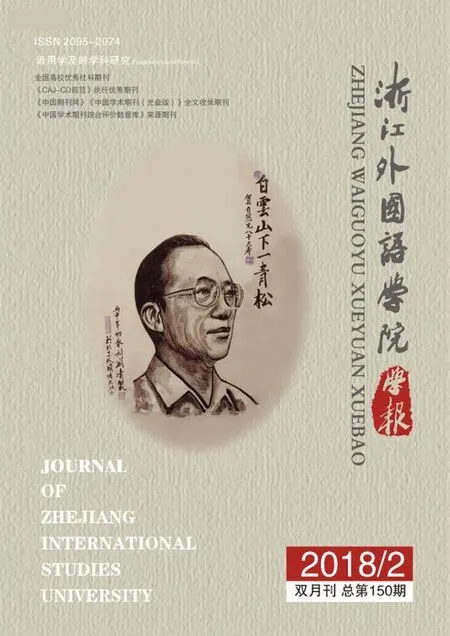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动物要素
董 科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动物要素
董 科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动物是人类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和伴侣,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动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牛、马、鸡、蚕等家养动物从中国或经中国传播至日本后,丰富了日本列岛的物种,改善了列岛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狮子、虎、豹等野生动物和中国人想象中的四神、祥瑞动物等所承载的科技、文化内涵深入列岛居民的心灵,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的思想力和想象力,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
动物;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一、引言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中,动物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举例而言,牛、马、虎、豹、羊、鹊等动物尽管在现代日本司空见惯,但在古代日本却并非如此。《三国志·魏书·东夷(倭人)》(陈寿 1959:855)载:“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可见这些当时已进入中国人生活的动物在日本列岛并无分布。然而,在此后的岁月里,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一些动物或与其相关的信息从中国传入日本并迅速为当地人所熟知。这些动物在日本列岛或被用作营生工具,或成为干支纪年法中的地支,或成为文艺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并最终成为当地社会、科技、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可以说,古代中日之间发生的动物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及途径,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关于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动物要素,目前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基于十二地支的民俗交流研究。该类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比较丰富。日本方面,南方熊楠撰写的《十二支考》系列论文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该系列论文最早于1914—1924年连载于《太阳》杂志上,后于1951年被修订编入《南方熊楠全集》①系列论文分别被修订编入涩泽敬三编的《南方熊楠全集 第1(十二支考 第1)》(東京:乾元社,1951年),以及《南方熊楠全集第2(十二支考 第2)》(東京:乾元社,1951年)。而《太阳》的原版目录暂未找到。,主要通过民俗调查和文献考证,系统地研究了十二地支所代表的十二种动物在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俗文化中的意义。此后,桥本增吉②桥本增吉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十干十二支考(上)》(《東洋学報》第21卷第2号,第137-202页,1934年)、《十干十二支考(中)》(《東洋学報》第21卷第4号,第471-505页,1934年)、《十干十二支考(下の1)》(《東洋学報》第22卷第1号,第1-53页,1934年)、《十干十二支考(下の2)》(《東洋学報》第22卷第3号,第323-356页,1935年)、《十干十二支考(下の3)》(《東洋学報》第 24卷第 2号,第151-219页,1937年)。、门田诚一③门田诚一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十二支像表現の東伝—新羅生肖系譜初探》(《文化史学》第45号,第57-76页,1989年)。、滨田阳④滨田阳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日本十二支考 :文化の時空を生きる》(東京:中央公論社,2017年)。等在南方熊楠的基础上,拓展了中日十二地支动物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国方面,王秀文撰写的系列论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⑤王秀文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日本“犬”民俗的传承及其文化内涵》(《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第35-37,53页)、《日本“猪”民俗的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108-111页)、《日本“鼠”民俗的传承及其文化内涵》(《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501-503,508页)、《从日本“牛”信仰看中日民间文化传承》(《大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83-88页)、《从日本“马”信仰看中日民间文化传承》(《大连近代史研究》,第11卷,大连: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40-449页)、《日本民俗中的“猴”信仰及其传承》(《大连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89-92页)、《日本民俗中的“鸡”信仰及其传承》(《大连大学学报》,2017年第 1期,第 90-94页)。,这些论文考察了十二地支动物在日本的民俗传承及文化内涵。二是文学作品中的动物文化研究。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寺山宏的《和汉古典动物考》(2002),该书较为系统地考证了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出现的140种动物,并对部分动物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有所涉及。总体而言,十二地支视角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十二地支动物,方法则主要是民俗学方法,而文学作品中的动物研究主要考察动物的文学意义。因此,两者均未能在将物种交换和文化交流纳入研究范畴的基础上,系统论述动物要素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
有鉴于此,本文欲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和汉古典动物考》为主要文献线索,选取非日本原产动物中具有代表性者,探析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期抛砖引玉。
二、家养动物与生产生活
在古代中日两国间动物交流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类动物便是直接对日本列岛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要作用的家养动物,它们包括牛、马、鸡、蚕、羊等。
(一)牛与马
牛(Bos taurus)和马(Equus caballus)广泛运用于农耕、运输、传递信息、战争、食用、乳用等领域,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早在公元前5000年欧洲就开始驯化牛,而马的驯化可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的伊朗(寺山宏 2002:43-44,52)。在中国,这两种动物的遗骸被发现于公元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雄生2008:45)。
《日本书纪·神代》对牛和马进行了如下描述:保食神被月读命杀死后,“唯有其神之顶化为牛马”;日本武尊弹蒜杀死了化作白鹿的信浓坂山神,“先是度信浓坂者,多得神气以瘼卧。但从杀白鹿之后,踰是山者,嚼蒜涂人及牛马,自不中神气也”(板勝美1966a:23,218)。然而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却显示,作为家畜的牛和马是在弥生时代以后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的(西中川駿 1990),这印证了《三国志》中所载公元3世纪日本列岛无牛马的情况。马进入日本列岛后便迅速为当地居民所熟知和使用,《日本书纪》载,垂仁皇后日叶酢媛命死去,天皇不忍按照传统以人殉葬,“唤上出云国之土部一百人,自领土部等,取埴以造作人、马及种种物形”(板勝美1966a:187)用以殉葬,日本各地出土的大量古坟时代的马形埴轮不仅为这段传说提供了事实依据,而且反映了马在日本的使用情况。
到了律令时代,日本设立了专门管理马匹的机构——左右马寮,而且牛马的使用及待遇更是被写入了法律。比如《养老令》模仿唐令设有《廐牧令》,唐《廐牧令》复原后有23条(仁井田陞 1989:625-640),日《廐牧令》有 28 条(板勝美1966f:171-178)。对比两令则可发现,唐令中有关于牛、马、驼、象的规定,而日本令中则仅涉及牛与马,可见与唐朝牛、马、驼、象并用相比,这一时期的日本主要使用牛、马。纵观“六国史”、《养老令》等史料,马在古代日本的最主要用途是传递信息及行军打仗,牛则主要用于耕作、取乳、制药及运输。在日本,牛和马也曾被用作食材,但可能是由于佛教的影响及其工具性日益受到重视,其食用在公元7世纪后被国家禁止。比如《日本书纪》载,天武天皇四年(675)四月有诏曰:“莫食牛马犬猿鸡之完(肉),……若有犯者罪之。”(板勝美1967:338)《续日本纪》载,天平十三年(741)二月圣武天皇有诏曰:“马牛代人,勤劳养人。因兹先有明制,不许屠杀。今闻国郡未能禁止,百姓犹有屠杀。宜其有犯者,不问荫赎,先决杖一百,然后科罪。”(板勝美 1966b:163)。由此可见,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对牛和马的重视程度。此外,日本还吸收了中国汉代“天人感应 阴阳灾异”的思想,仿效中国的做法,将牛生产畸形幼犊视作“牛祸”记录在包括“六国史”在内的各类史书中。
牛和马在奈良时代的成书和汉文集中已有出现,比如在《万叶集》中,与马有关的和歌达85首以上,与牛有关的则有3首(寺山宏 2002:46,57)。其中,编号3886的和歌《为蟹述痛一首》以螃蟹的口吻说道:“……東の中の門ゆ參納り來て命受くれば、馬にこそ絆掛くもの、牛にこそ鼻はくれ……”⑥杨烈的译文为:“东方入中门,参拜受命卑,如马受羁绊,如牛穿鼻危。”(佚名 1984:682)。(高木市之助,等1962:165)该和歌生动地将到京城为王者所食乃是螃蟹的使命,与接受马绊是马的使命以及接受鼻绳是牛的使命作类比,这反映了时人对牛和马的认知。又如《怀风藻》中所收录吉田连宜的《五言·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云:“西使言归日,南登饯送秋。人随蜀星远,骖带断云浮。一去殊乡国,万里绝风牛。未尽新知趣,还作飞乖愁”(小島憲之1964:141),以风马牛不相及的典故来比喻新罗客人归国再难相见。同书所收释辨正《五言·与朝主人》则云:“钟鼓沸城闉,戎蕃预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小島憲之1964:97)释辨正于公元702年赴唐留学,他在模仿李峤等人所作系列诗《奉和圣制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的基础上创作了该诗(胡志昂 2009)。“琴歌马上怨”展现的异域风情给彼时留学中国的释辨正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的诗作又给日本列岛居民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二)鸡
鸡(Gallus gallus var. domesticus)作为家禽来驯养,可能始于公元前2300年的印度,公元前1200年传至中国,此后再经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寺山宏 2002:342-343;東京農業大学講師聯合1922:6)。《日本书纪·神代》云:“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以鸡蛋来形容天地未分时的世界;《日本书纪·仁德纪》记载了额田大中彦皇子猎于斗鸡(地名)之事;《日本书纪·允恭纪》记载了统治斗鸡氏的斗鸡国造因冒犯允恭皇后而被贬姓稻置之事;《日本书纪·雄略纪》则记载了吉备前津屋叛乱前进行斗鸡之事(板勝美 1966a:1,314,338-339,369-370)。《万叶集》中有 6 首以鸡为主题的和歌,如编号1413的和歌说:“庭つ鳥の、垂尾の乱れ尾の、長き心も、思ほえぬかも”⑦杨烈的译文为:“庭鸡垂尾乱,乱尾亦何长,安有悠长意,斯人念不忘。”(佚名 1984:287)。(高木市之助,等1959:267),用鸡尾之长来比喻相思之长;编号2800的和歌则说:“と鳴くなり、よしゑやし、獨り寝る夜は、明けば明けぬとも”⑧杨烈的译文为:“拂晓听鸡鸣,虽鸣我不惊,夜来仍独宿,何惜此天明。”(佚名 1984:505)。(高木市之助,等1960:243),以鸡鸣作为早晨到来的象征。综上可知,在古代日本,鸡主要用于嬉戏与报晨。当然,如同牛和马一样,鸡在日本也曾被用作食材,但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国家的禁止,古代日本食鸡肉的习俗有所衰退。然而,作为重要蛋白质来源的鸡蛋却由于没有受到法律及佛教禁忌的约束而备受岛国居民的重视,人们甚至将它视为治疗万病的灵药,每户农家大抵都会养几只鸡,取蛋食用。《太阁记》中有云,天正年间(1573—1592),三河国有个叫入江的武士,舍弃弓矢之业,转而经营大规模养鸡场,并且成为了养鸡专家,可见古代日本可能也有过专业养殖户的存在(東京農業大学講師聯合1922:7)。
日本人对鸡的看法深受中国典故的影响。《类聚国史》天长元年(824)七月十二日平城太上天皇谅闇条中记载:“天皇识度沉敏,智谋潜通,躬亲万机,克己励精,省撤烦费,弃绝珍奇。法令严整,群下肃然。虽古先哲王不过也。……其后,倾心内宠,委政妇人。牝鸡戒晨,惟家之丧。呜呼惜哉……”(板勝美1965b:141)该文首先高度称赞了平城天皇的贤德与功绩,紧接着用“牝鸡戒晨”来形容天皇宠幸藤原药子使其干政,最终导致“药子之变”的发生。“牝鸡戒晨”缘自中国的著名典故,以母鸡打鸣比喻纣王宠幸妲己致使国家无道,《尚书·牧誓》载:“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今予发惟共行天之伐。”(慕平2009:122)这个典故被日本人直接用到了平城天皇身上。《枕草子》中藤原行成给清少纳言的信中写道:“驝孟嘗君のにはとりは函谷をひらきて、三千の客わづかに去れり」とあれども、これは逢坂のなり。”⑨陈美锦的译文为:“孟尝君的‘鸡’叫开了函谷关,让三千名食客得以逃脱,我这只鸡仅是叫开了逢坂关。”(清少纳言 2016:139)(池田鑑,等 1958:189-190)可见,《史记》中所载孟尝君靠着食客装狗叫盗取白狐裘以获得秦昭襄王宠妾为其求情,以及学雄鸡啼叫骗守城官兵打开函谷关成功脱险的故事已为古代日本人所熟知,并运用于文学创作。
(三)蚕
蚕(Bombyx mori)原产于中国,是在室内驯养桑木上的野蚕而得的昆虫。中国人至少在3000年前就开始养蚕,并将蚕丝用于纺织。养蚕术于公元前200年前后传至朝鲜半岛,其后再由朝鲜半岛传播至日本(寺山宏 2002:81)。《三国志·魏书·东夷(倭人)》中载:“(列岛居民)种禾稻、麻、蚕桑、缉绩,出细、缣绵”,正始四年(243)“倭王复遣使……上献生口、倭锦……”(陈寿 1959:857)由此可见,在公元3世纪,日本列岛居民已熟练掌握了养蚕和制作丝织品的技术。
日本神话中有关于养蚕起源的故事。比如《古事记》载:“须佐之男命……煞其大宜津比卖神,故所煞神于身生物者,于头生蚕……”(板勝美1966e:22)《日本书纪》则说,月读命斩杀保食神后,保食神尸体“眉上生蚕”,天熊人将之带回。天照大神“口里含蚕,便得抽丝。自此始有养蚕之道焉”(板勝美 1966a:23-24)。
《养老令》中则规定农家必须种植养蚕所用的桑树,“凡课桑漆,上户桑三百根……;中户桑二百根……;下户桑一百根……以上,五年种毕”(板勝美1966f:109)。《万叶集》中留有4首与蚕相关的和歌,其中编号2495的和歌说:“たらちねの、母が養ふ蚕の繭り、れる妹を、見むよしもがも”⑩杨烈的译文为:“吾母事蚕桑,蚕成作茧藏,妹藏何处所,欲见也无方。”(佚名 1984:468),以蚕茧比喻心爱之人藏起来无法相见;编号3086的和歌则说:“なかなかに、人とあらずは、桑子にも、ならましものを、玉の緒はかり”⑪杨烈的译文为:“不得为人道,无如短命蚕,桑蚕成牝牡,早死也心甘。”(佚名 1984:542)(高木市之助,等1960:187,303),用蚕的生命周期来比喻人生短暂。由此可见,在奈良时代,养蚕织丝已成为日本的一项重要产业,从文化精英到普通农家的各个阶层都已对植桑养蚕十分熟悉。
养蚕不仅为列岛蚕农提供了生计,更是为历代日本文学家提供了吟诵的对象。在俳句中,蚕成为了春季的季语,上蔟与蚕茧则成为了夏季的季语。松尾芭蕉、森川许六、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江户时代著名俳人均留有以蚕为对象的佳句。明治维新之后,养蚕缫丝业成为了日本出口的支柱产业,直到20世纪20年代蚕丝出口总额仍居全日本首位,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金(寺山宏2002:83-87)。
(四)羊(山羊和绵羊)
作为家畜的羊,可分为山羊(Capra hircus)和绵羊(Ovis aries)两种。公元前5500年左右,中东广大山区开始驯养羊。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羊”,往往不注明是绵羊还是山羊⑫日本的汉文文献除个别情况,往往也不对山羊和绵羊加以区分。。在原始畜牧业中,它们几乎是同时并存的(谢成侠 1985:139,143)。羊可能是在公元600年前后自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的。《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七年(599)九月一日条中有曰:“百济贡骆驼一疋、驴一疋、羊二头、白雉一只”(板勝美1967:136),这是日本文献中关于羊的最早记录。由于不具备耕种及运输功能,且日本列岛核心地区不适宜大规模放牧,羊在古代日本的驯养规模不及牛、马,直到近代之后,北海道、(日本)东北一带才开始成规模牧羊(寺山宏 2002:384)。在古代日本,天皇将羊皮作为赏赐品赐予臣下,例如《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十四年(685)九月十九日条中有曰:“皇太子以下,及诸王卿,并四十八人,赐罴皮、山羊皮各有差。”(板勝美1967:379)《续日本纪》天应元年(781)六月一日桓武天皇在诏令中说:“惟王之置百官也,量材授能。职员有限,自兹厥后,事豫议务稍繁,即量剧官,仍置员外,近古因循,其流益广,譬以十羊更成九牧。民之受弊,寔为此焉。”(板勝美1966b:472-473)该诏令以中国成语“十羊九牧”生动地揭示了当时日本官多民少的弊病,反映了古代日本对中国牧羊文化的受容。
三、异兽珍禽与异域想象
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有一些野生动物虽未被直接引进到日本,但其形象却已然植根于列岛居民心底,狮、虎、豹、象、鹊就是这类动物的代表。
(一)狮
狮(Panthera leo),亦称狻猊,是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猛兽之一,古代在中近东、南亚次大陆一带有广泛分布。该物种实体首次进入日本的时间是庆应二年(1866)(寺山宏 2002:246),但它的艺术形象至迟在唐代就已从中国传入日本。比如奈良法隆寺所藏国宝“四骑狮子狩文锦”便是中国唐代的丝织物,在这幅颇具萨珊王朝风格的织锦上,编织着四个骑马武士射杀狮子的图像(文化2017)。然而,在日本更加深入人心的狮子形象,却不是波斯武士的猎杀对象,而是佛教中备受尊崇的百兽之王。
在佛教的诞生地南亚,人们对狮子十分熟悉,并将其作为百兽之王来尊崇。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被尊称为“人中师子”“人中人师子”“大师子王”,而其祖父就是“师子颊王”;佛的座席被称为“师子座”;佛,特别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多被比喻为“师子吼”;佛教中“狮子身中虫”的比喻则把佛教僧团比作狮子,把居住在僧团内部破坏佛教的“诸恶比丘”比作狮子身体里的虫子(白化文1998)。
汉传佛教进入日本后,在佛经和佛教艺术品中频繁出现的狮子也迅速为列岛居民所熟知和尊崇。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在东大寺为大佛开眼时把狮子头等作为道具(胡小杰 1992),其“御葬之仪如奉佛,供具有师子座香炉……”(板勝美1966b:225)而文献中所载第一位亲眼目睹狮子的日本人可能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作者圆仁。《日本三代实录》记载了圆仁在(中国)五台山大华严寺求法时的一段逸闻:“圆仁住大华严寺涅院,经过一夏,垂至北台,云雾满山,径路难寻。雾气开霁,乃看路前,见一师子,其形甚可怖畏。圆仁却走二三里许,经于小时,更复进路,见彼师子犹在前路,蹲居不动。更复却走二三里许,弥增惊恐,数刻之后亦渐进行,师子犹在不去。遥见人来,即便起立入重雾中。”(板勝美1966d:125)相传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方庆奇、王学斌 1993),唐五代汉传佛教的壁画中文殊菩萨的坐骑多为狮子(马新广2013)。既然当时的五台山并没有狮子的分布,那么史料中圆仁在五台山看见狮子的传说,无疑是在隐喻他见到了文殊菩萨。这一点在《日本三代实录》中有所印证:“故延历寺座主慈觉(圆仁)本愿文殊五间影向楼一基……安置正体文殊坐像一躯……师子御者化现文殊大士立像一躯……昔者慈觉大师入唐求法之日,巡礼台山之时,感遇文殊化现师子圣灯圆光,赖此大圣之感应,得遂求道之大愿……”(板勝美1966d:377)此处,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被视为圆仁得遂求道大愿的契机之一。
《宇治拾遗物语·小野篁广才事》记载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嵯峨天皇为刁难小野篁书写了十二个“子”字命令他读。小野篁用“子”的四种读音答道:“ねこの子こねこ、しゝの子こじゝ”⑬大意为:猫咪的孩子小猫咪,狮子的孩子小狮子。(渡綱也,等1960:147),从而巧妙地化解了难题。用狮子(しゝ)来回答字谜,印证了在《宇治拾遗物语》成书的镰仓时代这种动物已为日本列岛居民所熟知的史实。
公元4世纪前后,狮子舞由西域传至中国中原地区,历经变化,在唐代时已发展成为一种宫廷乐舞,随后传入日本。据说,曾在唐朝留学很长时间的吉备真备奉圣武天皇之命制作了神面和狮子头,举行仪式后这些物品被奉纳于伊势国铃鹿郡椿大社。此后,每当新年来临之际,就会有艺人头戴狮子头,合着笛子、太鼓演奏的音乐起舞,走家串户,意在借助百兽之王狮子的神力来驱逐恶灵,并送上新年的祝福,这一风俗传承至今(寺山宏 2002:247;胡小杰 1992)。
(二)虎与豹
虎(Panthera tigris)、豹(Panthera pardus)与狮一样是大型猫科猛兽,广泛分布于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虎、豹皮毛美丽,常被用来制作褥、裘、帽子、坐垫等,自古以来为人类所贵重 (寺山宏2002:325,388-389)。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六年(545?)十一月条中有云,奉命出使百济的膳臣巴提在雪夜停宿于百济滨,其子为虎所害。巴提便找到了那只虎,为子复仇:“其虎进前开口欲噬,巴提便忽伸左手,执其虎舌,右手刺杀,剥取皮还。”(板勝美1967:71-72)通过在朝鲜半岛与虎的接触,列岛居民知晓了虎的威猛。《万叶集》所收《高市皇子尊城上殡宫之时柿本朝臣人麻吕作歌一首并短歌》(编号199-201)说:“……吹き響せる小角の音も、敵見たる虎が吼ゆると、諸人のおびゆるまでに……”⑭杨烈的译文为:“号角吹出虎吼声,敌人闻之心胆颤。”(佚名 1984:51)。(高木市之助,等1957:109),以虎的吼声来称赞高市皇子的威武军容。
在律令制下的古代日本,服饰中的虎、豹元素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比如冠位十二阶中位列三、四的大仁、小仁以豹尾髻华来体现,《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九年(611)五月五日条载:“是日,诸臣服色皆随冠色、各着髻华。则大德、小德并用金;大仁、小仁用豹尾;大礼以下用鸟尾。”(板勝美1967:153-154)再如只有五位以上者才可用虎皮,豹皮则只有参议及非参议三位以上者才可使用⑮三位以上为“贵”,五位以上为“通贵”。“贵”与“通贵”构成了日本律令制下的贵族。,《延喜式·弹正台》载:“凡五位以上,听用虎皮。但豹皮者,参议以上及非参议三位听之,自余不在听限。”(板勝美1965a:911)
(三)象
象(Elephantidae)是陆地上现存最大的哺乳动物,分布于亚洲及非洲,日本不产。日本列岛居民主要是通过中国的书籍以及象牙制品来获取象的相关信息。成书于公元10世纪上半叶的《倭名类聚抄》云:“象,《四声字苑》云兽名,似水牛,大耳长鼻,眼细牙长者也。”(中田祝夫 1978:208)这里的和名“岐佐”读作“きさ”,原意为木材纹理,因象牙上有相同纹理,故被日本人用来指象。在古代日本,人们将象牙视为贵重的装饰物。比如《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十年(671)十月条载:“是月,天皇遣使奉袈裟、金钵、象牙、沉水香、栴檀香及诸珍财于法兴寺佛”(板勝美1967:300);《日本纪略》延历十九年(800)四月廿二日条载:“勅,象牙阴阳之外,亲王□□以下不得服用”(板勝美 1965c:275);《日本后纪》弘仁六年(815)十月廿五日条中则有:“勅,亲王内亲王女御及三位已上嫡妻子,并听着苏芳色象牙刀子”(板勝美1966c:136);《延喜式·弹正台》中有:“凡内命妇三位以上,听用象牙栉……玳瑁、马瑙、斑犀、象牙、沙鱼皮、紫檀,五位已上通用”(板勝美 1965a:911)。
应永十五年(1408),完整的实物象首次来到日本。《若狭国守护职次第》是年六月廿二日条载:“南蕃船着岸……向日本国王献物等。生象一匹(黑),山马一只,孔雀二对,鹦鹉二对……”(神宮司1930:457)。然而,关于象形象的认知似乎未能比较完整地流传下来。建成于公元17世纪的日光东照宫上神库上有一件被称为“想象之象”的木雕作品,作品所雕两头象的形象虽然与《倭名类聚抄》中“似水牛,大耳长鼻,眼细牙长”(中田祝夫1978:208)的描述相符,但与象的真实形象仍有一定差距。由此看来,当时的列岛居民仍不明象之真容,只能凭文献资料等来塑造象的形象。享保十三年(1728),中国江南商人从广南国带来牝象牡象各一头至长崎,日本人仔细观察了它们后用写实风格绘制了 《驯象图》,并用翔实的文字记录了它们的形体特征,再配上关于象的种种考证,合成《象志》一册出版发行(著者不明1729)。自此,象的真实形象开始广为日本列岛居民所熟知。
(四)鹊
鹊(Pica pica),也称喜鹊,在欧洲、北非、北美及亚洲广大地区有原生分布。日本本无喜鹊,它最早是从新罗传到日本的。《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六年(598)四月条载:“难波吉士盘金至自新罗而献鹊二只,乃俾养于难波杜。因以巢枝而产之。”(板勝美1967:138)同书天武天皇十四年(685)五月廿六日条则载:“新罗王献马二疋、犬三头、鹦鹉二只、鹊二只,及种々宝物。”(板勝美 1967:377)然而,该物种并未在日本繁衍生息,侵略朝鲜期间,丰臣秀吉将少量喜鹊带回了日本,目前日本境内也仅九州岛北部的一部分地域有喜鹊(寺山宏 2002:103)。
与直接来源于朝鲜半岛的喜鹊实物相比,中国七夕的鹊桥传说更早地进入了日本人的心中。例如《怀风藻》中收录的出云介吉智首《五言·七夕》直接援引了鹊桥相会的传说:“冉冉逝不留,时节忽惊秋。菊风披夕雾,桂月照兰洲。仙车渡鹊桥,神驾越清流。天庭陈相喜,华阁释离愁。河横天欲曙,更叹后期悠。”(小島憲之 1964:122)
四、四神、瑞物和干支纪年
随着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存在于中国神话中的四神、瑞物,以及干支纪年等也逐渐为列岛居民所熟知与接受,并应用到国政与社会生活之中。
(一)四神
四神是一种以动物形象出现的神灵。《三辅黄图》将四神定义为苍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神图像可能起源于观象授时和时空合一的古代科技文化,仰韶文化墓葬遗址中的蚌塑龙虎图案、曾侯乙墓漆箱的龙虎彩绘可能都是四神图案的源流。在汉代,因五行思想的盛行,四神逐步固化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神像,被赋予了天文星象的意义及祈禳追求的象征,受到普遍崇拜(程万里 2012)。四神图像及信仰此后传入日本,对列岛居民的信仰产生了广泛影响。建于飞鸟至奈良时代的キトラ古坟与高松冢古坟中就有中国唐代风格的四神图(東潮 1999),而《日本书纪》大化五年(649)三月十七日条载:“阿倍大臣(内麻呂)薨,天皇幸朱雀门举哀而恸”(板勝美 1967:244),可见在难波宫时代,就已有以朱雀命名的宫门。《续日本纪》大宝元年(701)正月一日条中曰:“天皇御大极殿受朝。其仪:于正门树乌形幢,左日像青龙朱雀幡,右月像玄武白虎幡,蕃夷使者陈列左右。文物之仪,于是备矣”(板勝美1966b:9)。而此后的平城京以及平安京均按四神相应的风水来选址。平安时代后期的官吏中原广俊的诗作《夏日东光寺即事》道:“城东寻寺一逡巡,其地胜形备四神。草创以来经几岁,檀那在昔是何人?”(著者不明 1930:303)由此可知,四神相应同样也被用于古代日本寺庙的选址。
(二)瑞物
中国传说中象征祥瑞的神话动物广为古代日本列岛居民所接受。平安时代的《延喜式·治部省》祥瑞条规定了祥瑞的色目及等级,并附有对各种祥瑞的详细说明。在这些祥瑞中,神话动物或不常见的动物占很大比例,属于“大瑞”的有河精、麟、凤、鸾、比翼鸟、同心鸟、永乐鸟、富贵、吉利、神龟、龙、驺虞、白泽、神马、周帀、角端、解荐、比肩兽、六足兽、兹白、白象、一角兽、天鹿、虌封、酋耳、豹犬、露犬,共27种,占“大瑞”总数(60种)的45%;属于“上瑞”的有三角兽、白狼、赤罴、赤熊、赤狡、赤兔、九尾狐、白狐、玄狐、白鹿、白獐、兕、玄鹤、青乌、赤乌、三足乌、赤燕、赤雀、比目鱼,共计19种,占“上瑞”总数(38种)的50%;属于“中瑞”的有白鸠、白乌、苍乌、白睪、白雉、雉白首、翠乌、黄鹄、小鸟生大鸟、朱雁、五色雁、白雀、赤狐、黄罴、青熊、玄貉、赤豹、白兔、九真奇兽,共 19种,约占“中瑞”总数(33种)的 58%;属于“下瑞”的则有戴角麀鹿、駮鹿、神雀、冠雀、黑雉、白鹊,共6种,占“下瑞”总数15种的40%(板勝美 1965a:527-528)。
据研究,唐《礼部式》是东亚地区最早规定祥瑞色目的法律,而《延喜式·治部省》祥瑞条中关于祥瑞色目的规定几乎是照搬唐《礼部式》。与唐《礼部式》现存部分相比,《延喜式·治部省》的大部分条目中都多出了一段关于祥瑞色目的解释性文字。因为现存唐《礼部式》并不完整,所以不清楚这些解释性文字是唐原文中就有的,还是日本人按中国书籍的描述添加的,但无论如何,《延喜式·治部省》对色目的分类和解释无疑均源自中国(吴海航 2011)。中国文化中的瑞物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正仓院收藏的奈良时代宝物中,有4件以上与凤凰相关,其中东大寺大佛开眼时(752)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所使用“礼服御冠残欠”上的金工凤凰造型(正倉院,2017)与《延喜式·治部省》中对凤的描述“状如鹤,五彩以文,鸡冠燕喙,蛇头龙形”(板勝美1965a:527)相符,建造于平安时代中后期的平等院凤凰堂所用金铜凤凰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
(三)干支纪年
干支起源于中国,是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组合记录时间的方法,以甲子为始,癸亥为终,60组一个轮回。干支中的十二支分别代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等12种动物。这种记录时间的方法在殷代用于表示日期,王莽时代以后用于纪年。公元7世纪下半叶,这种记录时间的方法传播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佐藤正幸1998),其结果便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拥有了历法科技,十二支中衍生出的生肖等习俗也在这些国家生根结果。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动物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一方面,牛、马、鸡、蚕等家养动物的传入,丰富了日本列岛的物种,改善了列岛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动物所承载的科技、文化内涵深入列岛居民的心灵,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思想力和想象力,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
古代中日两国之间以动物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有着明显的方向性,这可看作是中国文明对日本单方面的馈赠。然而,这些动物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却并非仅源自中国,而是中东地区、印度、中国、朝鲜等复数古典文明的结晶。到了近现代,日本选育的良种家养动物、动物养殖技术乃至文艺作品中的动物艺术形象从日本反向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可以看作是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回馈。这些内容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张丽山、曾昭骏为本文撰写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
東潮.1999.北朝·隋唐と高句麗壁画——四神像と畏像を中心として[J].国立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80):261-325.
池田鑑,等,校注.1958.枕草子[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9.東京:岩波書店.
板勝美,編輯.1965a.延喜式[M]//新訂補国史大系2.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5b.類聚国史(前篇)[M]//新訂補国史大系系5.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5c.日本紀略(前篇)[M]//新訂補国史大系10.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6a.日本書紀(上)[M]//新訂補国史大系1(上).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6b.日本紀[M]//新訂補国史大系2.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6c.日本後紀[M]//新訂補国史大系3.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6d.日本三代録[M]//新訂補国史大系4.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6e.古事記 [M]//新訂補国史大系7.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6f.令義解[M]//新訂補国史大系22.東京:吉川弘文館.
板勝美,編輯.1967.日本書紀(下)[M]//新訂補国史大系1(下).東京:吉川弘文館.
胡志昂.2009.最盛期の遣唐使を支えた詩僧·弁正[J].埼玉学園大学紀要(人間学部篇)(9):345-358.
小島憲之,校注.1964.風藻[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東京:岩波書店.
佐藤正幸.1998.共同研究報告:日本における紀年認識の比較史的考察[J].日本研究 (18):177-204.
正倉院,.2017.正倉院宝物[DB/OL].[2017-11-28].http://shosoin. kunaicho. go. jp/ja-JP/Treasure?id=0000020679.
神宮司,編.1930.古事類苑(49)[M].東京:古事類苑刊行会.
高木市之助,等,校注.1957.万葉集(1)[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4.東京:岩波書店.
高木市之助,等,校注.1959.万葉集(2)[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東京:岩波書店.
高木市之助,等,校注.1960.万葉集(3)[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東京:岩波書店.
高木市之助,等,校注.1962.万葉集(4)[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東京:岩波書店.
著者不明.1729.象志[M].京都:梅英軒、寿陽堂.
著者不明.1930.本朝無題詩[M]//内外書籍株式会社,編.新校群書類6.東京:内外書籍.
寺山宏.2002.和漢古典動物考[M].東京:八坂書房.
東京農業大学講師聯合,編.1922.養講習録(第1)[M].東京:日本農業社.
中田祝夫,編.1978.倭名類聚抄(元和三年古活字版二十本)[M].東京:勉誠社.
西中川駿.1990.古代遺跡出土骨からみたわが国の牛,馬の渡来時期とその路にする研究(概要)[EB/OL].[2017-11-25].https://kaken. nii. ac. jp/ja/grant/KAKENHI-PROJECT-01490018/.
文化.2017.国家指定文化財等データベース[DB/OL].[2017-11-25].http://kunishitei. bunka. go. jp/bsys/index_pc. html.
渡綱也,等,校注.1960.宇治拾遺物語[M]//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7.東京:岩波書店.
白化文.1998.狮子与狮子吼——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J].文史知识 (12):37-42.
陈寿.1959.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程万里.2012.汉画四神图像[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方庆奇,王学斌.1993.五台山文殊菩萨[J].五台山研究 (4):14-23.
胡小杰.1992.西域狮子舞东渐及其在日本的嬗变[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47-51.
马新广.2013.唐五代佛寺壁画里的文殊[J].世界宗教文化 (3):79-81.
慕平,译注.2009.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
清少纳言.2016.枕草子[M].陈美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仁井田陞.1989.唐令拾遗[M].栗劲,霍存福,王占通,等,编译.长春:长春出版社.
吴海航.2011.唐礼部式祥瑞条与日本治部式祥瑞条“大瑞”色目关系考略[C]//赵秉志.主编.京师法律评论(第5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57-266.
谢成侠,编著.1985.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
佚名.1984.万叶集[M].杨烈,译.沈佩璐,张勤,施小炜,郑强,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曾雄生.2008.中国农学史(修订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Animal Factors in Ancient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DONG Ke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China)
Animals are not only indispensable tools and companions in human life and production, but also important carriers of human culture. They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ancient Japan. Domestic animals like cattle, horses, chickens and silkworms, after being spread from (or through)China to Japan, have enriched species in Japan and improve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of Japanese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rried by wild animals like lions, tigers, and leopards as well as The Four Gods (Qinglong, Baihu, Zhuque and Xuanwu)and other auspicious animals imagined by Chinese people, have penetrated deeply into Japanese people’ heart, greatly enriched ideology and imagination of Japanese people and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ulture.
animals; ancient times;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K901.6
A
2095-2074(2018)02-0091-09
2017-12-13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4NDJC147YB);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教外司留[2014]1685)
董科,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日文化交流史、亚洲史研究。邮箱:ashikag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