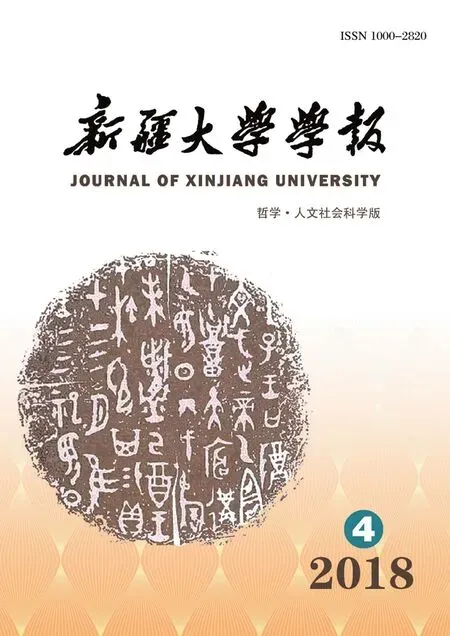清代西域诗对西域自然地理符号化书写的颠覆与重构*
唐彦临
(1.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乌鲁木齐830046;2.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西域山水自然以及物候特征是清代西域诗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这类诗章表现了诗人对西域自然环境的强烈感受。其书写的内容既根植于西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也根植于历史叙述中积淀的关于西域的种种感知与观念,历史叙述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它与诗人的个人心理一起,完成诗人对西域的书写。被感知的环境并非纯粹客观的环境,而是“过去人们眼中的、根据他们的文化爱好和文化偏见、由假设想象塑造的世界”[1]。“人类集团是带着固有文化进行环境知觉”[2]的,历史与文化规约着诗人身体与心理的限度,驱动着诗人看什么和怎样看的选择,也就是说,带着文化的眼光,诗人笔下的自然包容着特定的民族的或地域的道德、情感等形而上元素,文化语境使诗人的审美眼光中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丰富的预设的情怀。西域诗中对西域自然地理空间的书写,即是由诗人与他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共同完成的。参与西域自然景观书写的,不仅是亲历其地的诗人,还有其背负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内地形成的关于西域的认识。随着清代大量诗人因各种机缘亲历西域,对西域的认知渐次深入,西域诗不断打破固有文化所预设的秩序与界限,对西域自然空间的书写逐步剥离了想象的质素,呈现不断向客观性回归的趋势。
一、历史上各类书写中对西域自然地理空间的建构
由于西域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加之交通不便,导致历史上内地对西域认知的严重受限,各类史地著作对西域的重复性书写不断塑造并强化着人们的西域观念,这些著作递相沿袭,同时又缺乏实地体验与新的文化重构活动来丰富人们的西域认知,一些地理意象遂成为西域的文化标志物与符号象征。吴蔼宸先生在《历代西域诗钞·序》中,就明确表示其取舍西域诗的标准为:“推至篇中凡有‘天马'、‘天山'、‘塞庭'、‘瀚海'、‘沙碛'、‘玉关'、‘河源'等字者,皆认为西域之诗,其涉及地名者更无待论。”[3]撇开这一取舍依据的合理性不论,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及今,人们对西域的认知正是从这些特定的地理面貌和地名、事物开始的。在长期的文化建构过程中,这些物象被抽象、固化为西域文化符号,成为典型的文化标志物。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将九州以西的地理环境概括为“西被于流沙”[4];《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5]“流沙”成为上古时期中原人士对“九州”之外的地理面貌的总印象。从各类典籍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虽然对西域沙漠的认识模糊而混乱,但并无妨于“流沙是古人对西北广大沙漠地区的一个总概念”[6]的说法。除此而外,各类正史中的记载,也不断重绘着西域沙漠覆盖、景界荒凉的总印象,《史记·大宛列传》云:“宛国……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7]《汉书·西域传》云:“今县度之陀,……起皮山南……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8]3887《竹书纪年》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9]《周书·异域传》亦曰:“鄯善,古楼兰地,多沙卤。”[10]《魏书·西域传》则曰“西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11]等。《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直接记载西域地理环境的正史,于今看来,其描述之疏略不言而喻。然此后出现的各朝正史《西域传》几乎均未对其加以补充。虽然在汉代有关西域的记载中,已经多次提到西域的农业发展,但都难以抵挡沙漠作为西域的地标性印象。同时,史书中关于西域高寒的地貌特征的叙述,又加强了西域气候苦寒的印象。可以说,虽然史书中对西域自然地理物候的书写极其疏漏而简略,但其建构的西域地理观念却影响深远。
史书而外,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西域也逐渐成为文学书写的表达对象,西域的景观如山川、沙漠、植被、物产乃至气候特征等自然风貌,以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出现在各个时代的文学之中。按照美国学者马克·第尼亚的说法,自然与文化间的关系是一个“从‘自然的文化化'到‘文化的自然化'的永不停滞的发展过程。”[12]西域作为特殊的地域,也在文学书写中不断经历着“自然的文化化”的过程。从历史上不同文本对西域的书写来看,西域的荒凉、苦寒等印象是在重复的书写中被不断强化并最终固化为西域印象的符号的。汉《郊祀歌》中相传为汉武帝所做的《天马》就将沙漠作为表现对象:“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李陵歌》则唱:“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其中流沙西极的描写,是中原人对西域地域自然景观的最直观、最深刻、最典型的印象,对流沙的征服象喻着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及对相关地域的征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西域诗歌发展的重要的时期。其诗歌中着重书写的,也是集中于茫茫瀚海、戈壁风沙,崔嵬雪山、云沉天暗等具有壮美风格的典型地理意象,出现频率较高的有“风”、“沙”、“雪”“霜”、“寒”、“苦”等,其色调偏于黄、灰、白的冷色系,“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风暗无色,霜旗冻不翻。”(虞世南《出塞》)“黄云断春色,画角起边愁。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王维《送平澹然判官》)“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王翰《凉州词》)“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等。边塞诗人中的翘楚岑参两入西域,他对西域自然空间的描绘更为具体化,写荒漠风沙则“风头如刀面如割”、“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写荒凉则“日暮上北楼,杀气凝不开。大荒无鸟飞,但见白龙塠”(《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写寒则“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岑诗以其充满惊异的情感震撼力,不仅在内地人心目中普及了西域的物候知识,还进一步强化了西域肃杀萧瑟的环境氛围。“风”、“沙”、“雪”、“寒”等意象的高频率出现,进一步促成了西域特定地域符号的定格。由于岑参在西域诗人中尊崇的地位与深远影响,人们往往忽视了以“好奇”著称的岑参对西域自然空间的表达其实是呈现着鲜明的情感化偏向与选择性忽视的。
宋代版图不涉西域,鲜有亲历西域者,著名诗人陆游仅凭想象借用几个西域地理文化符号便创作出典型的西域诗,如“平沙风急卷寒蓬,天似穹庐月如水。”(《焉耆行》)、“明月如霜照白骨,恶风卷地吹黄沙”(《塞下曲》)。元代耶律楚材对西域的描写呈现出一定的客观化倾向,奈何由于元代诗歌总体成就的限制,能关注其诗的少之又少,影响十分有限。明代闭关而治,其统治范围最远到哈密,与西域的交往几乎隔绝,西域对这一时代的诗人来说已沦为陌生的异域,他们对西域的了解只能依靠不多的前代典籍中的表述,因此,其西域诗更突出地表现为西域地域意象的密集使用:“黄沙断碛千回转,玉关渐近长安远。轮台霜重角声寒,蒲海风高弓力软。”(曾棨《陈员郎奉使西域周寺副席中道别长句》)、“轮台雪满逢人少,蒲海霜空见雁稀”(王希范《送陈员外使西域》),“黄沙古迹行行见,白草寒云处处同”(胡若思《送陈员外子鲁奉使西域》),这些诗文的反复强调,进一步形成了西域荒凉冷落的刻板印象,西域丰富多样的地理气候样貌从而被遮蔽了。
二、清代西域诗中对西域自然地理空间的重新认知
与其它历史时期不同,清代诗人对西域的认知,除主观性与文化因素之外,明显具有了更为浓厚的客观性。将新疆划分为南北两域的天山,同时也带来了气候上的变化。天山以北气候虽然寒冷、干燥,但发源于天山的玛纳斯河、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伊犁河等,却浇灌并连接了一片片稷黍离离、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天山以南虽有塔克拉玛干沙漠,但由于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几条巨川的浸润,在其四周边缘形成了可田可溉、绿树蓊郁的绿洲沃壤。绿洲之中田园阡陌,村镇相望,颇有“十里桃花万杨柳”的旖旎风光。这样的自然景观,显然颠覆了初踏西域的清代诗人以往在书本中获得的对西域自然的总印象,对其心理形成了极大的震撼,许多诗人在其诗作中重现了这一印象被彻底颠覆的过程,如在出哈密后两站之路的松树塘,千松矗立,翁郁葱茏,与此前经过的戈壁荒沙的景致大相径庭,因而给行经之人留下了深刻的感受:“待过松塘风景异,淡烟细雨动乡情。”(黄濬《过天山仍次前韵》)“平原草长绿无际,远岫松明青有痕。满眼风光都入画,动人乡思欲销魂。”(杨炳堃《出得胜关抵松树塘》)这些明丽清新、绿意盎然的自然景观,不约而同地让诗人兴起了乡思之情,勾起了诗人对家乡的眷恋。被自然景物异化了的西域,如今由于景色上与内地的相似性而获得了诗人心理上的某种认同,正是这种亲身的经历,使清代诗人在西域的自然空间书写中打破了对西域自然景观描写的符号化模式,在诗歌中逐步恢复了西域多样化的自然景观样貌。
清代西域诗人,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还有意反拨以往书本中对西域的错误认知,对“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反驳就是其中之一。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以其震撼心灵的边塞愁怨与悲壮、苍凉的情感境界,传播甚广,成为内地人对西域认知的生动表达。“唐人把玉门关当作西北边塞的代名词,或说是边关的象征,或说是一个空间性意象。春天杨柳不绿,是玉门关外广大西北地区的特殊物候。”[13]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中对此二句的解释,更在自然景色的凄冷之外揭示出诗句背后所隐匿的出关后人们心灵中的被放逐感:“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14]当然,在唐代与王之涣有同样认识的不在少数:
匈奴几万里,春至不知来。(卢照邻(《梅花落》)
胡地无花草,春来不似春。(东方虬《昭君怨》)
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来无春。(柳中庸《凉州曲》)
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
类似吟咏的重复出现显示出古人对西域认知上的偏见,岑参在未到北庭之前,也有“春风曾不到,汉使亦应稀”(《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诗句。早在战国时代,中原人就已经在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天下”的观念。在他们的想象中,自己所在的地方既是世界中心,也是文明中心,在四边向外不断的延伸过程中,越靠近外缘,就越加荒芜,同时伴随着低等的文明。唐王朝的强大更加剧了唐人睥睨四方、君临万国的心理意识。尽管张骞、班超之后,亲历西域的人不在少数,对西域风土也多有撰述,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就对西域三十六国有详尽的描述,但是,习惯于从古典文献中接受知识的中国士人,对西域的想象仍然来自于对古典的揣摩和理解。《史记》、《汉书》这样的历史著作,因其记载以“历史”的名义而享有“真实”的质素,因而其文字被当作严谨的事实而忽视了这是文史不分时代的作品。如班超“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表述,从此将玉门关符号化为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在想象天下的思想史上,汉唐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多少平等的意识,‘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仍然支配着所有人对世界的想象。”[15]习惯于认同早期的华夏边界的唐人,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吟唱中昭示着来自中心对边缘的认识,显示了内地相对于偏远地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上述偏见在清代大量的诗人进入西域之后得到了校正,许多诗人不仅抒写了大量吟咏西域春光的诗篇,还在诗歌中直接反驳王之涣的《凉州词》:
春风早度玉关外,始悟旗亭唱者非。(国梁《郊外》)
极边自古无人到,便说春风不度关。(萨迎阿《用凉州词元韵》)
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度玉门关。(邓廷桢《回疆凯歌》)
应同笛里边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萧雄《西疆杂戍诗·草木》)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杨昌浚《恭颂左公西行甘棠》)
见说玉门春似海,不教三叠唱阳关。(徐步云《新疆纪胜诗》其二)
天路已週星宿海,春风终度玉门关。(陈寅《伊犁漫兴》其二)
这几首诗或直指《凉州词》的错谬,或推论错谬产生的原因,或以眼见桃红柳绿的盎然春景暗指“春风不度”的荒唐。萧雄与杨昌浚的诗歌则旨在歌颂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命将士广种杨柳,遂使沿途风景产生了“骎骎乎蔚然深秀”[16](诗注)的变化。“春风吹度玉门关”,不仅指自然之春的到来,也暗示了在驱逐了阿古柏的侵略之后,西域百姓获得了安定的生活。
中国在经历了唐宋等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后,留给清人的诗歌成长余地并不多,“翻案”成为清人避免雷同、显示独特新鲜立意的重要方式,虽然在清人看来“诗贵翻案”[17],然这里对王之涣诗句的翻新不能单纯地归于逆向思维意识的引导,更重要的是客观实践的结果与时代精神使然。亲历西域终于使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化上的心理优越感,学会以较为平等、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西域,逐渐消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西域的成见。
三、清代西域诗中秀丽风光与静谧田园的大量呈现
西域自然地理意象符号,多以粗犷、雄奇的外在形态显现壮美的风格,与建功边塞、一统天下的军旅悲苦生活相适应。亲历西域,行经戈壁风沙之时,诗人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脆弱和精神极度的紧张,一旦跨过这一特殊区域,天山南北秀丽的自然风光就使诗人的精神痛苦得以缓解。清代西域诗人对自然风光秀美特质描写的比重大大增加,以山为例,虽然俊迈、朗健的天山往往开启诗人崇高政治情怀的表达,而一些秀丽独特的小山峰,也往往“别开生面目”,引发诗人心灵对山水的贴近,因而常以秀美、圆润之笔触,来描绘它们的可爱,如:
沙路随山转,雄奇仰巨观。别开生面目,无数小峰峦。翠吐青莲瘦,烟凝玉笛寒。欲移屏障里,留作画图看。(祁韵士《晚过大河沿,南山极雄峻,其西忽见小山耸翠,一一秀削可爱,记之以诗》)
伊犁门户属三台,果子沟中图画开。青耸层峦峰断续,碧盤曲涧水萦回。参天柏秀和雪种(时树底雪未消),匝地花繁斗锦裁。巧助羁人归去乐,出山犹记入山来。(杨廷理《将抵松树头口占》)
与之相应,在这些诗人的笔下,西域的自然景观不再仅仅是雄阔而粗豪的,大量诗人选择表现西域地理空间中秀美清丽的侧面,如:
五月轮台路,花香蝶满衣。树深山鹊喜,沙暖雪鸡肥。霞鸟连红落,岚虹夹翠飞。结庐好烟景,漠外欲忘归。(方希孟《三台道中》)
草际飞湍洒,源通九曲溪。野花红似锦,寒菜绿成畦。忽动濠梁想,忘将笔砚携。尘心挑不起,鸟语夕阳西。(金德荣《水磨泉诗》)
穷荒谁得到,绝域我言归。野草湿晨露,边风吹客衣。雨酣新树碧,山霁远烟微,第一程堪纪,邮亭恋落辉。(颜检《至古牧地》)
侵晨新雨湿花茵,遣兴平畴学垫巾。嫩绿才匀边外柳,软红轻浥陌头尘。寻芳到处堪游目,作客何人不惜春。绝域漫惭空老大,天心万里惜孤臣。(毓奇《玉古尔察道中遣兴》)
雨丝风片洒郊埛,染出平芜一带青。泥泞细粘宛马足,溟濛轻湿水鸥翎。烟笼弱柳娇犹滴,路入深山梦已醒。百里相寻缘惜别,感君车笠话曾经。(杨廷理《雨中赴黄渠,别纳中峰元戎》)
这些描绘带有浓郁的江南色调的轻柔细巧,显得纤细敏感,若非诗歌标题或具体地名的提示,很难判断其描写的是西域风光,从而使人在西域的壮美之外又增添了秀美的审美感官体验。
“边方奇境须亲领,跋涉无嫌心力烦。”(颜检《过雪达坂》)这是清代诗人面对关于西域的历史知识与眼前实景的肺腑之言。与为迎合读者阅读期待的唐代边塞诗相比,亲历西域的诗人在诗歌描绘的主题方面对读者来说或许由于过于熟知而缺乏视觉与心灵上的震撼力,但这类对西域清新明秀景致的歌颂在西域诗歌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前代的边塞诗人们注重的是发掘文化的“异”质特征,因而其在诗歌中强调的是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特征,人为地夸大了西域与中原的差别。而这类诗歌的出现,是诗人摆脱了对西域认识的历史的、书本的经验,以写实的笔触,即景抒情,有意识地消除边地的隔膜感,展示出西域风光的另一面貌。其诗歌中常常出现的语汇如“花繁”、“夹翠”、“绿畦”、“鸟语”、“新绿”、“茂林”、“烟村”等,正是诗歌中常用的描绘内地自然景观尤其是江南景观常用的语汇。如果说清以前的诗人更多用求“异”的眼光来看待西域,而清代的诗人则开始摆脱这种思维模式,转而以求“同”的心理对待西域。在他们的诗歌中,西域的异域色彩日渐淡化,逐渐成为清代大一统王朝中的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欣赏这类风景时,常常将之与中原乃至江南的风景相比附,这一写法本身显示了诗人对西域心理上的认同,他们摒弃了对西域陌生化的抒写,熟识的景致安慰了他们躁动的心灵。在长途旅程或者长期的流放生活中,这种具有熟知而亲近的特征的自然使他们获得了优游的心态,以自由的心灵与审美的眼光去面对自然山水,因而在西域诗中呈现出了许多前人不曾注意或者故意忽略的审美特质:
漠暖百花红,禽声细雨中。海光飞白马,山气吐黄虹。麦露浮晴野,松云幂晚空。疏林隔渔火,几处似江东。(方希孟《巴里坤野宿》)
闻道斜沟胜,今来路欲迷。苍龙一径转,翠黛万山齐。古树根成石,清泉流作溪。小桥廻合处,疑在胜湖西。(陈寅《过果子沟》)
萧萧风雨夏犹寒,红上枝头绿半酣。醉里不知身万里,落花时节在江南。(史善长《对雨》)
一道湍流木垒河,人家两岸枕坡陀。望中谢墅青山在,踏去苏堤绿草多。(黄濬《木垒烟岚》)
天山积雪冻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铁保《哈密》二首之一)
玉翠垂杨叶,鹅黄细柳花。春风连夜雨,芳草遍天涯。紫燕双棲屋,红妆万里家。赏心新景丽,浑似到京华。(萨迎阿《乌什自志四首》其一)
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中,南北两地的审美风格与审美对象常常以对立的方式呈现,南重阴柔,北重阳刚,以农业文明的自然背景在内地诗人的审美意识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有趣的是,在这远隔万里的边塞异域,诗人不仅发现了戈壁荒沙等隶属于游牧民族的异类景观,同时也发现了溪桥流水、远烟新绿这样熟悉的自然风景。这些自然风景唤起了诗人对家园的记忆,抚慰了诗人置身异域而感受到的疏离陌生之感,诗人的心灵得到了安放与休憩之所。在他们心目中,西域并非一个截然的“异”类世界,这里同样可以找到归宿感与安全感。“关河限中外,风土未全殊。”(陈庭学《昌吉县》)、“乱日边疆今日治,异乡花鸟故乡同”,(萨迎阿《晚步后园即景》其一)这些诗句更是以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对西域的认识之变化。
除此而外,诗人还发现了西域田园风光的和平安宁之美。自《乌孙公主歌》中:“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唱出了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为西域贴上了游牧的标签。实际上,西域不仅适于游牧,而且许多地方泉甘土肥,十分宜于农业生产。《汉书·西域传》中对西域农业生产的情况多有记载,如:“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8]3879从当代许多考古发现也可以看到古代西域农作物的丰富[18]。清以前的边塞诗书写中,戈壁风沙渲染的壮美风格与山水田园构筑的宁静优美的美学境界标注着书写的两极。大漠书写的豪迈、悲壮阐释着极富使命感的外向的建功立业、戍边卫国的社会心理,而山水田园相比而言体现的是潜沉于内的更为私密化的个人情趣,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很少在边塞诗中获得统一。然而由于清代诗人内敛的个性和时代中重实风气的影响,加之清王朝自收复西域之初,即在这里施行的“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经营方略,因此,清代西域诗与前代的一大不同即是田园风光的书写大量呈现:
草莱弥漫麦苗匀,菜圃瓜畦入望新。柳荫垂街青漠漠,渠流绕郭碧粼粼。居民不改天方俗,丰乐无殊内地人。更向番王城畔过,林溪明媚景常春。(祁韵士《抵哈密》)
村落如棋布,炊烟屋上斜。耕田多服马,戽水不悬车。错壤平宜余,衡门半种瓜。停骖揖老叟,暂与话桑麻。(李銮宣《哈密四首》其四)
几处回庄隔短藩,深山始信有桃源。两行弱柳迎幽客,一带清溪抱碧园。流水纵横频欲枕,野花寂寞总无言。浓阴夏日欣游此,车马由他世外喧。(色桐岩《艾底尔回庄》)
稻草高于屋,泥垣白板扉。鸡豚过社少,牛马入秋肥。漠漠田千顷,阴阴木四围。此乡风景异,不见塞尘飞。(史善长《三台道上》)
暂息轮蹄处,边村落日斜。簷前栖怖鸽,树外听啼鸦。绕屋垂溪柳,当春放野花。此间有佳境,原不异中华。(颜检《长流水》)
杏花深处隐回村,遍引清渠绕四邻。淡淡绿阴嘶牧骑,喃喃紫燕迓征人。雨过香稻黄云湿,风飐春溪碧浪匀。多少旅情无限景,几曾辜负往来频。(毓奇《特尔格起克至特比斯道上口占》)
倡导人与自然的融洽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深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在向往建功立业的同时,在内心深处常将回归自然作为调适身心的重要方式。来到西域的诗人往往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和宦海风波,这时寄情山水田园表达了诗人超旷的人生态度与洒脱的生命境界,其背后有着丰富复杂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内蕴。同时,就边塞诗的书写传统而言,山水田园与大漠西域似乎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反差。相对于之前的西域诗,清代西域诗中这类诗歌的出现无疑显示了审美领域的拓展。从粗犷雄奇豪迈到宁静优美而素朴,这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意识在西域的延伸与拓展。唐代边塞诗的激昂中融入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体现出政治生活的“旨趣化”,而清代西域诗中的山水田园书写显示诗人更多地沉浸在自我的内心生活之中,书写着内心的和谐与宁静,更多地体现了个体自由意志与理性的升华。
结 语
清代西域诗自然景观的抒写呈现了与前代殊不相同的面貌,亲历其地大大丰富与提升了诗人们对于西域自然景观的认知,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西域观的限囿,传统中有关西域的文化符号的使用大大降低,这一状况意味着对汉唐两代文学书写中对西域景观的片面性凸显的消解,同时也意味着将西域视为他者的文化观念的消解,而这一变化,正是基于清代大一统背景下西域社会的安定和平以及西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客观存在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