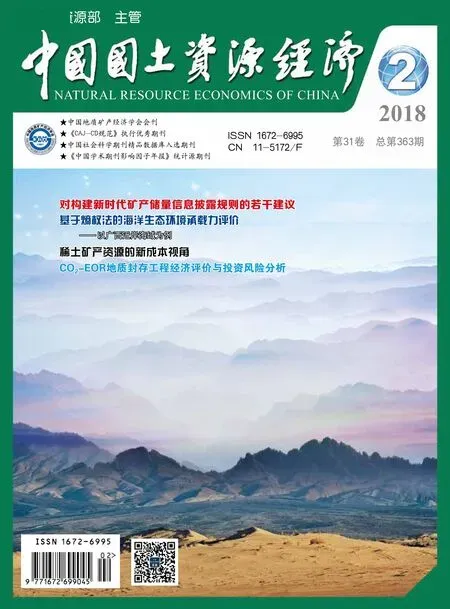稀土矿产资源的新成本视角
■ 刘虹桥/吴西顺
(1.巴黎政治大学,法国 巴黎 75005;2.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北京 100083;3.中国地质图书馆,北京 100083)
0 引言
稀土在现代工业中应用广泛,有“工业维生素”之称。进入21世纪后,与清洁技术和高新科技密切相关的永磁体、稀土合金、电池等产品的需求占比急剧增长,稀土被广泛用于与清洁技术和智能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产品,如智能手机、风力电机、储能电池、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等,用以提高产品性能,保障极端环境下的卓越表现。
已于2016年生效的《巴黎气候协议》设定了全球“去碳化”的发展目标,中国是最早加入该协定的国家之一。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夕发布“国家自主减排方案”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向世界郑重承诺削减化石能源使用,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1]。全球去碳化与绿色革命将推动全球清洁能源和节能储能领域的投资,钢铁行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行业也将迎来绿色革命。无论是风电机组还是电动汽车,都将迎来巨大的需求增长,而这些产业的发展都将转化为关键性的稀土原材料需求。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供应国,市场份额一度高达99% 。然而,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未为其赢得定价权;相反,这一战略资源以“白菜价”在市场上销售长达二十余年[2]。在2011年至2012年的价格波动之后,中国主要稀土企业深陷亏损,许多矿区停工。此外,由稀土黑市、过度开采、肆意排放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困扰中国稀土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目前,稀土开发造成的环境、健康和资源损失,主要由中央和各级政府承担;为推动稀土行业升级改造,国家和地方政府设立了专项发展基金。这些政府投入在某种程度上对稀土市场的低价形成了补贴。然而,此类补贴并非良性。为促进稀土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必要探讨稀土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原因,重新评估稀土定价,探讨可行方案,反映稀土的“真实成本”。
1 中国产量及份额的变化
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可以供应全部稀土元素的国家。国内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以不足全球23%的稀土资源储量供应了全球90%以上的稀土需求”[3]。而美国地质调查局(下称USGS)发布的同期数据显示,中国拥有全球36%的稀土储量[4]。
2010年,中国以12万吨的年产量供应了几乎整个全球稀土市场,相当于1994年稀土产量的三倍。当包揽了全球稀土市场92%供应量的中国宣告削减出口配额时,全球稀土市场立即陷入恐慌。此后五年,随着其他国家的稀土项目陆续投入使用,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的份额下降了7%,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
表面上看,全球稀土市场似乎终于摆脱了“中国时代”的绝对垄断,逐渐转向更为多元化的市场。实际上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2015年,中国凭借10.5万吨的年产量,占有全球85%的市场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所述的中国稀土全球市场份额下降的变化趋势是基于USGS的数据得出的,这与中国官方发布的稀土生产配额并不完全一致。USGS估计的中国历年生产量要远远高出中国官方允许生产的最大配额。2006年至2010年间,USGS报告的中国产量数据平均高出中国生产配额30%左右,2009年,差额达到最大,为36%。两组数据之间的差额,或许提供了一个评估“稀土黑市”规模的指标。
2 配额及国际贸易的裁定
中国曾为稀土行业发布了三套配额机制:国土资源部于2006年设立的“生产配额制”;工信部于2010年设立的“冶炼分离配额制”;由商务部发布的稀土出口配额(可追溯至2002年的稀土出口许可证制管理)。在WTO稀土争端败诉后,中国于2015年取消了稀土出口配额制度[5],但生产配额和冶炼分离配额沿用至今[6]。
从官方数据看,中国发布的稀土生产配额逐年上升,出口配额在波动中保持稳定。2008至2015年间,稀土生产配额从8.762万吨增加到10.5万吨。2016年,稀土生产配额与上一年持平。中国自2008年起开始大幅削减出口配额。2010年,稀土出口配额骤降至2.428万吨;2011年虽有上浮,但又在2012年降至2.0316万吨。2013年后,中国才将稀土出口配额恢复至3万吨。
2012年3月,美国经由WTO向中国提起磋商,欧盟、日本和加拿大随后加入。这些国家要求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中国就稀土、钨和钼出口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措施。上述国家认为,中国的做法不仅有违《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系世界贸易组织核心框架协议),也有违中国的《入世议定书》。
此次贸易争端的触发点是,中国于2010年削减了20%左右的稀土出口配额,直接导致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买家们担忧稀土供应中断,短时间内找不到替代来源,全球市场陷入恐慌,稀土价格随即飙升,镝(Dy)和钕(Nd)尤甚。连锁反应接踵而至:不少产品通过改变设计和制造工艺,削减特定稀土的使用量,一些产品甚至弃用稀土;中国之外的稀土探矿活动复苏,美国钼公司旗下的芒廷帕斯稀土矿结束了近十年的封存,重启开采[6]。
中方辩护说,上述争议措施是为保护国内自然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而设定的。中国政府强调,中国有权对稀土这种“可竭尽的自然资源”采取保护措施;并且,针对这些资源的保护政策,符合上述协定的例外条款。
2014年3月,WTO裁定中国败诉,要求中国取消有违WTO规则的稀土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2014年4月7日,中国就WTO裁定中的一些论证和相关证据提请上诉,但未挑战最终结论。2014年8月,WTO驳回了中国的上诉。据此,中国于2015年5月2日前取消了对企业出口稀土、钨、钼的贸易权管控措施,出口配额制度和出口关税亦相应取消。
重新开采稀土的美国钼公司的股票价格在2011年5月一度飙升至77.5美元[7]。在钼公司恢复生产后的五年时间,全球稀土供需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中国取消稀土配额制度并改革了稀土相关的资源税费制度。这使得中国稀土价格至少下跌15%~25%(仅考虑关税),进一步压缩了钼公司的利润。至2014年11月28日,美国钼公司的股价已跌破1美元。2015年6月,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宣布与其主要债务人重组17亿美金债务负担[8]。
钼公司“过山车式”的经历恰恰说明了稀土定价机制失效、国际市场失灵[9]。在后贸易争端时代,仍有许多遗留问题尚待解答:应由谁来承担稀土开采的环境代价?那些依赖中国稀土资源的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为何有些企业一方面宣传自身在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对稀土原料生产的环境影响视而不见?如果不能通过许可证和配额制度来管理稀土开采、加工和出口,又该采用怎样的治理机制呢?
3 国际价格偏低
在定价机制市场失灵的当下,稀土提取和加工的相关成本(包括符合环境标准的成本,满足技术要求和弥补负面健康影响)不由供应链上的公司支付,也不由稀土的个别最终用户如风力涡轮机或智能手机使用者来支付。价格计算中缺少的是战略和关键资源的稀缺性。轻稀土或重稀土早已列在欧盟委员会确定的二十种最关键的原料中。虽然稀土元素在地壳中的含量比金和银更丰富,但分布极不均匀,更重要的HREE非常难以在经济可行的水平上采矿(绝非目前的“白菜价格”)。中国以往环境监管不严,非法采矿猖獗。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和市场行动,体现稀土的“真正成本”,而单纯依赖于稀土的绿色技术和清洁未来的进展将是明显不可持续的。
定价失败使得机构投资者对稀土提取和加工业务的投资较少。具讽刺意味的是,2015年全球最大的两家稀土矿业公司申请破产,其中一家是Molycorp公司(下称“钼公司”,该公司在2015申请破产,后改组为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供应商。在中国,曾领先的稀土公司自2012年短期定价高峰期以来已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中国2010年处于主导地位,向全球市场提供了92%的稀土。然而,中国稀土工业的“真实成本”,从环境成本到职业病和公共卫生负担,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市场尚未得到适当的计算或讨论。2012年工业和信息部估计,过去二十年赣州市小规模稀土开采的清理和恢复成本大约380亿元(55亿美元)的账单,目前由中国的国库和地方财政支持[10]。尽管在过去二十年中,赣州是全球市场上中重稀土的主要来源地,但赣州的“稀土王国”在2015年仅占中国稀土总量提取率的8.6%。目前还不清楚其余90%的稀土产量在中国有多少是符合环保法规的,这对中国的环境保护来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负担,甚至可以说不应承受之重。
4 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
事实上,稀土在地壳中的含量比黄金和白银都丰富,稀土之所以“稀有”,主要是因为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矿床不多,而且开采过程复杂,又往往伴有严重的污染和毒性。“稀土”之名之所以沿用至今,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和环境成本高昂,长久以来难以找到可商业化的资源。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和低门槛的环境标准,在中国开采和加工稀土矿的成本远远低于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其它稀土资源丰富的国家。
在2013年的国际稀土年会上,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北方稀土集团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估计,国外重稀土的开采成本约在每吨20万元(约为3.4万美元)以上,远远高于中国[11]。据中国媒体报道,赣州市稀土开采的成本最低只需3万元左右,不过这个成本价并未涵盖资源税、许可证、第三方服务和其它费用[12]。中外重稀土生产成本相差悬殊,即便算上税费和合规成本,中国依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然而,这一成本优势,是以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居民健康为代价的。若能重新评估稀土开采与加工的环境成本,并通过资源税等经济调节手段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中国稀土的价格成本将大幅上升。市场价格越接近其真实价格,稀土的价格也将越高。
5 环境成本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后,中国几乎成为全球稀土市场上独当一面的资源供应国,一些稀土元素甚至只在中国生产。几乎所有的荧光灯,绝大多数的风力发电机、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DVD播放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子设备,都因产品中使用的稀土成分而携带着“中国开采”的基因。这些隐藏在产品背后的稀有金属元素,遍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稀土开采的环境代价惊人。工信部估计,仅在中重稀土主要产区、有着“稀土王国”美誉的江西赣州,修复无序稀土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就高达380亿元。此外,数以万计的居民饮用水源受到污染,千万亩农田受损。在“稀土之都”内蒙古包头,庞大的白云鄂博稀土尾矿库中,保守估计存有7万吨放射性元素钍。早年修建的尾矿库并没有防渗措施,有毒有害物质和放射性元素随污水、泥浆、粉尘,对周边村落造成严重的污染,甚至导致“癌症村”。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环境监管严格的国家,稀土开采加工行业同样没能有效解决与稀土开发相关的社会、政治和环境成本。有些国家就发生过严重的国内有毒物质泄漏事件,如美国的Mountain Pass矿山;还有些国家选择将有毒和放射性稀土处理活动转移到环境法规较为宽松的欠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公司Lynas将在本国开采的稀土矿运至马来西亚加工,并把有毒废弃物遗留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针对这些有毒废弃物的抗议声此起彼伏,民众呼吁关停加工厂。澳大利亚方面却无需顾虑有毒废弃物的处置问题。
稀土开采和生产加工链条上与生俱来的污染和毒性,是被掩盖的“不可忽视的真相”。据Hayes-Labruto等人的研究,每生产1吨稀土矿要产生6万立方米含盐酸的废气、200立方米含酸废水和1~1.4 吨放射性废弃物[14]。国务院发布的“稀土白皮书”也提到,每生产1吨稀土要产生2000吨有毒废物。稀土开采、冶炼、分离过程,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还会消耗大量的酸性物质和电力。另据《中国环境报》报导,赣州龙南县因稀土开采造成矿区下游黄沙、东江镇3万多人用水受到影响,4万余亩农田减产或绝收[15]。2013年环境监测信息显示,在中国最大的离子稀土矿区“龙南足洞稀土矿”,矿区周边地表水环境中的氨氮和总氮100%超标。其中,龙南渥江临塘流域氨氮和总氮最大超标倍数高达《地表水环境标准》规定的III类标准的295倍和358倍,濂江关西流域地表水最大超标倍数亦高达209倍和244倍[16]。
赣州稀土污染的380亿元环境修复账单比中国排名前五的稀土企业市值的四分之一还多。事实上,江西省的稀土生产配额只有全国总量的8.6%左右。如果充分考虑环境成本,稀土矿业公司的“经济可行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国家推行的“绿色稀土”战略顺利实施,那采购稀土原材料的下游科技产品必然将面临高涨的原材料成本。
6 终端产品价值
稀土市场的规模过小,以至于机构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未能给予它应得的关注。为打击稀土黑市、防治稀土污染,中国政府已将境内的稀土产业整合为六大集团。据工信部数据,2016年,全国稀土生产配额的99.9%都被分配给了这六大企业。除中国南方稀土集团,其余五家均为上市企业。2016年,五家上市企业获得的生产配额占到全国总量的74%,但总市值不过1540亿元。考虑到这五家上市企业还生产铝、钨等产品,中国稀土产业的实际市值应该低于六大集团的市值总量。
相较而言,用镝(Dy)、铽(Tb)、钇(Y)等稀土元素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的企业的市值就要大得多。以苹果公司和三星集团为例,二者市值分别为5215亿美元和1540亿美元。连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品牌小米的市值都达到了500亿美元。
以与全球去碳化直接相关的可再生能源风电为例。研究显示,一台典型的两兆瓦(2MW)风机里含有341~363公斤的钕(Nd)和59公斤左右的镝(Dy)。以此推演,2014年,中国已安装运行的0.96亿千瓦(96GW)风机约消耗1.64~1.75吨钕和2843吨镝。若中国在2015年至2020年间新增1亿千瓦(100GW)风电装机容量,则要额外消耗1.70~1.82吨的钕和2950吨的镝。需说明的是,这一保守估计并没有算上同期进行的风机维护、设备更新等所需消耗的稀土量。
2015年12月,国务院提出建设稀土产品追溯体系,为推动供应链管理奠定政策基础。然而,借助该追溯系统打造可持续、可追溯的全球稀土产业链,离不开下游消费国和商业社会的共同努力。丰田等汽车生产企业享用着电动汽车普锐斯带来的绿色形象,但受限于有限的信息披露和不透明的采购渠道,消费者无从获知该汽车产品采购稀土的来源是否合法,其资源生产、加工过程是否对当地社区造成环境损害或健康影响。
据联合国环境署(U N E P)和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于2016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全球环境犯罪的涉案值约为910~2580亿美元,比2014年的估值高出26%。这份报告将稀土与黄金、钻石一道列入“非法矿物采掘和贸易类环境犯罪”,其消极影响还包括资源流失、公众福祉损失和本国工业的原材料损失。
日本和美国这两大最主要的稀土进口国,为何对猖獗的走私行为充耳不闻?如果苹果、小米、三星等大品牌不采取行动,那么这些品牌的终端用户,即消费者,应有权获悉,他们是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促成了这条有毒的产业链的。电子信息通讯行业(ICT)的许多大品牌都已承诺,要从采购链中去除“冲突矿产”。那么,它们为何又对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健康毒害和发展问题视而不见?使用稀土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大品牌应该重新审视其稀土供应链,在保障原材料供应安全之外,着手关注隐藏在稀土供应链前段的“肮脏的秘密”。
考虑到公共资金和国家政策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各国也应重新评估其绿色战略。以德国为例,2014年,该国已经安装2.49万台风力发电机,这其中有多少稀土原材料来自黑市?如果稀土价格上涨、供应减少而替代技术方案尚未成熟,是否会导致未来新增风电装机的性能下降、效率降低,进而使得能源领域的绿色革命丧失吸引力?原材料风险只是表象,真正岌岌可危的是我们的绿色未来。
7 中国稀土产业升级改造
经过几十年的疯狂增长,中国稀土行业正在走向钢铁行业几十年前经历的国有化和集中化转型。毕竟,一旦政府通过政策调控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运营成本都将大幅度增加,只有大型国有企业能够在此低价市场中生存。这种转变可能有助于提高合规性能,并最终减少污染、终结黑市和非法开采。中央政府旨在将全国99.9%的稀土工业产能巩固为6个国有企业,这其中有5家企业已在中国大陆和/或香港上市。
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2号)。“十二五”期间,多部门联动,加速整治稀土行业乱象,打击非法黑市,严惩环境污染,加强资源保护,加速环保升级改造。仅环保改造投入,就达到80多亿元。进入“十三五”时期,稀土行业迎来有史以来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对稀土资源战略保护、规范生产秩序、化解过剩产能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如果中国全面贯彻最严格的环境标准,稀土原材料的售价势必将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而增长。目前看来,中国的稀土开采企业未来将不可避免地承担更多环境成本,但这些成本却未通过价格机制传递到购买和使用稀土的国际、国内相关产品。2016年,中国政府针对稀土产业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和发展计划,以加强稀土工业的管理,其中包括诸多综合指南。最新发布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体系、国家稀土采购和储存机制以及首个《稀土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力图降低20%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鼓励稀土回收和绿色应用的创新。最近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对污染者实行更严厉的惩罚,有望终结地方保护主义,强化执法,打击非法开采和稀土黑市。此外,国务院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2013年末发布的“气十条”、2015年4月发布的“水十条”,都将对稀土行业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全国性稀土采购和储存会议标志着,中央政府正在加快对战略原材料原产地和供应地的控制。
此外,国内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转型也意味着,中国或许无法像过去二十年那样满足国际市场对稀土原材料的需求。据国务院2012年发布的“稀土白皮书”,中国南方离子型稀土矿的储采比已由20年前的50降至15。换言之,若继续当前的年开采量,至2027年,中国已探明的离子型稀土矿将开采殆尽。届时,中国可能无法满足本国制造业升级转型和绿色发展的稀土需求,更别提庞大的国际市场了。
8 探讨
令人担忧的全球供应短缺问题,或将能够与环境成本一道,共同推动稀土价格的回升。早在各国达成《巴黎协定》之前,美国能源署、欧盟关键材料倡议组织、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等政府和政府间机构就已围绕稀土与绿色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等)进行多项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均预测,全球稀土需求将在未来持续增长;无论是轻稀土还是重稀土,都将在短期和中长期内面临供应短缺;目前仅由中国供应的少数稀土元素所面临的供应短缺风险更高。
鉴于稀土需求预计将在未来十年激增,需求和供应将出现巨大的不平衡,这将导致激烈的竞争和紧张局势。然而,稀土的战略价值和外部成本都没有反映在当前价格中。事实上,由于价格太过便宜,有人甚至将中国已经存在过量供应的稀土视为“洪水猛兽”。尽管其居于战略关键的位置,中国的稀土价格却非常低廉,稀土行业的利润远远无法弥补其环境成本及社会成本。
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稀土回收率不足1%,且以轻稀土为主,而智能手机等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中的重稀土元素回收率很低。如果能够从废旧电子产品、发动机、电池、荧光灯中回收稀土金属,那么既可以缓解供应不足的困境,还可以减少电子垃圾的环境毒害。这本是一举多得的做法,但恰是“工业维生素”特性使得回收异常困难。长期供过于求导致的“白菜价”,又使得回收利用无利润可言 。此外,缺乏政策支撑,使得循环经济的理念难以落地。
可叹的是,中国不仅要面对稀土开采加工带来的污染,还要处理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漂洋过海而来的“洋垃圾”。UNDOC(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每年约有800万吨“电子垃圾”通过走私渠道流向中国,价值达30亿美元,占东亚非法市场的八成左右。这些电子垃圾分解站多聚集在中国东南沿海和部分内陆省份的偏僻村镇,如以污染和癌症村而为众人所知的广东贵屿。当手机、iPad、平板电脑等象征科技和社会进步的智能设备以非法废弃物的身份来到中国,迎接它们的是肮脏而有毒害的“最后一程”。在这些通常是非法的小作坊里,电子垃圾的处理方式非常简单粗暴。从业者往往徒手拆解这些含有有毒有害化学品和金属原材料的废弃物,拆解过程还会使用额外的有毒有害化学品,对当地环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9 结语
中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经过几十年的不公平的价格待遇,是时候重新计算中国稀土的真实成本了。每一名消费者都应当为真正可持续的、清洁和低碳的绿色未来支付成本,站在价值链顶端的欧美发达国家更不能随意推卸责任。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启动退出国际环境公约的程序,这一趋势令人担忧。鉴于此,全球稀土市场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既保证资源价值被合理定价,又能体现环境成本、着眼于健康。
[1]程春育,宋伟,赵树良.巴黎气候大会“碳减排”对我国能源政策的启示[J].上海管理科学,2017,39(2):108-112.
[2]任咪娜,石畅,李一鹏.中国稀土缘何卖了“白菜价”?[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0-14(04).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EB/OL].(2012-06-20)[2017-11-28].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2/Document/1175421/1175421_1.htm.
[4]U.S.Geological Research.2012 Minerals Yearbook:Rare Earths[EB/OL].(2012-06)[2017-11-28].https://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mmodity/rare_earths/myb1-2012-raree.pdf.
[5]World Trade Organisation.Dispute Settlement(DS431)[EB/OL].(2015-05-20)[2017-11-28].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431_e.htm.
[6]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are Earth Elements:The Global Supply Ch6ain[R].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3.
[7]U.S Molycorp,Inc. Molycorp, Inc.Signs Restructuring Support Agreement With Key Creditors;Agreement Covers More Than 70% of 10% Secured Noteholders[N].U.S Molycorp,Inc.Molycorp,Inc,2015.
[8]U.S Wall Street Journal.Molycorp files for bankruptcy protection[N].2015-06-25.
[9]LIU Hongqiao. Rare Earth:Shades of Grey Can China continue to fuel global clean and smart future?[R].China Water Risk,2016.
[10]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国土资源部:稀土采矿证缩减出于环境保护考虑[EB/OL].(2012-9-27)[2017-11-28].http://www.gov.cn/jrzg/2012-09/27/content_2234627.htm.
[11]张忠.国外稀土资源开发现状以及对稀土产业发展的影响[J].稀土信息,2013(10):14-16.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发布会实录[R].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
[13]T.E GRAEDELL,E.M HARPER,N.T NASSAR,et al.Reck,On the materials basis of modern society[J].PNAS,112(20):6295-6300.
[14]LESLIE HAYES-LABRUTO, SIMON J.D SCHILLEBEECKX,et al.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hina's rare earths policies:Reframing the debate through a stakeholder lens[J].Energy Policy,2013(63):55-68.
[15]王奎庭.赣州稀土调查[N].中国环境报,2012-05-28(16).
[16]每经网.记者 于垚峰.赣州稀土整治“刮骨疗伤”价格上涨助推非法交易[EB/OL].(2012-05-03)[2017-11-28].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2-05-03/6514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