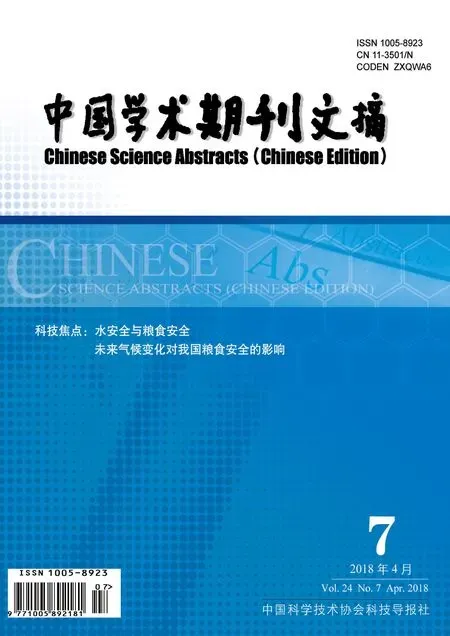“蓝色基本农田”:粮食安全保障与制度构想
韩立民 李大海 王波
一、引言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国务院于1998年颁布了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重新界定了基本农田的概念与范畴。自此,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成为中国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十几年以来,中国坚持和落实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耕地保护不仅要确保耕地的数量,而且要保证耕地的质量生态功能(曹瑞芬、张安录,2014),要实现对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全面管理。
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发展所秉承的基本原则,基本农田保护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政策制度、划定方法及保护技术等方面。关于基本农田保护的内涵,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强调基本农田的质量,即农田的生产能力。刘维新(2005)认为,只要基本农田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需求,避免遭受破坏,就达到了基本农田保护的目的。翟文侠、黄贤金(2005)则从生产利用的角度定义了以质量为核心的基本农田,突出强调其生产力特性。张沁文、许继光(1987)和聂庆华、包浩生(1999)认为,基本农田保护的核心内容是保存农田的生产力,必须保持其较高的土壤肥力与适宜的立地条件。张凤荣等(2005)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耕地占补平衡面临的问题,认为应将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重心向保持耕地生产能力平衡的方向转移,强调保持耕地质量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基本农田的数量,从耕地面积上保证耕地的粮食生产总能力,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些研究文献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分别以某些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区域耕地数量的变化,发现耕地总量都呈波动中下降的态势,并分析了其原因(例如许月卿、李秀彬,2001;梁俊花、马春燕,2008;杨朔、李世平,2013;邓楚雄等,2013)。李宗尧、杨桂山(2006)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安徽省沿长江地区的耕地变化情况,认为如果不对耕地加以保护,该地区的耕地总量将会持续减少,在中短期内将会影响粮食产量的提高,强调耕地数量的重要性。在基本农田保护政策方面,一些研究文献分析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局限性,认为国家仅从宏观层面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却忽视了农户在基本农田保护中的作用(例如周建春,2005;郭春华,2005;汤建东、梁山然,2005;陈美球等,2005)。刘彦随、乔陆印(2014)认为,中国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并未达到其预期目标,应从耕地保护政策、财政扶持、监督管理等方面加以改进。吴胜利(2012)分析了中国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认为应从耕地保护主体的权益、监管机制等方面完善基本农田保护补偿的法律规制。吴次芳、谭永忠(2002)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耕地保护的关键因素,并分别从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等层面分析了制度缺陷对耕地保护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从分级管理、经济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对基本农田保护进行了专门研究(例如王万茂、李边疆,2006;臧俊梅等,2006;段鹏飞等,2006)。在基本农田划定方面,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法与技术。许福涛(2005)从农田质量的角度,主张以“3S”技术为手段建立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耕地的动态监控;而钟太洋等(2006)从基本农田数量的角度,提出了区域人均基本农田需求面积测算模型,预测某一区域内基本农田的数量;钱蠢等(2006)、刘霈珈等(2015)则运用GIS技术及空间分析方法获取基本农田的数据,并进行了相关分析与评价;聂艳等(2013)运用景观破碎度指数以及空间聚类等方法探讨了耕地入选基本农田的过程,提出了基于土地评价和空间聚类划定基本农田的新方法。
在国外相关研究中,缺少具体针对基本农田保护的研究,大多是将其纳入农地保护的范畴。关于农地保护的内涵与目的,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重视土地的质量与数量。Shoshany和Goldshleger(2002)以以色列为例,研究了农地保护的原因以及保持一定数量农地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农地保护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农地保护就是对土地等资源与环境的保护。Duke和Aull-Hyde(2002)通过对美国特拉华州的实地调查,发现保持农业生产方式、保护相关资源(例如水资源)质量等是进行农地保护的最重要原因。在农地保护的主体方面,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农地保护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然而,Rosenbeiger(1998)认为,农地保护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还应该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农地保护协会。Kline 和 Wichelns(1998)则进一步论述了私人农地保护协会在农地保护过程中与政府机构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在农地划分方面,国外通常采用4种标准,即土质、环境意义、区域重要性和区位,这些标准往往是通过公众投票来决定的。Deaton等(2003)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农地等级划分与公众对农地保护支持态度的关系,分析了何种农地划分方式及标准更能够获得公众对农地保护的支持。Cynthia和Daniel (2003)则具体阐释了美国农地划分的过程,认为农地划分前的调查、听证、投票表决等程序是至关重要的。
国内外对基本农田(农地)保护制度的研究,为中国粮食安全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有益的经验借鉴。认真梳理相关文献资料,不难发现,现有研究都将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放在陆地上,却忽视了海洋这个更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食物供给系统。海水养殖业属于“蓝色农业”养殖海域是“蓝色农田”。经测算,中国居民从海洋水产品中摄入的蛋白质已经占到动物蛋白质摄入总量的大约10%(韩立民、李大海,2015)。相对于陆地“种植+养殖”的肉类生产模式,海洋生产动物性食物的空间优势、资源优势和产出效率优势十分突出,以海水养殖为代表的蓝色农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受资源环境质量下降、产业用海竞争、技术成本大且风险高等因素影响,中国海水养殖面临着“近岸趋于饱和,离岸开发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借鉴耕地保护中行之有效的基本农田制度,以养殖海域保护和结构优化为主要目标,在海洋建立并完善“蓝色基本农田”制度,有利于缓解中国食物生产中的总体资源环境压力,通过陆海统筹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主要阐释养殖海域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第三部分分析建立“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必要性;第四部分提出建立“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基本构想;第五部分阐述推行“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政策保障。
二、重视养殖海域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 km长的漫长海岸线、300万km2的管辖海域,所辖海域跨越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3个气候带,自然条件复杂多样,海洋生物物种十分丰富,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海水养殖的主要产品是动物性食物。这种生产模式较种植词料粮生产肉类的陆地“种植+养殖”生产模式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营养转化效率。在当前陆地资源紧张且生态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的形势下,保护和扩大海水养殖生产能力,对于缓解现阶段由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增长带来的粮食 安全压力,具有更加直接和显著的作用。
第一,海水贝类养殖无需投喂饲料,发展这类海水养殖相当于提高了海洋的食物净产出。2014年,中国海水贝类养殖产量1316.6万t,占海水养殖总产量的81.68%;养殖面积2295.6万亩,占总面积的70.3%。按贝类可食用部分占总重量的40%计,中国海水养殖贝类可食用部分重量约527万t,占海水养殖可食用部分重量的74.9%。就提供动物性食物及营养的数量而言,以猪肉作为肉类的代表性品种,按每生产1 kg猪肉消耗4 kg原粮计算,并且粮食平均单产取2014年中国实际数值(粮食总产量6.07亿t,播种面积16.9亿亩,单产为359 kg/亩),则每开发1亩贝类养殖养殖,就相当于开辟2.5亩耕地。2014年,中国仅贝类养殖就相当于增加耕地5800万亩,并由此节约灌溉水资源约174亿立方米,减少化肥使用量约174万t,减少牲畜粪便排放约5000万t。
第二,海水鱼类、甲壳类养殖需要投喂饲料,发展这类海水养殖相当于利用饲料水产品进口替代饲料粮进口,其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亦不应忽视。2014年,中国海水鱼类、甲壳类养殖产量262.3万t,占海水养殖总产量的16.3%;养殖面积579.23万亩,占总面积的17.7%。甲壳类与鱼类可食用部分分别按60%和70%计算,该两类产品的可食用部分重量合计为163万t,占海水养殖可食用部分重量的23.2%。所需饲料折算为低值海水鱼约800万t,其中约一半来自进口(鱼粉、鱼油等)经估算,中国海洋低值海水鱼捕捞产量约400万t;此外,如果中国海洋水产品得到充分加工,有望获得100万t加工副产品;两者相加,最多能够保障中国海水养殖饲料需求的2/3。未来中国海水鱼类和对虾养殖增产主要依靠国际渔业资源支撑。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年产300万t海水鱼类、甲壳类的养殖规模,这就相当于每年从国外进口相当于400万t低值饲料水产品。按照上文计算方法,与猪肉生产模式相比较,可替代约800万t饲料粮进口。
第三,发展海水养殖不存在占用耕地的问题,开发养殖海域相当于在海洋中开辟“蓝色农田”。中国陆地国土(特别是东部、中部地区)开发得比较充分,在天然湖泊、港汊、河道的水产养殖功能基本得到开发利用后,开挖鱼塘进行水产养殖往往与基本农田保护相冲突,使淡水养殖水面与耕地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竞争性开发关系。海水养殖主要位于海洋中的港湾、滩涂和浅水区域,开发养殖海域不会占用耕地,这是海水养殖开发与淡水养殖开发的一个显著区别。发展海水养殖相当于在陆地耕地系统之外再造一个新的食物生产系统。保护和扩大养殖海域,实质上是利用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可以缓解陆地的资源环境压力。
三、建立“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海水养殖规模居世界首位,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当前中国海水养殖发展中存在着空间格局失衡、资源环境退化、政策支持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海水养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蓝色基本农田”制度,加强对养殖海域的开发引导和保护。“蓝色基本农田”就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海洋水产品的需求,为确保基本的海水养殖空间,依据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沿海滩涂和近海水域。“建立‘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近岸开发饱和与离岸开发不足并存,产业空间格局有待优化。中国海水养殖绝大部分位于近岸海域。2014年,中国海水养殖面积230.5万hm2,其绝大部分位于10 m等深线以内的近岸海域。考虑到城市建设、港口航道等其他用途,近岸海水养殖发展受空间制约大,潜力有限。与之相对应的是,10 m等深线以外的离岸海域,除航行、捕捞作业占用外基本处于待开发状态,具有很大的海水养殖开发潜力。但是,目前由于成本、技术、风险等原因,除少量底播、深水网箱养殖外,离岸养殖海域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对此,需要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推动海水养殖从近岸向离岸发展,优化海水养殖空间格局,增强其发展后劲。
第二,空间环境制约日趋突出,发展后劲不足。近年来,中国沿海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第二第三产业开发利用的近岸海域面积不断增加,沿海城市的近岸海水养殖正呈现出快速萎缩的局面。以青岛市为例,2000年以来,由于城市滨海公园、港口、科研基地、临港工业区建设,市南区、崂山区、原黄岛区的养殖海域基本转为其他用途,即墨市、原胶南市的近岸养殖海域也被大量占用,使海水养殖规模和潜力均受到较大影响。除受空间制约外,环境恶化对海水养殖的影响不断显现。近岸海域污染持续加重,部分海域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赤潮、绿潮(浒苔等)发生频率增大,增加了海水养殖经营风险。因此,有必要集中连片规划海水养殖区,通过配套实施空间保护和环境改善政策,强化海域的食物生产主体功能。
第三,由于未纳入国家粮食安全总体战略,政策支持不到位。新形势下,保护和挖掘海水养殖利用海洋资源直接生产动物性食物的潜力,陆海统筹规划和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应当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政策设计的重要思路。但是,受长期以来一直将水产品定位为副食品观念的影响,目前的中国粮食安全政策过度着眼于耕地,忽视了养殖海域同样具有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一些沿海省份在执行耕地“占补平衡”的过程中,利用沿海滩涂、浅海养殖区围垦耕地。一方面,这些“新围垦耕地”丧失了海水养殖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土壤洗盐淡化周期长、成本高,以及耕种收益低等原因,出现了大片“新围垦耕地”撂荒、农田基础设施闲置损坏的现象。以沿海某县为例,该县在2010—2012年投资3.5亿元,按照耕地“占补平衡”的要求围海滩涂垦造耕地1万余亩,目前全部处于撂荒闲置状态。这显然与基本农田的政策设计初衷背道而驰。如果从陆海统筹的角度进行“基本农田”设计,允许通过开辟海水养殖(特别是无需投喂饲料的贝类养殖)区的方式来实现“占补平衡”则可以兼顾国家粮食安全、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多重目标,使基本农田制度设计更加优化。
四、建立“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基本构想
以充分挖掘和保护海洋的食物生产功能、保持和扩大海洋的食物生产能力为主要目标,比照现行基本农田政策,设计并实施“蓝色基本农田”制度,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延伸到养殖海域,使基本农田制度覆盖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陆海统筹优化和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一)划定“红线”
所谓“耕地红线”是指经常进行耕种的土地面积最低值,是中国耕地保护制度中划定的不可突破的下限。在“蓝色基本农田”制度设计中,也应划定类似的“红线”,从制度上保障海域的食物生产功能。现阶段中国海水养殖大部分属于近岸养殖。可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在现有养殖区内选择环境和細设施条件良好、与第二第三产业用海冲突小的集中连片海域初步划定近岸“蓝色基本农田”50万hm2,约占现有近岸海水养殖面积的20%。到2030年,近岸“蓝色基本农田”逐步扩展到100万hm2,约占届时近岸海 水养殖面积的50%。确保近岸海域基本的食物生产能力。
(二)离岸拓展
顺应海水养殖从近岸向离岸拓展的发展趋势,在现有养殖区以外(水深大于10 m左右、离岸超过1 km的开放式海域)划定离岸“蓝色基本农田”100万hm2。未来随着深水养殖技术和经营模式的成熟,离岸“蓝色基本农田”逐步扩大,到2030年拓展到500万hm2。
(三)政策引导
依托“蓝色基本农田”制度,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引导海水养殖集约化发展。主要实施路径是:在近岸海域,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环境、优化养殖模式等手段,提高海水养殖单位面积产量,实现对近岸海域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在离岸海域,通过加大投入和技术创新,发展以信息化、自动化、规模化为特点的设施养殖,以及以人工鱼礁建设和深水底播增殖为特征的海洋牧场。通过拓展蓝色产业发展空间,努力提升海洋空间的食物生产能力。
(四)陆海统筹
通过陆海统筹优化“基本农田”制度,在保持全国耕地(基本农田)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实现陆海基本农田的互补和衔接。对于沿海地区,可陆海统筹设计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对于利用海岸带和近海空间补偿耕地的,宜耕则耕、宜渔则渔,适当尝试以“蓝色基本农田”补偿“基本农田”的制度创新。
如果“蓝色基本农田”制度得以推行,到2030年,以近岸海水养殖平均单产12 t/hm2(年均增长3%)、离岸海水养殖平均单产2 t/hm2计算,仅“蓝色基本农田”即可实现增产2200万t。结合其他海水养殖和远洋渔业增产,中国海洋动物性食物生产能力将较目前扩大3000万t,相当于减少6000万t饲料粮需求,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全国由于耕地资源不足形成的粮食产需缺口,相当于在海上新开发1.6亿亩耕地。通过陆海统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五、推行“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政策保障
(一)明确政策实施主体
由国土、农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组织实施。主要工作包括“蓝色基本农田”的规划、相关支持和保护政策的制定、与陆地基本农田政策的衔接等。沿海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蓝色基本农田”制度的落实和日常管理工作。
(二)认真做好中长期规划
一是要合理规划、科学布局,以现有海水养殖分布为基础,从各次产业海域使用的长期发展趋势出发,合理划定“蓝色基本农田”的范围,并适当预留拓展区和生态隔离空间。二是要做好与各级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规划的衔接,将“蓝色基本农田”制度切实落实到现行规划体系中。三是要推动“蓝色基本农田”制度法制化,根据实践发展的需求,逐步出台相关规章、条例,最终推动该项制度写入《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
(三)加强与“基本农田”制度的对接
按照陆海统筹的要求,实现与陆地“基本农田”制度的衔接,是“蓝色基本农田”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是要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考量入手,在科学评估陆地和海洋两大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科学谋划食物供给的总体布局,并根据资源、环境、技术的发展变化逐步调整。二是建立陆海“基本农田”补偿制度。对于有条件的沿海地区,可将目前耕地保护“占补平衡”政策延伸到海洋,推进陆海基本农田之间的“占补平衡”允许以“蓝色农田”开发补偿被占用的耕地,最终目的是以资源环境消耗最小化来换取粮食安全保障程度最大化。
(四)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力度
综合运用税收、补贴、公共服务等政策手段,推动海洋食物生产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一是对“蓝色基本农田”减免海域使用金,降低开发成本,促进海洋食物开发从近岸海域向离岸海域延伸和转移。二是比照陆地“基本农田”加大对海域开发的补贴力度,对于人工鱼礁建设和深水网箱(或其他养殖设施)购置比照远洋渔船给予补贴,对于无需投喂饲料的海水贝类养殖参照粮食生产给予补贴。三是加大科技支持力度,设立重大工程专项,重点突破离岸设施化养殖以及近岸集约化养殖关键技术,形成较为完善的海水养殖技术体系。四是提供充足且良好的公共服务。开发海域信息库系统,提供满足生产需要的气象水文环境实时信息;建设离岸装备试验场,提供各类海水养殖设施及配套装备试验测试的基本服务。五是认真借鉴海洋捕捞业的发展经验,建立和完善海水养殖保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