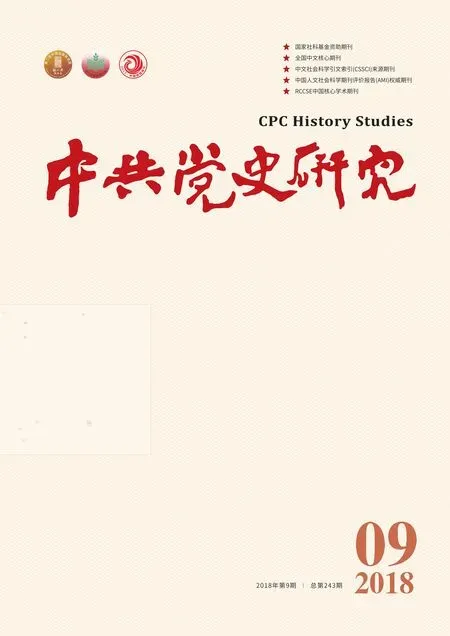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跨文化与地域”视野下知青史研究的新路径
丘 新 洋
一、对地域性知青史研究的反思
近些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基于地方档案的个案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诸多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史图景和地方性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与建构。学界之所以有此反思与突破,既得益于地方史料的新发现,又得益于学者们对现有研究模式不满而希望寻求一条理解当代史脉络新路径的努力。事实上,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知青史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想要有进一步的突破,除了应该做到从“走入知青”到“走出知青”外,还需要在地域性
①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知青史研究方面大做文章。
由于上层档案开放程度有限,加之早有定宜庄、刘小萌、潘鸣啸(Michel Bonnin)、伯恩斯坦(Thomas P.Bernstein)等人研究成果的珠玉在前,全国性知青史研究陷入低潮,相应地,地域性知青史的研究倾向却日趋明显。虽然地域性的个案研究极大细化和深化了知青史的内容,展现出全国各地知青运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它也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研究区域受到行政区划界线的规制。地域性知青史的个案研究多囿于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域,而忽视了一些边缘、交界地区客观存在的横向联系。其二,研究内容难以进一步拓宽或延伸。虽然学者们在知青下乡动因、回城安置、城乡关系、阅读经历、个人记忆、生产劳动、家庭婚姻、医疗卫生、教育学习等内容上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未能跳出知青史研究,展现人类历史中更为宏大的一面,如文化群体间的交流等。其三,研究成果同质化现象凸显,“尽管地区不一样,但关于知青运动的主题一样,政策的贯彻一样,形成的文献也类似,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也就难免‘千篇一律’”[注]易海涛:《资料·内容·理论方法:中国知青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由此可知,地域性知青史研究必须进行结构性和整体性的反思,比如,如何跳出知青史研究的范畴,以“文化地域”“社会移民”的角度将知青运动置于整个中国史乃至全球史的视域中去考察和理解?如何将地域性知青史研究的目光聚焦在边区地带和少数民族地区,在跨区域的视野下对比不同地区的知青运动,并对运动中乡村社会的经济、宗族等经典命题作一番探讨?
二、“他乡之客”:知青运动中的文化冲突
如果放在更为宏大的长时段中看,涉及上千万人的知青史又何尝不是一部人口移民史或文化交流史。人生而处于文化之中,并在社会交往中耳濡目染地习得和适应所处的文化。而中国自然、社会环境的极大差异使得各地城市、农村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形态。当城镇知青群体脱离长期生活的主体文化区域,以主体身份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客体文化区域时,便会因语言、风俗、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差异而产生不适应感,进而造成文化冲突。
笔者以为,知青运动中农民群体与知青群体的文化冲突是多元的,并在两个层面上得以体现:其一,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农村文化是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以农民为主体并建立在农村社区的文化,它是农民文化素质、价值观、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反映。然而随着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启动,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出现了较深的隔阂,所以当来自城镇的知青群体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群体相处时,两者便因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而发生冲突。比如,来自沿海城镇的女知青习惯在酷热的夏天下海游泳,而当她们在另外一种文化场景内仍穿着泳衣在水库或小溪游泳时,就与农村保守的思维观念发生了冲突。又如,知青对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表示不满,而农民则对知青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甚为反感,等等。其二,特定文化区域内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冲突。文化区域是具有同种或相似文化特征、生存方式的地理区划,其分布不以行政区划为界线,如客家文化区分布在闽粤赣边区,畲族文化区则主要集中于闽浙边区等。当外地知青进入特定文化区域时,文化冲突便会在语言风俗、宗族传统、婚姻观念等方面得以体现。其中语言最容易表现族群间的联系,特别是在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内,语言的巨大差异使得外地知青有种被围困、被隔绝的感觉。日常饮食和节日习俗上的文化冲突亦复如是,例如厦门人有在中秋节玩“博饼”的习俗,然而当这一做法被知青带入客家地区时,却被当地农民误解为赌博;又如,插队在山西农村的外地知青对当地婚礼上的“闹婚”习俗给予了抵制。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要关注知青运动中的文化冲突外,也要承认文化适应与文化融合的一面。比如,厦门知青积极主动地学习客家方言,福州知青在畲族地区插队时入乡随俗地尊重当地文化风俗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城镇知青在服饰、发式、婚恋观念、生产方式等方面对农村农民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杭州知青在建德山区插队时,周围的一些农村青年在穿着上、发式上也悄悄地学着他们的模样。
虽然文化冲突往往伴随着文化交融,但潘鸣啸对知青与农村关系的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文化上很难做到真正交融。事实上,知青群体之所以会有偷鸡摸狗、斗殴打架等“消极抵制行为”,文化冲突所造成的边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在以往解释相关行为的动机时常常被忽视。
文化冲突何以导致知青群体被边缘化?笔者浅见,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一方面,知青群体脱离了具有约束力的组织而成为“他乡之客”。知青群体是在城市、社区、学校的严格规训和家庭的监督约束下成长的,明确的组织关系使他们不敢有所逾越,而当他们进入农村社会时,这些外在的约束和规训便消失了。加之农村社会对知青群体缺乏强有力的管制,一些知青便游走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比如有人长年累月地在其他地区串联,拒绝下地干活,公社和大队干部对此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中复杂的宗族关系对文化不同的外来知青群体有一种排斥力。特别是在南方的山区农村,多山丘陵的地理形态使得血缘型家族村落得以赓续。虽然宗族势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社会革命中遭受严重打击,但其聚集的空间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破坏,甚至与此相关的传统民俗也还在农村地区延续着,所以作为“外来人”的知青群体是很难真正融入其中的,有不少知青甚至还卷入了村内复杂的宗族关系中,最终造成的伤害反而增大了知青群体对农村社会的离心力。虽然笔者认为文化冲突是导致知青群体出现消极抵制行为和逐渐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很多时候,口粮、工分、返城、安置等关乎切身利益的因素在农民和知青的冲突中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三、传统交流的延续:边区视域下的知青运动
地域性知青史的个案研究以省、市作为切入点,既易于操作又便于“解剖麻雀”,但对于一些特定区域,倘若仍以人为划定的行政界线来研究,便会忽视行政界线之外的客观联系,误将区域空间当作自足的封闭性实体。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研究中国帝国晚期城市时已注意到,区域系统的研究要摆脱传统的以行政单位为界线的方法[注]参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327—343页。。笔者以为,在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中亦当如此,所以除了继续拓宽和加深原有的地域性知青史研究外,还应该以“跨地域”的视野来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特定区域,如多个省份交界的边区地带和少数民族聚集地。
边区视角在对1949年以前历史的研究中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对革命根据地的考察往往围绕着闽粤赣、鄂豫皖、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进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加强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超越行政区划的边区模式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最近有研究成果表明,以边区视角展开研究仍具可行性[注]参见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例如,闽粤赣边区虽然被高山大岭割裂成三个互不统属的自然区域,但通过境内的赣江、汀江、梅江和众多支流,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商业贸易圈。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全国各地农村的商业贸易遭到强势挤压,农民也几乎丧失了迁移往来的自由。然而,一系列社会革命下的闽粤赣边区乡村社会依然延续着旧有的一些传统,即边区内的人口流动和商业往来常常大于边区外。比如在人口流动上,人口较为密集的粤东和闽西仍然会朝着较为稀疏的赣南迁移,具体来说,就是广东梅县地区的农民或前往赣南谋生,或嫁入赣南。当知青运动发生时,闽粤赣边区的知青亦被卷入上述迁徙趋势之中,如福建武平的厦门知青有时会前往赣州会昌串连,福建永定的厦门知青则会串连到隔壁的广东梅州,而他们所串联的路线与传统的商路几乎一致。
同时,人口流动促进了边区各地的经济往来。如广东地区的手工业者常到福建知青聚集地生产卫生香,制作桌椅,而靠近粤赣的福建知青也会参与边区经济生活中。由此可见,虽然50年代中期以来的统购统销已然成为国家政策,但是闽粤赣边区的商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依然继续着过去的商业传统,其中边区内的墟市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边区墟市的分布,正如施坚雅所言:“行政区划的边界很少与集市和贸易体系的边界相重合。”[注]〔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27页。比如,在福建武平的大禾地区,每逢三、八墟期,临近的江西永隆等地的村民都会前来赴墟。当然,除了边区的知青运动值得关注外,少数民族聚集地的知青运动亦应得到重视,比如上海、成都、北京等地的知青来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少福建知青在闽东的畲族乡村插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极为显著,加之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政策倾向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故而考察此类地区的知青运动是很有意义的。毋庸讳言,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及其政治影响对于任何地域都是决定性的,对知青运动而言亦是如此。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跨地域视角的知青史研究有利于发现行政区划之外常为人所忽视的历史存在,包括人际往来、人口交流和商业联系等。
总而言之,对边区地带和少数民族聚集地的跨地域研究为地域性知青史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之所以需要引入跨地域研究的方法,主要基于如下两个考虑:其一,跨地域知青史研究便于在各地区之间展开对比分析,比如闽粤赣边区三地虽均为客家文化区,但知青群体来源上的差异导致三地知青在婚姻家庭、生产生活、文化交融与冲突,乃至后知青时代的书写等方面都有着不一样的表现,通过对比分析,或可梳理出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性;其二,跨地域知青史研究跳出传统地域界线的框架,有利于注意到以往较少关注的边区地带和少数民族聚集地,还可以通过经济贸易、人口迁徙等问题重新审视革命与乡村、传统与变迁等经典话题,并分析知青群体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认为,地域性知青史研究若要有所突破,如下三点或许值得思考:
其一,应该从“走入知青”到“走出知青”,即以知青运动为研究对象,收集多重史料,在爬梳清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其放置于诸如地域文化、社会移民、文化冲突等更为宏大的议题中去讨论,进而与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文化冲突,乃至华人移民群体在其他国家遭遇的文化冲突进行学理上的对话,而非“就知青史谈知青史”。其二,应该适当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比如,关于知青运动中文化冲突和交融的材料是很难见于档案文件或报刊媒体的,正如曹锦清、张乐天在研究浙北乡村时所言:“文化既有其有形的因素,更多的却是无形的东西”,“纯依靠表格、问卷,并不能统计出无形但十分重要的文化因素;走马观花式的大面积走访虽能得到一些道听途说的表面浮浅的材料,我们却无法从中得到科学的结论。故而我们倾向于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注]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其三,应该在问题意识的导向下选择研究案例。地域性知青史研究在本质上属于个案研究,案例的选择应该在明确的问题意识引领下进行,即要搞清楚想解决什么问题,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要做到何种程度的突破,等等。反观近些年来的地域性知青史研究,虽然开创性地把一些从未探讨过的省、市、县作为研究案例,但因为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成果还是无法避免空泛、粗浅且趋于同质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