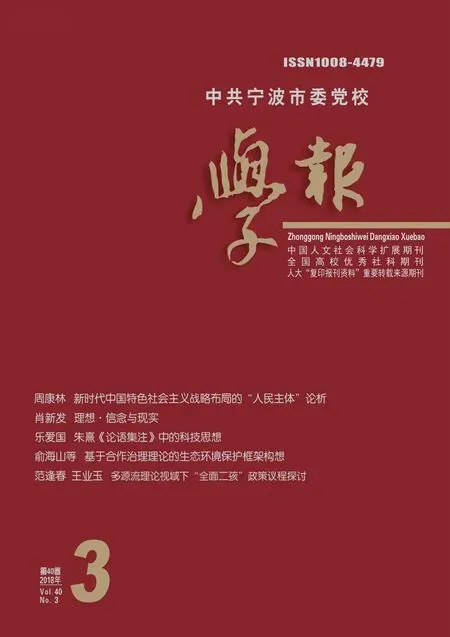宋明儒家对仁的本体化提升
——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例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0)
仁在先秦、汉初儒家那里,尽管并不缺乏高屋建瓴的本体论架构,如孟子、董仲舒之所为,但仍然保留着鲜活而浓厚的感性色彩。但自北宋开始,至有明一代,由于迎接佛教哲学挑战的迫切现实需要,在学习、吸收和消化佛教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新儒家们的理论兴趣主要集中在对心性、情理问题的探讨上,而不再笼统地泛泛而论所谓“爱人”了,孔孟仁学的基本主张、理想与要求悄悄地渗透或隐含在理学、心学的体系结构、概念观念和为学工夫之中,直接以仁为思想核心与主体内容,或者大力度、聚焦式、正面地议论仁的学者已属罕见。即便有所议论,也很少涉及仁之为德的因素,而多只侧重于仁之为道的方面,以性释仁,重视并褒扬性体道本,而直接排斥仁之中所包含的情的成分,进而,彻底扬弃了仁在原始儒家那里所具有的直观感性与心理学内容。
然而,因为能够不厌其烦地阐发仁的绝对性和超越性,更加凸显出仁之为道的可能与意义,所以,客观上又使仁既获得了一种可以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神圣力量,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本体论高度。这便成为宋明新儒论仁的一大鲜明的学术特色,无疑也应该是仁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向。
一、生之性便是仁
作为北宋道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濂学中的仁的观念可以直接追溯到他著名的《太极图说》。宇宙“自无极而为太极”之后,首先生出阴、阳两仪,而后,生出水、火、木、金、土五气,而后便历行四时。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水、火、木、金、土之“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由无极、太极而人极,先后有序,层次分明,特别是最后一个环节,人一出现,就伴随着中正仁义,可见,它们一定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立人之道,曰仁曰义”[1],有人在,人道就在。有人在,仁义就在。无极,指无形无象的物自身,一切存在者背后的本体境地。
太极,指人可见可感的现象世界的本源。而人极,则指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与法则规范。人极被安置在无极、太极之上,第一次为仁建立了无极的本体论基础。显然,这是周子对儒家仁学的一大突出贡献。仁与义就是由圣人首先发明并为人类确立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法则,作为“人极”,它们是人世生活最基本的规范法则,是人人都必须遵守与服从的绝对命令。“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2]尽管道、德、人,都是十分尊贵、非常难得的,但人活世间,真正最难得的却是修道德于一身。佛、道虽高妙玄奥,但无上者仍非儒家莫属,因为唯有儒家才能够真正面对残酷的生活世界,敢于对社会负责,积极担当起解决现实矛盾的重任。
虽然周敦颐也把仁理解为一种爱之德性,如“爱曰仁”[3],“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4],但是,真正构成周子仁学特色的乃是他以“生”对仁做出的一番别开生面而又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诠释。
“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
“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5]
仁是天的功能与特性,“人极”之中的仁,是天生化万物的德性在人际伦常生活中的必然反映,于是,天之仁也就是人之仁。天不生物,万物自生。仁由己出,属于内在本体之性。仁一旦形之于外,被人感知,则成为人人都得遵从的义。本体之仁尽管始终都在发挥对现象世界的决定作用,[6]但它自身却不为人所见,不为人所知,[7]所以只能称为“生”;而义则存在于人伦生活之中,可以为人们所经验和把握,所以应该称为“成”。
二、仁者,公也
沿着周敦颐的路线,程颢、程颐以“生之性”、“生意”、“生理”解释仁,认为仁来源于天道的生生之理而呈现于人心,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于此进一步将仁上升到心性本体的高度。程颐指出,仁者固然有四端、有博爱,但不能直接以“四端”、“博爱”为仁,因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8]。仁是性,爱是情。性是人的本体,而情则是本体的发用。仁是性体大本,爱则是性体的具体表出。所以,恻隐之心、博爱仍只是爱,仍属于一种原始化、情感性的心理反应,还不能达到仁所具有的本体高度。而“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皆中节,则无往而不善。”[9]仁是性,性即理,于是,仁则等同于理,理也不外于仁。可见,及至宋儒,仁之为德的因素与方面已经退居相当次要的位置了,甚至已被完全忽略,基本已被形上本体的追求所淹没。
以理释仁、以道解仁、合仁与道为一,也是二程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10]仁就是“理”,如果没有仁之理,人也始终只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物自身而已,与动物性存在无异。仁与人的统一,才可能有人道的出现。仁、理、心、天道都必须依靠并通过人心而实现,否则都是不可能的。一旦仁心发用,一旦人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仁性,或者天理落实在人的身上,那么,便形成了人道。在起源和基础上,天道、人道一体不二,仁与天道、人道不可拆分。所以,“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学道,则仁在其中矣。”[11]而“若论道,则万理皆具”[12]。于是,仁即道,即理,即性,仁之中蕴涵着善,仁是本体,善是现象,仁是善的来源与发端。如果一个人领会了道,那么,他也就能自然获得了仁,自然会做出善的事情来,仁与道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二程学说中的仁还可以与“公”相通。“仁者,公也。”又,“孔子之语仁以教人,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13]公是物自身的本体境地,不被人所感知,没有任何见分。“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14]人试图体验、领会公,于是便生发出仁心。“圣人致公,心尽天地万物之理,各得其分。”[15]“无纤毫私意”、“有少私意,便不是仁。”[16]致公、尽心、克除一己之私,则得尽万物之理,即已经达到了仁,回归于天地万物自身。从道体自身的本体论上观照,只有彻底克服了站在人自我立场上的成见、偏见、私欲、执着,才能真正达到物我一体、主客不分的仁性境地。
然而,二程的仁学思想最为特殊之处却在于开拓性地把仁诠释为万物的生生之理。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
“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使善也。”[17]
“‘生生之谓易’,生生之用则神也。”[18]
实际上,每一个物在生成自己、成为自己的一刹那间,其实就已经从道体仁性中秉承、分有了“万物一体”之“理”了,一物成,则一理具,没有时间先后,也没有空间距离。现象之中自有本体依据,它在现象生成的一瞬间即已经被赋予出去了。天地万物的基本功能或存在状态只在于生生不已,变化不息。然而,遗憾的是,物的生生状态总被人心实体化的思维方式、过强的联结力与想像力所遮蔽和淹没。
程颐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19]万物都具有一种生化、发生、生成、生产、生活的本能,物总是在自生、自在、自灭,一刻都不能停留下来。为每一个物自身都具有的那种自己为了自己、自己向着自己、自己生成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一如既往的动力与能力,就是仁。“‘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20]在程颢看来,万物最基本的存在状态就是不断地生出自己,成为自己。唯有生之意,才是物自身存在的最强烈、因而也最显著的特性与倾向。人不应该把自己只看做是一个孤立、渺小、可怜的存在,实际上,人也有伙伴,这个伙伴不仅包括自己的同类,而且还有看似静谧、肃穆的天地万物,因此在追求仁的工夫实践中,人也可以获得一种与自然同构、与万物为伍的心理体验,这就是“与天地参”的本体性超越。
人为什么最愿意观察并体验天地万物的生意呢?就是因为物的生意最能够代表仁的存在方式,生意就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天地万物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除开人世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万物的生,实际上就是人自己的生,人从万物的生生过程中,领会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本性,把握了自己的存在状态,进而,获得了与天地万物的绝对的、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参与和介入的大统一。物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物,甚至根本不必要分清谁是物、谁是自己,因为物、我已经回归本性,天人、主客、对象与自识的差异与界限已经消融,而不需要任何人为性质的“合”了。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21]仁即是物,而本体境地的物自身始终是浑沌无序的。仁是还没有进入人心意识的那个纯粹的物自身,在没有人心分别之前,仁、物、礼、义、智、信之间既可以说没有任何区别,也可以说彼此有巨大的区别,因为它们还没有被体认,它们彼此只是孤立的物,没有“之间”,没有关系,甚至连“它们”都不应该称呼,因为物自身永远只是单一的自己,而绝不可能有复数。仁的求证、确认与保持只有通过“诚”与“敬”来完成。唯有物自身对成为自己的执着、唯有物自身始终怀有专一的志向,它才能够达到自身的所是与所在。仁的状态下,任何认识论、工夫论意义上的努力与道德论的主体作为,如“防检”、“穷索”之类,都是多余的累赘。
而求仁的路径只在于“敬守”仁心。“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又,“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22]仁从己出,为仁由己,发明本心,即已见仁。内在之仁一旦发显于外,人所遭遇到的事事物物则都是仁的体现,都具有仁的因子与精气神,或都能够与本体之仁相一致。道与物、我与仁,并不是相与对峙、互有差异的存在。单纯的物自身不会意识到自己,禽兽显然有自我意识但却“不能推”,唯有人,才能够“通人、物”[23],即只有那种具备了反思、内省、察觉仁的能力的人类,才能够追求仁、达到仁。如果仁并不是由心而发出,那么,外在的天地万物与我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总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的主观之上、并始终存在于人们的自我意识之中。
但仁的实现还需要有一个由内而外、由己及物的推比过程。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24]
首先,儒家道德理想是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竭尽自己的仁心,真诚而忘我地推之于他人,推之于外物。以己及物、推己及人是君子行仁的两个基本方面。其次,程子的仁既可以是与万物为一体的宇宙本体,又是可以与恕并列的道德规范;既是本源性体,又是派生事物;既可以被理解为道德价值的主体自身,又可以被阐释为达到本体的工夫、方法。“忠”甚至也可以获得与仁同等重要的本体论地位。忠恕之道即是天理、人道。再次,行仁与行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方法论差异。为仁的基本路径是直接由自己内在本性而通达于万物自身。而为恕的基本路径则是把自己内在之仁推之于外在的客观对象,或别人,或他物。但在根本指向上,忠与恕相统一,由己与推己、天理与人道、本体与发用是一贯的。
三、心之德,爱之理
朱熹的仁学思想比较复杂,既有对周敦颐和二程的直接继承,又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发挥。朱子论仁,既涉及仁之为道的层面,又包括仁之为德的因素。朱子学中,仁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天地生物之心”与“理”两个方面。
在解释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时,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25]把发源于人心的仁予以本体论审视,就可以发现,原来它也是宇宙万物最基本的存在状态。世间万物因为来自于天,所以都必然以“天地生物之心”为一己之心,即自己的本性。于是,物自身一个最基本的属性与功能就是不断地生化出新的物自身,而所生化出的新的物自身又秉承了生化出新的物自身这一基本特性,代代相传,不断不绝。物自身的这一天然禀性非常真实地决定了它能够不断地创化自己、生成自己。人既然是人自身所生化出来的一物,当然也就赋予了生化不已的遗传能力与性格。于是,人“具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26]。而恻怛、慈爱一类的原始情感则又是“天地生物之心”中的应有内容与规定,谁人不具备,谁人欠缺过?
所以,朱熹说:“天包著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则得此生物之心为心,所以个个肖他,本不须说以生物为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都以“生物之心”为自心的本质特征,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物都没有死过,都在不停地生生,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古往今来,也没有一个物生过,都在不断地死去。“天地生物,自是温暖和煦,这个便是仁。”[27]“天地”并不能指现代意义上的天空与大地,毋宁指万物自身,每一个存在物其实都是在不断生生的,没有一时一刻停留过,物自身是把握不住自己的,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意识,没有记忆,没有想像力。生生不息、变化不已是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存在状态,甚至,也可以说,天地万物始终都处于生生状态之中。
“仁是天地之生气。”
“生底意思是仁。”
“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28]
生、生气、生生不已,已成为朱子之仁的内在规定和必然意义。朱熹晚年的弟子陈淳说过:“仁者,心之全德,兼统四者,义、礼、智,无仁不得。盖仁是心中个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彻始终无间断。苟无这生理,则心便死了。”[29]显然,仁的观念就是“生理”,仁等于生,生则又生生不息,没有间断,永不停歇,而“生气”又只不过是“天地生物之心”的感性表达与形象描述。“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30]所谓“浑然、温和之气”,仅就工夫论上说,只是仁的事象表征,世界万物无不具备此理、此气、此心。但从道体大本上看,则自然与人、理与心、体与用已经达到高度的统一,仁之生就是物之气,物之气就是天之心、人之心。进而,天人同构,万物一体,彼此从来就没有被分离过,这便是一直为宋儒所津津乐道的“圣人气象”。
然而,朱熹对仁的另一个明确规定则是:仁即理。相对于把仁归之于生生,朱熹将仁归之于理似乎更水到渠成,也更引人注目。“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31]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失去仁的规定,人则不成其为人。仁是理,这个理并非具有凡尘俗世性质的人理,而是绝对无条件的天理,但它还不直接就已经对人生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只有具备了反省意识和道德自觉的人主动把天理与生活实践结合、统一起来之后,才能够产生人际世界的法则规范。或者,仁之理,必须经过一番工夫实践之后,被人心所领会和消化,所以才能够成为“道”。理是天理,道是人道。于是,自然与自由、天理与人道原本两分于不同的领域,因为人的存在以及积极的工夫实践而一下子便能够现实地融合到一起。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32]
朱熹力图把仁之为道与仁之为德的两大方面做一次连结,而并不给予任何理论性的论证和演绎。在他那里,出于人心的“爱”与超越性的“理”,并不截然两分,在我心之内只是一个原体而已。而“心之德”,亦即“本心全体之德”[33],或“心体之全德”[34]。“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35]感性化的德已被提升到心体之道的高度。而同时,被“爱之理”所强调的则是理可以爱,爱不盲目,爱中有理。最终,仁中有爱,仁中有理,爱、理统一于仁,即“仁是天理之统体”[336]。
然而,爱、理都得一一落实于心。“一心之间,浑然天理,动容周旋,造次颠沛,不可违也。”“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别有仁也。”[37]在朱子看来,就道体而言,仁就是“本心”或“心体”,心体流行,所遭遇到的一切,无不仁。但因为“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38],所以就很难保证情都能够合乎性,而离开性的统领与引导的情,总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于是,“心与性自有分别”[39],心、性两开,必须警惕心对性的侵蚀与干扰。“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40]单就仁之发用被私欲蒙蔽而言,感官的血肉之心则可能有不仁动向。本体之心、形上之心却始终不会离开仁,或者直接就已经是仁自身。于此,原始儒家的一体之仁似乎被做了一次形上、形下的割断。[41]
但问题又并不这么简单,朱熹更多的时候却在强调天理与人心在经由现象界、认识论、工夫论层面的两分之后而又能够达到终极性本体境地里的统一。“看来人之生,便自是如此,不待作为,如说父子欲其亲,君臣欲其义,是他自会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会亲,君臣自会义,既自会恁地,便活泼泼地,便是仁。”[42]当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功夫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仁心便会自然流露,他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点点滴滴,无不体现出仁的内在要求与精神指向。自然如此,不假思问,不借认知,是一种获得自觉、自为与自在绝对统一的德性境地。这是仁在经历了现象、认知过程之后,对道体自身的一次回归。“以仁为爱体,爱为仁用,则于其血脉之所系,未尝不使之相为流通也。”[43]仁是体,爱是用,体与用之间、仁与爱之间相即相离,相分相合,存在着不可割断的内在关联,仁支配着爱,本体决定着发用,体用不分的境地就是仁爱性情的最高统一。[44]
而为仁的路径则在于“主敬”、克服“己私”及“格物致知”。朱熹说:“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45]而所谓“敬”的工夫,就在于“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只是收敛来”或“收敛个身心”,“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46]。“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47]于是,“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便是仁。”生活实践中,私欲对天理总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追求仁的儒者,应该尽力消除私欲,唯有私欲被祛除殆尽,天理才能够在自己的日用常行中流布盛行。“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48]
人要想达到天理,则必须“格物致知”。而所谓“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指尽。致,指推。格物,就是应接、领会一切外物,直至穷尽万物之天理;致知,就是从切己自我之知出发,逐步外推而能够洞察天地万物的根本性质。“极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则我方能有所知。”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穷尽天理。“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而穷理至极,“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著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亲便遇孝,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49]于是,天理消融在人伦生活的道德法则与伦理规范之中,体用相即,人性自觉与客观规律合而为一,这乃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地。
四、万物一体之仁
王阳明晚年的《大学问》一文,是一部天才的仁学纲领性文献,内容短小精悍,主要涉及“万物一体之仁”。他所谓的“大人之学”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在王阳明看来,“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50]无论大人、小人,实际上原本都具有“一体之仁”,并且,“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仁出自或者直接就已经是所谓“天命之性”,是人之为人自然而然呈现出来的特质秉性,它本身没有任何遮蔽,是昭然若揭的天道本体。
王阳明以仁心“未动于欲”、“未蔽于私”的境地来解释《礼记·大学》的“明德”。没有私欲之蔽,小人之心也可以拥有大人一般的“一体之仁”,而一旦蒙受私欲之蔽,大人之心也如同小人。“明明德”,就是要“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而“亲民”则要“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明明德”与“亲民”是实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两条最基本的路径,一为体,一为用。“明明德”必然反映于“亲民”,而“亲民”则是“明明德”的发用与落实。“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同样的仁心也可以推之于君臣、夫妇、朋友之中。这里的“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并不难以理解,儒家恕道的推己工夫一向如此要求,而“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之说则显得生硬、僵化,既然已经产生了“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的现象区分,又如何能够重新合并、归纳为“一体”呢?回归仁道本体只能靠修为实践,只能在主体自省与自身觉悟的过程中完成。而推己则无非弘扬仁道,使之进一步光大,也是一种“明明德”的工夫实践,“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知天、尽性的目的和任务无外乎把自己的仁心扩散、放大到整个伦常世界之中。
阳明学之仁的最基本内涵是“生生不息之理”。
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51]
生生不息之理体现在世界万物的身上,因此是无处不在的,具有普遍的性质,但它的发生却有一个过程。从本体论上看,仁无处不在,无物不是仁,因而仁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本体论性质,但在现象上却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是生生不息的。“渐”一字则试图说明本体内在之仁向现象生活世界的表出行为,因而只是一种在认识论上的描述与叙事,相当于心学的方便说。
仁在阳明学中的含义与地位几乎与“良知”无别,甚至,仁就是良知的代称。王阳明说:“良知者,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52],本体境地泯灭一切差异,同也不同,异也不异,一切都无所谓。而“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53]出于本体之心的性、理,也就是仁。良知始终处于仁心未发的状态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54]而一旦已发,即可发挥现实功用,进而能够构造出存在于我的世界里的万事万物。
仁是万物的自性。万物在发生、存在之初即已被赋予良知、精灵。所以,王阳明说: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
“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55]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
“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56]
从有机论、生存论的立场上看,人有良知,万物也有良知。良知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内部本质与存在根据。正因为人与万物都拥有共同的良知,所以,人与万物之间才可以进行交流与沟通。而从世界构成意义上看,我不看物,物怎么可能进入我的世界,又怎么可能被我认识、被我命名呢?一旦“良知”呈现与流行,遇物化物,遇事成事,我的世界里的一切事物便自行开显出来,一无滞碍。“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57]
而良知又是“至善”。“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然之极便是。”“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一处便是。”[58]“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59]这里,道德论中的至善概念,已经被用来解释本体论的仁与良知,于是,心之纯粹、透彻的本体状态即呈现为“至善”,它是一种绝对普遍的德性准则或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标准,并不等同、但却可以决定人伦生活中那些具体的纲常规范,发挥劝人为善的积极功用。至此,至善目的论、自然的合目的论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了。“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60]感官之心只是“至善”的暂时存在处所,但本体之心却直接就已经是仁,它依靠内心自反就可以获得,而不需要向外索求。没有进入人心意识的仁始终都只是一个绝对的大全、纯粹的道体,它自己只是自己而已,根本不需要、也无所谓被人心所认识、了解和掌握。然而,被人心所认识、理解和掌握之后的仁,肯定已经是对仁心道体做了分取、占有与偏执,也已经成为一个支离破碎、复杂多变的现象事物。
良知境地中,一物只是一物,而不能与别的一物相关联或交涉,没有关系牵连,没有因果作用。物始终只是它自己,而不能与他物来往和沟通。物与物,既有差别而又没有差别,万物自体,万物一体。
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61]
人的产生使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复杂了起来。人心意识使每一个物都变成了一种关系中的存在。人心意识突然把物变成了事物,即事中之物。一方面,人一旦体仁、达仁,即已能够与万物沟通,万物即等同于我,我也等同于万物。同样也无所谓我,也无所谓万物。而另一方面,我心开显或发散,作为被我所看、所感的世界万物则都从我而出,现象事物首先因为我的存在而被我所观,在我观之中,因而成为在我之内的存在者。我的事物只存在于我的世界里面。还没有被我所看到、所想到的事物一定只作为物自身而独自存在着。这就是“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62]的原因所在。
一旦人们在开展了格、致、诚、正、敬、集义、省察、克治之类一番修持工夫之后,就能够领会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地,进而,也能够在天与人、物与我、人与己之间,畅行无碍。“仁极仁”,“能穷仁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63]求仁、求良知,下遍所有外在工夫,也只不过是尽一己之性而已。穷尽了仁之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仁之性,当然也就达到了万物之性、万物之理。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于是,自然与自由、主体与客体、生人与万物便融合在一起,不可区别,不可两分,没有之间,也没有任何阻碍和隔断。为增强儒学理想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儒家学者们非常擅长于对万物一体的终极境界进行生动描述与大肆渲染,并且,几乎走到了极致的地步。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又,“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而“仁极仁”的具体路径则在于“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64]
然而,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似乎仍然没有真正解决仁心与人心的分离。仁体良知之中蕴藏着一个深刻的矛盾:既然仁心是性体、道体与本体,那么就应该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与纯粹性,是不可能落入人心的、不可认知、不可通过现象事物予以把握的灵明,这样的话,人又怎么去确证与体认它呢?如果普遍的良知可以、并只能通过个体主观去认识、把握,那么,它就不能算是普遍和纯粹的本体,而只能是特殊化、具体化的存在者。于是,良知的追寻又必然陷入完全个体化的经验与领会。进而,良知在人与人之间如何实现它自身的可通约性呢?即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有效的传播与流布呢?这是心学哲学的一大困难,很难克服。看来,还是孟子说得好:“人心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65]把仁心作理性化、礼化、义化的客观化处理,以可见、可知、可言说的社会伦理与意识形式引导仁走出个体化的泥潭,不失为解救心学的一条通途。
而解救心学的另一条路径则在于,将仁心回归于人心。明末刘宗周在批评王阳明把“心之本体”与“人心”对立起来时,曾严正指出:这“依旧只是程朱之见”、“居然只是宋儒衣钵”。刘宗周继承并发扬了孟子的仁心思想,直接以个体化的“人之心”取代“仁”,他说:“孟子曰:‘仁,心也。’人心便只‘人心也’之人心,道心即是仁字。以此思之,是一是二?人心本只是人之心,如何说他是伪心、欲心?”[66]实际上,对超越、绝对的仁的领会与实现始终离不开个体化的、感性的人心经验。不能在人心之上再安立一个道心,没有必要再床上叠床。人心、道心合二而一,一体不分。道心必须经由人心而获得提升和上扬,人心也离不开道心的控制与支配。仁只是身心统一。人心、仁心的区分实质上只是一种认识论、工夫论的需要,即将德性的发生与功用当做一个现实过程展示开来,给人们看,而这么做在本质上已远离了道体、仁心本身的真实。然而,将仁心回归于人心的努力,又绝不符合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潮流。随着人类思维水平的逐步提高,关于人心的研究与描述,必将日趋分疏化、细密化与专门化,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方式方法终究难以揭示发生于人心内部的情感与思维活动的真相,也不可能真正发现德性自觉形成的最后秘密。
[注 释]
[1][宋]周敦颐:《太极图说》,见《周子通书》,第 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宋]周敦颐:《周子通书·师友》,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文本语境中,“爱曰仁”是与“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一起作为“德”的基本构成而呈现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并行,仁的超越性、先验性与领导地位并没有凸显出来。引文见[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诚几德》,第32页。
[4][宋]周敦颐:《周子通书·爱敬》,第37页。
[5][宋]周敦颐:《周子通书·顺化》,第36页。
[6]正所谓“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见周敦颐《周子通书·诚几德》,第32页。
[7]因为“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见[宋]周敦颐《周子通书·顺化》,第36页。又,宋学四家中,周敦颐的话语方式最为特别,其著述言简意赅而蕴涵丰富,其思想却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正确理解周敦颐的仁,不能仅满足于做一般道德学上的伦理意义阐发,而必须在儒学本体论的框架里进行,还应当结合以无极、太极、动、静、公、诚一类具有超越性质的概念。
[8][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第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9][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第347页。
[10][宋]程颢、程颐:《二程外书·卷第六·罗氏本拾遗》,第32页。
[11][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第338页。
[12][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五·伊川先生语一》,第339页。
[13]在宋儒那里,伦理的本体化、本体的伦理化始终交织在一起,双向涵摄,彼此耦联,而难以再将二者作硬性区分。在以“公”释“仁”的同时,程颢、程颐还以五常之性诠解万物之性,“万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引文见《二程遗书·卷第九·二先生语九》,第152页。
[14][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五·伊川先生语一》,第200页。
[15][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四·明道先生语四》,第188页。
[16][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十二上·伊川先生语八上》,第339页。
[17][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第 84、79页。
[18][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第174页。
[19]性不同于情,心如谷物的种子,天生如此、未予萌发,即是性,也即是仁;阳气催发,谷物已经生长出枝叶、果实,则为情。所以,在程颐看来,“四端”存于心,但绝不是心的功用。“四端”与仁、与心具有一样源始而本真的性质与地位。引文见《二程遗书·卷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第232页。
[20][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第167页。
[21][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第66页。
[22][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上·二先生语二上》,第 64、65页。
[23]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禽兽无疑是“不能推”的,因为禽兽如果也能够推,人的尊严与地位岂不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了吗?!人心在根本上是无法承受这样的事实的。但禽兽是否真的“不能推”,显然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生命科学问题。人与禽兽各有各的边际限制。禽兽也应该是可以推的,但禽兽所推的对象和范围不可能是我们的人际世界,而应当只限于它们自己的种属与族类之中。禽兽不能推,禽兽之间就无法交流与沟通,但实际上禽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远比人类想象得要多,要丰富。人类不应该用自己所推的形式、标准、对象去衡量禽兽之所推。人之所推与禽兽之所推之间似乎也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即所谓可通约处,否则,一切禽兽就不懂人性了,人也就难以饲养、驯服和利用禽兽了。但人不可能彻底弄懂禽兽之推的全部意义,同样,禽兽更不可能彻底明白人心思绪的全部意图。引文见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二下·二先生语二下》,第108页。
[24][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一·明道先生语一》,第170页。
[2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上》,第237页,中华书局,1983年。
[2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二十章》,第28页。
[2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三·孟子三·公孙丑上之下》,第二册,第1144、1145页,岳麓书社,1997年。
[2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 97、100 页。
[29][宋]陈淳:《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第22页,中华书局,1983年。
[3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101页。
[31]把仁、人合而称为道,无疑是孟子的独到发明,这为儒家随俗入世大开了方便法门。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孙奭注疏曰:“孟子言为仁者,所以尽人道也,此仁者所以为人也。盖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与人而言之,则人道尽矣!”人、仁统一,则可以尽显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但朱熹这里却凭空冒出一个“仁之理”,这一解释显然难脱理学化的嫌疑。引文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尽心下》,第367页。
[3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梁惠王上》,第201页。
[3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上》,第239页。
[34][宋]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十二》,第2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仁不可见,必借助于德的表现。天理不可触摸,但可以通过气的形式使人们予以感知与确证。气禀于天理,才能够在现象世界里获得感性呈现。“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引文见《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101页。
[3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102页。
[37][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一·孟子十一·尽心下》,第二册,第1303页。
[38]关于心与性情之间的关系,朱熹还阐述说:“心,主宰之谓也。”“言主宰,则混然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儱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心统性情’,故言心之体用,尝跨过两头未发、已发处说。仁之得名,只专在未发上。恻隐便是已发,却是相对言之。”引文见《朱子语类·卷第五·性理二》,第一册,第 86、85 页。
[3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六·大学三》,第一册,第288页。
[4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五·程子之书一》,第三册,第2192页。
[41]这一割断虽大悖于孔儒的原始传统,但其客观效果却能够使儒家的观念体系与学说思想获得一次理性化的提升与超越,进而使儒家在与佛教哲学的激烈论战中为自己赢得的必要的生存地盘和发展空间。所以,走形上的路线,暂时放弃一点形下,可能是儒家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选择。在形上与形下之间,理学新儒们往往都强调前者,而鄙夷后者。朱熹就说过:“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浊者也。”引文见《朱子语类·卷第五·性理二》,第一册,第86页。
[4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102页。
[43][宋]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四》,第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上海。
[44]仁与心、仁与爱、仁与理之间,非常复杂,很难言说清楚,主要原因则在于涉及体与用之间的关系。关于体用,朱子曾说:“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见在底便是体,后来生底便是用。此身是体,动作处便是用。天是体,万物资始处便是用。地是体,万物资生处便是用。”见《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92页。
[4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103页。
[4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二·学六》,第一册,第 188、186、192 页。
[47]这里也可以看出,被朱熹所大肆强调的并不是一定要灭绝人欲,毋宁不让天理被人欲所破坏和摧毁。仁者趋赴于仁道,也并不是完全取消人欲的发出与流显,毕竟人心总会有遏止不住的私意,毕竟私意也是人性的内在规定与先天安排,所以,人之为人所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道德主体自身的积极修为与涵咏,让天理胜私欲,最终回归于礼乐规范。引文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颜渊》,第212页。
[4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第一册,第 106、107 页。
[49][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十五·大学二》,第一册,第 260、261、258 页。
[50]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第9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1][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上·陆澄录》,第79页。此外,《卷下·黄修易录》中,王阳明还说:“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见第279页。又,《卷下·黄以方录》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流行不息”,见第339页,岳麓书社,2004年,长沙。
[52][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第174页。
[53][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上·陆澄录》,第74页。
[54][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陆原静书(二)》,第178页。
[55]不止于此,本体论意义上的良知、精灵,还是人生的一种至乐境界。王阳明说,“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通达良知、精灵,便可以忘怀一切人情意义、知识价值、痛苦烦恼。人间没有一种快乐能够与体会本体、直击本体的快乐相比拟。引文见《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第289页。
[56]人为什么能够通达于物?认识论之所以可能、真理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不能只在人类自己的身上寻找,而应该扩大视野,将问题推及到万物的内部机理中去思考。“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正因为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在发生与起源上始终是一体的,各自成形之后,又都能够禀赋一样的天地之气,所以,人类才能够认识对象客体,把握万物的规律本质,物我才不至于隔绝。否则,人只是人,物只是物,两不交叉,互不融摄。引文见王阳明《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第297页。
[57][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聂文蔚(二)》,第233、234页。
[58][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第8、5页。
[59]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第969页。
[60]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第970页。
[61]万物一体,显然是一种本体论的境地。包括人自身在内的物与物之间原本是一种彻底相同,或彻底的差异的关系,甚至也没有所谓的“之间”,也没有所谓的“关系”。但一旦人心萌动、意识生发,则必然将物拖进复杂的关系世界之中。于是,原本绝对的公、无,则变成了有限的私、有。人只有在抛弃一切意识成见与思想包袱的情况下,才能够还原到物自身的本真状态,即仁的境界。引文见王阳明《传习录·卷下·黄省曾录》,第303页。
[62]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127页,岳麓书社,2004年,长沙。另据《传习录·卷下·黄以方录》记,弟子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王阳明则回答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见第342页。世界是被自己所认识和理解了的知性存在物,因此世界只在人心之中。世界不同于宇宙,前者由人心构造而成,其中一定已经发生了事情、关系;而后者则还没有人心的参与和介入,属于纯粹的物自身。一人一世界,并且,世界总是属于自己的。人与人之间共同的世界则构成了社会。人死了,他的世界也被带走了,而他所带不走的则一定是天地万物自身。
[63][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135、136页。
[64][明]王阳明:《传习录·卷中·答顾东桥书》,第152、153页。
[65]十三经注疏(标点版),[汉]赵岐,[宋]孙奭:《孟子注疏·告子上》,第3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6][明]刘宗周:《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三·阳明传信录·三》,见《刘宗周全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版,1996年,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