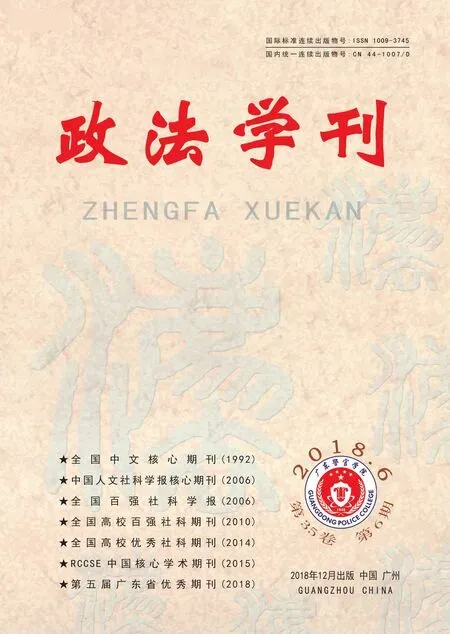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生发
吴 欢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一、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2016年5月,首届“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在曲阜召开。此次会议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与人和。所谓天时,当前正处于传统文化复兴和互联网秩序生发的关键时刻;所谓地利,山东曲阜是儒门圣地;所谓人和,与会人员涵盖儒学、互联网、法学等学科,可谓“跨界融合”。
讨论“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的问题,需界定三个基本概念,即“儒家文化”“互联网”和“秩序”。但就笔者目见所及,既有相关研究除极少数外,在这三个概念的理解与诠释上并无甚新意。大多数研究者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主要停留在道德伦理文化和哲学思辨文化层面,认为其能够为互联网秩序生成提供的主要是一些化解网络戾气、促进网络和谐、净化网络空间的微言大义抑或只言片语;在他们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充满戾气与纠纷的不和谐空间,因此需要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和谐伦理的浸润与调适;在他们眼中,所谓“秩序”也只是浅层次的不吵不闹不打架,以和为贵,而缺乏对互联网秩序生成原理的根本性深入思考,更遑论结合儒家文化探讨互联网根本秩序生发。①相关研究参见孟彩珍. 儒家义利观与网络伦理[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2008, (1): 44-47;张艳梅. 儒家伦理思想对网络伦理建设的意义[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 (1): 5-6;陈静枝. 先秦儒家诚信观与当代网络诚信建设研究[D]. 重庆师范大学.也就是说,大部分既有研究其实是简单化地、脸谱化地处理了这三个概念,并且缺乏对三者之间的可能张力与深层勾连及其建构途径的有解释力的分析。
笔者认为,这里的“儒家文化”不应当是那种博物馆化的、白胡子老头化的儒家文化,不应当只停留在哲学思辨抑或道德说教层面,而必然应当侧重于当代大陆新儒家所倡导的、具有政治维度和制度指向的、能够作为治理秩序之基石与灵魂的精神原则。①大陆新儒家的问题意识、话语范式和思想谱系,参见陈明. 大陆新儒家的问题意识、话语范式、思想谱系都已成型[EB/OL].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23113&ALL=1,2016-05-15;蒋庆. “大陆新儒家”正在形成中[A]. 陈明, 朱汉民主编:原道[C]. 总第26辑,223-243.换言之,主要是儒家之“道”而非“器”,主要是“礼”之“义”而非“仪”。这里的“儒家文化”必然是现时代的儒家文化,接纳社会科学新知的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儒家(哪怕是公羊家),如果不加纳和借助社会科学话语,“弘道”“原道”恐终无从入手,无所取材也。
进而,这里的“互联网”,也不能仅仅停留在PC机时代,或者说web1.0时代的局域网、万维网,而必然是已经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由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作为技术基础的、以跨界融合、连接一切、用户至上、体验为王为基本要义的“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今后甚至可以进一步期待“万物互联”的时代。在这个信息革命时代,互联网作为创新性基础设施,每时每刻都在打破和拓展物理和思维的疆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和存储的天量大数据是新型的生产资料,对大数据进行运用性计算将会释放出突破性的生产力。
最后,这里的“秩序”也不是政府监管部门所期待的那种浅层次的、井井有条的和谐秩序,而毋宁说是一种决定互联网生态环境的根本性秩序或曰“元规则”。在首届“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这个里程碑式的会议上,讨论的应该是这些根本性的秩序问题。这里的“秩序”应当是某些带有政治决断性的原则和理念,决定了这个秩序是丛林时代还是文明社会。
此外,还有一个隐含的关键词就是,“中国”。虽然儒家与互联网都具有相当大的时空上的延展性和包容性,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但今天的人们思考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中国”这一时空语境,因此需要关注,为什么在短短20年中,互联网在中国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迅猛发展,这与中国文化土壤尤其是儒家文化有何关联,这样的土壤孕育出的互联网生态又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这种中国式的互联网生态对于人类互联网秩序的生发又有何意义?
因此,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的“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的议题,意思应该是现代儒家文化能够为“互联网+”时代提供怎样的根本性秩序贡献,至少是理论解释与指导;反过来,“互联网+”时代能够为儒家治理秩序理想的实现提供怎样的助力,以及二者之间有何紧张冲突之处,如何促进前述贡献与助力之实现。当然,这个话题实在太大,远非笔者能够回答,也远非本次会议所能解决。故笔者以下的论述主要围绕着四对关键词:网络天下与万物互联,以人为本与用户至上,互惠原则与分享经济,责任伦理与道德情操,分别试图回答儒家文化视角下的互联网秩序是什么、秩序为什么,以及行动原则与行为限度等问题。
二、网罗天下、万物互联与互联网秩序生态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论是丛林时代还是文明世界,都有其基本的秩序生成原理。但在讨论具体的原理原则之前,有必要对这个秩序的全貌进行判断或者了解。借用自然界和互联网共通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个秩序的“生态”。自然界的生态毋庸赘言,社会科学界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也源远流长,在现时代,生态概念更受到互联网巨头们空前一致的强调。在对秩序生态的想象与描述上,“互联网+”时代的思想与实践与儒家文化有重大暗合。
“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秩序生态是“万物互联”。众所周知,数学领域有著名的六度空间理论,认为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能联系起两个陌生人。在“互联网+”时代,六度空间理论或许将被进一步修正成为三度空间理论。“互联网的实质是一种关系,‘互联网+’的实质是关系及其智能连接方式。互联网去中心化、降低信息不对等,重新解构了过去的组织结构、社会结构和关系结构,关系及其连接方式相对更具有随机性,主要是连接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在发挥作用;‘互联网+’真正实现了分布式、零距离,关系的建构与连接融汇了人的智能,是‘人工智能+人的智能+群体智能’的交汇。互联网是通过计算机的连接,部分地实现了人的连接、人和信息的连接;‘互联网+’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服务、人与场景、人与未来的连接。”[1]9“互联网+”时代的世界将会因沟通条件的改善变得更小,也会因互联互通的拓展而变得更大;在变小的同时将变得更扁平,在变大的同时将变得更多元。在“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技术革新是无界分享的,参与主体是众生平等的,数据信息的铺天盖地的,主体行动是无时无刻的,而其终极追求则是万物互联。互联网摧毁了固有身份,重塑了社会秩序,打破了固有边界,削弱了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升了全社会的运营效率,让组织、雇佣、合作都被重新定义,进而在弱关系社会里重新建立契约和信任关系,在连接的关系里产生了新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信息的民主化、参与的民主化、创造的民主化得以盛行。①云中智库专家研讨:你眼中的互联网+[Z]. 微信公众号“腾云”,2015-04-03.
儒家文化关于秩序生态的理解与实践可以用“网罗天下”来表述,这与“互联网+”时代“万物互联”的秩序生态观有着惊人的暗合。虽然“网罗天下”不是儒家原典中的固有词汇,但笔者认为可以用来较为准确地揭示儒家关于秩序生态的理解,即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生态是一张全方位立体式的“网”。首先,儒家理想的秩序生态是一张“网”,所有的生命都不是纯粹个体,而只是这张秩序之网上的一个扭结,并与周围的人事发生各种联系。更具体地说,传统中国每个人都生活在伦常秩序的网络之中,扮演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各种相对性的角色。其次,这张“网”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所以具有时间与空间、纵向与横向上的相当大的拓展和延伸。正如传统中国“家”的观念中,每个人既是祖先的子孙,又是子孙的祖先,在敬奉祖先与垂范子孙的香火传承中,个体有限的生命获得了无限的传承。在空间意义上,儒家伦常也不是封闭的,由于引入了“朋友”之伦,遂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包容与达观。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先生所说“投石入水、波纹四散”[2]1,也许仅仅是这张立体时空网络上的一个狭窄的凝固截面。第三,儒家还有一套在有形和无形中建构、拓展和延伸秩序之网的规则体系,这就是“礼”。“礼者,履也”,最初的来源就是丛林时代的禁忌和事神致福的行动,因而“礼”是生成的而非建构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尤其凸显了儒家秩序观中的“生态”色彩。儒家所谓的“礼”,也是一张具象化的规则之网,把所有人恰如其分地安顿在秩序之中。传统中国的每个人,都能够也必须在礼法秩序中获得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间与意义。
无论是“互联网+”时代的“万物互联”,还是儒家文化中的“网罗天下”,二者关于秩序生态的塑造与想象,均与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基础的近现代西方秩序观是截然不同的。孰优孰劣姑且不论,但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仍然较深层次地保留了儒家“网罗天下”色彩,并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进一步走向“万物互联”。说到底,仍在“网”中。当然,必须看到的是,“网罗天下”与“万物互联”之间虽然具有高度的理念契合性,但也存在一时难以消解的张力。比如,万物互联带来的去中心化、扁平化秩序格局与一般认为的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格局之间就可能存在较大抵牾。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现时代利用这种契合性以促成互联网秩序的生发?对此至少有三点值得强调:首先,在治理层级上,要由传统的金字塔型走向扁平化与多元化,这会极大地释放治理的效率效益,增强治理的可欲性与可接受性;其次,扁平化与多元化的治理网络与儒家传统治理秩序理念并不存在绝对冲突,中国传统乡村秩序的建构本身就是多元且分布式的;第三,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中心,这也就是本文要论及的第二个问题,以人为本、用户至上与互联网秩序目的。
三、以人为本、用户至上与互联网秩序目的
在描绘了“秩序是什么”之后,接着要讨论“秩序为什么”的问题。除了绝对的自然状态与真空环境①按照神学的观点,自然状态也是神的赐予,真空宇宙也是神的旨意。著名科幻小说《三体》中也反映了“重回宇宙的田园牧歌时代”的秩序追求。刘慈欣. 三体·死神永生[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0.,在任何时代,秩序本身都不是目的,秩序中的人才是根本目的。人们之所以建构治理秩序,或者说治理秩序之所以如此生发,都潜含着秩序中的“人”的治理目的性。因此,“去中心化”的治理秩序本身又必须实现“再中心化”,否则作为秩序目的的人就会被“物化”,进而出现秩序的“异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与互联网同样具有高度暗合。
儒家的秩序目的观可以用“以人为本”来统摄。这里的“以人为本”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儒家原典词汇,尽管其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固有表述是“以民为本”。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民为本”,其中的“人”和“民”都是秩序的目的而非手段。[3]毋庸讳言,在中华文明或曰儒家文化的早期,曾经有过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和人格神信仰,这种崇敬进而构成了统治合法性的论证与加持。幸而,在最早的儒家原典《尚书》中,华夏先哲和伟大的立法者们已经一咏三叹地反复申论了“天听民听”“天视民视”“民为邦本”等思想。“汤武革命”之后,治理者一方面恢复了“天道信仰”观念,但他们更加意识到,相对于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天命”,“人心”似乎更加值得关注。所以西周的治理者仍然“敬天”,但是他们“敬天”的目的是为了“保民”,即保持治理权和治理秩序的长期稳固。从此,“民”在治理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意义被发现,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思想进入了“以民为本”的时代。待到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提出“仁”学理论,“人(民)”作为秩序目的的理论进一步被系统性地提出和论证。[4]这无疑是一个伟大历史进步。相较于彼时尚在茹毛饮血或匍匐于神权之下的西方,中国先贤在对天的敬畏中发现了“人”,强调仁者爱人,人是终极目的。此后数千年,儒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的宗教,但通过宗法礼教和三纲八目,牢牢地树立了以“人”为核心的秩序目的观。近代以降,虽然西方政治哲学也讲“人民主权”,共产党人也讲“人民当家做主”,但前者之“人”是原子化的,后者之“民”是抽象化的,均不及儒家“以人为本”之“人”的具体与生动。
“用户至上”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基本思维,其背后的本质则是对人性的尊重。“互联网除却冰冷的技术性,其力量之强大最根本地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用户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性的重视。”“人性即体验,人性即敬畏,人性即驱动,人性即方向,人性即市场,人性即需求,人性即合作。人性是连接的最小单元、最佳协议、最后逻辑;人性化是连接的归宿,是融合的起点,是存在的理由。小到一次互动,大到一个平台,都要基于人性思考、开发、设计、运营、创新和改进。人性是检验的标尺,人性是关系的核心。”[1]54正如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所讲的,在“互联网+”的时代里,用户不会想了解你的技术是否很牛,不会想知道你的公司有什么伟大的梦想,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你的产品能解决什么问题,创造什么价值;在互联网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时候,谁能够从用户需求出发,把体验做到极致,最后让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感受到方便、愉悦、放心,谁就可以真正地赢得用户的信任;这就要求企业做产品的时候要时刻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发自内心地尊重用户的利益;无论商业模式千变万化,用户基础才是王道;只有重视人性、尊崇人性,不忘基于人性的初心,才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5]对用户人性的推崇和尊重已经构成了“互联网+”时代商业秩序的根本准则,并将进一步塑造这个时代的治理秩序。以法治政府建设为例,“互联网+”时代用户至上、体验为王的生存法则,将解构传统行政法律关系以行政权为中心的格局,生发出新的相对人中心主义的法治政府权力关系。[6]
在把“人”视为秩序目的而非手段的根本性问题上,儒家文化中的“以人为本”和“互联网+”时代的“用户至上”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可以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秩序建构原则。落实这一原则至少有两点要求:首先是永远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可以设想一下“互联网+”时代的秩序运行:基于互联网思维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其实就是治国理政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直接供应商,应当坚持用户至上的宗旨;如果政府以非正当的动机确立目标、设计制度、指导行动,作为产品和服务接受方的公民即可通过连接一切的互联网实现目的揭露、群体召集和多元共识行动,从而改善治理,达成善治;相反,如果政府的目标、制度与行动符合良法善治的方向,作为用户的公民将会报以好评、点赞、参与、配合和支持。[7]其次,这里的“人”必须是存在于互联网秩序网络中的具体真实生动的个人,而不能只是潜伏在网络背后孤立单一的“一条狗”。当然,人性复杂,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角落。在具体的互联网治理秩序建构/生发中,还应当充分尊重和因应人性的复杂性与真实性,确立基本的行动准则与行为限度。这就涉及本文将要论及的第三和第四个问题。
四、互惠原则、分享经济与互联网行动原则
在生物意义上,人欲生存,不能不消费,不能不生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们不得不合群并努力探索提高其合群之技艺,以扩大其群之规模,产出更多物品,养活更多人,以提升生存质量。[8]在秩序意义上,作为秩序目的与主体的人,不能不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交往与政治行动。既然在前文强调人的具体与生动,就必然涉及主体的行动与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互联网秩序中基本行动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思想与互联网实践之间也不乏暗合之处。
儒家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互惠原则”。这是组织人类共同体最基本的条件。先民无筋骨爪牙之利而能“群聚”①《吕氏春秋·恃君览》:“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立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组成共同体共同生活,抵御自然界的危险,就是享受了合作和集体的红利。汉人班固强调人类结成共同体是因为具有“仁爱”的本性②《汉书·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这是非常必要和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发挥人类本性中的仁爱因素,先民们无法结成共同体;即使结成共同体,也无法通过互助与合作享受共同体的福利,也就无法摆脱“以力相征”的争斗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儒家无视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因素。相反,儒家旗帜鲜明地正视了这一问题。在对自由商业先驱子贡的“因材施教”中,“至圣先师”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准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互惠原则”的最好表述,不仅大方地承认了“己有所欲”,指明了“己欲立”和“己欲达”的途径是“立人”和“达人”,而且十分清醒地警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无疑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和商业智慧,堪称是两千余年前共享经济、互联网经济的先声。③此番认识受益于北航姚中秋教授在曲阜会议期间参拜孔林于子贡草庐前的即兴演讲,特致谢忱。在政治上,儒家讲求“君君臣臣”,同时说“君不君则臣不臣”。这也是在讲求权利义务的双向性与非绝对性(儒家也反对权利义务上的绝对平等性与对价性)。这些都跟近代西方的原子化的、等价交换的权利义务观和人际交往原则有着极大的不同。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儒家也是以“互惠”为基本原则的。[9]农村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情境,比如红白喜事举全村之力操办,比如远亲近邻之间礼物的流转,比如农忙时节的换工帮工,比如“报”的观念,都是这种互惠原则的体现,也构成了儒家式自生自发秩序生成的实践基础。
“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最为火爆的经济模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何充分调动分散的闲置资源、集中解决现有市场难以消化的巨大需求,是分享经济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交换的时空局限被打破,双向沟通更加精准,互联网平台在技术上实现将分散的供给与需求统一对接,进而降低交易成本,让各类服务更加便宜、便捷,是分享经济得以发展的现实因素;分享经济运用互联网思维、倡导人人参与的理念,让传统意义上的单纯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更多角色,是分享经济能够快速吸引加入者的关键;但从根本上来讲,分享经济的本质是以租代买,让支配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资源可以在脱离支配权人的基础上让他人以租赁的形式使用,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资本拷贝”,用网络匹配更多的需求、创造出更多的价值。[10]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越来越多以利他主义为前提的成功商业模式,使人性自私的假设遭受了诸多现实的冲击与挑战。可以看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巨头都在讲利他主义,讲分享经济,讲免费模式。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利他主义。这个时代商业活动的目的仍然是利己,但却以利他主义方式行事,它以“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方式获取利润。换言之,“互联网+”时代利他主义的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买与卖之间的二维经济关系。这种新型的利他主义商业行为不能简单用传统的基于人性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解释。“互联网+”时代,一种以诚信为基础集聚用户量,以依赖为基础彰显用户体验为王,以“随时、随地、随心”重构的消费者主权时代已经来临,它要求利已的生意必须建立在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的基础之上,它让诚信成为商业成功的基础条件,它引导着产品提供者从利他中获得溢出的自我利益。[11]
无论是“互惠原则”,还是“分享经济”,都对传统经的以人性自私、人性本恶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巨大的冲击。不仅如此,二者也对以这一人性论为基础的近代治理秩序制度设计理念提出了重大的拷问。因为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国家建立的代议选举制、三权分立制、违宪审查制等一系列制度,均分享了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制度设计理念;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行政法体系,也都以控制行政权滥用,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为宗旨。[12]儒家“互惠原则”的重光和互联网“分享经济”的兴盛带来的启示是,虽然也许无法从生物上改变人性自私的基因,但在“互联网+”时代,诚实信用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个人还是商家,还是政府,都必须坚持此一原则。公开、共享和透明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用户从过去默默无闻、有气难出、有权难维的弱势局面,变成了随时可以用点赞、好评抑或差评、吐槽等方式形成压倒性规模的意见表达,从而扭转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而回归“用户就是上帝”的本源。
五、责任伦理、道德情操与互联网行为限度
在讨论了秩序生态是什么、秩序目的为什么和行动原则是什么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相关主体在“互联网+”时代前述秩序框架下的行为限度。恰恰在这个地方,当下的互联网世界出现了很多令人遗憾的现象,前两年引发网络热议的青年魏则西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关于魏则西事件,舆论的矛头多指向莆田系和百度公司,当然也有更深刻的反思指向监管弊病。在这个问题上,儒家文化可以为互联网秩序生发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常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但更多学者强调,这种“伦理型”文化具有强烈而多元的“责任”指向。“责任伦理”不是儒家原典词汇,但用来指代儒家文化对人作为秩序主体之行动限度的强调,或者说指称儒家对健全人格之养成与优良秩序之生发的期待,应该相去不远。[13]正如前文所说,不仅不应将儒家伦理文化“窄化”或者“矮化”为今日所谓个人层面的思想道德修养,而且应当体认到,儒家伦理文化本来和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秩序生发意涵。儒家之“伦”,是公共关系中的“伦”,儒家之“伦理”,是秩序网络中的“活法”。这里的“活法”,既是相较于制定法的“行动中的法”,更是老百姓日用而不知、习行而不察却又浸透于血液骨髓精神观念中的“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尚书·大禹谟》载:“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这里的“天叙”即是上天赐予,“天叙五典”就是上天向人间颁示五种伦常禁忌;故人间一切秩序都必须按照此五伦常而构建,日常礼仪(即“五礼”“五服”“五章”)及其处罚措施(“五刑”“五用”)都是对天叙“五伦”的运用和保障方式。[14]由此“五伦”而生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政治社会关系,各主体皆负有伦常上的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与义务甚至高于权力与权利,具有先定性。①当代法学界亦有主张“义务先定”者,参见张恒山. 义务先定论[M].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或曰儒家的权利义务是非对称的,但正是在不对称的地方隐藏着责任伦理。这种责任伦理的高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间层次是要“学为好人”,最不济也要“诸恶莫作”。
“道德情操”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借来的一个词汇。亚当·斯密的传世著作《国富论》堪称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教科书,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却不似前者那般流传广远。但恰恰在后一本著作里,作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行动方式进行了很多先知般的规劝,堪称西方《论语》。作者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学说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15]60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也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事实确实如此,近300年来的大多数人只记住了前者,于是有了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浸透着血泪”,“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可以藐视一切人间的法律。”更令人遗憾的是,100余年前马克斯·韦伯先后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等著作,原本只是理想型的归纳,却被中国学界奉为治学的圭臬,以致只知此“马克斯”而忘记彼“马克思”,在此指导下的所有研究也不过是为“韦伯神话”做各种注脚。
当今的“互联网+”时代,虽然有分享经济带来的诚实信用原则的高涨,但是在“道德情操”或曰“责任伦理”方面不尽如人意者仍然甚多。如果长期罔顾公众责任,“互联网+”时代的优良秩序决然无法妥善生发。特别是在我国,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必须重视和重构“互联网+”时代的责任伦理。这种责任伦理至少有私主体和公主体的两个面向。就私主体而言,由于互联网的“放大镜”“传声筒”和“隐身衣”效应,各种海量信息泥沙俱下,隐藏在信息网络背后的“人”更得以尽情地释放出人性中的某些阴暗丑陋,更遑论借助互联网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就公主体而言,现代社会公权力对私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干预已经无孔不入,如何在秩序维护、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之外,谨守公私权界,审慎运用权力,着实考验肉食者的智慧。此外,还需引起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时代的治理结构和权力关系出现扁平化和多元化格局,但互联网巨头们个个体量巨大,作为“私主体”隐然享有大量“准公权”,故尤其应承担公众责任。
结语:为人类互联网优良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以上从四个方面初步地论及了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生发要解决或者回应的问题。由于个人视角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前文都是在提出一些发散性的思考要点,而非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对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但解决或者思考的方式可以是中国式的,特别可以从儒家文化入手。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已有有7亿网民,未来必将是14亿人的大网络。中国在接入国际互联网后,短短20余年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互联网巨头。正如姚中秋教授在曲阜会议开幕式上的发问: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这么好?阿里巴巴是成功了,但他们能讲好自己的故事吗?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实践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生动的,未来互联网秩序的生发,中国儒家学者和政学各界有条件,更有责任为之贡献经验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