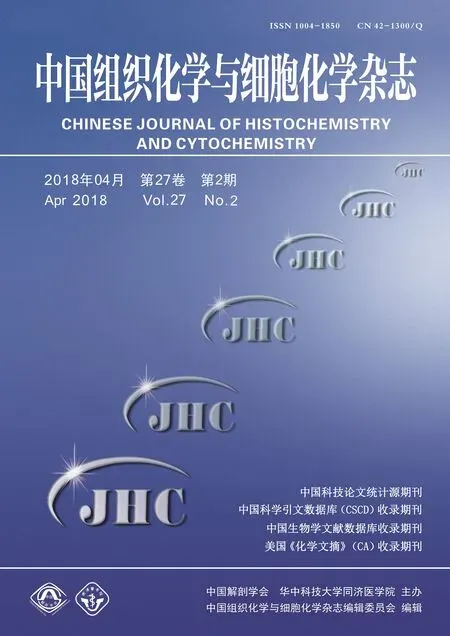组织学与胚胎学中的科技人物和名词(二)
张学明,岳占碰,郭斌,杨占清,唐博,赖良学,李子义
(1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长春 130062;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转化医学研究院,长春 130021)
在前文中,我们分别简介了绪论、细胞学和四大基本组织中的相关科技人物和名词术语[1]。在器官系统组织学与胚胎学中,也有许多相似的人名类名词,如浦肯野纤维与浦肯野细胞、朗格汉斯细胞与朗格汉斯岛、鲍曼囊与鲍曼层/板等[2]。教师如不讲清楚这些名词的来龙去脉,是否由同一人发现命名,则学生极易混淆。为此,本文按组织学与胚胎学一般章节内容的先后次序,主要基于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分别简介了各器官系统组织学及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科技人物和名词术语,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1 神经系统
Birdsey Renshaw (1911-1948),美国神经科学家,因研究脊髓灰质腹角的抑制性中间神经元而知名,其工作被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196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John Carew Eccles (1903-1997)证实,闰绍细胞因此得名。1948年11月因护理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妻儿而感染发病,不幸英年早逝。
Johannes Evangelist Purkinje (1787-1869),捷克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当时全球最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若从欧洲外给他写信,只需在信封上写“Purkinje,欧洲”即可。他是使用切片机的第一人,1829年描述了樟脑、鸦片、颠茄、松节油、肉豆蔻等对人体的作用;1837年发现小脑皮质中的大神经元浦肯野细胞;1839年创造“原生质(protoplasm)”一词,同年发现心内膜下层中的浦肯野纤维;其他发现还有生理学上的浦肯野效应、浦肯野斑等,还引入了血浆(plasma)一词。
Santiago Ramóny Cajal (1852-1934),西班牙杰出的病理学家、组织学家、神经学家,因其脑显微结构的开创性研究而被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其医学艺术堪称传奇,由他手绘的数百幅脑神经元示意图至今仍在使用。他发现了一种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细胞――间质卡哈尔细胞(interstitial cell of Cajal / interstitial Cajal cell, ICC)。Cajal一生著作等身,并以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出版。1906与Camillo Golgi[1,3]同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但有趣的是两人观点不同。
Carlo Martinotti (1859-1918),是Camillo Golgi[1,3]的学生,是大脑皮质小锥体细胞层中马丁诺蒂细胞的真正发现者,该细胞曾被误认为由意大利医生Giovanni Martinotti (1857-1928)发现。
Jules Baillarger (1809-1890),法国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大脑皮质分层的发现者,大脑皮质中的神经纤维柏氏外线、柏氏内线均因他得名。
2 循环系统
Wilhelm His Jr.(1863-1934),瑞士心脏病专家、解剖学家,是切片机发明者、解剖学家Wilhelm His Sr.(1831-1904)之子,1893年发现心脏的希氏束/房室束,Werner-His病(战壕热)也因他而得名。
Ewald R.Weibel (1929- ),瑞士医学家、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64年与其同事、诺贝尔奖获得者G.M.Palade[1,4]共同发现血管内皮细胞中的Weibel-Palade(怀布尔-帕拉德)小体。
Erik von Willebrand (1870–1949),芬兰医生,1924年首次描述了家族性遗传血液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vWD),并与血友病(hemophilia)、出血素质(bleeding diathesis)相区别。1950年后人们才知道该病由血浆因子vWF(von Willebrand factor,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缺乏引起。
3 被皮系统
Paul Langerhans(1847-1888),德国病理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学家。1868年用氯化金染人皮肤组织时发现朗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1869年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发现胰岛(islets of Langerhans,见消化系统),1874年不幸感染结核,1888年因尿毒症早逝。
Michael Stanley Clive Birbeck (1925-2005),英国科学家、电子显微镜学家,朗格汉斯细胞中伯贝克颗粒(Birbeck granule)的发现者[5]。
Friedrich Sigmund Merkel (1845-1919),19 世纪后期著名的德国解剖学家、组织病理学家。1875年发现梅克尔细胞(Merkel-cell或Merkel-Ranvier cell[1]),曾将二甲苯(xylene)创造性地引入组织学技术。另外解剖学上的股骨距(femoral calcar)也因他命名为梅克尔距(Merkel’s spur)。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杰出的比较解剖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因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几乎自学成才,创造“不可知论(agnostic)”一词。他关于脊椎动物进化关系的研究,特别是“鸟类从小食肉类恐龙进化而来”的理论广为人知。其精深的解剖学研究几为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科学教育活动所掩盖,对英国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毛内根鞘的赫胥黎层因他命名。其子孙人才辈出,这就是著名的Huxley家族(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xley_family),但有家族性精神疾病。
4 呼吸系统
Max Clara(1899-1966),奥地利解剖学家,发现人类肺中的克拉拉细胞(Clara cell),因其与纳粹党关系密切,2012年5月呼吸杂志编辑(Respiratory Journal Editors,由绝大多数主要的呼吸相关杂志的编辑组成)一致同意从2013年1月1日起将克拉拉细胞改名为克拉布细胞(Club cell)[6]。
Richard Axel (1946- ),美国分子生物学家,因嗅觉系统的出色工作,与其前博士后Linda Brown Buck共享2004年度诺贝尔生理医学奖。20世纪70年代曾与同事共同发明分子生物学的“共转化(cotransformation)”技术,曾指导过多位神经生物学的顶级科学家,其中7位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7]。其第二任妻子是嗅觉研究先驱Cornelia Bargmann (1961-)。
Linda Brown Buck (1947- ),女,美国生物学家,曾是Richard Axel实验室的博士后,因其嗅觉受体的研究工作,2004年与Richard Axel共享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5 消化系统
Leopold Auerbach (1828-1897),德国医生、解剖学家、神经病理学家,是第一批用组织学染色技术诊断神经系统疾病的医生,发现了消化管肌层中的奥尔巴赫神经丛并因他命名。以半侧面部肥大为特征的Friedreich–Auerbach病也因他和德国病理学家、神经学家Nikolaus Friedreich (1825-1882)而得名。
Johann Conrad Brunner (1653-1727),瑞士解剖学家,因对胰脏和十二指肠的研究而闻名。1687年首次描述了十二指肠腺,后者因此被命名为布伦内腺。
Joseph Paneth (1857-1890),澳大利亚生理学家,因发现肠黏膜免疫有关的帕内特细胞/潘氏细胞而闻名。其子Friedrich Paneth (1887-1958)为当时知名的化学家。
Karl Wilhelm von Kupffer (1829-1902), 德 国解剖学家,因其在神经解剖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工作而知名。1876年发现肝脏的库普弗细胞,但误认为是一种内皮细胞。后经Tadeusz Browicz鉴定为巨噬细胞。
Tadeusz Browicz (1847-1928),波兰病理学家,1874年首次描述了伤寒(typhoid fever)杆菌,1898年将库普弗细胞正确鉴定为巨噬细胞,还曾对黄疸、肝癌、心肌紊乱等做过重要研究。
Joseph Disse (1852-1912),德国解剖学家、组织学家,曾是H.von Waldeyer-Hartz[1]的助手,窦周隙/迪塞间隙因他而得名。
Karl Ewald Konstantin Hering (1834-1918),德国生理学家,对色觉、双眼知觉、眼的运动等多有研究,肝的闰管/Hering管因他而名。
Francis Glisson (1599? -1677),英国医学家、解剖学家,发现胆管壶腹扩约肌并对肝脏解剖研究有重要贡献。
Ruggero Oddi (1864-1913),意大利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在其学生阶段就描述了胆管上的壶腹扩约肌/奥迪扩约肌并鉴定了其生理功能,该处的炎症称为胆道口括约肌炎(Odditis)。
Frederick Grant Banting (1891-1941),加拿大医学家、医生、画家,因发现胰岛素与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于1923年同获诺贝尔奖,1934年受封爵士,2004被评为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之一。
John James Rickard Macleod (1876-1935),苏格兰生物化学家、生理学家,因胰岛素的发现和分离与Frederick Grant Banting同获诺贝尔奖。当时对其贡献颇有争议,几十年后人们才认识到其获奖乃是实至名归。
6 免疫系统
Arthur Hill Hassall (1817-1894),英国医生、化学家,1849年发现胸腺小体(Hassall小体),还发现了眼角膜的后界膜异常生长形成的Hassall-Henle小体。
Gerald Maurice Edelman (1929- ),美国生物学家,因抗体结构的发现而与Rodney Robert Porter共享1972年度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Rodney Robert Porter (1917-1985),英国生物化学家,是Frederick Sanger (1918-2013,1958因阐明胰岛素的结构、1980年因核酸测序两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博士生,因抗体结构的发现与Gerald Maurice Edelman同获1972年度诺贝尔奖。逝于交通事故。
Niels Kaj Jerne (1911-1994),丹麦免疫学家,长于理论而非实验,因免疫系统发育和控制特异性理论及发现单克隆抗体产生原理,与德国生物学家Georges J.F.Köhler (1946-1995)和阿根廷生物化学家César Milstein(1927-2002,曾与 Frederick Sanger一起工作)同获1984年度诺贝尔奖。
利根川进 (Susumu Tonegawa,1939- ),日本分子生物学家,因发现抗体多样性产生的遗传学原理而获1987年度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Karl Albert Ludwig Aschoff(1866-1942),德国医学家、病理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病理学家之一,被誉为德国继Rudolf Virchow (1821-1902)之后最重要的病理学家,在心脏病理学、病理生理学方面贡献颇多,1922年提出“网状内皮系统”一词。
Ralph van Furth (1929- ),荷兰细胞生物学家,因吞噬系统相关研究而闻名。1972年与其同事Z.A.Cohn提出新概念-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Zanvil Alexander Cohn (1926-1993),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免疫学家、洛克菲勒大学教授,在免疫学方面贡献卓著,其学生及合作者Ralph Marvin Steinman因树突状细胞研究于2011年获诺贝尔奖。
Ralph Marvin Steinman (1943-2011),加拿大细胞生物学家、免疫学家、201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之一。1973年在Zanvil Alexander Cohn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创造“树突状细胞”一词并致力于相关研究,2011在获诺贝尔奖三天前去逝。
Hieronymus Fabricius (1537-1619),意大利人,解剖学和外科学的开拓者之一,胚胎学的奠基人之一。1594年他革新了解剖学教学法,创建了第一个公共解剖室,W.Harvey[1]、A.van den Spiegel (1578-1625)等名人都是他的学生。他研究了胎儿的形成和食管、胃、小肠、眼、耳、咽、脑等的结构,甚至首次描述了静脉瓣,发明了气管切开术。1621年在他逝世后出版的手稿中首次描述了禽类中枢免疫器官腔上囊/法氏囊(bursa of Fabricius)。
7 内分泌系统
Emil Theodor Kocher (1841-1917),瑞士医学家,因对甲状腺的出色研究而获1909年度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瑞士第1人),对临床外科贡献巨大,使甲状腺切除术的死亡率降至1%以下。
Edward Calvin Kendall (1886-1972),美国化学家,1950年因发现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结构和生物效应与 Tadeusz Reichstein和 Philip Showalter Hench同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Tadeusz Reichstein (1897-1996),瑞士籍波兰裔化学家,曾合成维生素C,1950年因肾上腺皮质激素可的松的分离研究与Edward Calvin Kendall和Philip Showalter Hench同获诺贝尔奖,曾是最长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Philip Showalter Hench (1896-1965),美国医生,因可的松的发现和应用而获诺贝尔奖。
Martin Heinrich Rathke (1793-1860),德国胚胎学家、解剖学家,与von Baer[1]和C.H.Pander[1]并称为现代胚胎学的奠基人,曾首次描述胚胎发育中的鳃、拉特克囊(形成垂体前叶)等。
Percy Theodore Herring (1872-196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因首次描述神经垂体中的赫林体(Herring body)而知名。
Bernardo Alberto Houssay (1887-1971),阿根廷生理学家,1947年因发现垂体前叶激素在糖代谢中的作用而获一半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阿根廷人和拉丁美洲人。
8 感觉器官
William Bowman (1816-1892),英国外科医生、组织学家、解剖学家、一等男爵、皇家学会会员,因用显微镜术研究人体器官而闻名,发现并命名了鲍曼囊/肾小囊、鲍曼腺/嗅腺以及角膜的鲍曼膜/层等组织学结构。
Friedrich Schlemm (1795-1858),德国解剖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因利用尸体进行病理学研究而闻名。1816年曾与学生深夜挖出女尸研究妇女佝偻病而饱受诟病,并因此被判刑4周。他是角膜神经的发现者,还发现并描述了Schlemm管(现称巩膜静脉窦)。
Heinrich Müller (1820-1864),德国解剖学家,因其比较解剖学研究及眼研究等工作而知名。视网膜的米勒纤维、米勒细胞因他而得名。
Friedrich Matthias Claudius (1822-1869),德国解剖学家,1865年首次描述了内耳中的克劳迪乌斯细胞,其名还与骨盆的卵巢窝(ovarian fossa/Claudius fossa)有关。
Alfonso Giacomo Gaspare Corti (1822-1876),意大利解剖学家,对听觉系统多有研究,内耳的螺旋器/科尔蒂器因他而名。
Allvar Gullstrand (1862-1930),瑞典的眼科医生和验光师,因其眼的屈光学研究于1911年获诺贝尔奖生理医学奖。
9 泌尿系统
Friedrich Gustav Jakob Henle (1809-1885),德国医学家、病理学家、解剖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现代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发现并命名了多个组织学结构,如亨勒袢/髓袢、眼结膜的亨勒窝、毛囊根鞘的亨勒层、神经纤维外层的亨勒鞘等。
Morris J.Karnovsky (1926-2018),南非裔美国哈佛医学院教授、细胞生物学家、病理学家、生理学家。其最广为人知的贡献之一是通过引入二氨基联苯胺(DAB),将免疫组化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法应用到电镜样品中。另于1974年还与R.Rodewald共同提出了血-尿屏障足细胞裂孔膜的“拉链状”模型。
10 生殖系统
Enrico Sertoli (1842-1910),意大利生理学家、组织学家,1865年当他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时,发现睾丸支持细胞并进行了正确描述,Sertoli细胞(塞托利细胞)因此得名[8]。
Franz Leydig (1821-1908),德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家、伦敦皇家学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会员,1850年发现并描述了睾丸间质细胞(Leydig cell)。
Karl Sune Detlof Bergström (1916-2004),瑞典生物化学家,因发现前列腺素及其相关活性物质于1982年 与 Bengt Ingemar Samuelsson、John Robert Vane同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Bengt Ingemar Samuelsson (1934- ),瑞典生物化学家,因前列腺素及其相关活性物质的出色工作,1982年与 Karl Sune Detlof Bergström、John Robert Vane同享诺贝尔奖。
John Robert Vane (1927-2004),英国药理学家,对阿司匹林止痛、抗炎作用的阐明有重要作用,其工作对心血管疾病新疗法及前列腺素相关研究均有重要意义,1982年与上述两人同获诺贝尔奖。
11 早期胚胎发育
Min Chueh Chang (张明觉, 1908-1991),祖籍山西,美籍华人生殖生物学家,在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特别是体外受精方面贡献卓著,发现了精子获能、精子冷应激等现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复方口服避孕药。
Robert Geoffrey Edwards (1925-2013),英国生理学家、生殖医学体外受精(IVF)研究的先行者。与妇科医生Patrick Steptoe合作,利用IVF于1978年7月25日成功诞生了世界首例试管婴儿Louise Brown。他们为不育患者建立了第一个IVF标准方案并培训了大量相关科技人员。2010年Edwards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Mario Ramberg Capecchi (1937- ),美籍意裔分子遗传学家、美国犹他州人类遗传学和生物学教授,是DNA结构的发现者James Dewey Watson(1928-)的学生,因利用小鼠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s, ESCs)研究基因敲除鼠及Hox基因家族而闻名,2007年与Martin John Evans和Oliver Smithies同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Martin John Evans (1941- ),英国发育生物学家,与Matthew Kaufman(1942-2013,英国胚胎学家)于1981年共同建立第一个小鼠ESCs细胞系,并采用ESCs进行基因敲除鼠和基因打靶的研究,2007年与Mario Ramberg Capecchi和Olivr Smithies同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Oliver Smithies (1925- ),美籍英裔遗传学家,1955年发明凝胶电泳,后研究基因打靶、高血压等。2007年因他在基因打靶技术方面的贡献,与Mario Ramberg Capecchi和Martin John Evans同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August Rauber (1841-1917),德国解剖学家、胚胎学家,曾在Wilhelm His Sr.(见循环系统)手下工作,因将胚胎学、组织学和系统进化分析法相结合而知名,命名了胚盘的Rauber’s layer(滋养层膜)。
Christian Andreas Victor Hensen (1835-1924),德国动物学家,也涉猎于胚胎学和解剖学。他创造了“浮游生物”一词,为生物海洋学奠定了基础。耳中的汉森管(Hensen’s duct)、鸟类发育中出现的汉森结(Hensen’s node)都是他发现的。
12 结语
以上我们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组织学与胚胎学各章节中涉及的主要科技人物和名词术语,以期为本课程的相关教学人员提供参考。
[1]张学明,岳占碰,郭斌,等.组织学与胚胎学中的科技人物和名词(一).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2018,27(1):101-105.
[2]李子义,栾维民,岳占碰,等.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276-279.
[3]Drouin E, Piloquet P, Péréon Y.The first illustration of neurons by Camillo Golgi.Lancet Neurol, 2015, 14(6)∶567.
[4]Zorca SM, Zorca CE.The legacy of a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cell biology∶ George Emil Palade (1912-2008).Yale J Biol Med, 2011, 84(2)∶113-116.
[5]Al Aboud K, Al Aboud A.Eponyms in the dermatology literature linked to “Bodies’’, seen in skin biopsies.Our Dermatol Online, 2013, 4(4)∶ 564-568.
[6]Winkelmann A, Noack T.The Clara cell∶ a “Third Reich eponym”? Eur Respir J, 2010, 36(4)∶722-727.
[7]Axel R, Carniol K.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Axel.Cold Spring Harb Symp Quant Biol, 2014, 79∶ 258-259.
[8]França LR, Hess RA, Dufour JM, et al.The Sertoli cell∶one hundred fifty years of beauty and plasticity.Andrology,2016, 4(2)∶189-212.